《竹影》的三重解读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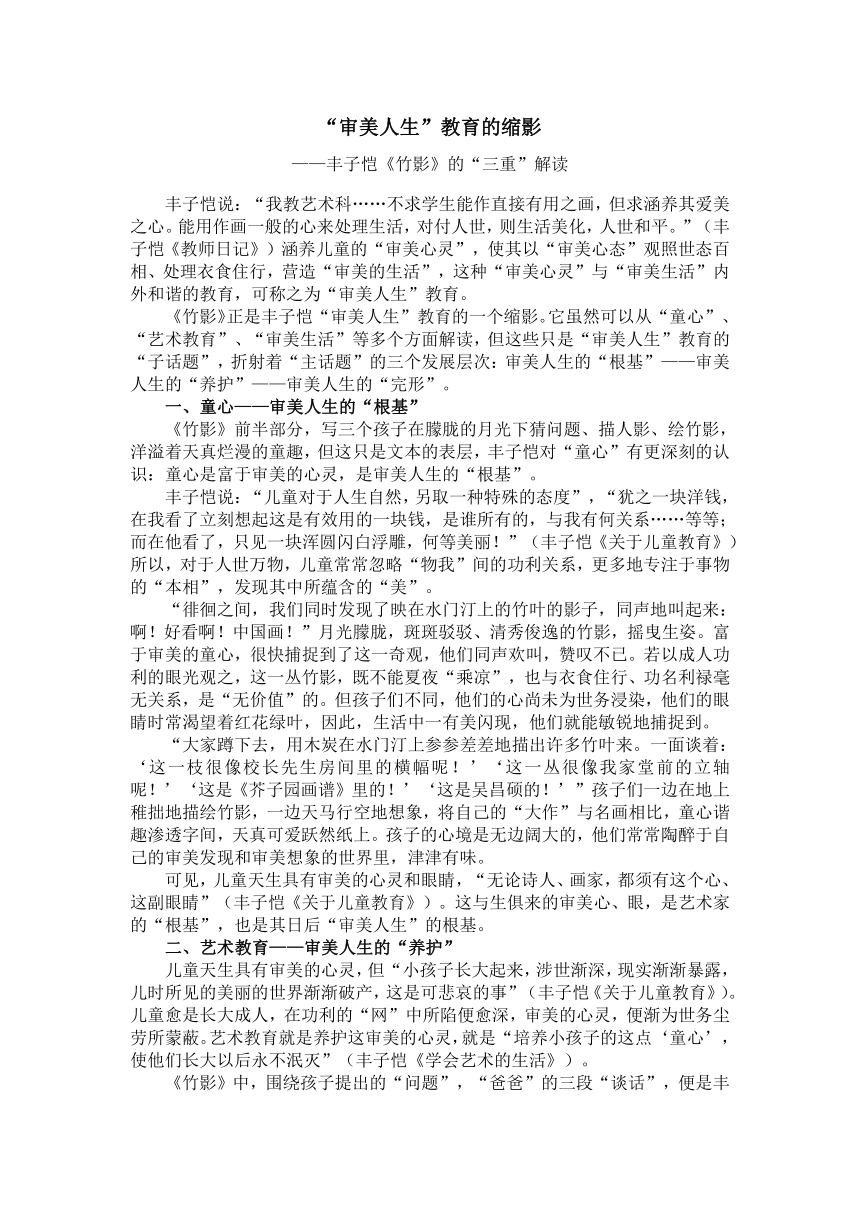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审美人生”教育的缩影
——丰子恺《竹影》的“三重”解读
丰子恺说:“我教艺术科……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丰子恺《教师日记》)涵养儿童的“审美心灵”,使其以“审美心态”观照世态百相、处理衣食住行,营造“审美的生活”,这种“审美心灵”与“审美生活”内外和谐的教育,可称之为“审美人生”教育。
《竹影》正是丰子恺“审美人生”教育的一个缩影。它虽然可以从“童心”、“艺术教育”、“审美生活”等多个方面解读,但这些只是“审美人生”教育的“子话题”,折射着“主话题”的三个发展层次:审美人生的“根基”——审美人生的“养护”——审美人生的“完形”。
一、童心——审美人生的“根基”
《竹影》前半部分,写三个孩子在朦胧的月光下猜问题、描人影、绘竹影,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童趣,但这只是文本的表层,丰子恺对“童心”有更深刻的认识:童心是富于审美的心灵,是审美人生的“根基”。
丰子恺说:“儿童对于人生自然,另取一种特殊的态度”,“犹之一块洋钱,在我看了立刻想起这是有效用的一块钱,是谁所有的,与我有何关系……等等;而在他看了,只见一块浑圆闪白浮雕,何等美丽!”(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所以,对于人世万物,儿童常常忽略“物我”间的功利关系,更多地专注于事物的“本相”,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美”。
“徘徊之间,我们同时发现了映在水门汀上的竹叶的影子,同声地叫起来:啊!好看啊!中国画!”月光朦胧,斑斑驳驳、清秀俊逸的竹影,摇曳生姿。富于审美的童心,很快捕捉到了这一奇观,他们同声欢叫,赞叹不已。若以成人功利的眼光观之,这一丛竹影,既不能夏夜“乘凉”,也与衣食住行、功名利禄毫无关系,是“无价值”的。但孩子们不同,他们的心尚未为世务浸染,他们的眼睛时常渴望着红花绿叶,因此,生活中一有美闪现,他们就能敏锐地捕捉到。
“大家蹲下去,用木炭在水门汀上参参差差地描出许多竹叶来。一面谈着:‘这一枝很像校长先生房间里的横幅呢!’‘这一丛很像我家堂前的立轴呢!’‘这是《芥子园画谱》里的!’‘这是吴昌硕的!’”孩子们一边在地上稚拙地描绘竹影,一边天马行空地想象,将自己的“大作”与名画相比,童心谐趣渗透字间,天真可爱跃然纸上。孩子的心境是无边阔大的,他们常常陶醉于自己的审美发现和审美想象的世界里,津津有味。
可见,儿童天生具有审美的心灵和眼睛,“无论诗人、画家,都须有这个心、这副眼睛”(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这与生俱来的审美心、眼,是艺术家的“根基”,也是其日后“审美人生”的根基。
二、艺术教育——审美人生的“养护”
儿童天生具有审美的心灵,但“小孩子长大起来,涉世渐深,现实渐渐暴露,儿时所见的美丽的世界渐渐破产,这是可悲哀的事”(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儿童愈是长大成人,在功利的“网”中所陷便愈深,审美的心灵,便渐为世务尘劳所蒙蔽。艺术教育就是养护这审美的心灵,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使他们长大以后永不泯灭”(丰子恺《学会艺术的生活》)。
《竹影》中,围绕孩子提出的“问题”,“爸爸”的三段“谈话”,便是丰子恺这一“艺术教育”思想的直观呈现:
第一个问题,“管夫人是谁?”
管夫人名叫“管道升”,她的竹画“笔意清绝”,后人评价其《竹石图》说:“……姿态百出,与怪石奔峭相间,气韵生动,真奇作也。”这些画竹史实,大画家丰子恺不会不知道。但课文中“爸爸”的回答却很简短:“她是一位善于画竹的女画家。丈夫名叫赵子昂……”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正折射出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艺术教育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涵养心灵,“是美的教育,是情的教育”(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因此,“爸爸”感兴趣的是后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竹有什么难画呢?”
对此,“爸爸”从绘画“构图”的角度,对孩子进行了“美的教育”。“画竹不是照真竹一样描,须经过选择和布置。画家选择竹的最好看的姿态,巧妙地布置在纸上……”这“最好看的姿态”,便是竹所呈现的“美”。画家要发现其“美”,并通过“选择和布置”表现其“美”。这样,才能提高感受美和表现美的能力,涵养“审美的心灵”。“依样画葫芦”,仅仅画得“像”,是较低层次的要求,虽容易画,但“终究缺乏画意,不过好玩罢了”。
第三个问题,“竹为什么不用绿颜料来画,而常用墨笔来画呢?”
“爸爸”是围绕中国画的审美特征来回答的。中国画更注重“画意”和“美感”,“凡画一物,只要能表现出像我们闭目回想时所见的一种神气,就是佳作了”。较之“照相式”的西洋画,这是更高境界的绘画。“照相”式的西洋画,“近乎‘冒充实物’,这种画不像一张‘画’,不像一个‘艺术品’。故讲到‘画意’、‘艺术味’,中国画比西洋画丰富得多”(丰子恺《绘事后素》)。因此,“符号”式的中国画,没有必要五颜六色全用,“只要用墨笔就够了”。
??? “墨”包含绿色但不是绿色,“朱”与绿色视觉差异悬殊。从画家的角度看,用这两种颜料,在画竹时可以更好地超越“绿”“形似”上的干扰,更多地将心神集中于竹的“美姿”和“神气”,更有利于“美感”的表达。从欣赏者的角度看,用“墨”和“朱”画竹,就会在“形似”上给欣赏带来一定的“阻拒”性,使其不得不集中心神去感受画的“美姿”与“神气”。所以,“倘然用了绿颜料,就因为太像实物,反而失却神气”。
??? 这种引导,更有利于孩子们的审美目光超越画的“形”,专注于画的“美感”,从而提高审美素养。
??? 三个问题,三种不同的角度,但都超越了艺术教育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养护审美的心灵,追求审美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是培养“胸怀芬芳”的人。
??? 三、审美生活——审美人生的“完形”
??? 艺术教育养护审美的心灵,使我们的世界处处美丽,生活处处滋润,“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的情味”(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这种审美生活便是审美心灵的外化,是审美人生的最终“完形”。
??? 课文中的“爸爸”,便是“审美生活”的典范。
??? 看到三个孩子画“竹影”,“爸爸”并没有因弄脏自家水门汀生气,而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融入其中:“忽然一个大人的声音在我们头上慢慢响出来:‘这是管夫人的!’”“爸爸”来得很久了,但一直沉醉于孩子们的绘画游戏中,随他们遨游于审美想象的“童话王国”,终于情不自禁,自己也参与了进去。“谁想出来的?这画法真好玩呢!我也来描几瓣看。”这不仅是对华明的安慰,还表明“爸爸”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对儿童“审美生活”一往情深。丰子恺曾借八指头陀的一首诗表达他的这种深情:“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
??? “爸爸”的生活原型——丰子恺”本人(参阅《少年美术音乐故事》可知),更是拥有“审美的生活”。
??? 在《闲居》中,丰子恺以绘画的“构图法”来布置书房,将生活“绘画审美化”:“主人的座位为全局的主眼……须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物品“各以主眼为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点集中于主人的座位,犹之画中的附属物、背景,均须有护卫主物,显衬主物的作用。这样妥帖之后,人在里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适。”他还说:“闲居的时候,我又欢喜把一天的生活的情调来比方音乐。”并将春天比作门德尔松,夏天比作贝多芬,秋日比作肖邦和舒曼,冬天比作舒伯特,这则是生活的“音乐审美化”了。
??? 司马长风评价丰子恺的散文说:“清如无云的蓝天,朴如无涯的大地,如春华秋实,夏绿冬雪。”我觉得这更是丰子恺“审美生活”的写照,因为他“将生活与散文浑融一片,散文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散文”(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
——丰子恺《竹影》的“三重”解读
丰子恺说:“我教艺术科……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丰子恺《教师日记》)涵养儿童的“审美心灵”,使其以“审美心态”观照世态百相、处理衣食住行,营造“审美的生活”,这种“审美心灵”与“审美生活”内外和谐的教育,可称之为“审美人生”教育。
《竹影》正是丰子恺“审美人生”教育的一个缩影。它虽然可以从“童心”、“艺术教育”、“审美生活”等多个方面解读,但这些只是“审美人生”教育的“子话题”,折射着“主话题”的三个发展层次:审美人生的“根基”——审美人生的“养护”——审美人生的“完形”。
一、童心——审美人生的“根基”
《竹影》前半部分,写三个孩子在朦胧的月光下猜问题、描人影、绘竹影,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童趣,但这只是文本的表层,丰子恺对“童心”有更深刻的认识:童心是富于审美的心灵,是审美人生的“根基”。
丰子恺说:“儿童对于人生自然,另取一种特殊的态度”,“犹之一块洋钱,在我看了立刻想起这是有效用的一块钱,是谁所有的,与我有何关系……等等;而在他看了,只见一块浑圆闪白浮雕,何等美丽!”(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所以,对于人世万物,儿童常常忽略“物我”间的功利关系,更多地专注于事物的“本相”,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美”。
“徘徊之间,我们同时发现了映在水门汀上的竹叶的影子,同声地叫起来:啊!好看啊!中国画!”月光朦胧,斑斑驳驳、清秀俊逸的竹影,摇曳生姿。富于审美的童心,很快捕捉到了这一奇观,他们同声欢叫,赞叹不已。若以成人功利的眼光观之,这一丛竹影,既不能夏夜“乘凉”,也与衣食住行、功名利禄毫无关系,是“无价值”的。但孩子们不同,他们的心尚未为世务浸染,他们的眼睛时常渴望着红花绿叶,因此,生活中一有美闪现,他们就能敏锐地捕捉到。
“大家蹲下去,用木炭在水门汀上参参差差地描出许多竹叶来。一面谈着:‘这一枝很像校长先生房间里的横幅呢!’‘这一丛很像我家堂前的立轴呢!’‘这是《芥子园画谱》里的!’‘这是吴昌硕的!’”孩子们一边在地上稚拙地描绘竹影,一边天马行空地想象,将自己的“大作”与名画相比,童心谐趣渗透字间,天真可爱跃然纸上。孩子的心境是无边阔大的,他们常常陶醉于自己的审美发现和审美想象的世界里,津津有味。
可见,儿童天生具有审美的心灵和眼睛,“无论诗人、画家,都须有这个心、这副眼睛”(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这与生俱来的审美心、眼,是艺术家的“根基”,也是其日后“审美人生”的根基。
二、艺术教育——审美人生的“养护”
儿童天生具有审美的心灵,但“小孩子长大起来,涉世渐深,现实渐渐暴露,儿时所见的美丽的世界渐渐破产,这是可悲哀的事”(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儿童愈是长大成人,在功利的“网”中所陷便愈深,审美的心灵,便渐为世务尘劳所蒙蔽。艺术教育就是养护这审美的心灵,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使他们长大以后永不泯灭”(丰子恺《学会艺术的生活》)。
《竹影》中,围绕孩子提出的“问题”,“爸爸”的三段“谈话”,便是丰子恺这一“艺术教育”思想的直观呈现:
第一个问题,“管夫人是谁?”
管夫人名叫“管道升”,她的竹画“笔意清绝”,后人评价其《竹石图》说:“……姿态百出,与怪石奔峭相间,气韵生动,真奇作也。”这些画竹史实,大画家丰子恺不会不知道。但课文中“爸爸”的回答却很简短:“她是一位善于画竹的女画家。丈夫名叫赵子昂……”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正折射出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艺术教育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涵养心灵,“是美的教育,是情的教育”(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因此,“爸爸”感兴趣的是后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竹有什么难画呢?”
对此,“爸爸”从绘画“构图”的角度,对孩子进行了“美的教育”。“画竹不是照真竹一样描,须经过选择和布置。画家选择竹的最好看的姿态,巧妙地布置在纸上……”这“最好看的姿态”,便是竹所呈现的“美”。画家要发现其“美”,并通过“选择和布置”表现其“美”。这样,才能提高感受美和表现美的能力,涵养“审美的心灵”。“依样画葫芦”,仅仅画得“像”,是较低层次的要求,虽容易画,但“终究缺乏画意,不过好玩罢了”。
第三个问题,“竹为什么不用绿颜料来画,而常用墨笔来画呢?”
“爸爸”是围绕中国画的审美特征来回答的。中国画更注重“画意”和“美感”,“凡画一物,只要能表现出像我们闭目回想时所见的一种神气,就是佳作了”。较之“照相式”的西洋画,这是更高境界的绘画。“照相”式的西洋画,“近乎‘冒充实物’,这种画不像一张‘画’,不像一个‘艺术品’。故讲到‘画意’、‘艺术味’,中国画比西洋画丰富得多”(丰子恺《绘事后素》)。因此,“符号”式的中国画,没有必要五颜六色全用,“只要用墨笔就够了”。
??? “墨”包含绿色但不是绿色,“朱”与绿色视觉差异悬殊。从画家的角度看,用这两种颜料,在画竹时可以更好地超越“绿”“形似”上的干扰,更多地将心神集中于竹的“美姿”和“神气”,更有利于“美感”的表达。从欣赏者的角度看,用“墨”和“朱”画竹,就会在“形似”上给欣赏带来一定的“阻拒”性,使其不得不集中心神去感受画的“美姿”与“神气”。所以,“倘然用了绿颜料,就因为太像实物,反而失却神气”。
??? 这种引导,更有利于孩子们的审美目光超越画的“形”,专注于画的“美感”,从而提高审美素养。
??? 三个问题,三种不同的角度,但都超越了艺术教育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养护审美的心灵,追求审美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是培养“胸怀芬芳”的人。
??? 三、审美生活——审美人生的“完形”
??? 艺术教育养护审美的心灵,使我们的世界处处美丽,生活处处滋润,“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的情味”(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这种审美生活便是审美心灵的外化,是审美人生的最终“完形”。
??? 课文中的“爸爸”,便是“审美生活”的典范。
??? 看到三个孩子画“竹影”,“爸爸”并没有因弄脏自家水门汀生气,而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融入其中:“忽然一个大人的声音在我们头上慢慢响出来:‘这是管夫人的!’”“爸爸”来得很久了,但一直沉醉于孩子们的绘画游戏中,随他们遨游于审美想象的“童话王国”,终于情不自禁,自己也参与了进去。“谁想出来的?这画法真好玩呢!我也来描几瓣看。”这不仅是对华明的安慰,还表明“爸爸”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对儿童“审美生活”一往情深。丰子恺曾借八指头陀的一首诗表达他的这种深情:“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
??? “爸爸”的生活原型——丰子恺”本人(参阅《少年美术音乐故事》可知),更是拥有“审美的生活”。
??? 在《闲居》中,丰子恺以绘画的“构图法”来布置书房,将生活“绘画审美化”:“主人的座位为全局的主眼……须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物品“各以主眼为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点集中于主人的座位,犹之画中的附属物、背景,均须有护卫主物,显衬主物的作用。这样妥帖之后,人在里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适。”他还说:“闲居的时候,我又欢喜把一天的生活的情调来比方音乐。”并将春天比作门德尔松,夏天比作贝多芬,秋日比作肖邦和舒曼,冬天比作舒伯特,这则是生活的“音乐审美化”了。
??? 司马长风评价丰子恺的散文说:“清如无云的蓝天,朴如无涯的大地,如春华秋实,夏绿冬雪。”我觉得这更是丰子恺“审美生活”的写照,因为他“将生活与散文浑融一片,散文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散文”(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2 爸爸的花儿落了
- 3*丑小鸭
- 4*诗两首
- 5 伤仲永
- 第二单元
- 6*黄河颂
- 7 最后一课
- 8*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 9*土地的誓言
- 10 木兰诗
- 第三单元
- 11 邓稼先
- 12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 13*音乐巨人贝多芬
- 14*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 15*孙权劝学《资治通鉴》
- 第四单元
- 16 社戏
- 17 安塞腰鼓
- 18*竹影
- 19*观舞记
- 20 口技
- 第五单元
- 21 伟大的悲剧
- 22 在沙漠中心
- 23*登上地球之巅
- 24*真正的英雄
- 25 短文两篇(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
- 第六单元
- 26 猫
- 27 斑羚飞渡
- 28*华南虎
- 29*马
- 30*狼
- 课外古诗词背诵
- 山中杂诗
- 竹里馆
- 峨眉山月歌
- 春夜洛城闻笛
- 逢入京使
- 滁州西涧
- 江南逢李龟年
- 送灵澈上人
- 约客
- 论诗
- 名著导读
- 童年
- 昆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