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促织教学设计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
文档属性
| 名称 | 14.1促织教学设计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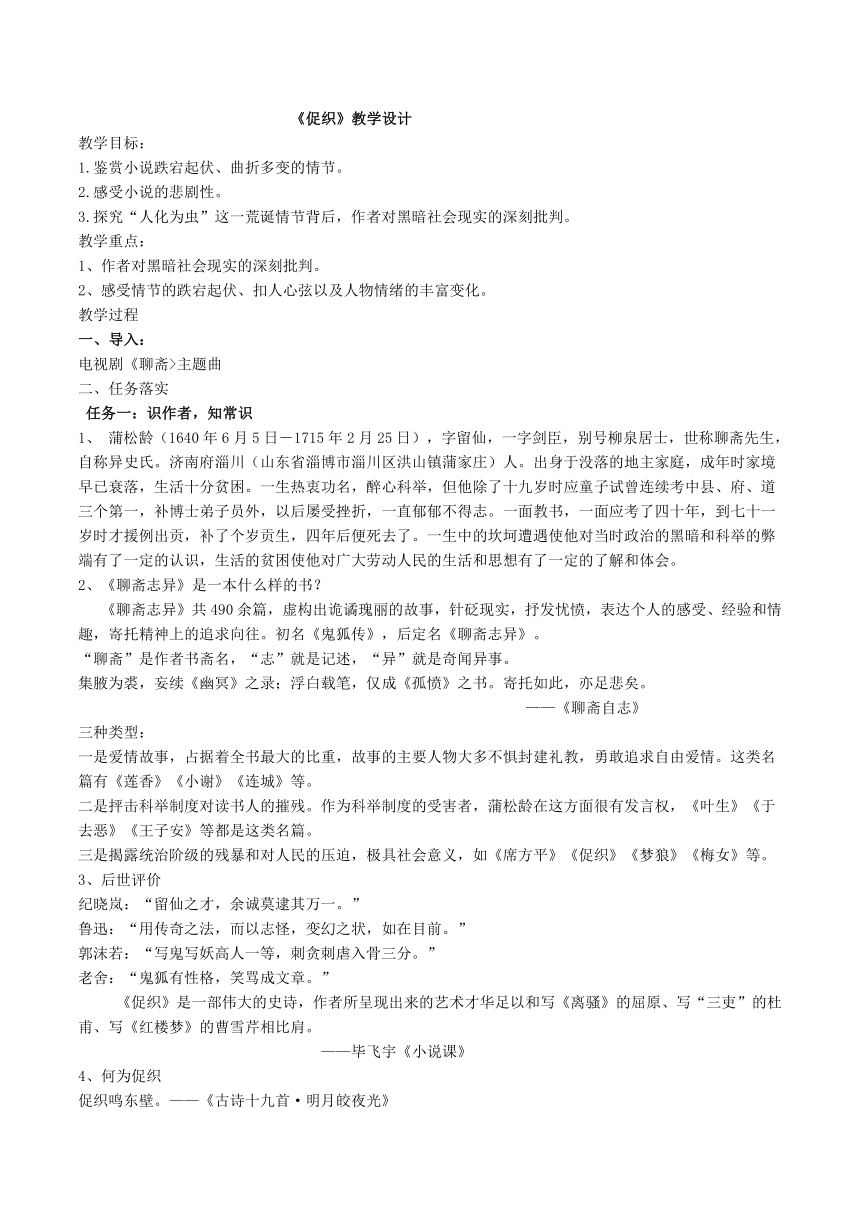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6.2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2-05-26 21:37:5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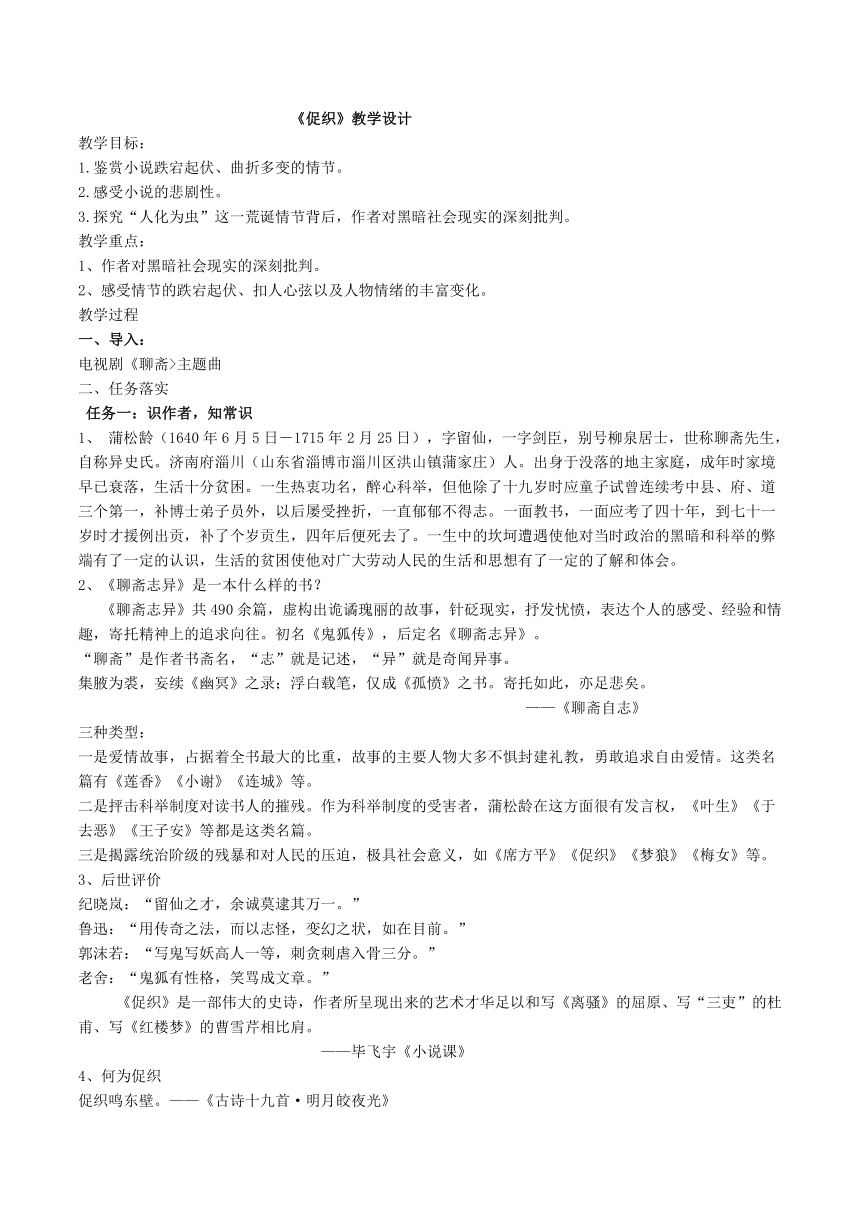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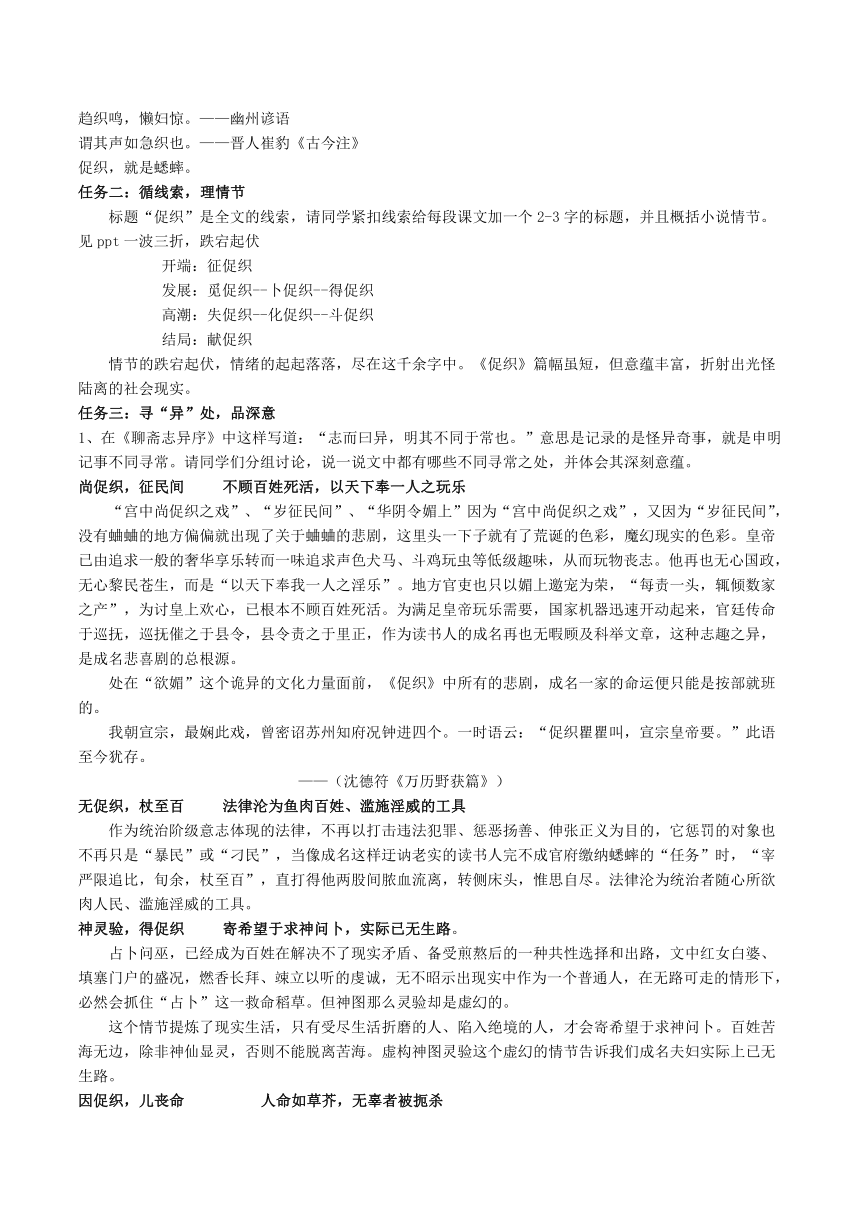
文档简介
《促织》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鉴赏小说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情节。
2.感受小说的悲剧性。
3.探究“人化为虫”这一荒诞情节背后,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教学重点:
1、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2、感受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以及人物情绪的丰富变化。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电视剧《聊斋>主题曲
二、任务落实
任务一:识作者,知常识
1、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成年时家境早已衰落,生活十分贫困。一生热衷功名,醉心科举,但他除了十九岁时应童子试曾连续考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外,以后屡受挫折,一直郁郁不得志。一面教书,一面应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出贡,补了个岁贡生,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他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生活的贫困使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体会。
2、《聊斋志异》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聊斋志异》共490余篇,虚构出诡谲瑰丽的故事,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初名《鬼狐传》,后定名《聊斋志异》。
“聊斋”是作者书斋名,“志”就是记述,“异”就是奇闻异事。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聊斋自志》
三种类型:
一是爱情故事,占据着全书最大的比重,故事的主要人物大多不惧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由爱情。这类名篇有《莲香》《小谢》《连城》等。
二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作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蒲松龄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叶生》《于去恶》《王子安》等都是这类名篇。
三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极具社会意义,如《席方平》《促织》《梦狼》《梅女》等。
3、后世评价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鲁迅:“用传奇之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
郭沫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
——毕飞宇《小说课》
4、何为促织
促织鸣东壁。——《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趋织鸣,懒妇惊。——幽州谚语
谓其声如急织也。——晋人崔豹《古今注》
促织,就是蟋蟀。
任务二:循线索,理情节
标题“促织”是全文的线索,请同学紧扣线索给每段课文加一个2-3字的标题,并且概括小说情节。
见ppt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开端:征促织
发展:觅促织--卜促织--得促织
高潮:失促织--化促织--斗促织
结局:献促织
情节的跌宕起伏,情绪的起起落落,尽在这千余字中。《促织》篇幅虽短,但意蕴丰富,折射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
任务三:寻“异”处,品深意
1、在《聊斋志异序》中这样写道:“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意思是记录的是怪异奇事,就是申明记事不同寻常。请同学们分组讨论,说一说文中都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并体会其深刻意蕴。
尚促织,征民间 不顾百姓死活,以天下奉一人之玩乐
“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华阴令媚上”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皇帝已由追求一般的奢华享乐转而一味追求声色犬马、斗鸡玩虫等低级趣味,从而玩物丧志。他再也无心国政,无心黎民苍生,而是“以天下奉我一人之淫乐”。地方官吏也只以媚上邀宠为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为讨皇上欢心,已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为满足皇帝玩乐需要,国家机器迅速开动起来,官廷传命于巡抚,巡抚催之于县令,县令责之于里正,作为读书人的成名再也无暇顾及科举文章,这种志趣之异,是成名悲喜剧的总根源。
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便只能是按部就班的。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四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
无促织,杖至百 法律沦为鱼肉百姓、滥施淫威的工具
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法律,不再以打击违法犯罪、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为目的,它惩罚的对象也不再只是“暴民”或“刁民”,当像成名这样迂讷老实的读书人完不成官府缴纳蟋蟀的“任务”时,“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直打得他两股间脓血流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法律沦为统治者随心所欲肉人民、滥施淫威的工具。
神灵验,得促织 寄希望于求神问卜,实际已无生路。
占卜问巫,已经成为百姓在解决不了现实矛盾、备受煎熬后的一种共性选择和出路,文中红女白婆、填塞门户的盛况,燃香长拜、竦立以听的虔诚,无不昭示出现实中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形下,必然会抓住“占卜”这一救命稻草。但神图那么灵验却是虚幻的。
这个情节提炼了现实生活,只有受尽生活折磨的人、陷入绝境的人,才会寄希望于求神问卜。百姓苦海无边,除非神仙显灵,否则不能脱离苦海。虚构神图灵验这个虚幻的情节告诉我们成名夫妇实际上已无生路。
因促织,儿丧命 人命如草芥,无辜者被扼杀
成名不在家,九岁的儿子因好奇,“窃发盆”,青麻头被儿子“扑死”。 儿子也因失手打死蟋蟀而投井自杀,九岁的成名之子有何罪 只是一个童心未泯,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无辜受害者被扼杀,被吞噬的过程。
不念儿,念促织 人被“异化” ,正常情感被扭曲
“僵卧长愁”“目不交睫” 成名一夜未眠,愁的不是儿子的安危,“不复以儿为念”从中可见,愁的是上哪儿捉蟋蟀,眼看期限在即,交不了差,唯有死路一条,真是一筹莫展,愁肠百结。对完不成官差的忧虑,对官府责罚的恐惧,是如何扭曲了人的正常情感,扭曲了作为人伦之道的父子之情。儿子的生命竟然不如一只小小的蟋蟀,作者写来真是满含悲愤。
失神识 ,化促织 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由人变为虫
这个虚幻情节,比成名夫妻的身陷绝境,更加震撼人心。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从这方面说,人的生存意义是超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的。可是在这个故事里,人不愿成为人,而甘愿变成一只虫子。在人与蟋蟀的关系中,人是弱者,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地掐住人的脖子,人与蟋蟀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人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宁愿自我否定,而魂化成一只蟋蟀。这种否定,是极其震撼人心的,它以寓言的形式影射了人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孩子爱他的爸爸,孩子想给爸爸解决问题。既然自己给爸爸惹了麻烦,那么,就让自己来解决吧。为了爸爸,孩子不惜让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这一段太感人的,父子情深。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这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毕飞宇
鸡虫斗,促织胜 战胜天敌增加传奇性,暗示非一般之虫
为什么不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了好几个促织,最后,天下第一,然后呢,成名完成了任务,成名的一家过上了富足幸福的日子?
从促织到鸡,推波助澜,小说的逻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
为什么是鸡?为什么不是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狼。
谁对昆虫的伤害最大?谁最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答案是唯一的,鸡。
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献促织,获封赏 违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事理,荒谬可笑
成名不能通过正常的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却因进贡一只上等蟋蟀而被县令特许人邑庠;先前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后却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县令以才能“卓异”闻名,只因他向抚军进献了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抚军不是因政绩优良而受皇帝褒扬,却因迎合皇帝特殊爱好而得到名马衣缎的奖赏。所有这些,都缺少最起码的因果逻辑,违背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事理和游戏法则。
根据文章内容完成表格,并探究形成种种“异化”的社会原因。
人物/物 身份 原本角色 异化后角色
明宣宗 皇帝 最高统治者 享乐者
华阴令、里胥、抚军 官吏 上位者 媚上者、压迫者
成名 百姓 读书人 捕虫者、“可怜虫”
成名子 百姓 幼子 拯救者
促织 昆虫 玩物 主宰者
人与物的“异化”一方面映照出人世间繁芜丛杂、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一方面痛诉着整个封建大明帝国压榨百姓的黑暗现实。
斗促织之风过甚,朝廷视百姓性命如草芥;官场贪腐成风,上至抚军下至县令、华胥,用种种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皇帝自身行为不检点,“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所谓“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3、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给这种“异化”安排一个看似喜剧的结局呢?
原型故事的结局
“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 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 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梅村诗集笺注》转引吕毖《明朝小史》
成名一家被官府逼迫交纳促织,以致倾家荡产,但结局又终获得升迁赏赐,你认为这结局符合客观现实吗?
成名一家为什么能获得升迁赏赐、裘马扬扬?因为拥有一只战无不胜的蟋蟀
从哪来的?成名之子魂化
现实中人不可能变成蟋蟀,成名之子,也不可能。
现实中成名一家不可能获得升迁赏赐,裘马扬扬。
普通百姓是无法摆脱厄运的,倾家荡产的命运是注定的。
《促织》的这种喜剧结局更能反衬出作品的悲剧色彩。成名的否极泰来,只是因为一只促织,而这只促织竟是儿子魂化而成,多么离奇的幻想!上位者对民间疾苦漠视和剥削,整个社会上行下效。成名之子昏睡中魂化促织,这个幼小的心灵为了“赎罪”,为了解除父母的痛苦,甘愿魂化促织,更体现出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它迫使“人”变为“非人”,这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一个幼小灵魂的蹂躏,何等残酷,何等酸楚!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和压迫暴露无遗,小说正是以喜剧结局反衬出更深层的悲剧意义。
任务四:知经历,探意图
蒲松龄生活在清朝康乾时代,他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故事?作者清朝人却写一个明宣德间的故事,对此该如何理解?
请同学们看到文章最后一段。
第一层:“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第二层:成名一贫一富,贫富变化说明是“天将以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寄托了天意的悲悯之情。
第三层:证实了“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嘲讽之意,愤懑之情。
“异史氏曰”句句是肺腑之言。
蒲松龄自幼饱读诗书、才高八斗、少年即颇有文名,19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其后却屡试不第,一直考到51岁,为生计所迫去当“塾师”。
封建科举制度表面上是选拔人才,但实际上是选拔“奴才”,真正有学识的正直之士得不到重用,处处受压制,蒲松龄正是对科举弊端与丑恶黑暗看得一清二楚,才揭得深刻、讽得辛辣、批得尖锐。
刻苦读书无用,科举误人终生。 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历史学家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蟋蟀盆清代以康熙,乾隆时制作者最精。康熙,乾隆宫中当亦尚促织之戏。
——(叶百丰《宫中尚促织之戏》上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蒲松龄生康熙年间,目睹其扰民为害之烈。由于不能明言,乃假托宣德间,基于史料创作了这则一家因蟋蟀的悲欢故事借古讽今。
作者借记述一个看似荒诞不经、有违常理的所谓前朝故事,来反映“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寄寓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民众的同情。小说末尾更通过异史氏之言“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点明了借古讽今的目的,即规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注意休养生息,爱惜民力,施行仁政。
任务五:细品味,明特色
① 情节曲折,构思严谨。
故事情节曲折,却构思严谨。纵观全文,起承转合,前呼后应,结构完整。《促织》一文以“促织”为线索,条理清晰,又曲折动人情节波折:波折一——岁征促织,成名破产受刑,无计可施,走投无路;波折二——神巫指点,成名得虫;波折三——节外生枝,成子弄死促织,投井自杀,成家陷入绝境;波折四——成子起死回生,魂化促织,成家因祸得福。
情节的跌宕起伏,充实、丰满了故事,深化了思想内容。
② 巧妙运用伏笔和暗示。
文章多处运用伏笔和暗示,使故事于情于理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在情节上前后呼应。如第一段中“此物故非西产”,句中的“故”字既是伏笔,又是暗示。促织本不是陕西一带的特产,而上至宫廷,下至县令却每年在民间强征,这为成名一家悲剧的必然性埋下了伏笔。
③ 多种手法刻画,形象生动。
作者非常善于运用白描手法进行勾勒,如成名夫妇得子尸于井的相关描写,描绘出人物亦悲亦愁的神态;又巧妙地借用衬托,以“茅舍无烟”“相对默然”来表现成名夫妇“不复聊赖”的精神状态。心理描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成名在儿子失手弄死促织到找到另一只促织的过程中,由“如被冰雪”而起,经过“怒—悲—喜—愁—惊—喜—惴”的心理变化。事态的急剧发展,造成人物心理的剧烈震荡。小说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成名焦急、悲愤、忧喜交加的复杂心理变化,极写成名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激起读者对制造这一痛苦的社会根源的强烈憎恨。动作描写。如“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段文字通“怒”“奔”“腾击”“跃”“张”“伸”“龁”等词,把斗虫过程中促织的神态和动作写得细腻逼真。
④ 运用现实与幻想交融的艺术手法。
“人变促织”后情节的戏剧性逆转,体会否极泰来的“喜剧”效果,认识了小说所揭示的悲剧意义:一个“人不如虫”的畸形社会,否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虚幻的手法由此产生了极具讽刺的艺术效果。
作业:如果让你来改写,你会给《促织》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请同学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教学目标:
1.鉴赏小说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情节。
2.感受小说的悲剧性。
3.探究“人化为虫”这一荒诞情节背后,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教学重点:
1、作者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2、感受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以及人物情绪的丰富变化。
教学过程
一、导入:
电视剧《聊斋>主题曲
二、任务落实
任务一:识作者,知常识
1、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成年时家境早已衰落,生活十分贫困。一生热衷功名,醉心科举,但他除了十九岁时应童子试曾连续考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外,以后屡受挫折,一直郁郁不得志。一面教书,一面应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出贡,补了个岁贡生,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他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生活的贫困使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体会。
2、《聊斋志异》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聊斋志异》共490余篇,虚构出诡谲瑰丽的故事,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初名《鬼狐传》,后定名《聊斋志异》。
“聊斋”是作者书斋名,“志”就是记述,“异”就是奇闻异事。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聊斋自志》
三种类型:
一是爱情故事,占据着全书最大的比重,故事的主要人物大多不惧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由爱情。这类名篇有《莲香》《小谢》《连城》等。
二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作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蒲松龄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叶生》《于去恶》《王子安》等都是这类名篇。
三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极具社会意义,如《席方平》《促织》《梦狼》《梅女》等。
3、后世评价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鲁迅:“用传奇之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
郭沫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
——毕飞宇《小说课》
4、何为促织
促织鸣东壁。——《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趋织鸣,懒妇惊。——幽州谚语
谓其声如急织也。——晋人崔豹《古今注》
促织,就是蟋蟀。
任务二:循线索,理情节
标题“促织”是全文的线索,请同学紧扣线索给每段课文加一个2-3字的标题,并且概括小说情节。
见ppt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开端:征促织
发展:觅促织--卜促织--得促织
高潮:失促织--化促织--斗促织
结局:献促织
情节的跌宕起伏,情绪的起起落落,尽在这千余字中。《促织》篇幅虽短,但意蕴丰富,折射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
任务三:寻“异”处,品深意
1、在《聊斋志异序》中这样写道:“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意思是记录的是怪异奇事,就是申明记事不同寻常。请同学们分组讨论,说一说文中都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并体会其深刻意蕴。
尚促织,征民间 不顾百姓死活,以天下奉一人之玩乐
“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华阴令媚上”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皇帝已由追求一般的奢华享乐转而一味追求声色犬马、斗鸡玩虫等低级趣味,从而玩物丧志。他再也无心国政,无心黎民苍生,而是“以天下奉我一人之淫乐”。地方官吏也只以媚上邀宠为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为讨皇上欢心,已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为满足皇帝玩乐需要,国家机器迅速开动起来,官廷传命于巡抚,巡抚催之于县令,县令责之于里正,作为读书人的成名再也无暇顾及科举文章,这种志趣之异,是成名悲喜剧的总根源。
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便只能是按部就班的。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四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
无促织,杖至百 法律沦为鱼肉百姓、滥施淫威的工具
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法律,不再以打击违法犯罪、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为目的,它惩罚的对象也不再只是“暴民”或“刁民”,当像成名这样迂讷老实的读书人完不成官府缴纳蟋蟀的“任务”时,“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直打得他两股间脓血流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法律沦为统治者随心所欲肉人民、滥施淫威的工具。
神灵验,得促织 寄希望于求神问卜,实际已无生路。
占卜问巫,已经成为百姓在解决不了现实矛盾、备受煎熬后的一种共性选择和出路,文中红女白婆、填塞门户的盛况,燃香长拜、竦立以听的虔诚,无不昭示出现实中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形下,必然会抓住“占卜”这一救命稻草。但神图那么灵验却是虚幻的。
这个情节提炼了现实生活,只有受尽生活折磨的人、陷入绝境的人,才会寄希望于求神问卜。百姓苦海无边,除非神仙显灵,否则不能脱离苦海。虚构神图灵验这个虚幻的情节告诉我们成名夫妇实际上已无生路。
因促织,儿丧命 人命如草芥,无辜者被扼杀
成名不在家,九岁的儿子因好奇,“窃发盆”,青麻头被儿子“扑死”。 儿子也因失手打死蟋蟀而投井自杀,九岁的成名之子有何罪 只是一个童心未泯,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无辜受害者被扼杀,被吞噬的过程。
不念儿,念促织 人被“异化” ,正常情感被扭曲
“僵卧长愁”“目不交睫” 成名一夜未眠,愁的不是儿子的安危,“不复以儿为念”从中可见,愁的是上哪儿捉蟋蟀,眼看期限在即,交不了差,唯有死路一条,真是一筹莫展,愁肠百结。对完不成官差的忧虑,对官府责罚的恐惧,是如何扭曲了人的正常情感,扭曲了作为人伦之道的父子之情。儿子的生命竟然不如一只小小的蟋蟀,作者写来真是满含悲愤。
失神识 ,化促织 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由人变为虫
这个虚幻情节,比成名夫妻的身陷绝境,更加震撼人心。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从这方面说,人的生存意义是超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的。可是在这个故事里,人不愿成为人,而甘愿变成一只虫子。在人与蟋蟀的关系中,人是弱者,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地掐住人的脖子,人与蟋蟀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人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宁愿自我否定,而魂化成一只蟋蟀。这种否定,是极其震撼人心的,它以寓言的形式影射了人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孩子爱他的爸爸,孩子想给爸爸解决问题。既然自己给爸爸惹了麻烦,那么,就让自己来解决吧。为了爸爸,孩子不惜让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这一段太感人的,父子情深。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这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毕飞宇
鸡虫斗,促织胜 战胜天敌增加传奇性,暗示非一般之虫
为什么不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了好几个促织,最后,天下第一,然后呢,成名完成了任务,成名的一家过上了富足幸福的日子?
从促织到鸡,推波助澜,小说的逻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
为什么是鸡?为什么不是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狼。
谁对昆虫的伤害最大?谁最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答案是唯一的,鸡。
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献促织,获封赏 违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事理,荒谬可笑
成名不能通过正常的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却因进贡一只上等蟋蟀而被县令特许人邑庠;先前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后却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县令以才能“卓异”闻名,只因他向抚军进献了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抚军不是因政绩优良而受皇帝褒扬,却因迎合皇帝特殊爱好而得到名马衣缎的奖赏。所有这些,都缺少最起码的因果逻辑,违背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事理和游戏法则。
根据文章内容完成表格,并探究形成种种“异化”的社会原因。
人物/物 身份 原本角色 异化后角色
明宣宗 皇帝 最高统治者 享乐者
华阴令、里胥、抚军 官吏 上位者 媚上者、压迫者
成名 百姓 读书人 捕虫者、“可怜虫”
成名子 百姓 幼子 拯救者
促织 昆虫 玩物 主宰者
人与物的“异化”一方面映照出人世间繁芜丛杂、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一方面痛诉着整个封建大明帝国压榨百姓的黑暗现实。
斗促织之风过甚,朝廷视百姓性命如草芥;官场贪腐成风,上至抚军下至县令、华胥,用种种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皇帝自身行为不检点,“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所谓“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3、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给这种“异化”安排一个看似喜剧的结局呢?
原型故事的结局
“宣宗酷爱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 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 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梅村诗集笺注》转引吕毖《明朝小史》
成名一家被官府逼迫交纳促织,以致倾家荡产,但结局又终获得升迁赏赐,你认为这结局符合客观现实吗?
成名一家为什么能获得升迁赏赐、裘马扬扬?因为拥有一只战无不胜的蟋蟀
从哪来的?成名之子魂化
现实中人不可能变成蟋蟀,成名之子,也不可能。
现实中成名一家不可能获得升迁赏赐,裘马扬扬。
普通百姓是无法摆脱厄运的,倾家荡产的命运是注定的。
《促织》的这种喜剧结局更能反衬出作品的悲剧色彩。成名的否极泰来,只是因为一只促织,而这只促织竟是儿子魂化而成,多么离奇的幻想!上位者对民间疾苦漠视和剥削,整个社会上行下效。成名之子昏睡中魂化促织,这个幼小的心灵为了“赎罪”,为了解除父母的痛苦,甘愿魂化促织,更体现出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它迫使“人”变为“非人”,这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一个幼小灵魂的蹂躏,何等残酷,何等酸楚!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和压迫暴露无遗,小说正是以喜剧结局反衬出更深层的悲剧意义。
任务四:知经历,探意图
蒲松龄生活在清朝康乾时代,他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故事?作者清朝人却写一个明宣德间的故事,对此该如何理解?
请同学们看到文章最后一段。
第一层:“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第二层:成名一贫一富,贫富变化说明是“天将以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寄托了天意的悲悯之情。
第三层:证实了“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嘲讽之意,愤懑之情。
“异史氏曰”句句是肺腑之言。
蒲松龄自幼饱读诗书、才高八斗、少年即颇有文名,19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其后却屡试不第,一直考到51岁,为生计所迫去当“塾师”。
封建科举制度表面上是选拔人才,但实际上是选拔“奴才”,真正有学识的正直之士得不到重用,处处受压制,蒲松龄正是对科举弊端与丑恶黑暗看得一清二楚,才揭得深刻、讽得辛辣、批得尖锐。
刻苦读书无用,科举误人终生。 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历史学家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蟋蟀盆清代以康熙,乾隆时制作者最精。康熙,乾隆宫中当亦尚促织之戏。
——(叶百丰《宫中尚促织之戏》上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蒲松龄生康熙年间,目睹其扰民为害之烈。由于不能明言,乃假托宣德间,基于史料创作了这则一家因蟋蟀的悲欢故事借古讽今。
作者借记述一个看似荒诞不经、有违常理的所谓前朝故事,来反映“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寄寓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民众的同情。小说末尾更通过异史氏之言“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点明了借古讽今的目的,即规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注意休养生息,爱惜民力,施行仁政。
任务五:细品味,明特色
① 情节曲折,构思严谨。
故事情节曲折,却构思严谨。纵观全文,起承转合,前呼后应,结构完整。《促织》一文以“促织”为线索,条理清晰,又曲折动人情节波折:波折一——岁征促织,成名破产受刑,无计可施,走投无路;波折二——神巫指点,成名得虫;波折三——节外生枝,成子弄死促织,投井自杀,成家陷入绝境;波折四——成子起死回生,魂化促织,成家因祸得福。
情节的跌宕起伏,充实、丰满了故事,深化了思想内容。
② 巧妙运用伏笔和暗示。
文章多处运用伏笔和暗示,使故事于情于理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在情节上前后呼应。如第一段中“此物故非西产”,句中的“故”字既是伏笔,又是暗示。促织本不是陕西一带的特产,而上至宫廷,下至县令却每年在民间强征,这为成名一家悲剧的必然性埋下了伏笔。
③ 多种手法刻画,形象生动。
作者非常善于运用白描手法进行勾勒,如成名夫妇得子尸于井的相关描写,描绘出人物亦悲亦愁的神态;又巧妙地借用衬托,以“茅舍无烟”“相对默然”来表现成名夫妇“不复聊赖”的精神状态。心理描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成名在儿子失手弄死促织到找到另一只促织的过程中,由“如被冰雪”而起,经过“怒—悲—喜—愁—惊—喜—惴”的心理变化。事态的急剧发展,造成人物心理的剧烈震荡。小说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成名焦急、悲愤、忧喜交加的复杂心理变化,极写成名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激起读者对制造这一痛苦的社会根源的强烈憎恨。动作描写。如“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段文字通“怒”“奔”“腾击”“跃”“张”“伸”“龁”等词,把斗虫过程中促织的神态和动作写得细腻逼真。
④ 运用现实与幻想交融的艺术手法。
“人变促织”后情节的戏剧性逆转,体会否极泰来的“喜剧”效果,认识了小说所揭示的悲剧意义:一个“人不如虫”的畸形社会,否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虚幻的手法由此产生了极具讽刺的艺术效果。
作业:如果让你来改写,你会给《促织》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请同学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 齐桓晋文之事 庖丁解牛)
- 2 烛之武退秦师
- 3 *鸿门宴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二单元
- 4 窦娥冤(节选)
- 5 雷雨(节选)
- 6 *哈姆莱特(节选)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三单元
- 7(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 8 *中国建筑的特征
- 9 说“木叶”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四单元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
- 学习活动
- 第五单元
- 10(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 11(谏逐客书 *与妻书)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六单元
- 12 祝福
- 13(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 装在套子里的人)
- 14(促织 * 变形记(节选))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七单元 整本书阅读
- 《红楼梦》
- 第八单元
- 15(谏太宗十思疏 * 答司马谏议书)
- 16(阿房宫赋 * 六国论)
- 单元学习任务
- 古诗词诵读
- 登岳阳楼
- 桂枝香·金陵怀古
- 念奴娇·过洞庭
- 游园([皂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