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必修上册《我与地坛(节选)》教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部编版必修上册《我与地坛(节选)》教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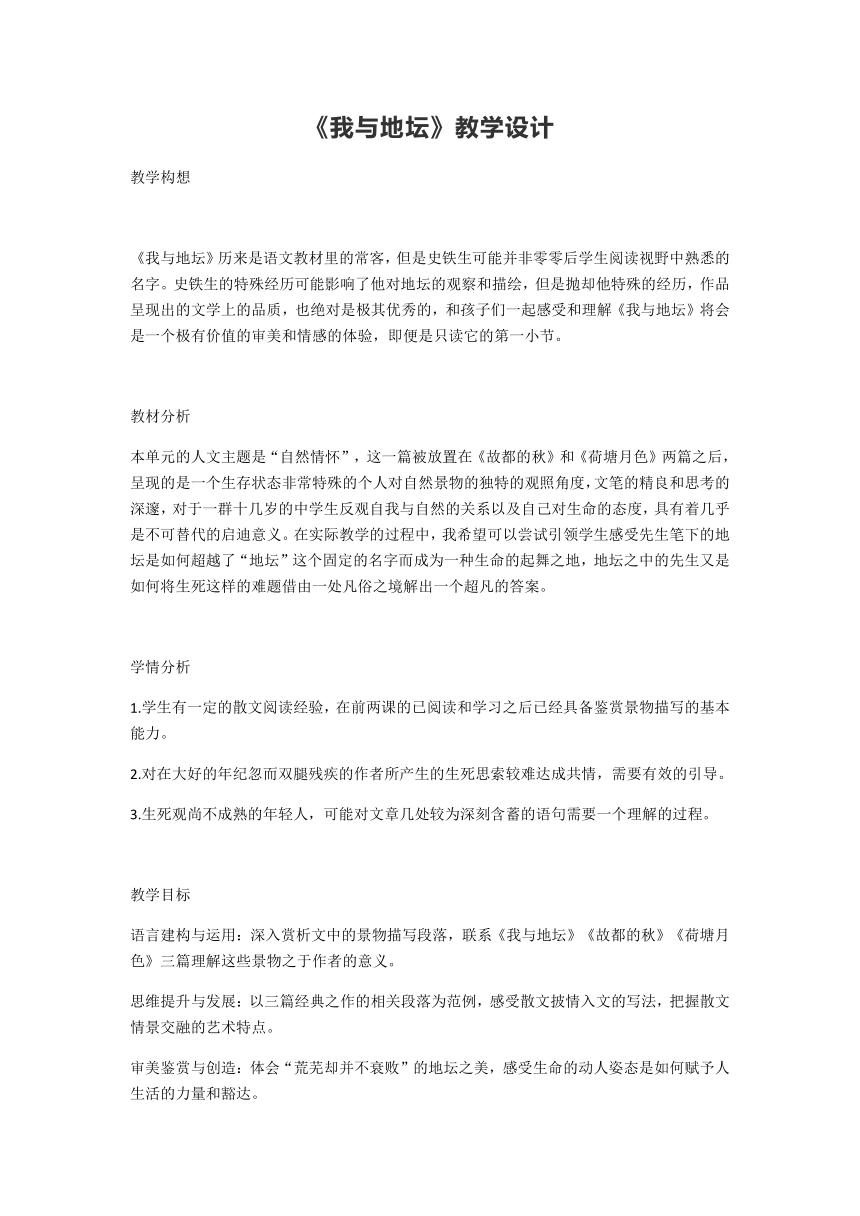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5.8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2-09-15 12:45:29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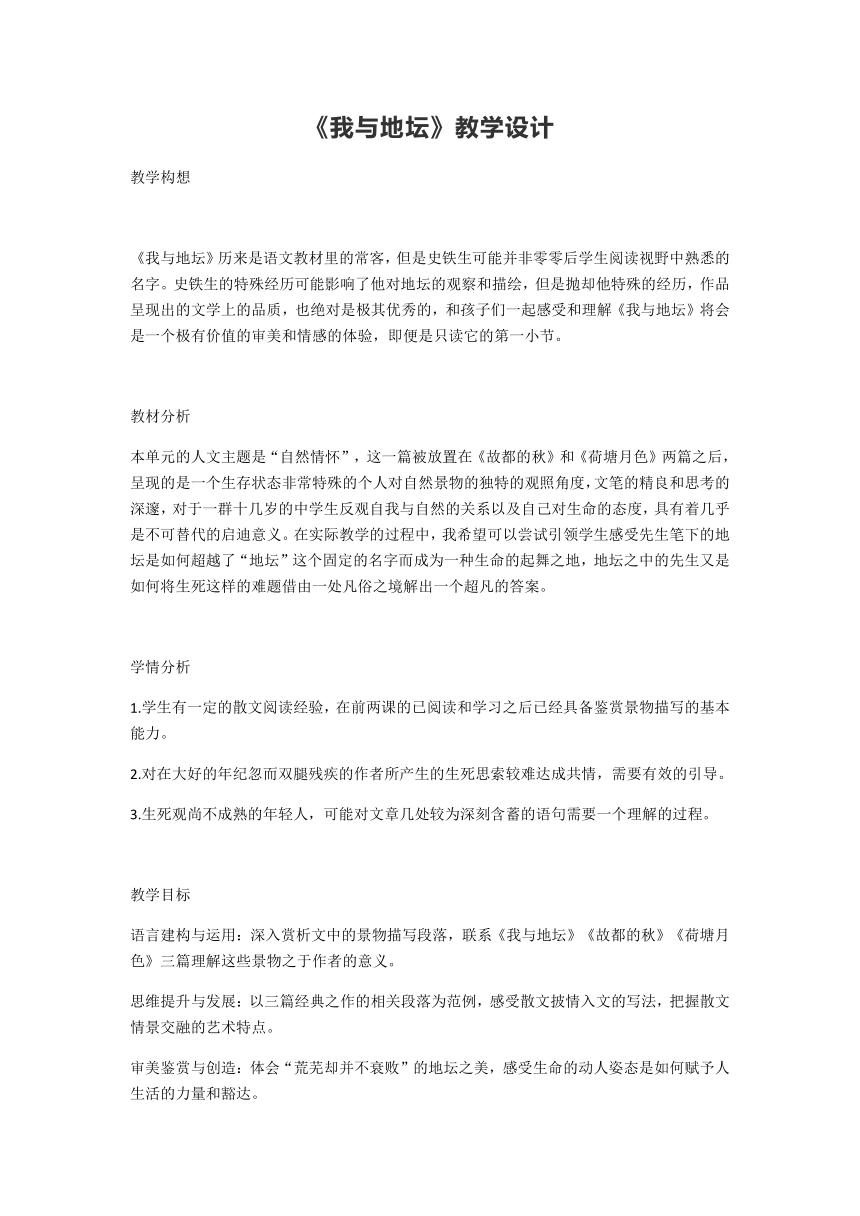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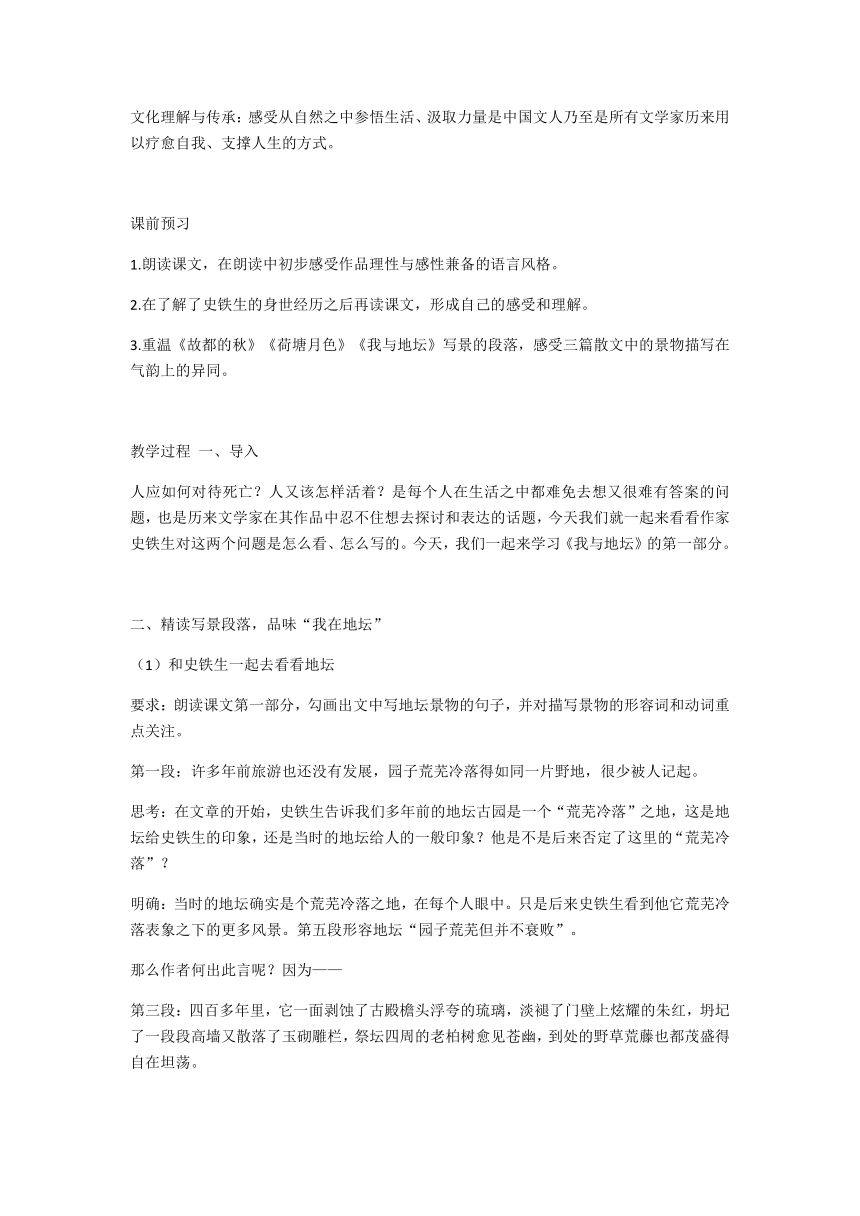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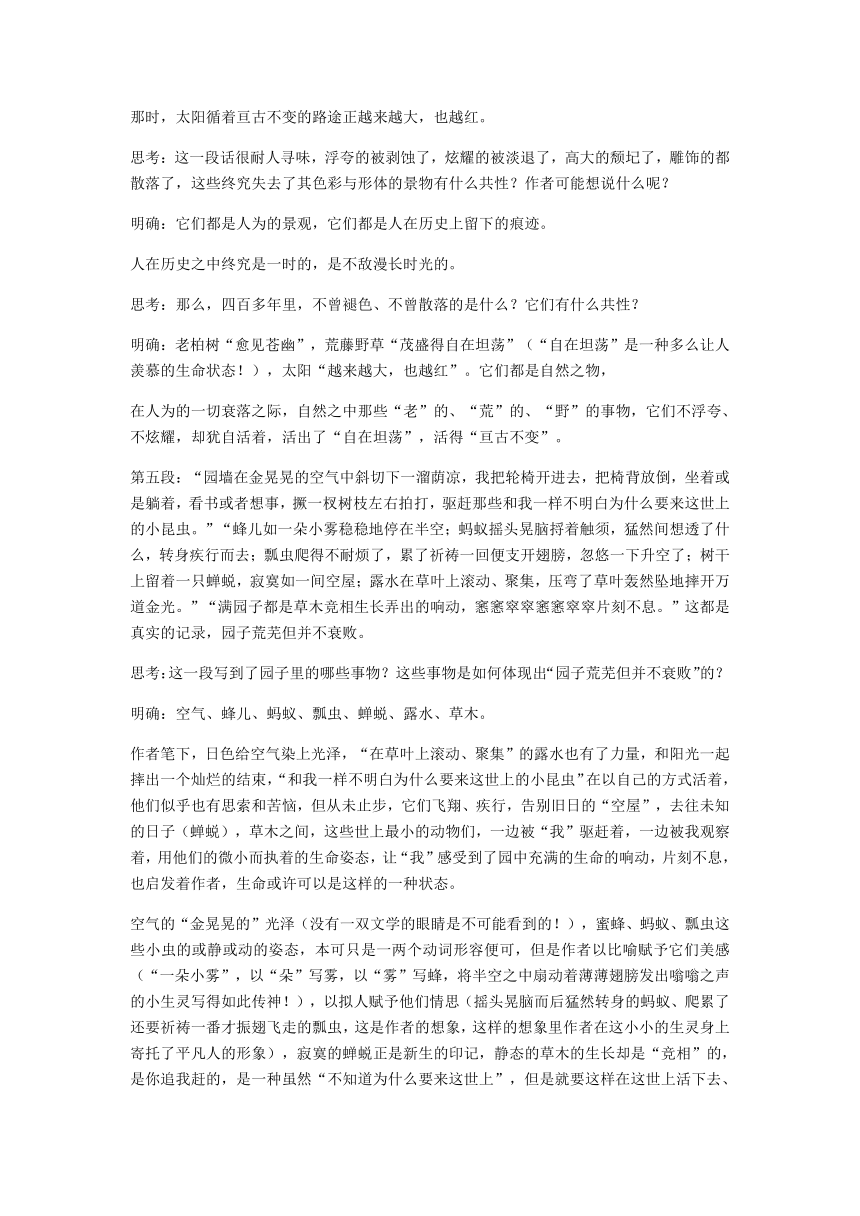
文档简介
《我与地坛》教学设计
教学构想
《我与地坛》历来是语文教材里的常客,但是史铁生可能并非零零后学生阅读视野中熟悉的名字。史铁生的特殊经历可能影响了他对地坛的观察和描绘,但是抛却他特殊的经历,作品呈现出的文学上的品质,也绝对是极其优秀的,和孩子们一起感受和理解《我与地坛》将会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审美和情感的体验,即便是只读它的第一小节。
教材分析
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自然情怀”,这一篇被放置在《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两篇之后,呈现的是一个生存状态非常特殊的个人对自然景物的独特的观照角度,文笔的精良和思考的深邃,对于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反观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具有着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启迪意义。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我希望可以尝试引领学生感受先生笔下的地坛是如何超越了“地坛”这个固定的名字而成为一种生命的起舞之地,地坛之中的先生又是如何将生死这样的难题借由一处凡俗之境解出一个超凡的答案。
学情分析
1.学生有一定的散文阅读经验,在前两课的已阅读和学习之后已经具备鉴赏景物描写的基本能力。
2.对在大好的年纪忽而双腿残疾的作者所产生的生死思索较难达成共情,需要有效的引导。
3.生死观尚不成熟的年轻人,可能对文章几处较为深刻含蓄的语句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
教学目标
语言建构与运用:深入赏析文中的景物描写段落,联系《我与地坛》《故都的秋》《荷塘月色》三篇理解这些景物之于作者的意义。
思维提升与发展:以三篇经典之作的相关段落为范例,感受散文披情入文的写法,把握散文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
审美鉴赏与创造:体会“荒芜却并不衰败”的地坛之美,感受生命的动人姿态是如何赋予人生活的力量和豁达。
文化理解与传承:感受从自然之中参悟生活、汲取力量是中国文人乃至是所有文学家历来用以疗愈自我、支撑人生的方式。
课前预习
1.朗读课文,在朗读中初步感受作品理性与感性兼备的语言风格。
2.在了解了史铁生的身世经历之后再读课文,形成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3.重温《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我与地坛》写景的段落,感受三篇散文中的景物描写在气韵上的异同。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人应如何对待死亡?人又该怎样活着?是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难免去想又很难有答案的问题,也是历来文学家在其作品中忍不住想去探讨和表达的话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作家史铁生对这两个问题是怎么看、怎么写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与地坛》的第一部分。
二、精读写景段落,品味“我在地坛”
(1)和史铁生一起去看看地坛
要求:朗读课文第一部分,勾画出文中写地坛景物的句子,并对描写景物的形容词和动词重点关注。
第一段:许多年前旅游也还没有发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思考:在文章的开始,史铁生告诉我们多年前的地坛古园是一个“荒芜冷落”之地,这是地坛给史铁生的印象,还是当时的地坛给人的一般印象?他是不是后来否定了这里的“荒芜冷落”?
明确:当时的地坛确实是个荒芜冷落之地,在每个人眼中。只是后来史铁生看到他它荒芜冷落表象之下的更多风景。第五段形容地坛“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那么作者何出此言呢?因为——
第三段: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
思考:这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浮夸的被剥蚀了,炫耀的被淡退了,高大的颓圮了,雕饰的都散落了,这些终究失去了其色彩与形体的景物有什么共性?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呢?
明确:它们都是人为的景观,它们都是人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人在历史之中终究是一时的,是不敌漫长时光的。
思考:那么,四百多年里,不曾褪色、不曾散落的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共性?
明确:老柏树“愈见苍幽”,荒藤野草“茂盛得自在坦荡”(“自在坦荡”是一种多么让人羡慕的生命状态!),太阳“越来越大,也越红”。它们都是自然之物,
在人为的一切衰落之际,自然之中那些“老”的、“荒”的、“野”的事物,它们不浮夸、不炫耀,却犹自活着,活出了“自在坦荡”,活得“亘古不变”。
第五段:“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思考:这一段写到了园子里的哪些事物?这些事物是如何体现出“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的?
明确:空气、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草木。
作者笔下,日色给空气染上光泽,“在草叶上滚动、聚集”的露水也有了力量,和阳光一起摔出一个灿烂的结束,“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在以自己的方式活着,他们似乎也有思索和苦恼,但从未止步,它们飞翔、疾行,告别旧日的“空屋”,去往未知的日子(蝉蜕),草木之间,这些世上最小的动物们,一边被“我”驱赶着,一边被我观察着,用他们的微小而执着的生命姿态,让“我”感受到了园中充满的生命的响动,片刻不息,也启发着作者,生命或许可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空气的“金晃晃的”光泽(没有一双文学的眼睛是不可能看到的!),蜜蜂、蚂蚁、瓢虫这些小虫的或静或动的姿态,本可只是一两个动词形容便可,但是作者以比喻赋予它们美感(“一朵小雾”,以“朵”写雾,以“雾”写蜂,将半空之中扇动着薄薄翅膀发出嗡嗡之声的小生灵写得如此传神!),以拟人赋予他们情思(摇头晃脑而后猛然转身的蚂蚁、爬累了还要祈祷一番才振翅飞走的瓢虫,这是作者的想象,这样的想象里作者在这小小的生灵身上寄托了平凡人的形象),寂寞的蝉蜕正是新生的印记,静态的草木的生长却是“竞相”的,是你追我赶的,是一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世上”,但是就要这样在这世上活下去、活一回的生命状态。
(个人认为,理解了这一段,对理解第七段对“怎么活”的回答有直接的意义,这里的“不衰败”就是因为这个园子是“活着”的。某种意义上,第七段是第五段的延伸。)
第七段: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思考:作者说在要回答“怎样活”的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提到地坛中“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共性吗?
明确:这些东西是作者十五年来在地坛听风沐雨看落日的所见所闻。落日无私映照每个坎坷,古柏镇静看着世人来去,雨燕高歌声动天地,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沉默,以及暴雨里的泥土气息和秋霜后的落叶味道,这些景象都流露着一种恒久、沉静的气质,让人感到地坛十五年如此,四百年如此。
地坛安静不语而生生不息,有声有色有味道有故事,地坛在四季流转的时光之中,兀自活着,没有回答“怎样活”,但是展示了“怎样活”。和第五段写道的那群小昆虫一样,地坛里的一切都坦然地接受着生命本身,奉献着每一个季节每一种气候每一分一秒应有的风景和韵味,只管活着,自在坦然。在作者笔下,地坛里的景物不比任何别处特殊,落日或者落叶,古柏或者雨燕,都不是特殊的意象,但是它们汇聚在这样一个段落里,构成的就是四季就是时光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活着,就演绎了活着本身,带着一种宁静的热忱,一种简洁的丰富,一种日常的超常。
(2)在地坛,史铁生看见了什么
思考:这几处景物描写,内在可有共性?
明确:综合看这一部分里的三段比较集中的写景文字,我们不难发它们内在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本着要记下这古园之中看似最平凡但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那些事物,来回答关于生死的这个重要问题。因为雕栏玉砌高墙古殿没有生命,或者说它们的生命已尽;而那些草木和昆虫、日光和风雨却从来都在,它们最有资格对生命之问做出回答。作者是有意选择了那些最能够表达自己感受的意象,写进了本文;或者说,是这些确乎启发了作者的自然事物,让作者真切地得到了关于生死的答案。他必须诚实地写下它们,感谢它们为失魂落魄的自己,又找回了魂魄。
三、细品哲理字句,感受“地坛在我”
(1)地坛里,有个什么样的“我”
在第三段,作者写道,“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地坛不言不语,对“我”这个忽然造访的人会有什么意图呢。与其说地坛有其“意图”,不如说是史铁生有其领悟。正如作者所写“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在这里,作者看到了怎样的自己呢?你能在文中找到作者描述当时的自己的句子吗?
明确:
“(在)最狂妄的年龄上(21岁)忽地残废了双腿”(第三段)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第五段)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第六段)
思考:我们在这些字句中看到“我”什么样的形象呢?
明确:非常年轻,遭遇双腿残疾的突然打击;没有工作没有出路,无处可去,只想逃离这个不能接纳自己的残酷世界;耗时几年终日沉浸于思考生死这样沉重难解的问题。
不难发现,这几句话之间是存在时间线的。生活中突然而至的意外重重摧毁一个年轻人的身体,随后摧毁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正常生活,自然就动摇了他对活着的信心,转而寻求关于生死的答案。
(2)对于“我”,地坛是个什么样的“人”
思考:第二段里有这样一句话,“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句话里,我和地坛有了情谊,它在等我,它被人格化了。那地坛对于我,是我的什么人呢?朋友?老师?恩人?
明确:我们要理解这样一件事,一个人如果顺顺当当地年轻走向年老,有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是不会忽然获得这么一段与地坛的日夜“厮守”的,是不会近乎固执地非要把生死这事儿想个明白的。不然这么一个双腿残废、无处可去的年轻人,需要给自己的活着以理由啊。所以,某种意义上,地坛之于史铁生,有救命之恩,是救命恩人。
地坛当然也是史铁生的朋友,哪里都“容不下他”的时候,只有地坛不拒绝他;也当然是他的老师,地坛里的雨雪风霜、古柏荒草和所有小小的生灵,都是他那些生死之问的回答者。
得到了这个回答,这个轮椅上的年轻人就可以像地坛之中的那些生命一起坦然地活着了。
思考:那他找到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吗?你找到那句话了么?
明确:“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第六段)
思考:对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你能带着对地坛景物的理解来谈对这句话的理解吗?
明确:每个人都可以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节日”总是值得纪念、值得欢庆的固定日期,一个人视死亡为节日,可见他以为死亡就在那里,不到那一日算不得节日;到了那一日,也无关悲伤。只有在反复的思量确认后,对为何出生不纠结,对何时死亡不惧怕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可是赋予史铁生对生死这份通透坦然的,不是任何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那些和人一起在这世上呼吸、生长,并且从生到死都无言的生命。他们不向生命问为什么,就接受了上帝给的这个事实。我史铁生也不例外。
思考:关于“怎样活的问题”,作者说“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这个作者看来要想上一生的问题,他没有直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结论,而是为我们描绘了非常动人的地坛景物。那些景物不特殊,却又明明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地坛里的一草一木、所有生灵都是那么尽兴而从容地活着,有光芒有色彩有气味有声响,又让人愿意像这些无言的一切一样,也好好地活上一回。
而一旦作者这样地理解了生死,带着地坛给予他的这份答案,他在与不在地坛,对自己的生命都将会好好地把握,用作者自己在《想念地坛》里的一句话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四、联系三篇作品,感悟自然与人
我们试着一起来回顾《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朱自清在日日经过的清华园,郁达夫在一椽破屋一方小院里,史铁生在“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的地坛公园,竟然都在某种意义上舒缓了自己的抑郁,找到了肯以“寿命的四分之三”去挽留的家园,参悟了生与死那个对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最重要的生死命题。
三位作家都回避了在自己的故事上大做文章,而是把眼光投向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置身于那些穿越数千年一直都在还将永远都在的日月下、花木旁,让自己获得了暂时的通达,或者——毕生的了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人的困扰和痛苦,总能在那些草木身上、小昆虫身上找到解答和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思考:试着去探寻一下三篇散文中的景物有什么共性?又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回顾梳理
三篇散文中的景物均是并非名胜的近在身边的自然景物,都是作者在情绪的低谷时所见所念的。
《故都的秋》 “清,静,悲凉”
《荷塘月色》 眼前的月下荷塘:宁静、风雅;
古人笔下的荷塘:单纯美好的爱情的发生地。
《我与地坛》 “荒芜却并不衰败”,“苍凉”“寂静”“自在坦荡”
写《故都的秋》时,从郁达夫的际遇来看,小家大国处处不幸,正是一个“悲秋”之际,他和北平,他和那清静悲凉的秋天是一种同病相怜、相互理解的交情,是愿许性命的懂得;
写《荷塘月色》那几天,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想要摆脱那些白天里“一定要说的话,一定要做的事”,而当晚的月色与荷香,熨平了朱自清心上的波澜;
《我与地坛》的写作背景就不必说了。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苦楚因了特定的时代原因和命运安排,一肚子的痛苦而又无从说起、难对人言,于是他们都想寻个幽僻的、清静的、冷落的所在,这里又不能全然是“死”的,必须得有一份生气,有某种美丽,可以让一个觉得自己没有被命运善待的人,原来也有机会、有权力获得平静和力量。其实纵观中国文人的许多作品,现实不如意时,他们总会或者总向往着归向自然,隐身山间,躬耕田园,垂纶江畔,总是以某一种和自然交流生命思索的方式,来安顿自己的人生。
这个单元里的《赤壁赋》《登泰山记》亦是明证。只是今人生活于城市之中,那用于安顿生命的山水,只能是城市之中小小的一方院子、一片荷塘、一座地坛。而对于那些忧伤、苦闷乃至不幸的作家们,也幸而有着这一个个珍贵的去处。
结语 所以我们回看《我与地坛》,或者能够明白,地坛给史铁生的,就是当初赤壁的江月给苏轼的,就清华园的荷花月色给朱自清的。自然在善感多思的人的心中,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寄托、情感牵绊、人生导师。
史铁生或许是这个单元所有作者里最不幸的,因为他承受了身体的残疾;但或许也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家离地坛很近。
教学构想
《我与地坛》历来是语文教材里的常客,但是史铁生可能并非零零后学生阅读视野中熟悉的名字。史铁生的特殊经历可能影响了他对地坛的观察和描绘,但是抛却他特殊的经历,作品呈现出的文学上的品质,也绝对是极其优秀的,和孩子们一起感受和理解《我与地坛》将会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审美和情感的体验,即便是只读它的第一小节。
教材分析
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自然情怀”,这一篇被放置在《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两篇之后,呈现的是一个生存状态非常特殊的个人对自然景物的独特的观照角度,文笔的精良和思考的深邃,对于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反观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具有着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启迪意义。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我希望可以尝试引领学生感受先生笔下的地坛是如何超越了“地坛”这个固定的名字而成为一种生命的起舞之地,地坛之中的先生又是如何将生死这样的难题借由一处凡俗之境解出一个超凡的答案。
学情分析
1.学生有一定的散文阅读经验,在前两课的已阅读和学习之后已经具备鉴赏景物描写的基本能力。
2.对在大好的年纪忽而双腿残疾的作者所产生的生死思索较难达成共情,需要有效的引导。
3.生死观尚不成熟的年轻人,可能对文章几处较为深刻含蓄的语句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
教学目标
语言建构与运用:深入赏析文中的景物描写段落,联系《我与地坛》《故都的秋》《荷塘月色》三篇理解这些景物之于作者的意义。
思维提升与发展:以三篇经典之作的相关段落为范例,感受散文披情入文的写法,把握散文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
审美鉴赏与创造:体会“荒芜却并不衰败”的地坛之美,感受生命的动人姿态是如何赋予人生活的力量和豁达。
文化理解与传承:感受从自然之中参悟生活、汲取力量是中国文人乃至是所有文学家历来用以疗愈自我、支撑人生的方式。
课前预习
1.朗读课文,在朗读中初步感受作品理性与感性兼备的语言风格。
2.在了解了史铁生的身世经历之后再读课文,形成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3.重温《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我与地坛》写景的段落,感受三篇散文中的景物描写在气韵上的异同。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人应如何对待死亡?人又该怎样活着?是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难免去想又很难有答案的问题,也是历来文学家在其作品中忍不住想去探讨和表达的话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作家史铁生对这两个问题是怎么看、怎么写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与地坛》的第一部分。
二、精读写景段落,品味“我在地坛”
(1)和史铁生一起去看看地坛
要求:朗读课文第一部分,勾画出文中写地坛景物的句子,并对描写景物的形容词和动词重点关注。
第一段:许多年前旅游也还没有发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思考:在文章的开始,史铁生告诉我们多年前的地坛古园是一个“荒芜冷落”之地,这是地坛给史铁生的印象,还是当时的地坛给人的一般印象?他是不是后来否定了这里的“荒芜冷落”?
明确:当时的地坛确实是个荒芜冷落之地,在每个人眼中。只是后来史铁生看到他它荒芜冷落表象之下的更多风景。第五段形容地坛“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那么作者何出此言呢?因为——
第三段: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
思考:这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浮夸的被剥蚀了,炫耀的被淡退了,高大的颓圮了,雕饰的都散落了,这些终究失去了其色彩与形体的景物有什么共性?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呢?
明确:它们都是人为的景观,它们都是人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人在历史之中终究是一时的,是不敌漫长时光的。
思考:那么,四百多年里,不曾褪色、不曾散落的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共性?
明确:老柏树“愈见苍幽”,荒藤野草“茂盛得自在坦荡”(“自在坦荡”是一种多么让人羡慕的生命状态!),太阳“越来越大,也越红”。它们都是自然之物,
在人为的一切衰落之际,自然之中那些“老”的、“荒”的、“野”的事物,它们不浮夸、不炫耀,却犹自活着,活出了“自在坦荡”,活得“亘古不变”。
第五段:“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思考:这一段写到了园子里的哪些事物?这些事物是如何体现出“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的?
明确:空气、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草木。
作者笔下,日色给空气染上光泽,“在草叶上滚动、聚集”的露水也有了力量,和阳光一起摔出一个灿烂的结束,“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在以自己的方式活着,他们似乎也有思索和苦恼,但从未止步,它们飞翔、疾行,告别旧日的“空屋”,去往未知的日子(蝉蜕),草木之间,这些世上最小的动物们,一边被“我”驱赶着,一边被我观察着,用他们的微小而执着的生命姿态,让“我”感受到了园中充满的生命的响动,片刻不息,也启发着作者,生命或许可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空气的“金晃晃的”光泽(没有一双文学的眼睛是不可能看到的!),蜜蜂、蚂蚁、瓢虫这些小虫的或静或动的姿态,本可只是一两个动词形容便可,但是作者以比喻赋予它们美感(“一朵小雾”,以“朵”写雾,以“雾”写蜂,将半空之中扇动着薄薄翅膀发出嗡嗡之声的小生灵写得如此传神!),以拟人赋予他们情思(摇头晃脑而后猛然转身的蚂蚁、爬累了还要祈祷一番才振翅飞走的瓢虫,这是作者的想象,这样的想象里作者在这小小的生灵身上寄托了平凡人的形象),寂寞的蝉蜕正是新生的印记,静态的草木的生长却是“竞相”的,是你追我赶的,是一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世上”,但是就要这样在这世上活下去、活一回的生命状态。
(个人认为,理解了这一段,对理解第七段对“怎么活”的回答有直接的意义,这里的“不衰败”就是因为这个园子是“活着”的。某种意义上,第七段是第五段的延伸。)
第七段: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思考:作者说在要回答“怎样活”的问题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提到地坛中“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共性吗?
明确:这些东西是作者十五年来在地坛听风沐雨看落日的所见所闻。落日无私映照每个坎坷,古柏镇静看着世人来去,雨燕高歌声动天地,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沉默,以及暴雨里的泥土气息和秋霜后的落叶味道,这些景象都流露着一种恒久、沉静的气质,让人感到地坛十五年如此,四百年如此。
地坛安静不语而生生不息,有声有色有味道有故事,地坛在四季流转的时光之中,兀自活着,没有回答“怎样活”,但是展示了“怎样活”。和第五段写道的那群小昆虫一样,地坛里的一切都坦然地接受着生命本身,奉献着每一个季节每一种气候每一分一秒应有的风景和韵味,只管活着,自在坦然。在作者笔下,地坛里的景物不比任何别处特殊,落日或者落叶,古柏或者雨燕,都不是特殊的意象,但是它们汇聚在这样一个段落里,构成的就是四季就是时光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活着,就演绎了活着本身,带着一种宁静的热忱,一种简洁的丰富,一种日常的超常。
(2)在地坛,史铁生看见了什么
思考:这几处景物描写,内在可有共性?
明确:综合看这一部分里的三段比较集中的写景文字,我们不难发它们内在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本着要记下这古园之中看似最平凡但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那些事物,来回答关于生死的这个重要问题。因为雕栏玉砌高墙古殿没有生命,或者说它们的生命已尽;而那些草木和昆虫、日光和风雨却从来都在,它们最有资格对生命之问做出回答。作者是有意选择了那些最能够表达自己感受的意象,写进了本文;或者说,是这些确乎启发了作者的自然事物,让作者真切地得到了关于生死的答案。他必须诚实地写下它们,感谢它们为失魂落魄的自己,又找回了魂魄。
三、细品哲理字句,感受“地坛在我”
(1)地坛里,有个什么样的“我”
在第三段,作者写道,“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地坛不言不语,对“我”这个忽然造访的人会有什么意图呢。与其说地坛有其“意图”,不如说是史铁生有其领悟。正如作者所写“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在这里,作者看到了怎样的自己呢?你能在文中找到作者描述当时的自己的句子吗?
明确:
“(在)最狂妄的年龄上(21岁)忽地残废了双腿”(第三段)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第五段)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第六段)
思考:我们在这些字句中看到“我”什么样的形象呢?
明确:非常年轻,遭遇双腿残疾的突然打击;没有工作没有出路,无处可去,只想逃离这个不能接纳自己的残酷世界;耗时几年终日沉浸于思考生死这样沉重难解的问题。
不难发现,这几句话之间是存在时间线的。生活中突然而至的意外重重摧毁一个年轻人的身体,随后摧毁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正常生活,自然就动摇了他对活着的信心,转而寻求关于生死的答案。
(2)对于“我”,地坛是个什么样的“人”
思考:第二段里有这样一句话,“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句话里,我和地坛有了情谊,它在等我,它被人格化了。那地坛对于我,是我的什么人呢?朋友?老师?恩人?
明确:我们要理解这样一件事,一个人如果顺顺当当地年轻走向年老,有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是不会忽然获得这么一段与地坛的日夜“厮守”的,是不会近乎固执地非要把生死这事儿想个明白的。不然这么一个双腿残废、无处可去的年轻人,需要给自己的活着以理由啊。所以,某种意义上,地坛之于史铁生,有救命之恩,是救命恩人。
地坛当然也是史铁生的朋友,哪里都“容不下他”的时候,只有地坛不拒绝他;也当然是他的老师,地坛里的雨雪风霜、古柏荒草和所有小小的生灵,都是他那些生死之问的回答者。
得到了这个回答,这个轮椅上的年轻人就可以像地坛之中的那些生命一起坦然地活着了。
思考:那他找到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吗?你找到那句话了么?
明确:“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第六段)
思考:对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你能带着对地坛景物的理解来谈对这句话的理解吗?
明确:每个人都可以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节日”总是值得纪念、值得欢庆的固定日期,一个人视死亡为节日,可见他以为死亡就在那里,不到那一日算不得节日;到了那一日,也无关悲伤。只有在反复的思量确认后,对为何出生不纠结,对何时死亡不惧怕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可是赋予史铁生对生死这份通透坦然的,不是任何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那些和人一起在这世上呼吸、生长,并且从生到死都无言的生命。他们不向生命问为什么,就接受了上帝给的这个事实。我史铁生也不例外。
思考:关于“怎样活的问题”,作者说“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这个作者看来要想上一生的问题,他没有直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结论,而是为我们描绘了非常动人的地坛景物。那些景物不特殊,却又明明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地坛里的一草一木、所有生灵都是那么尽兴而从容地活着,有光芒有色彩有气味有声响,又让人愿意像这些无言的一切一样,也好好地活上一回。
而一旦作者这样地理解了生死,带着地坛给予他的这份答案,他在与不在地坛,对自己的生命都将会好好地把握,用作者自己在《想念地坛》里的一句话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四、联系三篇作品,感悟自然与人
我们试着一起来回顾《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朱自清在日日经过的清华园,郁达夫在一椽破屋一方小院里,史铁生在“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的地坛公园,竟然都在某种意义上舒缓了自己的抑郁,找到了肯以“寿命的四分之三”去挽留的家园,参悟了生与死那个对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最重要的生死命题。
三位作家都回避了在自己的故事上大做文章,而是把眼光投向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置身于那些穿越数千年一直都在还将永远都在的日月下、花木旁,让自己获得了暂时的通达,或者——毕生的了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人的困扰和痛苦,总能在那些草木身上、小昆虫身上找到解答和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思考:试着去探寻一下三篇散文中的景物有什么共性?又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回顾梳理
三篇散文中的景物均是并非名胜的近在身边的自然景物,都是作者在情绪的低谷时所见所念的。
《故都的秋》 “清,静,悲凉”
《荷塘月色》 眼前的月下荷塘:宁静、风雅;
古人笔下的荷塘:单纯美好的爱情的发生地。
《我与地坛》 “荒芜却并不衰败”,“苍凉”“寂静”“自在坦荡”
写《故都的秋》时,从郁达夫的际遇来看,小家大国处处不幸,正是一个“悲秋”之际,他和北平,他和那清静悲凉的秋天是一种同病相怜、相互理解的交情,是愿许性命的懂得;
写《荷塘月色》那几天,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想要摆脱那些白天里“一定要说的话,一定要做的事”,而当晚的月色与荷香,熨平了朱自清心上的波澜;
《我与地坛》的写作背景就不必说了。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苦楚因了特定的时代原因和命运安排,一肚子的痛苦而又无从说起、难对人言,于是他们都想寻个幽僻的、清静的、冷落的所在,这里又不能全然是“死”的,必须得有一份生气,有某种美丽,可以让一个觉得自己没有被命运善待的人,原来也有机会、有权力获得平静和力量。其实纵观中国文人的许多作品,现实不如意时,他们总会或者总向往着归向自然,隐身山间,躬耕田园,垂纶江畔,总是以某一种和自然交流生命思索的方式,来安顿自己的人生。
这个单元里的《赤壁赋》《登泰山记》亦是明证。只是今人生活于城市之中,那用于安顿生命的山水,只能是城市之中小小的一方院子、一片荷塘、一座地坛。而对于那些忧伤、苦闷乃至不幸的作家们,也幸而有着这一个个珍贵的去处。
结语 所以我们回看《我与地坛》,或者能够明白,地坛给史铁生的,就是当初赤壁的江月给苏轼的,就清华园的荷花月色给朱自清的。自然在善感多思的人的心中,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寄托、情感牵绊、人生导师。
史铁生或许是这个单元所有作者里最不幸的,因为他承受了身体的残疾;但或许也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家离地坛很近。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 沁园春 长沙
- 2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红烛 *峨日朵雪峰之侧 *致云雀)
- 3 (百合花 *哦,香雪)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二单元
- 4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探界者”
- 5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 6 (芣苢 插秧歌)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三单元
- 7(短歌行 *归园田居(其一))
- 8(梦游天姥吟留别 登高 *琵琶行并序)
- 9(念奴娇·赤壁怀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声声慢(寻寻觅觅))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
- 学习活动
-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
- 《乡土中国》
- 第六单元
- 10(劝学 *师说)
- 11 反对党八股(节选)
- 12 拿来主义
- 13(*读书:目的和前提 *上图书馆)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七单元
- 14(故都的秋 *荷塘月色)
- 15 我与地坛(节选)
- 16(赤壁赋 *登泰山记)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八单元
- 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
- 古诗词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