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插叙的作用(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插叙的作用(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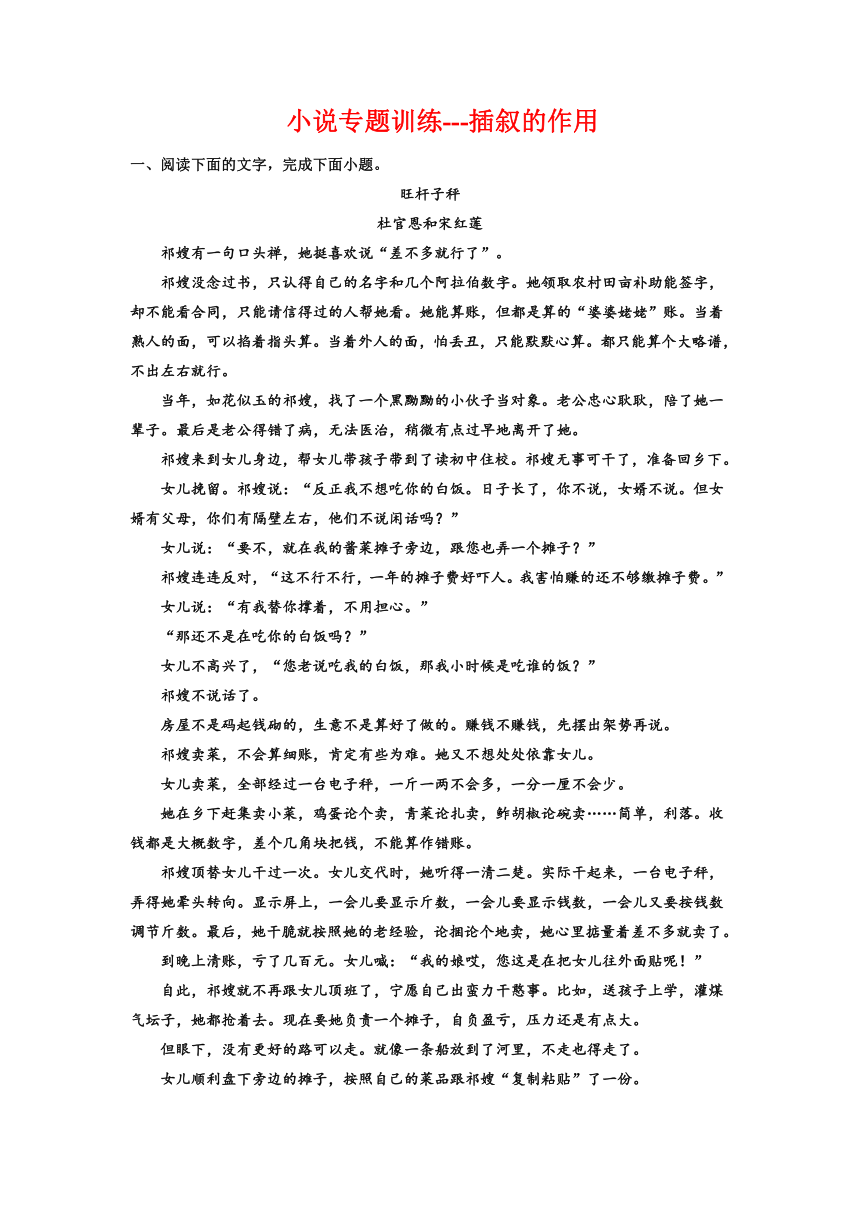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1.8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2-12-25 12:42:59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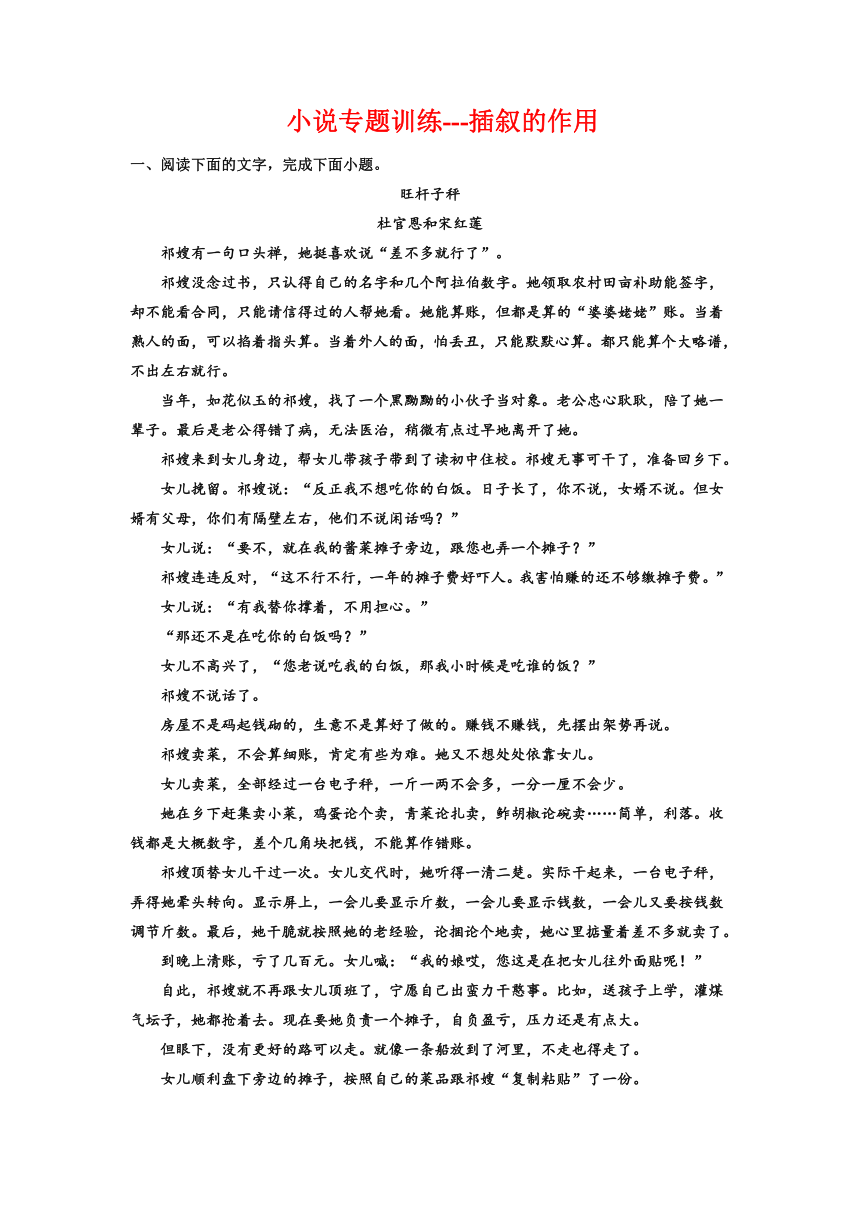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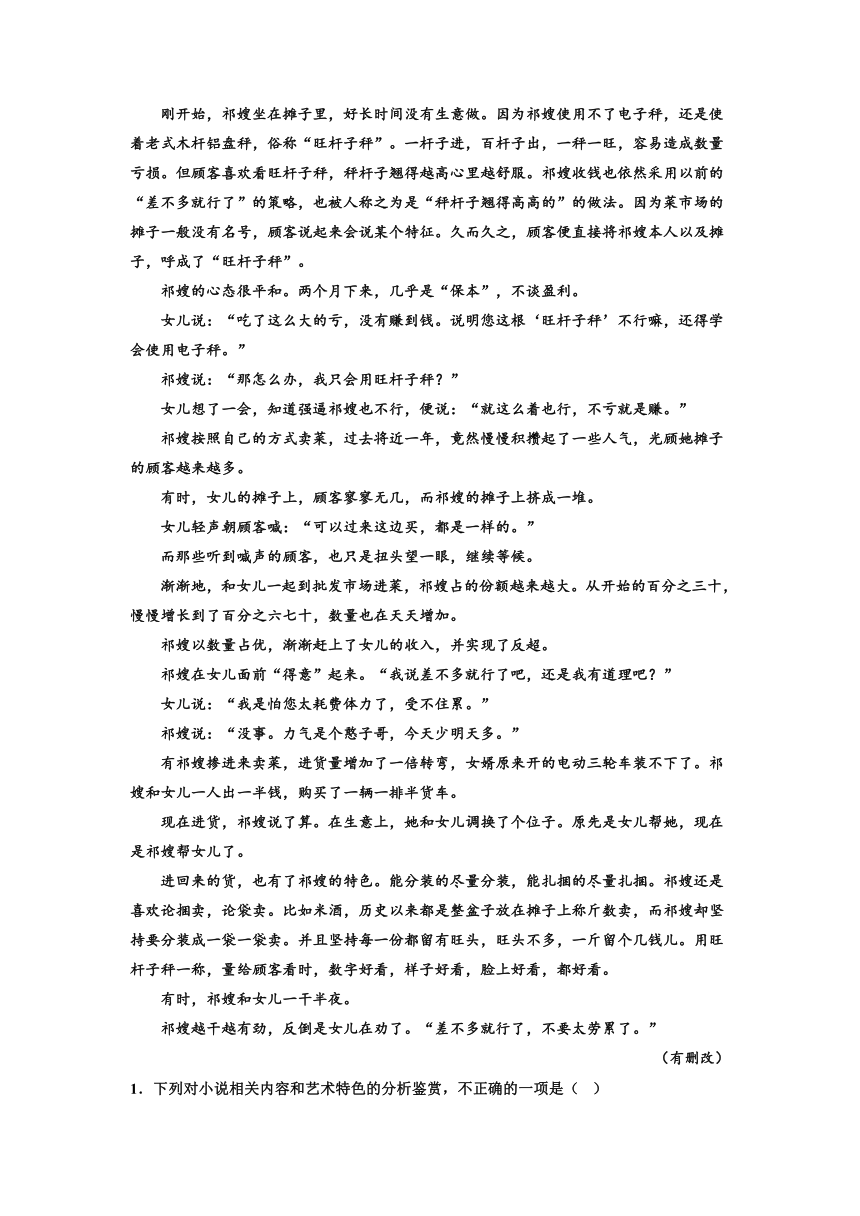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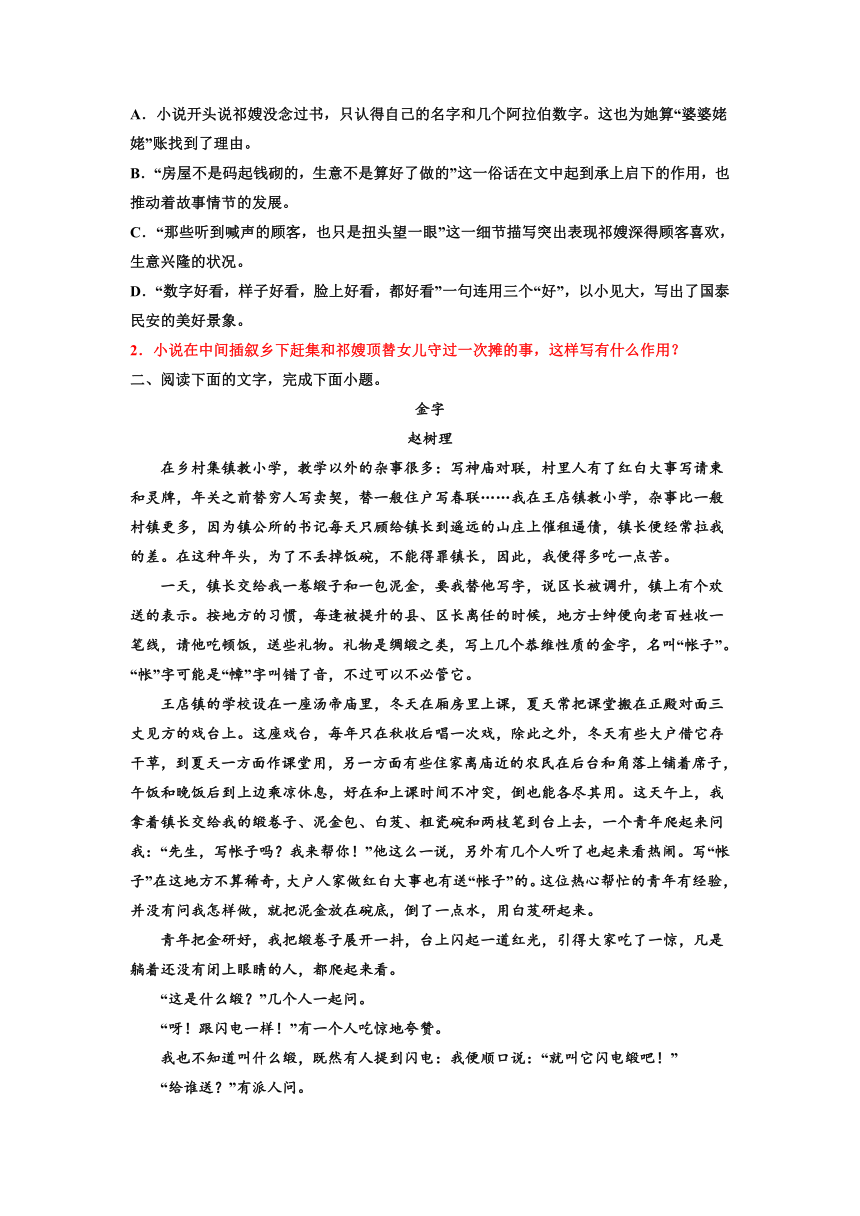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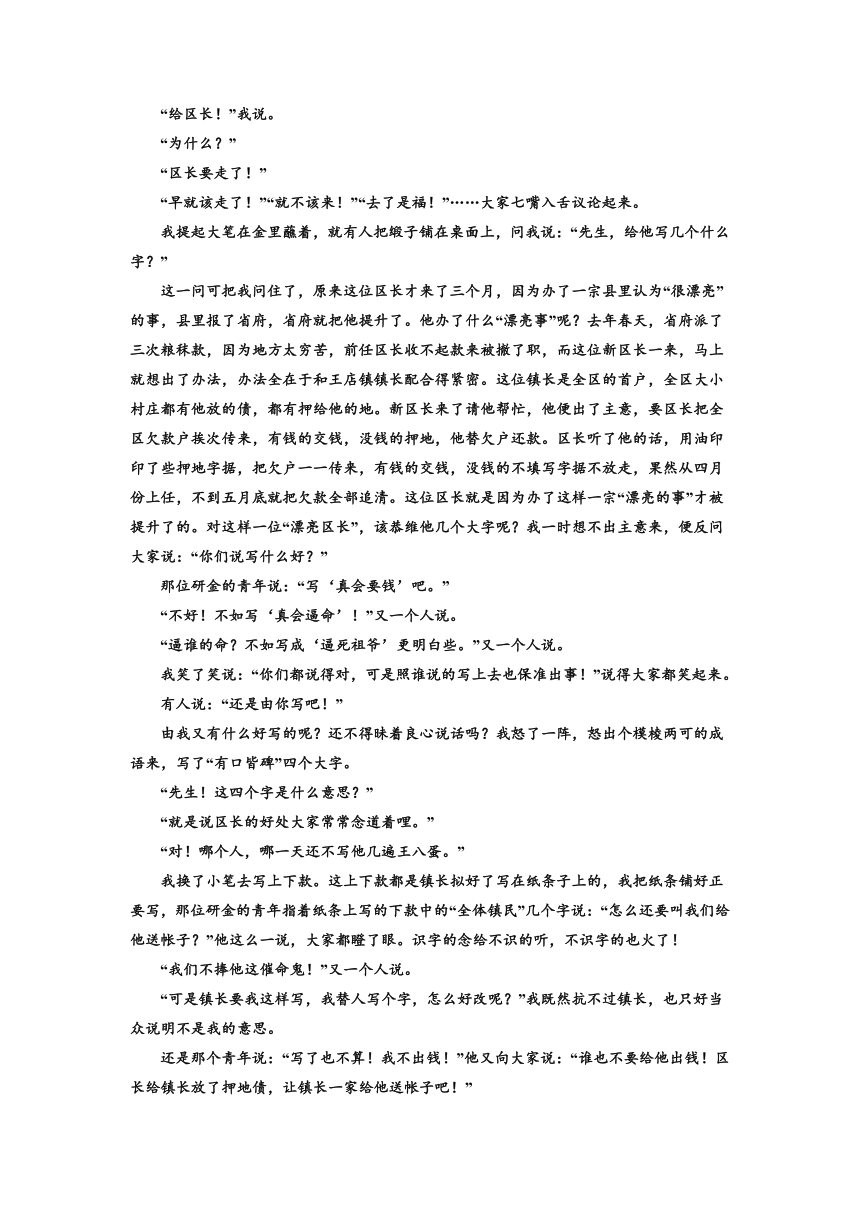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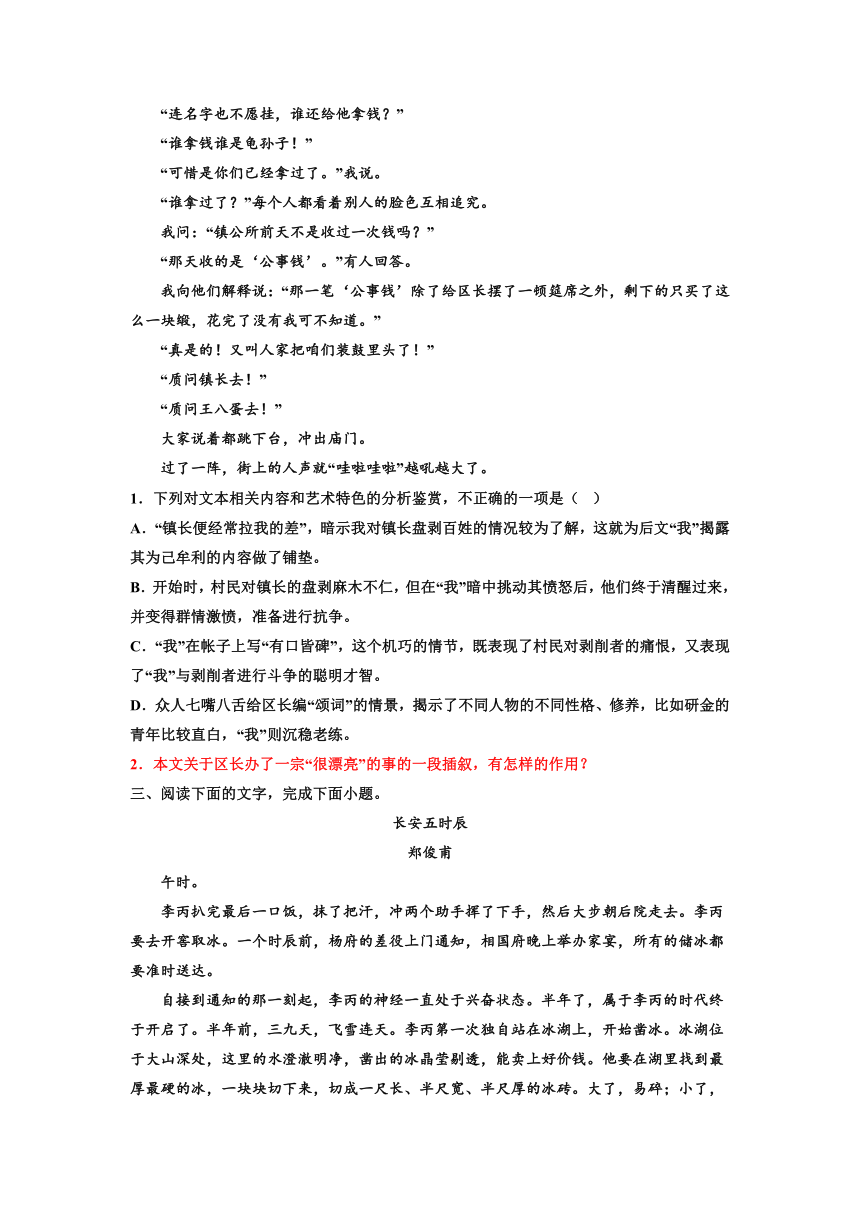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插叙的作用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旺杆子秤
杜官恩和宋红莲
祁嫂有一句口头禅,她挺喜欢说“差不多就行了”。
祁嫂没念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她领取农村田亩补助能签字,却不能看合同,只能请信得过的人帮她看。她能算账,但都是算的“婆婆姥姥”账。当着熟人的面,可以掐着指头算。当着外人的面,怕丢丑,只能默默心算。都只能算个大略谱,不出左右就行。
当年,如花似玉的祁嫂,找了一个黑黝黝的小伙子当对象。老公忠心耿耿,陪了她一辈子。最后是老公得错了病,无法医治,稍微有点过早地离开了她。
祁嫂来到女儿身边,帮女儿带孩子带到了读初中住校。祁嫂无事可干了,准备回乡下。
女儿挽留。祁嫂说:“反正我不想吃你的白饭。日子长了,你不说,女婿不说。但女婿有父母,你们有隔壁左右,他们不说闲话吗?”
女儿说:“要不,就在我的酱菜摊子旁边,跟您也弄一个摊子?”
祁嫂连连反对,“这不行不行,一年的摊子费好吓人。我害怕赚的还不够缴摊子费。”
女儿说:“有我替你撑着,不用担心。”
“那还不是在吃你的白饭吗?”
女儿不高兴了,“您老说吃我的白饭,那我小时候是吃谁的饭?”
祁嫂不说话了。
房屋不是码起钱砌的,生意不是算好了做的。赚钱不赚钱,先摆出架势再说。
祁嫂卖菜,不会算细账,肯定有些为难。她又不想处处依靠女儿。
女儿卖菜,全部经过一台电子秤,一斤一两不会多,一分一厘不会少。
她在乡下赶集卖小菜,鸡蛋论个卖,青菜论扎卖,鲊胡椒论碗卖……简单,利落。收钱都是大概数字,差个几角块把钱,不能算作错账。
祁嫂顶替女儿干过一次。女儿交代时,她听得一清二楚。实际干起来,一台电子秤,弄得她晕头转向。显示屏上,一会儿要显示斤数,一会儿要显示钱数,一会儿又要按钱数调节斤数。最后,她干脆就按照她的老经验,论捆论个地卖,她心里掂量着差不多就卖了。
到晚上清账,亏了几百元。女儿喊:“我的娘哎,您这是在把女儿往外面贴呢!”
自此,祁嫂就不再跟女儿顶班了,宁愿自己出蛮力干憨事。比如,送孩子上学,灌煤气坛子,她都抢着去。现在要她负责一个摊子,自负盈亏,压力还是有点大。
但眼下,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就像一条船放到了河里,不走也得走了。
女儿顺利盘下旁边的摊子,按照自己的菜品跟祁嫂“复制粘贴”了一份。
刚开始,祁嫂坐在摊子里,好长时间没有生意做。因为祁嫂使用不了电子秤,还是使着老式木杆铝盘秤,俗称“旺杆子秤”。一杆子进,百杆子出,一秤一旺,容易造成数量亏损。但顾客喜欢看旺杆子秤,秤杆子翘得越高心里越舒服。祁嫂收钱也依然采用以前的“差不多就行了”的策略,也被人称之为是“秤杆子翘得高高的”的做法。因为菜市场的摊子一般没有名号,顾客说起来会说某个特征。久而久之,顾客便直接将祁嫂本人以及摊子,呼成了“旺杆子秤”。
祁嫂的心态很平和。两个月下来,几乎是“保本”,不谈盈利。
女儿说:“吃了这么大的亏,没有赚到钱。说明您这根‘旺杆子秤’不行嘛,还得学会使用电子秤。”
祁嫂说:“那怎么办,我只会用旺杆子秤?”
女儿想了一会,知道强逼祁嫂也不行,便说:“就这么着也行,不亏就是赚。”
祁嫂按照自己的方式卖菜,过去将近一年,竟然慢慢积攒起了一些人气,光顾她摊子的顾客越来越多。
有时,女儿的摊子上,顾客寥寥无几,而祁嫂的摊子上挤成一堆。
女儿轻声朝顾客喊:“可以过来这边买,都是一样的。”
而那些听到喊声的顾客,也只是扭头望一眼,继续等候。
渐渐地,和女儿一起到批发市场进菜,祁嫂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从开始的百分之三十,慢慢增长到了百分之六七十,数量也在天天增加。
祁嫂以数量占优,渐渐赶上了女儿的收入,并实现了反超。
祁嫂在女儿面前“得意”起来。“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吧,还是我有道理吧?”
女儿说:“我是怕您太耗费体力了,受不住累。”
祁嫂说:“没事。力气是个憨子哥,今天少明天多。”
有祁嫂掺进来卖菜,进货量增加了一倍转弯,女婿原来开的电动三轮车装不下了。祁嫂和女儿一人出一半钱,购买了一辆一排半货车。
现在进货,祁嫂说了算。在生意上,她和女儿调换了个位子。原先是女儿帮她,现在是祁嫂帮女儿了。
进回来的货,也有了祁嫂的特色。能分装的尽量分装,能扎捆的尽量扎捆。祁嫂还是喜欢论捆卖,论袋卖。比如米酒,历史以来都是整盆子放在摊子上称斤数卖,而祁嫂却坚持要分装成一袋一袋卖。并且坚持每一份都留有旺头,旺头不多,一斤留个几钱儿。用旺杆子秤一称,量给顾客看时,数字好看,样子好看,脸上好看,都好看。
有时,祁嫂和女儿一干半夜。
祁嫂越干越有劲,反倒是女儿在劝了。“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劳累了。”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说祁嫂没念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这也为她算“婆婆姥姥”账找到了理由。
B.“房屋不是码起钱砌的,生意不是算好了做的”这一俗话在文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C.“那些听到喊声的顾客,也只是扭头望一眼”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祁嫂深得顾客喜欢,生意兴隆的状况。
D.“数字好看,样子好看,脸上好看,都好看”一句连用三个“好”,以小见大,写出了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
2.小说在中间插叙乡下赶集和祁嫂顶替女儿守过一次摊的事,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金字
赵树理
在乡村集镇教小学,教学以外的杂事很多:写神庙对联,村里人有了红白大事写请柬和灵牌,年关之前替穷人写卖契,替一般住户写春联……我在王店镇教小学,杂事比一般村镇更多,因为镇公所的书记每天只顾给镇长到遥远的山庄上催租逼债,镇长便经常拉我的差。在这种年头,为了不丢掉饭碗,不能得罪镇长,因此,我便得多吃一点苦。
一天,镇长交给我一卷缎子和一包泥金,要我替他写字,说区长被调升,镇上有个欢送的表示。按地方的习惯,每逢被提升的县、区长离任的时候,地方士绅便向老百姓收一笔线,请他吃顿饭,送些礼物。礼物是绸缎之类,写上几个恭维性质的金字,名叫“帐子”。“帐”字可能是“幛”字叫错了音,不过可以不必管它。
王店镇的学校设在一座汤帝庙里,冬天在厢房里上课,夏天常把课堂搬在正殿对面三丈见方的戏台上。这座戏台,每年只在秋收后唱一次戏,除此之外,冬天有些大户借它存干草,到夏天一方面作课堂用,另一方面有些住家离庙近的农民在后台和角落上铺着席子,午饭和晚饭后到上边乘凉休息,好在和上课时间不冲突,倒也能各尽其用。这天午上,我拿着镇长交给我的缎卷子、泥金包、白芨、粗瓷碗和两枝笔到台上去,一个青年爬起来问我:“先生,写帐子吗?我来帮你!”他这么一说,另外有几个人听了也起来看热闹。写“帐子”在这地方不算稀奇,大户人家做红白大事也有送“帐子”的。这位热心帮忙的青年有经验,并没有问我怎样做,就把泥金放在碗底,倒了一点水,用白芨研起来。
青年把金研好,我把缎卷子展开一抖,台上闪起一道红光,引得大家吃了一惊,凡是躺着还没有闭上眼睛的人,都爬起来看。
“这是什么缎?”几个人一起问。
“呀!跟闪电一样!”有一个人吃惊地夸赞。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缎,既然有人提到闪电:我便顺口说:“就叫它闪电缎吧!”
“给谁送?”有派人问。
“给区长!”我说。
“为什么?”
“区长要走了!”
“早就该走了!”“就不该来!”“去了是福!”……大家七嘴入舌议论起来。
我提起大笔在金里蘸着,就有人把缎子铺在桌面上,问我说:“先生,给他写几个什么字?”
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原来这位区长才来了三个月,因为办了一宗县里认为“很漂亮”的事,县里报了省府,省府就把他提升了。他办了什么“漂亮事”呢?去年春天,省府派了三次粮秣款,因为地方太穷苦,前任区长收不起款来被撤了职,而这位新区长一来,马上就想出了办法,办法全在于和王店镇镇长配合得紧密。这位镇长是全区的首户,全区大小村庄都有他放的债,都有押给他的地。新区长来了请他帮忙,他便出了主意,要区长把全区欠款户挨次传来,有钱的交钱,没钱的押地,他替欠户还款。区长听了他的话,用油印印了些押地字据,把欠户一一传来,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不填写字据不放走,果然从四月份上任,不到五月底就把欠款全部追清。这位区长就是因为办了这样一宗“漂亮的事”才被提升了的。对这样一位“漂亮区长”,该恭维他几个大字呢?我一时想不出主意来,便反问大家说:“你们说写什么好?”
那位研金的青年说:“写‘真会要钱’吧。”
“不好!不如写‘真会逼命’!”又一个人说。
“逼谁的命?不如写成‘逼死祖爷’更明白些。”又一个人说。
我笑了笑说:“你们都说得对,可是照谁说的写上去也保准出事!”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有人说:“还是由你写吧!”
由我又有什么好写的呢?还不得昧着良心说话吗?我怒了一阵,怒出个模棱两可的成语来,写了“有口皆碑”四个大字。
“先生!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区长的好处大家常常念道着哩。”
“对!哪个人,哪一天还不写他几遍王八蛋。”
我换了小笔去写上下款。这上下款都是镇长拟好了写在纸条子上的,我把纸条铺好正要写,那位研金的青年指着纸条上写的下款中的“全体镇民”几个字说:“怎么还要叫我们给他送帐子?”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瞪了眼。识字的念给不识的听,不识字的也火了!
“我们不捧他这催命鬼!”又一个人说。
“可是镇长要我这样写,我替人写个字,怎么好改呢?”我既然抗不过镇长,也只好当众说明不是我的意思。
还是那个青年说:“写了也不算!我不出钱!”他又向大家说:“谁也不要给他出钱!区长给镇长放了押地债,让镇长一家给他送帐子吧!”
“连名字也不愿挂,谁还给他拿钱?”
“谁拿钱谁是龟孙子!”
“可惜是你们已经拿过了。”我说。
“谁拿过了?”每个人都看着别人的脸色互相追究。
我问:“镇公所前天不是收过一次钱吗?”
“那天收的是‘公事钱’。”有人回答。
我向他们解释说:“那一笔‘公事钱’除了给区长摆了一顿筵席之外,剩下的只买了这么一块缎,花完了没有我可不知道。”
“真是的!又叫人家把咱们装鼓里头了!”
“质问镇长去!”
“质问王八蛋去!”
大家说着都跳下台,冲出庙门。
过了一阵,街上的人声就“哇啦哇啦”越吼越大了。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镇长便经常拉我的差”,暗示我对镇长盘剥百姓的情况较为了解,这就为后文“我”揭露其为己牟利的内容做了铺垫。
B.开始时,村民对镇长的盘剥麻木不仁,但在“我”暗中挑动其愤怒后,他们终于清醒过来,并变得群情激愤,准备进行抗争。
C.“我”在帐子上写“有口皆碑”,这个机巧的情节,既表现了村民对剥削者的痛恨,又表现了“我”与剥削者进行斗争的聪明才智。
D.众人七嘴八舌给区长编“颂词”的情景,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修养,比如研金的青年比较直白,“我”则沉稳老练。
2.本文关于区长办了一宗“很漂亮”的事的一段插叙,有怎样的作用?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长安五时辰
郑俊甫
午时。
李丙扒完最后一口饭,抹了把汗,冲两个助手挥了下手,然后大步朝后院走去。李丙要去开窖取冰。一个时辰前,杨府的差役上门通知,相国府晚上举办家宴,所有的储冰都要准时送达。
自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李丙的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半年了,属于李丙的时代终于开启了。半年前,三九天,飞雪连天。李丙第一次独自站在冰湖上,开始凿冰。冰湖位于大山深处,这里的水澄澈明净,凿出的冰晶莹剔透,能卖上好价钱。他要在湖里找到最厚最硬的冰,一块块切下来,切成一尺长、半尺宽、半尺厚的冰砖。大了,易碎;小了,浪费人工,还不易储存。
李丙生于储冰世家,祖上几代都以储冰为生。李丙的父亲也把这门手艺传给了李丙,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储冰是门手艺活,意要正,心要明,就像这冰一样,这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话,只有意正心明才能让冰晶莹齐缝。如果没有一年前雕冰场的那场意外,他现在应该还是跟在父亲的身后。那场意外带走了父亲,把他推到了台前。当时,他才19岁,日色玄黄,花树凋落。
院子不大,四周筑着高高的围墙,围墙边遍植槐树,绿荫遮天蔽日。房前廊下有两株海棠,矮矮小小,人人不当回事,“海棠?呸!”只有多年不第的李秀才,坐在两株海棠的前边,嘬着泥壶摇头晃脑,
“浓淡芳春满蜀乡,
半随风雨断莺肠。
浣花溪上堪惆怅,
子美无心为发扬。
株小花紧。前朝郑鹧鸪①责问得好呀。”
别人也摇着头,哂笑着走开了。父亲却很兴奋,不住说:株小花紧,株小花紧。
株小花紧,春天时能开硕大鲜红的花朵,一下子让整个院子生机勃勃。
冰窖就在海棠的前边,院子的中央,四四方方的土堆上,盖着一层厚厚的苇席,上面散着几片落叶。蝉声聒噪,正午的阳光因绿荫的遮挡,在园子里落下碎金似的斑点。
李丙和两个帮手在土堆边盘腿坐下。时辰已经算好,未时开挖,一个半时辰出冰,一个半时辰完成装车搬运,赶在戌时家宴开始前运到,一切刚好。一刻都早不得呀,三伏天,外头能热死个人。储冰一出窖,就开始融化,一滴一滴的水,就是一颗一颗的蚌珠、一粒一粒的金豆子。
李丙开始跟帮手唠叨,开窖和搬冰,看上去不过一件体力活儿,实际上处处都是技术。一着不慎,哗哗的钱就成了流水。好在帮手跟着李家已经干了多年,熟门熟路。李丙抬头看天,一丝笑意爬上嘴角。
未时。
开挖。李丙几乎是跳起来的,挖窖的工具在细碎的阳光里闪出一道弧线。冰窖在阴凉的地下——深挖五米的一口圆井,井下南北两面掏出一米见方的洞,下面用新鲜苇席铺垫,用以藏冰。冰砖摞满后,上面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再盖一层草毡,草毡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黄土,最后再用土把整个圆井密实地封起来。像这种民间建的冰窖,一个夏天只能打开一次。所以需要提前预约买主,预约量攒够了,才会开窖放冰。
不预约开窖取冰只有过一次。父亲去世前一年的夏天,李秀才母亲去世。李秀才家贫无以成殓,父亲出钱赙赠,七彩棺椁打从三十里外的崔家彩铺购进。崔家彩铺的棺椁讲究,木料从川陕深山购得,放置足十载才可开破。从定制而到家,需十天准头。那年父亲破例开窖取冰,贮存秀才母亲尸身。
申时。
开挖进展得很顺利,五米深的窖井很快见了底。外面的马车上摆上了冰鉴,冰鉴张着口,急迫地候着出窖的冰砖。全是花梨木,仿竹编式样,大口小底,外观如斗。苇席轻轻揭开,一股冰凉之气喷薄而出。冰窖中汗流浃背的三个人深深吸了口气,几乎同时大喊起来,每个毛孔都饱胀着欢快的情绪。
酉时。
车装好了,送冰。李丙紧紧抓着马缰绳,步子迈得小心翼翼,生怕车子颠簸。两个助手护在两边,防着路人靠近。李丙记得小时候,自己就做过护车的差事。父亲说:“遇到人流熙攘的街道,要学会把身子变成人墙,隔开路人身上的热气,也让车子走得顺畅些。”拉储冰的马车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裹得严实,可那冷气是裹不住的。大人还好些,难缠的是孩子。只要有淘气的打一声呼哨,大家就会飞蛾似的扑过去,拼命要把冷气吸进肚里。遇到实在躲不过的,父亲也有办法,他会在身上揣几枚钱币,掏出来,冲孩子们晃一晃。等到他们巴巴地跟过来,父亲手一扬,将几枚钱币抛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一窝蜂地去捡钱币,便离开了运冰的马车。
这一次还算顺利,李丙只丢撒了一次钱币,马车就稳稳地停在了相国府前。搬运冰鉴是差役的事,李丙要做的,是把冰砖摆成合适的样子。两个助手被拦在了门外,除了李丙,外人一律不准进去。以前,李丙跟着父亲,也是这样被拦在门外的。算起来,这也是李丙第一次迈进相府。
所有的冰鉴都摆在一个很大的亭子里,等待着主人的召唤。路上,李丙脑子里翻腾着无数冰砖的用途:切割成小块,含着吃;上面放果品、酒水,用以冰镇;最奢侈的,莫过于放置在客人手边,用来降温。最后才知道,整车的冰砖,都要从冰鉴里取出来,摞在亭子的一角,要摆成一座冰山,形状已经有了模板。亭子的另外三角,已经摆上了三座大块的冰雕,冰雕上嵌着造型各异的花灯。亭子四周还点缀着花花草草,假山峰峦叠翠。
父亲曾经做过各式冰雕。那年,却是被张公公的花斑狗蓦地冲咬,骇得跌落,肋部被一把冰剑刺穿而亡。李秀才对着海棠跌足捶胸,眼见着院子里那两株海棠萎落,只剩绿叶浓郁,再没有开过花。
李丙的脑子一时木然,直到结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了,窖藏半年的储冰,成了亭子一角堆叠的冰山。李丙看看脚下,还余两块冰砖。没等他开口,管家走过来,指指亭外一株海棠,轻描淡写地嘟囔了一句:“丢那儿吧。”
海棠树高大,绿叶婆娑。
李丙迟疑了一下,像是没听清。管家抻着脖子呵斥道:“宴会马上就开始了,还不麻溜点儿!误了时辰,公公怪罪,连老大人也吃罪不起不是!”
戌时。
走出相国府,李丙呆呆地靠着马车站着。相国府门前热闹起来,肥美的骏马晃人眼目。李丙听到了歌声,府内丝竹管弦之声此起彼伏。他忽然仰起头,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把身边两个满头大汗的助手吓了一跳。
亥时。
(摘编自《小小说选刊》)
注①:诗句出自《蜀中赏海棠》,作者郑谷,唐朝末期诗人,又以《鹧鸪诗》得名,人称郑鹧鸪。郑谷后“独守义命之戒,而不牵于名利之域”,毅然归隐故乡的仰山。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标题“长安五时辰”,时间是故事的时间主线,使小说的叙事有条不紊,适时出现的插叙又令叙事节奏灵活多变。
B.小说写了李丙给相国府送冰、李丙父亲的悲惨遭遇,以及李秀才的科举失意,三个故事层层套接,表达了共同的主题。
C.李丙父亲在运冰途中为避免出意外,向尾随的儿童抛撒钱币,也是他乐善好施的巧妙表现,丰富了李丙父亲的人物形象。
D.李丙在运冰途中脑子里翻腾着无数冰砖的用途,这一虚写,与现实中一年好冰被随意闲置对比,突出了权势阶层的奢靡。
2.请结合作品分析小说插叙李秀才吟咏前人诗句的作用。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唢呐
王宇
陈德广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向听话的儿子,竟然瞒着他,偷偷报考了艺术专业,并且在专业考试中,因为唢呐演奏,被省音乐学院录取了。
闷热的七月,太阳在半空中撒野,地上像着了火。陈德广吊着一张苦瓜脸,在屋里不停地兜圈,嘴里嗫嚅着:“儿大不由爹,要翻天了。”陈放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爹,大气不敢喘。
槐树沟男人爱吹唢呐,像是祖传的。农闲时,村头村尾,都是咿咿呀呀的唢呐声。爱吹,并不代表会吹;会吹,并不意味着能吹好。前沟的钟一鸣与后沟的陈德广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唢呐高手。陈德广吹唢呐花样多,用纸团塞一个鼻孔,会用另一个鼻孔吹唢呐。嘴里噙两个唢呐,能吹出两种不同的曲谱。玄绝的是,靠住墙,脚朝上,头杵地,倒立着,照样能吹。相比之下,钟一鸣就简单多了,眯上眼,鼓着腮帮子,悠扬沉稳,似乎只要有时间,一口气能从日出吹到日落。
乡下人婚丧嫁娶,都要请乐队。这两人各自组建团队,年头年尾,不间断地忙碌。有一次,陈德广和钟一鸣的两个唢呐团队在迎亲路上相遇了。看热闹的人不住撺掇,想让两个团队比一比,看谁更厉害。那会儿,他俩都年轻气盛,比就比,谁怕谁。陈德广唢呐上挑,锣鼓手心领神会。鼓面如撒了一碗青豆,骤然密集响起,从气势上压住对方。继而,陈德广鼻孔嘴唇轮番上阵,时不时来个倒栽葱,唢呐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折腾,都能吹出撩人的旋律,赢得一拨又一拨的掌声。再看钟一鸣那边,似乎渐入佳境,不急不躁,经典曲谱一个接一个涌出,如江河之水,不见尽头。热汗满面的陈德广心想,如再来一轮吹技表演,岂不让人笑话我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于是,陈德广憋着一口气,盯着钟一鸣对吹。
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两家迎亲的主事人,似乎忘了正事,并不着急要走。所有人从来没听过这么精彩的唢呐对决,就连晚归的羊群也站在路边,歪着脑袋,竖起耳朵,静静倾听。
吹奏到第十七个曲谱时,陈德广突觉心头一热,眼前发黑,一头杵在硬邦邦的黄土路上。槐树沟后沟离前沟并不远,事后,钟一鸣提着两瓶烧酒来到陈德广家,进门就说:“德广哥,你说咱俩干些啥事,你倒在地上,吓坏了我,以后可不敢这样了。”说着,拧开瓶盖,“今天不忙,咱哥俩喝上几杯。”陈德广似乎早就等钟一鸣过来,他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从堂柜里取出唢呐,一下狠似一下地砸在青石板做成的锅台上。“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吹唢呐了,我还要给我的子孙们说,谁也不许吹唢呐。”
钟一鸣眼看着唢呐碎了一地,站不是站,坐不是坐,搓着手,一时间不知怎么说才好。陈德广倒是不慌不忙,拧紧瓶盖,把两瓶酒塞进钟一鸣怀里,摆摆手,“不要再来我家了,我不想看见你。”
隔着窗纸,烫手的阳光进不了屋,可屋里屋外一样的闷热。陈德广来来回回不停地兜圈,口渴了,从水瓮里舀出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喝足了水,他转身问儿子:“是谁教你吹唢呐的?”陈放低着头,抠手指头,没说话。陈德广把水瓢扔进水瓮里,“快说,谁教的?”陈放怯生生地抬起头,看着窗棂,“是……是钟一鸣叔叔教我的。”陈德广听了儿子的话,瞪大眼,喘着粗气,抓起堂柜上的录取通知书,三下两下,撕得稀烂,扔进炉膛里。
上初中那年,陈放周末回槐树沟,一脚踏进沟口,就听见钟一鸣的唢呐声。陈放蹲在墙角,一曲一曲地听,听着听着,竟摇头晃脑,打着节奏,嘴里跟着哼曲谱,就像极度饥饿,闻到香喷喷的炖羊肉那么馋嘴。
也不知过了多久,钟一鸣蹲在陈放身边。
“好听?”
“好听!”
“想学?”
“想学。”
“你爹不让。”
“我偷着学。”
击掌,成交。钟一鸣笑了,陈放也笑了。至此,叔侄俩有了一个秘密约定,每个周末放学,陈放来钟一鸣家学吹唢呐。
太阳落坡,不见陈放回来,陈德广心里乱糟糟的,在院子里兜圈。忽闻敲门声,门口站着钟一鸣。
“你来干吗?”陈德广板着脸。
“喝酒。”钟一鸣轻咳一声,“还是那两瓶,一直没舍得喝。”
“不稀罕。”陈德广伸手就要关门,看见钟一鸣身后站着陈放,一惊,扭头回屋去了。钟一鸣跟着进屋,坐在炕沿儿上。
“你说,咱山里娃考音乐学院,容易吗?”
“我又没让他考音乐学院。”
“你真行,撕了录取通知书,这下陈放不用上学了。”
钟一鸣站起来,要走,陈德广拦在面前,“兄弟,想想办法,娃总得上学吧。”钟一鸣一脸无奈,“没办法。”
“兄弟,别急着走,咱喝酒。”说着,陈德广打开堂柜,胡乱翻腾。
“行了,别翻了,看看这是啥?”陈德广转过身,钟一鸣手里拿着一份崭新的录取通知书。陈德广惊呆了,“这,哪来的?”钟一鸣似笑非笑,“知道你这驴脾气,一准儿会撕了录取通知书,所以,我和陈放商量,事先准备了一份复制品。”
1.下列对小说修辞手法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太阳在半空中撒野”以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烈日当空,天气炎热的情景。
B.“爱吹,并不代表会吹;会吹,并不意味着能吹好”运用顶真,使句子结构整齐,语气贯通。
C.“程咬金的三板斧”采用了借代的手法,代指陈德广吹唢呐的技能有限,不能持久。
D.“就像极度饥饿,闻到香喷喷的炖羊肉那么馋嘴”用比喻表现陈放对学习唢呐的强烈渴望。
2.本文的插叙富有特点,请对其作用进行分析。
答案:
一、1、D“以小见大,写出了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错,“数字好看,样子好看,脸上好看,都好看”指的是祁嫂做生意,祁嫂和顾客都高兴,无法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选项过度解读。
2.①内容上:写出了乡下赶集做买卖简单,利落。祁嫂顶替女儿守过一次摊,按照她的老经验却亏了。②结构上:为下文祁嫂按照老经验做生意受到欢迎形成对比,使情节更完整,内容更充实。③人物塑造上:有助于表现祁嫂的行事作风与精神品质。(意思对即可)
二、1.B“开始时,村民对镇长的盘剥麻木不仁”错误,他们只是一开始不知道真相,并不是“麻木不仁”。
2.①内容上,这段插叙讲述了区长所做的“很漂亮”的事的具体情况,交代“我”写帐子一事的原委,使文章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②结构上,这段插叙上承写帐子之事以及青年的发问,下启“我”与村民的对话,引出了后文所述事件,使情节更加连贯,脉络更加清晰。③主旨上,这段插叙反映了一定的时代背景,揭露了地方官吏对乡民进行巧取豪夺的罪恶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主旨,深化了对罪恶势力的批判。④表达效果上,这段插叙利于读者理解文意,把握主旨。
三、1.C “他乐善好施的巧妙表现”理解错误,原文“父亲也有办法,他会在身上揣几枚钱币,掏出来,冲孩子们晃一晃。等到他们巴巴地跟过来,父亲手一扬,将几枚钱币抛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一窝蜂地去捡钱币,便离开了运冰的马车”,可知父亲撒钱是为了不让人群阻挡冰车的顺利前行,因为耽误一刻,冰就有消融的可能,一切劳作就没有了价值。
2.①李秀才在李丙家的海棠前吟咏前朝郑谷的海棠诗句既有对两株海棠的赞赏,更借郑谷对杜甫当年不歌咏海棠的遗憾,表达心中科考不顺的怨愤;②李秀才引用诗句,其实是将李丙父亲引为难得的知音,喻指二人有着相同傲岸的品性;③诗句中海棠的命运与结尾相国府的海棠互为反衬,暗示了李丙父亲的结局与李家储冰事业的命运。
四、1.C “程咬金的三板斧”不是借代,是比喻,比喻陈德广吹唢呐的技能有限,不能持久。2.(1)小说的插叙部分有两处,一是回顾陈德广和钟一鸣当年唢呐对决,陈德广落败,发誓再也不吹唢呐,二是陈冲偷偷向钟一鸣学习吹唢呐。(2)两次插叙交代了事情的前因,解答了读者的疑惑,使小说情节更加紧凑曲折;突出了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完整。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旺杆子秤
杜官恩和宋红莲
祁嫂有一句口头禅,她挺喜欢说“差不多就行了”。
祁嫂没念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她领取农村田亩补助能签字,却不能看合同,只能请信得过的人帮她看。她能算账,但都是算的“婆婆姥姥”账。当着熟人的面,可以掐着指头算。当着外人的面,怕丢丑,只能默默心算。都只能算个大略谱,不出左右就行。
当年,如花似玉的祁嫂,找了一个黑黝黝的小伙子当对象。老公忠心耿耿,陪了她一辈子。最后是老公得错了病,无法医治,稍微有点过早地离开了她。
祁嫂来到女儿身边,帮女儿带孩子带到了读初中住校。祁嫂无事可干了,准备回乡下。
女儿挽留。祁嫂说:“反正我不想吃你的白饭。日子长了,你不说,女婿不说。但女婿有父母,你们有隔壁左右,他们不说闲话吗?”
女儿说:“要不,就在我的酱菜摊子旁边,跟您也弄一个摊子?”
祁嫂连连反对,“这不行不行,一年的摊子费好吓人。我害怕赚的还不够缴摊子费。”
女儿说:“有我替你撑着,不用担心。”
“那还不是在吃你的白饭吗?”
女儿不高兴了,“您老说吃我的白饭,那我小时候是吃谁的饭?”
祁嫂不说话了。
房屋不是码起钱砌的,生意不是算好了做的。赚钱不赚钱,先摆出架势再说。
祁嫂卖菜,不会算细账,肯定有些为难。她又不想处处依靠女儿。
女儿卖菜,全部经过一台电子秤,一斤一两不会多,一分一厘不会少。
她在乡下赶集卖小菜,鸡蛋论个卖,青菜论扎卖,鲊胡椒论碗卖……简单,利落。收钱都是大概数字,差个几角块把钱,不能算作错账。
祁嫂顶替女儿干过一次。女儿交代时,她听得一清二楚。实际干起来,一台电子秤,弄得她晕头转向。显示屏上,一会儿要显示斤数,一会儿要显示钱数,一会儿又要按钱数调节斤数。最后,她干脆就按照她的老经验,论捆论个地卖,她心里掂量着差不多就卖了。
到晚上清账,亏了几百元。女儿喊:“我的娘哎,您这是在把女儿往外面贴呢!”
自此,祁嫂就不再跟女儿顶班了,宁愿自己出蛮力干憨事。比如,送孩子上学,灌煤气坛子,她都抢着去。现在要她负责一个摊子,自负盈亏,压力还是有点大。
但眼下,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就像一条船放到了河里,不走也得走了。
女儿顺利盘下旁边的摊子,按照自己的菜品跟祁嫂“复制粘贴”了一份。
刚开始,祁嫂坐在摊子里,好长时间没有生意做。因为祁嫂使用不了电子秤,还是使着老式木杆铝盘秤,俗称“旺杆子秤”。一杆子进,百杆子出,一秤一旺,容易造成数量亏损。但顾客喜欢看旺杆子秤,秤杆子翘得越高心里越舒服。祁嫂收钱也依然采用以前的“差不多就行了”的策略,也被人称之为是“秤杆子翘得高高的”的做法。因为菜市场的摊子一般没有名号,顾客说起来会说某个特征。久而久之,顾客便直接将祁嫂本人以及摊子,呼成了“旺杆子秤”。
祁嫂的心态很平和。两个月下来,几乎是“保本”,不谈盈利。
女儿说:“吃了这么大的亏,没有赚到钱。说明您这根‘旺杆子秤’不行嘛,还得学会使用电子秤。”
祁嫂说:“那怎么办,我只会用旺杆子秤?”
女儿想了一会,知道强逼祁嫂也不行,便说:“就这么着也行,不亏就是赚。”
祁嫂按照自己的方式卖菜,过去将近一年,竟然慢慢积攒起了一些人气,光顾她摊子的顾客越来越多。
有时,女儿的摊子上,顾客寥寥无几,而祁嫂的摊子上挤成一堆。
女儿轻声朝顾客喊:“可以过来这边买,都是一样的。”
而那些听到喊声的顾客,也只是扭头望一眼,继续等候。
渐渐地,和女儿一起到批发市场进菜,祁嫂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从开始的百分之三十,慢慢增长到了百分之六七十,数量也在天天增加。
祁嫂以数量占优,渐渐赶上了女儿的收入,并实现了反超。
祁嫂在女儿面前“得意”起来。“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吧,还是我有道理吧?”
女儿说:“我是怕您太耗费体力了,受不住累。”
祁嫂说:“没事。力气是个憨子哥,今天少明天多。”
有祁嫂掺进来卖菜,进货量增加了一倍转弯,女婿原来开的电动三轮车装不下了。祁嫂和女儿一人出一半钱,购买了一辆一排半货车。
现在进货,祁嫂说了算。在生意上,她和女儿调换了个位子。原先是女儿帮她,现在是祁嫂帮女儿了。
进回来的货,也有了祁嫂的特色。能分装的尽量分装,能扎捆的尽量扎捆。祁嫂还是喜欢论捆卖,论袋卖。比如米酒,历史以来都是整盆子放在摊子上称斤数卖,而祁嫂却坚持要分装成一袋一袋卖。并且坚持每一份都留有旺头,旺头不多,一斤留个几钱儿。用旺杆子秤一称,量给顾客看时,数字好看,样子好看,脸上好看,都好看。
有时,祁嫂和女儿一干半夜。
祁嫂越干越有劲,反倒是女儿在劝了。“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劳累了。”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说祁嫂没念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几个阿拉伯数字。这也为她算“婆婆姥姥”账找到了理由。
B.“房屋不是码起钱砌的,生意不是算好了做的”这一俗话在文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C.“那些听到喊声的顾客,也只是扭头望一眼”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祁嫂深得顾客喜欢,生意兴隆的状况。
D.“数字好看,样子好看,脸上好看,都好看”一句连用三个“好”,以小见大,写出了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
2.小说在中间插叙乡下赶集和祁嫂顶替女儿守过一次摊的事,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金字
赵树理
在乡村集镇教小学,教学以外的杂事很多:写神庙对联,村里人有了红白大事写请柬和灵牌,年关之前替穷人写卖契,替一般住户写春联……我在王店镇教小学,杂事比一般村镇更多,因为镇公所的书记每天只顾给镇长到遥远的山庄上催租逼债,镇长便经常拉我的差。在这种年头,为了不丢掉饭碗,不能得罪镇长,因此,我便得多吃一点苦。
一天,镇长交给我一卷缎子和一包泥金,要我替他写字,说区长被调升,镇上有个欢送的表示。按地方的习惯,每逢被提升的县、区长离任的时候,地方士绅便向老百姓收一笔线,请他吃顿饭,送些礼物。礼物是绸缎之类,写上几个恭维性质的金字,名叫“帐子”。“帐”字可能是“幛”字叫错了音,不过可以不必管它。
王店镇的学校设在一座汤帝庙里,冬天在厢房里上课,夏天常把课堂搬在正殿对面三丈见方的戏台上。这座戏台,每年只在秋收后唱一次戏,除此之外,冬天有些大户借它存干草,到夏天一方面作课堂用,另一方面有些住家离庙近的农民在后台和角落上铺着席子,午饭和晚饭后到上边乘凉休息,好在和上课时间不冲突,倒也能各尽其用。这天午上,我拿着镇长交给我的缎卷子、泥金包、白芨、粗瓷碗和两枝笔到台上去,一个青年爬起来问我:“先生,写帐子吗?我来帮你!”他这么一说,另外有几个人听了也起来看热闹。写“帐子”在这地方不算稀奇,大户人家做红白大事也有送“帐子”的。这位热心帮忙的青年有经验,并没有问我怎样做,就把泥金放在碗底,倒了一点水,用白芨研起来。
青年把金研好,我把缎卷子展开一抖,台上闪起一道红光,引得大家吃了一惊,凡是躺着还没有闭上眼睛的人,都爬起来看。
“这是什么缎?”几个人一起问。
“呀!跟闪电一样!”有一个人吃惊地夸赞。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缎,既然有人提到闪电:我便顺口说:“就叫它闪电缎吧!”
“给谁送?”有派人问。
“给区长!”我说。
“为什么?”
“区长要走了!”
“早就该走了!”“就不该来!”“去了是福!”……大家七嘴入舌议论起来。
我提起大笔在金里蘸着,就有人把缎子铺在桌面上,问我说:“先生,给他写几个什么字?”
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原来这位区长才来了三个月,因为办了一宗县里认为“很漂亮”的事,县里报了省府,省府就把他提升了。他办了什么“漂亮事”呢?去年春天,省府派了三次粮秣款,因为地方太穷苦,前任区长收不起款来被撤了职,而这位新区长一来,马上就想出了办法,办法全在于和王店镇镇长配合得紧密。这位镇长是全区的首户,全区大小村庄都有他放的债,都有押给他的地。新区长来了请他帮忙,他便出了主意,要区长把全区欠款户挨次传来,有钱的交钱,没钱的押地,他替欠户还款。区长听了他的话,用油印印了些押地字据,把欠户一一传来,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不填写字据不放走,果然从四月份上任,不到五月底就把欠款全部追清。这位区长就是因为办了这样一宗“漂亮的事”才被提升了的。对这样一位“漂亮区长”,该恭维他几个大字呢?我一时想不出主意来,便反问大家说:“你们说写什么好?”
那位研金的青年说:“写‘真会要钱’吧。”
“不好!不如写‘真会逼命’!”又一个人说。
“逼谁的命?不如写成‘逼死祖爷’更明白些。”又一个人说。
我笑了笑说:“你们都说得对,可是照谁说的写上去也保准出事!”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有人说:“还是由你写吧!”
由我又有什么好写的呢?还不得昧着良心说话吗?我怒了一阵,怒出个模棱两可的成语来,写了“有口皆碑”四个大字。
“先生!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区长的好处大家常常念道着哩。”
“对!哪个人,哪一天还不写他几遍王八蛋。”
我换了小笔去写上下款。这上下款都是镇长拟好了写在纸条子上的,我把纸条铺好正要写,那位研金的青年指着纸条上写的下款中的“全体镇民”几个字说:“怎么还要叫我们给他送帐子?”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瞪了眼。识字的念给不识的听,不识字的也火了!
“我们不捧他这催命鬼!”又一个人说。
“可是镇长要我这样写,我替人写个字,怎么好改呢?”我既然抗不过镇长,也只好当众说明不是我的意思。
还是那个青年说:“写了也不算!我不出钱!”他又向大家说:“谁也不要给他出钱!区长给镇长放了押地债,让镇长一家给他送帐子吧!”
“连名字也不愿挂,谁还给他拿钱?”
“谁拿钱谁是龟孙子!”
“可惜是你们已经拿过了。”我说。
“谁拿过了?”每个人都看着别人的脸色互相追究。
我问:“镇公所前天不是收过一次钱吗?”
“那天收的是‘公事钱’。”有人回答。
我向他们解释说:“那一笔‘公事钱’除了给区长摆了一顿筵席之外,剩下的只买了这么一块缎,花完了没有我可不知道。”
“真是的!又叫人家把咱们装鼓里头了!”
“质问镇长去!”
“质问王八蛋去!”
大家说着都跳下台,冲出庙门。
过了一阵,街上的人声就“哇啦哇啦”越吼越大了。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镇长便经常拉我的差”,暗示我对镇长盘剥百姓的情况较为了解,这就为后文“我”揭露其为己牟利的内容做了铺垫。
B.开始时,村民对镇长的盘剥麻木不仁,但在“我”暗中挑动其愤怒后,他们终于清醒过来,并变得群情激愤,准备进行抗争。
C.“我”在帐子上写“有口皆碑”,这个机巧的情节,既表现了村民对剥削者的痛恨,又表现了“我”与剥削者进行斗争的聪明才智。
D.众人七嘴八舌给区长编“颂词”的情景,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修养,比如研金的青年比较直白,“我”则沉稳老练。
2.本文关于区长办了一宗“很漂亮”的事的一段插叙,有怎样的作用?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长安五时辰
郑俊甫
午时。
李丙扒完最后一口饭,抹了把汗,冲两个助手挥了下手,然后大步朝后院走去。李丙要去开窖取冰。一个时辰前,杨府的差役上门通知,相国府晚上举办家宴,所有的储冰都要准时送达。
自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李丙的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半年了,属于李丙的时代终于开启了。半年前,三九天,飞雪连天。李丙第一次独自站在冰湖上,开始凿冰。冰湖位于大山深处,这里的水澄澈明净,凿出的冰晶莹剔透,能卖上好价钱。他要在湖里找到最厚最硬的冰,一块块切下来,切成一尺长、半尺宽、半尺厚的冰砖。大了,易碎;小了,浪费人工,还不易储存。
李丙生于储冰世家,祖上几代都以储冰为生。李丙的父亲也把这门手艺传给了李丙,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储冰是门手艺活,意要正,心要明,就像这冰一样,这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话,只有意正心明才能让冰晶莹齐缝。如果没有一年前雕冰场的那场意外,他现在应该还是跟在父亲的身后。那场意外带走了父亲,把他推到了台前。当时,他才19岁,日色玄黄,花树凋落。
院子不大,四周筑着高高的围墙,围墙边遍植槐树,绿荫遮天蔽日。房前廊下有两株海棠,矮矮小小,人人不当回事,“海棠?呸!”只有多年不第的李秀才,坐在两株海棠的前边,嘬着泥壶摇头晃脑,
“浓淡芳春满蜀乡,
半随风雨断莺肠。
浣花溪上堪惆怅,
子美无心为发扬。
株小花紧。前朝郑鹧鸪①责问得好呀。”
别人也摇着头,哂笑着走开了。父亲却很兴奋,不住说:株小花紧,株小花紧。
株小花紧,春天时能开硕大鲜红的花朵,一下子让整个院子生机勃勃。
冰窖就在海棠的前边,院子的中央,四四方方的土堆上,盖着一层厚厚的苇席,上面散着几片落叶。蝉声聒噪,正午的阳光因绿荫的遮挡,在园子里落下碎金似的斑点。
李丙和两个帮手在土堆边盘腿坐下。时辰已经算好,未时开挖,一个半时辰出冰,一个半时辰完成装车搬运,赶在戌时家宴开始前运到,一切刚好。一刻都早不得呀,三伏天,外头能热死个人。储冰一出窖,就开始融化,一滴一滴的水,就是一颗一颗的蚌珠、一粒一粒的金豆子。
李丙开始跟帮手唠叨,开窖和搬冰,看上去不过一件体力活儿,实际上处处都是技术。一着不慎,哗哗的钱就成了流水。好在帮手跟着李家已经干了多年,熟门熟路。李丙抬头看天,一丝笑意爬上嘴角。
未时。
开挖。李丙几乎是跳起来的,挖窖的工具在细碎的阳光里闪出一道弧线。冰窖在阴凉的地下——深挖五米的一口圆井,井下南北两面掏出一米见方的洞,下面用新鲜苇席铺垫,用以藏冰。冰砖摞满后,上面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再盖一层草毡,草毡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黄土,最后再用土把整个圆井密实地封起来。像这种民间建的冰窖,一个夏天只能打开一次。所以需要提前预约买主,预约量攒够了,才会开窖放冰。
不预约开窖取冰只有过一次。父亲去世前一年的夏天,李秀才母亲去世。李秀才家贫无以成殓,父亲出钱赙赠,七彩棺椁打从三十里外的崔家彩铺购进。崔家彩铺的棺椁讲究,木料从川陕深山购得,放置足十载才可开破。从定制而到家,需十天准头。那年父亲破例开窖取冰,贮存秀才母亲尸身。
申时。
开挖进展得很顺利,五米深的窖井很快见了底。外面的马车上摆上了冰鉴,冰鉴张着口,急迫地候着出窖的冰砖。全是花梨木,仿竹编式样,大口小底,外观如斗。苇席轻轻揭开,一股冰凉之气喷薄而出。冰窖中汗流浃背的三个人深深吸了口气,几乎同时大喊起来,每个毛孔都饱胀着欢快的情绪。
酉时。
车装好了,送冰。李丙紧紧抓着马缰绳,步子迈得小心翼翼,生怕车子颠簸。两个助手护在两边,防着路人靠近。李丙记得小时候,自己就做过护车的差事。父亲说:“遇到人流熙攘的街道,要学会把身子变成人墙,隔开路人身上的热气,也让车子走得顺畅些。”拉储冰的马车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裹得严实,可那冷气是裹不住的。大人还好些,难缠的是孩子。只要有淘气的打一声呼哨,大家就会飞蛾似的扑过去,拼命要把冷气吸进肚里。遇到实在躲不过的,父亲也有办法,他会在身上揣几枚钱币,掏出来,冲孩子们晃一晃。等到他们巴巴地跟过来,父亲手一扬,将几枚钱币抛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一窝蜂地去捡钱币,便离开了运冰的马车。
这一次还算顺利,李丙只丢撒了一次钱币,马车就稳稳地停在了相国府前。搬运冰鉴是差役的事,李丙要做的,是把冰砖摆成合适的样子。两个助手被拦在了门外,除了李丙,外人一律不准进去。以前,李丙跟着父亲,也是这样被拦在门外的。算起来,这也是李丙第一次迈进相府。
所有的冰鉴都摆在一个很大的亭子里,等待着主人的召唤。路上,李丙脑子里翻腾着无数冰砖的用途:切割成小块,含着吃;上面放果品、酒水,用以冰镇;最奢侈的,莫过于放置在客人手边,用来降温。最后才知道,整车的冰砖,都要从冰鉴里取出来,摞在亭子的一角,要摆成一座冰山,形状已经有了模板。亭子的另外三角,已经摆上了三座大块的冰雕,冰雕上嵌着造型各异的花灯。亭子四周还点缀着花花草草,假山峰峦叠翠。
父亲曾经做过各式冰雕。那年,却是被张公公的花斑狗蓦地冲咬,骇得跌落,肋部被一把冰剑刺穿而亡。李秀才对着海棠跌足捶胸,眼见着院子里那两株海棠萎落,只剩绿叶浓郁,再没有开过花。
李丙的脑子一时木然,直到结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了,窖藏半年的储冰,成了亭子一角堆叠的冰山。李丙看看脚下,还余两块冰砖。没等他开口,管家走过来,指指亭外一株海棠,轻描淡写地嘟囔了一句:“丢那儿吧。”
海棠树高大,绿叶婆娑。
李丙迟疑了一下,像是没听清。管家抻着脖子呵斥道:“宴会马上就开始了,还不麻溜点儿!误了时辰,公公怪罪,连老大人也吃罪不起不是!”
戌时。
走出相国府,李丙呆呆地靠着马车站着。相国府门前热闹起来,肥美的骏马晃人眼目。李丙听到了歌声,府内丝竹管弦之声此起彼伏。他忽然仰起头,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把身边两个满头大汗的助手吓了一跳。
亥时。
(摘编自《小小说选刊》)
注①:诗句出自《蜀中赏海棠》,作者郑谷,唐朝末期诗人,又以《鹧鸪诗》得名,人称郑鹧鸪。郑谷后“独守义命之戒,而不牵于名利之域”,毅然归隐故乡的仰山。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标题“长安五时辰”,时间是故事的时间主线,使小说的叙事有条不紊,适时出现的插叙又令叙事节奏灵活多变。
B.小说写了李丙给相国府送冰、李丙父亲的悲惨遭遇,以及李秀才的科举失意,三个故事层层套接,表达了共同的主题。
C.李丙父亲在运冰途中为避免出意外,向尾随的儿童抛撒钱币,也是他乐善好施的巧妙表现,丰富了李丙父亲的人物形象。
D.李丙在运冰途中脑子里翻腾着无数冰砖的用途,这一虚写,与现实中一年好冰被随意闲置对比,突出了权势阶层的奢靡。
2.请结合作品分析小说插叙李秀才吟咏前人诗句的作用。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唢呐
王宇
陈德广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向听话的儿子,竟然瞒着他,偷偷报考了艺术专业,并且在专业考试中,因为唢呐演奏,被省音乐学院录取了。
闷热的七月,太阳在半空中撒野,地上像着了火。陈德广吊着一张苦瓜脸,在屋里不停地兜圈,嘴里嗫嚅着:“儿大不由爹,要翻天了。”陈放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爹,大气不敢喘。
槐树沟男人爱吹唢呐,像是祖传的。农闲时,村头村尾,都是咿咿呀呀的唢呐声。爱吹,并不代表会吹;会吹,并不意味着能吹好。前沟的钟一鸣与后沟的陈德广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唢呐高手。陈德广吹唢呐花样多,用纸团塞一个鼻孔,会用另一个鼻孔吹唢呐。嘴里噙两个唢呐,能吹出两种不同的曲谱。玄绝的是,靠住墙,脚朝上,头杵地,倒立着,照样能吹。相比之下,钟一鸣就简单多了,眯上眼,鼓着腮帮子,悠扬沉稳,似乎只要有时间,一口气能从日出吹到日落。
乡下人婚丧嫁娶,都要请乐队。这两人各自组建团队,年头年尾,不间断地忙碌。有一次,陈德广和钟一鸣的两个唢呐团队在迎亲路上相遇了。看热闹的人不住撺掇,想让两个团队比一比,看谁更厉害。那会儿,他俩都年轻气盛,比就比,谁怕谁。陈德广唢呐上挑,锣鼓手心领神会。鼓面如撒了一碗青豆,骤然密集响起,从气势上压住对方。继而,陈德广鼻孔嘴唇轮番上阵,时不时来个倒栽葱,唢呐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折腾,都能吹出撩人的旋律,赢得一拨又一拨的掌声。再看钟一鸣那边,似乎渐入佳境,不急不躁,经典曲谱一个接一个涌出,如江河之水,不见尽头。热汗满面的陈德广心想,如再来一轮吹技表演,岂不让人笑话我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于是,陈德广憋着一口气,盯着钟一鸣对吹。
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两家迎亲的主事人,似乎忘了正事,并不着急要走。所有人从来没听过这么精彩的唢呐对决,就连晚归的羊群也站在路边,歪着脑袋,竖起耳朵,静静倾听。
吹奏到第十七个曲谱时,陈德广突觉心头一热,眼前发黑,一头杵在硬邦邦的黄土路上。槐树沟后沟离前沟并不远,事后,钟一鸣提着两瓶烧酒来到陈德广家,进门就说:“德广哥,你说咱俩干些啥事,你倒在地上,吓坏了我,以后可不敢这样了。”说着,拧开瓶盖,“今天不忙,咱哥俩喝上几杯。”陈德广似乎早就等钟一鸣过来,他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从堂柜里取出唢呐,一下狠似一下地砸在青石板做成的锅台上。“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吹唢呐了,我还要给我的子孙们说,谁也不许吹唢呐。”
钟一鸣眼看着唢呐碎了一地,站不是站,坐不是坐,搓着手,一时间不知怎么说才好。陈德广倒是不慌不忙,拧紧瓶盖,把两瓶酒塞进钟一鸣怀里,摆摆手,“不要再来我家了,我不想看见你。”
隔着窗纸,烫手的阳光进不了屋,可屋里屋外一样的闷热。陈德广来来回回不停地兜圈,口渴了,从水瓮里舀出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喝足了水,他转身问儿子:“是谁教你吹唢呐的?”陈放低着头,抠手指头,没说话。陈德广把水瓢扔进水瓮里,“快说,谁教的?”陈放怯生生地抬起头,看着窗棂,“是……是钟一鸣叔叔教我的。”陈德广听了儿子的话,瞪大眼,喘着粗气,抓起堂柜上的录取通知书,三下两下,撕得稀烂,扔进炉膛里。
上初中那年,陈放周末回槐树沟,一脚踏进沟口,就听见钟一鸣的唢呐声。陈放蹲在墙角,一曲一曲地听,听着听着,竟摇头晃脑,打着节奏,嘴里跟着哼曲谱,就像极度饥饿,闻到香喷喷的炖羊肉那么馋嘴。
也不知过了多久,钟一鸣蹲在陈放身边。
“好听?”
“好听!”
“想学?”
“想学。”
“你爹不让。”
“我偷着学。”
击掌,成交。钟一鸣笑了,陈放也笑了。至此,叔侄俩有了一个秘密约定,每个周末放学,陈放来钟一鸣家学吹唢呐。
太阳落坡,不见陈放回来,陈德广心里乱糟糟的,在院子里兜圈。忽闻敲门声,门口站着钟一鸣。
“你来干吗?”陈德广板着脸。
“喝酒。”钟一鸣轻咳一声,“还是那两瓶,一直没舍得喝。”
“不稀罕。”陈德广伸手就要关门,看见钟一鸣身后站着陈放,一惊,扭头回屋去了。钟一鸣跟着进屋,坐在炕沿儿上。
“你说,咱山里娃考音乐学院,容易吗?”
“我又没让他考音乐学院。”
“你真行,撕了录取通知书,这下陈放不用上学了。”
钟一鸣站起来,要走,陈德广拦在面前,“兄弟,想想办法,娃总得上学吧。”钟一鸣一脸无奈,“没办法。”
“兄弟,别急着走,咱喝酒。”说着,陈德广打开堂柜,胡乱翻腾。
“行了,别翻了,看看这是啥?”陈德广转过身,钟一鸣手里拿着一份崭新的录取通知书。陈德广惊呆了,“这,哪来的?”钟一鸣似笑非笑,“知道你这驴脾气,一准儿会撕了录取通知书,所以,我和陈放商量,事先准备了一份复制品。”
1.下列对小说修辞手法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太阳在半空中撒野”以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烈日当空,天气炎热的情景。
B.“爱吹,并不代表会吹;会吹,并不意味着能吹好”运用顶真,使句子结构整齐,语气贯通。
C.“程咬金的三板斧”采用了借代的手法,代指陈德广吹唢呐的技能有限,不能持久。
D.“就像极度饥饿,闻到香喷喷的炖羊肉那么馋嘴”用比喻表现陈放对学习唢呐的强烈渴望。
2.本文的插叙富有特点,请对其作用进行分析。
答案:
一、1、D“以小见大,写出了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错,“数字好看,样子好看,脸上好看,都好看”指的是祁嫂做生意,祁嫂和顾客都高兴,无法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美好景象。选项过度解读。
2.①内容上:写出了乡下赶集做买卖简单,利落。祁嫂顶替女儿守过一次摊,按照她的老经验却亏了。②结构上:为下文祁嫂按照老经验做生意受到欢迎形成对比,使情节更完整,内容更充实。③人物塑造上:有助于表现祁嫂的行事作风与精神品质。(意思对即可)
二、1.B“开始时,村民对镇长的盘剥麻木不仁”错误,他们只是一开始不知道真相,并不是“麻木不仁”。
2.①内容上,这段插叙讲述了区长所做的“很漂亮”的事的具体情况,交代“我”写帐子一事的原委,使文章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②结构上,这段插叙上承写帐子之事以及青年的发问,下启“我”与村民的对话,引出了后文所述事件,使情节更加连贯,脉络更加清晰。③主旨上,这段插叙反映了一定的时代背景,揭露了地方官吏对乡民进行巧取豪夺的罪恶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主旨,深化了对罪恶势力的批判。④表达效果上,这段插叙利于读者理解文意,把握主旨。
三、1.C “他乐善好施的巧妙表现”理解错误,原文“父亲也有办法,他会在身上揣几枚钱币,掏出来,冲孩子们晃一晃。等到他们巴巴地跟过来,父亲手一扬,将几枚钱币抛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一窝蜂地去捡钱币,便离开了运冰的马车”,可知父亲撒钱是为了不让人群阻挡冰车的顺利前行,因为耽误一刻,冰就有消融的可能,一切劳作就没有了价值。
2.①李秀才在李丙家的海棠前吟咏前朝郑谷的海棠诗句既有对两株海棠的赞赏,更借郑谷对杜甫当年不歌咏海棠的遗憾,表达心中科考不顺的怨愤;②李秀才引用诗句,其实是将李丙父亲引为难得的知音,喻指二人有着相同傲岸的品性;③诗句中海棠的命运与结尾相国府的海棠互为反衬,暗示了李丙父亲的结局与李家储冰事业的命运。
四、1.C “程咬金的三板斧”不是借代,是比喻,比喻陈德广吹唢呐的技能有限,不能持久。2.(1)小说的插叙部分有两处,一是回顾陈德广和钟一鸣当年唢呐对决,陈德广落败,发誓再也不吹唢呐,二是陈冲偷偷向钟一鸣学习吹唢呐。(2)两次插叙交代了事情的前因,解答了读者的疑惑,使小说情节更加紧凑曲折;突出了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