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人物语言描写(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人物语言描写(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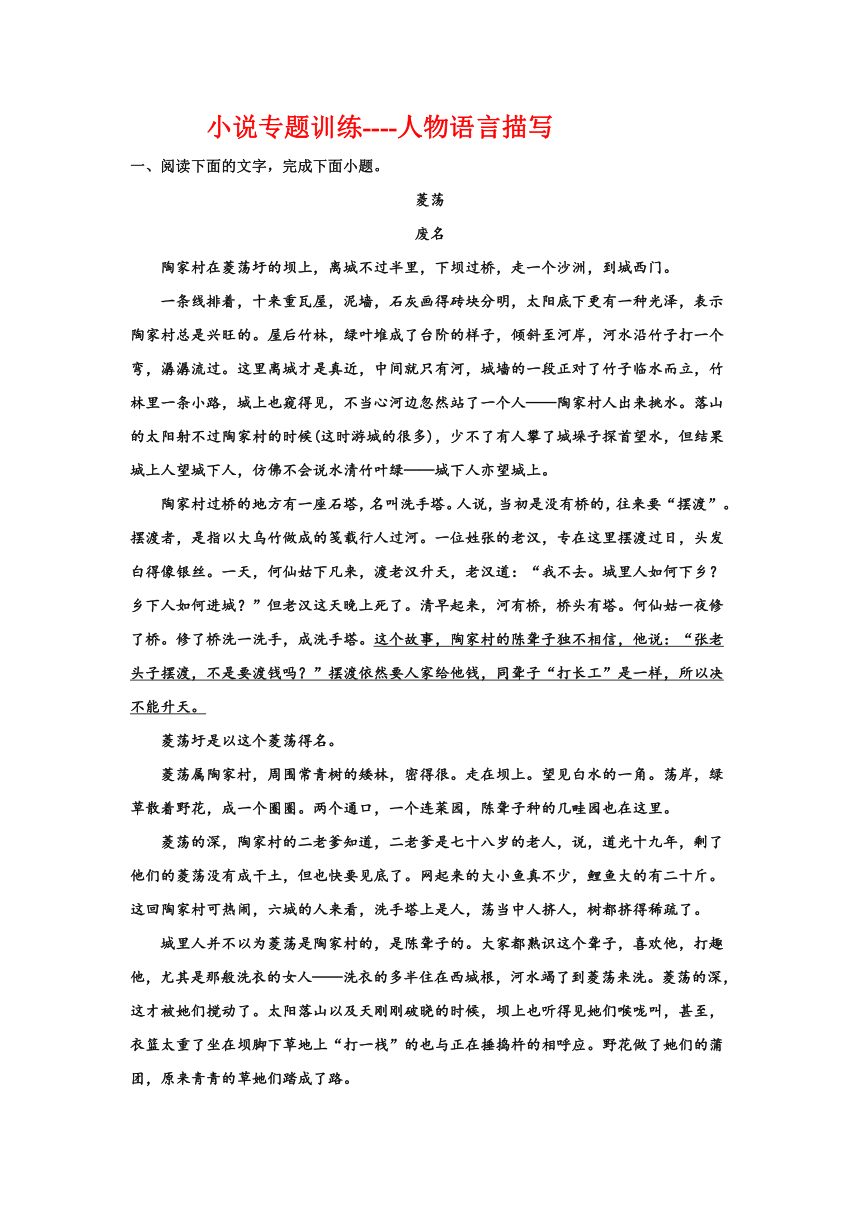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5.4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1-12 17:35:35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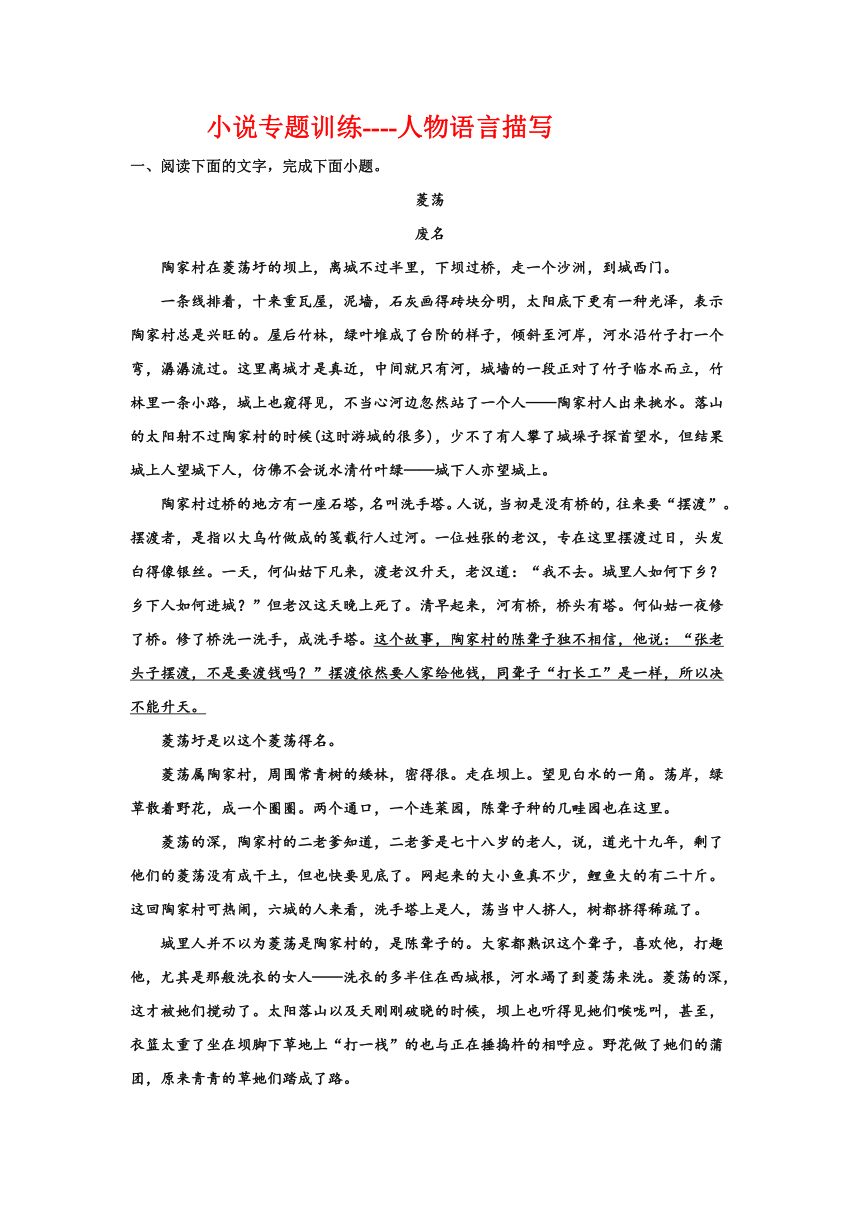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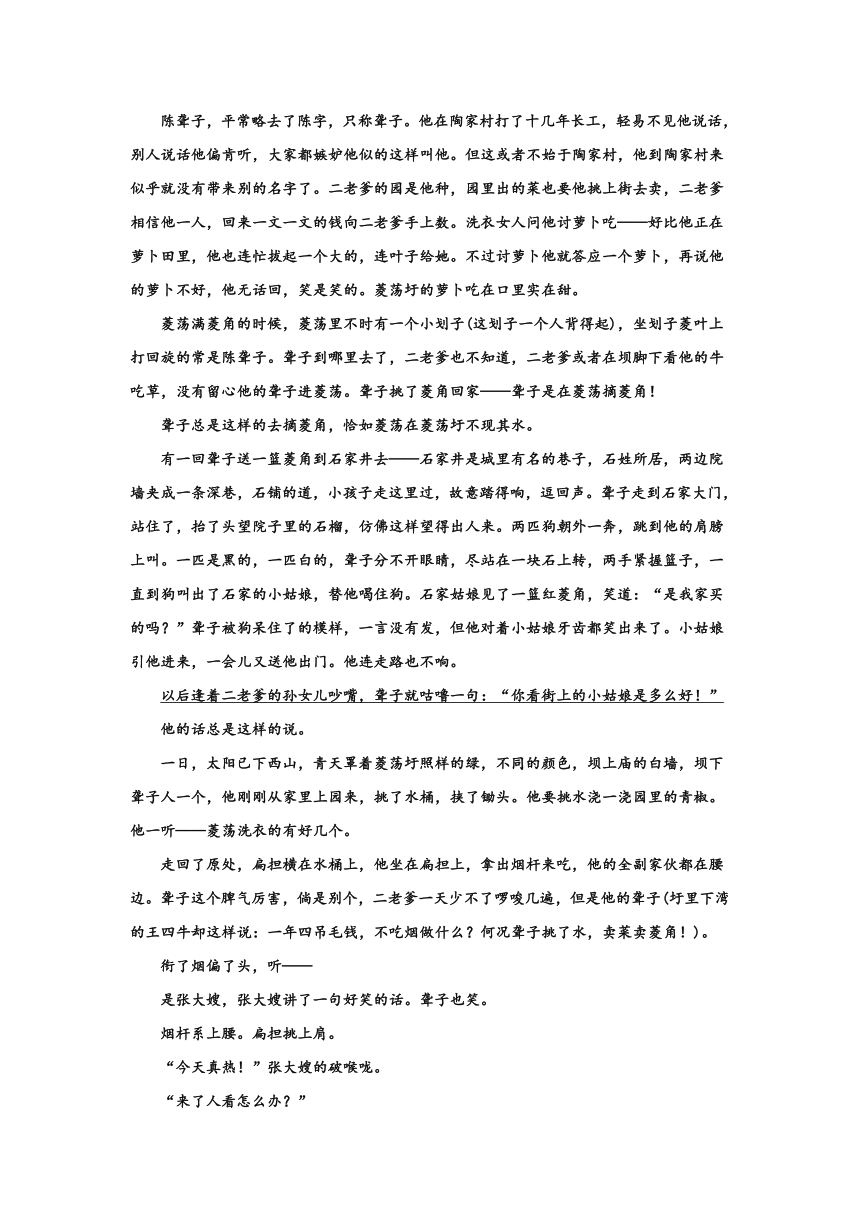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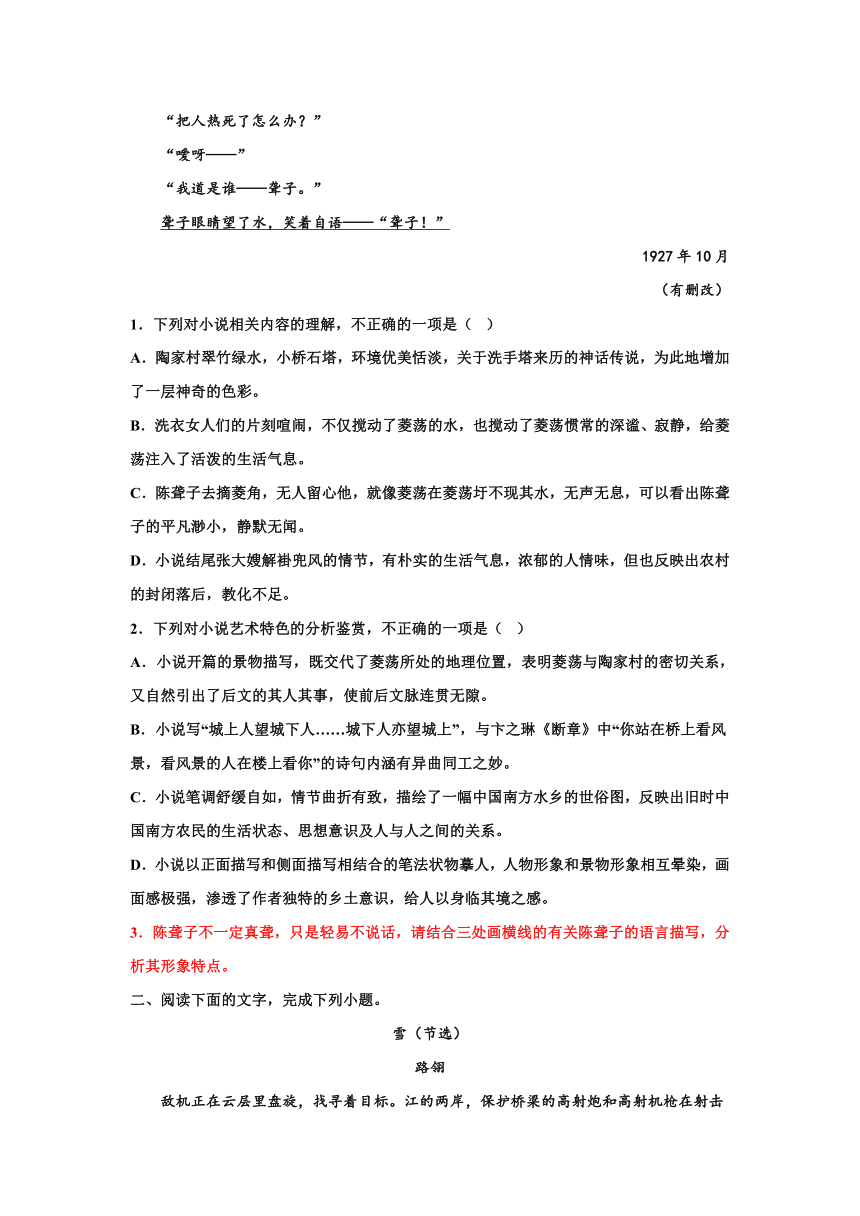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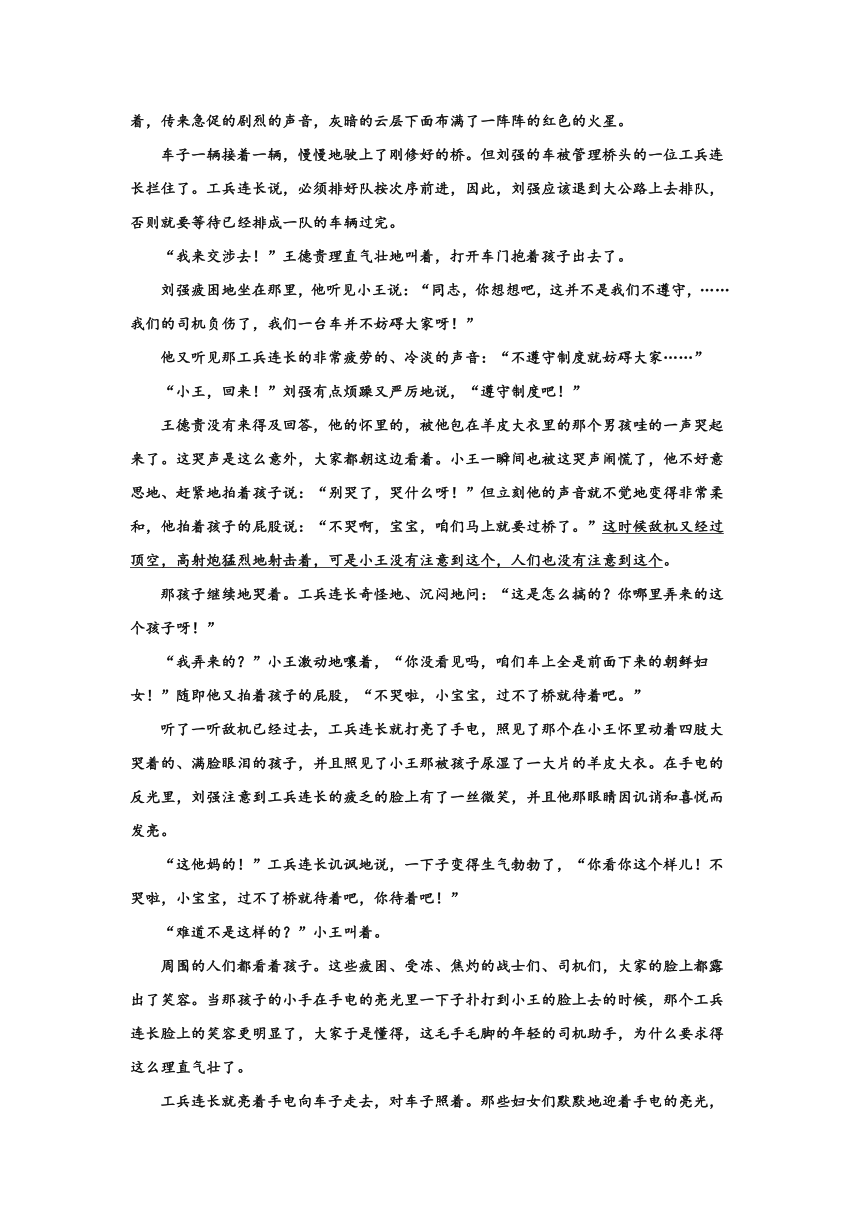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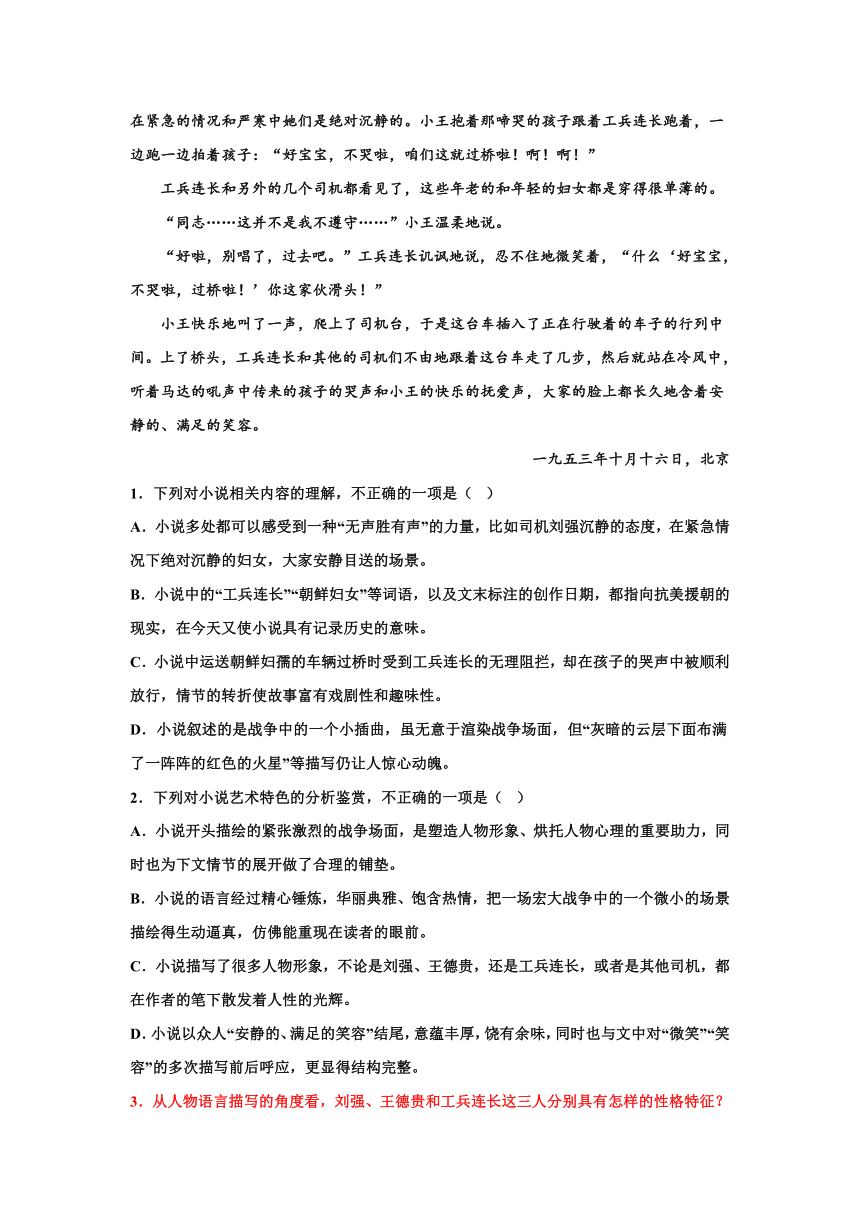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人物语言描写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菱荡
废名
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
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弯,潺潺流过。这里离城才是真近,中间就只有河,城墙的一段正对了竹子临水而立,竹林里一条小路,城上也窥得见,不当心河边忽然站了一个人——陶家村人出来挑水。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
陶家村过桥的地方有一座石塔,名叫洗手塔。人说,当初是没有桥的,往来要“摆渡”。摆渡者,是指以大乌竹做成的笺载行人过河。一位姓张的老汉,专在这里摆渡过日,头发白得像银丝。一天,何仙姑下凡来,渡老汉升天,老汉道:“我不去。城里人如何下乡?乡下人如何进城?”但老汉这天晚上死了。清早起来,河有桥,桥头有塔。何仙姑一夜修了桥。修了桥洗一洗手,成洗手塔。这个故事,陶家村的陈聋子独不相信,他说:“张老头子摆渡,不是要渡钱吗?”摆渡依然要人家给他钱,同聋子“打长工”是一样,所以决不能升天。
菱荡圩是以这个菱荡得名。
菱荡属陶家村,周围常青树的矮林,密得很。走在坝上。望见白水的一角。荡岸,绿草散着野花,成一个圈圈。两个通口,一个连菜园,陈聋子种的几畦园也在这里。
菱荡的深,陶家村的二老爹知道,二老爹是七十八岁的老人,说,道光十九年,剩了他们的菱荡没有成干土,但也快要见底了。网起来的大小鱼真不少,鲤鱼大的有二十斤。这回陶家村可热闹,六城的人来看,洗手塔上是人,荡当中人挤人,树都挤得稀疏了。
城里人并不以为菱荡是陶家村的,是陈聋子的。大家都熟识这个聋子,喜欢他,打趣他,尤其是那般洗衣的女人——洗衣的多半住在西城根,河水竭了到菱荡来洗。菱荡的深,这才被她们搅动了。太阳落山以及天刚刚破晓的时候,坝上也听得见她们喉咙叫,甚至,衣篮太重了坐在坝脚下草地上“打一栈”的也与正在捶捣杵的相呼应。野花做了她们的蒲团,原来青青的草她们踏成了路。
陈聋子,平常略去了陈字,只称聋子。他在陶家村打了十几年长工,轻易不见他说话,别人说话他偏肯听,大家都嫉妒他似的这样叫他。但这或者不始于陶家村,他到陶家村来似乎就没有带来别的名字了。二老爹的园是他种,园里出的菜也要他挑上街去卖,二老爹相信他一人,回来一文一文的钱向二老爹手上数。洗衣女人问他讨萝卜吃——好比他正在萝卜田里,他也连忙拔起一个大的,连叶子给她。不过讨萝卜他就答应一个萝卜,再说他的萝卜不好,他无话回,笑是笑的。菱荡圩的萝卜吃在口里实在甜。
菱荡满菱角的时候,菱荡里不时有一个小划子(这划子一个人背得起),坐划子菱叶上打回旋的常是陈聋子。聋子到哪里去了,二老爹也不知道,二老爹或者在坝脚下看他的牛吃草,没有留心他的聋子进菱荡。聋子挑了菱角回家——聋子是在菱荡摘菱角!
聋子总是这样的去摘菱角,恰如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
有一回聋子送一篮菱角到石家井去——石家井是城里有名的巷子,石姓所居,两边院墙夹成一条深巷,石铺的道,小孩子走这里过,故意踏得响,逗回声。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两匹狗朝外一奔,跳到他的肩膀上叫。一匹是黑的,一匹白的,聋子分不开眼睛,尽站在一块石上转,两手紧握篮子,一直到狗叫出了石家的小姑娘,替他喝住狗。石家姑娘见了一篮红菱角,笑道:“是我家买的吗?”聋子被狗呆住了的模样,一言没有发,但他对着小姑娘牙齿都笑出来了。小姑娘引他进来,一会儿又送他出门。他连走路也不响。
以后逢着二老爹的孙女儿吵嘴,聋子就咕噜一句:“你看街上的小姑娘是多么好!”
他的话总是这样的说。
一日,太阳已下西山,青天罩着菱荡圩照样的绿,不同的颜色,坝上庙的白墙,坝下聋子人一个,他刚刚从家里上园来,挑了水桶,挟了锄头。他要挑水浇一浇园里的青椒。他一听——菱荡洗衣的有好几个。
走回了原处,扁担横在水桶上,他坐在扁担上,拿出烟杆来吃,他的全副家伙都在腰边。聋子这个脾气厉害,倘是别个,二老爹一天少不了啰唆几遍,但是他的聋子(圩里下湾的王四牛却这样说:一年四吊毛钱,不吃烟做什么?何况聋子挑了水,卖菜卖菱角!)。
衔了烟偏了头,听——
是张大嫂,张大嫂讲了一句好笑的话。聋子也笑。
烟杆系上腰。扁担挑上肩。
“今天真热!”张大嫂的破喉咙。
“来了人看怎么办?”
“把人热死了怎么办?”
“嗳呀——”
“我道是谁——聋子。”
聋子眼睛望了水,笑着自语——“聋子!”
1927年10月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陶家村翠竹绿水,小桥石塔,环境优美恬淡,关于洗手塔来历的神话传说,为此地增加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B.洗衣女人们的片刻喧闹,不仅搅动了菱荡的水,也搅动了菱荡惯常的深谧、寂静,给菱荡注入了活泼的生活气息。
C.陈聋子去摘菱角,无人留心他,就像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无声无息,可以看出陈聋子的平凡渺小,静默无闻。
D.小说结尾张大嫂解褂兜风的情节,有朴实的生活气息,浓郁的人情味,但也反映出农村的封闭落后,教化不足。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篇的景物描写,既交代了菱荡所处的地理位置,表明菱荡与陶家村的密切关系,又自然引出了后文的其人其事,使前后文脉连贯无隙。
B.小说写“城上人望城下人……城下人亦望城上”,与卞之琳《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诗句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
C.小说笔调舒缓自如,情节曲折有致,描绘了一幅中国南方水乡的世俗图,反映出旧时中国南方农民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D.小说以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笔法状物摹人,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相互晕染,画面感极强,渗透了作者独特的乡土意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3.陈聋子不一定真聋,只是轻易不说话,请结合三处画横线的有关陈聋子的语言描写,分析其形象特点。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雪(节选)
路翎
敌机正在云层里盘旋,找寻着目标。江的两岸,保护桥梁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在射击着,传来急促的剧烈的声音,灰暗的云层下面布满了一阵阵的红色的火星。
车子一辆接着一辆,慢慢地驶上了刚修好的桥。但刘强的车被管理桥头的一位工兵连长拦住了。工兵连长说,必须排好队按次序前进,因此,刘强应该退到大公路上去排队,否则就要等待已经排成一队的车辆过完。
“我来交涉去!”王德贵理直气壮地叫着,打开车门抱着孩子出去了。
刘强疲困地坐在那里,他听见小王说:“同志,你想想吧,这并不是我们不遵守,……我们的司机负伤了,我们一台车并不妨碍大家呀!”
他又听见那工兵连长的非常疲劳的、冷淡的声音:“不遵守制度就妨碍大家……”
“小王,回来!”刘强有点烦躁又严厉地说,“遵守制度吧!”
王德贵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怀里的,被他包在羊皮大衣里的那个男孩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这哭声是这么意外,大家都朝这边看着。小王一瞬间也被这哭声闹慌了,他不好意思地、赶紧地拍着孩子说:“别哭了,哭什么呀!”但立刻他的声音就不觉地变得非常柔和,他拍着孩子的屁股说:“不哭啊,宝宝,咱们马上就要过桥了。”这时候敌机又经过顶空,高射炮猛烈地射击着,可是小王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个。
那孩子继续地哭着。工兵连长奇怪地、沉闷地问:“这是怎么搞的?你哪里弄来的这个孩子呀!”
“我弄来的?”小王激动地嚷着,“你没看见吗,咱们车上全是前面下来的朝鲜妇女!”随即他又拍着孩子的屁股,“不哭啦,小宝宝,过不了桥就待着吧。”
听了一听敌机已经过去,工兵连长就打亮了手电,照见了那个在小王怀里动着四肢大哭着的、满脸眼泪的孩子,并且照见了小王那被孩子尿湿了一大片的羊皮大衣。在手电的反光里,刘强注意到工兵连长的疲乏的脸上有了一丝微笑,并且他那眼睛因讥诮和喜悦而发亮。
“这他妈的!”工兵连长讥讽地说,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了,“你看你这个样儿!不哭啦,小宝宝,过不了桥就待着吧,你待着吧!”
“难道不是这样的?”小王叫着。
周围的人们都看着孩子。这些疲困、受冻、焦灼的战士们、司机们,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当那孩子的小手在手电的亮光里一下子扑打到小王的脸上去的时候,那个工兵连长脸上的笑容更明显了,大家于是懂得,这毛手毛脚的年轻的司机助手,为什么要求得这么理直气壮了。
工兵连长就亮着手电向车子走去,对车子照着。那些妇女们默默地迎着手电的亮光,在紧急的情况和严寒中她们是绝对沉静的。小王抱着那啼哭的孩子跟着工兵连长跑着,一边跑一边拍着孩子:“好宝宝,不哭啦,咱们这就过桥啦!啊!啊!”
工兵连长和另外的几个司机都看见了,这些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都是穿得很单薄的。
“同志……这并不是我不遵守……”小王温柔地说。
“好啦,别唱了,过去吧。”工兵连长讥讽地说,忍不住地微笑着,“什么‘好宝宝,不哭啦,过桥啦!’你这家伙滑头!”
小王快乐地叫了一声,爬上了司机台,于是这台车插入了正在行驶着的车子的行列中间。上了桥头,工兵连长和其他的司机们不由地跟着这台车走了几步,然后就站在冷风中,听着马达的吼声中传来的孩子的哭声和小王的快乐的抚爱声,大家的脸上都长久地含着安静的、满足的笑容。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北京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多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比如司机刘强沉静的态度,在紧急情况下绝对沉静的妇女,大家安静目送的场景。
B.小说中的“工兵连长”“朝鲜妇女”等词语,以及文末标注的创作日期,都指向抗美援朝的现实,在今天又使小说具有记录历史的意味。
C.小说中运送朝鲜妇孺的车辆过桥时受到工兵连长的无理阻拦,却在孩子的哭声中被顺利放行,情节的转折使故事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
D.小说叙述的是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虽无意于渲染战争场面,但“灰暗的云层下面布满了一阵阵的红色的火星”等描写仍让人惊心动魄。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描绘的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是塑造人物形象、烘托人物心理的重要助力,同时也为下文情节的展开做了合理的铺垫。
B.小说的语言经过精心锤炼,华丽典雅、饱含热情,把一场宏大战争中的一个微小的场景描绘得生动逼真,仿佛能重现在读者的眼前。
C.小说描写了很多人物形象,不论是刘强、王德贵,还是工兵连长,或者是其他司机,都在作者的笔下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D.小说以众人“安静的、满足的笑容”结尾,意蕴丰厚,饶有余味,同时也与文中对“微笑”“笑容”的多次描写前后呼应,更显得结构完整。
3.从人物语言描写的角度看,刘强、王德贵和工兵连长这三人分别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俄】契诃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并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对不起,要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你管得着赶散人群这种事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的人齐声喊道,“他搅得人不得安生,大人!我们忍了他十五年了!自从他退伍回乡,从那时起,弄得人简直想从村里逃走。”
“正是这样,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人都在抱怨。真没法跟他在一起生活!前几天,他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唱歌的。”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再提供证词,”调解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
中士操着哑嗓子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可要是民众闹事呢?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先生。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谁又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啥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画脚的?’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说,你们都龇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说过。”
“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反对官府?’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就不妙!’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我抡起拳头……你要是见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该睡觉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罢,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灯闲坐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说完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犯了哪条王法?”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通过人物对话推动故事情节展开,在人物对话中既全面细致地描述主人公的形象,又使故事的节奏变得更紧凑。
B.小说注意前后照应,如前文有“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后文有“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与之照应。
C.“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这一情节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D.契诃夫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这篇小说同《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根本目的是嘲讽像“普里希别耶夫”和“别里科夫”这样的人。
2.“法律”“规定”“秩序”频频出现在普里希别耶夫的语言描写中,请说说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楼梦》(节选)
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宝玉因叹道:“蠢才!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寻我的不是。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宝玉听了这些话,气得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因为你服侍得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又见宝玉已经气得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道:“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她!”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她一个胡涂人,你和他分争什么?”晴雯又冷笑道:“我原是胡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见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么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哪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晴雯哭道:“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宝玉一定要去回。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
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说话,只见林黛玉进来,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诉我,我问你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宝玉道:“你何苦来替她招骂名儿。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她。”袭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报嘴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一笑也就罢了。
黛玉去后,有人来说“薛大爷请”,宝玉只得去了。晚间回来,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院内,只见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设下,有个人睡着。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她,问道:“疼得好些了?”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却是晴雯。宝玉将她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不过说了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她,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作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睡着呢?”晴雯没得说,嗤的笑了,说:“你不来,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宝玉笑道:“我才又吃了好些酒,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咱们两个洗。”晴雯摇手笑道:“罢,我不敢惹爷。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宝玉笑道:“既这么着,你也不许洗去,只洗洗手来拿果子来吃罢。”晴雯笑道:“我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盘子,更了不得了。”宝玉笑道:“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递与她。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笑道:“少作些孽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她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着,一面叫袭人。大家乘凉,不消细说。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矛盾因晴雯跌扇产生,由晴雯撕扇结束,构思巧妙,在矛盾冲突中鲜明地塑造了宝玉、晴雯、袭人不同的形象。
B.由“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等语言看,晴雯最在意自己的地位。
C.“晴雯又冷笑道”“含泪说道”“晴雯没得说,嗤的笑了”,这些描写凸显了晴雯喜怒形于色、心直口快的特点。
D.贾宝玉为了哄晴雯,不但让她撕自己的扇子,还夺麝月的扇子让她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并不以主子身份自居。
2.本文有大量的语言描写,有什么作用?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答案】
一、1、D“农村的封闭落后,教化不足”分析错误,结合原文“‘今天真热!’张大嫂的破喉咙”可知,张大嫂在天热时,没有拘泥于礼法。结合全文可知,作者在此是以支持赞赏的态度看待她的行为的,并不是想通过她反映农村的封闭落后、教化不足。
C“情节曲折有致”说法有误。此篇小说,没有一般小说所具备的完整情节、丰富的人物形象,从结构上看有点“散”,语言又常“跳跃”,并且淡化了小说的情节机制,增加了诗和散文的艺术效益,不能说情节曲折有致。
3.①第一处:朴实率真,他用人间常理去判断神话传说的真实性,可见其憨厚朴实、直率真实。
②第二处:向善好礼,只要二老爹的孙女儿吵嘴,他就会想起街上小姑娘的友好懂礼,可见他也是一个平和善良、懂礼识礼的人。
③第三处:睿智达观,面对张大嫂的戏谑,他只是笑着自语,不计较不争辩又智慧打趣,可见他既睿智达观又开朗风趣。
二、1.C “小说中运送朝鲜妇孺的车辆过桥时受到工兵连长的无理阻拦”理解错误,依据原文“工兵连长说,必须排好队按次序前进”“不遵守制度就妨碍大家……”可知,工兵连长阻拦是因为有制度,过桥需要排队。
2.B“小说的语言……华丽典雅”分析错误,这篇小说语言平和朴实,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好宝宝,不哭了”,并且在其他人物语言和环境的描写上,都体现了平和自然的风格。
3.①刘强不愿求人放行,话语少且短句多,语调急促有力,说明他刚毅坚定、自尊心强。②王德贵为了朝鲜妇孺与人争执,说话时语气助词较多,说明他心地善良、率真冲动。③工兵连长从严格执法到同情放行,多次模仿他人口吻,说明他既严于职守,又善良风趣。
三、1.D “根本目的是嘲讽像‘普里希别耶夫’和‘别里科夫’这样的人”错,根本目的是抨击沙皇专制统治。
2.①表明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长久而沉重。
②讽刺了像普里希别耶夫一样旧制度、旧秩序的卫道者。
③揭示了当时人们生存环境的艰难。
四、1.B “晴雯最在意自己的地位”错误,由“晴雯听她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可知,晴雯在意的不是地位,而是和宝玉之间的情意。
2.①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个性。如宝玉斥责了晴雯,晴雯回嘴气得宝玉浑身乱战,表现出晴雯的率性。②推动情节发展。如晴雯、宝玉的拌嘴引出袭人的劝和。③笔墨集中,篇幅简省。大量对话描写,可使作者集中笔墨于核心情节,不蔓不枝。④丰富文章内容,展现人物间的关系。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菱荡
废名
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
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弯,潺潺流过。这里离城才是真近,中间就只有河,城墙的一段正对了竹子临水而立,竹林里一条小路,城上也窥得见,不当心河边忽然站了一个人——陶家村人出来挑水。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
陶家村过桥的地方有一座石塔,名叫洗手塔。人说,当初是没有桥的,往来要“摆渡”。摆渡者,是指以大乌竹做成的笺载行人过河。一位姓张的老汉,专在这里摆渡过日,头发白得像银丝。一天,何仙姑下凡来,渡老汉升天,老汉道:“我不去。城里人如何下乡?乡下人如何进城?”但老汉这天晚上死了。清早起来,河有桥,桥头有塔。何仙姑一夜修了桥。修了桥洗一洗手,成洗手塔。这个故事,陶家村的陈聋子独不相信,他说:“张老头子摆渡,不是要渡钱吗?”摆渡依然要人家给他钱,同聋子“打长工”是一样,所以决不能升天。
菱荡圩是以这个菱荡得名。
菱荡属陶家村,周围常青树的矮林,密得很。走在坝上。望见白水的一角。荡岸,绿草散着野花,成一个圈圈。两个通口,一个连菜园,陈聋子种的几畦园也在这里。
菱荡的深,陶家村的二老爹知道,二老爹是七十八岁的老人,说,道光十九年,剩了他们的菱荡没有成干土,但也快要见底了。网起来的大小鱼真不少,鲤鱼大的有二十斤。这回陶家村可热闹,六城的人来看,洗手塔上是人,荡当中人挤人,树都挤得稀疏了。
城里人并不以为菱荡是陶家村的,是陈聋子的。大家都熟识这个聋子,喜欢他,打趣他,尤其是那般洗衣的女人——洗衣的多半住在西城根,河水竭了到菱荡来洗。菱荡的深,这才被她们搅动了。太阳落山以及天刚刚破晓的时候,坝上也听得见她们喉咙叫,甚至,衣篮太重了坐在坝脚下草地上“打一栈”的也与正在捶捣杵的相呼应。野花做了她们的蒲团,原来青青的草她们踏成了路。
陈聋子,平常略去了陈字,只称聋子。他在陶家村打了十几年长工,轻易不见他说话,别人说话他偏肯听,大家都嫉妒他似的这样叫他。但这或者不始于陶家村,他到陶家村来似乎就没有带来别的名字了。二老爹的园是他种,园里出的菜也要他挑上街去卖,二老爹相信他一人,回来一文一文的钱向二老爹手上数。洗衣女人问他讨萝卜吃——好比他正在萝卜田里,他也连忙拔起一个大的,连叶子给她。不过讨萝卜他就答应一个萝卜,再说他的萝卜不好,他无话回,笑是笑的。菱荡圩的萝卜吃在口里实在甜。
菱荡满菱角的时候,菱荡里不时有一个小划子(这划子一个人背得起),坐划子菱叶上打回旋的常是陈聋子。聋子到哪里去了,二老爹也不知道,二老爹或者在坝脚下看他的牛吃草,没有留心他的聋子进菱荡。聋子挑了菱角回家——聋子是在菱荡摘菱角!
聋子总是这样的去摘菱角,恰如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
有一回聋子送一篮菱角到石家井去——石家井是城里有名的巷子,石姓所居,两边院墙夹成一条深巷,石铺的道,小孩子走这里过,故意踏得响,逗回声。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两匹狗朝外一奔,跳到他的肩膀上叫。一匹是黑的,一匹白的,聋子分不开眼睛,尽站在一块石上转,两手紧握篮子,一直到狗叫出了石家的小姑娘,替他喝住狗。石家姑娘见了一篮红菱角,笑道:“是我家买的吗?”聋子被狗呆住了的模样,一言没有发,但他对着小姑娘牙齿都笑出来了。小姑娘引他进来,一会儿又送他出门。他连走路也不响。
以后逢着二老爹的孙女儿吵嘴,聋子就咕噜一句:“你看街上的小姑娘是多么好!”
他的话总是这样的说。
一日,太阳已下西山,青天罩着菱荡圩照样的绿,不同的颜色,坝上庙的白墙,坝下聋子人一个,他刚刚从家里上园来,挑了水桶,挟了锄头。他要挑水浇一浇园里的青椒。他一听——菱荡洗衣的有好几个。
走回了原处,扁担横在水桶上,他坐在扁担上,拿出烟杆来吃,他的全副家伙都在腰边。聋子这个脾气厉害,倘是别个,二老爹一天少不了啰唆几遍,但是他的聋子(圩里下湾的王四牛却这样说:一年四吊毛钱,不吃烟做什么?何况聋子挑了水,卖菜卖菱角!)。
衔了烟偏了头,听——
是张大嫂,张大嫂讲了一句好笑的话。聋子也笑。
烟杆系上腰。扁担挑上肩。
“今天真热!”张大嫂的破喉咙。
“来了人看怎么办?”
“把人热死了怎么办?”
“嗳呀——”
“我道是谁——聋子。”
聋子眼睛望了水,笑着自语——“聋子!”
1927年10月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陶家村翠竹绿水,小桥石塔,环境优美恬淡,关于洗手塔来历的神话传说,为此地增加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B.洗衣女人们的片刻喧闹,不仅搅动了菱荡的水,也搅动了菱荡惯常的深谧、寂静,给菱荡注入了活泼的生活气息。
C.陈聋子去摘菱角,无人留心他,就像菱荡在菱荡圩不现其水,无声无息,可以看出陈聋子的平凡渺小,静默无闻。
D.小说结尾张大嫂解褂兜风的情节,有朴实的生活气息,浓郁的人情味,但也反映出农村的封闭落后,教化不足。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篇的景物描写,既交代了菱荡所处的地理位置,表明菱荡与陶家村的密切关系,又自然引出了后文的其人其事,使前后文脉连贯无隙。
B.小说写“城上人望城下人……城下人亦望城上”,与卞之琳《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诗句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
C.小说笔调舒缓自如,情节曲折有致,描绘了一幅中国南方水乡的世俗图,反映出旧时中国南方农民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D.小说以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笔法状物摹人,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相互晕染,画面感极强,渗透了作者独特的乡土意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3.陈聋子不一定真聋,只是轻易不说话,请结合三处画横线的有关陈聋子的语言描写,分析其形象特点。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雪(节选)
路翎
敌机正在云层里盘旋,找寻着目标。江的两岸,保护桥梁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在射击着,传来急促的剧烈的声音,灰暗的云层下面布满了一阵阵的红色的火星。
车子一辆接着一辆,慢慢地驶上了刚修好的桥。但刘强的车被管理桥头的一位工兵连长拦住了。工兵连长说,必须排好队按次序前进,因此,刘强应该退到大公路上去排队,否则就要等待已经排成一队的车辆过完。
“我来交涉去!”王德贵理直气壮地叫着,打开车门抱着孩子出去了。
刘强疲困地坐在那里,他听见小王说:“同志,你想想吧,这并不是我们不遵守,……我们的司机负伤了,我们一台车并不妨碍大家呀!”
他又听见那工兵连长的非常疲劳的、冷淡的声音:“不遵守制度就妨碍大家……”
“小王,回来!”刘强有点烦躁又严厉地说,“遵守制度吧!”
王德贵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怀里的,被他包在羊皮大衣里的那个男孩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这哭声是这么意外,大家都朝这边看着。小王一瞬间也被这哭声闹慌了,他不好意思地、赶紧地拍着孩子说:“别哭了,哭什么呀!”但立刻他的声音就不觉地变得非常柔和,他拍着孩子的屁股说:“不哭啊,宝宝,咱们马上就要过桥了。”这时候敌机又经过顶空,高射炮猛烈地射击着,可是小王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个。
那孩子继续地哭着。工兵连长奇怪地、沉闷地问:“这是怎么搞的?你哪里弄来的这个孩子呀!”
“我弄来的?”小王激动地嚷着,“你没看见吗,咱们车上全是前面下来的朝鲜妇女!”随即他又拍着孩子的屁股,“不哭啦,小宝宝,过不了桥就待着吧。”
听了一听敌机已经过去,工兵连长就打亮了手电,照见了那个在小王怀里动着四肢大哭着的、满脸眼泪的孩子,并且照见了小王那被孩子尿湿了一大片的羊皮大衣。在手电的反光里,刘强注意到工兵连长的疲乏的脸上有了一丝微笑,并且他那眼睛因讥诮和喜悦而发亮。
“这他妈的!”工兵连长讥讽地说,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了,“你看你这个样儿!不哭啦,小宝宝,过不了桥就待着吧,你待着吧!”
“难道不是这样的?”小王叫着。
周围的人们都看着孩子。这些疲困、受冻、焦灼的战士们、司机们,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当那孩子的小手在手电的亮光里一下子扑打到小王的脸上去的时候,那个工兵连长脸上的笑容更明显了,大家于是懂得,这毛手毛脚的年轻的司机助手,为什么要求得这么理直气壮了。
工兵连长就亮着手电向车子走去,对车子照着。那些妇女们默默地迎着手电的亮光,在紧急的情况和严寒中她们是绝对沉静的。小王抱着那啼哭的孩子跟着工兵连长跑着,一边跑一边拍着孩子:“好宝宝,不哭啦,咱们这就过桥啦!啊!啊!”
工兵连长和另外的几个司机都看见了,这些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都是穿得很单薄的。
“同志……这并不是我不遵守……”小王温柔地说。
“好啦,别唱了,过去吧。”工兵连长讥讽地说,忍不住地微笑着,“什么‘好宝宝,不哭啦,过桥啦!’你这家伙滑头!”
小王快乐地叫了一声,爬上了司机台,于是这台车插入了正在行驶着的车子的行列中间。上了桥头,工兵连长和其他的司机们不由地跟着这台车走了几步,然后就站在冷风中,听着马达的吼声中传来的孩子的哭声和小王的快乐的抚爱声,大家的脸上都长久地含着安静的、满足的笑容。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北京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多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比如司机刘强沉静的态度,在紧急情况下绝对沉静的妇女,大家安静目送的场景。
B.小说中的“工兵连长”“朝鲜妇女”等词语,以及文末标注的创作日期,都指向抗美援朝的现实,在今天又使小说具有记录历史的意味。
C.小说中运送朝鲜妇孺的车辆过桥时受到工兵连长的无理阻拦,却在孩子的哭声中被顺利放行,情节的转折使故事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
D.小说叙述的是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虽无意于渲染战争场面,但“灰暗的云层下面布满了一阵阵的红色的火星”等描写仍让人惊心动魄。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描绘的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是塑造人物形象、烘托人物心理的重要助力,同时也为下文情节的展开做了合理的铺垫。
B.小说的语言经过精心锤炼,华丽典雅、饱含热情,把一场宏大战争中的一个微小的场景描绘得生动逼真,仿佛能重现在读者的眼前。
C.小说描写了很多人物形象,不论是刘强、王德贵,还是工兵连长,或者是其他司机,都在作者的笔下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D.小说以众人“安静的、满足的笑容”结尾,意蕴丰厚,饶有余味,同时也与文中对“微笑”“笑容”的多次描写前后呼应,更显得结构完整。
3.从人物语言描写的角度看,刘强、王德贵和工兵连长这三人分别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俄】契诃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并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对不起,要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你管得着赶散人群这种事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的人齐声喊道,“他搅得人不得安生,大人!我们忍了他十五年了!自从他退伍回乡,从那时起,弄得人简直想从村里逃走。”
“正是这样,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人都在抱怨。真没法跟他在一起生活!前几天,他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唱歌的。”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再提供证词,”调解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
中士操着哑嗓子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可要是民众闹事呢?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先生。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谁又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啥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画脚的?’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说,你们都龇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说过。”
“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反对官府?’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就不妙!’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我抡起拳头……你要是见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该睡觉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罢,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灯闲坐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说完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犯了哪条王法?”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通过人物对话推动故事情节展开,在人物对话中既全面细致地描述主人公的形象,又使故事的节奏变得更紧凑。
B.小说注意前后照应,如前文有“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后文有“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与之照应。
C.“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这一情节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D.契诃夫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这篇小说同《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根本目的是嘲讽像“普里希别耶夫”和“别里科夫”这样的人。
2.“法律”“规定”“秩序”频频出现在普里希别耶夫的语言描写中,请说说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楼梦》(节选)
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宝玉因叹道:“蠢才!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寻我的不是。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宝玉听了这些话,气得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因为你服侍得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又见宝玉已经气得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道:“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她!”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她一个胡涂人,你和他分争什么?”晴雯又冷笑道:“我原是胡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见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么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哪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晴雯哭道:“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宝玉一定要去回。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
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说话,只见林黛玉进来,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诉我,我问你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宝玉道:“你何苦来替她招骂名儿。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她。”袭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报嘴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一笑也就罢了。
黛玉去后,有人来说“薛大爷请”,宝玉只得去了。晚间回来,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院内,只见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设下,有个人睡着。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她,问道:“疼得好些了?”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却是晴雯。宝玉将她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不过说了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她,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作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睡着呢?”晴雯没得说,嗤的笑了,说:“你不来,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宝玉笑道:“我才又吃了好些酒,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咱们两个洗。”晴雯摇手笑道:“罢,我不敢惹爷。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宝玉笑道:“既这么着,你也不许洗去,只洗洗手来拿果子来吃罢。”晴雯笑道:“我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盘子,更了不得了。”宝玉笑道:“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递与她。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笑道:“少作些孽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她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着,一面叫袭人。大家乘凉,不消细说。
(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矛盾因晴雯跌扇产生,由晴雯撕扇结束,构思巧妙,在矛盾冲突中鲜明地塑造了宝玉、晴雯、袭人不同的形象。
B.由“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等语言看,晴雯最在意自己的地位。
C.“晴雯又冷笑道”“含泪说道”“晴雯没得说,嗤的笑了”,这些描写凸显了晴雯喜怒形于色、心直口快的特点。
D.贾宝玉为了哄晴雯,不但让她撕自己的扇子,还夺麝月的扇子让她撕,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并不以主子身份自居。
2.本文有大量的语言描写,有什么作用?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答案】
一、1、D“农村的封闭落后,教化不足”分析错误,结合原文“‘今天真热!’张大嫂的破喉咙”可知,张大嫂在天热时,没有拘泥于礼法。结合全文可知,作者在此是以支持赞赏的态度看待她的行为的,并不是想通过她反映农村的封闭落后、教化不足。
C“情节曲折有致”说法有误。此篇小说,没有一般小说所具备的完整情节、丰富的人物形象,从结构上看有点“散”,语言又常“跳跃”,并且淡化了小说的情节机制,增加了诗和散文的艺术效益,不能说情节曲折有致。
3.①第一处:朴实率真,他用人间常理去判断神话传说的真实性,可见其憨厚朴实、直率真实。
②第二处:向善好礼,只要二老爹的孙女儿吵嘴,他就会想起街上小姑娘的友好懂礼,可见他也是一个平和善良、懂礼识礼的人。
③第三处:睿智达观,面对张大嫂的戏谑,他只是笑着自语,不计较不争辩又智慧打趣,可见他既睿智达观又开朗风趣。
二、1.C “小说中运送朝鲜妇孺的车辆过桥时受到工兵连长的无理阻拦”理解错误,依据原文“工兵连长说,必须排好队按次序前进”“不遵守制度就妨碍大家……”可知,工兵连长阻拦是因为有制度,过桥需要排队。
2.B“小说的语言……华丽典雅”分析错误,这篇小说语言平和朴实,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好宝宝,不哭了”,并且在其他人物语言和环境的描写上,都体现了平和自然的风格。
3.①刘强不愿求人放行,话语少且短句多,语调急促有力,说明他刚毅坚定、自尊心强。②王德贵为了朝鲜妇孺与人争执,说话时语气助词较多,说明他心地善良、率真冲动。③工兵连长从严格执法到同情放行,多次模仿他人口吻,说明他既严于职守,又善良风趣。
三、1.D “根本目的是嘲讽像‘普里希别耶夫’和‘别里科夫’这样的人”错,根本目的是抨击沙皇专制统治。
2.①表明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长久而沉重。
②讽刺了像普里希别耶夫一样旧制度、旧秩序的卫道者。
③揭示了当时人们生存环境的艰难。
四、1.B “晴雯最在意自己的地位”错误,由“晴雯听她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可知,晴雯在意的不是地位,而是和宝玉之间的情意。
2.①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个性。如宝玉斥责了晴雯,晴雯回嘴气得宝玉浑身乱战,表现出晴雯的率性。②推动情节发展。如晴雯、宝玉的拌嘴引出袭人的劝和。③笔墨集中,篇幅简省。大量对话描写,可使作者集中笔墨于核心情节,不蔓不枝。④丰富文章内容,展现人物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