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哲贵小说(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哲贵小说(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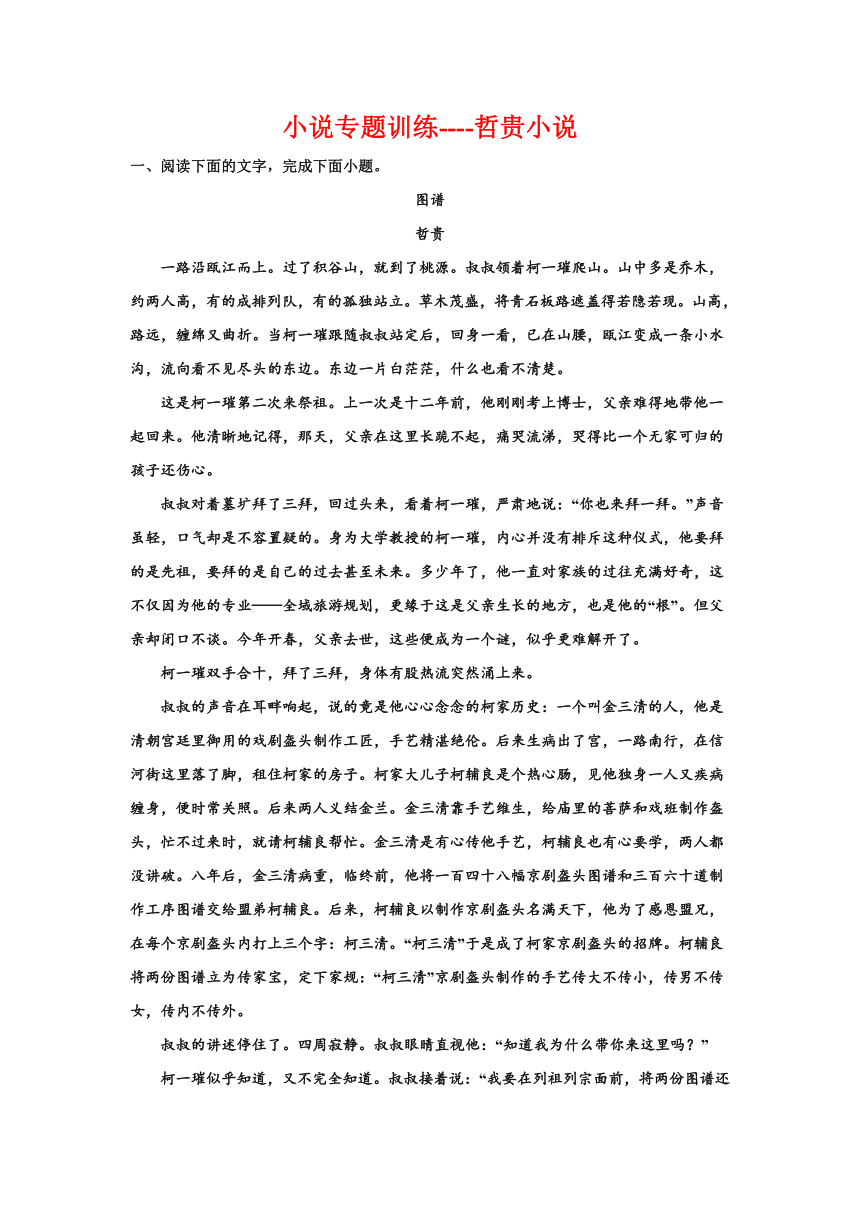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4.7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1-27 10:09:1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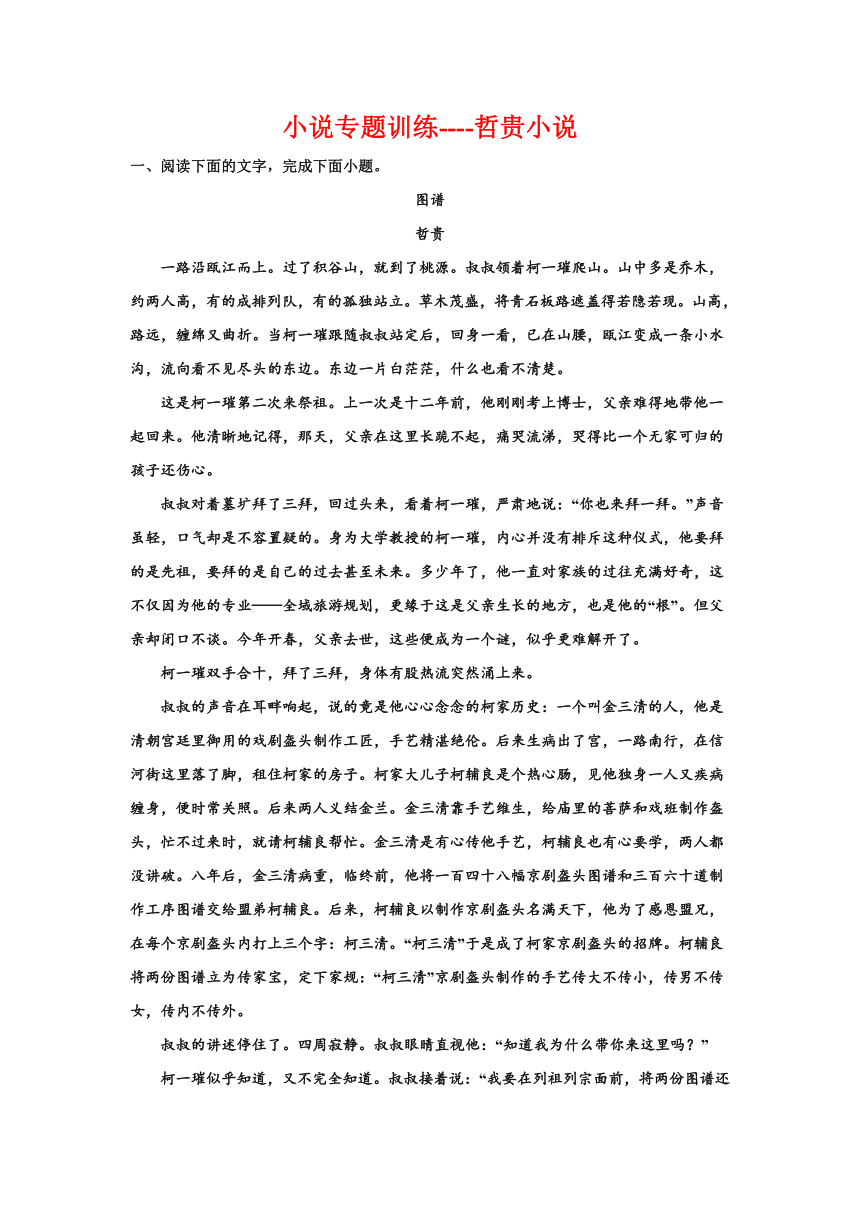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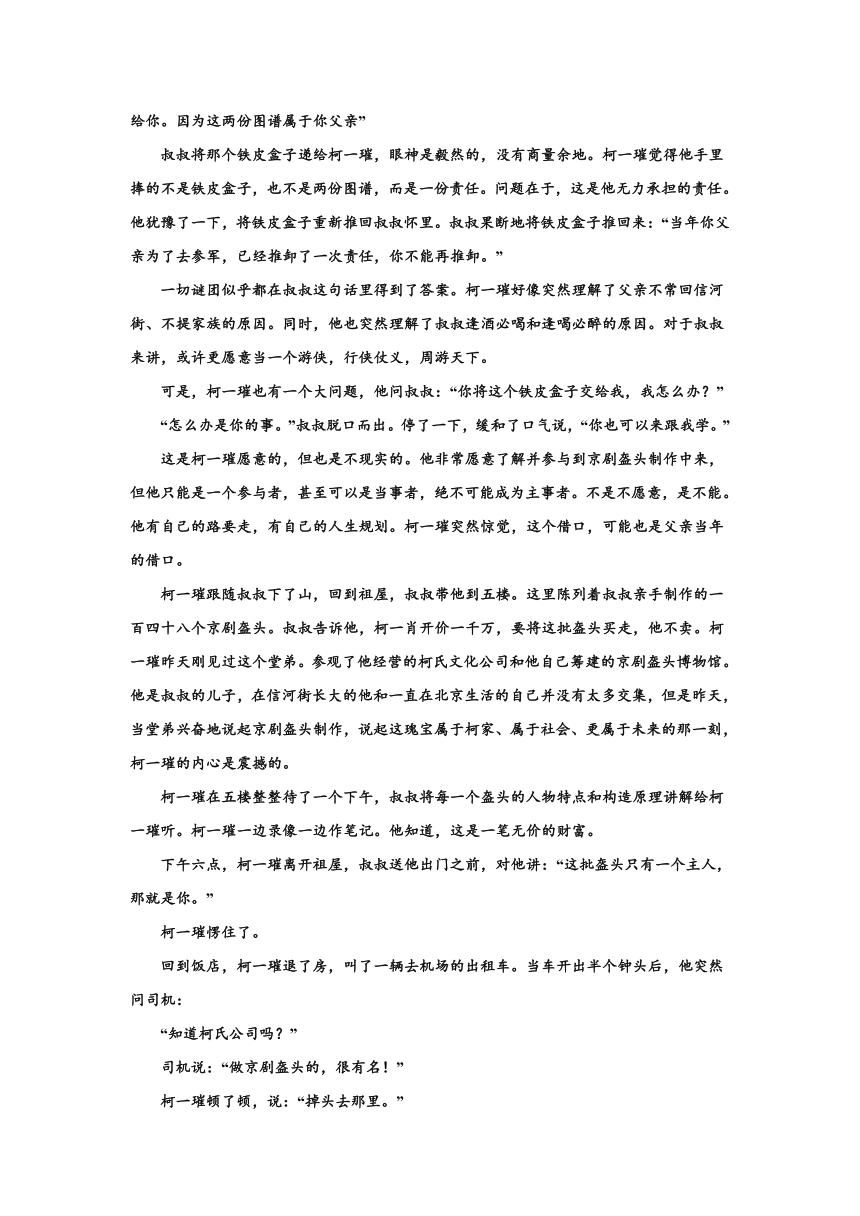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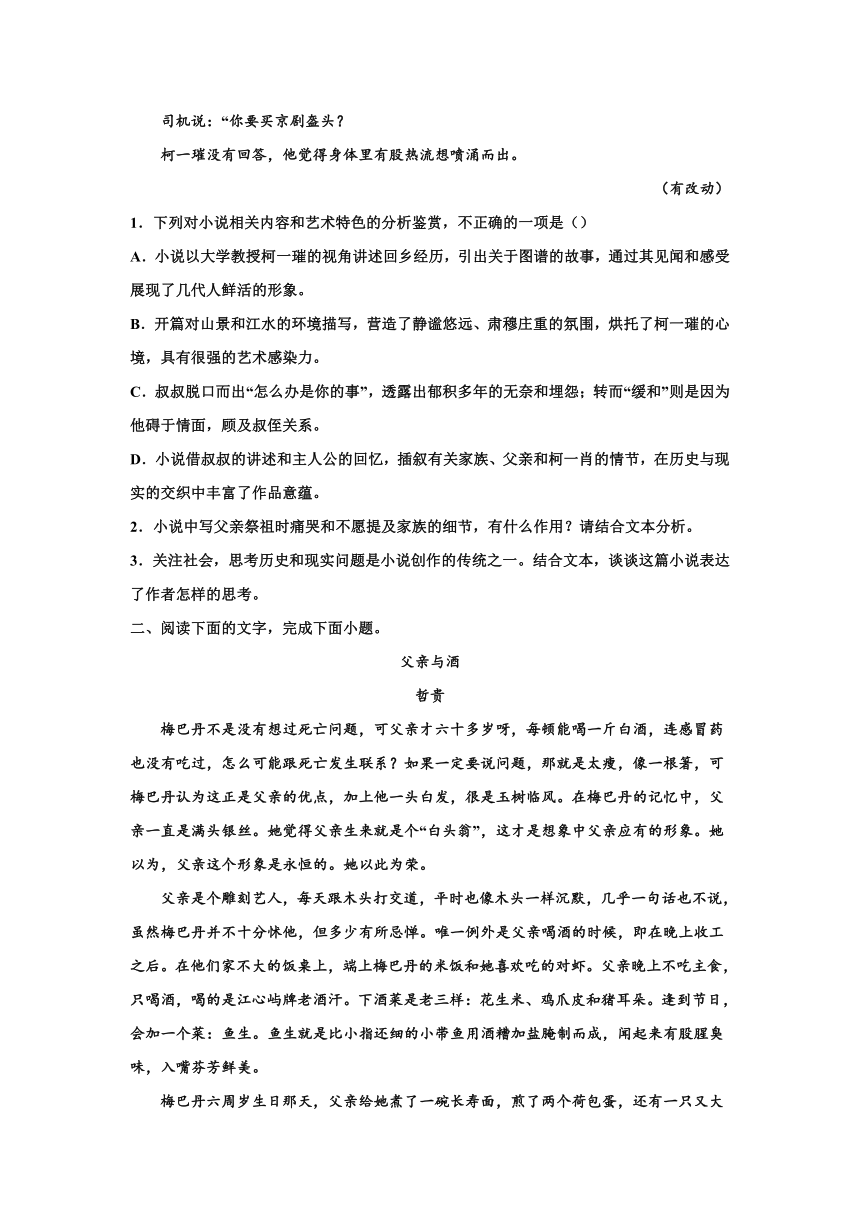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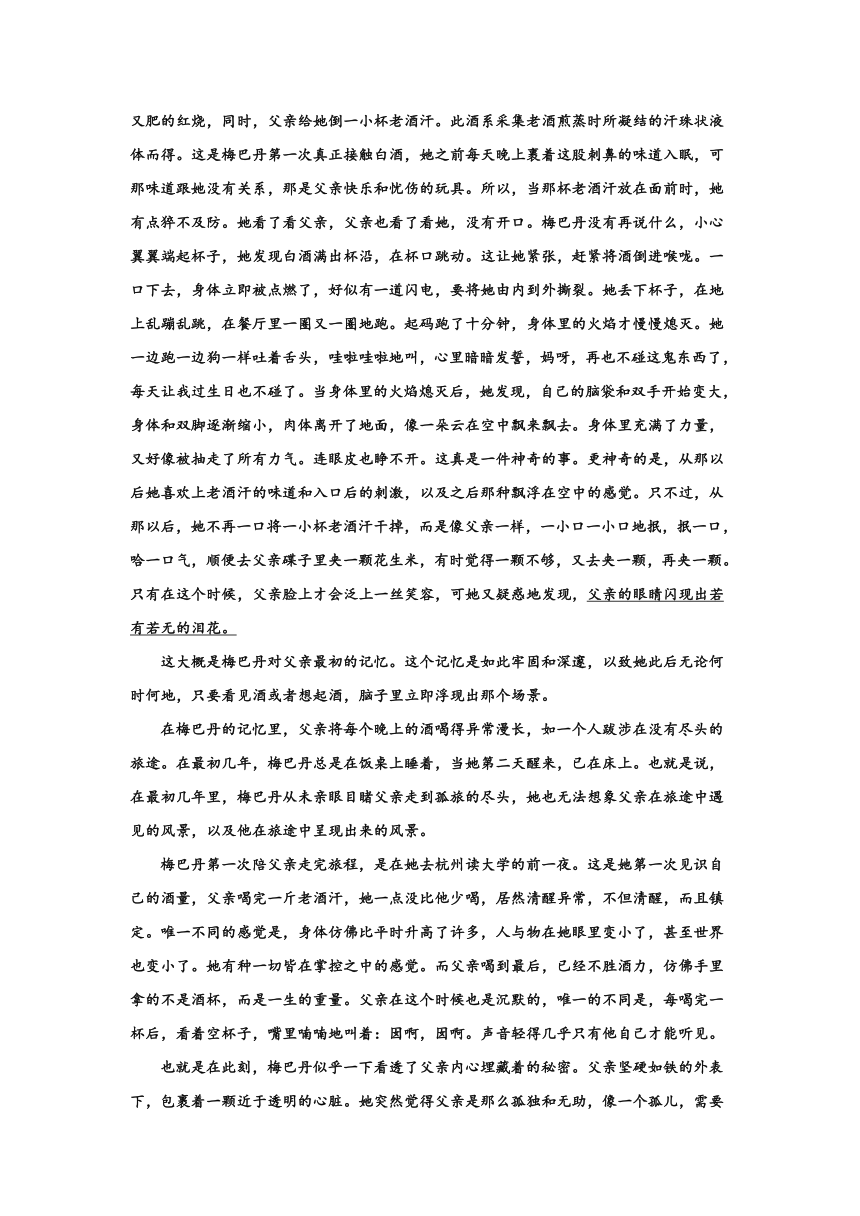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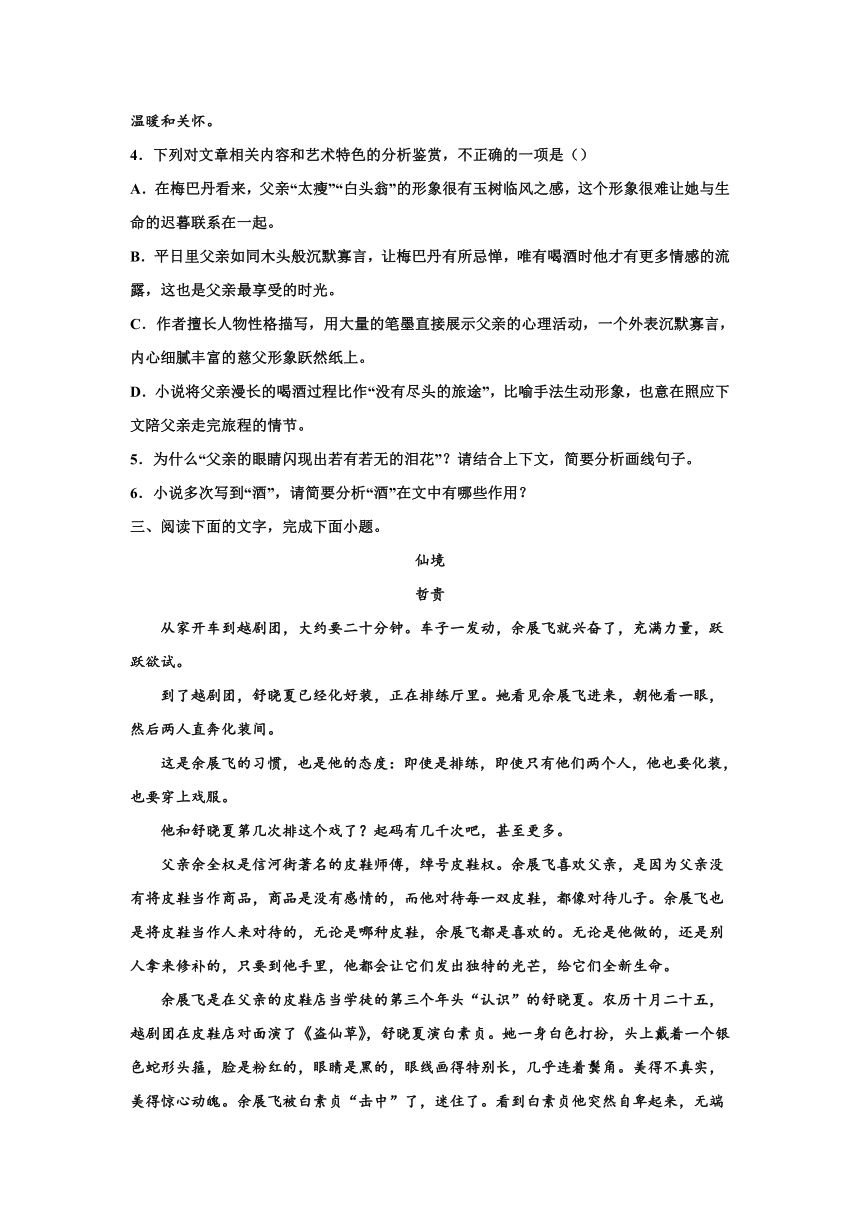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哲贵小说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图谱
哲贵
一路沿瓯江而上。过了积谷山,就到了桃源。叔叔领着柯一璀爬山。山中多是乔木,约两人高,有的成排列队,有的孤独站立。草木茂盛,将青石板路遮盖得若隐若现。山高,路远,缠绵又曲折。当柯一璀跟随叔叔站定后,回身一看,已在山腰,瓯江变成一条小水沟,流向看不见尽头的东边。东边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是柯一璀第二次来祭祖。上一次是十二年前,他刚刚考上博士,父亲难得地带他一起回来。他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在这里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哭得比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还伤心。
叔叔对着墓圹拜了三拜,回过头来,看着柯一璀,严肃地说:“你也来拜一拜。”声音虽轻,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身为大学教授的柯一璀,内心并没有排斥这种仪式,他要拜的是先祖,要拜的是自己的过去甚至未来。多少年了,他一直对家族的过往充满好奇,这不仅因为他的专业——全域旅游规划,更缘于这是父亲生长的地方,也是他的“根”。但父亲却闭口不谈。今年开春,父亲去世,这些便成为一个谜,似乎更难解开了。
柯一璀双手合十,拜了三拜,身体有股热流突然涌上来。
叔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说的竟是他心心念念的柯家历史:一个叫金三清的人,他是清朝宫廷里御用的戏剧盔头制作工匠,手艺精湛绝伦。后来生病出了宫,一路南行,在信河街这里落了脚,租住柯家的房子。柯家大儿子柯辅良是个热心肠,见他独身一人又疾病缠身,便时常关照。后来两人义结金兰。金三清靠手艺维生,给庙里的菩萨和戏班制作盔头,忙不过来时,就请柯辅良帮忙。金三清是有心传他手艺,柯辅良也有心要学,两人都没讲破。八年后,金三清病重,临终前,他将一百四十八幅京剧盔头图谱和三百六十道制作工序图谱交给盟弟柯辅良。后来,柯辅良以制作京剧盔头名满天下,他为了感恩盟兄,在每个京剧盔头内打上三个字:柯三清。“柯三清”于是成了柯家京剧盔头的招牌。柯辅良将两份图谱立为传家宝,定下家规:“柯三清”京剧盔头制作的手艺传大不传小,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叔叔的讲述停住了。四周寂静。叔叔眼睛直视他:“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柯一璀似乎知道,又不完全知道。叔叔接着说:“我要在列祖列宗面前,将两份图谱还给你。因为这两份图谱属于你父亲”
叔叔将那个铁皮盒子递给柯一璀,眼神是毅然的,没有商量余地。柯一璀觉得他手里捧的不是铁皮盒子,也不是两份图谱,而是一份责任。问题在于,这是他无力承担的责任。他犹豫了一下,将铁皮盒子重新推回叔叔怀里。叔叔果断地将铁皮盒子推回来:“当年你父亲为了去参军,已经推卸了一次责任,你不能再推卸。”
一切谜团似乎都在叔叔这句话里得到了答案。柯一璀好像突然理解了父亲不常回信河街、不提家族的原因。同时,他也突然理解了叔叔逢酒必喝和逢喝必醉的原因。对于叔叔来讲,或许更愿意当一个游侠,行侠仗义,周游天下。
可是,柯一璀也有一个大问题,他问叔叔:“你将这个铁皮盒子交给我,我怎么办?”
“怎么办是你的事。”叔叔脱口而出。停了一下,缓和了口气说,“你也可以来跟我学。”
这是柯一璀愿意的,但也是不现实的。他非常愿意了解并参与到京剧盔头制作中来,但他只能是一个参与者,甚至可以是当事者,绝不可能成为主事者。不是不愿意,是不能。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柯一璀突然惊觉,这个借口,可能也是父亲当年的借口。
柯一璀跟随叔叔下了山,回到祖屋,叔叔带他到五楼。这里陈列着叔叔亲手制作的一百四十八个京剧盔头。叔叔告诉他,柯一肖开价一千万,要将这批盔头买走,他不卖。柯一璀昨天刚见过这个堂弟。参观了他经营的柯氏文化公司和他自己筹建的京剧盔头博物馆。他是叔叔的儿子,在信河街长大的他和一直在北京生活的自己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昨天,当堂弟兴奋地说起京剧盔头制作,说起这瑰宝属于柯家、属于社会、更属于未来的那一刻,柯一璀的内心是震撼的。
柯一璀在五楼整整待了一个下午,叔叔将每一个盔头的人物特点和构造原理讲解给柯一璀听。柯一璀一边录像一边作笔记。他知道,这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下午六点,柯一璀离开祖屋,叔叔送他出门之前,对他讲:“这批盔头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你。”
柯一璀愣住了。
回到饭店,柯一璀退了房,叫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车。当车开出半个钟头后,他突然问司机:
“知道柯氏公司吗?”
司机说:“做京剧盔头的,很有名!”
柯一璀顿了顿,说:“掉头去那里。”
司机说:“你要买京剧盔头?
柯一璀没有回答,他觉得身体里有股热流想喷涌而出。
(有改动)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以大学教授柯一璀的视角讲述回乡经历,引出关于图谱的故事,通过其见闻和感受展现了几代人鲜活的形象。
B.开篇对山景和江水的环境描写,营造了静谧悠远、肃穆庄重的氛围,烘托了柯一璀的心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C.叔叔脱口而出“怎么办是你的事”,透露出郁积多年的无奈和埋怨;转而“缓和”则是因为他碍于情面,顾及叔侄关系。
D.小说借叔叔的讲述和主人公的回忆,插叙有关家族、父亲和柯一肖的情节,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丰富了作品意蕴。
2.小说中写父亲祭祖时痛哭和不愿提及家族的细节,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分析。
3.关注社会,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是小说创作的传统之一。结合文本,谈谈这篇小说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考。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父亲与酒
哲贵
梅巴丹不是没有想过死亡问题,可父亲才六十多岁呀,每顿能喝一斤白酒,连感冒药也没有吃过,怎么可能跟死亡发生联系?如果一定要说问题,那就是太瘦,像一根箸,可梅巴丹认为这正是父亲的优点,加上他一头白发,很是玉树临风。在梅巴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满头银丝。她觉得父亲生来就是个“白头翁”,这才是想象中父亲应有的形象。她以为,父亲这个形象是永恒的。她以此为荣。
父亲是个雕刻艺人,每天跟木头打交道,平时也像木头一样沉默,几乎一句话也不说,虽然梅巴丹并不十分怵他,但多少有所忌惮。唯一例外是父亲喝酒的时候,即在晚上收工之后。在他们家不大的饭桌上,端上梅巴丹的米饭和她喜欢吃的对虾。父亲晚上不吃主食,只喝酒,喝的是江心屿牌老酒汗。下酒菜是老三样:花生米、鸡爪皮和猪耳朵。逢到节日,会加一个菜:鱼生。鱼生就是比小指还细的小带鱼用酒糟加盐腌制而成,闻起来有股腥臭味,入嘴芬芳鲜美。
梅巴丹六周岁生日那天,父亲给她煮了一碗长寿面,煎了两个荷包蛋,还有一只又大又肥的红烧,同时,父亲给她倒一小杯老酒汗。此酒系采集老酒煎蒸时所凝结的汗珠状液体而得。这是梅巴丹第一次真正接触白酒,她之前每天晚上裹着这股刺鼻的味道入眠,可那味道跟她没有关系,那是父亲快乐和忧伤的玩具。所以,当那杯老酒汗放在面前时,她有点猝不及防。她看了看父亲,父亲也看了看她,没有开口。梅巴丹没有再说什么,小心翼翼端起杯子,她发现白酒满出杯沿,在杯口跳动。这让她紧张,赶紧将酒倒进喉咙。一口下去,身体立即被点燃了,好似有一道闪电,要将她由内到外撕裂。她丢下杯子,在地上乱蹦乱跳,在餐厅里一圈又一圈地跑。起码跑了十分钟,身体里的火焰才慢慢熄灭。她一边跑一边狗一样吐着舌头,哇啦哇啦地叫,心里暗暗发誓,妈呀,再也不碰这鬼东西了,每天让我过生日也不碰了。当身体里的火焰熄灭后,她发现,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开始变大,身体和双脚逐渐缩小,肉体离开了地面,像一朵云在空中飘来飘去。身体里充满了力量,又好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连眼皮也睁不开。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更神奇的是,从那以后她喜欢上老酒汗的味道和入口后的刺激,以及之后那种飘浮在空中的感觉。只不过,从那以后,她不再一口将一小杯老酒汗干掉,而是像父亲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抿一口,哈一口气,顺便去父亲碟子里夹一颗花生米,有时觉得一颗不够,又去夹一颗,再夹一颗。只有在这个时候,父亲脸上才会泛上一丝笑容,可她又疑惑地发现,父亲的眼睛闪现出若有若无的泪花。
这大概是梅巴丹对父亲最初的记忆。这个记忆是如此牢固和深邃,以致她此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酒或者想起酒,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那个场景。
在梅巴丹的记忆里,父亲将每个晚上的酒喝得异常漫长,如一个人跋涉在没有尽头的旅途。在最初几年,梅巴丹总是在饭桌上睡着,当她第二天醒来,已在床上。也就是说,在最初几年里,梅巴丹从未亲眼目睹父亲走到孤旅的尽头,她也无法想象父亲在旅途中遇见的风景,以及他在旅途中呈现出来的风景。
梅巴丹第一次陪父亲走完旅程,是在她去杭州读大学的前一夜。这是她第一次见识自己的酒量,父亲喝完一斤老酒汗,她一点没比他少喝,居然清醒异常,不但清醒,而且镇定。唯一不同的感觉是,身体仿佛比平时升高了许多,人与物在她眼里变小了,甚至世界也变小了。她有种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的感觉。而父亲喝到最后,已经不胜酒力,仿佛手里拿的不是酒杯,而是一生的重量。父亲在这个时候也是沉默的,唯一的不同是,每喝完一杯后,看着空杯子,嘴里喃喃地叫着:囡啊,囡啊。声音轻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也就是在此刻,梅巴丹似乎一下看透了父亲内心埋藏着的秘密。父亲坚硬如铁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近于透明的心脏。她突然觉得父亲是那么孤独和无助,像一个孤儿,需要温暖和关怀。
4.下列对文章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梅巴丹看来,父亲“太瘦”“白头翁”的形象很有玉树临风之感,这个形象很难让她与生命的迟暮联系在一起。
B.平日里父亲如同木头般沉默寡言,让梅巴丹有所忌惮,唯有喝酒时他才有更多情感的流露,这也是父亲最享受的时光。
C.作者擅长人物性格描写,用大量的笔墨直接展示父亲的心理活动,一个外表沉默寡言,内心细腻丰富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D.小说将父亲漫长的喝酒过程比作“没有尽头的旅途”,比喻手法生动形象,也意在照应下文陪父亲走完旅程的情节。
5.为什么“父亲的眼睛闪现出若有若无的泪花”?请结合上下文,简要分析画线句子。
6.小说多次写到“酒”,请简要分析“酒”在文中有哪些作用?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仙境
哲贵
从家开车到越剧团,大约要二十分钟。车子一发动,余展飞就兴奋了,充满力量,跃跃欲试。
到了越剧团,舒晓夏已经化好装,正在排练厅里。她看见余展飞进来,朝他看一眼,然后两人直奔化装间。
这是余展飞的习惯,也是他的态度:即使是排练,即使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也要化装,也要穿上戏服。
他和舒晓夏第几次排这个戏了?起码有几千次吧,甚至更多。
父亲余全权是信河街著名的皮鞋师傅,绰号皮鞋权。余展飞喜欢父亲,是因为父亲没有将皮鞋当作商品,商品是没有感情的,而他对待每一双皮鞋,都像对待儿子。余展飞也是将皮鞋当作人来对待的,无论是哪种皮鞋,余展飞都是喜欢的。无论是他做的,还是别人拿来修补的,只要到他手里,他都会让它们发出独特的光芒,给它们全新生命。
余展飞是在父亲的皮鞋店当学徒的第三个年头“认识”的舒晓夏。农历十月二十五,越剧团在皮鞋店对面演了《盗仙草》,舒晓夏演白素贞。她一身白色打扮,头上戴着一个银色蛇形头箍,脸是粉红的,眼睛是黑的,眼线画得特别长,几乎连着鬓角。美得不真实,美得惊心动魄。余展飞被白素贞“击中”了,迷住了。看到白素贞他突然自卑起来,无端地忧伤起来,无端地觉得自己完蛋了,这辈子没希望了。散场后,佘展飞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去越剧团,我要唱《盗仙草》,我要演白素贞。
他回到店里,对父亲说:“我要去学戏,我要唱越剧。”
“我要去学戏,我要唱越剧。”
那一个月里,余展飞只说一句话,其他什么事也不干。父亲很是无奈。他答应让余展飞学越剧,但只是业余,主业还是做皮鞋。
余展飞答应了。
父亲找到自己的酒友——信河街越剧团的鼓手,鼓手问余展飞想学什么,余展飞说他想学《盗仙草》,想当白素贞。鼓手一听就笑了,说:“要学《盗仙草》,想当白素贞,只能找俞小茹老师。俞老师是第一代白素贞,她的学生舒晓夏是第二代白素贞。”
鼓手带他去见俞小茹老师。俞老师心想,这孩子也就是一时心热,吃些苦头,自然知难而退。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余展飞是真下了狠心学戏,什么苦都能吃。俞老师让他练拿大顶,让他拿三分钟,他一定拿十分钟。俞老师让他拿十五分钟,他一定拿半个钟头。他做皮鞋时练,吃饭时练,睡觉也练。
余展飞第一次在剧团正式登台,是两年后的汇报演出,听说信河街文化局局长也来“观摩”。俞老师安排他演《盗仙草》。余展飞一直想让舒晓夏看看自己演的白素贞,他想让她知道,是她演的白素贞帮他打开一扇大门,让他突然从现实生活中飞起来,让他看到,除了皮鞋,他的生活还有梦想。
一上台,余展飞就忘记了音乐,他不需要音乐,他要的是仙草。音乐似乎又是存在的,变成一种提醒,让他不断向前、不断飞翔的提醒。
随着锣鼓声,台上的白素贞使用了“莲步水上漂”。他确实是“漂”上去,腾云驾雾,晃晃悠悠,却又风驰电掣。在舞台上转了小半圈,又回到右侧,他一抬头,开口喝道:峨眉山。舒晓夏能感觉到,这声音是一支射向峨眉山的利箭,穿破云雾,不达目的绝不回头。
回到台下,余展飞依然沉浸在那种情绪和情节之中,白素贞口衔仙草,飞向家中的许仙。他似乎听到舞台下巨大的掌声,看到俞老师跑到后台,激动地抱住他,不停地跺脚。
那次“演出”后,局长特批他进越剧团。进越剧团演戏,是余展飞这两年来的梦想。可是,当真正要成为专业演员时,当他即将成为真正的白素贞时,他又犹豫了。这意味着,他将抛弃皮鞋店和皮鞋厂。他只说:“我没问题,我回去问问我爸。”
俞老师托鼓手去做父亲的工作,鼓手回去问了俞老师一句话:“你说做生意和唱戏哪个有前途?”
之后,余展飞选择进入父亲的皮鞋厂,他把工厂顶楼的一个房间装修成排练厅,下班后,他会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
余展飞“主政”皮鞋厂后,做了几个“大动作”:第一是改厂名,将原来的“皮鞋佬”,改成“灵芝草”;第二是将工厂改成集团公司,工厂带有计划经济痕迹,而公司是市场经济产物;第三是花十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开出五千家专卖店,他要让“灵芝草”开遍各地;第四是“灵芝草集团公司”上市,敲锣当天,他个人市值三十三亿。
他依然每天会去公司排练室坐坐,有时会独自唱一段,或者练一阵花枪。有时只是坐坐,什么也没做,也就够了。
7.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想到排练就激动兴奋,即使是两个人排练,余展飞也要化装、穿戏服,这些表现了他对越剧的热爱和虔诚。
B.余展飞把皮鞋当作有生命的人来对待,来喜欢,所以他在当专业越剧演员还是做皮鞋中最终选择了做皮鞋。
C.文中插入余展飞初识舒晓夏的情节,突出舒晓夏饰演的白素贞的惊心动魄之美,交代余展飞学越剧的原因。
D.小说语言整体平实朴素,局部又富有文采,两种风格分别契合现实生活和余展飞向往的艺术境界的特点。
8.请分析小说中画横线部分的作用。
9.小说题为“仙境”,请结合文本概括其丰富意蕴。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化蝶
哲贵
讨论会开始了。
这个会议对剑湫来讲意义非凡,是她的“施政宣言”。她当这个团长,就两件事:排新戏和出新人。在剑湫看来,排新戏和出新人是相辅相成的——将新戏排出来,成为经典名剧,名剧催生名角。反之,也只有名角才能将一个戏经典化——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个戏,让一个戏起死回生。
还是拿老戏做文章。当然也可以排新戏,新戏的好处是,一张白纸,怎么画都行。但风险也是明显的,新戏缺少积淀,缺少厚重感,显得浅薄。排老戏当然也不容易,像《梁祝》这样的经典剧目,多少代人的心血结晶,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唱词,甚至每一个表情,都已印刻在观众心中,特别是那些老戏迷,改一句都不允许,那是欺师灭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如果要排老戏,必须出新,不出新就不能“出彩”,不“出彩”就没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就没有好结果。问题是怎么出新?
按照剧团惯例,先开会讨论剧本改编,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参加人员主要是这么几位:杜文灯和梅如烟是剧团顾问,重大的事,要邀请她们参加,她们的资历在那里,威望在那里,艺术修养在那里,她们的意见至关重要;加上编剧和主要演员剑湫和肖晓红。好了,五位“首脑”到齐,可以讨论了。
剑湫是召集人,也是主持人,她先发言。剑湫保留了原剧基本框架,做了四处调整:第一,充实了第一场“思读”的内容,突出祝英台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识,渴望自由,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种子”;第二,拿掉“山伯临终”那一场,她不让梁山伯死,在戏里弄死一个人太容易,活下去才难;第三,她将“楼台会”和“祝父逼嫁”次序对调,“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场“哭坟”拿掉,梁山伯没死,哭什么坟?改成“私奔”,她要让祝英台和梁山伯私奔,剧名就叫《私奔》。
剑湫说,这次改编就一个目的:让这个戏现代起来,让年轻观众走进我们剧场。就这么简单。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戏曲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让年轻的观众买票走进剧场是所有戏曲从业人员的梦想。多么美好的愿望。
剑湫说完,会议室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最先发言的是杜文灯。杜文灯其实不想先发言,她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梅如烟。梅如烟是演旦角的,演祝英台是她的拿手戏,应该由她先开口。但梅如烟没有开口,手一直扶着脑袋,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杜文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最先说道:
“《梁祝》原本是悲剧,这么一改,成了喜剧,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老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要考虑。”杜文灯提的意见太有道理了,《梁祝》是经典悲剧,已经深入人心,改成喜剧,确实有风险,甚至是冒险。这时,剑湫的“一根筋”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有新,才能出其不意,才能险中求胜。我就是要借这次改编,拿出一部不一样的《梁祝》,塑造出不一样的生角和旦角。”
杜文灯有点下不来台了,但她是“老艺术家”,是前辈,是不会跟晚辈“一般见识”的,她只是“微笑”——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在很多时候,“微笑”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武器。
大家都转头看肖晓红。剑湫说到这个份儿上,肖晓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可是,让肖晓红怎么回答?老实说,剑湫这么改,她接受不了,不“哭坟”了,不“化蝶”了,最经典的戏没了,还是《梁祝》吗?可她也知道剑湫说的没错,如果按照老路子演,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铤而走险,才有可能出新。所以,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烟,想听听梅如烟的意见。当然,也是转移“目标”。但梅如烟不看她,依然微闭着眼睛,谁也不看,又好像谁都看了。
还是杜文灯发话了,“微笑”着对肖晓红说:“你是艺术总监,你谈谈想法。”
还有退路吗?有人拿“枪”顶着后脑勺了。肖晓红只能硬着头皮上:“我觉得,剑湫团长的改编,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是对的,一开始加强祝英台追求自我、向往自由的性格,她能够女扮男装去杭州读书,为后来的私奔打下很扎实的基础。这么改编是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很讨巧,也很有新意。”
停了一下,肖晓红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
“我觉得,杜文灯顾问说的也很有道理。将悲剧变成了喜剧,特别是对经典剧目的改编,确实既要考虑年轻观众的感受,更要考虑老观众的感受。”
肖晓红发言就到这里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有说。“支持”了剑湫,也“支持”了杜文灯,谁都没得罪。这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既合情合理,又模棱两可。
接下来是编剧发言,编剧站在杜文灯一边。编剧的心态可以理解,改编剧本是他的事,剑湫将他的事干了,这不是砸他的饭碗吗?当然不干。
这就形成了对峙。如果说肖晓红属于中立的话,杜文灯和编剧形成了一个阵营。这个时候,梅如烟的发言显得尤为重要,她的态度不只是对艺术的讨论,而且是“站队”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
形成这个阵势,有剑湫和肖晓红的原因,但也不完全只是她们的原因。剧团的人都知道,剑湫和肖晓红背后,站着各自的师傅——杜文灯和梅如烟。
梅如烟的发言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她“支持”了剑湫。她“醒过来了”,脸上浮现着“微笑”,说:
“我老了,退休了,头晕脑涨,本不该来开会和说胡话。”
她说的这句话,当然指的是自己,可是,在座的人都听得出来,也暗指杜文灯。她接着说:
“我这个顾问只是随便挂个名的。剧团叫我来参加会议,来点个卯,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出个态度。我支持剑湫。我自己做不了事了,不能阻碍剧团做事,更不能在边上指手画脚。”
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杜文灯听完,当即想离席。但她是体面人,懂得优雅。于是脸上也泛出和梅如烟一样的笑容,对着梅如烟,更是对着肖晓红:
“我完全同意梅如烟顾问的话,更不会反对剑湫团长对新戏的改编。对于肖晓红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只是提了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而已。”
这是典型的杜文灯方式。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更不是一个将话说死的人,她是话里有话,是有所指的。
剑湫太了解她们两个的风格了,两个人刀光剑影“斗”了半辈子,还没有“停战”的意思。可如果缺少了这种“角力”,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话说到这份儿,剑湫看了看会议室里的人,说:
“那就先排起来吧!”
团长“拍板”了,该说的话说了,该留的余地留了。散会。
(有删改)
10.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中对杜文灯的“微笑”做了特别的描写。“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形象地写出了杜文灯的勉强和做作,表现了对剑湫观点的不认同。
B.文中“施政宣言”“首脑”“政治立场”“停战”等词语大词小用,不仅产生了一定的幽默效果,同时也衬托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C.小说在写肖晓红的表态之前,不仅分析了她的矛盾心理,还运用细节描写,突出了她渴望梅如烟替她挡枪的眼神,这些都表明她缺乏主见。
D.小说最后部分写了剑湫对两位老艺术家的争强斗胜进行了总结,为前文做出了补充解释。同时通过议论点出了其积极意义,有助于深化小说主旨。
11.文中画横线句说“可如果缺少了这种‘角力’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请结合小说内容谈谈如何看待这种“角力”。
12.小说以“化蝶”为题,请分析其意蕴。
【答案】
C“则是因为他碍于情面,顾及叔侄关系”有误,叔叔“缓和”的原因是对子辈的善意和关爱,更是希望图谱能够传承下去。
①展现父亲痛苦、愧疚、自责、逃避等复杂的心绪;②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兴趣;③与后文叔叔释疑、柯一璀犯难等情节相呼应。
3.①通过写父亲和柯一璀面对家族责任担当的纠结与痛苦,思考家族传承与个人追求之间的矛盾;②通过几代人在情义与利益间的选择,表现人性的真实与美好;③通过传统继承规则与现代发展实际间的矛盾,探索传统技艺的传承与现代文明融合的路径。
4.C“用大量的笔墨直接展示父亲的心理活动”错误,从文中来看,父亲的心理活动多是通过表情、行为、语言来表现的。
5.①酒是父亲“快乐和忧伤的玩具”,“泪花”是他酒后情绪的流露;②饮酒的过程如一场孤旅,坚硬如铁的外表下包裹着孤独无助、渴望关怀的心。
6.①“酒”是贯穿小说重要的线索通过饮酒,女儿一步步了解了父亲,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②丰富了父亲的人物形象,父亲外刚内柔、温情脉脉的形象是通过饮酒来展现的;③有助于表现小说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酒让梅巴丹明白:父亲衰老的时候也需要自己的关怀。
7.B“所以他在当专业越剧演员还是做皮鞋中最终选择了做皮鞋”错误。结合原文“我没问题,我回去问问我爸”“俞老师托鼓手去做父亲的工作,鼓手回去问了俞老师一句话:‘你说做生意和唱戏哪个有前途?’”,可见不是余展飞要选择做皮鞋,而是他父亲认为做皮鞋有前途。8.①人物上,表现了余展飞表演技艺的高超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
②结构上,照应上文余展飞刻苦练戏的情节,并为后文余展飞在工厂顶楼建排练厅练戏埋下伏笔。
③效果上,优美的语言,形象的描写,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9.①指越剧《盗仙草》中浪漫的艺术境界;
②指余展飞陶醉、向往的唱越剧的艺术生活;
③也指余展飞能兼顾创业和艺术而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
10.C“这些都表明她缺乏主见”错误,根据“老实说,剑湫这么改,她接受不了……可她也知道剑湫说的没错,如果按照老路子演,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铤而走险,才有可能出新。所以,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可知,她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得罪人11.①这种“角力”是一种互不服输的体现,有助于促进她们对艺术的追求;②这种“角力”虽然“刀光剑影”明争暗斗,但这正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失去了对手,生活便会了无趣味;③这也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角力,促进了戏曲人的新老交替,是传统戏曲得以延续的推动力。
12.①是指戏曲《梁祝》中的经典情节;②希望《梁祝》创新改编能产生“蝶变”的效果;③是指传统戏曲要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时代要素,走出没落,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典;④是指传统戏曲人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图谱
哲贵
一路沿瓯江而上。过了积谷山,就到了桃源。叔叔领着柯一璀爬山。山中多是乔木,约两人高,有的成排列队,有的孤独站立。草木茂盛,将青石板路遮盖得若隐若现。山高,路远,缠绵又曲折。当柯一璀跟随叔叔站定后,回身一看,已在山腰,瓯江变成一条小水沟,流向看不见尽头的东边。东边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是柯一璀第二次来祭祖。上一次是十二年前,他刚刚考上博士,父亲难得地带他一起回来。他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在这里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哭得比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还伤心。
叔叔对着墓圹拜了三拜,回过头来,看着柯一璀,严肃地说:“你也来拜一拜。”声音虽轻,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身为大学教授的柯一璀,内心并没有排斥这种仪式,他要拜的是先祖,要拜的是自己的过去甚至未来。多少年了,他一直对家族的过往充满好奇,这不仅因为他的专业——全域旅游规划,更缘于这是父亲生长的地方,也是他的“根”。但父亲却闭口不谈。今年开春,父亲去世,这些便成为一个谜,似乎更难解开了。
柯一璀双手合十,拜了三拜,身体有股热流突然涌上来。
叔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说的竟是他心心念念的柯家历史:一个叫金三清的人,他是清朝宫廷里御用的戏剧盔头制作工匠,手艺精湛绝伦。后来生病出了宫,一路南行,在信河街这里落了脚,租住柯家的房子。柯家大儿子柯辅良是个热心肠,见他独身一人又疾病缠身,便时常关照。后来两人义结金兰。金三清靠手艺维生,给庙里的菩萨和戏班制作盔头,忙不过来时,就请柯辅良帮忙。金三清是有心传他手艺,柯辅良也有心要学,两人都没讲破。八年后,金三清病重,临终前,他将一百四十八幅京剧盔头图谱和三百六十道制作工序图谱交给盟弟柯辅良。后来,柯辅良以制作京剧盔头名满天下,他为了感恩盟兄,在每个京剧盔头内打上三个字:柯三清。“柯三清”于是成了柯家京剧盔头的招牌。柯辅良将两份图谱立为传家宝,定下家规:“柯三清”京剧盔头制作的手艺传大不传小,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叔叔的讲述停住了。四周寂静。叔叔眼睛直视他:“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柯一璀似乎知道,又不完全知道。叔叔接着说:“我要在列祖列宗面前,将两份图谱还给你。因为这两份图谱属于你父亲”
叔叔将那个铁皮盒子递给柯一璀,眼神是毅然的,没有商量余地。柯一璀觉得他手里捧的不是铁皮盒子,也不是两份图谱,而是一份责任。问题在于,这是他无力承担的责任。他犹豫了一下,将铁皮盒子重新推回叔叔怀里。叔叔果断地将铁皮盒子推回来:“当年你父亲为了去参军,已经推卸了一次责任,你不能再推卸。”
一切谜团似乎都在叔叔这句话里得到了答案。柯一璀好像突然理解了父亲不常回信河街、不提家族的原因。同时,他也突然理解了叔叔逢酒必喝和逢喝必醉的原因。对于叔叔来讲,或许更愿意当一个游侠,行侠仗义,周游天下。
可是,柯一璀也有一个大问题,他问叔叔:“你将这个铁皮盒子交给我,我怎么办?”
“怎么办是你的事。”叔叔脱口而出。停了一下,缓和了口气说,“你也可以来跟我学。”
这是柯一璀愿意的,但也是不现实的。他非常愿意了解并参与到京剧盔头制作中来,但他只能是一个参与者,甚至可以是当事者,绝不可能成为主事者。不是不愿意,是不能。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柯一璀突然惊觉,这个借口,可能也是父亲当年的借口。
柯一璀跟随叔叔下了山,回到祖屋,叔叔带他到五楼。这里陈列着叔叔亲手制作的一百四十八个京剧盔头。叔叔告诉他,柯一肖开价一千万,要将这批盔头买走,他不卖。柯一璀昨天刚见过这个堂弟。参观了他经营的柯氏文化公司和他自己筹建的京剧盔头博物馆。他是叔叔的儿子,在信河街长大的他和一直在北京生活的自己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昨天,当堂弟兴奋地说起京剧盔头制作,说起这瑰宝属于柯家、属于社会、更属于未来的那一刻,柯一璀的内心是震撼的。
柯一璀在五楼整整待了一个下午,叔叔将每一个盔头的人物特点和构造原理讲解给柯一璀听。柯一璀一边录像一边作笔记。他知道,这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下午六点,柯一璀离开祖屋,叔叔送他出门之前,对他讲:“这批盔头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你。”
柯一璀愣住了。
回到饭店,柯一璀退了房,叫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车。当车开出半个钟头后,他突然问司机:
“知道柯氏公司吗?”
司机说:“做京剧盔头的,很有名!”
柯一璀顿了顿,说:“掉头去那里。”
司机说:“你要买京剧盔头?
柯一璀没有回答,他觉得身体里有股热流想喷涌而出。
(有改动)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以大学教授柯一璀的视角讲述回乡经历,引出关于图谱的故事,通过其见闻和感受展现了几代人鲜活的形象。
B.开篇对山景和江水的环境描写,营造了静谧悠远、肃穆庄重的氛围,烘托了柯一璀的心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C.叔叔脱口而出“怎么办是你的事”,透露出郁积多年的无奈和埋怨;转而“缓和”则是因为他碍于情面,顾及叔侄关系。
D.小说借叔叔的讲述和主人公的回忆,插叙有关家族、父亲和柯一肖的情节,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丰富了作品意蕴。
2.小说中写父亲祭祖时痛哭和不愿提及家族的细节,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分析。
3.关注社会,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是小说创作的传统之一。结合文本,谈谈这篇小说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考。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父亲与酒
哲贵
梅巴丹不是没有想过死亡问题,可父亲才六十多岁呀,每顿能喝一斤白酒,连感冒药也没有吃过,怎么可能跟死亡发生联系?如果一定要说问题,那就是太瘦,像一根箸,可梅巴丹认为这正是父亲的优点,加上他一头白发,很是玉树临风。在梅巴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满头银丝。她觉得父亲生来就是个“白头翁”,这才是想象中父亲应有的形象。她以为,父亲这个形象是永恒的。她以此为荣。
父亲是个雕刻艺人,每天跟木头打交道,平时也像木头一样沉默,几乎一句话也不说,虽然梅巴丹并不十分怵他,但多少有所忌惮。唯一例外是父亲喝酒的时候,即在晚上收工之后。在他们家不大的饭桌上,端上梅巴丹的米饭和她喜欢吃的对虾。父亲晚上不吃主食,只喝酒,喝的是江心屿牌老酒汗。下酒菜是老三样:花生米、鸡爪皮和猪耳朵。逢到节日,会加一个菜:鱼生。鱼生就是比小指还细的小带鱼用酒糟加盐腌制而成,闻起来有股腥臭味,入嘴芬芳鲜美。
梅巴丹六周岁生日那天,父亲给她煮了一碗长寿面,煎了两个荷包蛋,还有一只又大又肥的红烧,同时,父亲给她倒一小杯老酒汗。此酒系采集老酒煎蒸时所凝结的汗珠状液体而得。这是梅巴丹第一次真正接触白酒,她之前每天晚上裹着这股刺鼻的味道入眠,可那味道跟她没有关系,那是父亲快乐和忧伤的玩具。所以,当那杯老酒汗放在面前时,她有点猝不及防。她看了看父亲,父亲也看了看她,没有开口。梅巴丹没有再说什么,小心翼翼端起杯子,她发现白酒满出杯沿,在杯口跳动。这让她紧张,赶紧将酒倒进喉咙。一口下去,身体立即被点燃了,好似有一道闪电,要将她由内到外撕裂。她丢下杯子,在地上乱蹦乱跳,在餐厅里一圈又一圈地跑。起码跑了十分钟,身体里的火焰才慢慢熄灭。她一边跑一边狗一样吐着舌头,哇啦哇啦地叫,心里暗暗发誓,妈呀,再也不碰这鬼东西了,每天让我过生日也不碰了。当身体里的火焰熄灭后,她发现,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开始变大,身体和双脚逐渐缩小,肉体离开了地面,像一朵云在空中飘来飘去。身体里充满了力量,又好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连眼皮也睁不开。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更神奇的是,从那以后她喜欢上老酒汗的味道和入口后的刺激,以及之后那种飘浮在空中的感觉。只不过,从那以后,她不再一口将一小杯老酒汗干掉,而是像父亲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抿一口,哈一口气,顺便去父亲碟子里夹一颗花生米,有时觉得一颗不够,又去夹一颗,再夹一颗。只有在这个时候,父亲脸上才会泛上一丝笑容,可她又疑惑地发现,父亲的眼睛闪现出若有若无的泪花。
这大概是梅巴丹对父亲最初的记忆。这个记忆是如此牢固和深邃,以致她此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酒或者想起酒,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那个场景。
在梅巴丹的记忆里,父亲将每个晚上的酒喝得异常漫长,如一个人跋涉在没有尽头的旅途。在最初几年,梅巴丹总是在饭桌上睡着,当她第二天醒来,已在床上。也就是说,在最初几年里,梅巴丹从未亲眼目睹父亲走到孤旅的尽头,她也无法想象父亲在旅途中遇见的风景,以及他在旅途中呈现出来的风景。
梅巴丹第一次陪父亲走完旅程,是在她去杭州读大学的前一夜。这是她第一次见识自己的酒量,父亲喝完一斤老酒汗,她一点没比他少喝,居然清醒异常,不但清醒,而且镇定。唯一不同的感觉是,身体仿佛比平时升高了许多,人与物在她眼里变小了,甚至世界也变小了。她有种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的感觉。而父亲喝到最后,已经不胜酒力,仿佛手里拿的不是酒杯,而是一生的重量。父亲在这个时候也是沉默的,唯一的不同是,每喝完一杯后,看着空杯子,嘴里喃喃地叫着:囡啊,囡啊。声音轻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也就是在此刻,梅巴丹似乎一下看透了父亲内心埋藏着的秘密。父亲坚硬如铁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近于透明的心脏。她突然觉得父亲是那么孤独和无助,像一个孤儿,需要温暖和关怀。
4.下列对文章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梅巴丹看来,父亲“太瘦”“白头翁”的形象很有玉树临风之感,这个形象很难让她与生命的迟暮联系在一起。
B.平日里父亲如同木头般沉默寡言,让梅巴丹有所忌惮,唯有喝酒时他才有更多情感的流露,这也是父亲最享受的时光。
C.作者擅长人物性格描写,用大量的笔墨直接展示父亲的心理活动,一个外表沉默寡言,内心细腻丰富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D.小说将父亲漫长的喝酒过程比作“没有尽头的旅途”,比喻手法生动形象,也意在照应下文陪父亲走完旅程的情节。
5.为什么“父亲的眼睛闪现出若有若无的泪花”?请结合上下文,简要分析画线句子。
6.小说多次写到“酒”,请简要分析“酒”在文中有哪些作用?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仙境
哲贵
从家开车到越剧团,大约要二十分钟。车子一发动,余展飞就兴奋了,充满力量,跃跃欲试。
到了越剧团,舒晓夏已经化好装,正在排练厅里。她看见余展飞进来,朝他看一眼,然后两人直奔化装间。
这是余展飞的习惯,也是他的态度:即使是排练,即使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也要化装,也要穿上戏服。
他和舒晓夏第几次排这个戏了?起码有几千次吧,甚至更多。
父亲余全权是信河街著名的皮鞋师傅,绰号皮鞋权。余展飞喜欢父亲,是因为父亲没有将皮鞋当作商品,商品是没有感情的,而他对待每一双皮鞋,都像对待儿子。余展飞也是将皮鞋当作人来对待的,无论是哪种皮鞋,余展飞都是喜欢的。无论是他做的,还是别人拿来修补的,只要到他手里,他都会让它们发出独特的光芒,给它们全新生命。
余展飞是在父亲的皮鞋店当学徒的第三个年头“认识”的舒晓夏。农历十月二十五,越剧团在皮鞋店对面演了《盗仙草》,舒晓夏演白素贞。她一身白色打扮,头上戴着一个银色蛇形头箍,脸是粉红的,眼睛是黑的,眼线画得特别长,几乎连着鬓角。美得不真实,美得惊心动魄。余展飞被白素贞“击中”了,迷住了。看到白素贞他突然自卑起来,无端地忧伤起来,无端地觉得自己完蛋了,这辈子没希望了。散场后,佘展飞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去越剧团,我要唱《盗仙草》,我要演白素贞。
他回到店里,对父亲说:“我要去学戏,我要唱越剧。”
“我要去学戏,我要唱越剧。”
那一个月里,余展飞只说一句话,其他什么事也不干。父亲很是无奈。他答应让余展飞学越剧,但只是业余,主业还是做皮鞋。
余展飞答应了。
父亲找到自己的酒友——信河街越剧团的鼓手,鼓手问余展飞想学什么,余展飞说他想学《盗仙草》,想当白素贞。鼓手一听就笑了,说:“要学《盗仙草》,想当白素贞,只能找俞小茹老师。俞老师是第一代白素贞,她的学生舒晓夏是第二代白素贞。”
鼓手带他去见俞小茹老师。俞老师心想,这孩子也就是一时心热,吃些苦头,自然知难而退。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余展飞是真下了狠心学戏,什么苦都能吃。俞老师让他练拿大顶,让他拿三分钟,他一定拿十分钟。俞老师让他拿十五分钟,他一定拿半个钟头。他做皮鞋时练,吃饭时练,睡觉也练。
余展飞第一次在剧团正式登台,是两年后的汇报演出,听说信河街文化局局长也来“观摩”。俞老师安排他演《盗仙草》。余展飞一直想让舒晓夏看看自己演的白素贞,他想让她知道,是她演的白素贞帮他打开一扇大门,让他突然从现实生活中飞起来,让他看到,除了皮鞋,他的生活还有梦想。
一上台,余展飞就忘记了音乐,他不需要音乐,他要的是仙草。音乐似乎又是存在的,变成一种提醒,让他不断向前、不断飞翔的提醒。
随着锣鼓声,台上的白素贞使用了“莲步水上漂”。他确实是“漂”上去,腾云驾雾,晃晃悠悠,却又风驰电掣。在舞台上转了小半圈,又回到右侧,他一抬头,开口喝道:峨眉山。舒晓夏能感觉到,这声音是一支射向峨眉山的利箭,穿破云雾,不达目的绝不回头。
回到台下,余展飞依然沉浸在那种情绪和情节之中,白素贞口衔仙草,飞向家中的许仙。他似乎听到舞台下巨大的掌声,看到俞老师跑到后台,激动地抱住他,不停地跺脚。
那次“演出”后,局长特批他进越剧团。进越剧团演戏,是余展飞这两年来的梦想。可是,当真正要成为专业演员时,当他即将成为真正的白素贞时,他又犹豫了。这意味着,他将抛弃皮鞋店和皮鞋厂。他只说:“我没问题,我回去问问我爸。”
俞老师托鼓手去做父亲的工作,鼓手回去问了俞老师一句话:“你说做生意和唱戏哪个有前途?”
之后,余展飞选择进入父亲的皮鞋厂,他把工厂顶楼的一个房间装修成排练厅,下班后,他会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
余展飞“主政”皮鞋厂后,做了几个“大动作”:第一是改厂名,将原来的“皮鞋佬”,改成“灵芝草”;第二是将工厂改成集团公司,工厂带有计划经济痕迹,而公司是市场经济产物;第三是花十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开出五千家专卖店,他要让“灵芝草”开遍各地;第四是“灵芝草集团公司”上市,敲锣当天,他个人市值三十三亿。
他依然每天会去公司排练室坐坐,有时会独自唱一段,或者练一阵花枪。有时只是坐坐,什么也没做,也就够了。
7.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想到排练就激动兴奋,即使是两个人排练,余展飞也要化装、穿戏服,这些表现了他对越剧的热爱和虔诚。
B.余展飞把皮鞋当作有生命的人来对待,来喜欢,所以他在当专业越剧演员还是做皮鞋中最终选择了做皮鞋。
C.文中插入余展飞初识舒晓夏的情节,突出舒晓夏饰演的白素贞的惊心动魄之美,交代余展飞学越剧的原因。
D.小说语言整体平实朴素,局部又富有文采,两种风格分别契合现实生活和余展飞向往的艺术境界的特点。
8.请分析小说中画横线部分的作用。
9.小说题为“仙境”,请结合文本概括其丰富意蕴。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化蝶
哲贵
讨论会开始了。
这个会议对剑湫来讲意义非凡,是她的“施政宣言”。她当这个团长,就两件事:排新戏和出新人。在剑湫看来,排新戏和出新人是相辅相成的——将新戏排出来,成为经典名剧,名剧催生名角。反之,也只有名角才能将一个戏经典化——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个戏,让一个戏起死回生。
还是拿老戏做文章。当然也可以排新戏,新戏的好处是,一张白纸,怎么画都行。但风险也是明显的,新戏缺少积淀,缺少厚重感,显得浅薄。排老戏当然也不容易,像《梁祝》这样的经典剧目,多少代人的心血结晶,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唱词,甚至每一个表情,都已印刻在观众心中,特别是那些老戏迷,改一句都不允许,那是欺师灭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如果要排老戏,必须出新,不出新就不能“出彩”,不“出彩”就没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就没有好结果。问题是怎么出新?
按照剧团惯例,先开会讨论剧本改编,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参加人员主要是这么几位:杜文灯和梅如烟是剧团顾问,重大的事,要邀请她们参加,她们的资历在那里,威望在那里,艺术修养在那里,她们的意见至关重要;加上编剧和主要演员剑湫和肖晓红。好了,五位“首脑”到齐,可以讨论了。
剑湫是召集人,也是主持人,她先发言。剑湫保留了原剧基本框架,做了四处调整:第一,充实了第一场“思读”的内容,突出祝英台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识,渴望自由,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种子”;第二,拿掉“山伯临终”那一场,她不让梁山伯死,在戏里弄死一个人太容易,活下去才难;第三,她将“楼台会”和“祝父逼嫁”次序对调,“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场“哭坟”拿掉,梁山伯没死,哭什么坟?改成“私奔”,她要让祝英台和梁山伯私奔,剧名就叫《私奔》。
剑湫说,这次改编就一个目的:让这个戏现代起来,让年轻观众走进我们剧场。就这么简单。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戏曲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让年轻的观众买票走进剧场是所有戏曲从业人员的梦想。多么美好的愿望。
剑湫说完,会议室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最先发言的是杜文灯。杜文灯其实不想先发言,她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梅如烟。梅如烟是演旦角的,演祝英台是她的拿手戏,应该由她先开口。但梅如烟没有开口,手一直扶着脑袋,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杜文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最先说道:
“《梁祝》原本是悲剧,这么一改,成了喜剧,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老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要考虑。”杜文灯提的意见太有道理了,《梁祝》是经典悲剧,已经深入人心,改成喜剧,确实有风险,甚至是冒险。这时,剑湫的“一根筋”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有新,才能出其不意,才能险中求胜。我就是要借这次改编,拿出一部不一样的《梁祝》,塑造出不一样的生角和旦角。”
杜文灯有点下不来台了,但她是“老艺术家”,是前辈,是不会跟晚辈“一般见识”的,她只是“微笑”——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在很多时候,“微笑”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武器。
大家都转头看肖晓红。剑湫说到这个份儿上,肖晓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可是,让肖晓红怎么回答?老实说,剑湫这么改,她接受不了,不“哭坟”了,不“化蝶”了,最经典的戏没了,还是《梁祝》吗?可她也知道剑湫说的没错,如果按照老路子演,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铤而走险,才有可能出新。所以,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烟,想听听梅如烟的意见。当然,也是转移“目标”。但梅如烟不看她,依然微闭着眼睛,谁也不看,又好像谁都看了。
还是杜文灯发话了,“微笑”着对肖晓红说:“你是艺术总监,你谈谈想法。”
还有退路吗?有人拿“枪”顶着后脑勺了。肖晓红只能硬着头皮上:“我觉得,剑湫团长的改编,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是对的,一开始加强祝英台追求自我、向往自由的性格,她能够女扮男装去杭州读书,为后来的私奔打下很扎实的基础。这么改编是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很讨巧,也很有新意。”
停了一下,肖晓红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
“我觉得,杜文灯顾问说的也很有道理。将悲剧变成了喜剧,特别是对经典剧目的改编,确实既要考虑年轻观众的感受,更要考虑老观众的感受。”
肖晓红发言就到这里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有说。“支持”了剑湫,也“支持”了杜文灯,谁都没得罪。这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既合情合理,又模棱两可。
接下来是编剧发言,编剧站在杜文灯一边。编剧的心态可以理解,改编剧本是他的事,剑湫将他的事干了,这不是砸他的饭碗吗?当然不干。
这就形成了对峙。如果说肖晓红属于中立的话,杜文灯和编剧形成了一个阵营。这个时候,梅如烟的发言显得尤为重要,她的态度不只是对艺术的讨论,而且是“站队”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
形成这个阵势,有剑湫和肖晓红的原因,但也不完全只是她们的原因。剧团的人都知道,剑湫和肖晓红背后,站着各自的师傅——杜文灯和梅如烟。
梅如烟的发言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她“支持”了剑湫。她“醒过来了”,脸上浮现着“微笑”,说:
“我老了,退休了,头晕脑涨,本不该来开会和说胡话。”
她说的这句话,当然指的是自己,可是,在座的人都听得出来,也暗指杜文灯。她接着说:
“我这个顾问只是随便挂个名的。剧团叫我来参加会议,来点个卯,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出个态度。我支持剑湫。我自己做不了事了,不能阻碍剧团做事,更不能在边上指手画脚。”
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杜文灯听完,当即想离席。但她是体面人,懂得优雅。于是脸上也泛出和梅如烟一样的笑容,对着梅如烟,更是对着肖晓红:
“我完全同意梅如烟顾问的话,更不会反对剑湫团长对新戏的改编。对于肖晓红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只是提了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而已。”
这是典型的杜文灯方式。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更不是一个将话说死的人,她是话里有话,是有所指的。
剑湫太了解她们两个的风格了,两个人刀光剑影“斗”了半辈子,还没有“停战”的意思。可如果缺少了这种“角力”,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话说到这份儿,剑湫看了看会议室里的人,说:
“那就先排起来吧!”
团长“拍板”了,该说的话说了,该留的余地留了。散会。
(有删改)
10.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中对杜文灯的“微笑”做了特别的描写。“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形象地写出了杜文灯的勉强和做作,表现了对剑湫观点的不认同。
B.文中“施政宣言”“首脑”“政治立场”“停战”等词语大词小用,不仅产生了一定的幽默效果,同时也衬托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C.小说在写肖晓红的表态之前,不仅分析了她的矛盾心理,还运用细节描写,突出了她渴望梅如烟替她挡枪的眼神,这些都表明她缺乏主见。
D.小说最后部分写了剑湫对两位老艺术家的争强斗胜进行了总结,为前文做出了补充解释。同时通过议论点出了其积极意义,有助于深化小说主旨。
11.文中画横线句说“可如果缺少了这种‘角力’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请结合小说内容谈谈如何看待这种“角力”。
12.小说以“化蝶”为题,请分析其意蕴。
【答案】
C“则是因为他碍于情面,顾及叔侄关系”有误,叔叔“缓和”的原因是对子辈的善意和关爱,更是希望图谱能够传承下去。
①展现父亲痛苦、愧疚、自责、逃避等复杂的心绪;②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兴趣;③与后文叔叔释疑、柯一璀犯难等情节相呼应。
3.①通过写父亲和柯一璀面对家族责任担当的纠结与痛苦,思考家族传承与个人追求之间的矛盾;②通过几代人在情义与利益间的选择,表现人性的真实与美好;③通过传统继承规则与现代发展实际间的矛盾,探索传统技艺的传承与现代文明融合的路径。
4.C“用大量的笔墨直接展示父亲的心理活动”错误,从文中来看,父亲的心理活动多是通过表情、行为、语言来表现的。
5.①酒是父亲“快乐和忧伤的玩具”,“泪花”是他酒后情绪的流露;②饮酒的过程如一场孤旅,坚硬如铁的外表下包裹着孤独无助、渴望关怀的心。
6.①“酒”是贯穿小说重要的线索通过饮酒,女儿一步步了解了父亲,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②丰富了父亲的人物形象,父亲外刚内柔、温情脉脉的形象是通过饮酒来展现的;③有助于表现小说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酒让梅巴丹明白:父亲衰老的时候也需要自己的关怀。
7.B“所以他在当专业越剧演员还是做皮鞋中最终选择了做皮鞋”错误。结合原文“我没问题,我回去问问我爸”“俞老师托鼓手去做父亲的工作,鼓手回去问了俞老师一句话:‘你说做生意和唱戏哪个有前途?’”,可见不是余展飞要选择做皮鞋,而是他父亲认为做皮鞋有前途。8.①人物上,表现了余展飞表演技艺的高超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
②结构上,照应上文余展飞刻苦练戏的情节,并为后文余展飞在工厂顶楼建排练厅练戏埋下伏笔。
③效果上,优美的语言,形象的描写,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9.①指越剧《盗仙草》中浪漫的艺术境界;
②指余展飞陶醉、向往的唱越剧的艺术生活;
③也指余展飞能兼顾创业和艺术而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
10.C“这些都表明她缺乏主见”错误,根据“老实说,剑湫这么改,她接受不了……可她也知道剑湫说的没错,如果按照老路子演,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铤而走险,才有可能出新。所以,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可知,她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得罪人11.①这种“角力”是一种互不服输的体现,有助于促进她们对艺术的追求;②这种“角力”虽然“刀光剑影”明争暗斗,但这正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失去了对手,生活便会了无趣味;③这也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角力,促进了戏曲人的新老交替,是传统戏曲得以延续的推动力。
12.①是指戏曲《梁祝》中的经典情节;②希望《梁祝》创新改编能产生“蝶变”的效果;③是指传统戏曲要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时代要素,走出没落,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典;④是指传统戏曲人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