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阐明推荐理由(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阐明推荐理由(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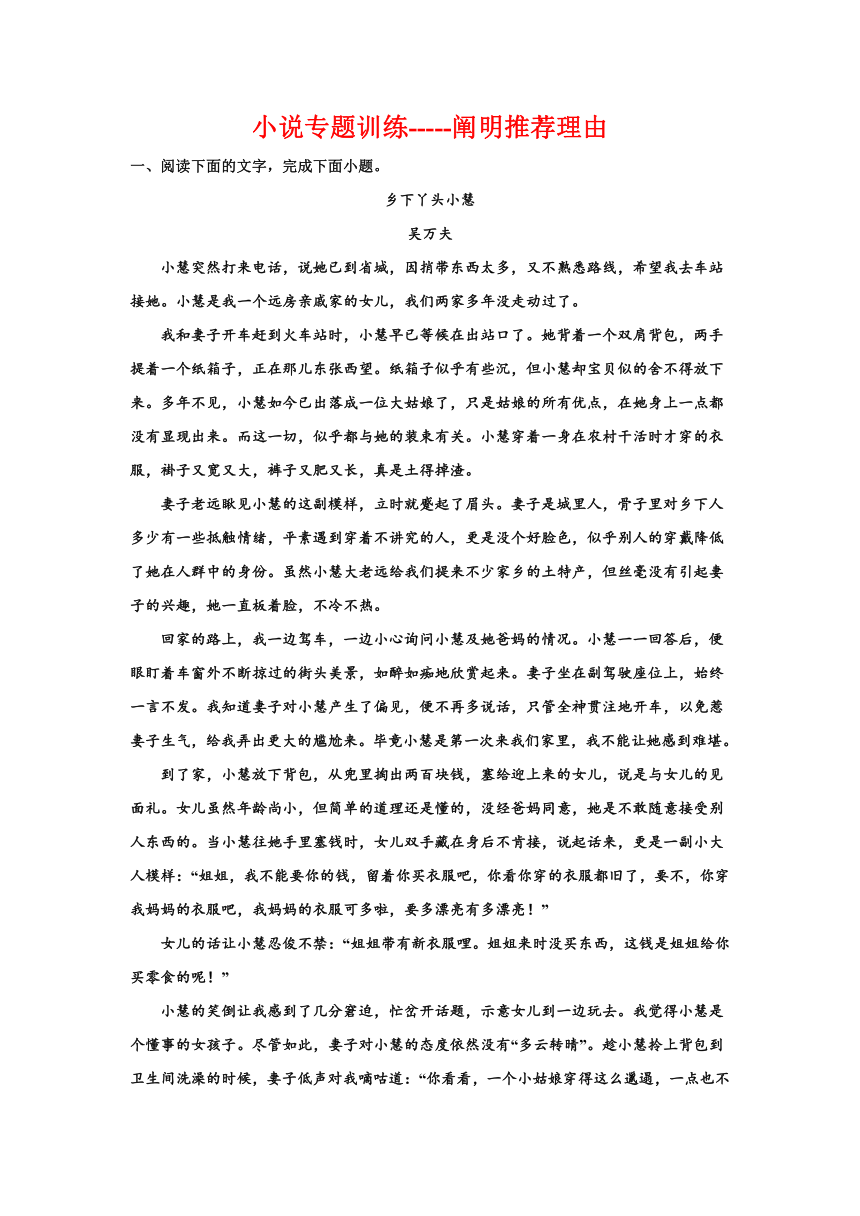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7.0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2-04 10:40:11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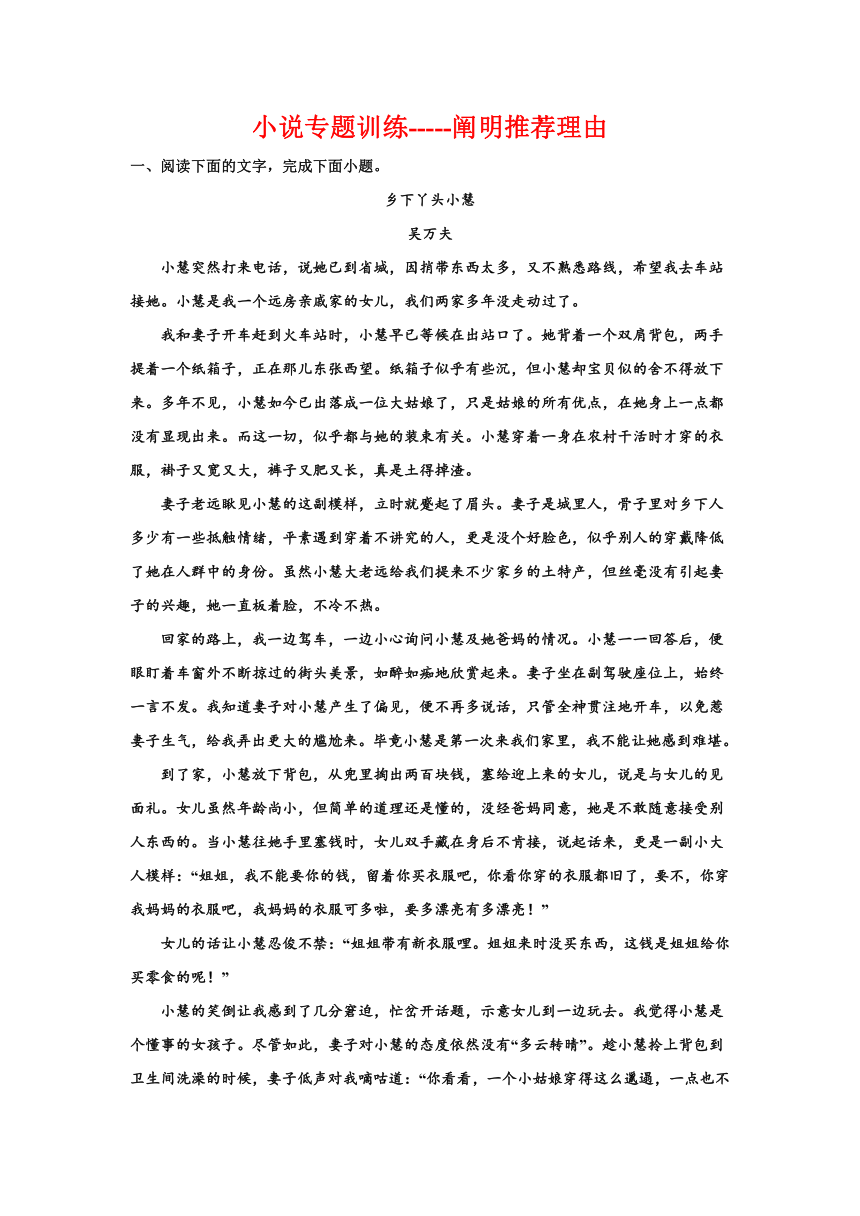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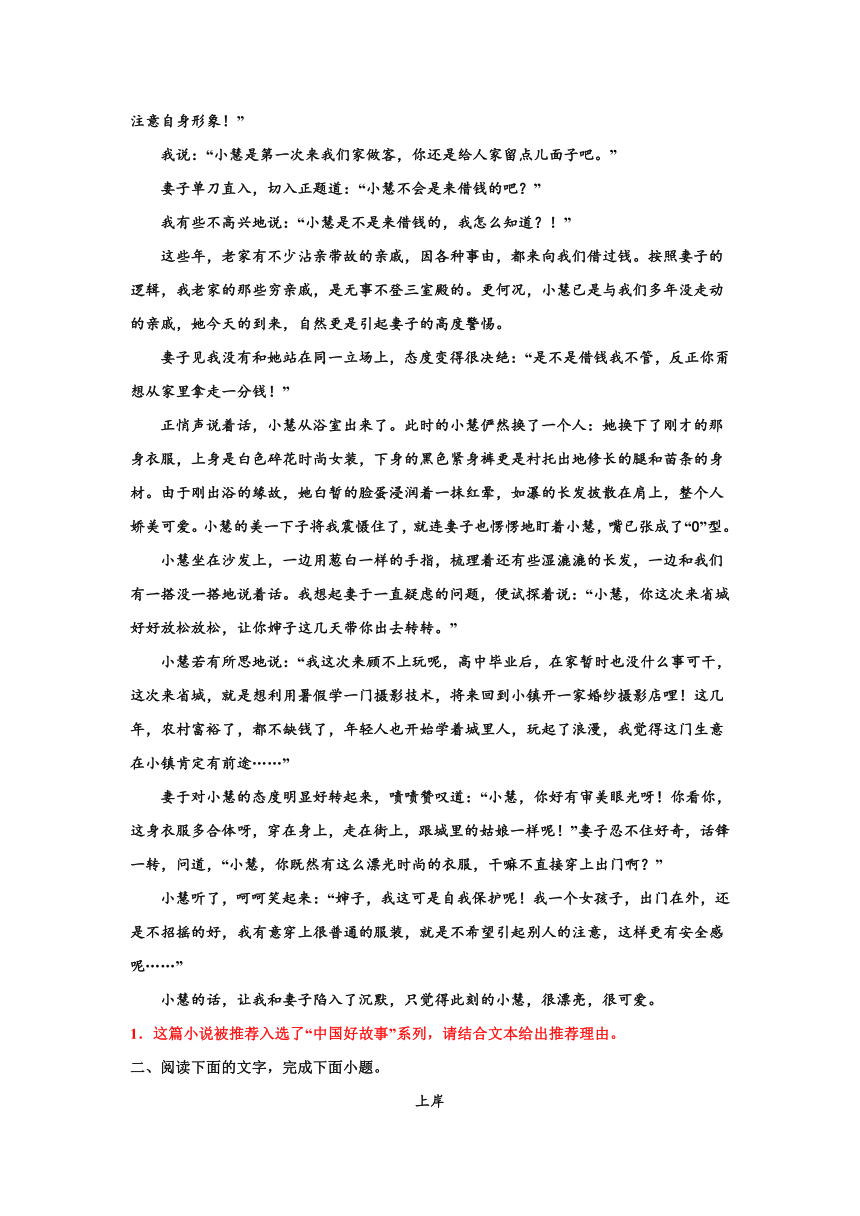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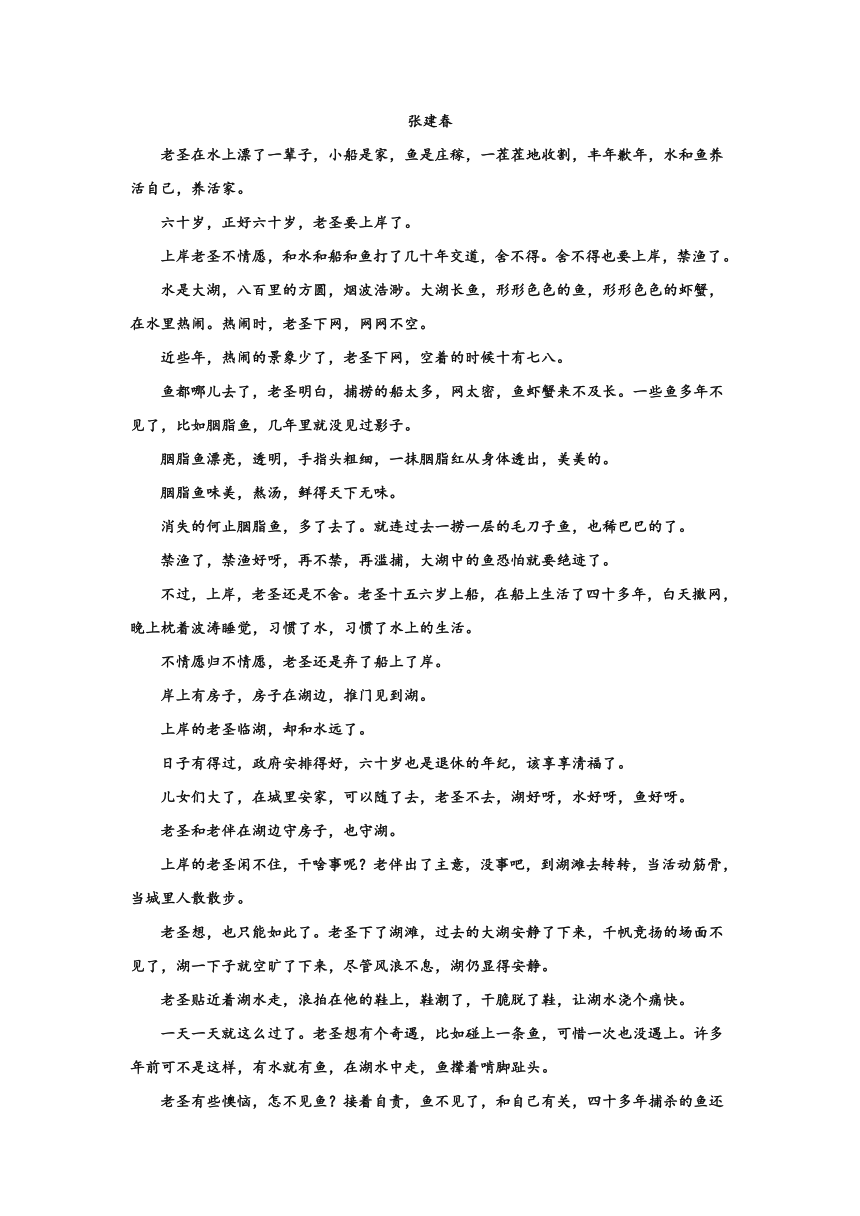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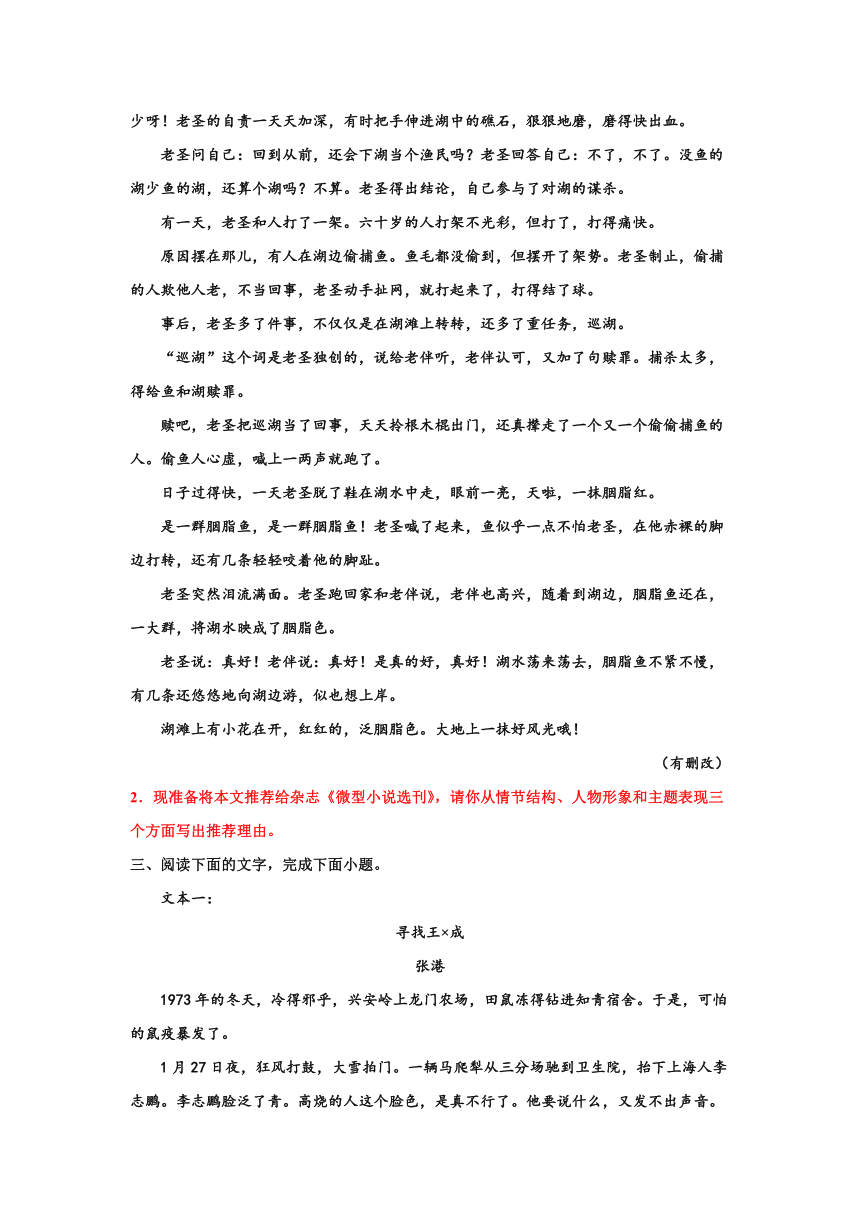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阐明推荐理由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下丫头小慧
吴万夫
小慧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已到省城,因捎带东西太多,又不熟悉路线,希望我去车站接她。小慧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女儿,我们两家多年没走动过了。
我和妻子开车赶到火车站时,小慧早已等候在出站口了。她背着一个双肩背包,两手提着一个纸箱子,正在那儿东张西望。纸箱子似乎有些沉,但小慧却宝贝似的舍不得放下来。多年不见,小慧如今已出落成一位大姑娘了,只是姑娘的所有优点,在她身上一点都没有显现出来。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她的装束有关。小慧穿着一身在农村干活时才穿的衣服,褂子又宽又大,裤子又肥又长,真是土得掉渣。
妻子老远瞅见小慧的这副模样,立时就蹙起了眉头。妻子是城里人,骨子里对乡下人多少有一些抵触情绪,平素遇到穿着不讲究的人,更是没个好脸色,似乎别人的穿戴降低了她在人群中的身份。虽然小慧大老远给我们提来不少家乡的土特产,但丝毫没有引起妻子的兴趣,她一直板着脸,不冷不热。
回家的路上,我一边驾车,一边小心询问小慧及她爸妈的情况。小慧一一回答后,便眼盯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街头美景,如醉如痴地欣赏起来。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始终一言不发。我知道妻子对小慧产生了偏见,便不再多说话,只管全神贯注地开车,以免惹妻子生气,给我弄出更大的尴尬来。毕竟小慧是第一次来我们家里,我不能让她感到难堪。
到了家,小慧放下背包,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迎上来的女儿,说是与女儿的见面礼。女儿虽然年龄尚小,但简单的道理还是懂的,没经爸妈同意,她是不敢随意接受别人东西的。当小慧往她手里塞钱时,女儿双手藏在身后不肯接,说起话来,更是一副小大人模样:“姐姐,我不能要你的钱,留着你买衣服吧,你看你穿的衣服都旧了,要不,你穿我妈妈的衣服吧,我妈妈的衣服可多啦,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女儿的话让小慧忍俊不禁:“姐姐带有新衣服哩。姐姐来时没买东西,这钱是姐姐给你买零食的呢!”
小慧的笑倒让我感到了几分窘迫,忙岔开话题,示意女儿到一边玩去。我觉得小慧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尽管如此,妻子对小慧的态度依然没有“多云转晴”。趁小慧拎上背包到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妻子低声对我嘀咕道:“你看看,一个小姑娘穿得这么邋遢,一点也不注意自身形象!”
我说:“小慧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做客,你还是给人家留点儿面子吧。”
妻子单刀直入,切入正题道:“小慧不会是来借钱的吧?”
我有些不高兴地说:“小慧是不是来借钱的,我怎么知道?!”
这些年,老家有不少沾亲带故的亲戚,因各种事由,都来向我们借过钱。按照妻子的逻辑,我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是无事不登三室殿的。更何况,小慧已是与我们多年没走动的亲戚,她今天的到来,自然更是引起妻子的高度警惕。
妻子见我没有和她站在同一立场上,态度变得很决绝:“是不是借钱我不管,反正你甭想从家里拿走一分钱!”
正悄声说着话,小慧从浴室出来了。此时的小慧俨然换了一个人:她换下了刚才的那身衣服,上身是白色碎花时尚女装,下身的黑色紧身裤更是衬托出地修长的腿和苗条的身材。由于刚出浴的缘故,她白暂的脸蛋浸润着一抹红晕,如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整个人娇美可爱。小慧的美一下子将我震慑住了,就连妻子也愣愣地盯着小慧,嘴已张成了“O”型。
小慧坐在沙发上,一边用葱白一样的手指,梳理着还有些湿漉漉的长发,一边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想起妻于一直疑虑的问题,便试探着说:“小慧,你这次来省城好好放松放松,让你婶子这几天带你出去转转。”
小慧若有所思地说:“我这次来顾不上玩呢,高中毕业后,在家暂时也没什么事可干,这次来省城,就是想利用暑假学一门摄影技术,将来回到小镇开一家婚纱摄影店哩!这几年,农村富裕了,都不缺钱了,年轻人也开始学着城里人,玩起了浪漫,我觉得这门生意在小镇肯定有前途……”
妻于对小慧的态度明显好转起来,啧啧赞叹道:“小慧,你好有审美眼光呀!你看你,这身衣服多合体呀,穿在身上,走在街上,跟城里的姑娘一样呢!”妻子忍不住好奇,话锋一转,问道,“小慧,你既然有这么漂光时尚的衣服,干嘛不直接穿上出门啊?”
小慧听了,呵呵笑起来:“婶子,我这可是自我保护呢!我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还是不招摇的好,我有意穿上很普通的服装,就是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更有安全感呢……”
小慧的话,让我和妻子陷入了沉默,只觉得此刻的小慧,很漂亮,很可爱。
1.这篇小说被推荐入选了“中国好故事”系列,请结合文本给出推荐理由。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上岸
张建春
老圣在水上漂了一辈子,小船是家,鱼是庄稼,一茬茬地收割,丰年歉年,水和鱼养活自己,养活家。
六十岁,正好六十岁,老圣要上岸了。
上岸老圣不情愿,和水和船和鱼打了几十年交道,舍不得。舍不得也要上岸,禁渔了。
水是大湖,八百里的方圆,烟波浩渺。大湖长鱼,形形色色的鱼,形形色色的虾蟹,在水里热闹。热闹时,老圣下网,网网不空。
近些年,热闹的景象少了,老圣下网,空着的时候十有七八。
鱼都哪儿去了,老圣明白,捕捞的船太多,网太密,鱼虾蟹来不及长。一些鱼多年不见了,比如胭脂鱼,几年里就没见过影子。
胭脂鱼漂亮,透明,手指头粗细,一抹胭脂红从身体透出,美美的。
胭脂鱼味美,熬汤,鲜得天下无味。
消失的何止胭脂鱼,多了去了。就连过去一捞一层的毛刀子鱼,也稀巴巴的了。
禁渔了,禁渔好呀,再不禁,再滥捕,大湖中的鱼恐怕就要绝迹了。
不过,上岸,老圣还是不舍。老圣十五六岁上船,在船上生活了四十多年,白天撒网,晚上枕着波涛睡觉,习惯了水,习惯了水上的生活。
不情愿归不情愿,老圣还是弃了船上了岸。
岸上有房子,房子在湖边,推门见到湖。
上岸的老圣临湖,却和水远了。
日子有得过,政府安排得好,六十岁也是退休的年纪,该享享清福了。
儿女们大了,在城里安家,可以随了去,老圣不去,湖好呀,水好呀,鱼好呀。
老圣和老伴在湖边守房子,也守湖。
上岸的老圣闲不住,干啥事呢?老伴出了主意,没事吧,到湖滩去转转,当活动筋骨,当城里人散散步。
老圣想,也只能如此了。老圣下了湖滩,过去的大湖安静了下来,千帆竞扬的场面不见了,湖一下子就空旷了下来,尽管风浪不息,湖仍显得安静。
老圣贴近着湖水走,浪拍在他的鞋上,鞋潮了,干脆脱了鞋,让湖水浇个痛快。
一天一天就这么过了。老圣想有个奇遇,比如碰上一条鱼,可惜一次也没遇上。许多年前可不是这样,有水就有鱼,在湖水中走,鱼撵着啃脚趾头。
老圣有些懊恼,怎不见鱼?接着自责,鱼不见了,和自己有关,四十多年捕杀的鱼还少呀!老圣的自责一天天加深,有时把手伸进湖中的礁石,狠狠地磨,磨得快出血。
老圣问自己:回到从前,还会下湖当个渔民吗?老圣回答自己:不了,不了。没鱼的湖少鱼的湖,还算个湖吗?不算。老圣得出结论,自己参与了对湖的谋杀。
有一天,老圣和人打了一架。六十岁的人打架不光彩,但打了,打得痛快。
原因摆在那儿,有人在湖边偷捕鱼。鱼毛都没偷到,但摆开了架势。老圣制止,偷捕的人欺他人老,不当回事,老圣动手扯网,就打起来了,打得结了球。
事后,老圣多了件事,不仅仅是在湖滩上转转,还多了重任务,巡湖。
“巡湖”这个词是老圣独创的,说给老伴听,老伴认可,又加了句赎罪。捕杀太多,得给鱼和湖赎罪。
赎吧,老圣把巡湖当了回事,天天拎根木棍出门,还真撵走了一个又一个偷偷捕鱼的人。偷鱼人心虚,喊上一两声就跑了。
日子过得快,一天老圣脱了鞋在湖水中走,眼前一亮,天啦,一抹胭脂红。
是一群胭脂鱼,是一群胭脂鱼!老圣喊了起来,鱼似乎一点不怕老圣,在他赤裸的脚边打转,还有几条轻轻咬着他的脚趾。
老圣突然泪流满面。老圣跑回家和老伴说,老伴也高兴,随着到湖边,胭脂鱼还在,一大群,将湖水映成了胭脂色。
老圣说:真好!老伴说:真好!是真的好,真好!湖水荡来荡去,胭脂鱼不紧不慢,有几条还悠悠地向湖边游,似也想上岸。
湖滩上有小花在开,红红的,泛胭脂色。大地上一抹好风光哦!
(有删改)
2.现准备将本文推荐给杂志《微型小说选刊》,请你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主题表现三个方面写出推荐理由。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寻找王×成
张港
1973年的冬天,冷得邪乎,兴安岭上龙门农场,田鼠冻得钻进知青宿舍。于是,可怕的鼠疫暴发了。
1月27日夜,狂风打鼓,大雪拍门。一辆马爬犁从三分场驰到卫生院,抬下上海人李志鹏。李志鹏脸泛了青。高烧的人这个脸色,是真不行了。他要说什么,又发不出声音。他指指我上衣口袋,比画着。我明白了,他是要写字。我的破钢笔其实只是摆设,极少用。
李志鹏哆嗦着接笔,哆嗦着摸出一块挺旧的手绢包。在手绢上,他费力地写出个“王”,笔就不下水了。我接来笔,用舌头洇了洇,又下水了。他接着写,写得太费力,写了老长时间,之后他就闭上了眼睛。送他来的上海人比画:“把这个包——交给这个人——对吗?”
李志鹏点点头,我们几个人连声喊:“一定一定一定。”李志鹏的眼睛睁了一下又合上,就再也没有睁开。
上海小伙子李志鹏就这样走了。最后陪他的,只有三个上海知青加上一个东北的我。处理完后事,我们想起了那手绢包。
脏兮兮的旧手绢,里面是钞票,35元。皱手绢上的字,歪歪扭扭,第一个是“王”;第三个是“成”;中间这个,有人说是“之”,有人说像“云”,有人分析是“立”。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将这手绢包送到王×成手上——我们点头了,我们答应过李志鹏。
龙门农场也就五六千人,找一个人还不难。我们先从三分场开始,先从上海人入手,可是,没有王×成。
我们成立了“专案小组”,分工负责,分片包干,拉开大网。然而,还是找不到。
一转眼,上海知青大返城,专案小组成员最后剩了我一个。每一个人走时,都对我说“一定一定,一定要找到王×成”。
之后,我与上海书信不断,上海与我书信不断。
一晃,我也离开了农场,也娶着了媳妇。我给媳妇讲手绢包的事。媳妇手指在舌上抹湿,一张一张数过那35元钱。她将手指头塞进我的秋衣破洞里,一转一搅:“真的不少哩!够织件毛衣哩!”她枕在我的手臂上,日子穷而甜。
儿子降生,特能吃,而他娘没奶。因为钱断了,所以奶粉断了。媳妇先是骂我无能,然后又是骂我无能,最后,她摸出手绢包摔在炕上。我狠狠地瞪她,说:“不行!”
我与上海书信不断,上海与我书信不断。可是,那个王×成,就是找不到。
寻找王×成的队伍渐渐发展壮大,我们这些最穷的人家却最先安装上电话,打着长途电话研究王×成,研究手绢包。
那一年,上海来了兴致勃勃的电话:“找到了,在上海,原来的龙门知青。”电话要我带上东西,赶赴沪上。“邮不行吗?”“不行,面当面,物对人,得确认。”
想想那个大风雪之夜的李志鹏,我带上干粮,买了车票。那人叫王子成,手绢不对,钱的数额也不对。虽然路费是上海人出的,可我欠了债,债是大田的野草,锄了又长。
一晃,我发现自己老了。这个手绢包,让我长出许多皱纹。可是,怎么办呢?那个大风雪之夜,李志鹏最后那样子,总在梦里,总在醒时。我与上海人通话,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总攻——
不管不顾地不分时间地点人物地大讲这个手绢包的故事,发动群众,搜寻王×成。
这天,我接到个电话,那人自称龙门农场的,在城里治病。事情重要,电话说不行,要我到医院会面。
路上,我忽然想到,这自称叫于诚的人,莫不就是找了20年的王×成?
比我还老的于诚,果然就是“王×成”。
于诚摸着手绢包:“是不是 35 块?是不是两张 10 块,一张 5 块,剩下 1 元的,还有两张 5 角?”
“是是是,对对对!”
“两张10块的,卖榛子钱;一张5块的,土豆钱……”于诚老泪纵横。
“找了 20 年呀!原来是你。”我终于明白了,在农场时,我是知青,他是山东移民,我们相隔二十多公里。
于诚翻来覆去地看手绢,翻来覆去摩挲那些市面上已难见的旧纸币。突然,他将钱拍我手上,说:“原来张眼镜就是你呀!这些钱是你的呀!”
我傻了,我不能不傻。
于诚缓缓气,说:“去过六分场吧。”
我没去过。
“去六分场的路,总走过吧!”
我记不得。
“一辆胶轮拖拉机着火,你们知青救火。这还不记得?”
好像——这事有。
“有个人,救火烧了毛衣。后来我打听了,他叫张眼镜。我就攒了钱,托人买上海毛线,我得赔人家毛衣呀!托来转去,没了下落。想不到,钱钱钱……钱在这儿,你你你……你在这儿。”
泪如水泼,我不会说话了。
(2020年24期)
文本二:
从体裁来说,故事应该与小说有显著区别,否则它就不是一种文体。故事的基本涵义是旧事、旧业、先例、典故等,因此,故事一般讲的是已过去的真实事件,不可过于夸张或扭曲。当然,故事中的虚构与小说中的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这里面有个谁主谁次的问题,故事中事件主体不能背离,这是大原则,小说则不一样,芝麻可以说成西瓜,这是它们之间真实与虚构的区别或差异。
故事中事件的真实性决定其运用的表达形式,即说故事主要通过叙述的方式来讲一个带有寓意的事件。因此,写故事又叫讲故事,主要用的是叙述的方法,而小说常用的是描写的方法。我们认为一个故事“好”,亦因为它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跌宕起伏,从而阐发某种道理或者价值观。试想,如果你在讲故事过程中大量使用情景描写,别人会怎么看你,肯定会认为你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吹牛皮!
另外,讲述一个故事,必须话有所指,意有所图,这就是说讲故事要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也就是故事中所谓的故事核。故事核就像目的地,是故事中要鲜明的。这在讲故事过程中也常要有所提示,或头或尾或文中,这在寓言故事中更是可见一斑。寓言故事的讲述者始终是主导,其目标方向很明确,故事中所运用的各种手法,目的总是先将读者引向歧途(这很关键),最后再引向故事核。
故事留给读者的是事,人反而淡化了。好的故事,几十年后不忘的还是故事本身,而不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当然,故事本身也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但那只是副产品。
3.读了文本二,如果要把《寻找王×成》推荐给《故事会》,你将从哪些方面阐明理由?
答案
1.①小慧的形象展示了新一代农村人坦诚、自信、有远见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小说描绘普通人的日常情态,如小慧出门换装,“妻子”怕借钱等情节,贴近生活,易于使读者产生共鸣。③小说也表达了对以貌取人、囿于城乡差距偏见的否定,富有教育意义。
2.①小说在短小的篇幅中设置精妙的结构,既有前后对比,又有前后照应。
②小说的主人公老圣朴实的形象鲜明生动,既贴近现实生活,又具有新时代特征。
③小说的主题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符合新时代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
3.①事件真实感人;②叙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③故事本身是一篇好故事,主旨明确,赞美高尚人性,极具普世价值。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下丫头小慧
吴万夫
小慧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已到省城,因捎带东西太多,又不熟悉路线,希望我去车站接她。小慧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女儿,我们两家多年没走动过了。
我和妻子开车赶到火车站时,小慧早已等候在出站口了。她背着一个双肩背包,两手提着一个纸箱子,正在那儿东张西望。纸箱子似乎有些沉,但小慧却宝贝似的舍不得放下来。多年不见,小慧如今已出落成一位大姑娘了,只是姑娘的所有优点,在她身上一点都没有显现出来。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她的装束有关。小慧穿着一身在农村干活时才穿的衣服,褂子又宽又大,裤子又肥又长,真是土得掉渣。
妻子老远瞅见小慧的这副模样,立时就蹙起了眉头。妻子是城里人,骨子里对乡下人多少有一些抵触情绪,平素遇到穿着不讲究的人,更是没个好脸色,似乎别人的穿戴降低了她在人群中的身份。虽然小慧大老远给我们提来不少家乡的土特产,但丝毫没有引起妻子的兴趣,她一直板着脸,不冷不热。
回家的路上,我一边驾车,一边小心询问小慧及她爸妈的情况。小慧一一回答后,便眼盯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街头美景,如醉如痴地欣赏起来。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始终一言不发。我知道妻子对小慧产生了偏见,便不再多说话,只管全神贯注地开车,以免惹妻子生气,给我弄出更大的尴尬来。毕竟小慧是第一次来我们家里,我不能让她感到难堪。
到了家,小慧放下背包,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迎上来的女儿,说是与女儿的见面礼。女儿虽然年龄尚小,但简单的道理还是懂的,没经爸妈同意,她是不敢随意接受别人东西的。当小慧往她手里塞钱时,女儿双手藏在身后不肯接,说起话来,更是一副小大人模样:“姐姐,我不能要你的钱,留着你买衣服吧,你看你穿的衣服都旧了,要不,你穿我妈妈的衣服吧,我妈妈的衣服可多啦,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女儿的话让小慧忍俊不禁:“姐姐带有新衣服哩。姐姐来时没买东西,这钱是姐姐给你买零食的呢!”
小慧的笑倒让我感到了几分窘迫,忙岔开话题,示意女儿到一边玩去。我觉得小慧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尽管如此,妻子对小慧的态度依然没有“多云转晴”。趁小慧拎上背包到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妻子低声对我嘀咕道:“你看看,一个小姑娘穿得这么邋遢,一点也不注意自身形象!”
我说:“小慧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做客,你还是给人家留点儿面子吧。”
妻子单刀直入,切入正题道:“小慧不会是来借钱的吧?”
我有些不高兴地说:“小慧是不是来借钱的,我怎么知道?!”
这些年,老家有不少沾亲带故的亲戚,因各种事由,都来向我们借过钱。按照妻子的逻辑,我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是无事不登三室殿的。更何况,小慧已是与我们多年没走动的亲戚,她今天的到来,自然更是引起妻子的高度警惕。
妻子见我没有和她站在同一立场上,态度变得很决绝:“是不是借钱我不管,反正你甭想从家里拿走一分钱!”
正悄声说着话,小慧从浴室出来了。此时的小慧俨然换了一个人:她换下了刚才的那身衣服,上身是白色碎花时尚女装,下身的黑色紧身裤更是衬托出地修长的腿和苗条的身材。由于刚出浴的缘故,她白暂的脸蛋浸润着一抹红晕,如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整个人娇美可爱。小慧的美一下子将我震慑住了,就连妻子也愣愣地盯着小慧,嘴已张成了“O”型。
小慧坐在沙发上,一边用葱白一样的手指,梳理着还有些湿漉漉的长发,一边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想起妻于一直疑虑的问题,便试探着说:“小慧,你这次来省城好好放松放松,让你婶子这几天带你出去转转。”
小慧若有所思地说:“我这次来顾不上玩呢,高中毕业后,在家暂时也没什么事可干,这次来省城,就是想利用暑假学一门摄影技术,将来回到小镇开一家婚纱摄影店哩!这几年,农村富裕了,都不缺钱了,年轻人也开始学着城里人,玩起了浪漫,我觉得这门生意在小镇肯定有前途……”
妻于对小慧的态度明显好转起来,啧啧赞叹道:“小慧,你好有审美眼光呀!你看你,这身衣服多合体呀,穿在身上,走在街上,跟城里的姑娘一样呢!”妻子忍不住好奇,话锋一转,问道,“小慧,你既然有这么漂光时尚的衣服,干嘛不直接穿上出门啊?”
小慧听了,呵呵笑起来:“婶子,我这可是自我保护呢!我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还是不招摇的好,我有意穿上很普通的服装,就是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更有安全感呢……”
小慧的话,让我和妻子陷入了沉默,只觉得此刻的小慧,很漂亮,很可爱。
1.这篇小说被推荐入选了“中国好故事”系列,请结合文本给出推荐理由。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上岸
张建春
老圣在水上漂了一辈子,小船是家,鱼是庄稼,一茬茬地收割,丰年歉年,水和鱼养活自己,养活家。
六十岁,正好六十岁,老圣要上岸了。
上岸老圣不情愿,和水和船和鱼打了几十年交道,舍不得。舍不得也要上岸,禁渔了。
水是大湖,八百里的方圆,烟波浩渺。大湖长鱼,形形色色的鱼,形形色色的虾蟹,在水里热闹。热闹时,老圣下网,网网不空。
近些年,热闹的景象少了,老圣下网,空着的时候十有七八。
鱼都哪儿去了,老圣明白,捕捞的船太多,网太密,鱼虾蟹来不及长。一些鱼多年不见了,比如胭脂鱼,几年里就没见过影子。
胭脂鱼漂亮,透明,手指头粗细,一抹胭脂红从身体透出,美美的。
胭脂鱼味美,熬汤,鲜得天下无味。
消失的何止胭脂鱼,多了去了。就连过去一捞一层的毛刀子鱼,也稀巴巴的了。
禁渔了,禁渔好呀,再不禁,再滥捕,大湖中的鱼恐怕就要绝迹了。
不过,上岸,老圣还是不舍。老圣十五六岁上船,在船上生活了四十多年,白天撒网,晚上枕着波涛睡觉,习惯了水,习惯了水上的生活。
不情愿归不情愿,老圣还是弃了船上了岸。
岸上有房子,房子在湖边,推门见到湖。
上岸的老圣临湖,却和水远了。
日子有得过,政府安排得好,六十岁也是退休的年纪,该享享清福了。
儿女们大了,在城里安家,可以随了去,老圣不去,湖好呀,水好呀,鱼好呀。
老圣和老伴在湖边守房子,也守湖。
上岸的老圣闲不住,干啥事呢?老伴出了主意,没事吧,到湖滩去转转,当活动筋骨,当城里人散散步。
老圣想,也只能如此了。老圣下了湖滩,过去的大湖安静了下来,千帆竞扬的场面不见了,湖一下子就空旷了下来,尽管风浪不息,湖仍显得安静。
老圣贴近着湖水走,浪拍在他的鞋上,鞋潮了,干脆脱了鞋,让湖水浇个痛快。
一天一天就这么过了。老圣想有个奇遇,比如碰上一条鱼,可惜一次也没遇上。许多年前可不是这样,有水就有鱼,在湖水中走,鱼撵着啃脚趾头。
老圣有些懊恼,怎不见鱼?接着自责,鱼不见了,和自己有关,四十多年捕杀的鱼还少呀!老圣的自责一天天加深,有时把手伸进湖中的礁石,狠狠地磨,磨得快出血。
老圣问自己:回到从前,还会下湖当个渔民吗?老圣回答自己:不了,不了。没鱼的湖少鱼的湖,还算个湖吗?不算。老圣得出结论,自己参与了对湖的谋杀。
有一天,老圣和人打了一架。六十岁的人打架不光彩,但打了,打得痛快。
原因摆在那儿,有人在湖边偷捕鱼。鱼毛都没偷到,但摆开了架势。老圣制止,偷捕的人欺他人老,不当回事,老圣动手扯网,就打起来了,打得结了球。
事后,老圣多了件事,不仅仅是在湖滩上转转,还多了重任务,巡湖。
“巡湖”这个词是老圣独创的,说给老伴听,老伴认可,又加了句赎罪。捕杀太多,得给鱼和湖赎罪。
赎吧,老圣把巡湖当了回事,天天拎根木棍出门,还真撵走了一个又一个偷偷捕鱼的人。偷鱼人心虚,喊上一两声就跑了。
日子过得快,一天老圣脱了鞋在湖水中走,眼前一亮,天啦,一抹胭脂红。
是一群胭脂鱼,是一群胭脂鱼!老圣喊了起来,鱼似乎一点不怕老圣,在他赤裸的脚边打转,还有几条轻轻咬着他的脚趾。
老圣突然泪流满面。老圣跑回家和老伴说,老伴也高兴,随着到湖边,胭脂鱼还在,一大群,将湖水映成了胭脂色。
老圣说:真好!老伴说:真好!是真的好,真好!湖水荡来荡去,胭脂鱼不紧不慢,有几条还悠悠地向湖边游,似也想上岸。
湖滩上有小花在开,红红的,泛胭脂色。大地上一抹好风光哦!
(有删改)
2.现准备将本文推荐给杂志《微型小说选刊》,请你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主题表现三个方面写出推荐理由。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寻找王×成
张港
1973年的冬天,冷得邪乎,兴安岭上龙门农场,田鼠冻得钻进知青宿舍。于是,可怕的鼠疫暴发了。
1月27日夜,狂风打鼓,大雪拍门。一辆马爬犁从三分场驰到卫生院,抬下上海人李志鹏。李志鹏脸泛了青。高烧的人这个脸色,是真不行了。他要说什么,又发不出声音。他指指我上衣口袋,比画着。我明白了,他是要写字。我的破钢笔其实只是摆设,极少用。
李志鹏哆嗦着接笔,哆嗦着摸出一块挺旧的手绢包。在手绢上,他费力地写出个“王”,笔就不下水了。我接来笔,用舌头洇了洇,又下水了。他接着写,写得太费力,写了老长时间,之后他就闭上了眼睛。送他来的上海人比画:“把这个包——交给这个人——对吗?”
李志鹏点点头,我们几个人连声喊:“一定一定一定。”李志鹏的眼睛睁了一下又合上,就再也没有睁开。
上海小伙子李志鹏就这样走了。最后陪他的,只有三个上海知青加上一个东北的我。处理完后事,我们想起了那手绢包。
脏兮兮的旧手绢,里面是钞票,35元。皱手绢上的字,歪歪扭扭,第一个是“王”;第三个是“成”;中间这个,有人说是“之”,有人说像“云”,有人分析是“立”。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将这手绢包送到王×成手上——我们点头了,我们答应过李志鹏。
龙门农场也就五六千人,找一个人还不难。我们先从三分场开始,先从上海人入手,可是,没有王×成。
我们成立了“专案小组”,分工负责,分片包干,拉开大网。然而,还是找不到。
一转眼,上海知青大返城,专案小组成员最后剩了我一个。每一个人走时,都对我说“一定一定,一定要找到王×成”。
之后,我与上海书信不断,上海与我书信不断。
一晃,我也离开了农场,也娶着了媳妇。我给媳妇讲手绢包的事。媳妇手指在舌上抹湿,一张一张数过那35元钱。她将手指头塞进我的秋衣破洞里,一转一搅:“真的不少哩!够织件毛衣哩!”她枕在我的手臂上,日子穷而甜。
儿子降生,特能吃,而他娘没奶。因为钱断了,所以奶粉断了。媳妇先是骂我无能,然后又是骂我无能,最后,她摸出手绢包摔在炕上。我狠狠地瞪她,说:“不行!”
我与上海书信不断,上海与我书信不断。可是,那个王×成,就是找不到。
寻找王×成的队伍渐渐发展壮大,我们这些最穷的人家却最先安装上电话,打着长途电话研究王×成,研究手绢包。
那一年,上海来了兴致勃勃的电话:“找到了,在上海,原来的龙门知青。”电话要我带上东西,赶赴沪上。“邮不行吗?”“不行,面当面,物对人,得确认。”
想想那个大风雪之夜的李志鹏,我带上干粮,买了车票。那人叫王子成,手绢不对,钱的数额也不对。虽然路费是上海人出的,可我欠了债,债是大田的野草,锄了又长。
一晃,我发现自己老了。这个手绢包,让我长出许多皱纹。可是,怎么办呢?那个大风雪之夜,李志鹏最后那样子,总在梦里,总在醒时。我与上海人通话,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总攻——
不管不顾地不分时间地点人物地大讲这个手绢包的故事,发动群众,搜寻王×成。
这天,我接到个电话,那人自称龙门农场的,在城里治病。事情重要,电话说不行,要我到医院会面。
路上,我忽然想到,这自称叫于诚的人,莫不就是找了20年的王×成?
比我还老的于诚,果然就是“王×成”。
于诚摸着手绢包:“是不是 35 块?是不是两张 10 块,一张 5 块,剩下 1 元的,还有两张 5 角?”
“是是是,对对对!”
“两张10块的,卖榛子钱;一张5块的,土豆钱……”于诚老泪纵横。
“找了 20 年呀!原来是你。”我终于明白了,在农场时,我是知青,他是山东移民,我们相隔二十多公里。
于诚翻来覆去地看手绢,翻来覆去摩挲那些市面上已难见的旧纸币。突然,他将钱拍我手上,说:“原来张眼镜就是你呀!这些钱是你的呀!”
我傻了,我不能不傻。
于诚缓缓气,说:“去过六分场吧。”
我没去过。
“去六分场的路,总走过吧!”
我记不得。
“一辆胶轮拖拉机着火,你们知青救火。这还不记得?”
好像——这事有。
“有个人,救火烧了毛衣。后来我打听了,他叫张眼镜。我就攒了钱,托人买上海毛线,我得赔人家毛衣呀!托来转去,没了下落。想不到,钱钱钱……钱在这儿,你你你……你在这儿。”
泪如水泼,我不会说话了。
(2020年24期)
文本二:
从体裁来说,故事应该与小说有显著区别,否则它就不是一种文体。故事的基本涵义是旧事、旧业、先例、典故等,因此,故事一般讲的是已过去的真实事件,不可过于夸张或扭曲。当然,故事中的虚构与小说中的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这里面有个谁主谁次的问题,故事中事件主体不能背离,这是大原则,小说则不一样,芝麻可以说成西瓜,这是它们之间真实与虚构的区别或差异。
故事中事件的真实性决定其运用的表达形式,即说故事主要通过叙述的方式来讲一个带有寓意的事件。因此,写故事又叫讲故事,主要用的是叙述的方法,而小说常用的是描写的方法。我们认为一个故事“好”,亦因为它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跌宕起伏,从而阐发某种道理或者价值观。试想,如果你在讲故事过程中大量使用情景描写,别人会怎么看你,肯定会认为你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吹牛皮!
另外,讲述一个故事,必须话有所指,意有所图,这就是说讲故事要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也就是故事中所谓的故事核。故事核就像目的地,是故事中要鲜明的。这在讲故事过程中也常要有所提示,或头或尾或文中,这在寓言故事中更是可见一斑。寓言故事的讲述者始终是主导,其目标方向很明确,故事中所运用的各种手法,目的总是先将读者引向歧途(这很关键),最后再引向故事核。
故事留给读者的是事,人反而淡化了。好的故事,几十年后不忘的还是故事本身,而不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当然,故事本身也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但那只是副产品。
3.读了文本二,如果要把《寻找王×成》推荐给《故事会》,你将从哪些方面阐明理由?
答案
1.①小慧的形象展示了新一代农村人坦诚、自信、有远见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小说描绘普通人的日常情态,如小慧出门换装,“妻子”怕借钱等情节,贴近生活,易于使读者产生共鸣。③小说也表达了对以貌取人、囿于城乡差距偏见的否定,富有教育意义。
2.①小说在短小的篇幅中设置精妙的结构,既有前后对比,又有前后照应。
②小说的主人公老圣朴实的形象鲜明生动,既贴近现实生活,又具有新时代特征。
③小说的主题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符合新时代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
3.①事件真实感人;②叙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③故事本身是一篇好故事,主旨明确,赞美高尚人性,极具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