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开放试题(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开放试题(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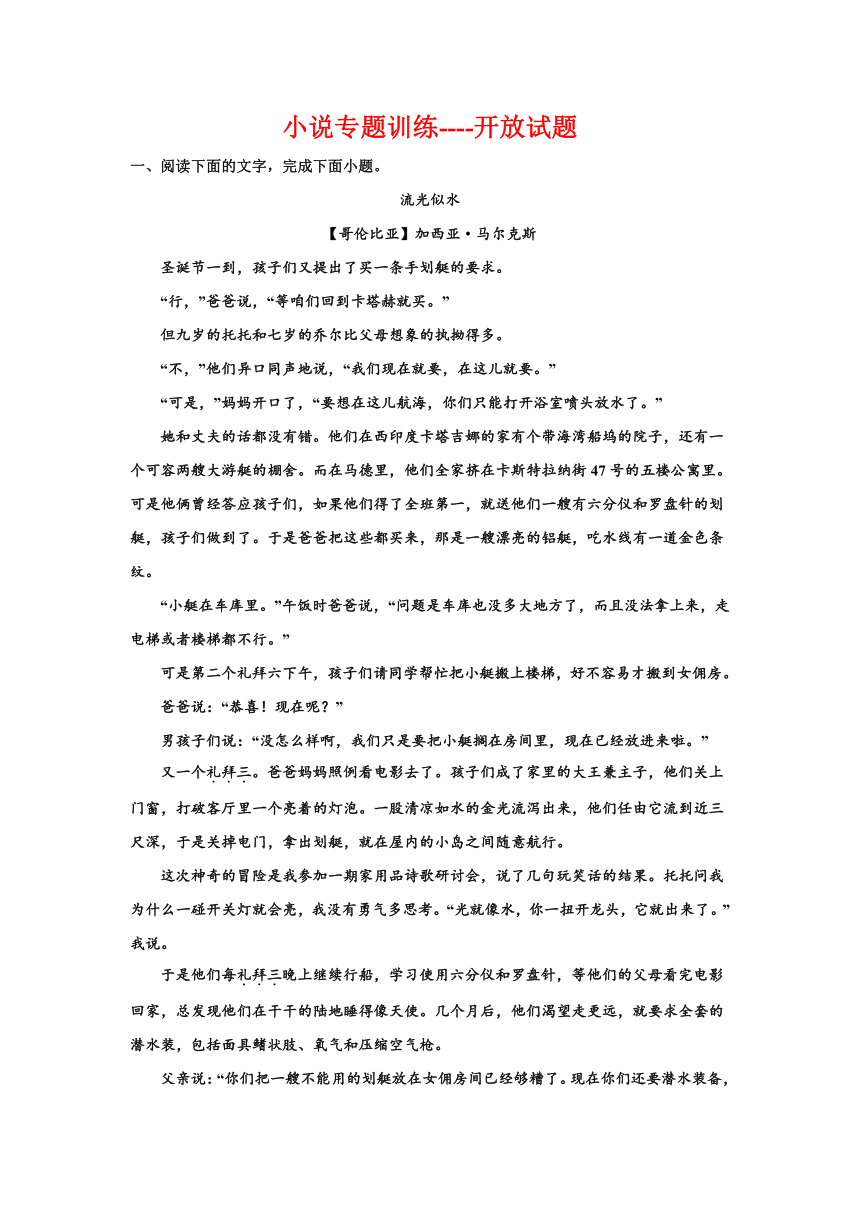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8.1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2-04 13:31:0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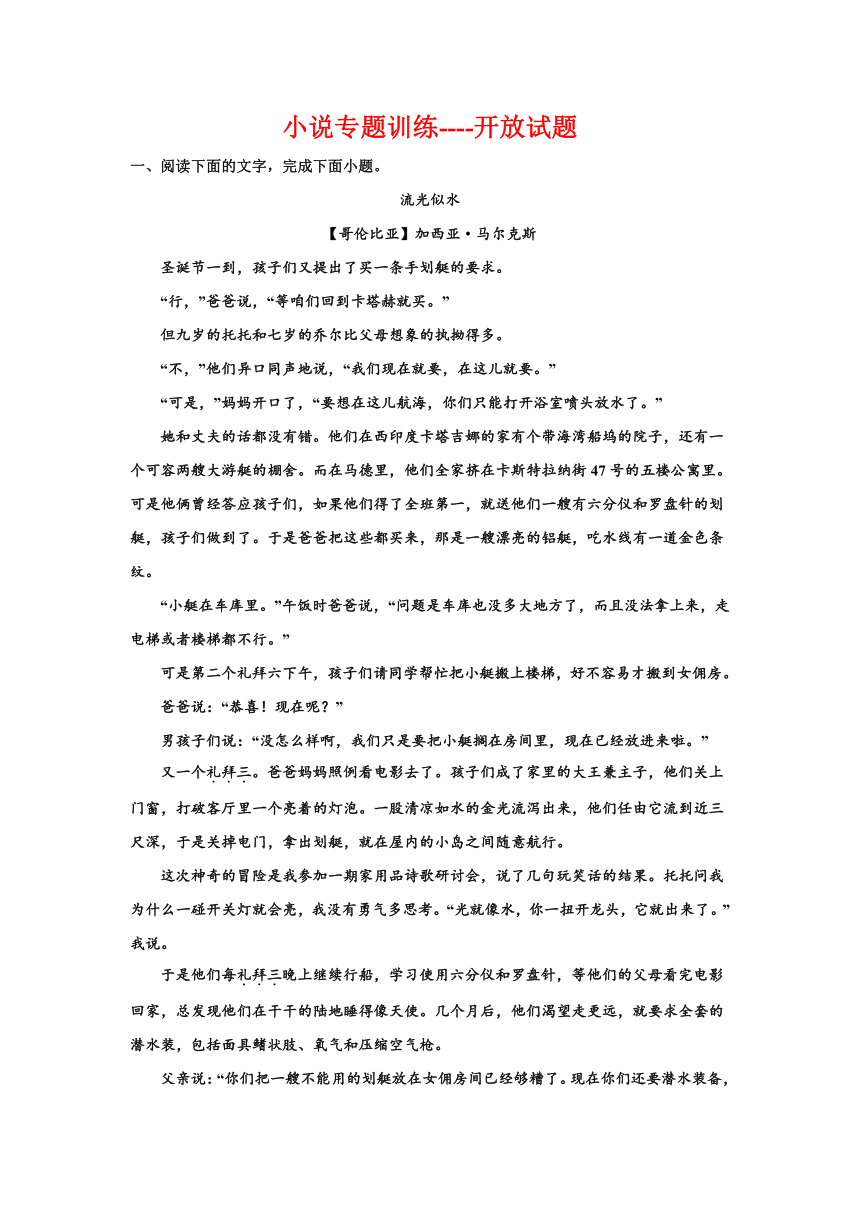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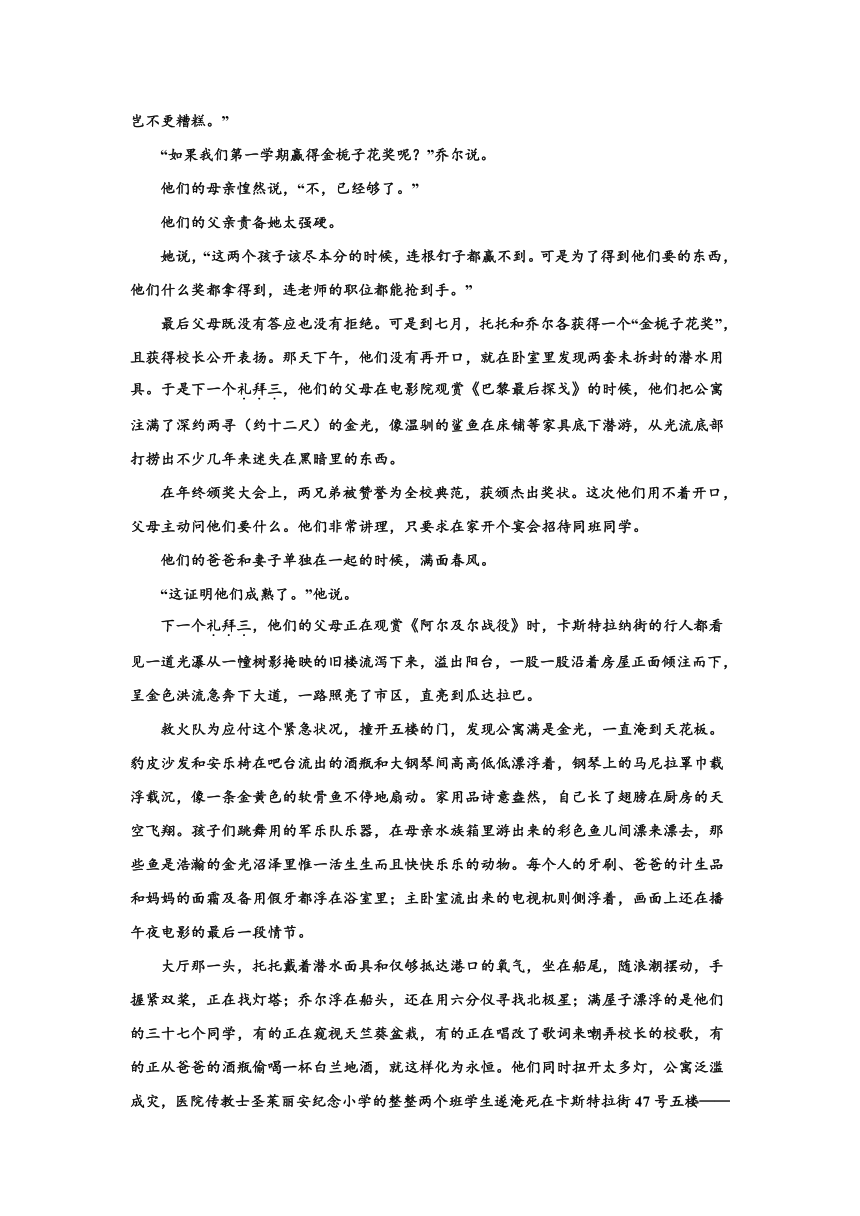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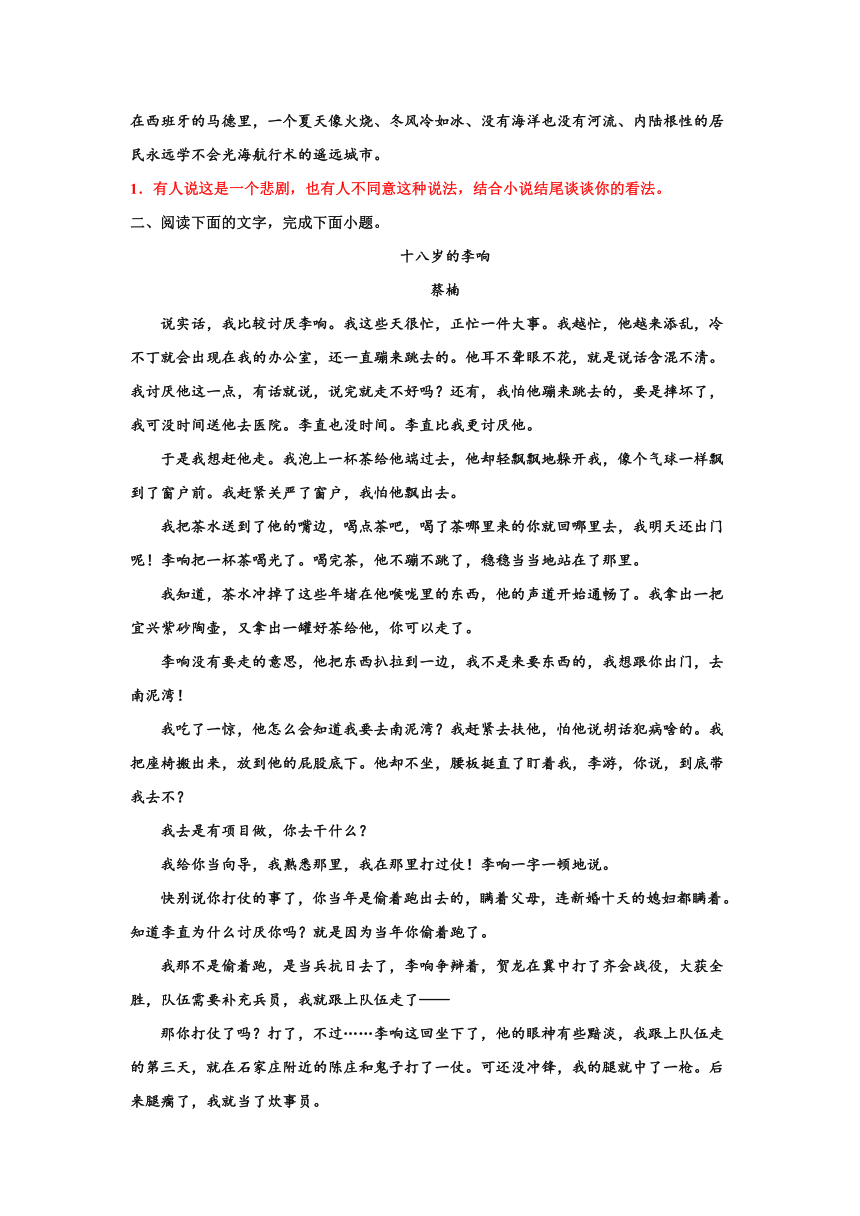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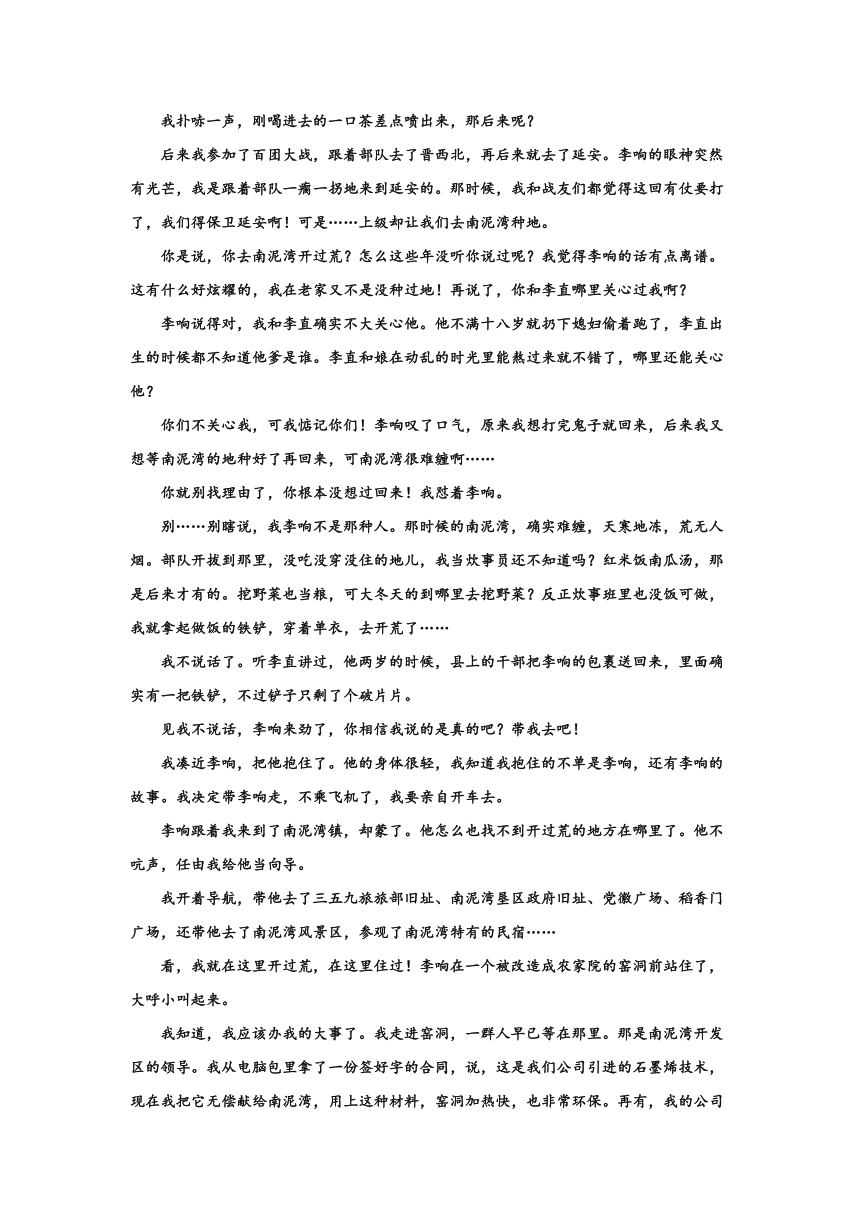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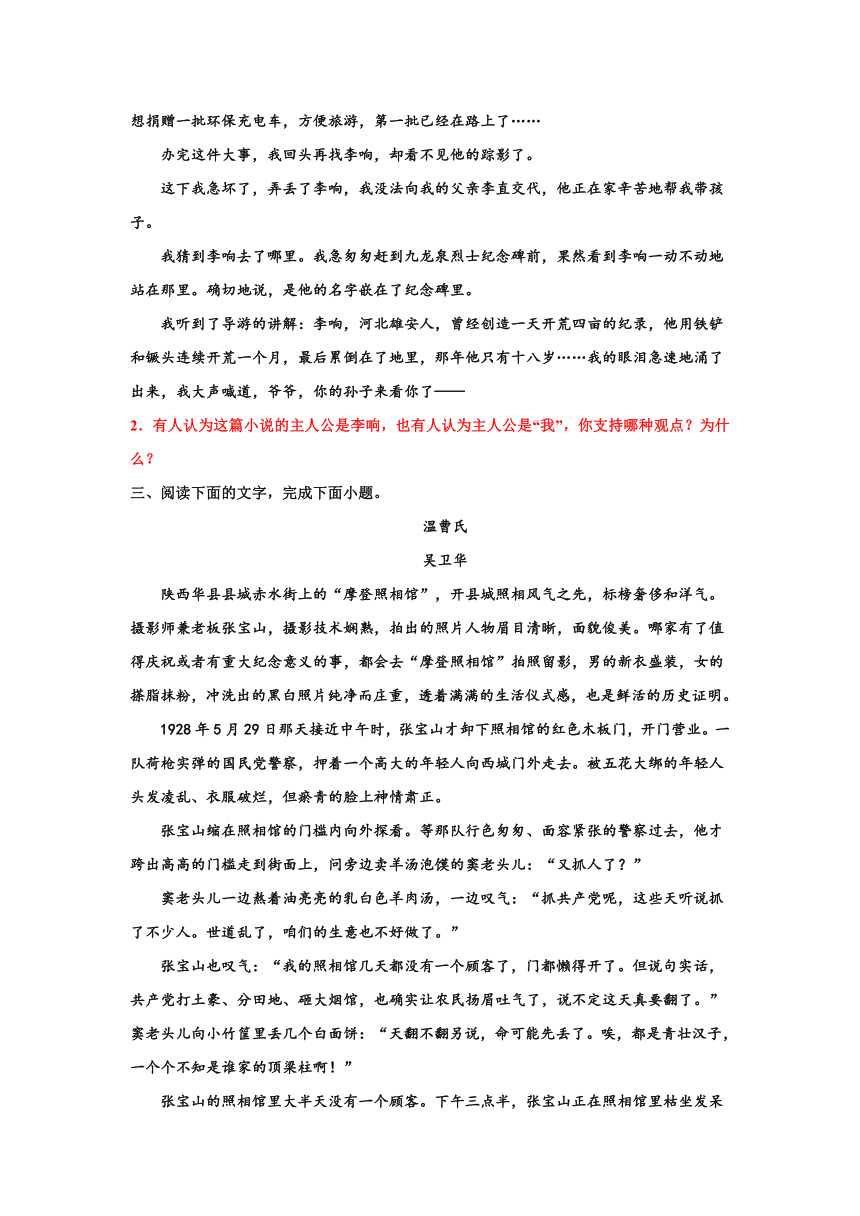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开放试题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约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爸爸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每个人的牙刷、爸爸的计生品和妈妈的面霜及备用假牙都浮在浴室里;主卧室流出来的电视机则侧浮着,画面上还在播午夜电影的最后一段情节。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1.有人说这是一个悲剧,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结合小说结尾谈谈你的看法。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十八岁的李响
蔡楠
说实话,我比较讨厌李响。我这些天很忙,正忙一件大事。我越忙,他越来添乱,冷不丁就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还一直蹦来跳去的。他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说话含混不清。我讨厌他这一点,有话就说,说完就走不好吗?还有,我怕他蹦来跳去的,要是摔坏了,我可没时间送他去医院。李直也没时间。李直比我更讨厌他。
于是我想赶他走。我泡上一杯茶给他端过去,他却轻飘飘地躲开我,像个气球一样飘到了窗户前。我赶紧关严了窗户,我怕他飘出去。
我把茶水送到了他的嘴边,喝点茶吧,喝了茶哪里来的你就回哪里去,我明天还出门呢!李响把一杯茶喝光了。喝完茶,他不蹦不跳了,稳稳当当地站在了那里。
我知道,茶水冲掉了这些年堵在他喉咙里的东西,他的声道开始通畅了。我拿出一把宜兴紫砂陶壶,又拿出一罐好茶给他,你可以走了。
李响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把东西扒拉到一边,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想跟你出门,去南泥湾!
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南泥湾?我赶紧去扶他,怕他说胡话犯病啥的。我把座椅搬出来,放到他的屁股底下。他却不坐,腰板挺直了盯着我,李游,你说,到底带我去不?
我去是有项目做,你去干什么?
我给你当向导,我熟悉那里,我在那里打过仗!李响一字一顿地说。
快别说你打仗的事了,你当年是偷着跑出去的,瞒着父母,连新婚十天的媳妇都瞒着。知道李直为什么讨厌你吗?就是因为当年你偷着跑了。
我那不是偷着跑,是当兵抗日去了,李响争辩着,贺龙在冀中打了齐会战役,大获全胜,队伍需要补充兵员,我就跟上队伍走了——
那你打仗了吗?打了,不过……李响这回坐下了,他的眼神有些黯淡,我跟上队伍走的第三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陈庄和鬼子打了一仗。可还没冲锋,我的腿就中了一枪。后来腿瘸了,我就当了炊事员。
我扑哧一声,刚喝进去的一口茶差点喷出来,那后来呢?
后来我参加了百团大战,跟着部队去了晋西北,再后来就去了延安。李响的眼神突然有光芒,我是跟着部队一瘸一拐地来到延安的。那时候,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这回有仗要打了,我们得保卫延安啊!可是……上级却让我们去南泥湾种地。
你是说,你去南泥湾开过荒?怎么这些年没听你说过呢?我觉得李响的话有点离谱。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在老家又不是没种过地!再说了,你和李直哪里关心过我啊?
李响说得对,我和李直确实不大关心他。他不满十八岁就扔下媳妇偷着跑了,李直出生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爹是谁。李直和娘在动乱的时光里能熬过来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关心他?
你们不关心我,可我惦记你们!李响叹了口气,原来我想打完鬼子就回来,后来我又想等南泥湾的地种好了再回来,可南泥湾很难缠啊……
你就别找理由了,你根本没想过回来!我怼着李响。
别……别瞎说,我李响不是那种人。那时候的南泥湾,确实难缠,天寒地冻,荒无人烟。部队开拔到那里,没吃没穿没住的地儿,我当炊事员还不知道吗?红米饭南瓜汤,那是后来才有的。挖野菜也当粮,可大冬天的到哪里去挖野菜?反正炊事班里也没饭可做,我就拿起做饭的铁铲,穿着单衣,去开荒了……
我不说话了。听李直讲过,他两岁的时候,县上的干部把李响的包裹送回来,里面确实有一把铁铲,不过铲子只剩了个破片片。
见我不说话,李响来劲了,你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吧?带我去吧!
我凑近李响,把他抱住了。他的身体很轻,我知道我抱住的不单是李响,还有李响的故事。我决定带李响走,不乘飞机了,我要亲自开车去。
李响跟着我来到了南泥湾镇,却蒙了。他怎么也找不到开过荒的地方在哪里了。他不吭声,任由我给他当向导。
我开着导航,带他去了三五九旅旅部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址、党徽广场、稻香门广场,还带他去了南泥湾风景区,参观了南泥湾特有的民宿……
看,我就在这里开过荒,在这里住过!李响在一个被改造成农家院的窑洞前站住了,大呼小叫起来。
我知道,我应该办我的大事了。我走进窑洞,一群人早已等在那里。那是南泥湾开发区的领导。我从电脑包里拿了一份签好字的合同,说,这是我们公司引进的石墨烯技术,现在我把它无偿献给南泥湾,用上这种材料,窑洞加热快,也非常环保。再有,我的公司想捐赠一批环保充电车,方便旅游,第一批已经在路上了……
办完这件大事,我回头再找李响,却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这下我急坏了,弄丢了李响,我没法向我的父亲李直交代,他正在家辛苦地帮我带孩子。
我猜到李响去了哪里。我急匆匆赶到九龙泉烈士纪念碑前,果然看到李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确切地说,是他的名字嵌在了纪念碑里。
我听到了导游的讲解:李响,河北雄安人,曾经创造一天开荒四亩的纪录,他用铁铲和镢头连续开荒一个月,最后累倒在了地里,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我的眼泪急速地涌了出来,我大声喊道,爷爷,你的孙子来看你了——
2.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李响,也有人认为主人公是“我”,你支持哪种观点?为什么?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温曹氏
吴卫华
陕西华县县城赤水街上的“摩登照相馆”,开县城照相风气之先,标榜奢侈和洋气。摄影师兼老板张宝山,摄影技术娴熟,拍出的照片人物眉目清晰,面貌俊美。哪家有了值得庆祝或者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都会去“摩登照相馆”拍照留影,男的新衣盛装,女的搽脂抹粉,冲洗出的黑白照片纯净而庄重,透着满满的生活仪式感,也是鲜活的历史证明。
1928年5月29日那天接近中午时,张宝山才卸下照相馆的红色木板门,开门营业。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押着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向西城门外走去。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头发凌乱、衣服破烂,但瘀青的脸上神情肃正。
张宝山缩在照相馆的门槛内向外探看。等那队行色匆匆、面容紧张的警察过去,他才跨出高高的门槛走到街面上,问旁边卖羊汤泡馍的窦老头儿:“又抓人了?”
窦老头儿一边熬着油亮亮的乳白色羊肉汤,一边叹气:“抓共产党呢,这些天听说抓了不少人。世道乱了,咱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了。”
张宝山也叹气:“我的照相馆几天都没有一个顾客了,门都懒得开了。但说句实话,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砸大烟馆,也确实让农民扬眉吐气了,说不定这天真要翻了。”窦老头儿向小竹筐里丢几个白面饼:“天翻不翻另说,命可能先丢了。唉,都是青壮汉子,一个个不知是谁家的顶梁柱啊!”
张宝山的照相馆里大半天没有一个顾客。下午三点半,张宝山正在照相馆里枯坐发呆时,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终于有顾客上门了,张宝山忙露出笑容,起身招呼客人:“咱们这儿的价格很公道,您是照大相还是小相?”
年轻女人的目光发直。她看着张宝山,张宝山却分明感觉她没有看到自己。年轻女人从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放到桌子上,张宝山一愣,就是照一整套相也用不了这么多钱:“您这是要怎么照?”
女人神思恍惚地说:“请您上门照相。”
张宝山一口回绝:“我这是坐家生意.不上门服务。”
女人又掏出两块光洋放到桌子上:“要照相的人不能亲自来。我只有这些了,请您务必关照!”
张宝山看看桌子上诱人的光洋,又看看神色肃然的女人,问:“你家住在哪儿?”
女人说:“露泽院西村。”
张宝山拿起照相机:“在西关那块儿,也不远,走吧。”
女人是走来照相馆的,张宝山骑着洋车(自行车)驮着女人,很快就到了不远的露泽院西村。
“去哪条巷子?进哪户人家?”张宝山在村里的主路分岔口问女人。
女人说:“穿过村子去西头的小庙。”
张宝山还从没有在庙里给人照过相,心里虽然疑惑,还是驮着女人到了村西头的小庙。
女人说:“到了。”
两人下车进庙,庙的主建筑又小又寒碜,一副破败相,两个窗户用乱砖填塞着,庙前场地还算宽敞。女人说:“您在这儿等着,我去请照相的人来。”
张宝山满腹狐疑地问女人:“你是哪家的人?”“温家的。”女人说完匆匆地走了。
一会儿,女人匆匆地回来了,右肩上扛着一把罗圈椅,左手提着个高脚荼几。她把罗圈椅和高脚茶几摆放在庙墙边的窗户下,又匆匆地走了。张宝山看得一头雾水:瞧这精细的家具,也是富裕人家了,怎么要在这么晦气破败的小庙旁照相呢?
女人又一次回来时,是同三个人一块儿来的:一个戴麦秸草帽的汉子,吃力地背着一个戴瓜皮帽的男子,那男子的袍褂鞋袜簇新得直扎张宝山的眼睛;女人在后面一手拉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一手扶着新衣男子。他们到了摆放好的罗圈椅跟前,戴草帽的汉子退步找好椅面位置,在女人的帮助下,费劲地把背上的男子安放到罗圈椅里坐好。新衣男子以一种怪异的僵硬姿势坐着,就像一个在夏天里尸僵缓慢肢体还能弯曲的死人。张宝山心想这要照相的人病得还真不轻,上前伸手去扶持一把时,顿感新衣男子的肢体冰凉僵硬;又仔细看,见他面色灰青、双眼紧闭,而且很像上午从他照相馆前经过的被绑着的年轻人。
张宝山吓得一激灵,后退几步:“他?”
女人平静地说:“这是我家先生,温济厚【注】。”
戴草帽的汉子声音嘶哑地说:“七里寺小学的校长、共产党员温济厚,今天上午在西门外被枪杀。我是他族弟温志德,亲眼看着他被枪杀,上午跟嫂子把尸体搬运回来,要照一张‘全家福’!”
女人深情地看着温济厚,喃喃地说:“我把你整理得像个样子了,血迹完全擦去了,身上的鞭伤和烙铁的烫伤,被新买的寿衣遮住了,你脸上也搽了粉,这样看起来显得精神些。你一直说要照张‘全家福’,我今儿把县城里最好的摄影师请了来。家里嫌晦气不让我们照,我们就在这小庙照。”
张宝山突然热泪盈眶,他举起相机,打开镜盖。女人抱起孩子,用右胳膊顶住双眼紧闭的温济厚,不让他身子斜歪。四个人努力面向照相机。张宝山的手有些哆嗦,他努力稳住手,习惯性地冲镜头里的四个人喊出:“一、二、三,不要闭眼!”
咔嚓一声,历史定格,书生温济厚永远定格在25岁!
(有删改)
【注】温济厚: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华州乡露泽院西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渭华起义爆发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温济厚牺牲后,妻子温曹氏和族弟温志德一起将他的遗体运回,拍摄了一张“全家福”。
3.从标题看,文章的主人公是“温曹氏”,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主人公应该是“温济厚”,对此你如何理解?
四、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女巫的面包
马莎·米查姆小姐是街角上那家小面包店的女老板。她今年四十岁了,有两千元的银行存款、两枚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结过婚的女人可不少,但同马莎小姐一比,她们的条件可差得远啦。
有一个顾客每星期来两三次,马莎小姐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个中年人,戴眼镜,棕色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他的衣服有的地方磨破了,经过织补,有的地方皱得不成样子。但他的外表仍旧很整饬,礼貌又十分周全。
这个顾客老是买两个陈面包。新鲜面包是五分钱一个,陈面包五分钱可以买两个。除了陈面包以外,他从来没有买过别的东西。
有一次,马莎小姐注意到他的手指上有一块红褐色的污迹。她立刻断定这位顾客是艺术家,并且十分穷困。毫无疑问,他准是住阁楼的人物,他在那里画画,啃啃陈面包,呆想着马莎小姐面包店里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
马莎小姐坐下来吃肉排、面包卷、果酱和红茶的时候,常常会好端端地叹起气来,希望那个斯文的艺术家能够分享她的美味的饭菜,不必待在阁楼里啃硬面包。马莎小姐的心,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是多情的。
最近一个时期,他来了以后往往隔着货柜聊一会儿。他似乎也渴望同马莎小姐进行愉快的谈话。
他一直买陈面包。从没有买过蛋糕、馅儿饼,或者她店里的可口的甜茶点。
她觉得他仿佛瘦了一点,精神也有点颓唐。她很想在他买的寒酸东西里加上一些好吃的东西,只是鼓不起勇气。她不敢冒失。她了解艺术家高傲的心理。
马莎小姐在店堂里的时候,也穿起那件蓝点子的绸背心来了。她在后房里熬了一种神秘的榅桲和硼砂的混合物。有许多人用这种汁水美容。
一天,那个顾客又像平时那样来了,把五分镍币往柜台上一搁,买他的陈面包。马莎小姐去拿面包的当儿,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喇叭声和警钟声,一辆救火车隆隆驶过。
顾客跑到门口去张望,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这样做的。马莎小姐突然灵机一动,抓住了这个机会。
柜台后面最低的一格架子里放着一磅新鲜黄油,送牛奶的人拿来还不到十分钟。马莎小姐用切面包的刀子把两个陈面包都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各塞进一大片黄油,再把面包按紧。
顾客再进来时,她已经把面包用纸包好了。
他们分外愉快地扯了几句。顾客走了,马莎小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可是心头不免有点着慌。
她是不是太大胆了呢?他会不高兴吗?绝对不会的。食物并不代表语言。黄油并不象征有失闺秀身份的冒失行为。
那天,她的心思老是在这件事上打转。她揣摩着他发现这场小骗局时的情景。他会放下画笔和调色板。画架上支着他正在创作的图画,那幅画的透视法肯定是无可指摘的。
他会拿起干面包和清水当午饭。他会切开一个面包——啊!
想到这里,马莎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吃面包的时候,会不会想到那只把黄油塞在里面的手呢?他会不会——
前门上面的铃铛恼人地响了。有人闹闹嚷嚷地走进来。
马莎小姐赶到店堂里去。那儿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叼着烟斗的年轻人——她以前从没有见过,另一个就是她的艺术家。
他的脸涨得通红,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头发揉得乱蓬蓬的。他攥紧拳头,狠狠地朝马莎小姐摇晃。竟然向马莎小姐摇晃。
“笨蛋!”他拉开嗓子嚷道;接着又喊了一声“千雷轰顶的!”或者类似的德国话。
年轻的那个竭力想把他拖开。
“我不走,”他怒气冲冲地说,“我非同她说个明白不可。”
他擂鼓似的敲着马莎小姐的柜台。
“你把我给毁啦,”他嚷道,他的蓝眼睛几乎要在镜片后面闪出火来,“我对你说吧。你是个惹人讨厌的老猫!"
马莎小姐虚弱无力地倚在货架上,一手按着那件蓝点子的背心。年轻人抓住同伴的衣领。
“走吧,”他说,“你骂也骂够啦。”他把那个暴跳如雷的人拖到门外,自己又回来。
“夫人,我认为应当把这场吵闹的原因告诉你,”他说,“那个人姓布卢姆伯格。他是建筑图样设计师。我和他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
“他在绘制一份新市政厅的平面图,辛辛苦苦地干了三个月。准备参加有奖竞赛。他昨天刚上完墨。你明白,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打底稿的。上好墨之后,就用陈面包擦去铅笔印。陈面包比擦字橡皮好得多。"
“布卢姆伯格一向在你这里买面包。嗯,今天——嗯——你明白,夫人,里面的黄油可不——嗯,布卢姆伯格的图样成了废纸。只能裁开来包三明治啦。”
马莎小姐走进后房。她脱下蓝点子的绸背心,换上那件穿旧了的棕色哔叽衣服。接着,她把榅桲和硼砂煎汁倒在窗外的垃圾箱里。
4.有人认为最后一段很精彩,也有人认为冗余,删除了更好。你认为呢?请写出理由。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酒楼上
鲁迅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
我所住的旅馆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我于是立即出街向那酒楼去。
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我转脸向饭桌,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也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看着废园,渐渐地感到孤独,但又不愿别的酒客上来。
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地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地,然而颇不自然地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地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地向我说。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地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地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到得坟地,果然,河水离坟已不到二尺远。我的心颤动着,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地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坟旁埋掉了。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地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选自《彷徨》,有删改)
5.有人认为,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代表了鲁迅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我”和“吕纬甫”都带有鲁迅自己的影子。你同意哪一个观点?请说明理由。
答案
1.看法一:这是悲剧。
①小说以37个孩子(集体)意外溺亡在“光海”里为结局,凄惨悲怆。
②孩子们因追逐梦想(或“自由”,或“快乐”,或“诗意”)而不幸丧命,令人哀伤悲悯。
③没有现实土壤的梦想是令人悲叹的(或“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会做梦的城市里,这是社会的悲哀”)。
④将人生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警醒读者思考人生,这是悲剧的本质特征。
看法二:这不是悲剧。
①结尾不是现实意义的死亡,而是一种心灵迷失。即习惯于旧体制的孩子们为美妙梦想所惑,迷失在天马行空的梦里。
②孩子们在金色的光海中获得了一份“永恒”的快乐(或“自由”,或“诗意”)。
③兄弟俩掌握了光海航行术,勇敢而执着追梦的孩子或许能成功找到灯塔与彼岸。
④孩子们探索了航行术,看到了海,比起永远禁锢在大陆上的其他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经历。
2.支持李响是主人公。因为:
①小说题目是“十八岁的李响”,表明主要人物就是李响。
②李响这个人物贯穿小说始终,而且小说主要介绍的就是李响的事迹,可以说主要情节都是围绕李响展开的。
③小说通过塑造李响这个革命战争年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安排,积极投入到各种革命运动中去的英雄形象,表达革命先烈舍小家顾大家、为了革命胜利不怕流血牺牲、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
支持“我”是主人公。因为:
①我贯穿小说始终,李响的主要事迹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介绍出来的。
②我去南泥湾是小说情节的最重要一环,是我带着李响去的,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我”起主要作用。我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③我去南泥湾是为了送技术,还打算赠送一些节能车,有助于突出新时代愿意为革命老区的新发展献上自己一份力量的主题。
3.观点一:主人公是温曹氏。①从情节上看,全文主要围绕温曹氏展开,讲述了温曹氏为英勇就义的丈夫温济厚拍摄全家福的故事;②从人物上看,文章着重塑造了温曹氏这一人物形象,全文通过对温曹氏的叙述和描写塑造并赞美了她挚爱丈夫、坚强勇敢的形象;③从主题上看,文章主要是借温曹氏这一人物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观点二:主人公是温济厚。①从情节上看,故事以温济厚被五花大绑押走开篇,以为牺牲的温济厚拍照结尾,故事情节完整;②从人物上看,文章塑造温曹氏这一形象的目的是从侧面烘托革命党人温济厚钢铁般的革命意志;③从主题上看,文章主要歌颂的是革命者温济厚的牺牲精神,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4.我认为应保留最后一段。
①情节上,小说最后一段描绘了玛莎小姐走进后房的一系列动作,脱下蓝点子绸背心,倒掉温棒子和硼砂煎汁,与前文的情节相互照应,这样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
②人物形象上,这一情节也成功地刻画出玛莎小姐爱情破灭后悲痛心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③小说的主旨及艺术效果,小说对玛莎小姐的予以讽刺的同时也给予了同情,保留最后一段文字更能激发读者对玛莎小姐的同情,从而更好地体现小说的艺术效果。
我认为应该删去最后一段。
①从文章主旨而言,更加体现了“好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突显了小说主题。
②与前文的层层伏笔形成呼应,最终揭示布卢姆伯格的身份,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
③体现了小说留白艺术,给读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更能体现欧亨利小说的艺术特色。
5.观点一的理由:①“我”是一个抱有希望和热情的革命者,最后仍选择在风雪中前进;②“我”否定吕纬甫颓唐的人生态度,对逃避革命甚至妥协的态度加以否定;③“我”代表了作者的立场,号召革命人士要坚持奋进;而吕纬甫是作者批判的对象,批判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观点二的理由:①“我”是孤独的追梦者,是鲁迅坚持革命理想的一面;②吕纬甫回归现实,不再追梦,是鲁迅犹豫彷徨的一面;③“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可看作是鲁迅自我的心灵对话与思想剖析,作者其实想借小说中两个人的对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反思。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约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爸爸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每个人的牙刷、爸爸的计生品和妈妈的面霜及备用假牙都浮在浴室里;主卧室流出来的电视机则侧浮着,画面上还在播午夜电影的最后一段情节。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1.有人说这是一个悲剧,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结合小说结尾谈谈你的看法。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十八岁的李响
蔡楠
说实话,我比较讨厌李响。我这些天很忙,正忙一件大事。我越忙,他越来添乱,冷不丁就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还一直蹦来跳去的。他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说话含混不清。我讨厌他这一点,有话就说,说完就走不好吗?还有,我怕他蹦来跳去的,要是摔坏了,我可没时间送他去医院。李直也没时间。李直比我更讨厌他。
于是我想赶他走。我泡上一杯茶给他端过去,他却轻飘飘地躲开我,像个气球一样飘到了窗户前。我赶紧关严了窗户,我怕他飘出去。
我把茶水送到了他的嘴边,喝点茶吧,喝了茶哪里来的你就回哪里去,我明天还出门呢!李响把一杯茶喝光了。喝完茶,他不蹦不跳了,稳稳当当地站在了那里。
我知道,茶水冲掉了这些年堵在他喉咙里的东西,他的声道开始通畅了。我拿出一把宜兴紫砂陶壶,又拿出一罐好茶给他,你可以走了。
李响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把东西扒拉到一边,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想跟你出门,去南泥湾!
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南泥湾?我赶紧去扶他,怕他说胡话犯病啥的。我把座椅搬出来,放到他的屁股底下。他却不坐,腰板挺直了盯着我,李游,你说,到底带我去不?
我去是有项目做,你去干什么?
我给你当向导,我熟悉那里,我在那里打过仗!李响一字一顿地说。
快别说你打仗的事了,你当年是偷着跑出去的,瞒着父母,连新婚十天的媳妇都瞒着。知道李直为什么讨厌你吗?就是因为当年你偷着跑了。
我那不是偷着跑,是当兵抗日去了,李响争辩着,贺龙在冀中打了齐会战役,大获全胜,队伍需要补充兵员,我就跟上队伍走了——
那你打仗了吗?打了,不过……李响这回坐下了,他的眼神有些黯淡,我跟上队伍走的第三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陈庄和鬼子打了一仗。可还没冲锋,我的腿就中了一枪。后来腿瘸了,我就当了炊事员。
我扑哧一声,刚喝进去的一口茶差点喷出来,那后来呢?
后来我参加了百团大战,跟着部队去了晋西北,再后来就去了延安。李响的眼神突然有光芒,我是跟着部队一瘸一拐地来到延安的。那时候,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这回有仗要打了,我们得保卫延安啊!可是……上级却让我们去南泥湾种地。
你是说,你去南泥湾开过荒?怎么这些年没听你说过呢?我觉得李响的话有点离谱。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在老家又不是没种过地!再说了,你和李直哪里关心过我啊?
李响说得对,我和李直确实不大关心他。他不满十八岁就扔下媳妇偷着跑了,李直出生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爹是谁。李直和娘在动乱的时光里能熬过来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关心他?
你们不关心我,可我惦记你们!李响叹了口气,原来我想打完鬼子就回来,后来我又想等南泥湾的地种好了再回来,可南泥湾很难缠啊……
你就别找理由了,你根本没想过回来!我怼着李响。
别……别瞎说,我李响不是那种人。那时候的南泥湾,确实难缠,天寒地冻,荒无人烟。部队开拔到那里,没吃没穿没住的地儿,我当炊事员还不知道吗?红米饭南瓜汤,那是后来才有的。挖野菜也当粮,可大冬天的到哪里去挖野菜?反正炊事班里也没饭可做,我就拿起做饭的铁铲,穿着单衣,去开荒了……
我不说话了。听李直讲过,他两岁的时候,县上的干部把李响的包裹送回来,里面确实有一把铁铲,不过铲子只剩了个破片片。
见我不说话,李响来劲了,你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吧?带我去吧!
我凑近李响,把他抱住了。他的身体很轻,我知道我抱住的不单是李响,还有李响的故事。我决定带李响走,不乘飞机了,我要亲自开车去。
李响跟着我来到了南泥湾镇,却蒙了。他怎么也找不到开过荒的地方在哪里了。他不吭声,任由我给他当向导。
我开着导航,带他去了三五九旅旅部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址、党徽广场、稻香门广场,还带他去了南泥湾风景区,参观了南泥湾特有的民宿……
看,我就在这里开过荒,在这里住过!李响在一个被改造成农家院的窑洞前站住了,大呼小叫起来。
我知道,我应该办我的大事了。我走进窑洞,一群人早已等在那里。那是南泥湾开发区的领导。我从电脑包里拿了一份签好字的合同,说,这是我们公司引进的石墨烯技术,现在我把它无偿献给南泥湾,用上这种材料,窑洞加热快,也非常环保。再有,我的公司想捐赠一批环保充电车,方便旅游,第一批已经在路上了……
办完这件大事,我回头再找李响,却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这下我急坏了,弄丢了李响,我没法向我的父亲李直交代,他正在家辛苦地帮我带孩子。
我猜到李响去了哪里。我急匆匆赶到九龙泉烈士纪念碑前,果然看到李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确切地说,是他的名字嵌在了纪念碑里。
我听到了导游的讲解:李响,河北雄安人,曾经创造一天开荒四亩的纪录,他用铁铲和镢头连续开荒一个月,最后累倒在了地里,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我的眼泪急速地涌了出来,我大声喊道,爷爷,你的孙子来看你了——
2.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李响,也有人认为主人公是“我”,你支持哪种观点?为什么?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温曹氏
吴卫华
陕西华县县城赤水街上的“摩登照相馆”,开县城照相风气之先,标榜奢侈和洋气。摄影师兼老板张宝山,摄影技术娴熟,拍出的照片人物眉目清晰,面貌俊美。哪家有了值得庆祝或者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都会去“摩登照相馆”拍照留影,男的新衣盛装,女的搽脂抹粉,冲洗出的黑白照片纯净而庄重,透着满满的生活仪式感,也是鲜活的历史证明。
1928年5月29日那天接近中午时,张宝山才卸下照相馆的红色木板门,开门营业。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押着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向西城门外走去。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头发凌乱、衣服破烂,但瘀青的脸上神情肃正。
张宝山缩在照相馆的门槛内向外探看。等那队行色匆匆、面容紧张的警察过去,他才跨出高高的门槛走到街面上,问旁边卖羊汤泡馍的窦老头儿:“又抓人了?”
窦老头儿一边熬着油亮亮的乳白色羊肉汤,一边叹气:“抓共产党呢,这些天听说抓了不少人。世道乱了,咱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了。”
张宝山也叹气:“我的照相馆几天都没有一个顾客了,门都懒得开了。但说句实话,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砸大烟馆,也确实让农民扬眉吐气了,说不定这天真要翻了。”窦老头儿向小竹筐里丢几个白面饼:“天翻不翻另说,命可能先丢了。唉,都是青壮汉子,一个个不知是谁家的顶梁柱啊!”
张宝山的照相馆里大半天没有一个顾客。下午三点半,张宝山正在照相馆里枯坐发呆时,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终于有顾客上门了,张宝山忙露出笑容,起身招呼客人:“咱们这儿的价格很公道,您是照大相还是小相?”
年轻女人的目光发直。她看着张宝山,张宝山却分明感觉她没有看到自己。年轻女人从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放到桌子上,张宝山一愣,就是照一整套相也用不了这么多钱:“您这是要怎么照?”
女人神思恍惚地说:“请您上门照相。”
张宝山一口回绝:“我这是坐家生意.不上门服务。”
女人又掏出两块光洋放到桌子上:“要照相的人不能亲自来。我只有这些了,请您务必关照!”
张宝山看看桌子上诱人的光洋,又看看神色肃然的女人,问:“你家住在哪儿?”
女人说:“露泽院西村。”
张宝山拿起照相机:“在西关那块儿,也不远,走吧。”
女人是走来照相馆的,张宝山骑着洋车(自行车)驮着女人,很快就到了不远的露泽院西村。
“去哪条巷子?进哪户人家?”张宝山在村里的主路分岔口问女人。
女人说:“穿过村子去西头的小庙。”
张宝山还从没有在庙里给人照过相,心里虽然疑惑,还是驮着女人到了村西头的小庙。
女人说:“到了。”
两人下车进庙,庙的主建筑又小又寒碜,一副破败相,两个窗户用乱砖填塞着,庙前场地还算宽敞。女人说:“您在这儿等着,我去请照相的人来。”
张宝山满腹狐疑地问女人:“你是哪家的人?”“温家的。”女人说完匆匆地走了。
一会儿,女人匆匆地回来了,右肩上扛着一把罗圈椅,左手提着个高脚荼几。她把罗圈椅和高脚茶几摆放在庙墙边的窗户下,又匆匆地走了。张宝山看得一头雾水:瞧这精细的家具,也是富裕人家了,怎么要在这么晦气破败的小庙旁照相呢?
女人又一次回来时,是同三个人一块儿来的:一个戴麦秸草帽的汉子,吃力地背着一个戴瓜皮帽的男子,那男子的袍褂鞋袜簇新得直扎张宝山的眼睛;女人在后面一手拉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一手扶着新衣男子。他们到了摆放好的罗圈椅跟前,戴草帽的汉子退步找好椅面位置,在女人的帮助下,费劲地把背上的男子安放到罗圈椅里坐好。新衣男子以一种怪异的僵硬姿势坐着,就像一个在夏天里尸僵缓慢肢体还能弯曲的死人。张宝山心想这要照相的人病得还真不轻,上前伸手去扶持一把时,顿感新衣男子的肢体冰凉僵硬;又仔细看,见他面色灰青、双眼紧闭,而且很像上午从他照相馆前经过的被绑着的年轻人。
张宝山吓得一激灵,后退几步:“他?”
女人平静地说:“这是我家先生,温济厚【注】。”
戴草帽的汉子声音嘶哑地说:“七里寺小学的校长、共产党员温济厚,今天上午在西门外被枪杀。我是他族弟温志德,亲眼看着他被枪杀,上午跟嫂子把尸体搬运回来,要照一张‘全家福’!”
女人深情地看着温济厚,喃喃地说:“我把你整理得像个样子了,血迹完全擦去了,身上的鞭伤和烙铁的烫伤,被新买的寿衣遮住了,你脸上也搽了粉,这样看起来显得精神些。你一直说要照张‘全家福’,我今儿把县城里最好的摄影师请了来。家里嫌晦气不让我们照,我们就在这小庙照。”
张宝山突然热泪盈眶,他举起相机,打开镜盖。女人抱起孩子,用右胳膊顶住双眼紧闭的温济厚,不让他身子斜歪。四个人努力面向照相机。张宝山的手有些哆嗦,他努力稳住手,习惯性地冲镜头里的四个人喊出:“一、二、三,不要闭眼!”
咔嚓一声,历史定格,书生温济厚永远定格在25岁!
(有删改)
【注】温济厚: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华州乡露泽院西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渭华起义爆发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温济厚牺牲后,妻子温曹氏和族弟温志德一起将他的遗体运回,拍摄了一张“全家福”。
3.从标题看,文章的主人公是“温曹氏”,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主人公应该是“温济厚”,对此你如何理解?
四、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女巫的面包
马莎·米查姆小姐是街角上那家小面包店的女老板。她今年四十岁了,有两千元的银行存款、两枚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结过婚的女人可不少,但同马莎小姐一比,她们的条件可差得远啦。
有一个顾客每星期来两三次,马莎小姐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个中年人,戴眼镜,棕色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他的衣服有的地方磨破了,经过织补,有的地方皱得不成样子。但他的外表仍旧很整饬,礼貌又十分周全。
这个顾客老是买两个陈面包。新鲜面包是五分钱一个,陈面包五分钱可以买两个。除了陈面包以外,他从来没有买过别的东西。
有一次,马莎小姐注意到他的手指上有一块红褐色的污迹。她立刻断定这位顾客是艺术家,并且十分穷困。毫无疑问,他准是住阁楼的人物,他在那里画画,啃啃陈面包,呆想着马莎小姐面包店里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
马莎小姐坐下来吃肉排、面包卷、果酱和红茶的时候,常常会好端端地叹起气来,希望那个斯文的艺术家能够分享她的美味的饭菜,不必待在阁楼里啃硬面包。马莎小姐的心,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是多情的。
最近一个时期,他来了以后往往隔着货柜聊一会儿。他似乎也渴望同马莎小姐进行愉快的谈话。
他一直买陈面包。从没有买过蛋糕、馅儿饼,或者她店里的可口的甜茶点。
她觉得他仿佛瘦了一点,精神也有点颓唐。她很想在他买的寒酸东西里加上一些好吃的东西,只是鼓不起勇气。她不敢冒失。她了解艺术家高傲的心理。
马莎小姐在店堂里的时候,也穿起那件蓝点子的绸背心来了。她在后房里熬了一种神秘的榅桲和硼砂的混合物。有许多人用这种汁水美容。
一天,那个顾客又像平时那样来了,把五分镍币往柜台上一搁,买他的陈面包。马莎小姐去拿面包的当儿,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喇叭声和警钟声,一辆救火车隆隆驶过。
顾客跑到门口去张望,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这样做的。马莎小姐突然灵机一动,抓住了这个机会。
柜台后面最低的一格架子里放着一磅新鲜黄油,送牛奶的人拿来还不到十分钟。马莎小姐用切面包的刀子把两个陈面包都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各塞进一大片黄油,再把面包按紧。
顾客再进来时,她已经把面包用纸包好了。
他们分外愉快地扯了几句。顾客走了,马莎小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可是心头不免有点着慌。
她是不是太大胆了呢?他会不高兴吗?绝对不会的。食物并不代表语言。黄油并不象征有失闺秀身份的冒失行为。
那天,她的心思老是在这件事上打转。她揣摩着他发现这场小骗局时的情景。他会放下画笔和调色板。画架上支着他正在创作的图画,那幅画的透视法肯定是无可指摘的。
他会拿起干面包和清水当午饭。他会切开一个面包——啊!
想到这里,马莎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吃面包的时候,会不会想到那只把黄油塞在里面的手呢?他会不会——
前门上面的铃铛恼人地响了。有人闹闹嚷嚷地走进来。
马莎小姐赶到店堂里去。那儿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叼着烟斗的年轻人——她以前从没有见过,另一个就是她的艺术家。
他的脸涨得通红,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头发揉得乱蓬蓬的。他攥紧拳头,狠狠地朝马莎小姐摇晃。竟然向马莎小姐摇晃。
“笨蛋!”他拉开嗓子嚷道;接着又喊了一声“千雷轰顶的!”或者类似的德国话。
年轻的那个竭力想把他拖开。
“我不走,”他怒气冲冲地说,“我非同她说个明白不可。”
他擂鼓似的敲着马莎小姐的柜台。
“你把我给毁啦,”他嚷道,他的蓝眼睛几乎要在镜片后面闪出火来,“我对你说吧。你是个惹人讨厌的老猫!"
马莎小姐虚弱无力地倚在货架上,一手按着那件蓝点子的背心。年轻人抓住同伴的衣领。
“走吧,”他说,“你骂也骂够啦。”他把那个暴跳如雷的人拖到门外,自己又回来。
“夫人,我认为应当把这场吵闹的原因告诉你,”他说,“那个人姓布卢姆伯格。他是建筑图样设计师。我和他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
“他在绘制一份新市政厅的平面图,辛辛苦苦地干了三个月。准备参加有奖竞赛。他昨天刚上完墨。你明白,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打底稿的。上好墨之后,就用陈面包擦去铅笔印。陈面包比擦字橡皮好得多。"
“布卢姆伯格一向在你这里买面包。嗯,今天——嗯——你明白,夫人,里面的黄油可不——嗯,布卢姆伯格的图样成了废纸。只能裁开来包三明治啦。”
马莎小姐走进后房。她脱下蓝点子的绸背心,换上那件穿旧了的棕色哔叽衣服。接着,她把榅桲和硼砂煎汁倒在窗外的垃圾箱里。
4.有人认为最后一段很精彩,也有人认为冗余,删除了更好。你认为呢?请写出理由。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酒楼上
鲁迅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
我所住的旅馆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我于是立即出街向那酒楼去。
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我转脸向饭桌,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也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看着废园,渐渐地感到孤独,但又不愿别的酒客上来。
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地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地,然而颇不自然地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地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地向我说。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地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地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到得坟地,果然,河水离坟已不到二尺远。我的心颤动着,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地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坟旁埋掉了。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地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选自《彷徨》,有删改)
5.有人认为,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代表了鲁迅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我”和“吕纬甫”都带有鲁迅自己的影子。你同意哪一个观点?请说明理由。
答案
1.看法一:这是悲剧。
①小说以37个孩子(集体)意外溺亡在“光海”里为结局,凄惨悲怆。
②孩子们因追逐梦想(或“自由”,或“快乐”,或“诗意”)而不幸丧命,令人哀伤悲悯。
③没有现实土壤的梦想是令人悲叹的(或“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会做梦的城市里,这是社会的悲哀”)。
④将人生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警醒读者思考人生,这是悲剧的本质特征。
看法二:这不是悲剧。
①结尾不是现实意义的死亡,而是一种心灵迷失。即习惯于旧体制的孩子们为美妙梦想所惑,迷失在天马行空的梦里。
②孩子们在金色的光海中获得了一份“永恒”的快乐(或“自由”,或“诗意”)。
③兄弟俩掌握了光海航行术,勇敢而执着追梦的孩子或许能成功找到灯塔与彼岸。
④孩子们探索了航行术,看到了海,比起永远禁锢在大陆上的其他人,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经历。
2.支持李响是主人公。因为:
①小说题目是“十八岁的李响”,表明主要人物就是李响。
②李响这个人物贯穿小说始终,而且小说主要介绍的就是李响的事迹,可以说主要情节都是围绕李响展开的。
③小说通过塑造李响这个革命战争年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安排,积极投入到各种革命运动中去的英雄形象,表达革命先烈舍小家顾大家、为了革命胜利不怕流血牺牲、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
支持“我”是主人公。因为:
①我贯穿小说始终,李响的主要事迹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介绍出来的。
②我去南泥湾是小说情节的最重要一环,是我带着李响去的,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我”起主要作用。我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③我去南泥湾是为了送技术,还打算赠送一些节能车,有助于突出新时代愿意为革命老区的新发展献上自己一份力量的主题。
3.观点一:主人公是温曹氏。①从情节上看,全文主要围绕温曹氏展开,讲述了温曹氏为英勇就义的丈夫温济厚拍摄全家福的故事;②从人物上看,文章着重塑造了温曹氏这一人物形象,全文通过对温曹氏的叙述和描写塑造并赞美了她挚爱丈夫、坚强勇敢的形象;③从主题上看,文章主要是借温曹氏这一人物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观点二:主人公是温济厚。①从情节上看,故事以温济厚被五花大绑押走开篇,以为牺牲的温济厚拍照结尾,故事情节完整;②从人物上看,文章塑造温曹氏这一形象的目的是从侧面烘托革命党人温济厚钢铁般的革命意志;③从主题上看,文章主要歌颂的是革命者温济厚的牺牲精神,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4.我认为应保留最后一段。
①情节上,小说最后一段描绘了玛莎小姐走进后房的一系列动作,脱下蓝点子绸背心,倒掉温棒子和硼砂煎汁,与前文的情节相互照应,这样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
②人物形象上,这一情节也成功地刻画出玛莎小姐爱情破灭后悲痛心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③小说的主旨及艺术效果,小说对玛莎小姐的予以讽刺的同时也给予了同情,保留最后一段文字更能激发读者对玛莎小姐的同情,从而更好地体现小说的艺术效果。
我认为应该删去最后一段。
①从文章主旨而言,更加体现了“好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突显了小说主题。
②与前文的层层伏笔形成呼应,最终揭示布卢姆伯格的身份,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
③体现了小说留白艺术,给读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更能体现欧亨利小说的艺术特色。
5.观点一的理由:①“我”是一个抱有希望和热情的革命者,最后仍选择在风雪中前进;②“我”否定吕纬甫颓唐的人生态度,对逃避革命甚至妥协的态度加以否定;③“我”代表了作者的立场,号召革命人士要坚持奋进;而吕纬甫是作者批判的对象,批判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观点二的理由:①“我”是孤独的追梦者,是鲁迅坚持革命理想的一面;②吕纬甫回归现实,不再追梦,是鲁迅犹豫彷徨的一面;③“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可看作是鲁迅自我的心灵对话与思想剖析,作者其实想借小说中两个人的对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