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人物形象的异同(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人物形象的异同(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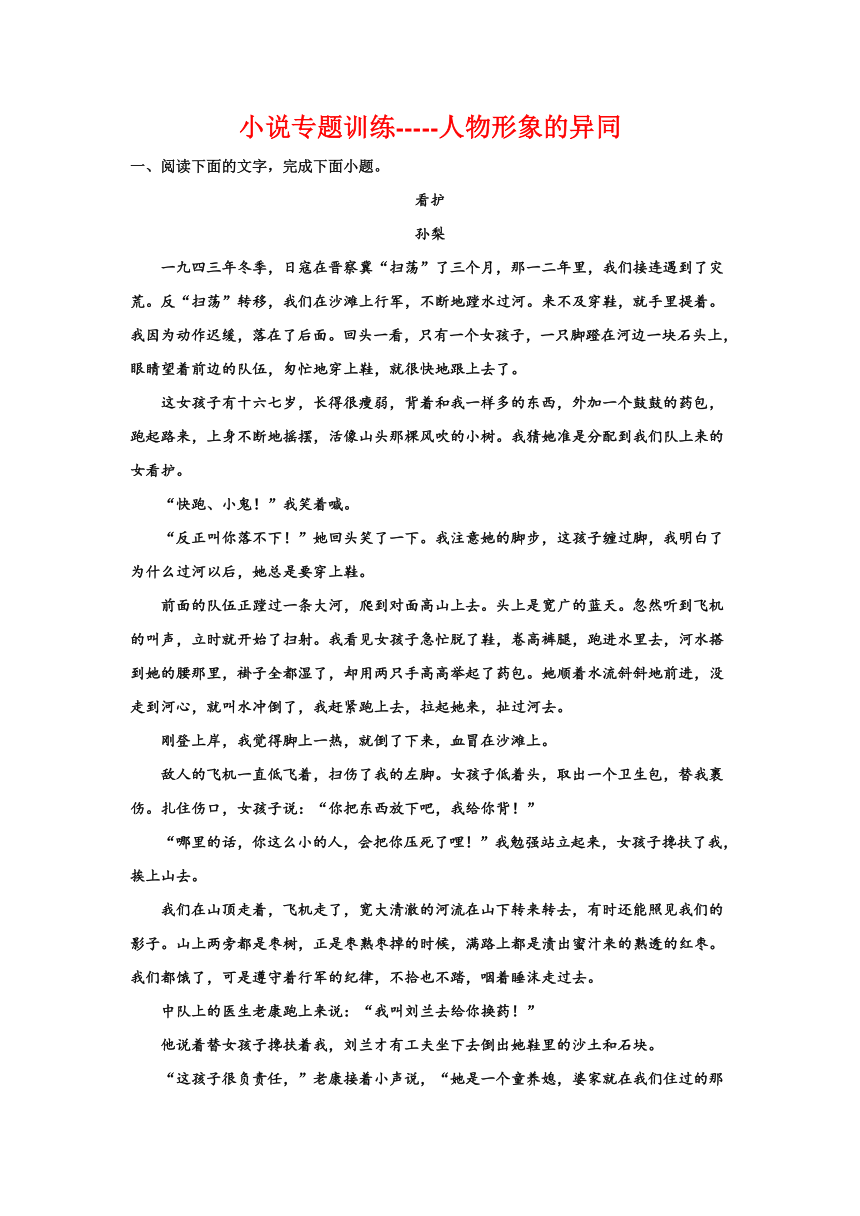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4.9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2-19 16:31:28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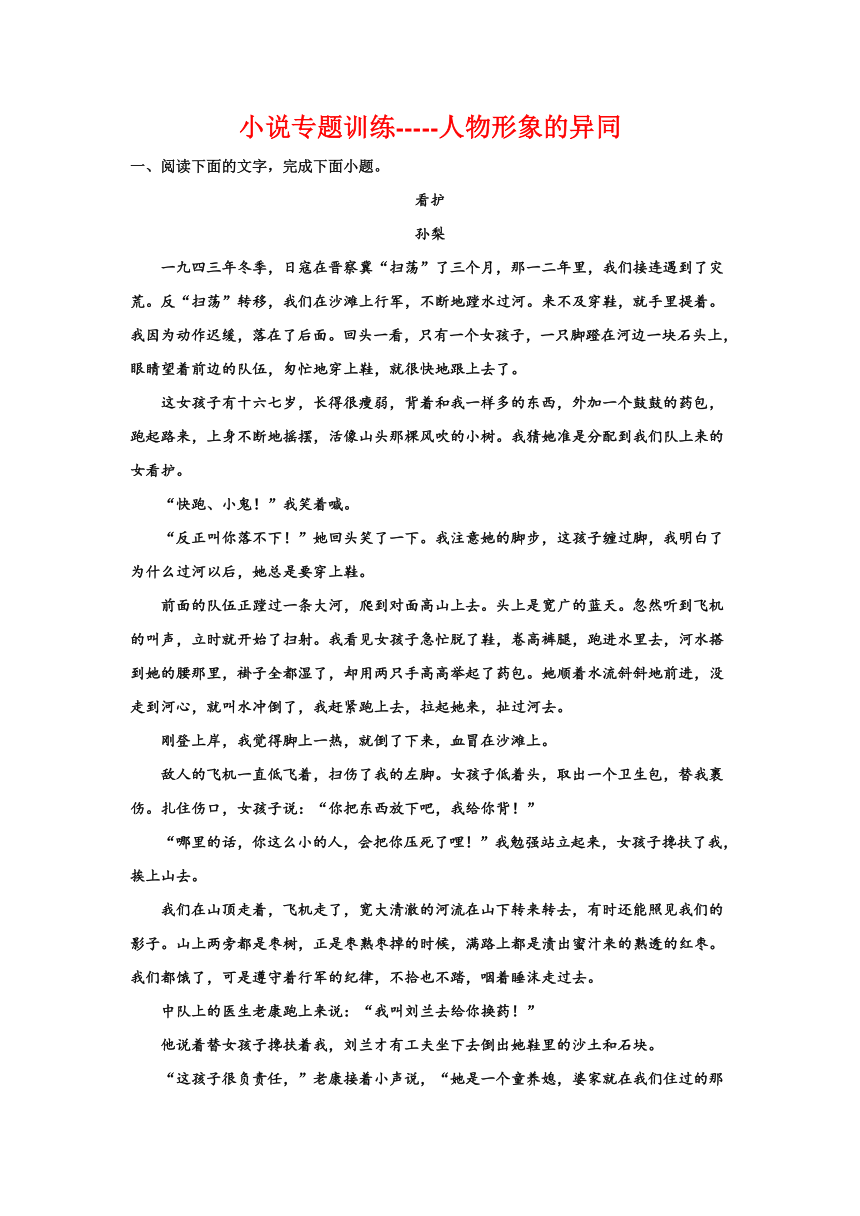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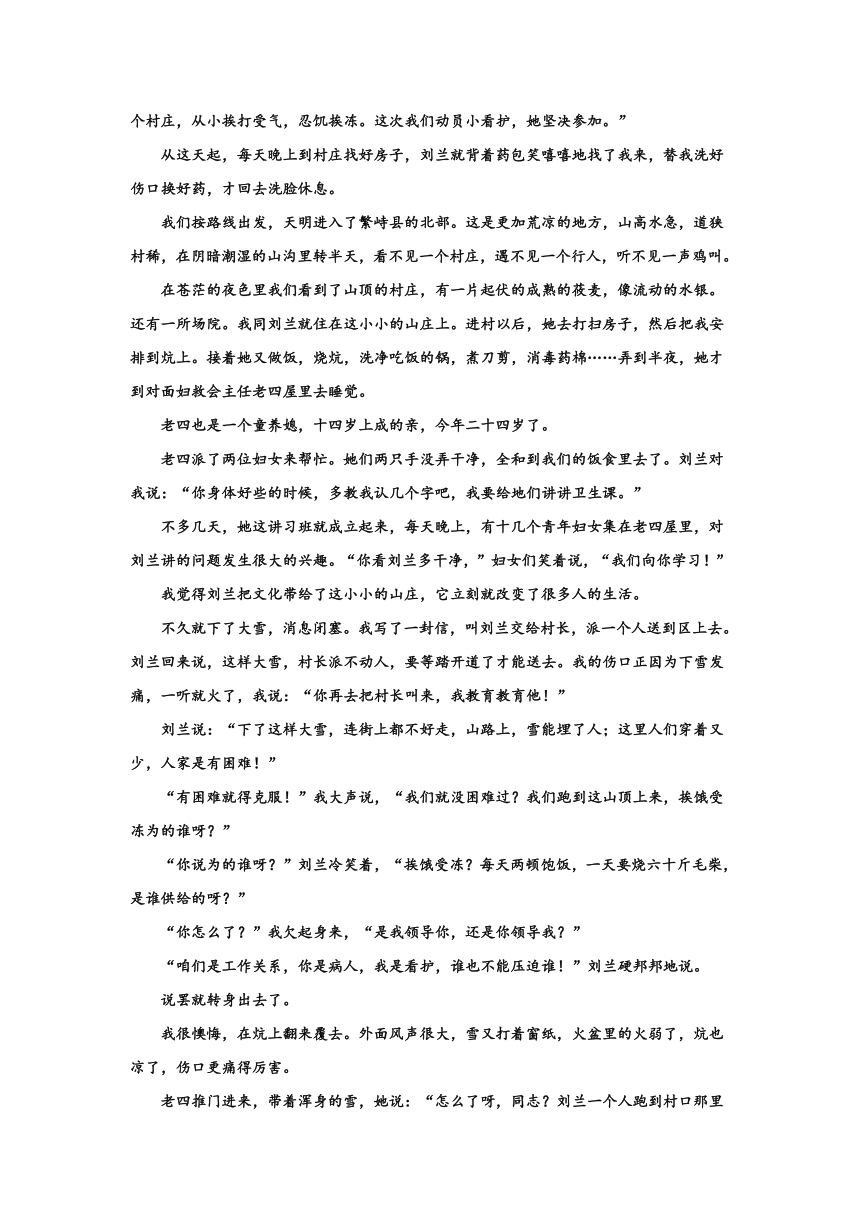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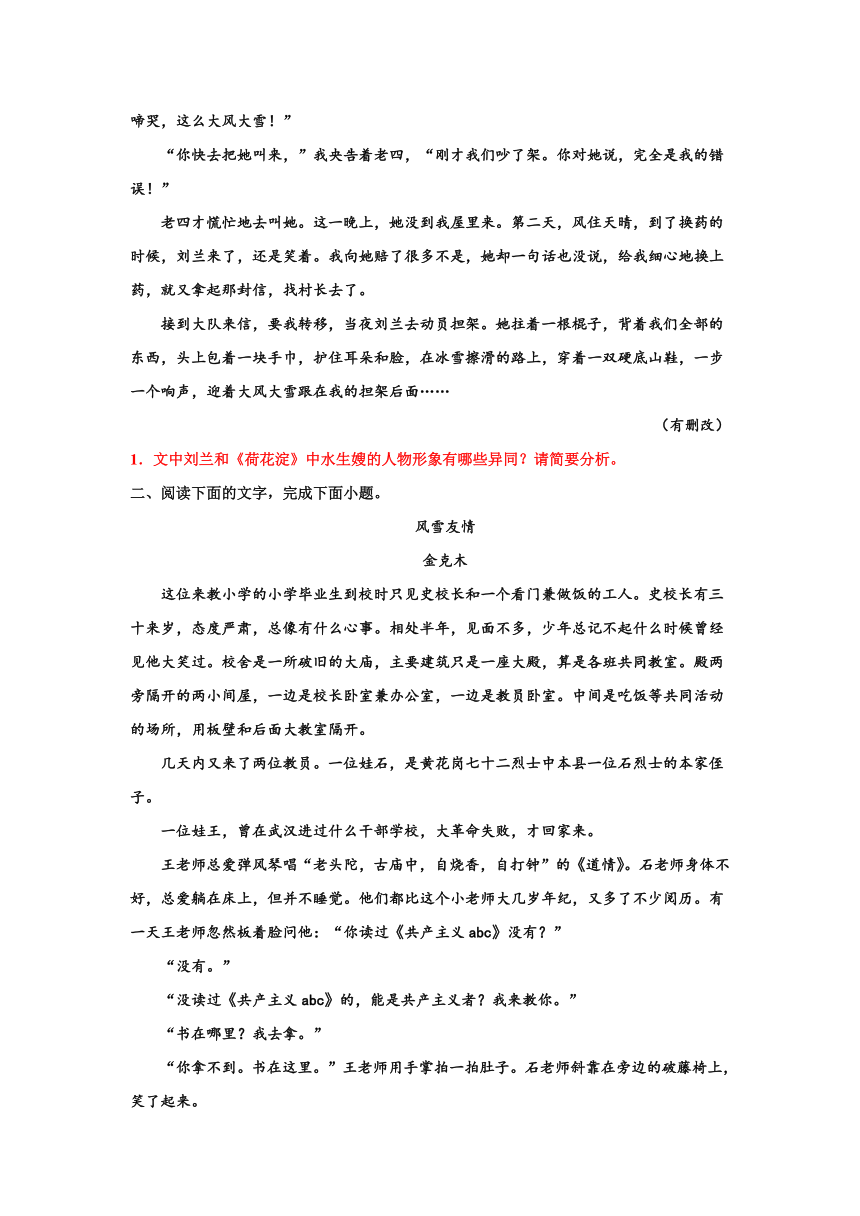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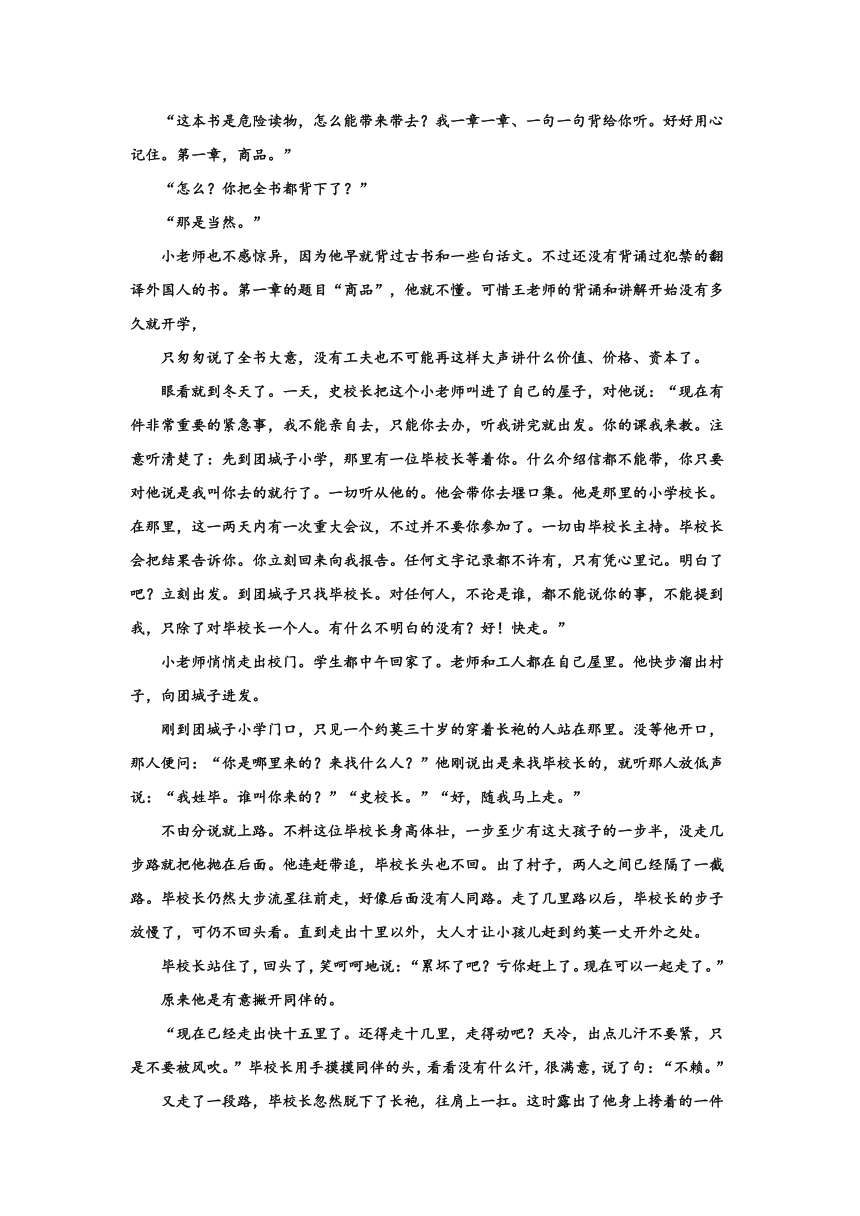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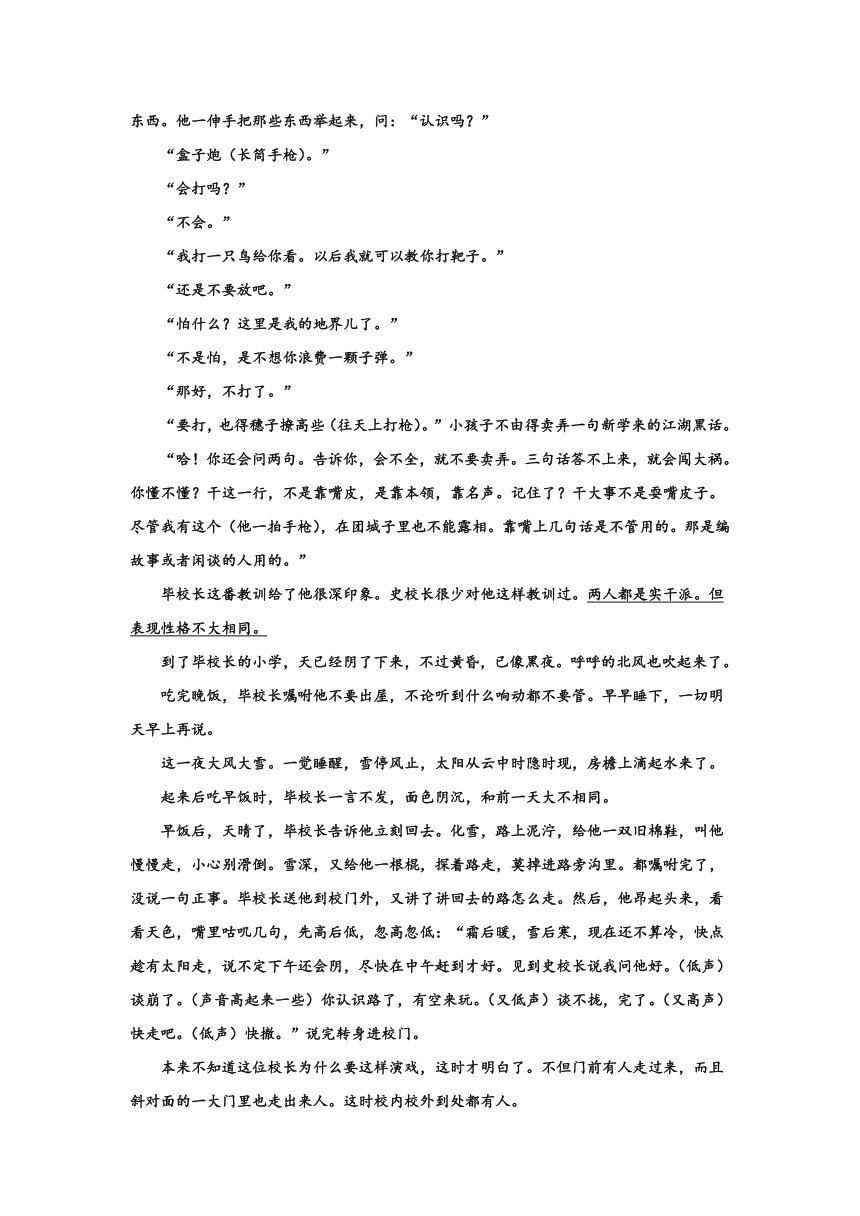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人物形象的异同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看护
孙梨
一九四三年冬季,日寇在晋察冀“扫荡”了三个月,那一二年里,我们接连遇到了灾荒。反“扫荡”转移,我们在沙滩上行军,不断地蹚水过河。来不及穿鞋,就手里提着。我因为动作迟缓,落在了后面。回头一看,只有一个女孩子,一只脚蹬在河边一块石头上,眼睛望着前边的队伍,匆忙地穿上鞋,就很快地跟上去了。
这女孩子有十六七岁,长得很瘦弱,背着和我一样多的东西,外加一个鼓鼓的药包,跑起路来,上身不断地摇摆,活像山头那棵风吹的小树。我猜她准是分配到我们队上来的女看护。
“快跑、小鬼!”我笑着喊。
“反正叫你落不下!”她回头笑了一下。我注意她的脚步,这孩子缠过脚,我明白了为什么过河以后,她总是要穿上鞋。
前面的队伍正蹚过一条大河,爬到对面高山上去。头上是宽广的蓝天。忽然听到飞机的叫声,立时就开始了扫射。我看见女孩子急忙脱了鞋,卷高裤腿,跑进水里去,河水搭到她的腰那里,褂子全都湿了,却用两只手高高举起了药包。她顺着水流斜斜地前进,没走到河心,就叫水冲倒了,我赶紧跑上去,拉起她来,扯过河去。
刚登上岸,我觉得脚上一热,就倒了下来,血冒在沙滩上。
敌人的飞机一直低飞着,扫伤了我的左脚。女孩子低着头,取出一个卫生包,替我裹伤。扎住伤口,女孩子说:“你把东西放下吧,我给你背!”
“哪里的话,你这么小的人,会把你压死了哩!”我勉强站立起来,女孩子搀扶了我,挨上山去。
我们在山顶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有时还能照见我们的影子。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渍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踏,咽着睡沫走过去。
中队上的医生老康跑上来说:“我叫刘兰去给你换药!”
他说着替女孩子搀扶着我,刘兰才有工夫坐下去倒出她鞋里的沙土和石块。
“这孩子很负责任,”老康接着小声说,“她是一个童养媳,婆家就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村庄,从小挨打受气,忍饥挨冻。这次我们动员小看护,她坚决参加。”
从这天起,每天晚上到村庄找好房子,刘兰就背着药包笑嘻嘻地找了我来,替我洗好伤口换好药,才回去洗脸休息。
我们按路线出发,天明进入了繁峙县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山高水急,道狭村稀,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遇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
在苍茫的夜色里我们看到了山顶的村庄,有一片起伏的成熟的莜麦,像流动的水银。还有一所场院。我同刘兰就住在这小小的山庄上。进村以后,她去打扫房子,然后把我安排到炕上。接着她又做饭,烧炕,洗净吃饭的锅,煮刀剪,消毒药棉……弄到半夜,她才到对面妇救会主任老四屋里去睡觉。
老四也是一个童养媳,十四岁上成的亲,今年二十四岁了。
老四派了两位妇女来帮忙。她们两只手没弄干净,全和到我们的饭食里去了。刘兰对我说:“你身体好些的时候,多教我认几个字吧,我要给地们讲讲卫生课。”
不多几天,她这讲习班就成立起来,每天晚上,有十几个青年妇女集在老四屋里,对刘兰讲的问题发生很大的兴趣。“你看刘兰多干净,”妇女们笑着说,“我们向你学习!”
我觉得刘兰把文化带给了这小小的山庄,它立刻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不久就下了大雪,消息闭塞。我写了一封信,叫刘兰交给村长,派一个人送到区上去。刘兰回来说,这样大雪,村长派不动人,要等踏开道了才能送去。我的伤口正因为下雪发痛,一听就火了,我说:“你再去把村长叫来,我教育教育他!”
刘兰说:“下了这样大雪,连街上都不好走,山路上,雪能埋了人;这里人们穿着又少,人家是有困难!”
“有困难就得克服!”我大声说,“我们就没困难过?我们跑到这山顶上来,挨饿受冻为的谁呀?”
“你说为的谁呀?”刘兰冷笑着,“挨饿受冻?每天两顿饱饭,一天要烧六十斤毛柴,是谁供给的呀?”
“你怎么了?”我欠起身来,“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
“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刘兰硬邦邦地说。
说罢就转身出去了。
我很懊悔,在炕上翻来覆去。外面风声很大,雪又打着窗纸,火盆里的火弱了,炕也凉了,伤口更痛得厉害。
老四推门进来,带着浑身的雪,她说:“怎么了呀,同志?刘兰一个人跑到村口那里啼哭,这么大风大雪!”
“你快去把她叫来,”我央告着老四,“刚才我们吵了架。你对她说,完全是我的错误!”
老四才慌忙地去叫她。这一晚上,她没到我屋里来。第二天,风住天晴,到了换药的时候,刘兰来了,还是笑着。我向她赔了很多不是,她却一句话也没说,给我细心地换上药,就又拿起那封信,找村长去了。
接到大队来信,要我转移,当夜刘兰去动员担架。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块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一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
(有删改)
1.文中刘兰和《荷花淀》中水生嫂的人物形象有哪些异同?请简要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风雪友情
金克木
这位来教小学的小学毕业生到校时只见史校长和一个看门兼做饭的工人。史校长有三十来岁,态度严肃,总像有什么心事。相处半年,见面不多,少年总记不起什么时候曾经见他大笑过。校舍是一所破旧的大庙,主要建筑只是一座大殿,算是各班共同教室。殿两旁隔开的两小间屋,一边是校长卧室兼办公室,一边是教员卧室。中间是吃饭等共同活动的场所,用板壁和后面大教室隔开。
几天内又来了两位教员。一位娃石,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本县一位石烈士的本家侄子。
一位娃王,曾在武汉进过什么干部学校,大革命失败,才回家来。
王老师总爱弹风琴唱“老头陀,古庙中,自烧香,自打钟”的《道情》。石老师身体不好,总爱躺在床上,但并不睡觉。他们都比这个小老师大几岁年纪,又多了不少阅历。有一天王老师忽然板着脸问他:“你读过《共产主义abc》没有?”
“没有。”
“没读过《共产主义abc》的,能是共产主义者?我来教你。”
“书在哪里?我去拿。”
“你拿不到。书在这里。”王老师用手掌拍一拍肚子。石老师斜靠在旁边的破藤椅上,笑了起来。
“这本书是危险读物,怎么能带来带去?我一章一章、一句一句背给你听。好好用心记住。第一章,商品。”
“怎么?你把全书都背下了?”
“那是当然。”
小老师也不感惊异,因为他早就背过古书和一些白话文。不过还没有背诵过犯禁的翻译外国人的书。第一章的题目“商品”,他就不懂。可惜王老师的背诵和讲解开始没有多久就开学,
只匆匆说了全书大意,没有工夫也不可能再这样大声讲什么价值、价格、资本了。
眼看就到冬天了。一天,史校长把这个小老师叫进了自己的屋子,对他说:“现在有件非常重要的紧急事,我不能亲自去,只能你去办,听我讲完就出发。你的课我来教。注意听清楚了:先到团城子小学,那里有一位毕校长等着你。什么介绍信都不能带,你只要对他说是我叫你去的就行了。一切听从他的。他会带你去堰口集。他是那里的小学校长。在那里,这一两天内有一次重大会议,不过并不要你参加了。一切由毕校长主持。毕校长会把结果告诉你。你立刻回来向我报告。任何文字记录都不许有,只有凭心里记。明白了吧?立刻出发。到团城子只找毕校长。对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能说你的事,不能提到我,只除了对毕校长一个人。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好!快走。”
小老师悄悄走出校门。学生都中午回家了。老师和工人都在自己屋里。他快步溜出村子,向团城子进发。
刚到团城子小学门口,只见一个约莫三十岁的穿着长袍的人站在那里。没等他开口,那人便问:“你是哪里来的?来找什么人?”他刚说出是来找毕校长的,就听那人放低声说:“我姓毕。谁叫你来的?”“史校长。”“好,随我马上走。”
不由分说就上路。不料这位毕校长身高体壮,一步至少有这大孩子的一步半,没走几步路就把他抛在后面。他连赶带追,毕校长头也不回。出了村子,两人之间已经隔了一截路。毕校长仍然大步流星往前走,好像后面没有人同路。走了几里路以后,毕校长的步子放慢了,可仍不回头看。直到走出十里以外,大人才让小孩儿赶到约莫一丈开外之处。
毕校长站住了,回头了,笑呵呵地说:“累坏了吧?亏你赶上了。现在可以一起走了。”
原来他是有意撇开同伴的。
“现在已经走出快十五里了。还得走十几里,走得动吧?天冷,出点儿汗不要紧,只是不要被风吹。”毕校长用手摸摸同伴的头,看看没有什么汗,很满意,说了句:“不赖。”
又走了一段路,毕校长忽然脱下了长袍,往肩上一扛。这时露出了他身上挎着的一件东西。他一伸手把那些东西举起来,问:“认识吗?”
“盒子炮(长筒手枪)。”
“会打吗?”
“不会。”
“我打一只鸟给你看。以后我就可以教你打靶子。”
“还是不要放吧。”
“怕什么?这里是我的地界儿了。”
“不是怕,是不想你浪费一颗子弹。”
“那好,不打了。”
“要打,也得穗子撩高些(往天上打枪)。”小孩子不由得卖弄一句新学来的江湖黑话。
“哈!你还会问两句。告诉你,会不全,就不要卖弄。三句话答不上来,就会闯大祸。你懂不懂?干这一行,不是靠嘴皮,是靠本领,靠名声。记住了?干大事不是耍嘴皮子。尽管我有这个(他一拍手枪),在团城子里也不能露相。靠嘴上几句话是不管用的。那是编故事或者闲谈的人用的。”
毕校长这番教训给了他很深印象。史校长很少对他这样教训过。两人都是实干派。但表现性格不大相同。
到了毕校长的小学,天已经阴了下来,不过黄昏,已像黑夜。呼呼的北风也吹起来了。
吃完晚饭,毕校长嘱咐他不要出屋,不论听到什么响动都不要管。早早睡下,一切明天早上再说。
这一夜大风大雪。一觉睡醒,雪停风止,太阳从云中时隐时现,房檐上滴起水来了。
起来后吃早饭时,毕校长一言不发,面色阴沉,和前一天大不相同。
早饭后,天晴了,毕校长告诉他立刻回去。化雪,路上泥泞,给他一双旧棉鞋,叫他慢慢走,小心别滑倒。雪深,又给他一根棍,探着路走,莫掉进路旁沟里。都嘱咐完了,没说一句正事。毕校长送他到校门外,又讲了讲回去的路怎么走。然后,他昂起头来,看看天色,嘴里咕叽几句,先高后低,忽高忽低:“霜后暖,雪后寒,现在还不算冷,快点趁有太阳走,说不定下午还会阴,尽快在中午赶到才好。见到史校长说我问他好。(低声)谈崩了。(声音高起来一些)你认识路了,有空来玩。(又低声)谈不拢,完了。(又高声)快走吧。(低声)快撤。”说完转身进校门。
本来不知道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演戏,这时才明白了。不但门前有人走过来,而且斜对面的一大门里也走出来人。这时校内校外到处都有人。
他赶回学校,两脚和两腿都成了泥糊的,身上也沾了不少泥。尽管有根棍,仍然滑跌了几次,幸好没有掉下沟。史校长等得不耐烦了,一听声音,跑出屋门,一把拉他进屋。
“毕校长说:‘谈崩了。谈不拢,完了。快撤。’就这几句话。”
史校长眉头一皱,吁了一口气,伸头向门外一望,转身把他推出去,说:“快回屋,把泥鞋、泥衣裳都换掉。你到什么地方去,做了什么,对任何人也不许说。”
他换好罩衣、罩裤、鞋袜,再出来时,史校长门上一把锁。他不知哪里去了,饭也没吃。
2.文章从“小老师”的角度,交代了史校长和毕校长“两人都是实干派,但表现性格不大相同”。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两人性格特点的异同。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自由
陈忠实
从师范学校的操场上朝南望去,可以看见挺拔雄伟的秦岭的峰峦;从眼前逐渐漫坡增高到山根的广阔的平原上,星散着大大小小的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小河川道里,挑着稻捆的农民从木板搭成的便桥上忽闪忽闪走过去;田间小路上,农民拉着装满包谷棒子的小推车朝邻近的村庄走去。沉到平原西部的太阳,在落沉下去之前,向平原上的人们投射过来热情的最后的一瞥,把瑰丽的红光洒满村庄、田野、河水和挑担拉车的农民的脸上,秦岭陡峭的崖壁上红光闪耀。
我坐在操场边角的草地上,温习算术。我的语文课似乎不成多大困难,算术就吃劲了。“呀!徐慎独,你找了个好清静的地方!”
是田芳,不用抬头也听得出她的声音。我慌忙站起,看着她抿着嘴嗔笑着,倒不知该说什么了,该请她在草地上坐下呢?还是就这么站着?我对于女性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慌恐感,一见着女人,我总是感到心里很紧张。
她坐着不动,忽然盯住我的眼,问:“你为啥一天到晚不和我说话呢?”
我的心里一悸,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使我措辞不及,不知怎样回答。班主任王老师指定我和她同坐在一条长凳上,共用一张桌子,至今有两个月了,我没有主动和她说过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文化水平低。”她说,“你瞧不起我吧?”
我遭到误解了,连忙说:“我……没有没有!”
“那……我是老虎、是魔鬼吗?”她讽讥地说,“怕我吃了你!?”
我的脸轰然发热了,不由地低下头。我想起了在宿舍里听到的那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老和尚威吓小和尚时把女人说成是魔鬼,我似乎就是那个可怜的小和尚了。我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听讲或做作业,我从来也没有敢大胆地扭过头去注视她的脸。我只是在她不在意的时候,装作漫不经心地注视过她的眼睛和脸膛,其实我很想和她说话,和她对视,像她和班里的任何男生一样大大方方交谈或者开玩笑。我不行。越有这样想法,我却越要摆出一副毫不在意毫不动心的神态。我的心里有一道森严的壁垒,坚硬的外壳,对一切异性实行习惯性的排斥与反弹,我只好掩饰说:“我这人……不善辞令!”
“好啊!‘不善辞令’!”她笑了,“你何必那么拘拘束束呢?你自个不觉得难受吗?我呀!一天不笑几场,不唱几场,心里就憋得难受。”
我已经注意自己口头用语中那些文绉绉的词句。“我太……古板。”我说,她的话正说到我的痛处,其实我比她说的还要痛苦。
她笑着,恳切地说:“咱们速成班,在一块不过两年,大家难得遇在一搭,毕业后就各自东西南北地去工作了,再见面也难了。你甭摆出那么一副老学究的样儿好不好?甭老是做出一派正儿八经的样儿好不好?走路就随随便便地走,甭迈那个八字步!说话就爽爽快快地说,甭那么斯斯文文地咬文嚼字!你看……我心里有话都端给你了!”
我难为情地笑笑,我想象不出,我斯斯文文说起话来和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的样子究竟可笑到怎样的程度,却明白大伙对我摆出正儿八经的老学究的样子是不屑一顾的。我想告诉她,走惯了八字步倒不会随随便便走路了,咬文嚼字的说话习惯也难于一下子改过来,我的父亲苦心孤诣给我训戒下的这一套,像铁甲一样把我箍起来。我说:“改是要改,一下子还是改不掉!”
“先把你的蓝布长袍脱下吧!”她说。
“那我穿什么?”我问;
“‘列宁服’,而今时兴。”
“我能穿‘列宁服’吗?”
“当然能。”她肯定地说,“你正年轻,身段也好,穿一身‘列宁服’,保险好看。”
“有卖现成的吗?”我受到鼓舞,尤其她说我身段好,肯定在她看来,我的身材长得并不难看,“山门镇上能买到不?”
“你把长袍改一改。”她说,“山门镇上有个裁缝铺,花一点钱改成‘列宁服’还能省一点。”
“那我现在就去!”
“咱们一块去,我给你参谋。”
那个秃顶的老裁缝,取出改好的衣服,又取出剩余的布头,交给我。
“试试。”她说,“看看合身不?”
我有点难为情,当着她的面脱袍子,不大雅观,就说:“我回去试。”
“在这儿试试,有不合尺寸的地方,老师傅看了也好改。”她说。
“试试吧!”老师傅也这样说。
我不好推辞,就背过她,脱下蓝布长袍来,尽管我袍子下有两层衬衣衬裤,心里还是止不住惶惑,似乎这蓝袍一揭去,我的五脏六腑全部暴露无遗了。
“到镜子前头去照照。”师傅说。
我站在穿衣镜前,自己看见了陌生的自己,竟然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在镜子里第一次发现,我的模样是很俊的,眉骨耸高了,脸上的棱角也明显了,再不是像我父亲骂我的那样一种女子气儿的少年了。
“挺好。”她说,“刚合身。”
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然感到浑身舒展了。天呀!走出裁缝铺的门,踏上山门镇石板铺成的街道,我居然不会走路了!脱掉蓝袍,穿上“列宁服”,那个八字步迈不开了,抬脚举步十分别扭,她刚出门,看着我的走路的样子,噗哧一声笑了,像是压抑了许久似的,我才理会了,她在裁缝面前保持着与我的谨慎的距离,不敢说出太热情的话来。
“呀!衣服换了,路也不会走了!”我也自嘲地说。
“放开走!随随便便走!想蹦就蹦起来!”她说,像是和谁赌着气,“你敢不敢蹦起来?试试你的胆子,徐老先生?”
她在激我,开我的玩笑,我心里一急,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立即就愣住了。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个栈铺拥挤的街镇上,我居然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
“好啊!蓝袍先生敢动手打一个女学生了!真是进步了,解放了!”她讥诮地斜过我一眼,使人感到亲切的讥诮呀!她说,“再勇敢一点,蹦起来!”
我鼓了鼓勇气,连着蹦起来三次,蹦起来,挥一下手臂,落到地上的时候,我脸红耳赤,索性不去看街道上那些市民的脸色。我对她说:“我今天才解放了!”
“对对对!”她连声附和,也很激动,“为啥不蹦呢?为啥不说不笑不唱呢?旧社会,尽让别人尽性儿蹦了,尽情儿笑了唱了,而今解放了,轮着我们妇女了!”
“我可不是妇女!”我分辩说。
“你比妇女还封建!”她哈哈笑着。
“我究竟是什么且不管,”我也笑着说,“反正我自由了!自由多么好哇!”
“唱歌吧!”她说,“有勇气,跟我唱着走过去!”
“我不会唱……”我不承认我没有勇气。
“跟我顺着溜吧!”她说着就唱起来。我和她并排走着,顺着她唱的音调溜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临近校门的时候,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说:“你把八字步全忘了!”
我心里一惊,真的,唱着歌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的脚步从八字步里解放了,自由了!
(节选自陈忠实《蓝袍先生》,有删改)
3.在作品中,蓝袍先生的学生悲叹道:“我送他(蓝袍先生)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感到压抑,一种被铁箍死死地封锁着的压抑,使人几乎透不过气来。”请联系《装在套子里的人》,分析蓝袍先生徐慎独与别里科夫的异同。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苦恼
契诃夫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车夫约纳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达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沾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快点跑!”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腔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回到大车店。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文本有删改)
4.请将本文中的主人公和鲁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处境进行比较,结合文本谈谈二者之间的异同。
参考答案:
1.同:都淳朴、善良、勤劳,深明大义,追求进步,在斗争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异:
①刘兰还有作为看护尽职尽责,传播文化,引领新风的形象特点。
②水生嫂对家庭任劳任怨,对丈夫温柔体贴的形象特点。
2.同:二人对待革命事业都尽心尽力、小心谨慎。
异:史校长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毕校长为人热心、坦诚直率。
3.相同点:徐慎独和别里科夫都有保守、封闭、敏感的特点,两人都是旧制度、旧思想文化的受害者。
不同点:①产生的根源不同:徐慎独深受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但对于旧制度和旧文化有着质疑的态度;别里科夫既是沙皇专制统治的产物,也是其维护者。②两人受害程度不同:徐慎独在他人的感召下,脱下了蓝袍,抛弃了八字步,走向了自由;别里科夫未能在爱情面前获得拯救,依然缩回到了“套子”之中。这表明两人受害的程度不同。
4.同:他们都是刚死了儿子,想向别人倾诉心中的痛苦,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安慰,但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愿望竟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异:①祥林嫂是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认识的人听,而本文主人公的倾诉对象则是自己的顾客,是陌生人。②祥林嫂是在她多次重复讲述时才碰壁的,而姚纳却是在他第一次讲述时就碰了壁。③祥林嫂是有人倾听的,只是人们把倾听后只是想要嘲讽她,咀嚼她的痛苦;而本文主人公却找不到一个听众。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看护
孙梨
一九四三年冬季,日寇在晋察冀“扫荡”了三个月,那一二年里,我们接连遇到了灾荒。反“扫荡”转移,我们在沙滩上行军,不断地蹚水过河。来不及穿鞋,就手里提着。我因为动作迟缓,落在了后面。回头一看,只有一个女孩子,一只脚蹬在河边一块石头上,眼睛望着前边的队伍,匆忙地穿上鞋,就很快地跟上去了。
这女孩子有十六七岁,长得很瘦弱,背着和我一样多的东西,外加一个鼓鼓的药包,跑起路来,上身不断地摇摆,活像山头那棵风吹的小树。我猜她准是分配到我们队上来的女看护。
“快跑、小鬼!”我笑着喊。
“反正叫你落不下!”她回头笑了一下。我注意她的脚步,这孩子缠过脚,我明白了为什么过河以后,她总是要穿上鞋。
前面的队伍正蹚过一条大河,爬到对面高山上去。头上是宽广的蓝天。忽然听到飞机的叫声,立时就开始了扫射。我看见女孩子急忙脱了鞋,卷高裤腿,跑进水里去,河水搭到她的腰那里,褂子全都湿了,却用两只手高高举起了药包。她顺着水流斜斜地前进,没走到河心,就叫水冲倒了,我赶紧跑上去,拉起她来,扯过河去。
刚登上岸,我觉得脚上一热,就倒了下来,血冒在沙滩上。
敌人的飞机一直低飞着,扫伤了我的左脚。女孩子低着头,取出一个卫生包,替我裹伤。扎住伤口,女孩子说:“你把东西放下吧,我给你背!”
“哪里的话,你这么小的人,会把你压死了哩!”我勉强站立起来,女孩子搀扶了我,挨上山去。
我们在山顶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有时还能照见我们的影子。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渍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踏,咽着睡沫走过去。
中队上的医生老康跑上来说:“我叫刘兰去给你换药!”
他说着替女孩子搀扶着我,刘兰才有工夫坐下去倒出她鞋里的沙土和石块。
“这孩子很负责任,”老康接着小声说,“她是一个童养媳,婆家就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村庄,从小挨打受气,忍饥挨冻。这次我们动员小看护,她坚决参加。”
从这天起,每天晚上到村庄找好房子,刘兰就背着药包笑嘻嘻地找了我来,替我洗好伤口换好药,才回去洗脸休息。
我们按路线出发,天明进入了繁峙县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山高水急,道狭村稀,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遇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
在苍茫的夜色里我们看到了山顶的村庄,有一片起伏的成熟的莜麦,像流动的水银。还有一所场院。我同刘兰就住在这小小的山庄上。进村以后,她去打扫房子,然后把我安排到炕上。接着她又做饭,烧炕,洗净吃饭的锅,煮刀剪,消毒药棉……弄到半夜,她才到对面妇救会主任老四屋里去睡觉。
老四也是一个童养媳,十四岁上成的亲,今年二十四岁了。
老四派了两位妇女来帮忙。她们两只手没弄干净,全和到我们的饭食里去了。刘兰对我说:“你身体好些的时候,多教我认几个字吧,我要给地们讲讲卫生课。”
不多几天,她这讲习班就成立起来,每天晚上,有十几个青年妇女集在老四屋里,对刘兰讲的问题发生很大的兴趣。“你看刘兰多干净,”妇女们笑着说,“我们向你学习!”
我觉得刘兰把文化带给了这小小的山庄,它立刻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不久就下了大雪,消息闭塞。我写了一封信,叫刘兰交给村长,派一个人送到区上去。刘兰回来说,这样大雪,村长派不动人,要等踏开道了才能送去。我的伤口正因为下雪发痛,一听就火了,我说:“你再去把村长叫来,我教育教育他!”
刘兰说:“下了这样大雪,连街上都不好走,山路上,雪能埋了人;这里人们穿着又少,人家是有困难!”
“有困难就得克服!”我大声说,“我们就没困难过?我们跑到这山顶上来,挨饿受冻为的谁呀?”
“你说为的谁呀?”刘兰冷笑着,“挨饿受冻?每天两顿饱饭,一天要烧六十斤毛柴,是谁供给的呀?”
“你怎么了?”我欠起身来,“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
“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刘兰硬邦邦地说。
说罢就转身出去了。
我很懊悔,在炕上翻来覆去。外面风声很大,雪又打着窗纸,火盆里的火弱了,炕也凉了,伤口更痛得厉害。
老四推门进来,带着浑身的雪,她说:“怎么了呀,同志?刘兰一个人跑到村口那里啼哭,这么大风大雪!”
“你快去把她叫来,”我央告着老四,“刚才我们吵了架。你对她说,完全是我的错误!”
老四才慌忙地去叫她。这一晚上,她没到我屋里来。第二天,风住天晴,到了换药的时候,刘兰来了,还是笑着。我向她赔了很多不是,她却一句话也没说,给我细心地换上药,就又拿起那封信,找村长去了。
接到大队来信,要我转移,当夜刘兰去动员担架。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块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一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
(有删改)
1.文中刘兰和《荷花淀》中水生嫂的人物形象有哪些异同?请简要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风雪友情
金克木
这位来教小学的小学毕业生到校时只见史校长和一个看门兼做饭的工人。史校长有三十来岁,态度严肃,总像有什么心事。相处半年,见面不多,少年总记不起什么时候曾经见他大笑过。校舍是一所破旧的大庙,主要建筑只是一座大殿,算是各班共同教室。殿两旁隔开的两小间屋,一边是校长卧室兼办公室,一边是教员卧室。中间是吃饭等共同活动的场所,用板壁和后面大教室隔开。
几天内又来了两位教员。一位娃石,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本县一位石烈士的本家侄子。
一位娃王,曾在武汉进过什么干部学校,大革命失败,才回家来。
王老师总爱弹风琴唱“老头陀,古庙中,自烧香,自打钟”的《道情》。石老师身体不好,总爱躺在床上,但并不睡觉。他们都比这个小老师大几岁年纪,又多了不少阅历。有一天王老师忽然板着脸问他:“你读过《共产主义abc》没有?”
“没有。”
“没读过《共产主义abc》的,能是共产主义者?我来教你。”
“书在哪里?我去拿。”
“你拿不到。书在这里。”王老师用手掌拍一拍肚子。石老师斜靠在旁边的破藤椅上,笑了起来。
“这本书是危险读物,怎么能带来带去?我一章一章、一句一句背给你听。好好用心记住。第一章,商品。”
“怎么?你把全书都背下了?”
“那是当然。”
小老师也不感惊异,因为他早就背过古书和一些白话文。不过还没有背诵过犯禁的翻译外国人的书。第一章的题目“商品”,他就不懂。可惜王老师的背诵和讲解开始没有多久就开学,
只匆匆说了全书大意,没有工夫也不可能再这样大声讲什么价值、价格、资本了。
眼看就到冬天了。一天,史校长把这个小老师叫进了自己的屋子,对他说:“现在有件非常重要的紧急事,我不能亲自去,只能你去办,听我讲完就出发。你的课我来教。注意听清楚了:先到团城子小学,那里有一位毕校长等着你。什么介绍信都不能带,你只要对他说是我叫你去的就行了。一切听从他的。他会带你去堰口集。他是那里的小学校长。在那里,这一两天内有一次重大会议,不过并不要你参加了。一切由毕校长主持。毕校长会把结果告诉你。你立刻回来向我报告。任何文字记录都不许有,只有凭心里记。明白了吧?立刻出发。到团城子只找毕校长。对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能说你的事,不能提到我,只除了对毕校长一个人。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好!快走。”
小老师悄悄走出校门。学生都中午回家了。老师和工人都在自己屋里。他快步溜出村子,向团城子进发。
刚到团城子小学门口,只见一个约莫三十岁的穿着长袍的人站在那里。没等他开口,那人便问:“你是哪里来的?来找什么人?”他刚说出是来找毕校长的,就听那人放低声说:“我姓毕。谁叫你来的?”“史校长。”“好,随我马上走。”
不由分说就上路。不料这位毕校长身高体壮,一步至少有这大孩子的一步半,没走几步路就把他抛在后面。他连赶带追,毕校长头也不回。出了村子,两人之间已经隔了一截路。毕校长仍然大步流星往前走,好像后面没有人同路。走了几里路以后,毕校长的步子放慢了,可仍不回头看。直到走出十里以外,大人才让小孩儿赶到约莫一丈开外之处。
毕校长站住了,回头了,笑呵呵地说:“累坏了吧?亏你赶上了。现在可以一起走了。”
原来他是有意撇开同伴的。
“现在已经走出快十五里了。还得走十几里,走得动吧?天冷,出点儿汗不要紧,只是不要被风吹。”毕校长用手摸摸同伴的头,看看没有什么汗,很满意,说了句:“不赖。”
又走了一段路,毕校长忽然脱下了长袍,往肩上一扛。这时露出了他身上挎着的一件东西。他一伸手把那些东西举起来,问:“认识吗?”
“盒子炮(长筒手枪)。”
“会打吗?”
“不会。”
“我打一只鸟给你看。以后我就可以教你打靶子。”
“还是不要放吧。”
“怕什么?这里是我的地界儿了。”
“不是怕,是不想你浪费一颗子弹。”
“那好,不打了。”
“要打,也得穗子撩高些(往天上打枪)。”小孩子不由得卖弄一句新学来的江湖黑话。
“哈!你还会问两句。告诉你,会不全,就不要卖弄。三句话答不上来,就会闯大祸。你懂不懂?干这一行,不是靠嘴皮,是靠本领,靠名声。记住了?干大事不是耍嘴皮子。尽管我有这个(他一拍手枪),在团城子里也不能露相。靠嘴上几句话是不管用的。那是编故事或者闲谈的人用的。”
毕校长这番教训给了他很深印象。史校长很少对他这样教训过。两人都是实干派。但表现性格不大相同。
到了毕校长的小学,天已经阴了下来,不过黄昏,已像黑夜。呼呼的北风也吹起来了。
吃完晚饭,毕校长嘱咐他不要出屋,不论听到什么响动都不要管。早早睡下,一切明天早上再说。
这一夜大风大雪。一觉睡醒,雪停风止,太阳从云中时隐时现,房檐上滴起水来了。
起来后吃早饭时,毕校长一言不发,面色阴沉,和前一天大不相同。
早饭后,天晴了,毕校长告诉他立刻回去。化雪,路上泥泞,给他一双旧棉鞋,叫他慢慢走,小心别滑倒。雪深,又给他一根棍,探着路走,莫掉进路旁沟里。都嘱咐完了,没说一句正事。毕校长送他到校门外,又讲了讲回去的路怎么走。然后,他昂起头来,看看天色,嘴里咕叽几句,先高后低,忽高忽低:“霜后暖,雪后寒,现在还不算冷,快点趁有太阳走,说不定下午还会阴,尽快在中午赶到才好。见到史校长说我问他好。(低声)谈崩了。(声音高起来一些)你认识路了,有空来玩。(又低声)谈不拢,完了。(又高声)快走吧。(低声)快撤。”说完转身进校门。
本来不知道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演戏,这时才明白了。不但门前有人走过来,而且斜对面的一大门里也走出来人。这时校内校外到处都有人。
他赶回学校,两脚和两腿都成了泥糊的,身上也沾了不少泥。尽管有根棍,仍然滑跌了几次,幸好没有掉下沟。史校长等得不耐烦了,一听声音,跑出屋门,一把拉他进屋。
“毕校长说:‘谈崩了。谈不拢,完了。快撤。’就这几句话。”
史校长眉头一皱,吁了一口气,伸头向门外一望,转身把他推出去,说:“快回屋,把泥鞋、泥衣裳都换掉。你到什么地方去,做了什么,对任何人也不许说。”
他换好罩衣、罩裤、鞋袜,再出来时,史校长门上一把锁。他不知哪里去了,饭也没吃。
2.文章从“小老师”的角度,交代了史校长和毕校长“两人都是实干派,但表现性格不大相同”。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两人性格特点的异同。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自由
陈忠实
从师范学校的操场上朝南望去,可以看见挺拔雄伟的秦岭的峰峦;从眼前逐渐漫坡增高到山根的广阔的平原上,星散着大大小小的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小河川道里,挑着稻捆的农民从木板搭成的便桥上忽闪忽闪走过去;田间小路上,农民拉着装满包谷棒子的小推车朝邻近的村庄走去。沉到平原西部的太阳,在落沉下去之前,向平原上的人们投射过来热情的最后的一瞥,把瑰丽的红光洒满村庄、田野、河水和挑担拉车的农民的脸上,秦岭陡峭的崖壁上红光闪耀。
我坐在操场边角的草地上,温习算术。我的语文课似乎不成多大困难,算术就吃劲了。“呀!徐慎独,你找了个好清静的地方!”
是田芳,不用抬头也听得出她的声音。我慌忙站起,看着她抿着嘴嗔笑着,倒不知该说什么了,该请她在草地上坐下呢?还是就这么站着?我对于女性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慌恐感,一见着女人,我总是感到心里很紧张。
她坐着不动,忽然盯住我的眼,问:“你为啥一天到晚不和我说话呢?”
我的心里一悸,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使我措辞不及,不知怎样回答。班主任王老师指定我和她同坐在一条长凳上,共用一张桌子,至今有两个月了,我没有主动和她说过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文化水平低。”她说,“你瞧不起我吧?”
我遭到误解了,连忙说:“我……没有没有!”
“那……我是老虎、是魔鬼吗?”她讽讥地说,“怕我吃了你!?”
我的脸轰然发热了,不由地低下头。我想起了在宿舍里听到的那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老和尚威吓小和尚时把女人说成是魔鬼,我似乎就是那个可怜的小和尚了。我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听讲或做作业,我从来也没有敢大胆地扭过头去注视她的脸。我只是在她不在意的时候,装作漫不经心地注视过她的眼睛和脸膛,其实我很想和她说话,和她对视,像她和班里的任何男生一样大大方方交谈或者开玩笑。我不行。越有这样想法,我却越要摆出一副毫不在意毫不动心的神态。我的心里有一道森严的壁垒,坚硬的外壳,对一切异性实行习惯性的排斥与反弹,我只好掩饰说:“我这人……不善辞令!”
“好啊!‘不善辞令’!”她笑了,“你何必那么拘拘束束呢?你自个不觉得难受吗?我呀!一天不笑几场,不唱几场,心里就憋得难受。”
我已经注意自己口头用语中那些文绉绉的词句。“我太……古板。”我说,她的话正说到我的痛处,其实我比她说的还要痛苦。
她笑着,恳切地说:“咱们速成班,在一块不过两年,大家难得遇在一搭,毕业后就各自东西南北地去工作了,再见面也难了。你甭摆出那么一副老学究的样儿好不好?甭老是做出一派正儿八经的样儿好不好?走路就随随便便地走,甭迈那个八字步!说话就爽爽快快地说,甭那么斯斯文文地咬文嚼字!你看……我心里有话都端给你了!”
我难为情地笑笑,我想象不出,我斯斯文文说起话来和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的样子究竟可笑到怎样的程度,却明白大伙对我摆出正儿八经的老学究的样子是不屑一顾的。我想告诉她,走惯了八字步倒不会随随便便走路了,咬文嚼字的说话习惯也难于一下子改过来,我的父亲苦心孤诣给我训戒下的这一套,像铁甲一样把我箍起来。我说:“改是要改,一下子还是改不掉!”
“先把你的蓝布长袍脱下吧!”她说。
“那我穿什么?”我问;
“‘列宁服’,而今时兴。”
“我能穿‘列宁服’吗?”
“当然能。”她肯定地说,“你正年轻,身段也好,穿一身‘列宁服’,保险好看。”
“有卖现成的吗?”我受到鼓舞,尤其她说我身段好,肯定在她看来,我的身材长得并不难看,“山门镇上能买到不?”
“你把长袍改一改。”她说,“山门镇上有个裁缝铺,花一点钱改成‘列宁服’还能省一点。”
“那我现在就去!”
“咱们一块去,我给你参谋。”
那个秃顶的老裁缝,取出改好的衣服,又取出剩余的布头,交给我。
“试试。”她说,“看看合身不?”
我有点难为情,当着她的面脱袍子,不大雅观,就说:“我回去试。”
“在这儿试试,有不合尺寸的地方,老师傅看了也好改。”她说。
“试试吧!”老师傅也这样说。
我不好推辞,就背过她,脱下蓝布长袍来,尽管我袍子下有两层衬衣衬裤,心里还是止不住惶惑,似乎这蓝袍一揭去,我的五脏六腑全部暴露无遗了。
“到镜子前头去照照。”师傅说。
我站在穿衣镜前,自己看见了陌生的自己,竟然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在镜子里第一次发现,我的模样是很俊的,眉骨耸高了,脸上的棱角也明显了,再不是像我父亲骂我的那样一种女子气儿的少年了。
“挺好。”她说,“刚合身。”
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然感到浑身舒展了。天呀!走出裁缝铺的门,踏上山门镇石板铺成的街道,我居然不会走路了!脱掉蓝袍,穿上“列宁服”,那个八字步迈不开了,抬脚举步十分别扭,她刚出门,看着我的走路的样子,噗哧一声笑了,像是压抑了许久似的,我才理会了,她在裁缝面前保持着与我的谨慎的距离,不敢说出太热情的话来。
“呀!衣服换了,路也不会走了!”我也自嘲地说。
“放开走!随随便便走!想蹦就蹦起来!”她说,像是和谁赌着气,“你敢不敢蹦起来?试试你的胆子,徐老先生?”
她在激我,开我的玩笑,我心里一急,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立即就愣住了。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个栈铺拥挤的街镇上,我居然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
“好啊!蓝袍先生敢动手打一个女学生了!真是进步了,解放了!”她讥诮地斜过我一眼,使人感到亲切的讥诮呀!她说,“再勇敢一点,蹦起来!”
我鼓了鼓勇气,连着蹦起来三次,蹦起来,挥一下手臂,落到地上的时候,我脸红耳赤,索性不去看街道上那些市民的脸色。我对她说:“我今天才解放了!”
“对对对!”她连声附和,也很激动,“为啥不蹦呢?为啥不说不笑不唱呢?旧社会,尽让别人尽性儿蹦了,尽情儿笑了唱了,而今解放了,轮着我们妇女了!”
“我可不是妇女!”我分辩说。
“你比妇女还封建!”她哈哈笑着。
“我究竟是什么且不管,”我也笑着说,“反正我自由了!自由多么好哇!”
“唱歌吧!”她说,“有勇气,跟我唱着走过去!”
“我不会唱……”我不承认我没有勇气。
“跟我顺着溜吧!”她说着就唱起来。我和她并排走着,顺着她唱的音调溜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临近校门的时候,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说:“你把八字步全忘了!”
我心里一惊,真的,唱着歌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的脚步从八字步里解放了,自由了!
(节选自陈忠实《蓝袍先生》,有删改)
3.在作品中,蓝袍先生的学生悲叹道:“我送他(蓝袍先生)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感到压抑,一种被铁箍死死地封锁着的压抑,使人几乎透不过气来。”请联系《装在套子里的人》,分析蓝袍先生徐慎独与别里科夫的异同。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苦恼
契诃夫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车夫约纳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达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沾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快点跑!”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腔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回到大车店。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文本有删改)
4.请将本文中的主人公和鲁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处境进行比较,结合文本谈谈二者之间的异同。
参考答案:
1.同:都淳朴、善良、勤劳,深明大义,追求进步,在斗争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异:
①刘兰还有作为看护尽职尽责,传播文化,引领新风的形象特点。
②水生嫂对家庭任劳任怨,对丈夫温柔体贴的形象特点。
2.同:二人对待革命事业都尽心尽力、小心谨慎。
异:史校长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毕校长为人热心、坦诚直率。
3.相同点:徐慎独和别里科夫都有保守、封闭、敏感的特点,两人都是旧制度、旧思想文化的受害者。
不同点:①产生的根源不同:徐慎独深受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但对于旧制度和旧文化有着质疑的态度;别里科夫既是沙皇专制统治的产物,也是其维护者。②两人受害程度不同:徐慎独在他人的感召下,脱下了蓝袍,抛弃了八字步,走向了自由;别里科夫未能在爱情面前获得拯救,依然缩回到了“套子”之中。这表明两人受害的程度不同。
4.同:他们都是刚死了儿子,想向别人倾诉心中的痛苦,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安慰,但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愿望竟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异:①祥林嫂是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认识的人听,而本文主人公的倾诉对象则是自己的顾客,是陌生人。②祥林嫂是在她多次重复讲述时才碰壁的,而姚纳却是在他第一次讲述时就碰了壁。③祥林嫂是有人倾听的,只是人们把倾听后只是想要嘲讽她,咀嚼她的痛苦;而本文主人公却找不到一个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