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毕飞宇的小说(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毕飞宇的小说(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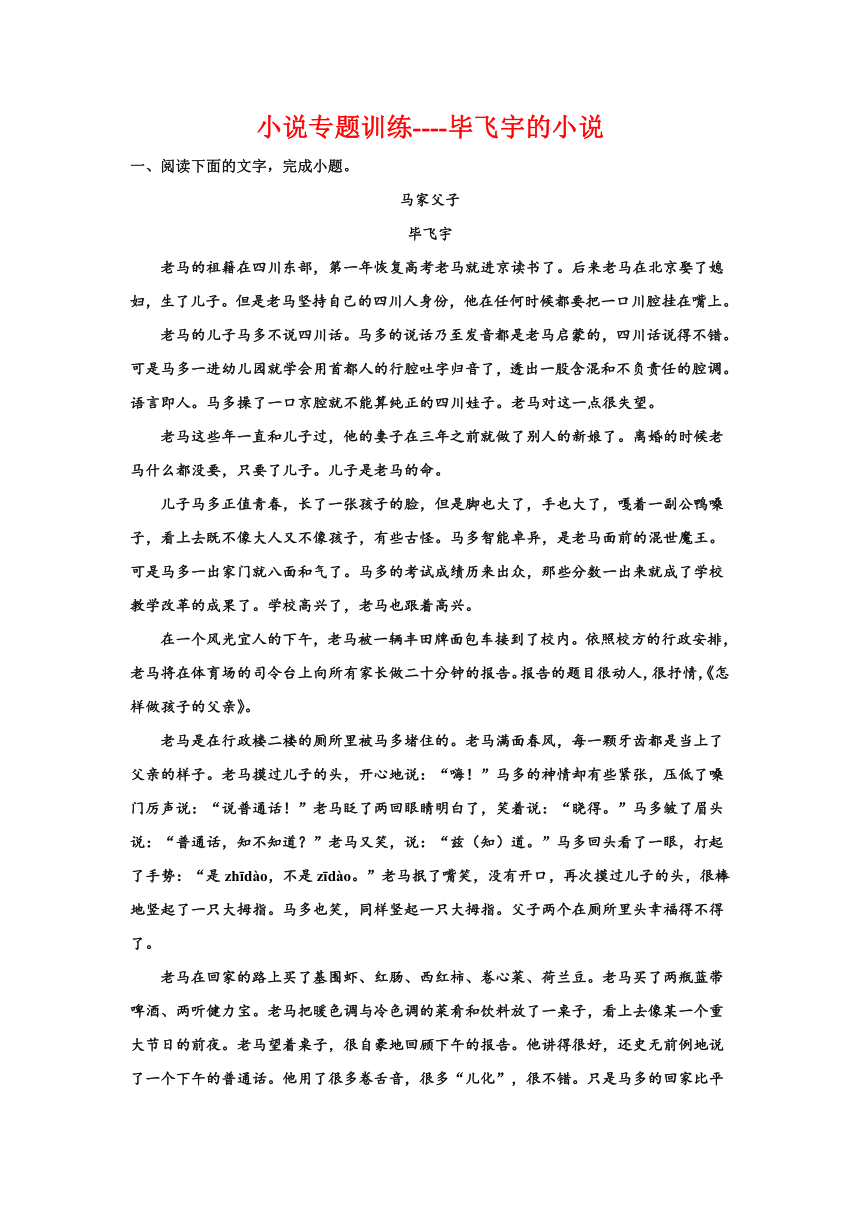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57.7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通用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2-28 22:54:25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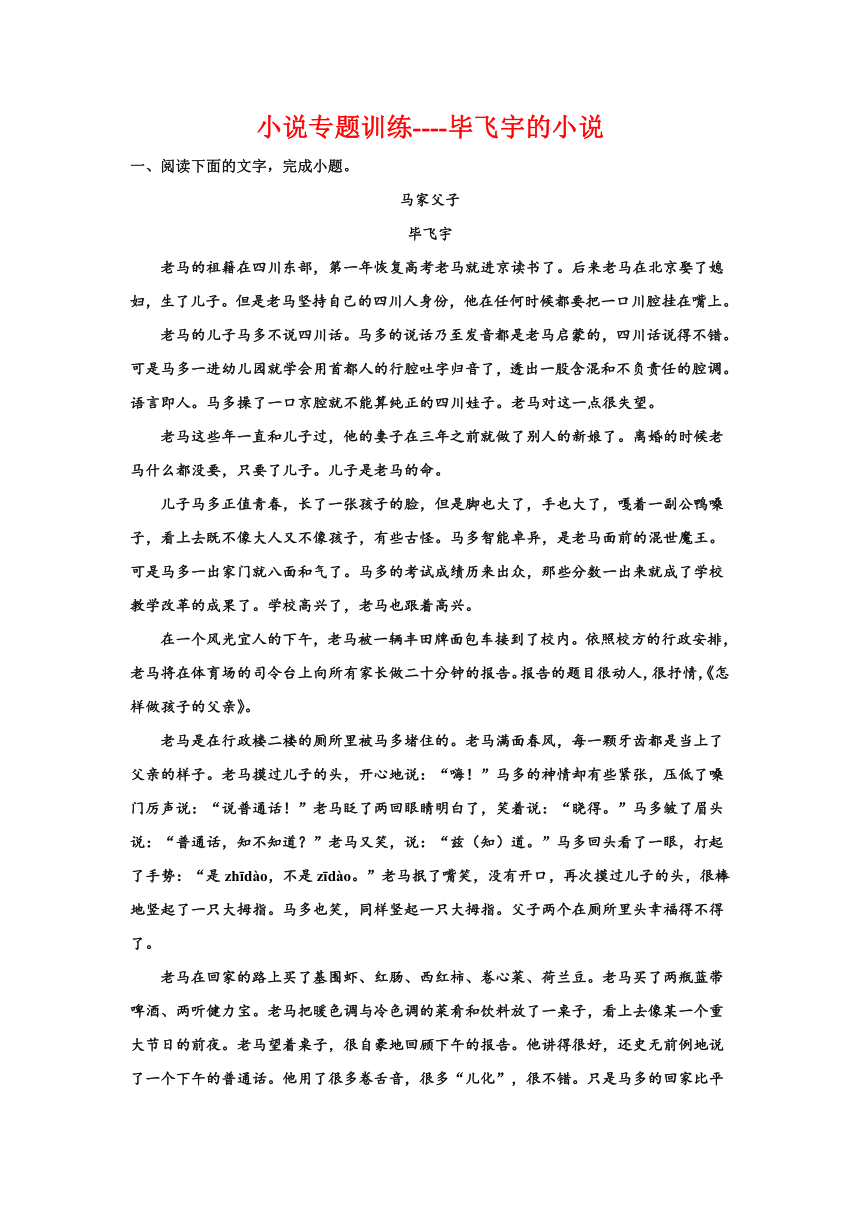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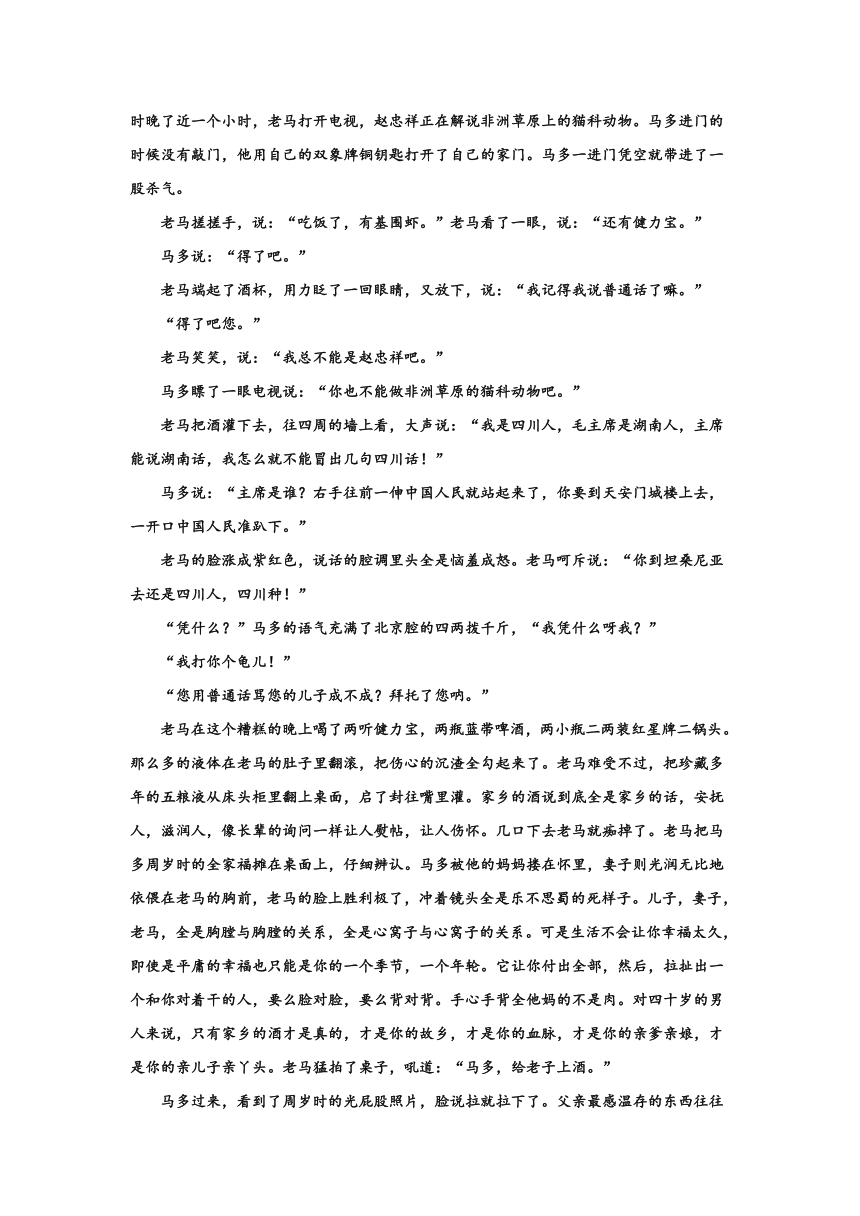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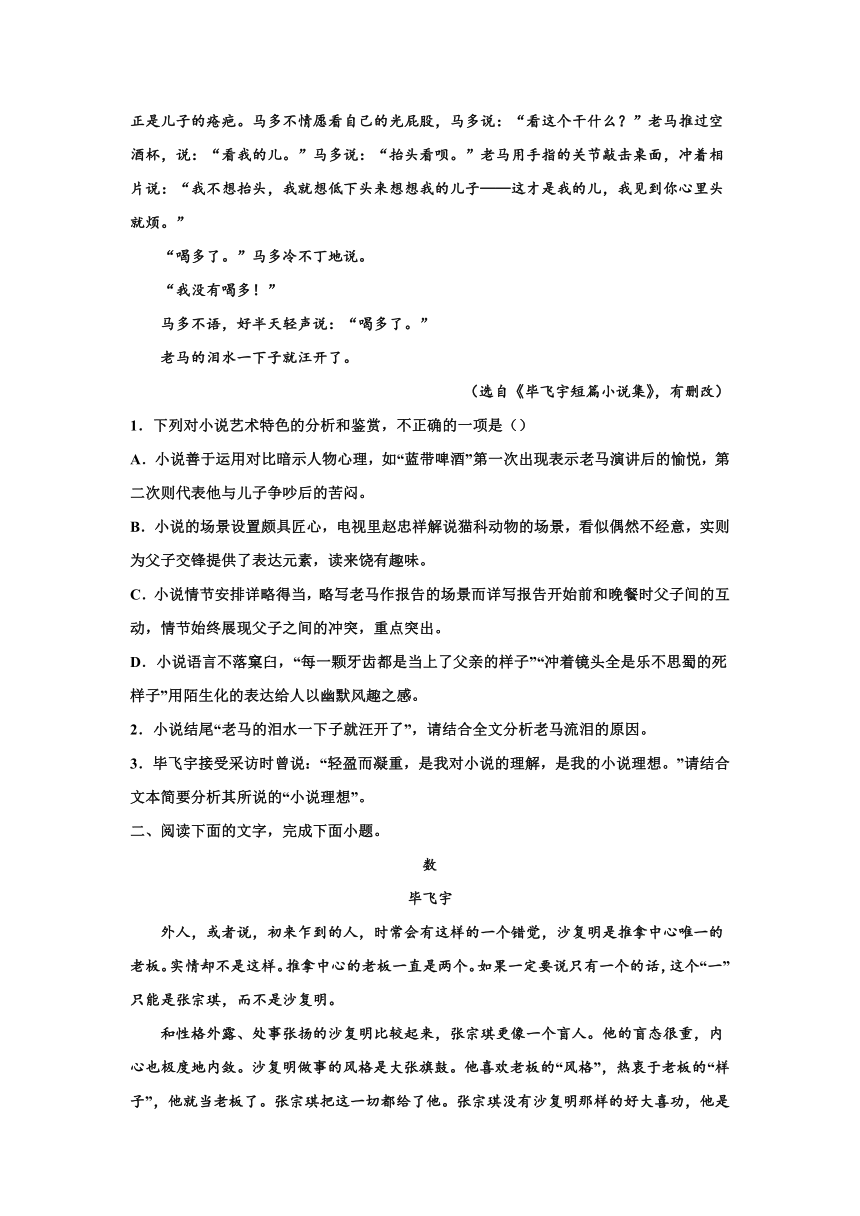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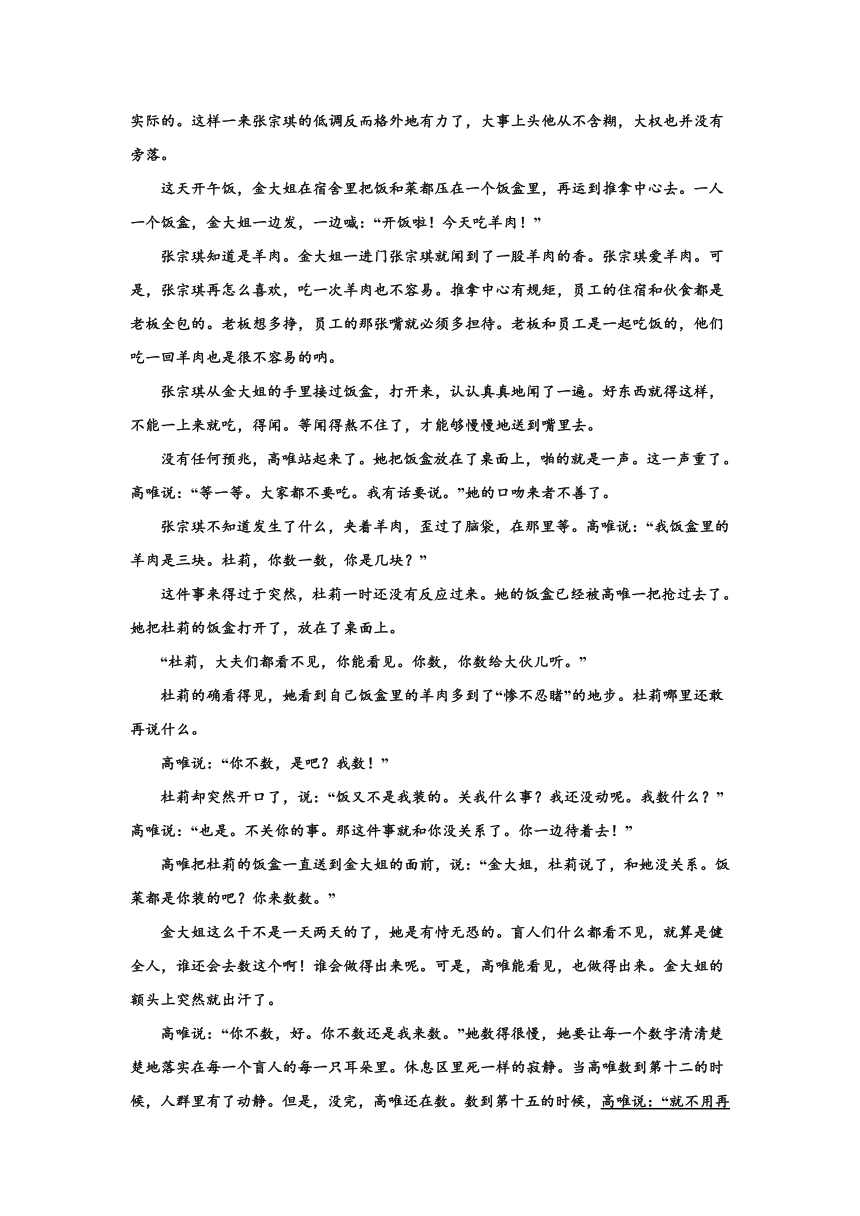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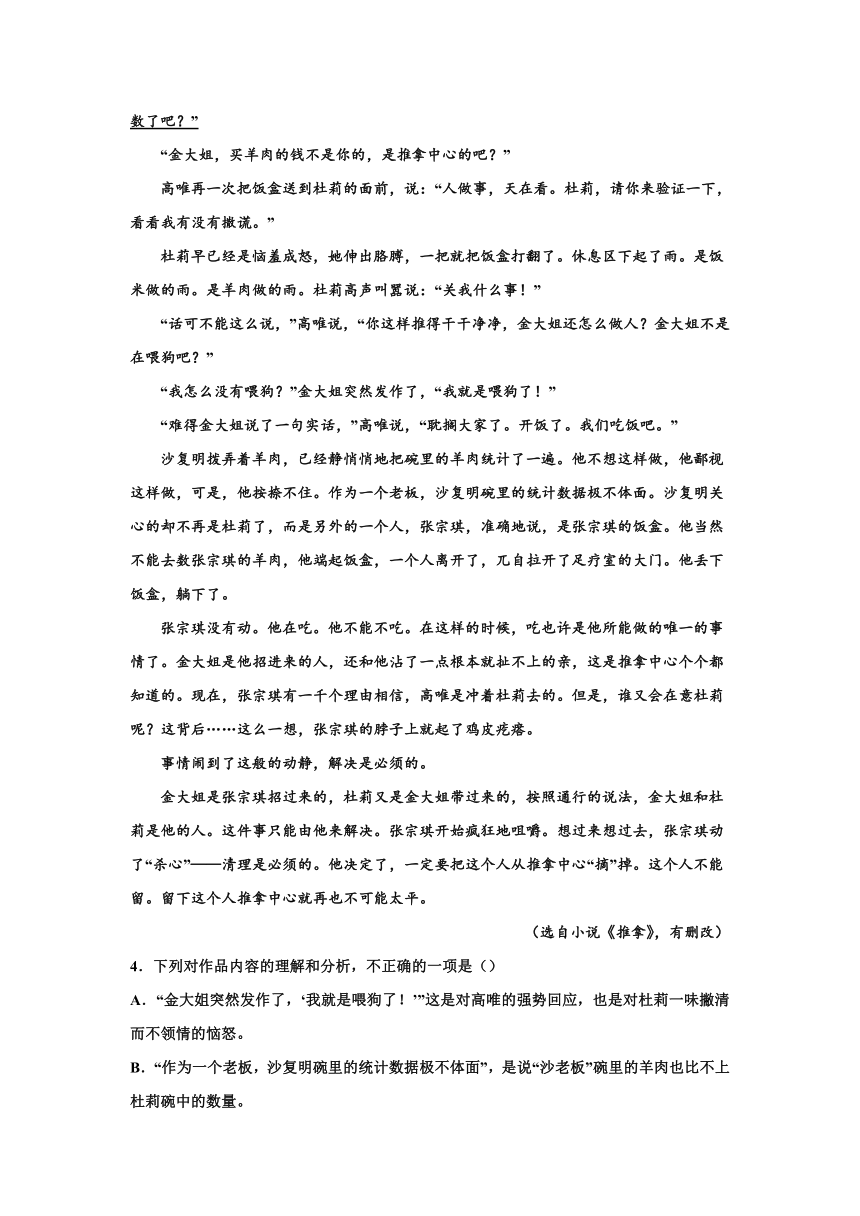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毕飞宇的小说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马家父子
毕飞宇
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嘴上。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子。儿子是老马的命。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出众,那些分数一出来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
在一个风光宜人的下午,老马被一辆丰田牌面包车接到了校内。依照校方的行政安排,老马将在体育场的司令台上向所有家长做二十分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很动人,很抒情,《怎样做孩子的父亲》。
老马是在行政楼二楼的厕所里被马多堵住的。老马满面春风,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老马摸过儿子的头,开心地说:“嗨!”马多的神情却有些紧张,压低了嗓门厉声说:“说普通话!”老马眨了两回眼睛明白了,笑着说:“晓得。”马多皱了眉头说:“普通话,知不知道?”老马又笑,说:“兹(知)道。”马多回头看了一眼,打起了手势:“是zhīdào,不是zīdào。”老马抿了嘴笑,没有开口,再次摸过儿子的头,很棒地竖起了一只大拇指。马多也笑,同样竖起一只大拇指。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得了。
老马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基围虾、红肠、西红柿、卷心菜、荷兰豆。老马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两听健力宝。老马把暖色调与冷色调的菜肴和饮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个重大节日的前夜。老马望着桌子,很自豪地回顾下午的报告。他讲得很好,还史无前例地说了一个下午的普通话。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儿化”,很不错。只是马多的回家比平时晚了近一个小时,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在解说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马多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他用自己的双象牌铜钥匙打开了自己的家门。马多一进门凭空就带进了一股杀气。
老马搓搓手,说:“吃饭了,有基围虾。”老马看了一眼,说:“还有健力宝。”
马多说:“得了吧。”
老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说:“我记得我说普通话了嘛。”
“得了吧您。”
老马笑笑,说:“我总不能是赵忠祥吧。”
马多瞟了一眼电视说:“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猫科动物吧。”
老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墙上看,大声说:“我是四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说湖南话,我怎么就不能冒出几句四川话!”
马多说:“主席是谁?右手往前一伸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你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一开口中国人民准趴下。”
老马的脸涨成紫红色,说话的腔调里头全是恼羞成怒。老马呵斥说:“你到坦桑尼亚去还是四川人,四川种!”
“凭什么?”马多的语气充满了北京腔的四两拨千斤,“我凭什么呀我?”
“我打你个龟儿!”
“您用普通话骂您的儿子成不成?拜托了您呐。”
老马在这个糟糕的晚上喝了两听健力宝,两瓶蓝带啤酒,两小瓶二两装红星牌二锅头。那么多的液体在老马的肚子里翻滚,把伤心的沉渣全勾起来了。老马难受不过,把珍藏多年的五粮液从床头柜里翻上桌面,启了封往嘴里灌。家乡的酒说到底全是家乡的话,安抚人,滋润人,像长辈的询问一样让人熨帖,让人伤怀。几口下去老马就痴掉了。老马把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摊在桌面上,仔细辨认。马多被他的妈妈搂在怀里,妻子则光润无比地依偎在老马的胸前,老马的脸上胜利极了,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儿子,妻子,老马,全是胸膛与胸膛的关系,全是心窝子与心窝子的关系。可是生活不会让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只能是你的一个季节,一个年轮。它让你付出全部,然后,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手心手背全他妈的不是肉。对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只有家乡的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乡,才是你的血脉,才是你的亲爹亲娘,才是你的亲儿子亲丫头。老马猛拍了桌子,吼道:“马多,给老子上酒。”
马多过来,看到了周岁时的光屁股照片,脸说拉就拉下了。父亲最感温存的东西往往正是儿子的疮疤。马多不情愿看自己的光屁股,马多说:“看这个干什么?”老马推过空酒杯,说:“看我的儿。”马多说:“抬头看呗。”老马用手指的关节敲击桌面,冲着相片说:“我不想抬头,我就想低下头来想想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我见到你心里头就烦。”
“喝多了。”马多冷不丁地说。
“我没有喝多!”
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多了。”
老马的泪水一下子就汪开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集》,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善于运用对比暗示人物心理,如“蓝带啤酒”第一次出现表示老马演讲后的愉悦,第二次则代表他与儿子争吵后的苦闷。
B.小说的场景设置颇具匠心,电视里赵忠祥解说猫科动物的场景,看似偶然不经意,实则为父子交锋提供了表达元素,读来饶有趣味。
C.小说情节安排详略得当,略写老马作报告的场景而详写报告开始前和晚餐时父子间的互动,情节始终展现父子之间的冲突,重点突出。
D.小说语言不落窠臼,“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用陌生化的表达给人以幽默风趣之感。
2.小说结尾“老马的泪水一下子就汪开了”,请结合全文分析老马流泪的原因。
3.毕飞宇接受采访时曾说:“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其所说的“小说理想”。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数
毕飞宇
外人,或者说,初来乍到的人,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沙复明是推拿中心唯一的老板。实情却不是这样。推拿中心的老板一直是两个。如果一定要说只有一个的话,这个“一”只能是张宗琪,而不是沙复明。
和性格外露、处事张扬的沙复明比较起来,张宗琪更像一个盲人。他的盲态很重,内心也极度地内敛。沙复明做事的风格是大张旗鼓。他喜欢老板的“风格”,热衷于老板的“样子”,他就当老板了。张宗琪把这一切都给了他。张宗琪没有沙复明那样的好大喜功,他是实际的。这样一来张宗琪的低调反而格外地有力了,大事上头他从不含糊,大权也并没有旁落。
这天开午饭,金大姐在宿舍里把饭和菜都压在一个饭盒里,再运到推拿中心去。一人一个饭盒,金大姐一边发,一边喊:“开饭啦!今天吃羊肉!”
张宗琪知道是羊肉。金大姐一进门张宗琪就闻到了一股羊肉的香。张宗琪爱羊肉。可是,张宗琪再怎么喜欢,吃一次羊肉也不容易。推拿中心有规矩,员工的住宿和伙食都是老板全包的。老板想多挣,员工的那张嘴就必须多担待。老板和员工是一起吃饭的,他们吃一回羊肉也是很不容易的呐。
张宗琪从金大姐的手里接过饭盒,打开来,认认真真地闻了一遍。好东西就得这样,不能一上来就吃,得闻。等闻得熬不住了,才能够慢慢地送到嘴里去。
没有任何预兆,高唯站起来了。她把饭盒放在了桌面上,啪的就是一声。这一声重了。高唯说:“等一等。大家都不要吃。我有话要说。”她的口吻来者不善了。
张宗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夹着羊肉,歪过了脑袋,在那里等。高唯说:“我饭盒里的羊肉是三块。杜莉,你数一数,你是几块?”
这件事来得过于突然,杜莉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她的饭盒已经被高唯一把抢过去了。她把杜莉的饭盒打开了,放在了桌面上。
“杜莉,大夫们都看不见,你能看见。你数,你数给大伙儿听。”
杜莉的确看得见,她看到自己饭盒里的羊肉多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杜莉哪里还敢再说什么。
高唯说:“你不数,是吧?我数!”
杜莉却突然开口了,说:“饭又不是我装的。关我什么事?我还没动呢。我数什么?”高唯说:“也是。不关你的事。那这件事就和你没关系了。你一边待着去!”
高唯把杜莉的饭盒一直送到金大姐的面前,说:“金大姐,杜莉说了,和她没关系。饭菜都是你装的吧?你来数数。”
金大姐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她是有恃无恐的。盲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就算是健全人,谁还会去数这个啊!谁会做得出来呢。可是,高唯能看见,也做得出来。金大姐的额头上突然就出汗了。
高唯说:“你不数,好。你不数还是我来数。”她数得很慢,她要让每一个数字清清楚楚地落实在每一个盲人的每一只耳朵里。休息区里死一样的寂静。当高唯数到第十二的时候,人群里有了动静。但是,没完,高唯还在数。数到第十五的时候,高唯说:“就不用再数了吧?”
“金大姐,买羊肉的钱不是你的,是推拿中心的吧?”
高唯再一次把饭盒送到杜莉的面前,说:“人做事,天在看。杜莉,请你来验证一下,看看我有没有撒谎。”
杜莉早已经是恼羞成怒,她伸出胳膊,一把就把饭盒打翻了。休息区下起了雨。是饭米做的雨。是羊肉做的雨。杜莉高声叫嚣说:“关我什么事!”
“话可不能这么说,”高唯说,“你这样推得干干净净,金大姐还怎么做人?金大姐不是在喂狗吧?”
“我怎么没有喂狗?”金大姐突然发作了,“我就是喂狗了!”
“难得金大姐说了一句实话,”高唯说,“耽搁大家了。开饭了。我们吃饭吧。”
沙复明拨弄着羊肉,已经静悄悄地把碗里的羊肉统计了一遍。他不想这样做,他鄙视这样做,可是,他按捺不住。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碗里的统计数据极不体面。沙复明关心的却不再是杜莉了,而是另外的一个人,张宗琪,准确地说,是张宗琪的饭盒。他当然不能去数张宗琪的羊肉,他端起饭盒,一个人离开了,兀自拉开了足疗室的大门。他丢下饭盒,躺下了。
张宗琪没有动。他在吃。他不能不吃。在这样的时候,吃也许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金大姐是他招进来的人,还和他沾了一点根本就扯不上的亲,这是推拿中心个个都知道的。现在,张宗琪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高唯是冲着杜莉去的。但是,谁又会在意杜莉呢?这背后……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
事情闹到了这般的动静,解决是必须的。
金大姐是张宗琪招过来的,杜莉又是金大姐带过来的,按照通行的说法,金大姐和杜莉是他的人。这件事只能由他来解决。张宗琪开始疯狂地咀嚼。想过来想过去,张宗琪动了“杀心”——清理是必须的。他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个人从推拿中心“摘”掉。这个人不能留。留下这个人推拿中心就再也不可能太平。
(选自小说《推拿》,有删改)
4.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金大姐突然发作了,‘我就是喂狗了!’”这是对高唯的强势回应,也是对杜莉一味撇清而不领情的恼怒。
B.“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碗里的统计数据极不体面”,是说“沙老板”碗里的羊肉也比不上杜莉碗中的数量。
C.“谁又会在意杜莉呢……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是他意识到冲突最终针对的是自己。
D.小说看似围绕杜莉与高唯之间的矛盾展开,实质上暴露的是健全人利用先天优势来欺侮残疾人这一根本问题。
5.下列对作品艺术特色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开篇就运用对比,以第三人称冷静叙述推拿中心的“两个老板”的真实状况,并且将对比贯串全篇。
B.“休息区里死一样的寂静”,这句话既营造了尴尬压抑的氛围,也似乎预示着一场矛盾冲突的爆发。
C.“休息区下起了雨”,运用比喻,把洒落的米饭和羊肉比作雨,同时也象征推拿中心里发生的纠纷。
D.小说“以小见大”,取材于推拿中心,通过普通人群的生存状态,引领读者领悟并思考其中的意蕴。
6.文中画线句在电视剧中被改成“高唯说:‘十五块,是我的五倍。’”请比较并分析两个版本的不同表达效果。
7.小说结尾处,张宗琪决定摘掉“这个人”。你认为“这个人”是谁?请结合故事和人物分析,简述你的理由。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①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孩子们开始向麦秸秆或菜籽秆上爬去。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
②一到夜间蚕婆婆就会坐在床沿,眺望窗外的夜。蚕婆婆看久了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空洞,一种无从说起的空洞。这种空洞被夜的黑色放大了,有点漫无边际。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
③日子一过了谷雨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水汽大了,站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就像是在天上,再也看不见地面了。站了一阵子,感觉到大楼在不停地往天上钻,真的是云里雾里。蚕婆婆对自己说:“一定得回乡下,和天上的云活在一起总不是事。”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
蚕婆婆再也没有料到儿子给她带回来两盒东西。蚕婆婆定了定神,发现盒底黑糊糊的,像爬了一层蚂蚁。她发现那些黑色小颗粒一个个蠕动起来了,有了爬行的迹象。它们是蚕,是黑色的蚕苗。蚕婆婆的胸口咕嘟一声就跳出了一颗大太阳。另一只盒子里塞满了桑叶芽。蚕婆婆捧过来,吸了一口,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蚕婆婆捧着两只纸盒,眼里汪着泪,嗫嗫嚅嚅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第二十九层开始了养蚕生活,就此生龙活虎了起来。她拉上窗帘,在阳台上架起了篾匾,一副回到断桥镇的样子。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二十九层开始了与桑蚕的共同生活。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
蚕仔的身体一转白就开始飞快地成长了。所用的篾匾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面积一天比一天大。阳台和整个客厅差不多都占满了。
离春蚕上山还有四五天了,大儿子突然要飞一趟东北。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仿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儿子又回到了眼前。
意外事件说发生就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蚕婆婆会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蚕婆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阵风过,门被风关上了。关死了。蚕婆婆握着钱包,十分慌乱地扒在门上,拍了十几下,蚕婆婆失声叫道:“儿,儿,给你妈开开门!”
三天之后的清晨,儿子提了密码箱走出了电梯,一拐弯就看见自己的母亲睡在了过道上,身边堆的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母亲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儿子打开门,蚕婆婆随即就跟过来了。蚕婆婆走到蚕床边,蚕婆婆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蚕床都空空荡荡,所有的桑蚕都不翼而飞。
蚕婆婆喘着大气,在二十九层楼的高空神经质地呼喊:“蚕!我的蚕呢!”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选自毕飞宇《中国短经典·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8.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断桥镇是蚕婆婆昔日生活的地方,在断桥镇,蚕婆婆生活自在,养蚕得心应手,拉扯大了孩子。
B.新时代大厦二十九楼是蚕婆婆现在生活的地方,在这里,蚕婆婆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天上,很不适应。
C.小说善于描摹物象表现情境,文中的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等物品构成了现代生活情境。
D.蚕婆婆不适应现代生活,与社会发展变化太快和自己的文化水平有关系,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9.对小说语言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②节中,“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句中的“蚕”,寄托了蚕婆婆对断桥镇养蚕生活的割舍不断的深情。
B.第③节中,“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句中的“雾”和“云”形象地表现出蚕婆婆此时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状态。
C.第节中,“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句,用愉快、伤心这两种情绪代表了蚕婆婆的生活内容,用词凝练,却也凸显了生活的滋味,让人唏嘘。
D.本文多处运用比喻、排比、拟人等修辞,语言生动形象,充满韵味,表现出断桥镇生活的充实、诗意和浪漫,让人不禁对断桥镇充满向往。
10.文章一开始就用大量的笔墨来写蚕婆婆的回忆,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11.小说中“蚕”有怎样的寓意?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枸杞子
毕飞宇
①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父亲进城以前采了两筐枸杞子,用它们换了那锃亮的东西。枸杞是我们家乡生长得最为疯狂的植物,每年盛夏河岸沟谷都要结满籽粒,红得炯炯有神。
②他穿过一丛又一丛枸杞走进我们家天井,大声说,我买了把手电!手电在黄昏时分发出清冽冰凉的光。母亲问,里头是什么?父亲说,是亮。
③第二天全村都晓得我们家有手电了。村里人都说,我们家买了把手电,一家子眼睛都像通了电。晚上我家天井里来了好多人。夏夜清清爽爽,每一颗星都干干净净。话题一直在手电的边缘。夜很晚了,狗都安静了,他们就是不走。母亲很不高兴,她的芭蕉扇在大腿上拍得噼啪起劲。后来母亲站到了皂荚树下,手里拿了那把锃亮的东西,说,你们睁大眼睛看够了!母亲用了很大的努力打开开关,一道雪亮的光柱横在了院子中间,皂荚树上的栖鸟被惊飞起,羽翼带着长长的哨声彗星一样划过,使人的听觉充满夜的宇宙感。
④母亲突然灭了手电,人们在黑暗里默不作声。
⑤勘探船在那个夏夜进村了。勘探队长戴了一顶黄色头盔。勘探队长说他们是来找石油的,而石油就在我们村的地底下,再不打上来油就要流到美国去了。当天他们就在村北打了个洞,一声轰隆,村子像筛糠。村里人立即把父亲叫过去,他们坚信,只有父亲能够阻止他们。父亲走到村北,站立在勘探队长的面前,双手抱在胸前说,不许打了!
⑥勘探队长说,你是谁?
⑦父亲说,再打你就麻烦了!他把这句话撂在村北,一个人回家玩手电去了。
⑧天黑之后来到我家天井的是勘探队队长。他称我的父亲为“亲爱的同志”,然后用科学论证石油和马路、汽车的关系,尤其强调了石油与电的关系。他说石油就是电,有了石油,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电在哪里呢?——电在油里;而油又在哪里?——油在地下。队长说,这是科学!父亲后来沉默了。母亲说,你听他瞎扯。父亲严肃无比地说,你不懂。母亲反驳说,你懂!父亲说,这是科学!
⑨父亲对勘探队长说,你们随便打。
⑩民间想象力的发达总与村落的未来有关。父亲的手电暂时给忽略了。人们一次又一次憧憬着电气化时代。父亲说,到那时水里也装上了电灯,人只要站在岸上就能看见王八、泥鳅与水婆子。父亲设想到那时,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人看鱼就像神仙在天上看我们那样。总之,科学似乎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
而勘探队的勘探进程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不慌不忙地打眼,贮药,点火,起爆。河里的鱼全给震昏了,浮出水面,在水面上漂了一层。勘探队长整日待在井口,面对地下蹿出来的黄泥汤忧心忡忡,有点担心找不出油来。“亲爱的同志们”不会接受没有结果的科学的。那些队员早就疲沓了,日午时分睡倒在树荫下,黄色头盔罩在脸上,打着鼾。
这时,父亲和乡亲们认真地趴在井口,看着黑洞洞的井底。有人提议说用手电照照。父亲回家拿来了手电,照下去,一无所有。有人问下面有科学吗?父亲默然不语,他把科学和希望全闭在了嘴里。太阳金灿灿的,枸杞子红艳艳的。
即将收割的稻子和正成长的棉花被踩得遍地狼藉。乡亲们站在自己的稼禾上心情无比矛盾。勘探队长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这里将是三十八层高楼,四周墙面全是玻璃,在电灯光的照耀下无限辉煌。尔后稼禾带给他们的心疼被满满的憧憬替代了,但高楼和灯光在他们贫瘠的想象中像雾一样难以成形。
父亲一次又一次与勘探队长讨论出石油的可能性。父亲每次都得到肯定回答。父亲一次又一次把那些话传给乡亲,乡亲们默然不语。父亲大声说,不出二十年,我保证大家住上高楼,用上电灯。大伙听了这样的话慢腾腾地散开去,他们的表情一片茫然。
不久,大哥偷走了父亲的手电到村东找蛐蛐,不小心把手电掉到河里,开着的手电竟然沉下河底去了。有人发现了河底的亮光,有两三丈那么长。许多人赶到了河边,河底的光呈墨绿色,麦芒一样四处开张。人们站在岸边手拉手,肩贴肩。人们以恐怖和绝望的心情看着河里的墨绿光慢慢地变暗,消亡。山羊胡子老爹说,动了地气了,动了地气了。一个晚上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千遍。
勘探队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又开始了爆炸。河里没有再死鱼。因为河里已经没有鱼可以死了。他们的动作失去了围观,只留下单调的爆炸和伤感的回音。
在暮色苍茫的时候,勘探队长脱掉了他的长裤,露出的双腿堆满伤疤,他一个劲地说话。他说,这个世上到处是疤,枯叶是风的疤,水泥路是地的疤,井是土的疤。说着这些疯话,他悄然走上船。
浓雾使大早充满瞌睡相。鸡打鸣,撂了两嗓子,就睡回头觉了。浓雾里头父亲做着梦,他梦见了石油光滑油亮的背脊在地底下蠕动的模样。
太阳出来了,雾散了,太阳使村庄愈加鲜嫩可爱。这时候有人说,勘探队!勘探队!人们走东窜西没有发现勘探队的人影子。只有无尽的枸杞子被浓雾乳得干干净净、水灵灵。大伙跟在父亲的身后来到河边,河边空着,满眼是细浪和飞鸟。浓雾退尽后的河面有一片“之”字形水迹,如一只大疤,拉到河面的拐角。这个疤一直烙在父亲的伤心处。父亲的眼里起了大雾,弥漫了父亲的那个夏季。
(有删改)
12.下列对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村民们聚集在“我”家,在时间已经很晚且母亲明显的暗示下仍不愿意离开“我”家,表现出村民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理。
B.对于勘探队,父亲态度转变的原因是父亲懂得了什么是科学,知道只有依靠科学,自己的村子才能发生变化。
C.手电筒在河底发出墨绿色光亮并逐渐变暗、消亡,村民们感到恐怖和绝望,甚至有人认为“动了地气”,表明了那个年代村民思想的落后。
D.小说结尾写“太阳出来了,雾散了”意蕴丰富,村庄勘探石油事件就此结束了,而父亲眼里却起了大雾,表现出父亲的迷茫。
13.下列对小说艺术特点的理解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展开叙述,详写了勘探队来到村中勘探石油的事件,首尾呼应,条理清晰。
B.小说环境描写富有深意,勘探中受破坏的村庄景象和村民们憧憬的生活环境形成对比,引人深思。
C.第⑧段中父亲和勘探队长、父亲和母亲的对话,语言简洁,多用短句,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D.小说中村民群像的塑造不可或缺,他们既暗示了小说的环境背景,也有力地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14.请结合文本,分析画线句“这个疤一直烙在父亲的伤心处”中“疤”的内涵。
15.关于小说的标题,有人认为“手电”好,有人认为“枸杞子”好,你认为哪个更好?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答案
1、C“情节始终展现父子之间的冲突”错误,根据“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行”可知,父子在报告开始前达成一致,并未发生冲突。
2.①曾经幸福圆满的家庭生活与如今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现状形成对比,使老马心中苦涩; ②与儿子难以沟通的痛苦压抑; ③异乡漂泊而无人理解的孤独与寂寞;④从马多延缓的回答和放低的声调中,感受到儿子对自己的理解后的感动
3.轻盈:①整体语言风格活泼:作者多处用揶揄诙谐的语气调侃马家父子,幽默风趣。 ②情节寻常:选材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凝重:①部分语言凝重,充满哲理性:作者在幽默调侃中经常插入凝练着思辨与智性的议论性话语,如“语言即人”“生活会让你付出全部,然后,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这些语句使小说充满理性的深度与厚重。②主题严肃(主题深刻):小说反映了代际沟通面临的实际困境以及对马多这样的年轻人丧失地缘根脉观念的忧思。
4、D“实质上暴露的是健全人利用先天优势来欺侮残疾人这一根本问题”错误。从“现在,张宗琪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高唯是冲着杜莉去的。但是,谁又会在意杜莉呢?高唯的背后是谁?是哪一个指使的呢?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自己怎么一直都蒙在鼓里?亏你还是个老江湖”可知,应该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并非健全人利用先天优势来欺侮残疾人,更不能解读为“实质”“根本问题”。
5.A“贯串全篇”错误,是通过沙复明的“大张旗鼓”与张宗琪的“内敛”“不含糊”对比,反衬张宗琪作为推拿中心“唯一的老板”的处事态度与方法。
6.(1)小说版效果:①以反问句式表达了对杜莉、金大姐的讽刺;②同时给每一个当事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更体现出高唯的工于心计。(2)电视剧版效果:①明确数目,并以“五倍”加以重复强调,突出了两人待遇的反差;②同时给观众以心理冲击。这体现了阅读书籍和观看电视不同的受众心理特征。
7.(示例一)这个人是金大姐。
①金大姐是张宗琪的人,但她对自己人过于偏心,分配羊肉不公,引发了激烈矛盾,影响了推拿中心的安定与稳定。
②张宗琪是真正的老板,“低调”“内敛”,遇大事却“从不含糊”。他要尽责维持推拿中心的“太平”,也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威望。
(示例二)这个人是高唯。
①高唯眼见不公平,却以“数羊肉”挑起和激化矛盾,行为粗暴,体现了性格的刻薄尖锐,影响了推拿中心的安定与稳定。②张宗琪是真正的老板,“低调”“内敛”,遇大事却“从不含糊”。他要尽责维持推拿中心的“太平”,也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威望。
8、D“社会发展变化太快和自己的文化水平”错误,从文中来看,蚕婆婆不适应现代生活主要与蚕婆婆对充实的乡村生活的怀念以及精神需求无处安放有关。
9.D“诗意与浪漫”错误,由第一段蚕婆婆追忆的断桥镇养蚕的日子可以看出,断桥镇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接地气的,是安然的,并非“诗意浪漫”。
10.(1)表现了蚕婆婆对充实的乡村生活的怀念,也反映了对现在生活的不适和孤寂;
(2)与实写二十九楼的生活相呼应,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也凸显了情节的合理性;
(3)表现了转型生活的无奈和困惑(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精神需求的错位)。
11.①断桥镇的蚕是蚕婆婆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②二十九楼上的蚕是蚕婆婆的陪伴和精神寄托;③作茧自缚的蚕象征蚕婆婆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和无法突破的精神困境。
12.B“父亲懂得了什么是科学”错,队长的解释并不能使父亲懂得什么是“科学”,父亲态度的转变只是因为父亲认为勘探队能给村庄带来变化。
13.C“父亲和勘探队长、父亲和母亲的对话……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错误,父亲和勘探队长、父亲和母亲的对话并没有体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14.①生态之“疤”:勘探队对村庄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令父亲痛心。②失望之“疤”:勘探队开采的失败让父亲对“新生活”的期待落空,令父亲失望。③愧疚之“疤”:村民们信任父亲并在父亲的描绘下一起憧憬着美好未来,但最终期待落空,令父亲内疚。
15.[示例一]以“手电”为题好。理由:①“手电”在文中象征着“新事物”与“科学”,反映出父亲及村民们对“新事物”改变生活现状的渴望。②“手电”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手电”与“勘探队”构成小说行文的两条线索:买回“手电”一村民好奇一“手电”掉河底;勘探队到来一村民憧憬一勘探队无果而终。③“手电”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父亲对新生活的追求、村民们的落后思想及对新事物的好奇均通过“手电”呈现。
[示例二]以“枸杞子”为题好。理由:①“枸杞子”作为文章线索,贯穿全文:勘探队来前(枸杞子承载希望)一勘探队来后(枸杞子与庄稼一样被忽略)一勘探队离开(枸杞子依然生机盎然)。②“枸杞子”作为当时村庄里常见的野生物种,在文中象征着简单、质朴的传统乡村生活。③文章结尾充满生机的“枸杞子”与被勘探队弄得“伤痕累累”的村庄形成鲜明对比,易引起读者对“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马家父子
毕飞宇
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嘴上。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子。儿子是老马的命。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出众,那些分数一出来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
在一个风光宜人的下午,老马被一辆丰田牌面包车接到了校内。依照校方的行政安排,老马将在体育场的司令台上向所有家长做二十分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很动人,很抒情,《怎样做孩子的父亲》。
老马是在行政楼二楼的厕所里被马多堵住的。老马满面春风,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老马摸过儿子的头,开心地说:“嗨!”马多的神情却有些紧张,压低了嗓门厉声说:“说普通话!”老马眨了两回眼睛明白了,笑着说:“晓得。”马多皱了眉头说:“普通话,知不知道?”老马又笑,说:“兹(知)道。”马多回头看了一眼,打起了手势:“是zhīdào,不是zīdào。”老马抿了嘴笑,没有开口,再次摸过儿子的头,很棒地竖起了一只大拇指。马多也笑,同样竖起一只大拇指。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得了。
老马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基围虾、红肠、西红柿、卷心菜、荷兰豆。老马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两听健力宝。老马把暖色调与冷色调的菜肴和饮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个重大节日的前夜。老马望着桌子,很自豪地回顾下午的报告。他讲得很好,还史无前例地说了一个下午的普通话。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儿化”,很不错。只是马多的回家比平时晚了近一个小时,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在解说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马多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他用自己的双象牌铜钥匙打开了自己的家门。马多一进门凭空就带进了一股杀气。
老马搓搓手,说:“吃饭了,有基围虾。”老马看了一眼,说:“还有健力宝。”
马多说:“得了吧。”
老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说:“我记得我说普通话了嘛。”
“得了吧您。”
老马笑笑,说:“我总不能是赵忠祥吧。”
马多瞟了一眼电视说:“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猫科动物吧。”
老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墙上看,大声说:“我是四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说湖南话,我怎么就不能冒出几句四川话!”
马多说:“主席是谁?右手往前一伸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你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一开口中国人民准趴下。”
老马的脸涨成紫红色,说话的腔调里头全是恼羞成怒。老马呵斥说:“你到坦桑尼亚去还是四川人,四川种!”
“凭什么?”马多的语气充满了北京腔的四两拨千斤,“我凭什么呀我?”
“我打你个龟儿!”
“您用普通话骂您的儿子成不成?拜托了您呐。”
老马在这个糟糕的晚上喝了两听健力宝,两瓶蓝带啤酒,两小瓶二两装红星牌二锅头。那么多的液体在老马的肚子里翻滚,把伤心的沉渣全勾起来了。老马难受不过,把珍藏多年的五粮液从床头柜里翻上桌面,启了封往嘴里灌。家乡的酒说到底全是家乡的话,安抚人,滋润人,像长辈的询问一样让人熨帖,让人伤怀。几口下去老马就痴掉了。老马把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摊在桌面上,仔细辨认。马多被他的妈妈搂在怀里,妻子则光润无比地依偎在老马的胸前,老马的脸上胜利极了,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儿子,妻子,老马,全是胸膛与胸膛的关系,全是心窝子与心窝子的关系。可是生活不会让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只能是你的一个季节,一个年轮。它让你付出全部,然后,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手心手背全他妈的不是肉。对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只有家乡的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乡,才是你的血脉,才是你的亲爹亲娘,才是你的亲儿子亲丫头。老马猛拍了桌子,吼道:“马多,给老子上酒。”
马多过来,看到了周岁时的光屁股照片,脸说拉就拉下了。父亲最感温存的东西往往正是儿子的疮疤。马多不情愿看自己的光屁股,马多说:“看这个干什么?”老马推过空酒杯,说:“看我的儿。”马多说:“抬头看呗。”老马用手指的关节敲击桌面,冲着相片说:“我不想抬头,我就想低下头来想想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我见到你心里头就烦。”
“喝多了。”马多冷不丁地说。
“我没有喝多!”
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多了。”
老马的泪水一下子就汪开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集》,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善于运用对比暗示人物心理,如“蓝带啤酒”第一次出现表示老马演讲后的愉悦,第二次则代表他与儿子争吵后的苦闷。
B.小说的场景设置颇具匠心,电视里赵忠祥解说猫科动物的场景,看似偶然不经意,实则为父子交锋提供了表达元素,读来饶有趣味。
C.小说情节安排详略得当,略写老马作报告的场景而详写报告开始前和晚餐时父子间的互动,情节始终展现父子之间的冲突,重点突出。
D.小说语言不落窠臼,“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用陌生化的表达给人以幽默风趣之感。
2.小说结尾“老马的泪水一下子就汪开了”,请结合全文分析老马流泪的原因。
3.毕飞宇接受采访时曾说:“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其所说的“小说理想”。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数
毕飞宇
外人,或者说,初来乍到的人,时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沙复明是推拿中心唯一的老板。实情却不是这样。推拿中心的老板一直是两个。如果一定要说只有一个的话,这个“一”只能是张宗琪,而不是沙复明。
和性格外露、处事张扬的沙复明比较起来,张宗琪更像一个盲人。他的盲态很重,内心也极度地内敛。沙复明做事的风格是大张旗鼓。他喜欢老板的“风格”,热衷于老板的“样子”,他就当老板了。张宗琪把这一切都给了他。张宗琪没有沙复明那样的好大喜功,他是实际的。这样一来张宗琪的低调反而格外地有力了,大事上头他从不含糊,大权也并没有旁落。
这天开午饭,金大姐在宿舍里把饭和菜都压在一个饭盒里,再运到推拿中心去。一人一个饭盒,金大姐一边发,一边喊:“开饭啦!今天吃羊肉!”
张宗琪知道是羊肉。金大姐一进门张宗琪就闻到了一股羊肉的香。张宗琪爱羊肉。可是,张宗琪再怎么喜欢,吃一次羊肉也不容易。推拿中心有规矩,员工的住宿和伙食都是老板全包的。老板想多挣,员工的那张嘴就必须多担待。老板和员工是一起吃饭的,他们吃一回羊肉也是很不容易的呐。
张宗琪从金大姐的手里接过饭盒,打开来,认认真真地闻了一遍。好东西就得这样,不能一上来就吃,得闻。等闻得熬不住了,才能够慢慢地送到嘴里去。
没有任何预兆,高唯站起来了。她把饭盒放在了桌面上,啪的就是一声。这一声重了。高唯说:“等一等。大家都不要吃。我有话要说。”她的口吻来者不善了。
张宗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夹着羊肉,歪过了脑袋,在那里等。高唯说:“我饭盒里的羊肉是三块。杜莉,你数一数,你是几块?”
这件事来得过于突然,杜莉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她的饭盒已经被高唯一把抢过去了。她把杜莉的饭盒打开了,放在了桌面上。
“杜莉,大夫们都看不见,你能看见。你数,你数给大伙儿听。”
杜莉的确看得见,她看到自己饭盒里的羊肉多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杜莉哪里还敢再说什么。
高唯说:“你不数,是吧?我数!”
杜莉却突然开口了,说:“饭又不是我装的。关我什么事?我还没动呢。我数什么?”高唯说:“也是。不关你的事。那这件事就和你没关系了。你一边待着去!”
高唯把杜莉的饭盒一直送到金大姐的面前,说:“金大姐,杜莉说了,和她没关系。饭菜都是你装的吧?你来数数。”
金大姐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她是有恃无恐的。盲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就算是健全人,谁还会去数这个啊!谁会做得出来呢。可是,高唯能看见,也做得出来。金大姐的额头上突然就出汗了。
高唯说:“你不数,好。你不数还是我来数。”她数得很慢,她要让每一个数字清清楚楚地落实在每一个盲人的每一只耳朵里。休息区里死一样的寂静。当高唯数到第十二的时候,人群里有了动静。但是,没完,高唯还在数。数到第十五的时候,高唯说:“就不用再数了吧?”
“金大姐,买羊肉的钱不是你的,是推拿中心的吧?”
高唯再一次把饭盒送到杜莉的面前,说:“人做事,天在看。杜莉,请你来验证一下,看看我有没有撒谎。”
杜莉早已经是恼羞成怒,她伸出胳膊,一把就把饭盒打翻了。休息区下起了雨。是饭米做的雨。是羊肉做的雨。杜莉高声叫嚣说:“关我什么事!”
“话可不能这么说,”高唯说,“你这样推得干干净净,金大姐还怎么做人?金大姐不是在喂狗吧?”
“我怎么没有喂狗?”金大姐突然发作了,“我就是喂狗了!”
“难得金大姐说了一句实话,”高唯说,“耽搁大家了。开饭了。我们吃饭吧。”
沙复明拨弄着羊肉,已经静悄悄地把碗里的羊肉统计了一遍。他不想这样做,他鄙视这样做,可是,他按捺不住。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碗里的统计数据极不体面。沙复明关心的却不再是杜莉了,而是另外的一个人,张宗琪,准确地说,是张宗琪的饭盒。他当然不能去数张宗琪的羊肉,他端起饭盒,一个人离开了,兀自拉开了足疗室的大门。他丢下饭盒,躺下了。
张宗琪没有动。他在吃。他不能不吃。在这样的时候,吃也许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金大姐是他招进来的人,还和他沾了一点根本就扯不上的亲,这是推拿中心个个都知道的。现在,张宗琪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高唯是冲着杜莉去的。但是,谁又会在意杜莉呢?这背后……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
事情闹到了这般的动静,解决是必须的。
金大姐是张宗琪招过来的,杜莉又是金大姐带过来的,按照通行的说法,金大姐和杜莉是他的人。这件事只能由他来解决。张宗琪开始疯狂地咀嚼。想过来想过去,张宗琪动了“杀心”——清理是必须的。他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个人从推拿中心“摘”掉。这个人不能留。留下这个人推拿中心就再也不可能太平。
(选自小说《推拿》,有删改)
4.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金大姐突然发作了,‘我就是喂狗了!’”这是对高唯的强势回应,也是对杜莉一味撇清而不领情的恼怒。
B.“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碗里的统计数据极不体面”,是说“沙老板”碗里的羊肉也比不上杜莉碗中的数量。
C.“谁又会在意杜莉呢……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是他意识到冲突最终针对的是自己。
D.小说看似围绕杜莉与高唯之间的矛盾展开,实质上暴露的是健全人利用先天优势来欺侮残疾人这一根本问题。
5.下列对作品艺术特色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开篇就运用对比,以第三人称冷静叙述推拿中心的“两个老板”的真实状况,并且将对比贯串全篇。
B.“休息区里死一样的寂静”,这句话既营造了尴尬压抑的氛围,也似乎预示着一场矛盾冲突的爆发。
C.“休息区下起了雨”,运用比喻,把洒落的米饭和羊肉比作雨,同时也象征推拿中心里发生的纠纷。
D.小说“以小见大”,取材于推拿中心,通过普通人群的生存状态,引领读者领悟并思考其中的意蕴。
6.文中画线句在电视剧中被改成“高唯说:‘十五块,是我的五倍。’”请比较并分析两个版本的不同表达效果。
7.小说结尾处,张宗琪决定摘掉“这个人”。你认为“这个人”是谁?请结合故事和人物分析,简述你的理由。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①蚕婆婆在这个悲伤的夜间开始追忆断桥镇养蚕的日子。成千上万的桑蚕交相辉映,洋溢着星空一般的灿烂荧光。它们弯起背脊,又伸长了身体,一起涌向了蚕婆婆。它们的身体像梦的指头,抚摩着蚕婆婆。每一个蚕季最后的几天总是难熬的,一到夜深人静,这个世界上最喧闹的只剩下桑蚕啃噬桑叶的沙沙声了。蚕婆婆像给爱蹬被单的婴孩盖棉被一样整夜为它们铺桑叶,往往是最后一张蚕床刚刚铺完,第一张蚕床上的桑叶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然后,某一个午夜就这样来临了,孩子们开始向麦秸秆或菜籽秆上爬去。蚕婆婆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桑蚕,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它们会昂起头,像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既像晓通人事,又像懵懂无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神情与你对视。蚕婆婆每一次都要被这样的对视所感动,被爬行的感触是那样地切肤,附带滋生出一种很异样的温存。
②一到夜间蚕婆婆就会坐在床沿,眺望窗外的夜。蚕婆婆看久了就会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空洞,一种无从说起的空洞。这种空洞被夜的黑色放大了,有点漫无边际。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
③日子一过了谷雨连着下了几天的小雨,水汽大了,站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就像是在天上,再也看不见地面了。站了一阵子,感觉到大楼在不停地往天上钻,真的是云里雾里。蚕婆婆对自己说:“一定得回乡下,和天上的云活在一起总不是事。”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
蚕婆婆再也没有料到儿子给她带回来两盒东西。蚕婆婆定了定神,发现盒底黑糊糊的,像爬了一层蚂蚁。她发现那些黑色小颗粒一个个蠕动起来了,有了爬行的迹象。它们是蚕,是黑色的蚕苗。蚕婆婆的胸口咕嘟一声就跳出了一颗大太阳。另一只盒子里塞满了桑叶芽。蚕婆婆捧过来,吸了一口,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蚕婆婆捧着两只纸盒,眼里汪着泪,嗫嗫嚅嚅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第二十九层开始了养蚕生活,就此生龙活虎了起来。她拉上窗帘,在阳台上架起了篾匾,一副回到断桥镇的样子。
蚕婆婆在新时代大厦的二十九层开始了与桑蚕的共同生活。她抚弄着蚕,和它们拉家常,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家乡话。蚕婆婆的唠叨涉及了她这一辈子的全部内容,没有时间顺序,没有逻辑关联,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
蚕仔的身体一转白就开始飞快地成长了。所用的篾匾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面积一天比一天大。阳台和整个客厅差不多都占满了。
离春蚕上山还有四五天了,大儿子突然要飞一趟东北。蚕婆婆一个人在家,心情很不错。她打开了一扇窗,在窗户底下仔细慈爱地打量她的蚕宝宝。快上山的桑蚕身子开始笨重了,显得又大又长。蚕婆婆从蚕床上挑了五只最大的桑蚕,让它们爬在自己的胳膊上。蚕婆婆指着它们,自语说:“你是老大,你是老二……”蚕婆婆逗弄着桑蚕,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重新怀了一遍,重新分娩了一遍,重新哺育了一遍。仿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儿子又回到了眼前。
意外事件说发生就发生了,谁也没有料到蚕婆婆会把自己锁在门外了。蚕婆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阵风过,门被风关上了。关死了。蚕婆婆握着钱包,十分慌乱地扒在门上,拍了十几下,蚕婆婆失声叫道:“儿,儿,给你妈开开门!”
三天之后的清晨,儿子提了密码箱走出了电梯,一拐弯就看见自己的母亲睡在了过道上,身边堆的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母亲面色如土,头发散乱。
儿子打开门,蚕婆婆随即就跟过来了。蚕婆婆走到蚕床边,蚕婆婆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蚕床都空空荡荡,所有的桑蚕都不翼而飞。
蚕婆婆喘着大气,在二十九层楼的高空神经质地呼喊:“蚕!我的蚕呢!”
大儿子仰起了头,雪白的墙面上正开始着许多秘密。墙体与墙体的拐角全部结上了蚕茧。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蚕婆婆合起双手,紧抿了双唇。蚕婆婆说:“罪过,罪过噢,还没有吃饱呢,——它们一个都没吃饱呢!”
桑蚕们不再关心这些了。它们还在缓慢地吐。沿着半透明的蚕茧内侧一圈又一圈地包裹自己,围困自己。在变成昏睡的蚕蛹之前,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且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使内质完完全全地成为躯壳,然后,被自己束之高阁。
(选自毕飞宇《中国短经典·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8.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断桥镇是蚕婆婆昔日生活的地方,在断桥镇,蚕婆婆生活自在,养蚕得心应手,拉扯大了孩子。
B.新时代大厦二十九楼是蚕婆婆现在生活的地方,在这里,蚕婆婆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天上,很不适应。
C.小说善于描摹物象表现情境,文中的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等物品构成了现代生活情境。
D.蚕婆婆不适应现代生活,与社会发展变化太快和自己的文化水平有关系,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9.对小说语言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②节中,“星星在天上闪烁,泪水涌起的时候满天的星斗像爬满夜空的蚕”句中的“蚕”,寄托了蚕婆婆对断桥镇养蚕生活的割舍不断的深情。
B.第③节中,“蚕婆婆望着窗外,心里全是茶色的雾,全是大捆大捆的乱云在迅速地飘移”句中的“雾”和“云”形象地表现出蚕婆婆此时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状态。
C.第节中,“只是一个又一个愉快,一个又一个伤心”句,用愉快、伤心这两种情绪代表了蚕婆婆的生活内容,用词凝练,却也凸显了生活的滋味,让人唏嘘。
D.本文多处运用比喻、排比、拟人等修辞,语言生动形象,充满韵味,表现出断桥镇生活的充实、诗意和浪漫,让人不禁对断桥镇充满向往。
10.文章一开始就用大量的笔墨来写蚕婆婆的回忆,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11.小说中“蚕”有怎样的寓意?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枸杞子
毕飞宇
①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父亲进城以前采了两筐枸杞子,用它们换了那锃亮的东西。枸杞是我们家乡生长得最为疯狂的植物,每年盛夏河岸沟谷都要结满籽粒,红得炯炯有神。
②他穿过一丛又一丛枸杞走进我们家天井,大声说,我买了把手电!手电在黄昏时分发出清冽冰凉的光。母亲问,里头是什么?父亲说,是亮。
③第二天全村都晓得我们家有手电了。村里人都说,我们家买了把手电,一家子眼睛都像通了电。晚上我家天井里来了好多人。夏夜清清爽爽,每一颗星都干干净净。话题一直在手电的边缘。夜很晚了,狗都安静了,他们就是不走。母亲很不高兴,她的芭蕉扇在大腿上拍得噼啪起劲。后来母亲站到了皂荚树下,手里拿了那把锃亮的东西,说,你们睁大眼睛看够了!母亲用了很大的努力打开开关,一道雪亮的光柱横在了院子中间,皂荚树上的栖鸟被惊飞起,羽翼带着长长的哨声彗星一样划过,使人的听觉充满夜的宇宙感。
④母亲突然灭了手电,人们在黑暗里默不作声。
⑤勘探船在那个夏夜进村了。勘探队长戴了一顶黄色头盔。勘探队长说他们是来找石油的,而石油就在我们村的地底下,再不打上来油就要流到美国去了。当天他们就在村北打了个洞,一声轰隆,村子像筛糠。村里人立即把父亲叫过去,他们坚信,只有父亲能够阻止他们。父亲走到村北,站立在勘探队长的面前,双手抱在胸前说,不许打了!
⑥勘探队长说,你是谁?
⑦父亲说,再打你就麻烦了!他把这句话撂在村北,一个人回家玩手电去了。
⑧天黑之后来到我家天井的是勘探队队长。他称我的父亲为“亲爱的同志”,然后用科学论证石油和马路、汽车的关系,尤其强调了石油与电的关系。他说石油就是电,有了石油,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电在哪里呢?——电在油里;而油又在哪里?——油在地下。队长说,这是科学!父亲后来沉默了。母亲说,你听他瞎扯。父亲严肃无比地说,你不懂。母亲反驳说,你懂!父亲说,这是科学!
⑨父亲对勘探队长说,你们随便打。
⑩民间想象力的发达总与村落的未来有关。父亲的手电暂时给忽略了。人们一次又一次憧憬着电气化时代。父亲说,到那时水里也装上了电灯,人只要站在岸上就能看见王八、泥鳅与水婆子。父亲设想到那时,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人看鱼就像神仙在天上看我们那样。总之,科学似乎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
而勘探队的勘探进程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不慌不忙地打眼,贮药,点火,起爆。河里的鱼全给震昏了,浮出水面,在水面上漂了一层。勘探队长整日待在井口,面对地下蹿出来的黄泥汤忧心忡忡,有点担心找不出油来。“亲爱的同志们”不会接受没有结果的科学的。那些队员早就疲沓了,日午时分睡倒在树荫下,黄色头盔罩在脸上,打着鼾。
这时,父亲和乡亲们认真地趴在井口,看着黑洞洞的井底。有人提议说用手电照照。父亲回家拿来了手电,照下去,一无所有。有人问下面有科学吗?父亲默然不语,他把科学和希望全闭在了嘴里。太阳金灿灿的,枸杞子红艳艳的。
即将收割的稻子和正成长的棉花被踩得遍地狼藉。乡亲们站在自己的稼禾上心情无比矛盾。勘探队长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这里将是三十八层高楼,四周墙面全是玻璃,在电灯光的照耀下无限辉煌。尔后稼禾带给他们的心疼被满满的憧憬替代了,但高楼和灯光在他们贫瘠的想象中像雾一样难以成形。
父亲一次又一次与勘探队长讨论出石油的可能性。父亲每次都得到肯定回答。父亲一次又一次把那些话传给乡亲,乡亲们默然不语。父亲大声说,不出二十年,我保证大家住上高楼,用上电灯。大伙听了这样的话慢腾腾地散开去,他们的表情一片茫然。
不久,大哥偷走了父亲的手电到村东找蛐蛐,不小心把手电掉到河里,开着的手电竟然沉下河底去了。有人发现了河底的亮光,有两三丈那么长。许多人赶到了河边,河底的光呈墨绿色,麦芒一样四处开张。人们站在岸边手拉手,肩贴肩。人们以恐怖和绝望的心情看着河里的墨绿光慢慢地变暗,消亡。山羊胡子老爹说,动了地气了,动了地气了。一个晚上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千遍。
勘探队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又开始了爆炸。河里没有再死鱼。因为河里已经没有鱼可以死了。他们的动作失去了围观,只留下单调的爆炸和伤感的回音。
在暮色苍茫的时候,勘探队长脱掉了他的长裤,露出的双腿堆满伤疤,他一个劲地说话。他说,这个世上到处是疤,枯叶是风的疤,水泥路是地的疤,井是土的疤。说着这些疯话,他悄然走上船。
浓雾使大早充满瞌睡相。鸡打鸣,撂了两嗓子,就睡回头觉了。浓雾里头父亲做着梦,他梦见了石油光滑油亮的背脊在地底下蠕动的模样。
太阳出来了,雾散了,太阳使村庄愈加鲜嫩可爱。这时候有人说,勘探队!勘探队!人们走东窜西没有发现勘探队的人影子。只有无尽的枸杞子被浓雾乳得干干净净、水灵灵。大伙跟在父亲的身后来到河边,河边空着,满眼是细浪和飞鸟。浓雾退尽后的河面有一片“之”字形水迹,如一只大疤,拉到河面的拐角。这个疤一直烙在父亲的伤心处。父亲的眼里起了大雾,弥漫了父亲的那个夏季。
(有删改)
12.下列对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村民们聚集在“我”家,在时间已经很晚且母亲明显的暗示下仍不愿意离开“我”家,表现出村民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理。
B.对于勘探队,父亲态度转变的原因是父亲懂得了什么是科学,知道只有依靠科学,自己的村子才能发生变化。
C.手电筒在河底发出墨绿色光亮并逐渐变暗、消亡,村民们感到恐怖和绝望,甚至有人认为“动了地气”,表明了那个年代村民思想的落后。
D.小说结尾写“太阳出来了,雾散了”意蕴丰富,村庄勘探石油事件就此结束了,而父亲眼里却起了大雾,表现出父亲的迷茫。
13.下列对小说艺术特点的理解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展开叙述,详写了勘探队来到村中勘探石油的事件,首尾呼应,条理清晰。
B.小说环境描写富有深意,勘探中受破坏的村庄景象和村民们憧憬的生活环境形成对比,引人深思。
C.第⑧段中父亲和勘探队长、父亲和母亲的对话,语言简洁,多用短句,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D.小说中村民群像的塑造不可或缺,他们既暗示了小说的环境背景,也有力地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14.请结合文本,分析画线句“这个疤一直烙在父亲的伤心处”中“疤”的内涵。
15.关于小说的标题,有人认为“手电”好,有人认为“枸杞子”好,你认为哪个更好?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答案
1、C“情节始终展现父子之间的冲突”错误,根据“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行”可知,父子在报告开始前达成一致,并未发生冲突。
2.①曾经幸福圆满的家庭生活与如今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现状形成对比,使老马心中苦涩; ②与儿子难以沟通的痛苦压抑; ③异乡漂泊而无人理解的孤独与寂寞;④从马多延缓的回答和放低的声调中,感受到儿子对自己的理解后的感动
3.轻盈:①整体语言风格活泼:作者多处用揶揄诙谐的语气调侃马家父子,幽默风趣。 ②情节寻常:选材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凝重:①部分语言凝重,充满哲理性:作者在幽默调侃中经常插入凝练着思辨与智性的议论性话语,如“语言即人”“生活会让你付出全部,然后,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这些语句使小说充满理性的深度与厚重。②主题严肃(主题深刻):小说反映了代际沟通面临的实际困境以及对马多这样的年轻人丧失地缘根脉观念的忧思。
4、D“实质上暴露的是健全人利用先天优势来欺侮残疾人这一根本问题”错误。从“现在,张宗琪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高唯是冲着杜莉去的。但是,谁又会在意杜莉呢?高唯的背后是谁?是哪一个指使的呢?这么一想张宗琪的脖子上就起了鸡皮疙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自己怎么一直都蒙在鼓里?亏你还是个老江湖”可知,应该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并非健全人利用先天优势来欺侮残疾人,更不能解读为“实质”“根本问题”。
5.A“贯串全篇”错误,是通过沙复明的“大张旗鼓”与张宗琪的“内敛”“不含糊”对比,反衬张宗琪作为推拿中心“唯一的老板”的处事态度与方法。
6.(1)小说版效果:①以反问句式表达了对杜莉、金大姐的讽刺;②同时给每一个当事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更体现出高唯的工于心计。(2)电视剧版效果:①明确数目,并以“五倍”加以重复强调,突出了两人待遇的反差;②同时给观众以心理冲击。这体现了阅读书籍和观看电视不同的受众心理特征。
7.(示例一)这个人是金大姐。
①金大姐是张宗琪的人,但她对自己人过于偏心,分配羊肉不公,引发了激烈矛盾,影响了推拿中心的安定与稳定。
②张宗琪是真正的老板,“低调”“内敛”,遇大事却“从不含糊”。他要尽责维持推拿中心的“太平”,也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威望。
(示例二)这个人是高唯。
①高唯眼见不公平,却以“数羊肉”挑起和激化矛盾,行为粗暴,体现了性格的刻薄尖锐,影响了推拿中心的安定与稳定。②张宗琪是真正的老板,“低调”“内敛”,遇大事却“从不含糊”。他要尽责维持推拿中心的“太平”,也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威望。
8、D“社会发展变化太快和自己的文化水平”错误,从文中来看,蚕婆婆不适应现代生活主要与蚕婆婆对充实的乡村生活的怀念以及精神需求无处安放有关。
9.D“诗意与浪漫”错误,由第一段蚕婆婆追忆的断桥镇养蚕的日子可以看出,断桥镇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接地气的,是安然的,并非“诗意浪漫”。
10.(1)表现了蚕婆婆对充实的乡村生活的怀念,也反映了对现在生活的不适和孤寂;
(2)与实写二十九楼的生活相呼应,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也凸显了情节的合理性;
(3)表现了转型生活的无奈和困惑(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精神需求的错位)。
11.①断桥镇的蚕是蚕婆婆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②二十九楼上的蚕是蚕婆婆的陪伴和精神寄托;③作茧自缚的蚕象征蚕婆婆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和无法突破的精神困境。
12.B“父亲懂得了什么是科学”错,队长的解释并不能使父亲懂得什么是“科学”,父亲态度的转变只是因为父亲认为勘探队能给村庄带来变化。
13.C“父亲和勘探队长、父亲和母亲的对话……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错误,父亲和勘探队长、父亲和母亲的对话并没有体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14.①生态之“疤”:勘探队对村庄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令父亲痛心。②失望之“疤”:勘探队开采的失败让父亲对“新生活”的期待落空,令父亲失望。③愧疚之“疤”:村民们信任父亲并在父亲的描绘下一起憧憬着美好未来,但最终期待落空,令父亲内疚。
15.[示例一]以“手电”为题好。理由:①“手电”在文中象征着“新事物”与“科学”,反映出父亲及村民们对“新事物”改变生活现状的渴望。②“手电”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手电”与“勘探队”构成小说行文的两条线索:买回“手电”一村民好奇一“手电”掉河底;勘探队到来一村民憧憬一勘探队无果而终。③“手电”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父亲对新生活的追求、村民们的落后思想及对新事物的好奇均通过“手电”呈现。
[示例二]以“枸杞子”为题好。理由:①“枸杞子”作为文章线索,贯穿全文:勘探队来前(枸杞子承载希望)一勘探队来后(枸杞子与庄稼一样被忽略)一勘探队离开(枸杞子依然生机盎然)。②“枸杞子”作为当时村庄里常见的野生物种,在文中象征着简单、质朴的传统乡村生活。③文章结尾充满生机的“枸杞子”与被勘探队弄得“伤痕累累”的村庄形成鲜明对比,易引起读者对“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