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次要人物的作用(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次要人物的作用(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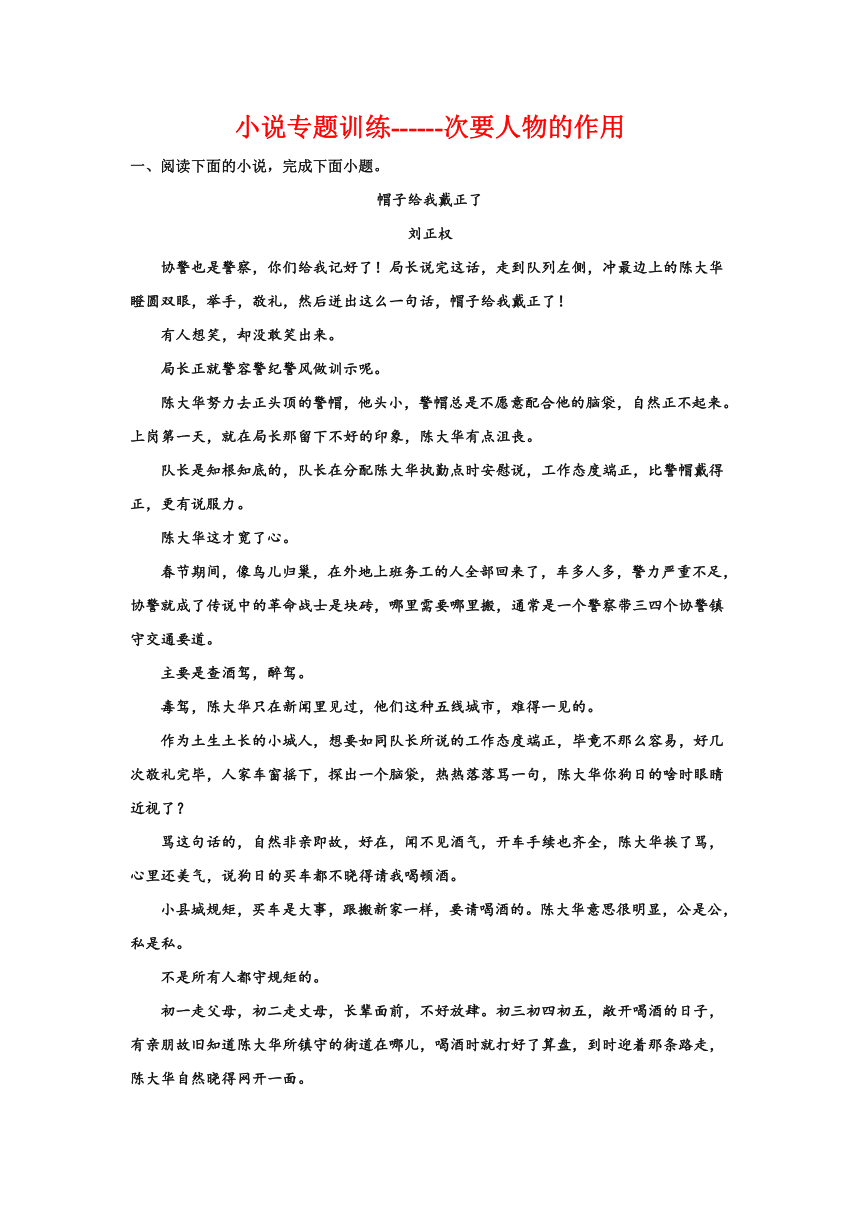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0.2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3-07 20:53:45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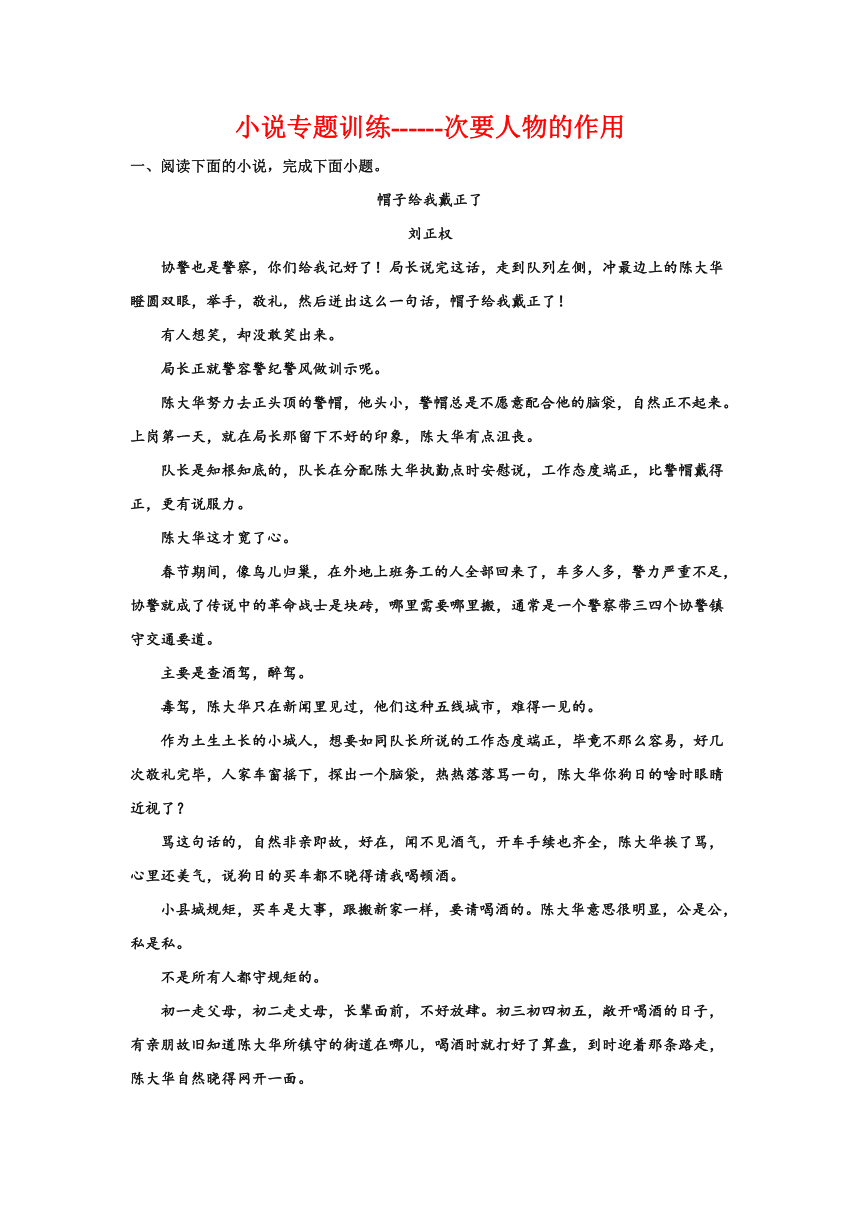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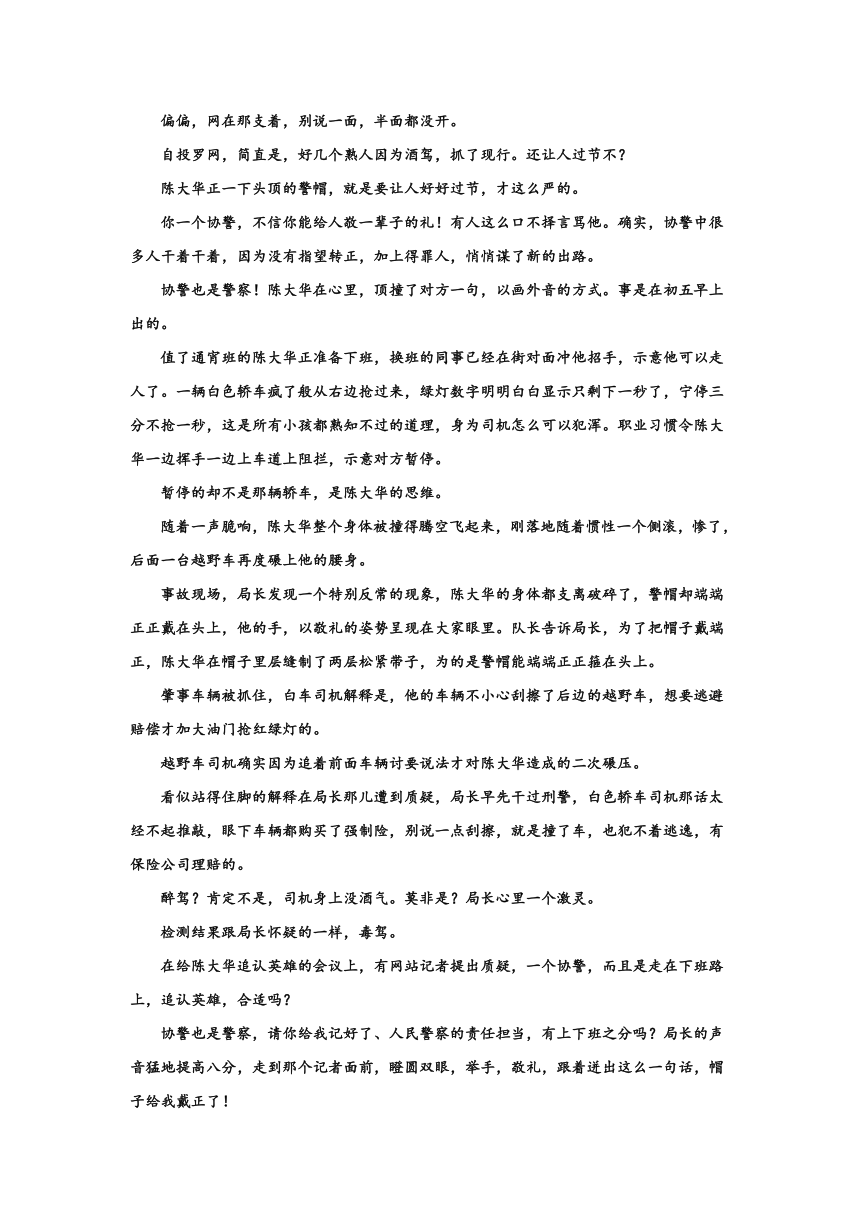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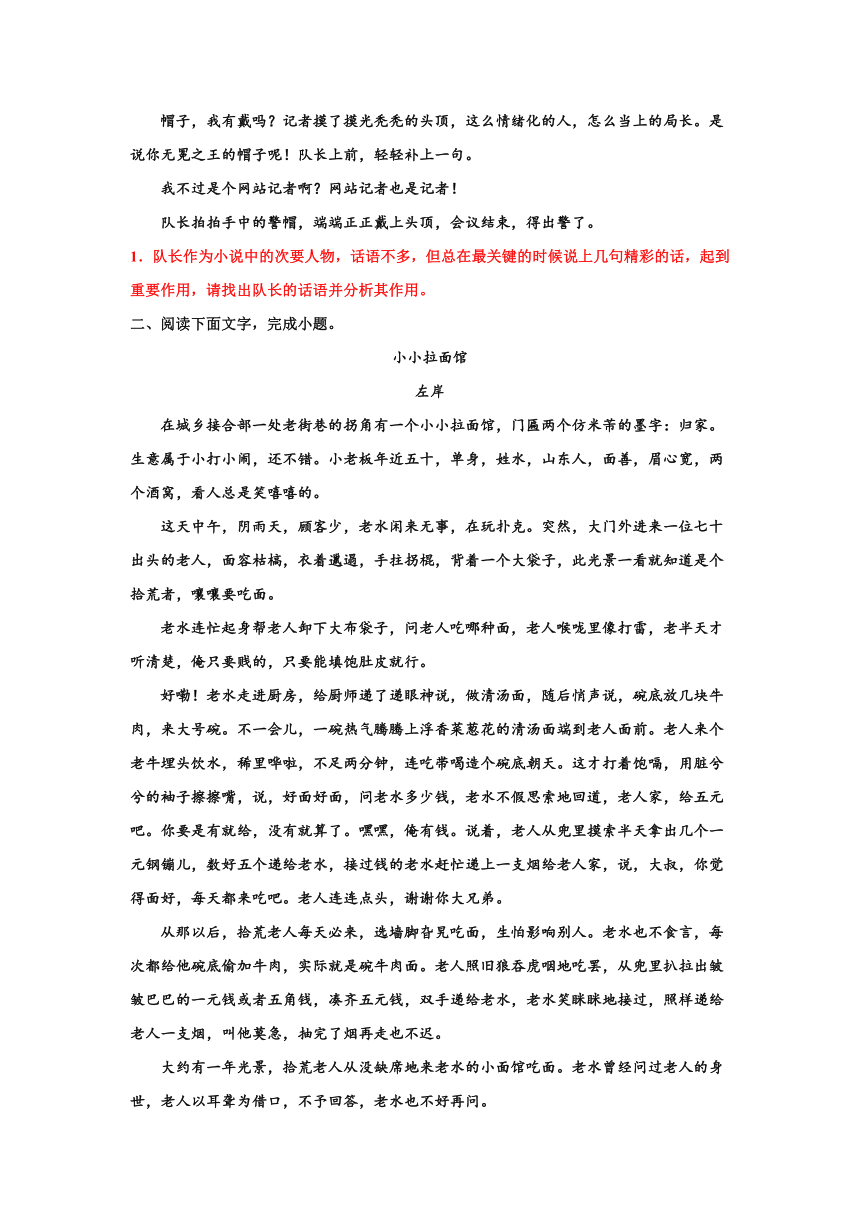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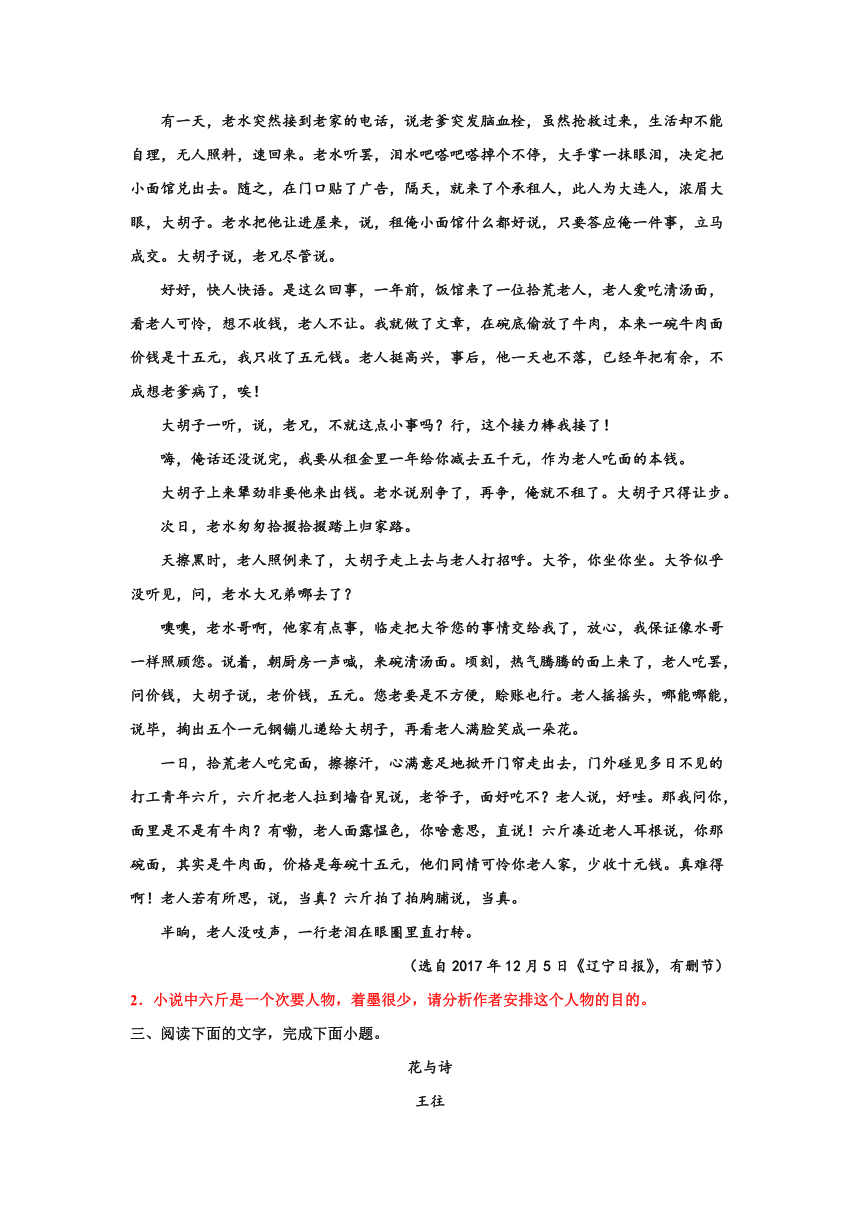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次要人物的作用
一、阅读下面的小说,完成下面小题。
帽子给我戴正了
刘正权
协警也是警察,你们给我记好了!局长说完这话,走到队列左侧,冲最边上的陈大华瞪圆双眼,举手,敬礼,然后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有人想笑,却没敢笑出来。
局长正就警容警纪警风做训示呢。
陈大华努力去正头顶的警帽,他头小,警帽总是不愿意配合他的脑袋,自然正不起来。上岗第一天,就在局长那留下不好的印象,陈大华有点沮丧。
队长是知根知底的,队长在分配陈大华执勤点时安慰说,工作态度端正,比警帽戴得正,更有说服力。
陈大华这才宽了心。
春节期间,像鸟儿归巢,在外地上班务工的人全部回来了,车多人多,警力严重不足,协警就成了传说中的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通常是一个警察带三四个协警镇守交通要道。
主要是查酒驾,醉驾。
毒驾,陈大华只在新闻里见过,他们这种五线城市,难得一见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城人,想要如同队长所说的工作态度端正,毕竟不那么容易,好几次敬礼完毕,人家车窗摇下,探出一个脑袋,热热落落骂一句,陈大华你狗日的啥时眼睛近视了?
骂这句话的,自然非亲即故,好在,闻不见酒气,开车手续也齐全,陈大华挨了骂,心里还美气,说狗日的买车都不晓得请我喝顿酒。
小县城规矩,买车是大事,跟搬新家一样,要请喝酒的。陈大华意思很明显,公是公,私是私。
不是所有人都守规矩的。
初一走父母,初二走丈母,长辈面前,不好放肆。初三初四初五,敞开喝酒的日子,有亲朋故旧知道陈大华所镇守的街道在哪儿,喝酒时就打好了算盘,到时迎着那条路走,陈大华自然晓得网开一面。
偏偏,网在那支着,别说一面,半面都没开。
自投罗网,简直是,好几个熟人因为酒驾,抓了现行。还让人过节不?
陈大华正一下头顶的警帽,就是要让人好好过节,才这么严的。
你一个协警,不信你能给人敬一辈子的礼!有人这么口不择言骂他。确实,协警中很多人干着干着,因为没有指望转正,加上得罪人,悄悄谋了新的出路。
协警也是警察!陈大华在心里,顶撞了对方一句,以画外音的方式。事是在初五早上出的。
值了通宵班的陈大华正准备下班,换班的同事已经在街对面冲他招手,示意他可以走人了。一辆白色轿车疯了般从右边抢过来,绿灯数字明明白白显示只剩下一秒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是所有小孩都熟知不过的道理,身为司机怎么可以犯浑。职业习惯令陈大华一边挥手一边上车道上阻拦,示意对方暂停。
暂停的却不是那辆轿车,是陈大华的思维。
随着一声脆响,陈大华整个身体被撞得腾空飞起来,刚落地随着惯性一个侧滚,惨了,后面一台越野车再度碾上他的腰身。
事故现场,局长发现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陈大华的身体都支离破碎了,警帽却端端正正戴在头上,他的手,以敬礼的姿势呈现在大家眼里。队长告诉局长,为了把帽子戴端正,陈大华在帽子里层缝制了两层松紧带子,为的是警帽能端端正正箍在头上。
肇事车辆被抓住,白车司机解释是,他的车辆不小心刮擦了后边的越野车,想要逃避赔偿才加大油门抢红绿灯的。
越野车司机确实因为追着前面车辆讨要说法才对陈大华造成的二次碾压。
看似站得住脚的解释在局长那儿遭到质疑,局长早先干过刑警,白色轿车司机那话太经不起推敲,眼下车辆都购买了强制险,别说一点刮擦,就是撞了车,也犯不着逃逸,有保险公司理赔的。
醉驾?肯定不是,司机身上没酒气。莫非是?局长心里一个激灵。
检测结果跟局长怀疑的一样,毒驾。
在给陈大华追认英雄的会议上,有网站记者提出质疑,一个协警,而且是走在下班路上,追认英雄,合适吗?
协警也是警察,请你给我记好了、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有上下班之分吗?局长的声音猛地提高八分,走到那个记者面前,瞪圆双眼,举手,敬礼,跟着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帽子,我有戴吗?记者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这么情绪化的人,怎么当上的局长。是说你无冕之王的帽子呢!队长上前,轻轻补上一句。
我不过是个网站记者啊?网站记者也是记者!
队长拍拍手中的警帽,端端正正戴上头顶,会议结束,得出警了。
1.队长作为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话语不多,但总在最关键的时候说上几句精彩的话,起到重要作用,请找出队长的话语并分析其作用。
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小小拉面馆
左岸
在城乡接合部一处老街巷的拐角有一个小小拉面馆,门匾两个仿米芾的墨字:归家。生意属于小打小闹,还不错。小老板年近五十,单身,姓水,山东人,面善,眉心宽,两个酒窝,看人总是笑嘻嘻的。
这天中午,阴雨天,顾客少,老水闲来无事,在玩扑克。突然,大门外进来一位七十出头的老人,面容枯槁,衣着邋遢,手拄拐棍,背着一个大袋子,此光景一看就知道是个拾荒者,嚷嚷要吃面。
老水连忙起身帮老人卸下大布袋子,问老人吃哪种面,老人喉咙里像打雷,老半天才听清楚,俺只要贱的,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行。
好嘞!老水走进厨房,给厨师递了递眼神说,做清汤面,随后悄声说,碗底放几块牛肉,来大号碗。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上浮香菜葱花的清汤面端到老人面前。老人来个老牛埋头饮水,稀里哗啦,不足两分钟,连吃带喝造个碗底朝天。这才打着饱嗝,用脏兮兮的袖子擦擦嘴,说,好面好面,问老水多少钱,老水不假思索地回道,老人家,给五元吧。你要是有就给,没有就算了。嘿嘿,俺有钱。说着,老人从兜里摸索半天拿出几个一元钢镚儿,数好五个递给老水,接过钱的老水赶忙递上一支烟给老人家,说,大叔,你觉得面好,每天都来吃吧。老人连连点头,谢谢你大兄弟。
从那以后,拾荒老人每天必来,选墙脚旮旯吃面,生怕影响别人。老水也不食言,每次都给他碗底偷加牛肉,实际就是碗牛肉面。老人照旧狼吞虎咽地吃罢,从兜里扒拉出皱皱巴巴的一元钱或者五角钱,凑齐五元钱,双手递给老水,老水笑眯眯地接过,照样递给老人一支烟,叫他莫急,抽完了烟再走也不迟。
大约有一年光景,拾荒老人从没缺席地来老水的小面馆吃面。老水曾经问过老人的身世,老人以耳聋为借口,不予回答,老水也不好再问。
有一天,老水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说老爹突发脑血栓,虽然抢救过来,生活却不能自理,无人照料,速回来。老水听罢,泪水吧嗒吧嗒掉个不停,大手掌一抹眼泪,决定把小面馆兑出去。随之,在门口贴了广告,隔天,就来了个承租人,此人为大连人,浓眉大眼,大胡子。老水把他让进屋来,说,租俺小面馆什么都好说,只要答应俺一件事,立马成交。大胡子说,老兄尽管说。
好好,快人快语。是这么回事,一年前,饭馆来了一位拾荒老人,老人爱吃清汤面,看老人可怜,想不收钱,老人不让。我就做了文章,在碗底偷放了牛肉,本来一碗牛肉面价钱是十五元,我只收了五元钱。老人挺高兴,事后,他一天也不落,已经年把有余,不成想老爹病了,唉!
大胡子一听,说,老兄,不就这点小事吗?行,这个接力棒我接了!
嗨,俺话还没说完,我要从租金里一年给你减去五千元,作为老人吃面的本钱。
大胡子上来犟劲非要他来出钱。老水说别争了,再争,俺就不租了。大胡子只得让步。
次日,老水匆匆拾掇拾掇踏上归家路。
天擦黑时,老人照例来了,大胡子走上去与老人打招呼。大爷,你坐你坐。大爷似乎没听见,问,老水大兄弟哪去了?
噢噢,老水哥啊,他家有点事,临走把大爷您的事情交给我了,放心,我保证像水哥一样照顾您。说着,朝厨房一声喊,来碗清汤面。顷刻,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老人吃罢,问价钱,大胡子说,老价钱,五元。您老要是不方便,赊账也行。老人摇摇头,哪能哪能,说毕,掏出五个一元钢镚儿递给大胡子,再看老人满脸笑成一朵花。
一日,拾荒老人吃完面,擦擦汗,心满意足地掀开门帘走出去,门外碰见多日不见的打工青年六斤,六斤把老人拉到墙旮旯说,老爷子,面好吃不?老人说,好哇。那我问你,面里是不是有牛肉?有嘞,老人面露愠色,你啥意思,直说!六斤凑近老人耳根说,你那碗面,其实是牛肉面,价格是每碗十五元,他们同情可怜你老人家,少收十元钱。真难得啊!老人若有所思,说,当真?六斤拍了拍胸脯说,当真。
半晌,老人没吱声,一行老泪在眼圈里直打转。
(选自2017年12月5日《辽宁日报》,有删节)
2.小说中六斤是一个次要人物,着墨很少,请分析作者安排这个人物的目的。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花与诗
王往
那一年三月,我们市的作协与石湖镇联办了一个笔会,就是冲着千亩桃园美景去的。春光大好,吃饱喝足,既可亲近乡土,又可借物咏怀,还可以营造一下和谐局面,谁不高兴呢?市内的、各县区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装了一辆大巴车,另有领导专车和个别自驾者,一路欢歌,奔向了石湖镇。
镇长也是个诗人,特别热心此项活动,在桃园里辟了一块地,搭了舞台。上午开完会后,下午就是歌咏会:作家们自娱自乐,以唱歌、朗诵为主。与会者都夸这个策划好,别出心裁。我没报表演节目,就在台下看着,好看的就多看一会儿,不好看的就随意走动走动。
当我走到舞台前方西北角时,看到一个小媳妇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站在舞台边。因为眼前总有人走动,她不时地左右侧着身子。小男孩想挣脱她的手,被她一用力又拉住了。小男孩说:“妈妈,我看不见。”她说:“妈妈抱你。”说着,就去抱孩子。孩子往后一退说:“我不要你抱,你抱不动我。”她笑笑:“那你自己玩,别瞎跑啊。”孩子笑着跑开了。
她的身材娇小,瓜子脸上有一双漂亮的凤眼。不过,脸色有些憔悴。别人都穿着夹克,她还穿着羽绒衣,和这桃花朵朵开的春色极不协调。
她看得很投入。有一个诗人朗诵得比较动情,她的眼里就溢出了泪水。
这时候,一个老妇走到她身边,半是抱怨半是心疼地说:“三蝶,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身体能出来吗?走,跟我回去,孩子呢?”这个叫三蝶的少妇指着人群里的孩子说:“在那儿呢!妈,你回去,我看一会儿再走。”老妇说:“你怎么不听话呢?快带孩子回去,别受了凉。”少妇有些着急,眉头拧了一下说:“我自己知道,一点儿风没有,哪会受凉?”
老妇很无奈地叹着气。
我挪了个地方,又站下了。这时候,老妇走到我身边,嘀咕了一句:“唉,好话也不听。”
我朝老妇看了一下,老妇似有好多苦恼急于说出,朝小媳妇的方向望了一眼对我说:
“那是我儿媳妇,她的病不轻呢。”
我说:“哦?”
老妇说:“生的是那种病,治不好了。”
我很吃惊,“那种病”是我们这里人对“癌症”的讳称。
老妇又说:“这孩子命苦,十几岁就出去打工了,得了这病时才25岁。就在去年,人家都说是在化工厂做工受了污染。”
我一阵难过,问老妇:“治了多长时间?”
老妇说:“去了几回医院,就没钱了,男人现在还在外头挣钱呢,她在家吃点中药,拖着。唉,也不晓得能拖多长时间,要是能拖下去就好了……有病了,脾气不好,不听话……”老妇说完,擦了一下眼睛,我不忍心看,低下头去。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把野花上了台,献给了正唱歌的一位作家,作家显然很感动,接过花后给小女孩鞠了一躬,观众们也很意外,想不到小女孩会有这么个机灵劲儿,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一位女诗人朗诵完了,那个小媳妇的儿子跑了上去,也献上了一束野花。主持人煽情地说:“这是最朴素的花,也是最有原生态气息的花,最美的花。鲜花送诗人,说明我们石湖镇是个有情有义的地方,说明我们石湖镇的孩子天生具有诗的品性,让我们为孩子为诗人为这春天的聚会鼓掌!”主持人一讲话,小男孩倒紧张了,又抹鼻涕又挠耳朵,不知怎么办好,突然拔腿就跑,跑到台边时跌了一跤,马上爬起来,又跑走了。台下笑成一片,再次鼓掌。
我看到小男孩跑到了他母亲身边。他大口喘着气,鼻尖冒着汗,小脸蛋涨得通红。他一到母亲身边,就紧紧依偎着母亲。他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发,朝他笑着。她的脸色好像不再那么憔悴了,呈现出淡淡的红晕。
歌咏会结束了,离晚宴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文友就往桃园深处走去,边走边聊。走了一段路,我看见了那个小媳妇和她的儿子。小男孩又采了一把野花,递给他的母亲。
小男孩说:“妈妈,你也会写诗,刚才人家说有花送诗人,我要送你花。”
小媳妇纠正儿子说:“是鲜花送诗人,不是有花送诗人,懂不懂?”
小男孩说:“嗯,懂了,是鲜花。”
小媳妇接过花说:“好看!宝贝,妈妈以后不写诗了,你送不送妈妈花?”
小男孩说:“你写嘛,写那么长那么长——”小男孩伸开胳膊比画着。
小媳妇笑了:“好的,妈妈写,以后,妈妈就在这桃园里写了,天天在这儿,年年在这儿,想妈妈时,就给妈妈送花,好不好?”
小男孩说:“好!”
小媳妇又笑了,想要亲儿子时,看见了我们,有些羞,拉起儿子的手说:“宝贝,走,回家去。”
小男孩挣脱小媳妇的手,在前面蹦蹦跳跳,小媳妇加快了步子。
很快,他们就走远了,隐入花海中了。
(有删改)
3.“我”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我”在小说中的作用。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秦腔(节选)
贾平凹
夏天义在庆玉家的稻田里撒化肥,瞎子二婶整个下午刮土豆皮,刮了半盆子,就煮了土豆做拌面疙瘩汤。哑巴在院子里劈柴火,柴火是两块大树根,哑巴抡了斧头劈了半天,才劈开了一块。二婶说:“你缓缓,挣出毛病了又害我呀!”哑巴不住手,抡一斧头吼一声,天摇地动。五个儿子曾经提议让老人每周轮流到各家吃饭,夏天义不同意,觉得儿子儿媳们都忙,不方便。更何况夏天义心性强,才不愿意每天拉着瞎眼老婆去上门吃饭,那算什么呀,要饭呀?!夏天义就说:“地我们是不种了,全分给你们,一年每家给我拿小麦五十斤,稻子一百斤,各类豆子杂粮五斤,蔬菜随便在谁家地里拔。而饭是我们做我们吃。”这样的日子实行了几年,夏天义没有一天不在儿子们的田地里劳作,但劳作并没落下多少好,几个儿媳们倒埋怨公公给这家干活多了,给那家干活少了。这些话夏天义没往心上搁,他劳作是他愿意,不在地里干活反觉得心慌,爱惦着父母早逝,如今孤独一人的哑巴,让哑巴常年就吃住在他那儿。
夏天义进门的时候,光着双腿,人累得腰都弯下了。他没有感觉腿肚子上还趴了一条马虎虫,哑巴看见了,就一个巴掌拍去,使夏天义冷不防受了一惊,低头看,腿上却出了血股子顺腿流,像是个蚯蚓。夏天义去锅里盛了一碗拌汤煮土豆给了二婶,自己也盛了一碗,却见碗里漂了一层白虫子,说:“面里生了虫,我重做些别的吃。”二婶说:“有虫啦?倒了多可惜。”夏天义也觉得把一锅饭倒了可惜,就把虫子一个一个往外捡。庆金进了门,二婶从脚步声中分辨出是大儿子,庆金说:“吃的啥饭,我也来碗。”去盛饭时就叫着这么多虫子怎个吃呀,一时心里酸酸的,端锅把饭倒了,自己给老人重做。
夏天义到伏牛梁小儿子瞎瞎的葱地边,一边浇尿,一边骂瞎瞎,看见紧挨着的那一块只有二亩大左右的地里长满了铁杆蒿、爬地龙和麻黄草,知道是俊奇的堂哥俊德家的。俊奇背着电工包从312国道上过,夏天义说:“多好的地荒着,这就不种啦?!你堂哥最近回来了没?”俊奇说:“过年回来了一次再没回来过。”夏天义说:“他就这样糟踏土地?!他不种了,你也不种了?”俊奇说:“他说过要我种,却要我每年给他二百斤粮食,还得缴土地税。再说我一天忙得不沾家,我家的地都种不过来哩。”夏天义说:“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来种!”
晚上,俊奇拨通了俊德的电话,俊德同意代耕,俊奇就代表堂兄和夏天义写了个协议:土地税由夏天义承担外,每年给俊德一百斤小麦和一百斤稻子。写了协议,俊奇娘说:“他二叔,你种了一辈子地,老了老了,还种这二亩地干啥呀,你还缺吃少穿的?”夏天义说:“地不能荒着么,好好的一碗饭,倒在地上了,能不心疼?我还不至于太老吧?!”
俊奇送夏天义回。天上满是星星,一颗一颗都在挤眉弄眼。夏天义的情绪特别好,顺口唱了:“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巷道拐过弯是段斜坡,夏天义明明看着两个石阶,要一步跨上去,但脚步没踩住,咚地窝在了地上。俊奇忙去扶他,他不让扶,也不让再送。
庆金在家里和四个弟弟、弟媳们正商量,听见四叔夏天智在院门外喊:“养儿防老,养的你们干啥?你爹给你们各家帮着种地,我都有些看不下去,现在竟然让你爹去种别人的地?!”庆金就解释,说这事他们事先都不知道,正商量咋办呀。
庆金回到屋里。老二庆玉说:“四叔倚老卖老!”四媳竹青说:“话不敢这样说,四叔还不是为了咱?咱想一想,为啥爹要种人家的地?”庆堂说:“是不是咱给爹的粮食不够吃?”老三庆满说:“是你一到饭辰了就唆着自家的娃去么?”瞎瞎看着老三说:“我儿子小,能吃他爷多少饭,爹把一个外人——哑巴常年放家,他饭量大,当然不够吃了。”庆满说:“你咋不看哑巴也给老人干活?”声音都高起来,庆金说:“吵啥呀?!咱把爹的地分着种了,是想让爹歇着,可爹身子骨还硬朗,这些年还不是看谁家活忙就帮谁干?爹一定在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弄一块地种。”庆玉庆满说:“是这个想法。爹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现在不当了,他得有个事干呀!就让他去种吧。”
(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略有删改)
4.小说设置了“哑巴”这一次要人物,作者这样安排有什么用意?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答案
(1)第一次“工作态度端正,比警帽戴得正,更有说服力”,作用:安慰陈大华,侧面表现了陈大华的训练扎实,工作认真,更推动了陈大华认真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为后面陈大华的突出表现做铺垫。(2)第二次“队长告诉局长,为了把帽子戴端正,陈大华在帽子里层缝制了两层松紧带子,为的是警帽能端端正正箍在头上。”补充说明,表现了陈大华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的平凡英雄形象。(3)第三次“是说你无冕之王的帽子呢!”“网站记者也是记者!”升华主旨,突出强调,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要端正态度,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
①从情节安排上,小说最后通过六斤讲出事情的真相,使小说情节更加完整。②从人物塑造上,老人知道真相以后流下了眼泪,说明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同时更突出了老水尊老敬老,淳朴善良,热心助人的形象。③从小说的主题上,深化了主题,通过老水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一个热情助人,一个充满了感激,符合人们对此事的期待,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①“我”的观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参加笔会没报节目,随意走动走动,这才看见了小媳妇,遇到了她婆婆,有了后文一系列的情节,②文章以“我”为叙述视角,便于叙述故事,增强了故事的真情实感。③通过写“我”的感受,人物形象(如纯朴真诚的小媳妇)被刻画得更加立体丰满。
4.①衬托人物品性。夏天义夫妇收留孤儿哑巴,“爱惦着父母早逝孤独一人的哑巴,让哑巴常年就吃住在他那儿”,表现老一代农民的淳朴善良。②与夏家的孩子们构成对比,暗含褒贬态度。哑巴作为残疾人,帮夏天义家劈柴,以及拍掉夏天义腿上一条马虎虫等富有人情、人性美的温馨场面的描写,与夏家的儿子媳妇们的计较、自私构成对比,体现作者的褒贬态度。③丰富文章内容。哑巴在夏家的生活,哑巴被收留在夏家引起孩子们的争论等,丰富了文章的内容。
一、阅读下面的小说,完成下面小题。
帽子给我戴正了
刘正权
协警也是警察,你们给我记好了!局长说完这话,走到队列左侧,冲最边上的陈大华瞪圆双眼,举手,敬礼,然后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有人想笑,却没敢笑出来。
局长正就警容警纪警风做训示呢。
陈大华努力去正头顶的警帽,他头小,警帽总是不愿意配合他的脑袋,自然正不起来。上岗第一天,就在局长那留下不好的印象,陈大华有点沮丧。
队长是知根知底的,队长在分配陈大华执勤点时安慰说,工作态度端正,比警帽戴得正,更有说服力。
陈大华这才宽了心。
春节期间,像鸟儿归巢,在外地上班务工的人全部回来了,车多人多,警力严重不足,协警就成了传说中的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通常是一个警察带三四个协警镇守交通要道。
主要是查酒驾,醉驾。
毒驾,陈大华只在新闻里见过,他们这种五线城市,难得一见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城人,想要如同队长所说的工作态度端正,毕竟不那么容易,好几次敬礼完毕,人家车窗摇下,探出一个脑袋,热热落落骂一句,陈大华你狗日的啥时眼睛近视了?
骂这句话的,自然非亲即故,好在,闻不见酒气,开车手续也齐全,陈大华挨了骂,心里还美气,说狗日的买车都不晓得请我喝顿酒。
小县城规矩,买车是大事,跟搬新家一样,要请喝酒的。陈大华意思很明显,公是公,私是私。
不是所有人都守规矩的。
初一走父母,初二走丈母,长辈面前,不好放肆。初三初四初五,敞开喝酒的日子,有亲朋故旧知道陈大华所镇守的街道在哪儿,喝酒时就打好了算盘,到时迎着那条路走,陈大华自然晓得网开一面。
偏偏,网在那支着,别说一面,半面都没开。
自投罗网,简直是,好几个熟人因为酒驾,抓了现行。还让人过节不?
陈大华正一下头顶的警帽,就是要让人好好过节,才这么严的。
你一个协警,不信你能给人敬一辈子的礼!有人这么口不择言骂他。确实,协警中很多人干着干着,因为没有指望转正,加上得罪人,悄悄谋了新的出路。
协警也是警察!陈大华在心里,顶撞了对方一句,以画外音的方式。事是在初五早上出的。
值了通宵班的陈大华正准备下班,换班的同事已经在街对面冲他招手,示意他可以走人了。一辆白色轿车疯了般从右边抢过来,绿灯数字明明白白显示只剩下一秒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是所有小孩都熟知不过的道理,身为司机怎么可以犯浑。职业习惯令陈大华一边挥手一边上车道上阻拦,示意对方暂停。
暂停的却不是那辆轿车,是陈大华的思维。
随着一声脆响,陈大华整个身体被撞得腾空飞起来,刚落地随着惯性一个侧滚,惨了,后面一台越野车再度碾上他的腰身。
事故现场,局长发现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陈大华的身体都支离破碎了,警帽却端端正正戴在头上,他的手,以敬礼的姿势呈现在大家眼里。队长告诉局长,为了把帽子戴端正,陈大华在帽子里层缝制了两层松紧带子,为的是警帽能端端正正箍在头上。
肇事车辆被抓住,白车司机解释是,他的车辆不小心刮擦了后边的越野车,想要逃避赔偿才加大油门抢红绿灯的。
越野车司机确实因为追着前面车辆讨要说法才对陈大华造成的二次碾压。
看似站得住脚的解释在局长那儿遭到质疑,局长早先干过刑警,白色轿车司机那话太经不起推敲,眼下车辆都购买了强制险,别说一点刮擦,就是撞了车,也犯不着逃逸,有保险公司理赔的。
醉驾?肯定不是,司机身上没酒气。莫非是?局长心里一个激灵。
检测结果跟局长怀疑的一样,毒驾。
在给陈大华追认英雄的会议上,有网站记者提出质疑,一个协警,而且是走在下班路上,追认英雄,合适吗?
协警也是警察,请你给我记好了、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有上下班之分吗?局长的声音猛地提高八分,走到那个记者面前,瞪圆双眼,举手,敬礼,跟着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帽子,我有戴吗?记者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这么情绪化的人,怎么当上的局长。是说你无冕之王的帽子呢!队长上前,轻轻补上一句。
我不过是个网站记者啊?网站记者也是记者!
队长拍拍手中的警帽,端端正正戴上头顶,会议结束,得出警了。
1.队长作为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话语不多,但总在最关键的时候说上几句精彩的话,起到重要作用,请找出队长的话语并分析其作用。
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小小拉面馆
左岸
在城乡接合部一处老街巷的拐角有一个小小拉面馆,门匾两个仿米芾的墨字:归家。生意属于小打小闹,还不错。小老板年近五十,单身,姓水,山东人,面善,眉心宽,两个酒窝,看人总是笑嘻嘻的。
这天中午,阴雨天,顾客少,老水闲来无事,在玩扑克。突然,大门外进来一位七十出头的老人,面容枯槁,衣着邋遢,手拄拐棍,背着一个大袋子,此光景一看就知道是个拾荒者,嚷嚷要吃面。
老水连忙起身帮老人卸下大布袋子,问老人吃哪种面,老人喉咙里像打雷,老半天才听清楚,俺只要贱的,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行。
好嘞!老水走进厨房,给厨师递了递眼神说,做清汤面,随后悄声说,碗底放几块牛肉,来大号碗。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上浮香菜葱花的清汤面端到老人面前。老人来个老牛埋头饮水,稀里哗啦,不足两分钟,连吃带喝造个碗底朝天。这才打着饱嗝,用脏兮兮的袖子擦擦嘴,说,好面好面,问老水多少钱,老水不假思索地回道,老人家,给五元吧。你要是有就给,没有就算了。嘿嘿,俺有钱。说着,老人从兜里摸索半天拿出几个一元钢镚儿,数好五个递给老水,接过钱的老水赶忙递上一支烟给老人家,说,大叔,你觉得面好,每天都来吃吧。老人连连点头,谢谢你大兄弟。
从那以后,拾荒老人每天必来,选墙脚旮旯吃面,生怕影响别人。老水也不食言,每次都给他碗底偷加牛肉,实际就是碗牛肉面。老人照旧狼吞虎咽地吃罢,从兜里扒拉出皱皱巴巴的一元钱或者五角钱,凑齐五元钱,双手递给老水,老水笑眯眯地接过,照样递给老人一支烟,叫他莫急,抽完了烟再走也不迟。
大约有一年光景,拾荒老人从没缺席地来老水的小面馆吃面。老水曾经问过老人的身世,老人以耳聋为借口,不予回答,老水也不好再问。
有一天,老水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说老爹突发脑血栓,虽然抢救过来,生活却不能自理,无人照料,速回来。老水听罢,泪水吧嗒吧嗒掉个不停,大手掌一抹眼泪,决定把小面馆兑出去。随之,在门口贴了广告,隔天,就来了个承租人,此人为大连人,浓眉大眼,大胡子。老水把他让进屋来,说,租俺小面馆什么都好说,只要答应俺一件事,立马成交。大胡子说,老兄尽管说。
好好,快人快语。是这么回事,一年前,饭馆来了一位拾荒老人,老人爱吃清汤面,看老人可怜,想不收钱,老人不让。我就做了文章,在碗底偷放了牛肉,本来一碗牛肉面价钱是十五元,我只收了五元钱。老人挺高兴,事后,他一天也不落,已经年把有余,不成想老爹病了,唉!
大胡子一听,说,老兄,不就这点小事吗?行,这个接力棒我接了!
嗨,俺话还没说完,我要从租金里一年给你减去五千元,作为老人吃面的本钱。
大胡子上来犟劲非要他来出钱。老水说别争了,再争,俺就不租了。大胡子只得让步。
次日,老水匆匆拾掇拾掇踏上归家路。
天擦黑时,老人照例来了,大胡子走上去与老人打招呼。大爷,你坐你坐。大爷似乎没听见,问,老水大兄弟哪去了?
噢噢,老水哥啊,他家有点事,临走把大爷您的事情交给我了,放心,我保证像水哥一样照顾您。说着,朝厨房一声喊,来碗清汤面。顷刻,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了,老人吃罢,问价钱,大胡子说,老价钱,五元。您老要是不方便,赊账也行。老人摇摇头,哪能哪能,说毕,掏出五个一元钢镚儿递给大胡子,再看老人满脸笑成一朵花。
一日,拾荒老人吃完面,擦擦汗,心满意足地掀开门帘走出去,门外碰见多日不见的打工青年六斤,六斤把老人拉到墙旮旯说,老爷子,面好吃不?老人说,好哇。那我问你,面里是不是有牛肉?有嘞,老人面露愠色,你啥意思,直说!六斤凑近老人耳根说,你那碗面,其实是牛肉面,价格是每碗十五元,他们同情可怜你老人家,少收十元钱。真难得啊!老人若有所思,说,当真?六斤拍了拍胸脯说,当真。
半晌,老人没吱声,一行老泪在眼圈里直打转。
(选自2017年12月5日《辽宁日报》,有删节)
2.小说中六斤是一个次要人物,着墨很少,请分析作者安排这个人物的目的。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花与诗
王往
那一年三月,我们市的作协与石湖镇联办了一个笔会,就是冲着千亩桃园美景去的。春光大好,吃饱喝足,既可亲近乡土,又可借物咏怀,还可以营造一下和谐局面,谁不高兴呢?市内的、各县区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装了一辆大巴车,另有领导专车和个别自驾者,一路欢歌,奔向了石湖镇。
镇长也是个诗人,特别热心此项活动,在桃园里辟了一块地,搭了舞台。上午开完会后,下午就是歌咏会:作家们自娱自乐,以唱歌、朗诵为主。与会者都夸这个策划好,别出心裁。我没报表演节目,就在台下看着,好看的就多看一会儿,不好看的就随意走动走动。
当我走到舞台前方西北角时,看到一个小媳妇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站在舞台边。因为眼前总有人走动,她不时地左右侧着身子。小男孩想挣脱她的手,被她一用力又拉住了。小男孩说:“妈妈,我看不见。”她说:“妈妈抱你。”说着,就去抱孩子。孩子往后一退说:“我不要你抱,你抱不动我。”她笑笑:“那你自己玩,别瞎跑啊。”孩子笑着跑开了。
她的身材娇小,瓜子脸上有一双漂亮的凤眼。不过,脸色有些憔悴。别人都穿着夹克,她还穿着羽绒衣,和这桃花朵朵开的春色极不协调。
她看得很投入。有一个诗人朗诵得比较动情,她的眼里就溢出了泪水。
这时候,一个老妇走到她身边,半是抱怨半是心疼地说:“三蝶,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身体能出来吗?走,跟我回去,孩子呢?”这个叫三蝶的少妇指着人群里的孩子说:“在那儿呢!妈,你回去,我看一会儿再走。”老妇说:“你怎么不听话呢?快带孩子回去,别受了凉。”少妇有些着急,眉头拧了一下说:“我自己知道,一点儿风没有,哪会受凉?”
老妇很无奈地叹着气。
我挪了个地方,又站下了。这时候,老妇走到我身边,嘀咕了一句:“唉,好话也不听。”
我朝老妇看了一下,老妇似有好多苦恼急于说出,朝小媳妇的方向望了一眼对我说:
“那是我儿媳妇,她的病不轻呢。”
我说:“哦?”
老妇说:“生的是那种病,治不好了。”
我很吃惊,“那种病”是我们这里人对“癌症”的讳称。
老妇又说:“这孩子命苦,十几岁就出去打工了,得了这病时才25岁。就在去年,人家都说是在化工厂做工受了污染。”
我一阵难过,问老妇:“治了多长时间?”
老妇说:“去了几回医院,就没钱了,男人现在还在外头挣钱呢,她在家吃点中药,拖着。唉,也不晓得能拖多长时间,要是能拖下去就好了……有病了,脾气不好,不听话……”老妇说完,擦了一下眼睛,我不忍心看,低下头去。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把野花上了台,献给了正唱歌的一位作家,作家显然很感动,接过花后给小女孩鞠了一躬,观众们也很意外,想不到小女孩会有这么个机灵劲儿,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一位女诗人朗诵完了,那个小媳妇的儿子跑了上去,也献上了一束野花。主持人煽情地说:“这是最朴素的花,也是最有原生态气息的花,最美的花。鲜花送诗人,说明我们石湖镇是个有情有义的地方,说明我们石湖镇的孩子天生具有诗的品性,让我们为孩子为诗人为这春天的聚会鼓掌!”主持人一讲话,小男孩倒紧张了,又抹鼻涕又挠耳朵,不知怎么办好,突然拔腿就跑,跑到台边时跌了一跤,马上爬起来,又跑走了。台下笑成一片,再次鼓掌。
我看到小男孩跑到了他母亲身边。他大口喘着气,鼻尖冒着汗,小脸蛋涨得通红。他一到母亲身边,就紧紧依偎着母亲。他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发,朝他笑着。她的脸色好像不再那么憔悴了,呈现出淡淡的红晕。
歌咏会结束了,离晚宴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文友就往桃园深处走去,边走边聊。走了一段路,我看见了那个小媳妇和她的儿子。小男孩又采了一把野花,递给他的母亲。
小男孩说:“妈妈,你也会写诗,刚才人家说有花送诗人,我要送你花。”
小媳妇纠正儿子说:“是鲜花送诗人,不是有花送诗人,懂不懂?”
小男孩说:“嗯,懂了,是鲜花。”
小媳妇接过花说:“好看!宝贝,妈妈以后不写诗了,你送不送妈妈花?”
小男孩说:“你写嘛,写那么长那么长——”小男孩伸开胳膊比画着。
小媳妇笑了:“好的,妈妈写,以后,妈妈就在这桃园里写了,天天在这儿,年年在这儿,想妈妈时,就给妈妈送花,好不好?”
小男孩说:“好!”
小媳妇又笑了,想要亲儿子时,看见了我们,有些羞,拉起儿子的手说:“宝贝,走,回家去。”
小男孩挣脱小媳妇的手,在前面蹦蹦跳跳,小媳妇加快了步子。
很快,他们就走远了,隐入花海中了。
(有删改)
3.“我”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我”在小说中的作用。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秦腔(节选)
贾平凹
夏天义在庆玉家的稻田里撒化肥,瞎子二婶整个下午刮土豆皮,刮了半盆子,就煮了土豆做拌面疙瘩汤。哑巴在院子里劈柴火,柴火是两块大树根,哑巴抡了斧头劈了半天,才劈开了一块。二婶说:“你缓缓,挣出毛病了又害我呀!”哑巴不住手,抡一斧头吼一声,天摇地动。五个儿子曾经提议让老人每周轮流到各家吃饭,夏天义不同意,觉得儿子儿媳们都忙,不方便。更何况夏天义心性强,才不愿意每天拉着瞎眼老婆去上门吃饭,那算什么呀,要饭呀?!夏天义就说:“地我们是不种了,全分给你们,一年每家给我拿小麦五十斤,稻子一百斤,各类豆子杂粮五斤,蔬菜随便在谁家地里拔。而饭是我们做我们吃。”这样的日子实行了几年,夏天义没有一天不在儿子们的田地里劳作,但劳作并没落下多少好,几个儿媳们倒埋怨公公给这家干活多了,给那家干活少了。这些话夏天义没往心上搁,他劳作是他愿意,不在地里干活反觉得心慌,爱惦着父母早逝,如今孤独一人的哑巴,让哑巴常年就吃住在他那儿。
夏天义进门的时候,光着双腿,人累得腰都弯下了。他没有感觉腿肚子上还趴了一条马虎虫,哑巴看见了,就一个巴掌拍去,使夏天义冷不防受了一惊,低头看,腿上却出了血股子顺腿流,像是个蚯蚓。夏天义去锅里盛了一碗拌汤煮土豆给了二婶,自己也盛了一碗,却见碗里漂了一层白虫子,说:“面里生了虫,我重做些别的吃。”二婶说:“有虫啦?倒了多可惜。”夏天义也觉得把一锅饭倒了可惜,就把虫子一个一个往外捡。庆金进了门,二婶从脚步声中分辨出是大儿子,庆金说:“吃的啥饭,我也来碗。”去盛饭时就叫着这么多虫子怎个吃呀,一时心里酸酸的,端锅把饭倒了,自己给老人重做。
夏天义到伏牛梁小儿子瞎瞎的葱地边,一边浇尿,一边骂瞎瞎,看见紧挨着的那一块只有二亩大左右的地里长满了铁杆蒿、爬地龙和麻黄草,知道是俊奇的堂哥俊德家的。俊奇背着电工包从312国道上过,夏天义说:“多好的地荒着,这就不种啦?!你堂哥最近回来了没?”俊奇说:“过年回来了一次再没回来过。”夏天义说:“他就这样糟踏土地?!他不种了,你也不种了?”俊奇说:“他说过要我种,却要我每年给他二百斤粮食,还得缴土地税。再说我一天忙得不沾家,我家的地都种不过来哩。”夏天义说:“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来种!”
晚上,俊奇拨通了俊德的电话,俊德同意代耕,俊奇就代表堂兄和夏天义写了个协议:土地税由夏天义承担外,每年给俊德一百斤小麦和一百斤稻子。写了协议,俊奇娘说:“他二叔,你种了一辈子地,老了老了,还种这二亩地干啥呀,你还缺吃少穿的?”夏天义说:“地不能荒着么,好好的一碗饭,倒在地上了,能不心疼?我还不至于太老吧?!”
俊奇送夏天义回。天上满是星星,一颗一颗都在挤眉弄眼。夏天义的情绪特别好,顺口唱了:“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我王宝钏。”巷道拐过弯是段斜坡,夏天义明明看着两个石阶,要一步跨上去,但脚步没踩住,咚地窝在了地上。俊奇忙去扶他,他不让扶,也不让再送。
庆金在家里和四个弟弟、弟媳们正商量,听见四叔夏天智在院门外喊:“养儿防老,养的你们干啥?你爹给你们各家帮着种地,我都有些看不下去,现在竟然让你爹去种别人的地?!”庆金就解释,说这事他们事先都不知道,正商量咋办呀。
庆金回到屋里。老二庆玉说:“四叔倚老卖老!”四媳竹青说:“话不敢这样说,四叔还不是为了咱?咱想一想,为啥爹要种人家的地?”庆堂说:“是不是咱给爹的粮食不够吃?”老三庆满说:“是你一到饭辰了就唆着自家的娃去么?”瞎瞎看着老三说:“我儿子小,能吃他爷多少饭,爹把一个外人——哑巴常年放家,他饭量大,当然不够吃了。”庆满说:“你咋不看哑巴也给老人干活?”声音都高起来,庆金说:“吵啥呀?!咱把爹的地分着种了,是想让爹歇着,可爹身子骨还硬朗,这些年还不是看谁家活忙就帮谁干?爹一定在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弄一块地种。”庆玉庆满说:“是这个想法。爹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现在不当了,他得有个事干呀!就让他去种吧。”
(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略有删改)
4.小说设置了“哑巴”这一次要人物,作者这样安排有什么用意?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答案
(1)第一次“工作态度端正,比警帽戴得正,更有说服力”,作用:安慰陈大华,侧面表现了陈大华的训练扎实,工作认真,更推动了陈大华认真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为后面陈大华的突出表现做铺垫。(2)第二次“队长告诉局长,为了把帽子戴端正,陈大华在帽子里层缝制了两层松紧带子,为的是警帽能端端正正箍在头上。”补充说明,表现了陈大华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的平凡英雄形象。(3)第三次“是说你无冕之王的帽子呢!”“网站记者也是记者!”升华主旨,突出强调,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要端正态度,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
①从情节安排上,小说最后通过六斤讲出事情的真相,使小说情节更加完整。②从人物塑造上,老人知道真相以后流下了眼泪,说明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同时更突出了老水尊老敬老,淳朴善良,热心助人的形象。③从小说的主题上,深化了主题,通过老水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一个热情助人,一个充满了感激,符合人们对此事的期待,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①“我”的观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参加笔会没报节目,随意走动走动,这才看见了小媳妇,遇到了她婆婆,有了后文一系列的情节,②文章以“我”为叙述视角,便于叙述故事,增强了故事的真情实感。③通过写“我”的感受,人物形象(如纯朴真诚的小媳妇)被刻画得更加立体丰满。
4.①衬托人物品性。夏天义夫妇收留孤儿哑巴,“爱惦着父母早逝孤独一人的哑巴,让哑巴常年就吃住在他那儿”,表现老一代农民的淳朴善良。②与夏家的孩子们构成对比,暗含褒贬态度。哑巴作为残疾人,帮夏天义家劈柴,以及拍掉夏天义腿上一条马虎虫等富有人情、人性美的温馨场面的描写,与夏家的儿子媳妇们的计较、自私构成对比,体现作者的褒贬态度。③丰富文章内容。哑巴在夏家的生活,哑巴被收留在夏家引起孩子们的争论等,丰富了文章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