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比较标题的优劣(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比较标题的优劣(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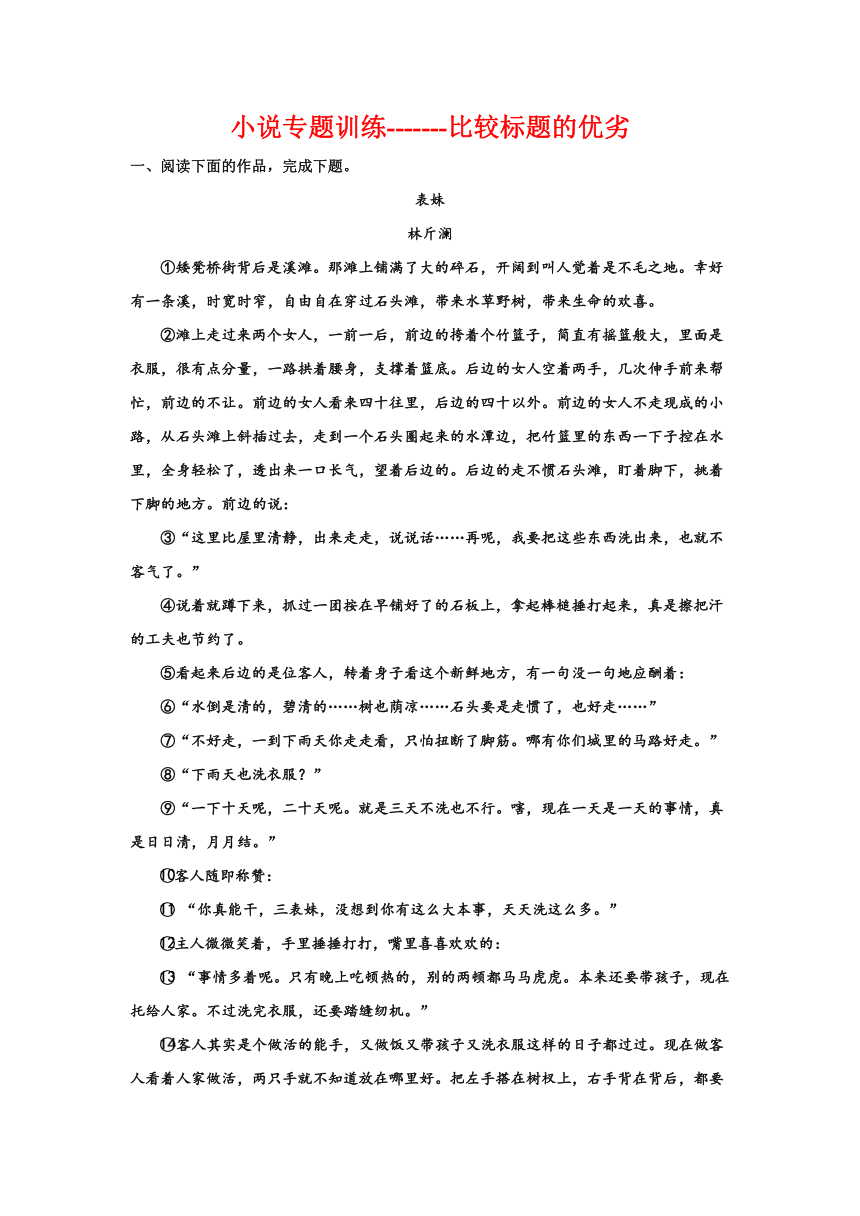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93.6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3-11 20:33:34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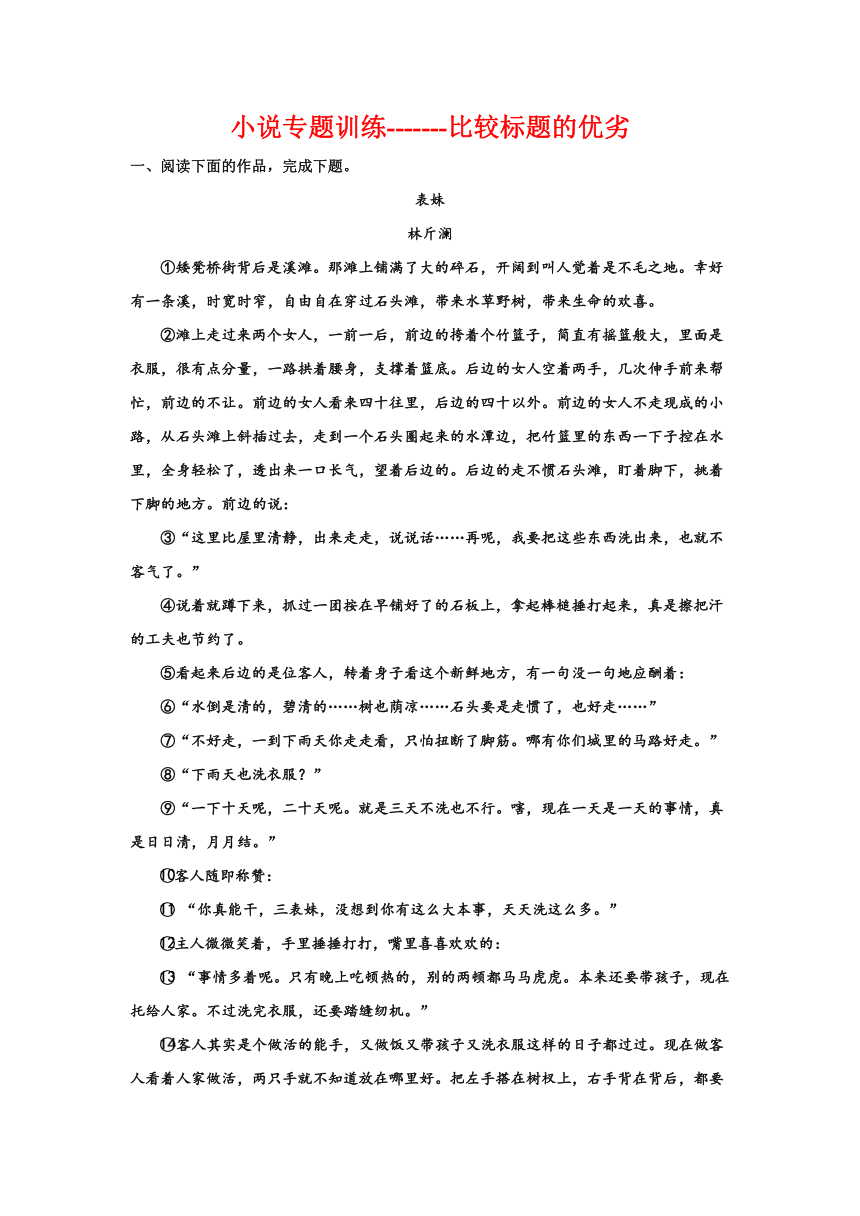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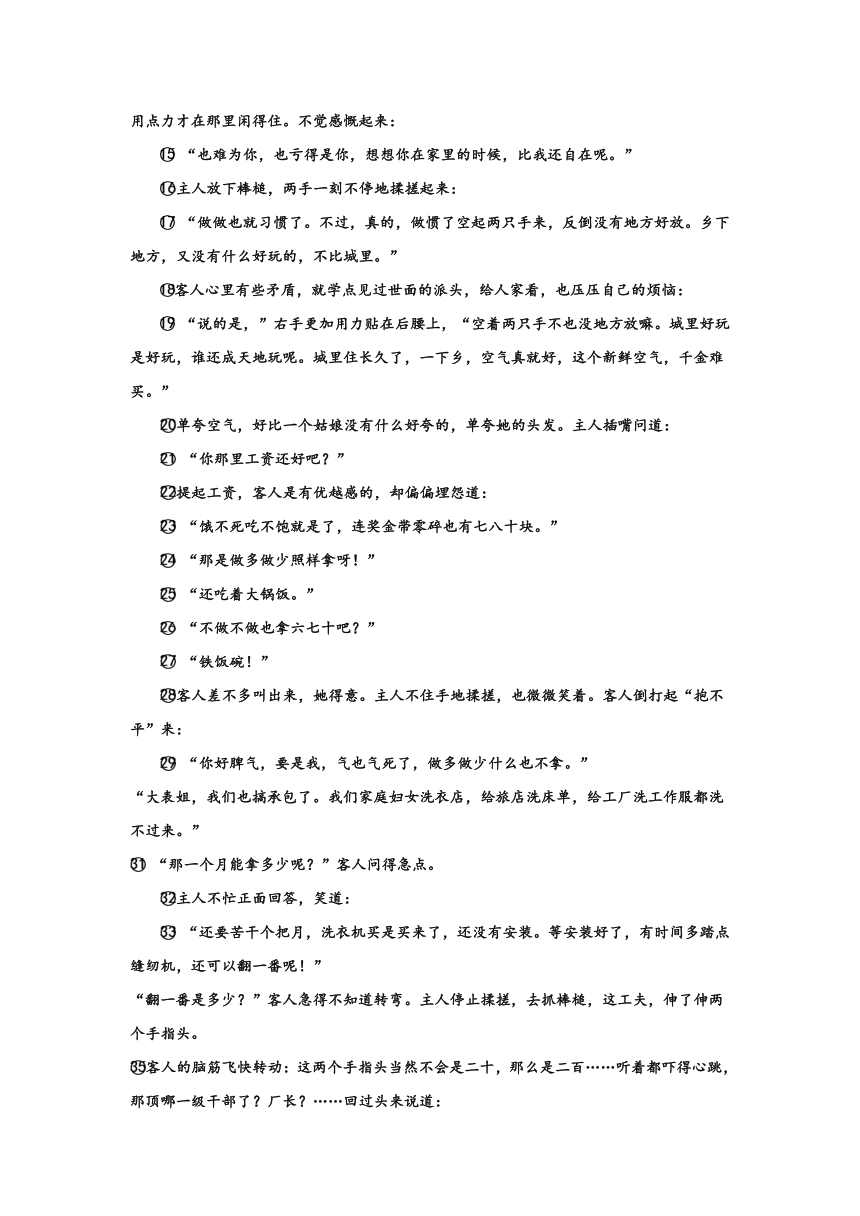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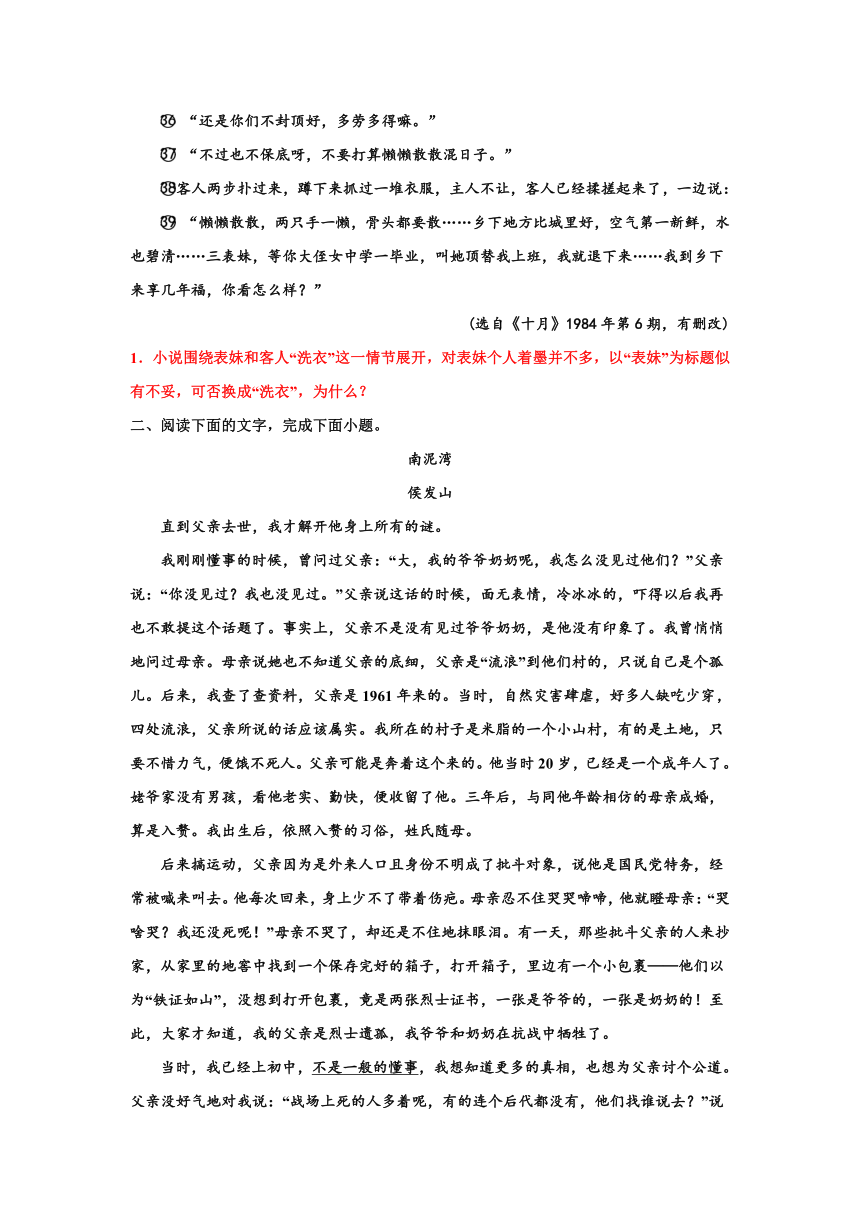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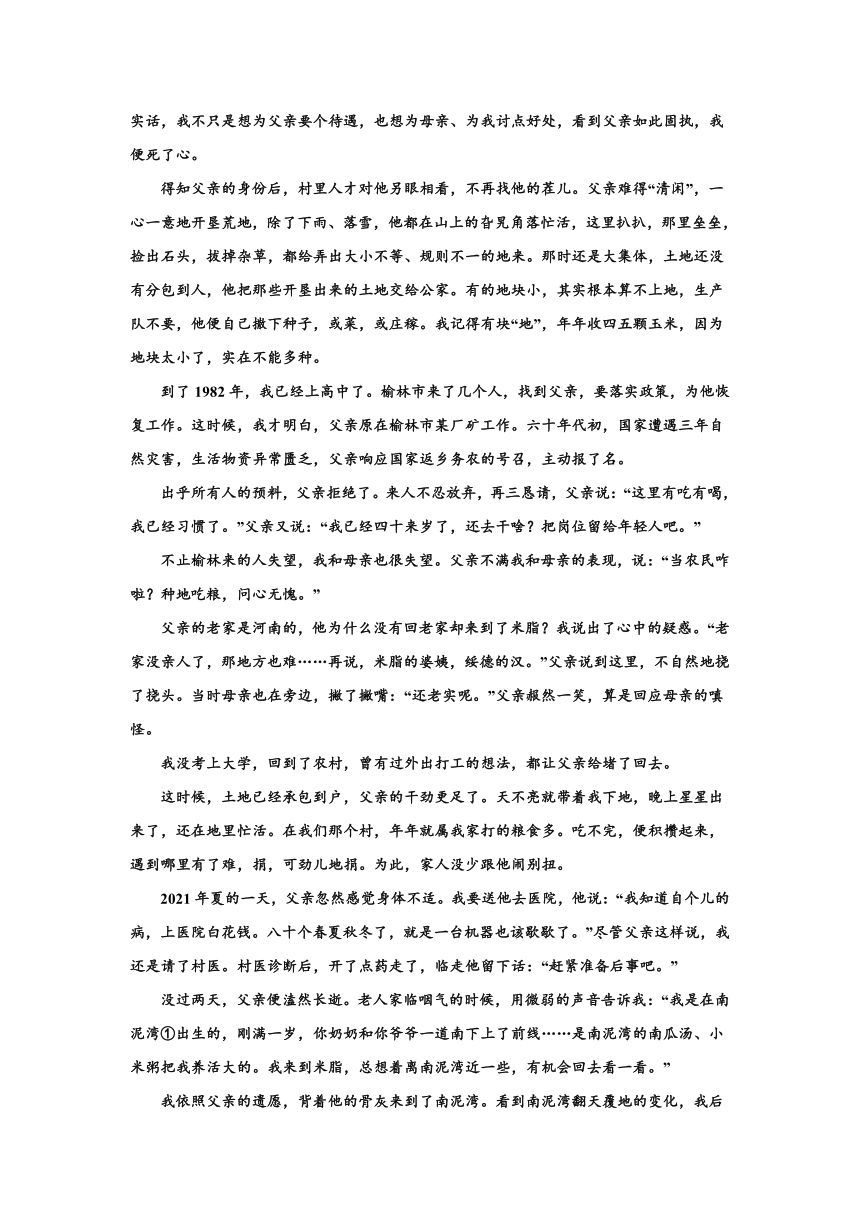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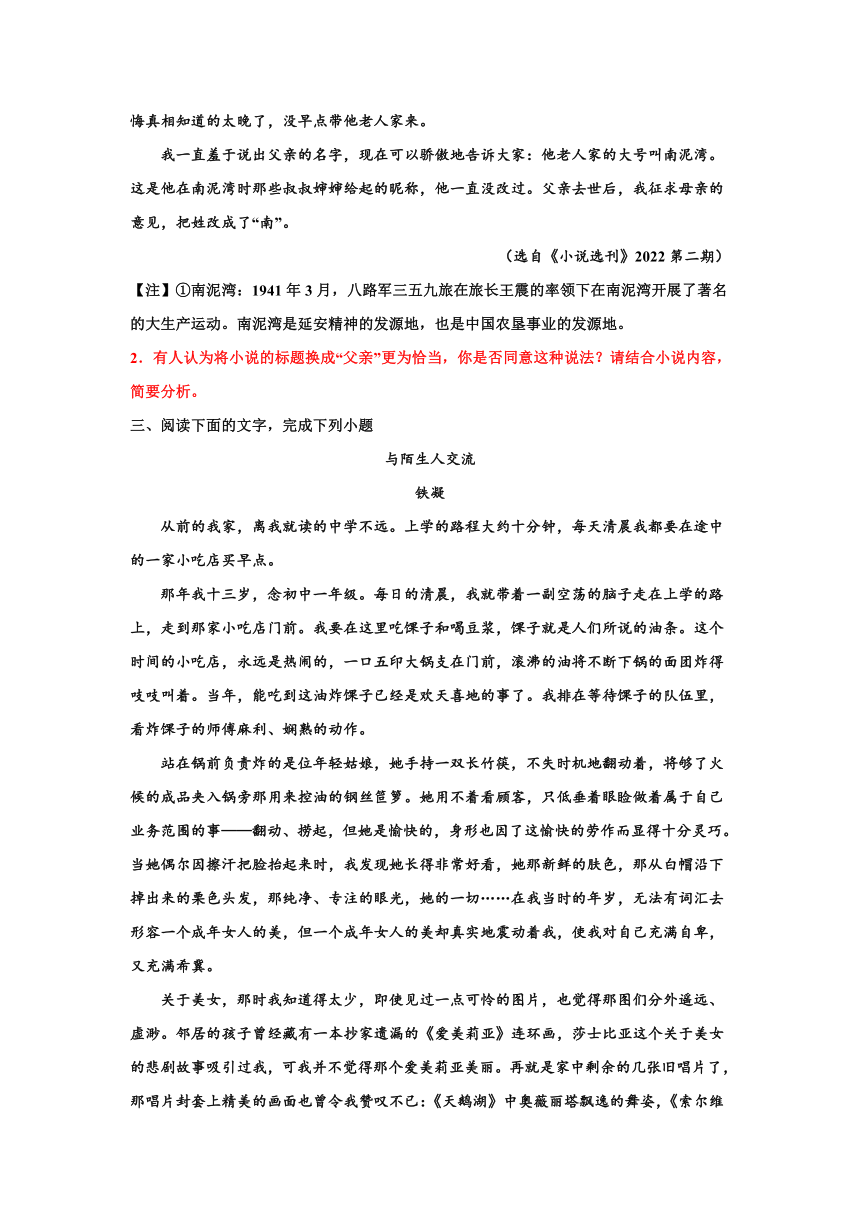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比较标题的优劣
一、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题。
表妹
林斤澜
①矮凳桥街背后是溪滩。那滩上铺满了大的碎石,开阔到叫人觉着是不毛之地。幸好有一条溪,时宽时窄,自由自在穿过石头滩,带来水草野树,带来生命的欢喜。
②滩上走过来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前边的挎着个竹篮子,简直有摇篮般大,里面是衣服,很有点分量,一路拱着腰身,支撑着篮底。后边的女人空着两手,几次伸手前来帮忙,前边的不让。前边的女人看来四十往里,后边的四十以外。前边的女人不走现成的小路,从石头滩上斜插过去,走到一个石头圈起来的水潭边,把竹篮里的东西一下子控在水里,全身轻松了,透出来一口长气,望着后边的。后边的走不惯石头滩,盯着脚下,挑着下脚的地方。前边的说:
③“这里比屋里清静,出来走走,说说话……再呢,我要把这些东西洗出来,也就不客气了。”
④说着就蹲下来,抓过一团按在早铺好了的石板上,拿起棒槌捶打起来,真是擦把汗的工夫也节约了。
⑤看起来后边的是位客人,转着身子看这个新鲜地方,有一句没一句地应酬着:
⑥“水倒是清的,碧清的……树也荫凉……石头要是走惯了,也好走……”
⑦“不好走,一到下雨天你走走看,只怕扭断了脚筋。哪有你们城里的马路好走。”
⑧“下雨天也洗衣服?”
⑨“一下十天呢,二十天呢。就是三天不洗也不行。嗐,现在一天是一天的事情,真是日日清,月月结。”
客人随即称赞:
“你真能干,三表妹,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天天洗这么多。”
主人微微笑着,手里捶捶打打,嘴里喜喜欢欢的:
“事情多着呢。只有晚上吃顿热的,别的两顿都马马虎虎。本来还要带孩子,现在托给人家。不过洗完衣服,还要踏缝纫机。”
客人其实是个做活的能手,又做饭又带孩子又洗衣服这样的日子都过过。现在做客人看着人家做活,两只手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把左手搭在树杈上,右手背在背后,都要用点力才在那里闲得住。不觉感慨起来:
“也难为你,也亏得是你,想想你在家里的时候,比我还自在呢。”
主人放下棒槌,两手一刻不停地揉搓起来:
“做做也就习惯了。不过,真的,做惯了空起两只手来,反倒没有地方好放。乡下地方,又没有什么好玩的,不比城里。”
客人心里有些矛盾,就学点见过世面的派头,给人家看,也压压自己的烦恼:
“说的是,”右手更加用力贴在后腰上,“空着两只手不也没地方放嘛。城里好玩是好玩,谁还成天地玩呢。城里住长久了,一下乡,空气真就好,这个新鲜空气,千金难买。”
单夸空气,好比一个姑娘没有什么好夸的,单夸她的头发。主人插嘴问道:
“你那里工资还好吧?”
提起工资,客人是有优越感的,却偏偏埋怨道:
“饿不死吃不饱就是了,连奖金带零碎也有七八十块。”
“那是做多做少照样拿呀!”
“还吃着大锅饭。”
“不做不做也拿六七十吧?”
“铁饭碗!”
客人差不多叫出来,她得意。主人不住手地揉搓,也微微笑着。客人倒打起“抱不平”来:
“你好脾气,要是我,气也气死了,做多做少什么也不拿。”
“大表姐,我们也搞承包了。我们家庭妇女洗衣店,给旅店洗床单,给工厂洗工作服都洗不过来。”
“那一个月能拿多少呢?”客人问得急点。
主人不忙正面回答,笑道:
“还要苦干个把月,洗衣机买是买来了,还没有安装。等安装好了,有时间多踏点缝纫机,还可以翻一番呢!”
“翻一番是多少?”客人急得不知道转弯。主人停止揉搓,去抓棒槌,这工夫,伸了伸两个手指头。
客人的脑筋飞快转动:这两个手指头当然不会是二十,那么是二百……听着都吓得心跳,那顶哪一级干部了?厂长?……回过头来说道:
“还是你们不封顶好,多劳多得嘛。”
“不过也不保底呀,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
客人两步扑过来,蹲下来抓过一堆衣服,主人不让,客人已经揉搓起来了,一边说:
“懒懒散散,两只手一懒,骨头都要散……乡下地方比城里好,空气第一新鲜,水也碧清……三表妹,等你大侄女中学一毕业,叫她顶替我上班,我就退下来……我到乡下来享几年福,你看怎么样?”
(选自《十月》1984年第6期,有删改)
1.小说围绕表妹和客人“洗衣”这一情节展开,对表妹个人着墨并不多,以“表妹”为标题似有不妥,可否换成“洗衣”,为什么?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南泥湾
侯发山
直到父亲去世,我才解开他身上所有的谜。
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曾问过父亲:“大,我的爷爷奶奶呢,我怎么没见过他们?”父亲说:“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父亲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吓得以后我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事实上,父亲不是没有见过爷爷奶奶,是他没有印象了。我曾悄悄地问过母亲。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父亲的底细,父亲是“流浪”到他们村的,只说自己是个孤儿。后来,我查了查资料,父亲是1961年来的。当时,自然灾害肆虐,好多人缺吃少穿,四处流浪,父亲所说的话应该属实。我所在的村子是米脂的一个小山村,有的是土地,只要不惜力气,便饿不死人。父亲可能是奔着这个来的。他当时20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姥爷家没有男孩,看他老实、勤快,便收留了他。三年后,与同他年龄相仿的母亲成婚,算是入赘。我出生后,依照入赘的习俗,姓氏随母。
后来搞运动,父亲因为是外来人口且身份不明成了批斗对象,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经常被喊来叫去。他每次回来,身上少不了带着伤疤。母亲忍不住哭哭啼啼,他就瞪母亲:“哭啥哭?我还没死呢!”母亲不哭了,却还是不住地抹眼泪。有一天,那些批斗父亲的人来抄家,从家里的地窖中找到一个保存完好的箱子,打开箱子,里边有一个小包裹——他们以为“铁证如山”,没想到打开包裹,竟是两张烈士证书,一张是爷爷的,一张是奶奶的!至此,大家才知道,我的父亲是烈士遗孤,我爷爷和奶奶在抗战中牺牲了。
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不是一般的懂事,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也想为父亲讨个公道。父亲没好气地对我说:“战场上死的人多着呢,有的连个后代都没有,他们找谁说去?”说实话,我不只是想为父亲要个待遇,也想为母亲、为我讨点好处,看到父亲如此固执,我便死了心。
得知父亲的身份后,村里人才对他另眼相看,不再找他的茬儿。父亲难得“清闲”,一心一意地开垦荒地,除了下雨、落雪,他都在山上的旮旯角落忙活,这里扒扒,那里垒垒,捡出石头,拔掉杂草,都给弄出大小不等、规则不一的地来。那时还是大集体,土地还没有分包到人,他把那些开垦出来的土地交给公家。有的地块小,其实根本算不上地,生产队不要,他便自己撒下种子,或菜,或庄稼。我记得有块“地”,年年收四五颗玉米,因为地块太小了,实在不能多种。
到了1982年,我已经上高中了。榆林市来了几个人,找到父亲,要落实政策,为他恢复工作。这时候,我才明白,父亲原在榆林市某厂矿工作。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物资异常匮乏,父亲响应国家返乡务农的号召,主动报了名。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父亲拒绝了。来人不忍放弃,再三恳请,父亲说:“这里有吃有喝,我已经习惯了。”父亲又说:“我已经四十来岁了,还去干啥?把岗位留给年轻人吧。”
不止榆林来的人失望,我和母亲也很失望。父亲不满我和母亲的表现,说:“当农民咋啦?种地吃粮,问心无愧。”
父亲的老家是河南的,他为什么没有回老家却来到了米脂?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老家没亲人了,那地方也难……再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父亲说到这里,不自然地挠了挠头。当时母亲也在旁边,撇了撇嘴:“还老实呢。”父亲赧然一笑,算是回应母亲的嗔怪。
我没考上大学,回到了农村,曾有过外出打工的想法,都让父亲给堵了回去。
这时候,土地已经承包到户,父亲的干劲更足了。天不亮就带着我下地,晚上星星出来了,还在地里忙活。在我们那个村,年年就属我家打的粮食多。吃不完,便积攒起来,遇到哪里有了难,捐,可劲儿地捐。为此,家人没少跟他闹别扭。
2021年夏的一天,父亲忽然感觉身体不适。我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我知道自个儿的病,上医院白花钱。八十个春夏秋冬了,就是一台机器也该歇歇了。”尽管父亲这样说,我还是请了村医。村医诊断后,开了点药走了,临走他留下话:“赶紧准备后事吧。”
没过两天,父亲便溘然长逝。老人家临咽气的时候,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我是在南泥湾①出生的,刚满一岁,你奶奶和你爷爷一道南下上了前线……是南泥湾的南瓜汤、小米粥把我养活大的。我来到米脂,总想着离南泥湾近一些,有机会回去看一看。”
我依照父亲的遗愿,背着他的骨灰来到了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后悔真相知道的太晚了,没早点带他老人家来。
我一直羞于说出父亲的名字,现在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他老人家的大号叫南泥湾。这是他在南泥湾时那些叔叔婶婶给起的昵称,他一直没改过。父亲去世后,我征求母亲的意见,把姓改成了“南”。
(选自《小说选刊》2022第二期)
【注】①南泥湾: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发源地。
2.有人认为将小说的标题换成“父亲”更为恰当,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与陌生人交流
铁凝
从前的我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十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
那年我十三岁,念初中一年级。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馃子和喝豆浆,馃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当年,能吃到这油炸馃子已经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馃子的队伍里,看炸馃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动作。
站在锅前负责炸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夹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她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她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劳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她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她长得非常好看,她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沿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她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有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
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得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们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爱美莉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爱美莉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薇丽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袁运甫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不可即。惟有这炸馃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地成长。
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式,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她的摹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我觉出一个新的我自己正在我身上诞生。
后来我们搬了家。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
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们同那位炸馃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她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式擦汗。她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却了从前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她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笸萝里的馃子其实都被她嚼过。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她,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馃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
我匆匆地向她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
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馃子的师傅无法与她们相比,偶尔地想起她来,仿佛只为着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
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她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她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呵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儿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她不过四十来岁。
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呵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
“小时候我常在这买馃子。”我说。
“现在没有。”她漠然地告诉我。
“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我说。
“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她打断我。
“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您……”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几乎怪我打断了她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
“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
“嗯?”她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她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她那声意外的“嗯”,和她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她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她的赞美。
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她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沿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就的小发卷儿为她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她以她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
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她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作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愿意坚信的:她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
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
(选自《铁凝文集》,有删改)
3.有人认为本文题目可以换成《炸馃子姑娘》,你觉得哪个标题更好?请结合文章说明理由。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桃花水
蒋子龙
午后,在黄土高原特有的蓝天骄阳下,面包车沿着五百里无定河岸缓缓爬行。无定河,浮浮漾漾,缓缓而下。
“安静!先别下车!”发声者竟然是平时极少说话经常用相机挡住眼睛和嘴巴的祝冰教授。大家顺着他的镜头望去:
在大道与高塬之间有块不大的三角地,三角地中央兀突突立着一盘石碾子,两个半大小子和一个略小一些的姑娘,一位老太太,在说说笑笑地推着碾子碾米;一位少妇,头发在脑后,深绛色的斜襟短袄,一动不动像尊雕像。背后的夕阳反射出满天红光,衬得她沉静秀异,神韵天然。
祝教授一声不吭,摇下车窗,按了许多次快门之后才让大家下车。十来位艺术家下车后大多都奔向左侧看河,尤其是画家和摄影家,对风景的兴趣最炽烈,对在没有村庄的大道边、凭空出现的碾米一家人充满好奇。
少妇起身,用簸箕从地上的口袋里舀出黍米,倒在碾盘的中间,又把碾子边上已经碾好的黏面用簸箕收起,倒进老人的细箩里,一看便知这是那种能承担生活压力的俏女子。
“刚才拍了你,我晚上来给你送照片。”
到了榆林市内,祝教授先去照相馆洗照片,饭后向领队请了假,回房间提上那一坨雕塑用泥,坐出租车去照相馆取了照片,然后直奔清水湾。
他,一张张地挑选,自己需要的留下,放进外套口袋,剩下的都送给少妇一家人,有老人的,有孩子的,他们会高兴的……
少妇这一晚上却有些心神不宁,主要是那个乱发教授临走前扔下的那句要给送照片来的话。如果他真来,就得到大道边去接一下,不然这塬上一片黑灯瞎火,他往哪儿去找?如果他就是随便一说,这十冬腊月的晚上,她一个人站在土坡上,岂不是冒傻气?犹豫再三,她还是穿上大衣,裹好围巾,拿着手电筒出了屋门。
仗着路熟,她打开手电筒顺着坡道缓缓往下走,为了来人远远地就能看到,她没有去河边,而是站在高坡上,手电的光柱指向从榆林来的方向。四野一片寂静,连无定河都没有一点击响,大道上没有一辆车,眼看就到年根底下了,跑车的人谁不往家里跑啊?
她蓦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这已经是他第四个春节没有回来过年了。
她的脑子里胡思乱想,却没有影响她看到从市里来的方向,真的出现了一对车灯,向着这边越驶越近,她赶紧移步下坡迎上去。
车在她脚边停下来,祝教授慌忙从车里钻出来,声音里带着异乎寻常地感动:“不好意思,害得你等候,冻坏了吧?”“快上车,里面暖和。”
少妇迟疑着,她以为对方把照片交给她不就可以返回了吗?
祝教授解释说:“我想到你家给你塑个像,只是打草稿,不会占用你太长的时间。方便不方便?”
少妇虽然还不完全明白“打草稿塑像”的意思,却不好拒绝他想到她家里去的要求,何况自己的母亲下午邀请在先。于是她上了车,引导着爬坡上塬,来到自家院门前,她下车打开院门,让车开进院子,然后将乱发贵客或者说是不速之客让进屋里。
祝教授从兜子里掏出照片放到桌上。拍照片是祝教授专业的一部分,相机又好,照片自然拍得很好,而且人人有份,个个神态自然生动。大人孩子抢着看,一阵惊讶,一阵欢笑。
祝教授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少妇:“我叫祝冰,是中国工艺美大的教师,搞雕塑的,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
少妇一边低头看着祝冰的名片,一边答道:“我叫孙秀禾。”
祝教授反客为主,把墙边的凳搬到屋子中间光线最好的地方,让孙秀禾身子微微向左侧着坐下。他将桌子移到孙秀禾对面,把塑泥放到桌上,眼睛像刻刀一样在孙秀禾的脸上死死地盯了一会儿,两只手倏然变得像魔术师一样灵巧有力,那坨泥在他的手里既柔软又坚硬,软到随着他的手指任意变化着形状,凡经他捏出来的形状就硬到绝不扭塌。
屋子安静下来,老人和孩子们不再看照片,而是围在祝教授身边看那塑像,首先是孙秀禾的儿子嚷起来:“像,像妈妈!”
其他孩子连同老太太也都随声附和:“是像,还真像!”
祝教授,不说话,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塑像上,拧着眉头,闪出一股兴奋和冲动,过了好一阵子,他停下手,抬起头,端详着塑像,自言自语:“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回去再细加工。”
孙秀禾早就忍不住走过来看那塑像,心里一阵惊喜。这个教授真行,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重新塑造了一个孙秀禾。她太喜欢了,比自己更漂亮、更有精神。
祝教授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零碎儿全放进随身带的大兜子,穿上毛背心和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孙秀禾手里:“这个信封里有一张卡,信封上的数字就是密码,这不是你让我塑像的报酬,是给孩子过年的红包。”
孙秀禾吃一惊,没想到这个教授还有这一手,坚决不要。但他强把卡塞进抽屉里,然后用自己的围巾裹好塑像,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走出了院门。
她站在院门前,呆呆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处…
很快到了农历三月,塬上桃花开了,无定河的桃花水下来了。塬上的春耕春种也开始了,祝教授来看她。
“以前不敢跟你说明,怕你不同意,这毕竟使用了你的肖像权,如果你不同意,我还要在面部做些改动,改得在像与不像之间。可我不想改,我就想以你的面貌在博物馆立一个《大地之母》像,黄土高原上的母亲。”
4.“桃花水”即桃花盛开时江河里暴涨的水,本文并没有写桃花水,能不能把标题换成“无定河的水”?为什么?
参考答案:
1.(示例一)不可以。因为这篇小说主要介绍了表妹的新生活,通过表妹的新生活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利用剩余劳动力搞活经济的新现象;也通过“表妹”这个勤劳致富的农民形象,表达了对劳动、勤劳致富和新时代的赞美之情。以“表妹”为标题突出了主要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的情感态度。
(示例二)可以。这篇小说对表妹着墨并不多,而是以“洗衣”为线索展开情节,“洗衣”是小说的主要事件,以事件为标题也是常见的拟标题的方式;小说通过“洗衣”这件事塑造了“表妹”和“表姐”两个典型人物形象,展现了城乡差距和城乡居民的心理;小说通过洗衣挣钱这件小事,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活跃、农民劳动致富的新景象,展现了农村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表现了作者对新时代的赞美。
2.不同意。因为“父亲”作为标题虽然显得亲切而且贯穿整个情节,但其意蕴远不及“南泥湾”丰富:(1)“南泥湾”是父亲的大名,那是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友对烈士遗孤的昵称,承载了浓郁的战友情;(2)“南泥湾”是父亲的出生地,是他的父母亲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也是父亲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3)“南泥湾”是革命圣地,象征着革命精神和传统,影响了父亲的人生,也将照亮年轻一代的前进方向。
3.观点一:原标题更好。
①《与陌生人交流》是本文的主要情节。文章围绕这一情节展开叙述,以独特的“交流”方式呈现了一个追求美的故事。
②以《与陌生人交流》为题设置了悬念。让读者不禁思考“为何要与陌生人交
流”“与陌生人如何交流”,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趣。
③揭示文章的主旨。号召大家放下架子和虚荣心,多与陌生人交流,在这个过
程中收获人性之美。
观点二:《炸馃子姑娘》更好。
①以“炸馃子姑娘”为题,更能凸显她是本文的主要人物。
②“炸馃子姑娘”的形象变化推动了文章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转变使得情节层层推进。
③“炸馃子姑娘”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紧扣文章中心,揭示了与像“炸馃子姑娘”这样的陌生人交流会给平淡的生活带来陌生的魅力的主旨。
4.示例一:不能。因为让秀禾期盼的祝教授隔了几个月终于要来塬上,让人十分开心,心情如桃花一般盛开;桃花水写出了此时正是桃花盛开、一切美妙之时,也暗指《大地之母》像的成功就是教授盛开的艺术之花;桃花水也指明了春耕春种的季节,从而侧面赞扬了黄土高原上辛劳的母亲们。
示例二:能。“无定河的水”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无定”两字还与故事发生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吻合,与文中多处写到的无定河及其水相照应。
一、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题。
表妹
林斤澜
①矮凳桥街背后是溪滩。那滩上铺满了大的碎石,开阔到叫人觉着是不毛之地。幸好有一条溪,时宽时窄,自由自在穿过石头滩,带来水草野树,带来生命的欢喜。
②滩上走过来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前边的挎着个竹篮子,简直有摇篮般大,里面是衣服,很有点分量,一路拱着腰身,支撑着篮底。后边的女人空着两手,几次伸手前来帮忙,前边的不让。前边的女人看来四十往里,后边的四十以外。前边的女人不走现成的小路,从石头滩上斜插过去,走到一个石头圈起来的水潭边,把竹篮里的东西一下子控在水里,全身轻松了,透出来一口长气,望着后边的。后边的走不惯石头滩,盯着脚下,挑着下脚的地方。前边的说:
③“这里比屋里清静,出来走走,说说话……再呢,我要把这些东西洗出来,也就不客气了。”
④说着就蹲下来,抓过一团按在早铺好了的石板上,拿起棒槌捶打起来,真是擦把汗的工夫也节约了。
⑤看起来后边的是位客人,转着身子看这个新鲜地方,有一句没一句地应酬着:
⑥“水倒是清的,碧清的……树也荫凉……石头要是走惯了,也好走……”
⑦“不好走,一到下雨天你走走看,只怕扭断了脚筋。哪有你们城里的马路好走。”
⑧“下雨天也洗衣服?”
⑨“一下十天呢,二十天呢。就是三天不洗也不行。嗐,现在一天是一天的事情,真是日日清,月月结。”
客人随即称赞:
“你真能干,三表妹,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天天洗这么多。”
主人微微笑着,手里捶捶打打,嘴里喜喜欢欢的:
“事情多着呢。只有晚上吃顿热的,别的两顿都马马虎虎。本来还要带孩子,现在托给人家。不过洗完衣服,还要踏缝纫机。”
客人其实是个做活的能手,又做饭又带孩子又洗衣服这样的日子都过过。现在做客人看着人家做活,两只手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把左手搭在树杈上,右手背在背后,都要用点力才在那里闲得住。不觉感慨起来:
“也难为你,也亏得是你,想想你在家里的时候,比我还自在呢。”
主人放下棒槌,两手一刻不停地揉搓起来:
“做做也就习惯了。不过,真的,做惯了空起两只手来,反倒没有地方好放。乡下地方,又没有什么好玩的,不比城里。”
客人心里有些矛盾,就学点见过世面的派头,给人家看,也压压自己的烦恼:
“说的是,”右手更加用力贴在后腰上,“空着两只手不也没地方放嘛。城里好玩是好玩,谁还成天地玩呢。城里住长久了,一下乡,空气真就好,这个新鲜空气,千金难买。”
单夸空气,好比一个姑娘没有什么好夸的,单夸她的头发。主人插嘴问道:
“你那里工资还好吧?”
提起工资,客人是有优越感的,却偏偏埋怨道:
“饿不死吃不饱就是了,连奖金带零碎也有七八十块。”
“那是做多做少照样拿呀!”
“还吃着大锅饭。”
“不做不做也拿六七十吧?”
“铁饭碗!”
客人差不多叫出来,她得意。主人不住手地揉搓,也微微笑着。客人倒打起“抱不平”来:
“你好脾气,要是我,气也气死了,做多做少什么也不拿。”
“大表姐,我们也搞承包了。我们家庭妇女洗衣店,给旅店洗床单,给工厂洗工作服都洗不过来。”
“那一个月能拿多少呢?”客人问得急点。
主人不忙正面回答,笑道:
“还要苦干个把月,洗衣机买是买来了,还没有安装。等安装好了,有时间多踏点缝纫机,还可以翻一番呢!”
“翻一番是多少?”客人急得不知道转弯。主人停止揉搓,去抓棒槌,这工夫,伸了伸两个手指头。
客人的脑筋飞快转动:这两个手指头当然不会是二十,那么是二百……听着都吓得心跳,那顶哪一级干部了?厂长?……回过头来说道:
“还是你们不封顶好,多劳多得嘛。”
“不过也不保底呀,不要打算懒懒散散混日子。”
客人两步扑过来,蹲下来抓过一堆衣服,主人不让,客人已经揉搓起来了,一边说:
“懒懒散散,两只手一懒,骨头都要散……乡下地方比城里好,空气第一新鲜,水也碧清……三表妹,等你大侄女中学一毕业,叫她顶替我上班,我就退下来……我到乡下来享几年福,你看怎么样?”
(选自《十月》1984年第6期,有删改)
1.小说围绕表妹和客人“洗衣”这一情节展开,对表妹个人着墨并不多,以“表妹”为标题似有不妥,可否换成“洗衣”,为什么?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南泥湾
侯发山
直到父亲去世,我才解开他身上所有的谜。
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曾问过父亲:“大,我的爷爷奶奶呢,我怎么没见过他们?”父亲说:“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父亲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吓得以后我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事实上,父亲不是没有见过爷爷奶奶,是他没有印象了。我曾悄悄地问过母亲。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父亲的底细,父亲是“流浪”到他们村的,只说自己是个孤儿。后来,我查了查资料,父亲是1961年来的。当时,自然灾害肆虐,好多人缺吃少穿,四处流浪,父亲所说的话应该属实。我所在的村子是米脂的一个小山村,有的是土地,只要不惜力气,便饿不死人。父亲可能是奔着这个来的。他当时20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姥爷家没有男孩,看他老实、勤快,便收留了他。三年后,与同他年龄相仿的母亲成婚,算是入赘。我出生后,依照入赘的习俗,姓氏随母。
后来搞运动,父亲因为是外来人口且身份不明成了批斗对象,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经常被喊来叫去。他每次回来,身上少不了带着伤疤。母亲忍不住哭哭啼啼,他就瞪母亲:“哭啥哭?我还没死呢!”母亲不哭了,却还是不住地抹眼泪。有一天,那些批斗父亲的人来抄家,从家里的地窖中找到一个保存完好的箱子,打开箱子,里边有一个小包裹——他们以为“铁证如山”,没想到打开包裹,竟是两张烈士证书,一张是爷爷的,一张是奶奶的!至此,大家才知道,我的父亲是烈士遗孤,我爷爷和奶奶在抗战中牺牲了。
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不是一般的懂事,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也想为父亲讨个公道。父亲没好气地对我说:“战场上死的人多着呢,有的连个后代都没有,他们找谁说去?”说实话,我不只是想为父亲要个待遇,也想为母亲、为我讨点好处,看到父亲如此固执,我便死了心。
得知父亲的身份后,村里人才对他另眼相看,不再找他的茬儿。父亲难得“清闲”,一心一意地开垦荒地,除了下雨、落雪,他都在山上的旮旯角落忙活,这里扒扒,那里垒垒,捡出石头,拔掉杂草,都给弄出大小不等、规则不一的地来。那时还是大集体,土地还没有分包到人,他把那些开垦出来的土地交给公家。有的地块小,其实根本算不上地,生产队不要,他便自己撒下种子,或菜,或庄稼。我记得有块“地”,年年收四五颗玉米,因为地块太小了,实在不能多种。
到了1982年,我已经上高中了。榆林市来了几个人,找到父亲,要落实政策,为他恢复工作。这时候,我才明白,父亲原在榆林市某厂矿工作。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物资异常匮乏,父亲响应国家返乡务农的号召,主动报了名。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父亲拒绝了。来人不忍放弃,再三恳请,父亲说:“这里有吃有喝,我已经习惯了。”父亲又说:“我已经四十来岁了,还去干啥?把岗位留给年轻人吧。”
不止榆林来的人失望,我和母亲也很失望。父亲不满我和母亲的表现,说:“当农民咋啦?种地吃粮,问心无愧。”
父亲的老家是河南的,他为什么没有回老家却来到了米脂?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老家没亲人了,那地方也难……再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父亲说到这里,不自然地挠了挠头。当时母亲也在旁边,撇了撇嘴:“还老实呢。”父亲赧然一笑,算是回应母亲的嗔怪。
我没考上大学,回到了农村,曾有过外出打工的想法,都让父亲给堵了回去。
这时候,土地已经承包到户,父亲的干劲更足了。天不亮就带着我下地,晚上星星出来了,还在地里忙活。在我们那个村,年年就属我家打的粮食多。吃不完,便积攒起来,遇到哪里有了难,捐,可劲儿地捐。为此,家人没少跟他闹别扭。
2021年夏的一天,父亲忽然感觉身体不适。我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我知道自个儿的病,上医院白花钱。八十个春夏秋冬了,就是一台机器也该歇歇了。”尽管父亲这样说,我还是请了村医。村医诊断后,开了点药走了,临走他留下话:“赶紧准备后事吧。”
没过两天,父亲便溘然长逝。老人家临咽气的时候,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我是在南泥湾①出生的,刚满一岁,你奶奶和你爷爷一道南下上了前线……是南泥湾的南瓜汤、小米粥把我养活大的。我来到米脂,总想着离南泥湾近一些,有机会回去看一看。”
我依照父亲的遗愿,背着他的骨灰来到了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后悔真相知道的太晚了,没早点带他老人家来。
我一直羞于说出父亲的名字,现在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他老人家的大号叫南泥湾。这是他在南泥湾时那些叔叔婶婶给起的昵称,他一直没改过。父亲去世后,我征求母亲的意见,把姓改成了“南”。
(选自《小说选刊》2022第二期)
【注】①南泥湾: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发源地。
2.有人认为将小说的标题换成“父亲”更为恰当,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与陌生人交流
铁凝
从前的我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十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
那年我十三岁,念初中一年级。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馃子和喝豆浆,馃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当年,能吃到这油炸馃子已经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馃子的队伍里,看炸馃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动作。
站在锅前负责炸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夹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她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她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劳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她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她长得非常好看,她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沿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她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有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
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得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们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爱美莉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爱美莉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薇丽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袁运甫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不可即。惟有这炸馃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地成长。
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式,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她的摹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我觉出一个新的我自己正在我身上诞生。
后来我们搬了家。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
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们同那位炸馃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她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式擦汗。她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却了从前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她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笸萝里的馃子其实都被她嚼过。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她,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馃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
我匆匆地向她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
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馃子的师傅无法与她们相比,偶尔地想起她来,仿佛只为着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
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她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她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呵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儿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她不过四十来岁。
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呵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
“小时候我常在这买馃子。”我说。
“现在没有。”她漠然地告诉我。
“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我说。
“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她打断我。
“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您……”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几乎怪我打断了她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
“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
“嗯?”她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她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她那声意外的“嗯”,和她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她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她的赞美。
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她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沿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就的小发卷儿为她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她以她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
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她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作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愿意坚信的:她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
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
(选自《铁凝文集》,有删改)
3.有人认为本文题目可以换成《炸馃子姑娘》,你觉得哪个标题更好?请结合文章说明理由。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桃花水
蒋子龙
午后,在黄土高原特有的蓝天骄阳下,面包车沿着五百里无定河岸缓缓爬行。无定河,浮浮漾漾,缓缓而下。
“安静!先别下车!”发声者竟然是平时极少说话经常用相机挡住眼睛和嘴巴的祝冰教授。大家顺着他的镜头望去:
在大道与高塬之间有块不大的三角地,三角地中央兀突突立着一盘石碾子,两个半大小子和一个略小一些的姑娘,一位老太太,在说说笑笑地推着碾子碾米;一位少妇,头发在脑后,深绛色的斜襟短袄,一动不动像尊雕像。背后的夕阳反射出满天红光,衬得她沉静秀异,神韵天然。
祝教授一声不吭,摇下车窗,按了许多次快门之后才让大家下车。十来位艺术家下车后大多都奔向左侧看河,尤其是画家和摄影家,对风景的兴趣最炽烈,对在没有村庄的大道边、凭空出现的碾米一家人充满好奇。
少妇起身,用簸箕从地上的口袋里舀出黍米,倒在碾盘的中间,又把碾子边上已经碾好的黏面用簸箕收起,倒进老人的细箩里,一看便知这是那种能承担生活压力的俏女子。
“刚才拍了你,我晚上来给你送照片。”
到了榆林市内,祝教授先去照相馆洗照片,饭后向领队请了假,回房间提上那一坨雕塑用泥,坐出租车去照相馆取了照片,然后直奔清水湾。
他,一张张地挑选,自己需要的留下,放进外套口袋,剩下的都送给少妇一家人,有老人的,有孩子的,他们会高兴的……
少妇这一晚上却有些心神不宁,主要是那个乱发教授临走前扔下的那句要给送照片来的话。如果他真来,就得到大道边去接一下,不然这塬上一片黑灯瞎火,他往哪儿去找?如果他就是随便一说,这十冬腊月的晚上,她一个人站在土坡上,岂不是冒傻气?犹豫再三,她还是穿上大衣,裹好围巾,拿着手电筒出了屋门。
仗着路熟,她打开手电筒顺着坡道缓缓往下走,为了来人远远地就能看到,她没有去河边,而是站在高坡上,手电的光柱指向从榆林来的方向。四野一片寂静,连无定河都没有一点击响,大道上没有一辆车,眼看就到年根底下了,跑车的人谁不往家里跑啊?
她蓦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这已经是他第四个春节没有回来过年了。
她的脑子里胡思乱想,却没有影响她看到从市里来的方向,真的出现了一对车灯,向着这边越驶越近,她赶紧移步下坡迎上去。
车在她脚边停下来,祝教授慌忙从车里钻出来,声音里带着异乎寻常地感动:“不好意思,害得你等候,冻坏了吧?”“快上车,里面暖和。”
少妇迟疑着,她以为对方把照片交给她不就可以返回了吗?
祝教授解释说:“我想到你家给你塑个像,只是打草稿,不会占用你太长的时间。方便不方便?”
少妇虽然还不完全明白“打草稿塑像”的意思,却不好拒绝他想到她家里去的要求,何况自己的母亲下午邀请在先。于是她上了车,引导着爬坡上塬,来到自家院门前,她下车打开院门,让车开进院子,然后将乱发贵客或者说是不速之客让进屋里。
祝教授从兜子里掏出照片放到桌上。拍照片是祝教授专业的一部分,相机又好,照片自然拍得很好,而且人人有份,个个神态自然生动。大人孩子抢着看,一阵惊讶,一阵欢笑。
祝教授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少妇:“我叫祝冰,是中国工艺美大的教师,搞雕塑的,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
少妇一边低头看着祝冰的名片,一边答道:“我叫孙秀禾。”
祝教授反客为主,把墙边的凳搬到屋子中间光线最好的地方,让孙秀禾身子微微向左侧着坐下。他将桌子移到孙秀禾对面,把塑泥放到桌上,眼睛像刻刀一样在孙秀禾的脸上死死地盯了一会儿,两只手倏然变得像魔术师一样灵巧有力,那坨泥在他的手里既柔软又坚硬,软到随着他的手指任意变化着形状,凡经他捏出来的形状就硬到绝不扭塌。
屋子安静下来,老人和孩子们不再看照片,而是围在祝教授身边看那塑像,首先是孙秀禾的儿子嚷起来:“像,像妈妈!”
其他孩子连同老太太也都随声附和:“是像,还真像!”
祝教授,不说话,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塑像上,拧着眉头,闪出一股兴奋和冲动,过了好一阵子,他停下手,抬起头,端详着塑像,自言自语:“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回去再细加工。”
孙秀禾早就忍不住走过来看那塑像,心里一阵惊喜。这个教授真行,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重新塑造了一个孙秀禾。她太喜欢了,比自己更漂亮、更有精神。
祝教授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零碎儿全放进随身带的大兜子,穿上毛背心和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孙秀禾手里:“这个信封里有一张卡,信封上的数字就是密码,这不是你让我塑像的报酬,是给孩子过年的红包。”
孙秀禾吃一惊,没想到这个教授还有这一手,坚决不要。但他强把卡塞进抽屉里,然后用自己的围巾裹好塑像,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走出了院门。
她站在院门前,呆呆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处…
很快到了农历三月,塬上桃花开了,无定河的桃花水下来了。塬上的春耕春种也开始了,祝教授来看她。
“以前不敢跟你说明,怕你不同意,这毕竟使用了你的肖像权,如果你不同意,我还要在面部做些改动,改得在像与不像之间。可我不想改,我就想以你的面貌在博物馆立一个《大地之母》像,黄土高原上的母亲。”
4.“桃花水”即桃花盛开时江河里暴涨的水,本文并没有写桃花水,能不能把标题换成“无定河的水”?为什么?
参考答案:
1.(示例一)不可以。因为这篇小说主要介绍了表妹的新生活,通过表妹的新生活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利用剩余劳动力搞活经济的新现象;也通过“表妹”这个勤劳致富的农民形象,表达了对劳动、勤劳致富和新时代的赞美之情。以“表妹”为标题突出了主要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的情感态度。
(示例二)可以。这篇小说对表妹着墨并不多,而是以“洗衣”为线索展开情节,“洗衣”是小说的主要事件,以事件为标题也是常见的拟标题的方式;小说通过“洗衣”这件事塑造了“表妹”和“表姐”两个典型人物形象,展现了城乡差距和城乡居民的心理;小说通过洗衣挣钱这件小事,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活跃、农民劳动致富的新景象,展现了农村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表现了作者对新时代的赞美。
2.不同意。因为“父亲”作为标题虽然显得亲切而且贯穿整个情节,但其意蕴远不及“南泥湾”丰富:(1)“南泥湾”是父亲的大名,那是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友对烈士遗孤的昵称,承载了浓郁的战友情;(2)“南泥湾”是父亲的出生地,是他的父母亲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也是父亲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3)“南泥湾”是革命圣地,象征着革命精神和传统,影响了父亲的人生,也将照亮年轻一代的前进方向。
3.观点一:原标题更好。
①《与陌生人交流》是本文的主要情节。文章围绕这一情节展开叙述,以独特的“交流”方式呈现了一个追求美的故事。
②以《与陌生人交流》为题设置了悬念。让读者不禁思考“为何要与陌生人交
流”“与陌生人如何交流”,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趣。
③揭示文章的主旨。号召大家放下架子和虚荣心,多与陌生人交流,在这个过
程中收获人性之美。
观点二:《炸馃子姑娘》更好。
①以“炸馃子姑娘”为题,更能凸显她是本文的主要人物。
②“炸馃子姑娘”的形象变化推动了文章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转变使得情节层层推进。
③“炸馃子姑娘”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紧扣文章中心,揭示了与像“炸馃子姑娘”这样的陌生人交流会给平淡的生活带来陌生的魅力的主旨。
4.示例一:不能。因为让秀禾期盼的祝教授隔了几个月终于要来塬上,让人十分开心,心情如桃花一般盛开;桃花水写出了此时正是桃花盛开、一切美妙之时,也暗指《大地之母》像的成功就是教授盛开的艺术之花;桃花水也指明了春耕春种的季节,从而侧面赞扬了黄土高原上辛劳的母亲们。
示例二:能。“无定河的水”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无定”两字还与故事发生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吻合,与文中多处写到的无定河及其水相照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