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人物语言描写(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人物语言描写(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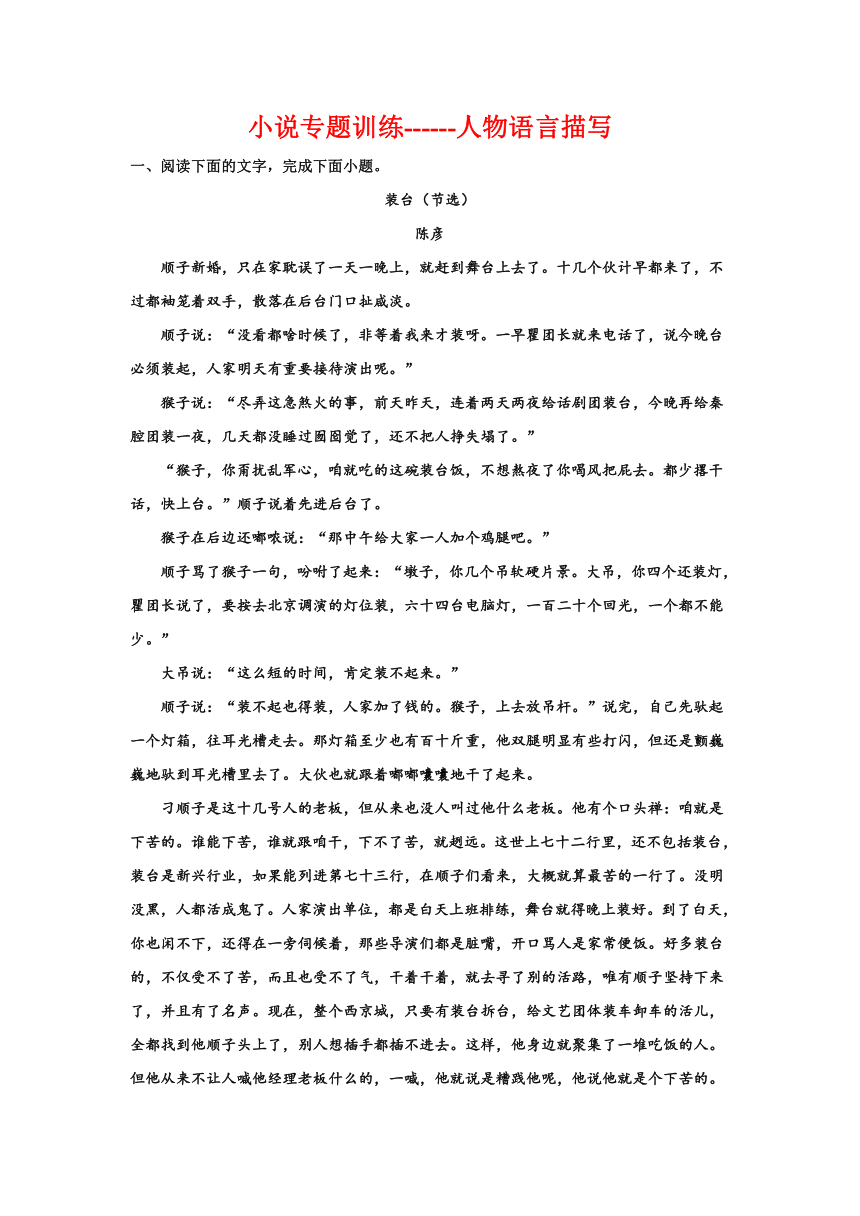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3.4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通用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4-11 16:04:16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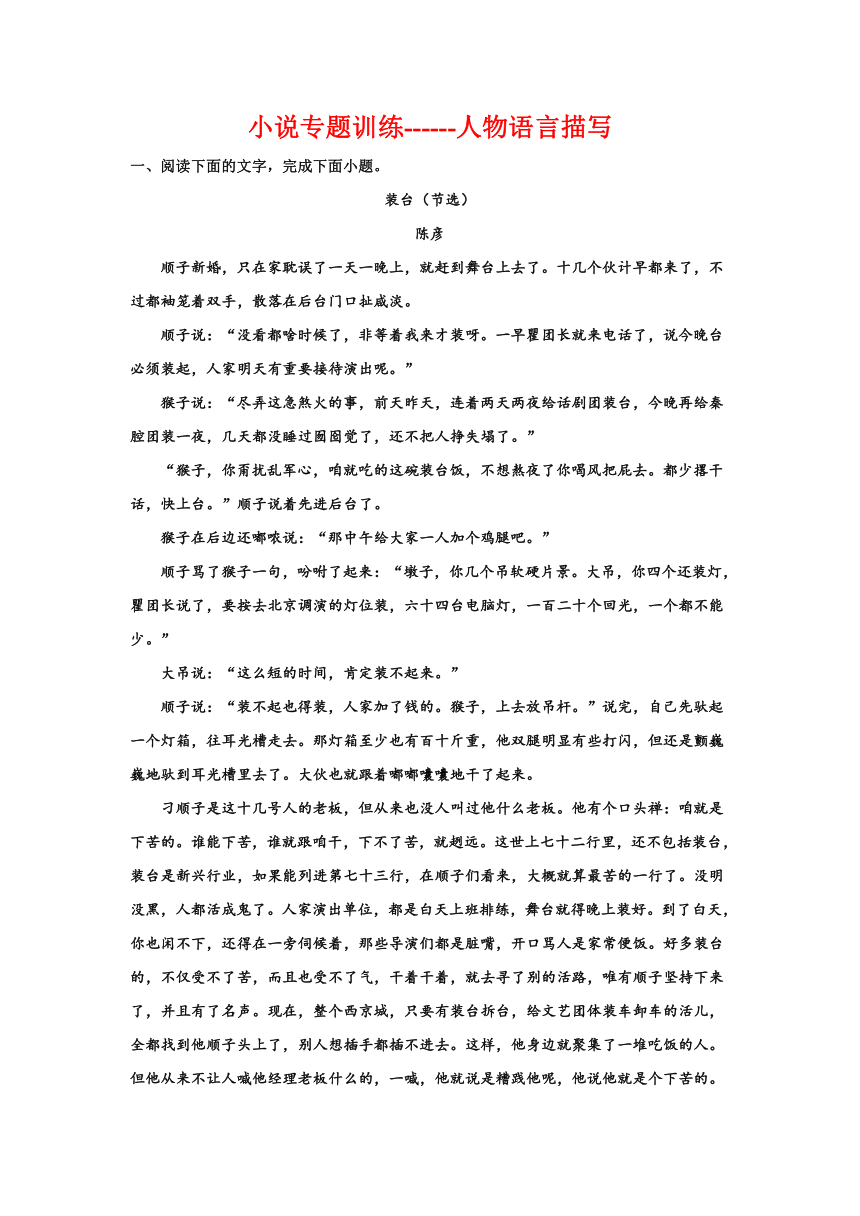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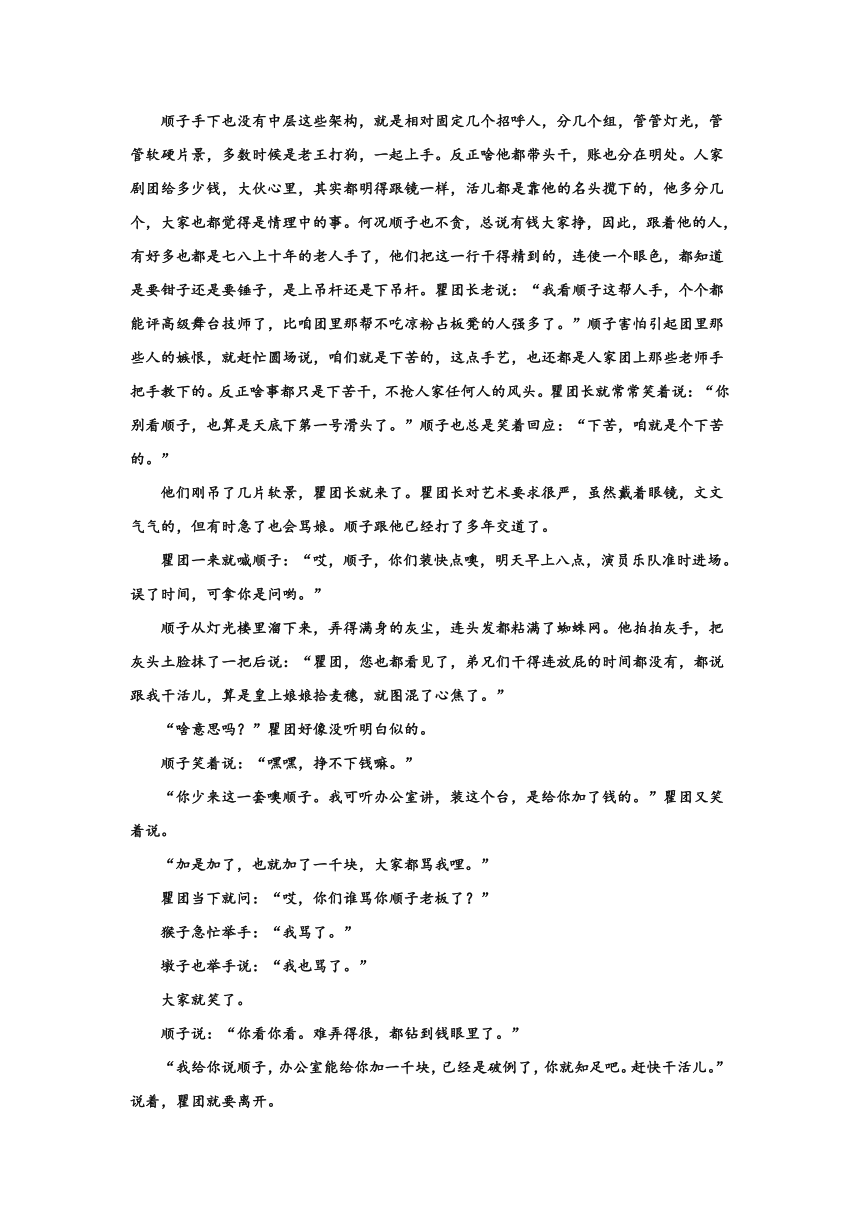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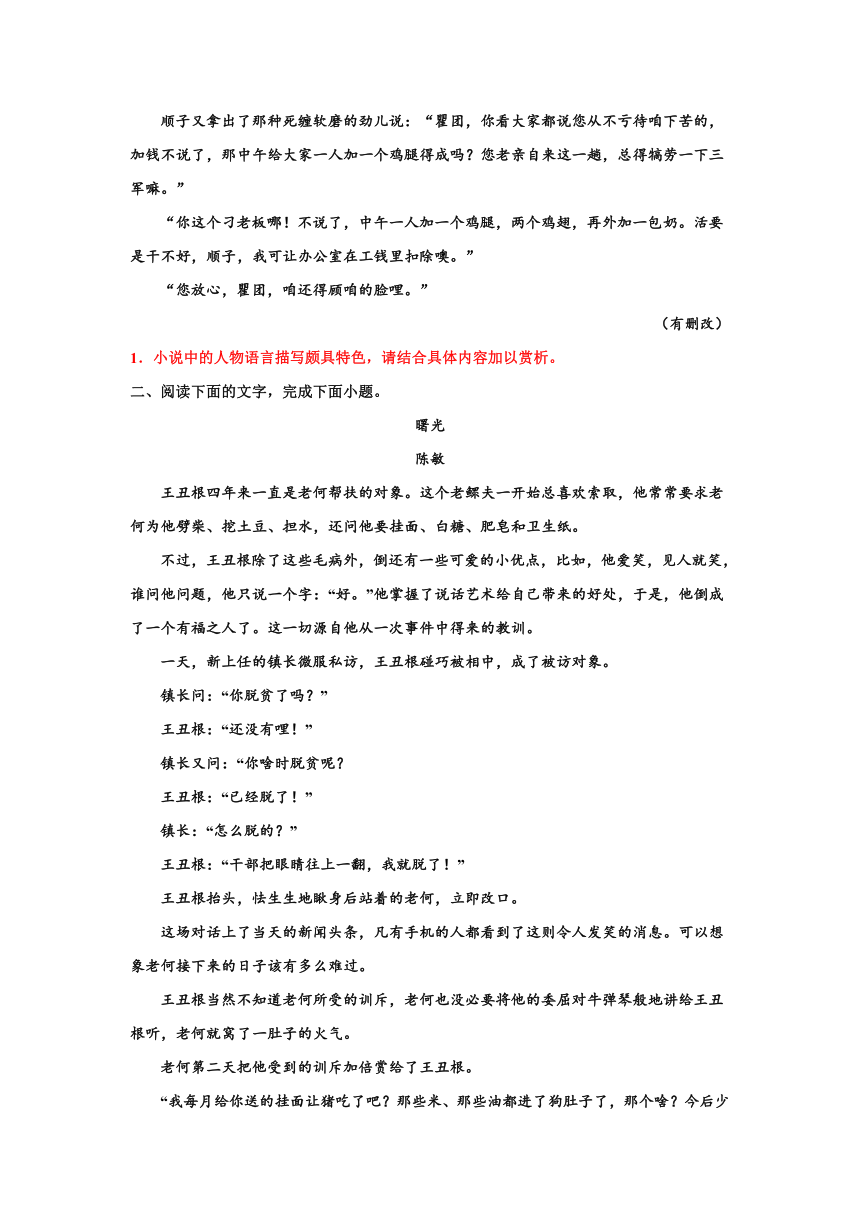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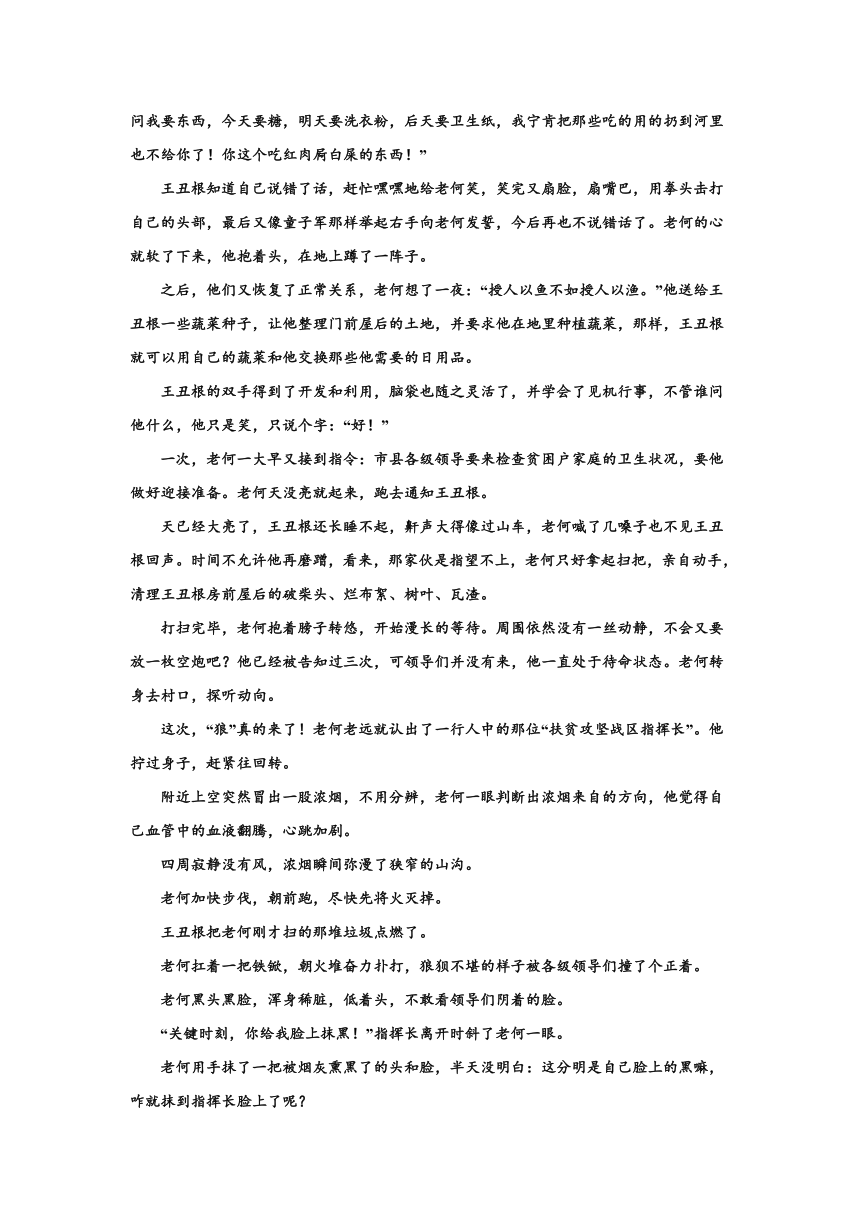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人物语言描写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装台(节选)
陈彦
顺子新婚,只在家耽误了一天一晚上,就赶到舞台上去了。十几个伙计早都来了,不过都袖笼着双手,散落在后台门口扯咸淡。
顺子说:“没看都啥时候了,非等着我来才装呀。一早瞿团长就来电话了,说今晚台必须装起,人家明天有重要接待演出呢。”
猴子说:“尽弄这急煞火的事,前天昨天,连着两天两夜给话剧团装台,今晚再给秦腔团装一夜,几天都没睡过囫囵觉了,还不把人挣失塌了。”
“猴子,你甭扰乱军心,咱就吃的这碗装台饭,不想熬夜了你喝风把屁去。都少撂干话,快上台。”顺子说着先进后台了。
猴子在后边还嘟哝说:“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加个鸡腿吧。”
顺子骂了猴子一句,吩咐了起来:“墩子,你几个吊软硬片景。大吊,你四个还装灯,瞿团长说了,要按去北京调演的灯位装,六十四台电脑灯,一百二十个回光,一个都不能少。”
大吊说:“这么短的时间,肯定装不起来。”
顺子说:“装不起也得装,人家加了钱的。猴子,上去放吊杆。”说完,自己先驮起一个灯箱,往耳光槽走去。那灯箱至少也有百十斤重,他双腿明显有些打闪,但还是颤巍巍地驮到耳光槽里去了。大伙也就跟着嘟嘟囔囔地干了起来。
刁顺子是这十几号人的老板,但从来也没人叫过他什么老板。他有个口头禅:咱就是下苦的。谁能下苦,谁就跟咱干,下不了苦,就趔远。这世上七十二行里,还不包括装台,装台是新兴行业,如果能列进第七十三行,在顺子们看来,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人家演出单位,都是白天上班排练,舞台就得晚上装好。到了白天,你也闲不下,还得在一旁伺候着,那些导演们都是脏嘴,开口骂人是家常便饭。好多装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也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现在,整个西京城,只要有装台拆台,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儿,全都找到他顺子头上了,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这样,他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但他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一喊,他就说是糟践他呢,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
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就是相对固定几个招呼人,分几个组,管管灯光,管管软硬片景,多数时候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反正啥他都带头干,账也分在明处。人家剧团给多少钱,大伙心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活儿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他多分几个,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何况顺子也不贪,总说有钱大家挣,因此,跟着他的人,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他们把这一行干得精到的,连使一个眼色,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是上吊杆还是下吊杆。瞿团长老说:“我看顺子这帮人手,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占板凳的人强多了。”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就赶忙圆场说,咱们就是下苦的,这点手艺,也还都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反正啥事都只是下苦干,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瞿团长就常常笑着说:“你别看顺子,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顺子也总是笑着回应:“下苦,咱就是个下苦的。”
他们刚吊了几片软景,瞿团长就来了。瞿团长对艺术要求很严,虽然戴着眼镜,文文气气的,但有时急了也会骂娘。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
瞿团一来就喊顺子:“哎,顺子,你们装快点噢,明天早上八点,演员乐队准时进场。误了时间,可拿你是问哟。”
顺子从灯光楼里溜下来,弄得满身的灰尘,连头发都粘满了蜘蛛网。他拍拍灰手,把灰头土脸抹了一把后说:“瞿团,您也都看见了,弟兄们干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都说跟我干活儿,算是皇上娘娘拾麦穗,就图混了心焦了。”
“啥意思吗?”瞿团好像没听明白似的。
顺子笑着说:“嘿嘿,挣不下钱嘛。”
“你少来这一套噢顺子。我可听办公室讲,装这个台,是给你加了钱的。”瞿团又笑着说。
“加是加了,也就加了一千块,大家都骂我哩。”
瞿团当下就问:“哎,你们谁骂你顺子老板了?”
猴子急忙举手:“我骂了。”
墩子也举手说:“我也骂了。”
大家就笑了。
顺子说:“你看你看。难弄得很,都钻到钱眼里了。”
“我给你说顺子,办公室能给你加一千块,已经是破例了,你就知足吧。赶快干活儿。”说着,瞿团就要离开。
顺子又拿出了那种死缠软磨的劲儿说:“瞿团,你看大家都说您从不亏待咱下苦的,加钱不说了,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加一个鸡腿得成吗?您老亲自来这一趟,总得犒劳一下三军嘛。”
“你这个刁老板哪!不说了,中午一人加一个鸡腿,两个鸡翅,再外加一包奶。活要是干不好,顺子,我可让办公室在工钱里扣除噢。”
“您放心,瞿团,咱还得顾咱的脸哩。”
(有删改)
1.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描写颇具特色,请结合具体内容加以赏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曙光
陈敏
王丑根四年来一直是老何帮扶的对象。这个老鳏夫一开始总喜欢索取,他常常要求老何为他劈柴、挖土豆、担水,还问他要挂面、白糖、肥皂和卫生纸。
不过,王丑根除了这些毛病外,倒还有一些可爱的小优点,比如,他爱笑,见人就笑,谁问他问题,他只说一个字:“好。”他掌握了说话艺术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于是,他倒成了一个有福之人了。这一切源自他从一次事件中得来的教训。
一天,新上任的镇长微服私访,王丑根碰巧被相中,成了被访对象。
镇长问:“你脱贫了吗?”
王丑根:“还没有哩!”
镇长又问:“你啥时脱贫呢?
王丑根:“已经脱了!”
镇长:“怎么脱的?”
王丑根:“干部把眼睛往上一翻,我就脱了!”
王丑根抬头,怯生生地瞅身后站着的老何,立即改口。
这场对话上了当天的新闻头条,凡有手机的人都看到了这则令人发笑的消息。可以想象老何接下来的日子该有多么难过。
王丑根当然不知道老何所受的训斥,老何也没必要将他的委屈对牛弹琴般地讲给王丑根听,老何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气。
老何第二天把他受到的训斥加倍赏给了王丑根。
“我每月给你送的挂面让猪吃了吧?那些米、那些油都进了狗肚子了,那个啥?今后少问我要东西,今天要糖,明天要洗衣粉,后天要卫生纸,我宁肯把那些吃的用的扔到河里也不给你了!你这个吃红肉屙白屎的东西!”
王丑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赶忙嘿嘿地给老何笑,笑完又扇脸,扇嘴巴,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头部,最后又像童子军那样举起右手向老何发誓,今后再也不说错话了。老何的心就软了下来,他抱着头,在地上蹲了一阵子。
之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关系,老何想了一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送给王丑根一些蔬菜种子,让他整理门前屋后的土地,并要求他在地里种植蔬菜,那样,王丑根就可以用自己的蔬菜和他交换那些他需要的日用品。
王丑根的双手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脑袋也随之灵活了,并学会了见机行事,不管谁问他什么,他只是笑,只说个字:“好!”
一次,老何一大早又接到指令:市县各级领导要来检查贫困户家庭的卫生状况,要他做好迎接准备。老何天没亮就起来,跑去通知王丑根。
天已经大亮了,王丑根还长睡不起,鼾声大得像过山车,老何喊了几嗓子也不见王丑根回声。时间不允许他再磨蹭,看来,那家伙是指望不上,老何只好拿起扫把,亲自动手,清理王丑根房前屋后的破柴头、烂布絮、树叶、瓦渣。
打扫完毕,老何抱着膀子转悠,开始漫长的等待。周围依然没有一丝动静,不会又要放一枚空炮吧?他已经被告知过三次,可领导们并没有来,他一直处于待命状态。老何转身去村口,探听动向。
这次,“狼”真的来了!老何老远就认出了一行人中的那位“扶贫攻坚战区指挥长”。他拧过身子,赶紧往回转。
附近上空突然冒出一股浓烟,不用分辨,老何一眼判断出浓烟来自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血管中的血液翻腾,心跳加剧。
四周寂静没有风,浓烟瞬间弥漫了狭窄的山沟。
老何加快步伐,朝前跑,尽快先将火灭掉。
王丑根把老何刚才扫的那堆垃圾点燃了。
老何扛着一把铁锨,朝火堆奋力扑打,狼狈不堪的样子被各级领导们撞了个正着。
老何黑头黑脸,浑身稀脏,低着头,不敢看领导们阴着的脸。
“关键时刻,你给我脸上抹黑!”指挥长离开时斜了老何一眼。
老何用手抹了一把被烟灰熏黑了的头和脸,半天没明白:这分明是自己脸上的黑嘛,咋就抹到指挥长脸上了呢?
倒是王丑根此时得意得不得了,他“嘿嘿”地笑,不住地给每个人说“好”。
“好你个屁呀!”老何顿时怒火上涌,“嘭”的一脚,踢向王丑根额头。这个动作让他立即意识到接下来的结局。
老何连夜写了五千言的检查稿。他被要求在全镇干群大会上作深刻反思。
创卫突击检查,老何挂了,他顺便把晋升正科的机会也给丢了。
老何抽了一夜闷烟。第二天天没亮,他掐灭最后一支烟头,披着大衣,赶往王丑根住处。
黎明的曙光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走近,是王丑根。
“你干啥呀?”
“好!我到地里呀!”王丑根扛着板锄,露出一嘴白牙,给老何笑。
王丑根生平第一次勤快起来了。
老何猛一抬头,见东方露出一抹曙光,一轮红日喷薄欲出。
(原载《河洛文摘》2020年1月5日)
2.小说在叙写老何扶贫王丑根的故事时多处运用语言描写,这样处理有怎样的艺术效果?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头发的故事
鲁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①。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公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出一个国民来,挺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九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我不堪纪念这些事。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至于髡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③,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④。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N救回目光望向我,继续他的絮叨:“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N用胳膊在空中比划着手杖,说:“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债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噘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有删改)
【注】①双十节: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武昌举行反清起义,次年1月1日建立中华民国,9月2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将10月10日定为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故称“双十节”②髡(kūn):中国古代刑法分为五等,“去发”的刑不在五刑之列,但亦为刑罚之一。③扬州十日,喜定屠城;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对汉族人民进行了十天的大屠杀,是年稍后,清军攻入嘉定城,又三次大规模屠杀汉人。④拖辫子: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1644年清世祖入北京后,多次强令全国男子遵从满俗,曾引起汉人强烈反抗。
3.本文主要运用人物语言描写的手法,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其表达效果。
答案
1.①语言个性化,生动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如写顺子把“咱就是下苦的”当作口头禅,表现了他不怕辛苦、谦卑待人的性格特点。②语言口语化,生活气息浓郁。如“袖笼着双手”“咱还得顾咱的脸哩”等。③多用方言土语,地域特色鲜明。如“急煞火”挣失塌”“撂干话”等。④语言风趣幽默,善于营造轻松氛围。如“你别看顺子,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您老亲自来这一趟,总得犒劳一下三军嘛”
2.①展现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例如从开篇镇长和王丑根对话中,可以看出王丑根最初的无知;老何受到训斥之后的语言描写,反应出他内心的无奈、憋闷。
②使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干部把眼睛往上一翻,我就脱了!”“你干啥呀?”“好!我到地里呀!”王丑根由之前对扶贫工作漠不关心,只知道一味索取,发展为亲自下地干活。
③小说多用方言口语,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比如“你这个吃红肉屙白屎的东西!“”好你个屁呀!”等,增添了小说的乡土气息。
3.①便于刻画人物形象。N先生一个人“唱独角戏”,充分展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对“双十节”纪念的形式主义批判的态度更加明。②使故事情节更集中,脉络更清晰。N先生一个人叙述他的经历和感悟,赴免了他人插入的节外生枝,文章单线条展开,线索清晰明了。③使文章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N先生旁若无人式的叙述和评论,将人们形式主义的纪念活动展示得淋漓尽致,批判的态度明确而深刻,主题更加突出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装台(节选)
陈彦
顺子新婚,只在家耽误了一天一晚上,就赶到舞台上去了。十几个伙计早都来了,不过都袖笼着双手,散落在后台门口扯咸淡。
顺子说:“没看都啥时候了,非等着我来才装呀。一早瞿团长就来电话了,说今晚台必须装起,人家明天有重要接待演出呢。”
猴子说:“尽弄这急煞火的事,前天昨天,连着两天两夜给话剧团装台,今晚再给秦腔团装一夜,几天都没睡过囫囵觉了,还不把人挣失塌了。”
“猴子,你甭扰乱军心,咱就吃的这碗装台饭,不想熬夜了你喝风把屁去。都少撂干话,快上台。”顺子说着先进后台了。
猴子在后边还嘟哝说:“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加个鸡腿吧。”
顺子骂了猴子一句,吩咐了起来:“墩子,你几个吊软硬片景。大吊,你四个还装灯,瞿团长说了,要按去北京调演的灯位装,六十四台电脑灯,一百二十个回光,一个都不能少。”
大吊说:“这么短的时间,肯定装不起来。”
顺子说:“装不起也得装,人家加了钱的。猴子,上去放吊杆。”说完,自己先驮起一个灯箱,往耳光槽走去。那灯箱至少也有百十斤重,他双腿明显有些打闪,但还是颤巍巍地驮到耳光槽里去了。大伙也就跟着嘟嘟囔囔地干了起来。
刁顺子是这十几号人的老板,但从来也没人叫过他什么老板。他有个口头禅:咱就是下苦的。谁能下苦,谁就跟咱干,下不了苦,就趔远。这世上七十二行里,还不包括装台,装台是新兴行业,如果能列进第七十三行,在顺子们看来,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人家演出单位,都是白天上班排练,舞台就得晚上装好。到了白天,你也闲不下,还得在一旁伺候着,那些导演们都是脏嘴,开口骂人是家常便饭。好多装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也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现在,整个西京城,只要有装台拆台,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儿,全都找到他顺子头上了,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这样,他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但他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一喊,他就说是糟践他呢,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
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就是相对固定几个招呼人,分几个组,管管灯光,管管软硬片景,多数时候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反正啥他都带头干,账也分在明处。人家剧团给多少钱,大伙心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活儿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他多分几个,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何况顺子也不贪,总说有钱大家挣,因此,跟着他的人,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他们把这一行干得精到的,连使一个眼色,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是上吊杆还是下吊杆。瞿团长老说:“我看顺子这帮人手,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占板凳的人强多了。”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就赶忙圆场说,咱们就是下苦的,这点手艺,也还都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反正啥事都只是下苦干,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瞿团长就常常笑着说:“你别看顺子,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顺子也总是笑着回应:“下苦,咱就是个下苦的。”
他们刚吊了几片软景,瞿团长就来了。瞿团长对艺术要求很严,虽然戴着眼镜,文文气气的,但有时急了也会骂娘。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
瞿团一来就喊顺子:“哎,顺子,你们装快点噢,明天早上八点,演员乐队准时进场。误了时间,可拿你是问哟。”
顺子从灯光楼里溜下来,弄得满身的灰尘,连头发都粘满了蜘蛛网。他拍拍灰手,把灰头土脸抹了一把后说:“瞿团,您也都看见了,弟兄们干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都说跟我干活儿,算是皇上娘娘拾麦穗,就图混了心焦了。”
“啥意思吗?”瞿团好像没听明白似的。
顺子笑着说:“嘿嘿,挣不下钱嘛。”
“你少来这一套噢顺子。我可听办公室讲,装这个台,是给你加了钱的。”瞿团又笑着说。
“加是加了,也就加了一千块,大家都骂我哩。”
瞿团当下就问:“哎,你们谁骂你顺子老板了?”
猴子急忙举手:“我骂了。”
墩子也举手说:“我也骂了。”
大家就笑了。
顺子说:“你看你看。难弄得很,都钻到钱眼里了。”
“我给你说顺子,办公室能给你加一千块,已经是破例了,你就知足吧。赶快干活儿。”说着,瞿团就要离开。
顺子又拿出了那种死缠软磨的劲儿说:“瞿团,你看大家都说您从不亏待咱下苦的,加钱不说了,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加一个鸡腿得成吗?您老亲自来这一趟,总得犒劳一下三军嘛。”
“你这个刁老板哪!不说了,中午一人加一个鸡腿,两个鸡翅,再外加一包奶。活要是干不好,顺子,我可让办公室在工钱里扣除噢。”
“您放心,瞿团,咱还得顾咱的脸哩。”
(有删改)
1.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描写颇具特色,请结合具体内容加以赏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曙光
陈敏
王丑根四年来一直是老何帮扶的对象。这个老鳏夫一开始总喜欢索取,他常常要求老何为他劈柴、挖土豆、担水,还问他要挂面、白糖、肥皂和卫生纸。
不过,王丑根除了这些毛病外,倒还有一些可爱的小优点,比如,他爱笑,见人就笑,谁问他问题,他只说一个字:“好。”他掌握了说话艺术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于是,他倒成了一个有福之人了。这一切源自他从一次事件中得来的教训。
一天,新上任的镇长微服私访,王丑根碰巧被相中,成了被访对象。
镇长问:“你脱贫了吗?”
王丑根:“还没有哩!”
镇长又问:“你啥时脱贫呢?
王丑根:“已经脱了!”
镇长:“怎么脱的?”
王丑根:“干部把眼睛往上一翻,我就脱了!”
王丑根抬头,怯生生地瞅身后站着的老何,立即改口。
这场对话上了当天的新闻头条,凡有手机的人都看到了这则令人发笑的消息。可以想象老何接下来的日子该有多么难过。
王丑根当然不知道老何所受的训斥,老何也没必要将他的委屈对牛弹琴般地讲给王丑根听,老何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气。
老何第二天把他受到的训斥加倍赏给了王丑根。
“我每月给你送的挂面让猪吃了吧?那些米、那些油都进了狗肚子了,那个啥?今后少问我要东西,今天要糖,明天要洗衣粉,后天要卫生纸,我宁肯把那些吃的用的扔到河里也不给你了!你这个吃红肉屙白屎的东西!”
王丑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赶忙嘿嘿地给老何笑,笑完又扇脸,扇嘴巴,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头部,最后又像童子军那样举起右手向老何发誓,今后再也不说错话了。老何的心就软了下来,他抱着头,在地上蹲了一阵子。
之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关系,老何想了一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送给王丑根一些蔬菜种子,让他整理门前屋后的土地,并要求他在地里种植蔬菜,那样,王丑根就可以用自己的蔬菜和他交换那些他需要的日用品。
王丑根的双手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脑袋也随之灵活了,并学会了见机行事,不管谁问他什么,他只是笑,只说个字:“好!”
一次,老何一大早又接到指令:市县各级领导要来检查贫困户家庭的卫生状况,要他做好迎接准备。老何天没亮就起来,跑去通知王丑根。
天已经大亮了,王丑根还长睡不起,鼾声大得像过山车,老何喊了几嗓子也不见王丑根回声。时间不允许他再磨蹭,看来,那家伙是指望不上,老何只好拿起扫把,亲自动手,清理王丑根房前屋后的破柴头、烂布絮、树叶、瓦渣。
打扫完毕,老何抱着膀子转悠,开始漫长的等待。周围依然没有一丝动静,不会又要放一枚空炮吧?他已经被告知过三次,可领导们并没有来,他一直处于待命状态。老何转身去村口,探听动向。
这次,“狼”真的来了!老何老远就认出了一行人中的那位“扶贫攻坚战区指挥长”。他拧过身子,赶紧往回转。
附近上空突然冒出一股浓烟,不用分辨,老何一眼判断出浓烟来自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血管中的血液翻腾,心跳加剧。
四周寂静没有风,浓烟瞬间弥漫了狭窄的山沟。
老何加快步伐,朝前跑,尽快先将火灭掉。
王丑根把老何刚才扫的那堆垃圾点燃了。
老何扛着一把铁锨,朝火堆奋力扑打,狼狈不堪的样子被各级领导们撞了个正着。
老何黑头黑脸,浑身稀脏,低着头,不敢看领导们阴着的脸。
“关键时刻,你给我脸上抹黑!”指挥长离开时斜了老何一眼。
老何用手抹了一把被烟灰熏黑了的头和脸,半天没明白:这分明是自己脸上的黑嘛,咋就抹到指挥长脸上了呢?
倒是王丑根此时得意得不得了,他“嘿嘿”地笑,不住地给每个人说“好”。
“好你个屁呀!”老何顿时怒火上涌,“嘭”的一脚,踢向王丑根额头。这个动作让他立即意识到接下来的结局。
老何连夜写了五千言的检查稿。他被要求在全镇干群大会上作深刻反思。
创卫突击检查,老何挂了,他顺便把晋升正科的机会也给丢了。
老何抽了一夜闷烟。第二天天没亮,他掐灭最后一支烟头,披着大衣,赶往王丑根住处。
黎明的曙光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走近,是王丑根。
“你干啥呀?”
“好!我到地里呀!”王丑根扛着板锄,露出一嘴白牙,给老何笑。
王丑根生平第一次勤快起来了。
老何猛一抬头,见东方露出一抹曙光,一轮红日喷薄欲出。
(原载《河洛文摘》2020年1月5日)
2.小说在叙写老何扶贫王丑根的故事时多处运用语言描写,这样处理有怎样的艺术效果?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头发的故事
鲁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①。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公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出一个国民来,挺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九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我不堪纪念这些事。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至于髡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③,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④。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N救回目光望向我,继续他的絮叨:“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N用胳膊在空中比划着手杖,说:“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债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噘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有删改)
【注】①双十节: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武昌举行反清起义,次年1月1日建立中华民国,9月2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将10月10日定为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故称“双十节”②髡(kūn):中国古代刑法分为五等,“去发”的刑不在五刑之列,但亦为刑罚之一。③扬州十日,喜定屠城;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对汉族人民进行了十天的大屠杀,是年稍后,清军攻入嘉定城,又三次大规模屠杀汉人。④拖辫子: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1644年清世祖入北京后,多次强令全国男子遵从满俗,曾引起汉人强烈反抗。
3.本文主要运用人物语言描写的手法,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其表达效果。
答案
1.①语言个性化,生动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如写顺子把“咱就是下苦的”当作口头禅,表现了他不怕辛苦、谦卑待人的性格特点。②语言口语化,生活气息浓郁。如“袖笼着双手”“咱还得顾咱的脸哩”等。③多用方言土语,地域特色鲜明。如“急煞火”挣失塌”“撂干话”等。④语言风趣幽默,善于营造轻松氛围。如“你别看顺子,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您老亲自来这一趟,总得犒劳一下三军嘛”
2.①展现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例如从开篇镇长和王丑根对话中,可以看出王丑根最初的无知;老何受到训斥之后的语言描写,反应出他内心的无奈、憋闷。
②使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干部把眼睛往上一翻,我就脱了!”“你干啥呀?”“好!我到地里呀!”王丑根由之前对扶贫工作漠不关心,只知道一味索取,发展为亲自下地干活。
③小说多用方言口语,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比如“你这个吃红肉屙白屎的东西!“”好你个屁呀!”等,增添了小说的乡土气息。
3.①便于刻画人物形象。N先生一个人“唱独角戏”,充分展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对“双十节”纪念的形式主义批判的态度更加明。②使故事情节更集中,脉络更清晰。N先生一个人叙述他的经历和感悟,赴免了他人插入的节外生枝,文章单线条展开,线索清晰明了。③使文章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N先生旁若无人式的叙述和评论,将人们形式主义的纪念活动展示得淋漓尽致,批判的态度明确而深刻,主题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