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分析作者用意(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分析作者用意(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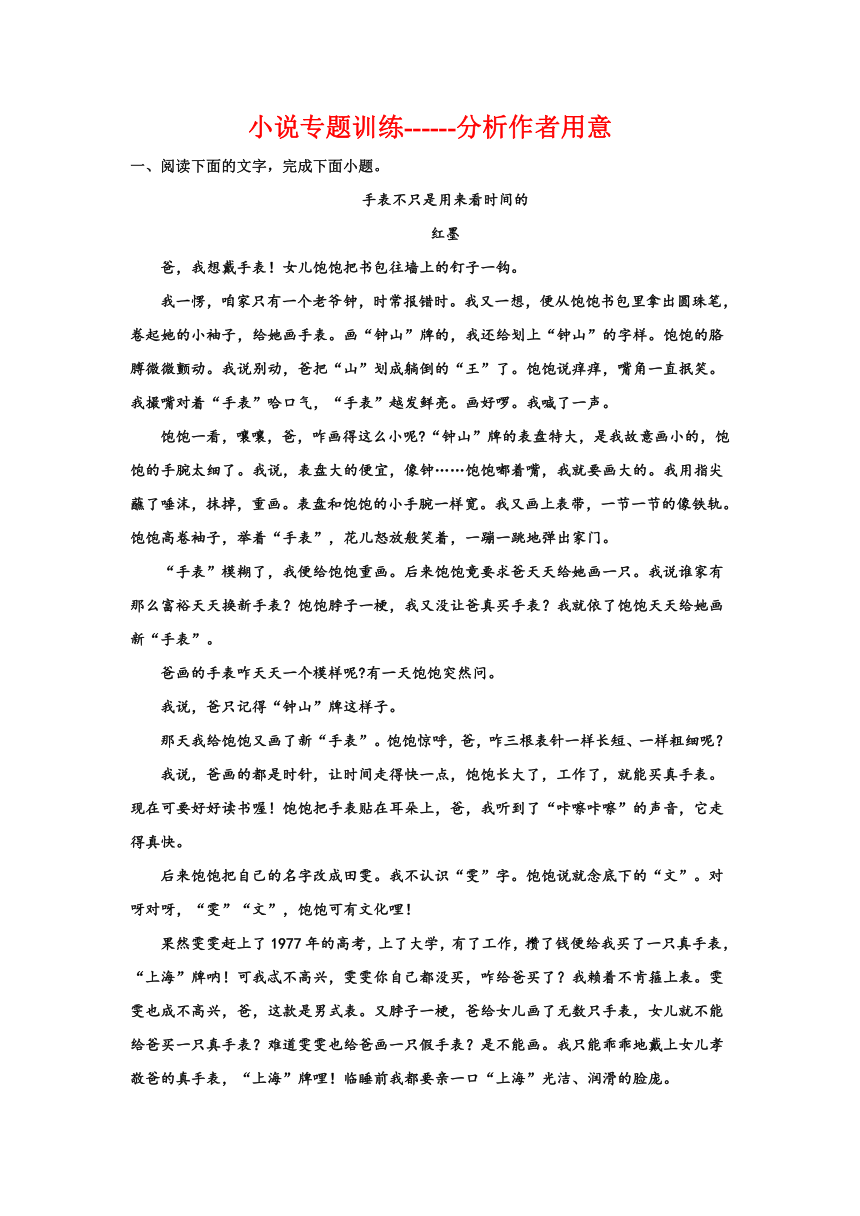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2.1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通用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4-25 17:43:33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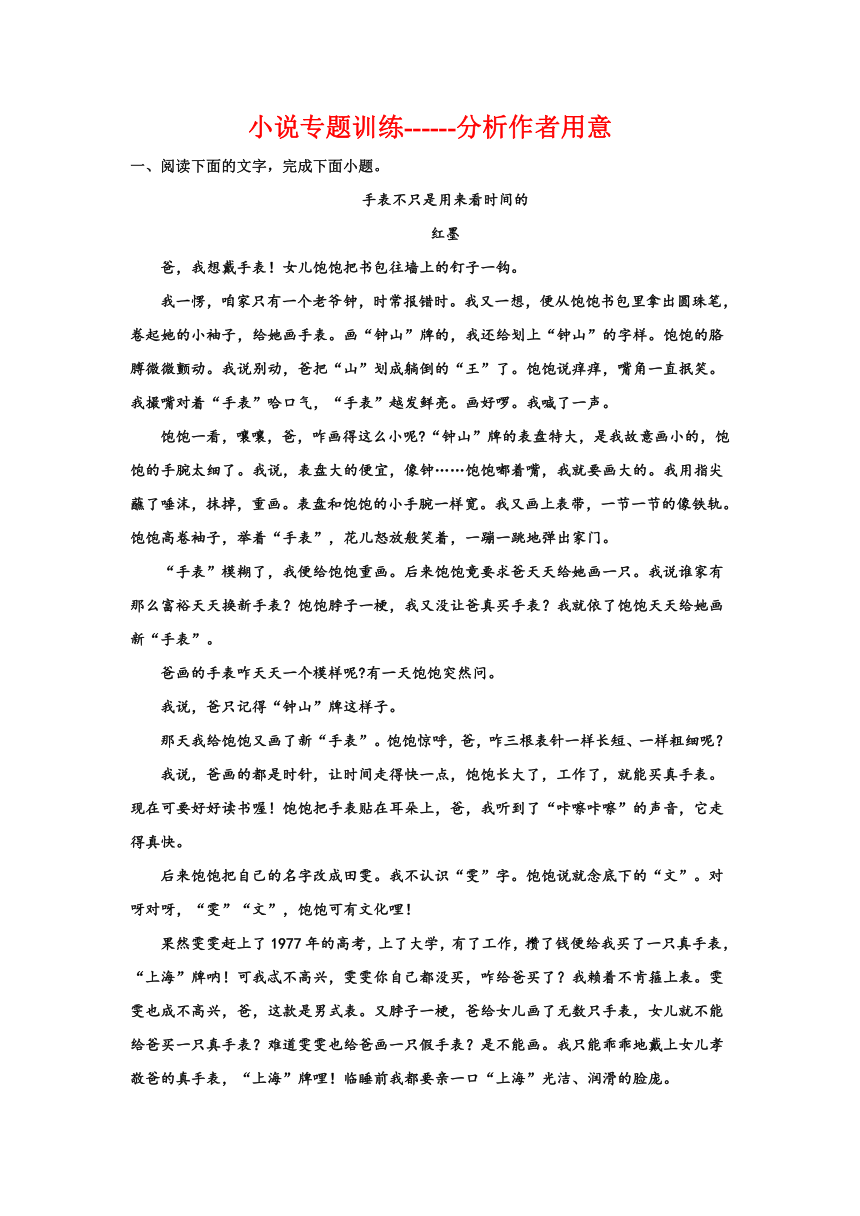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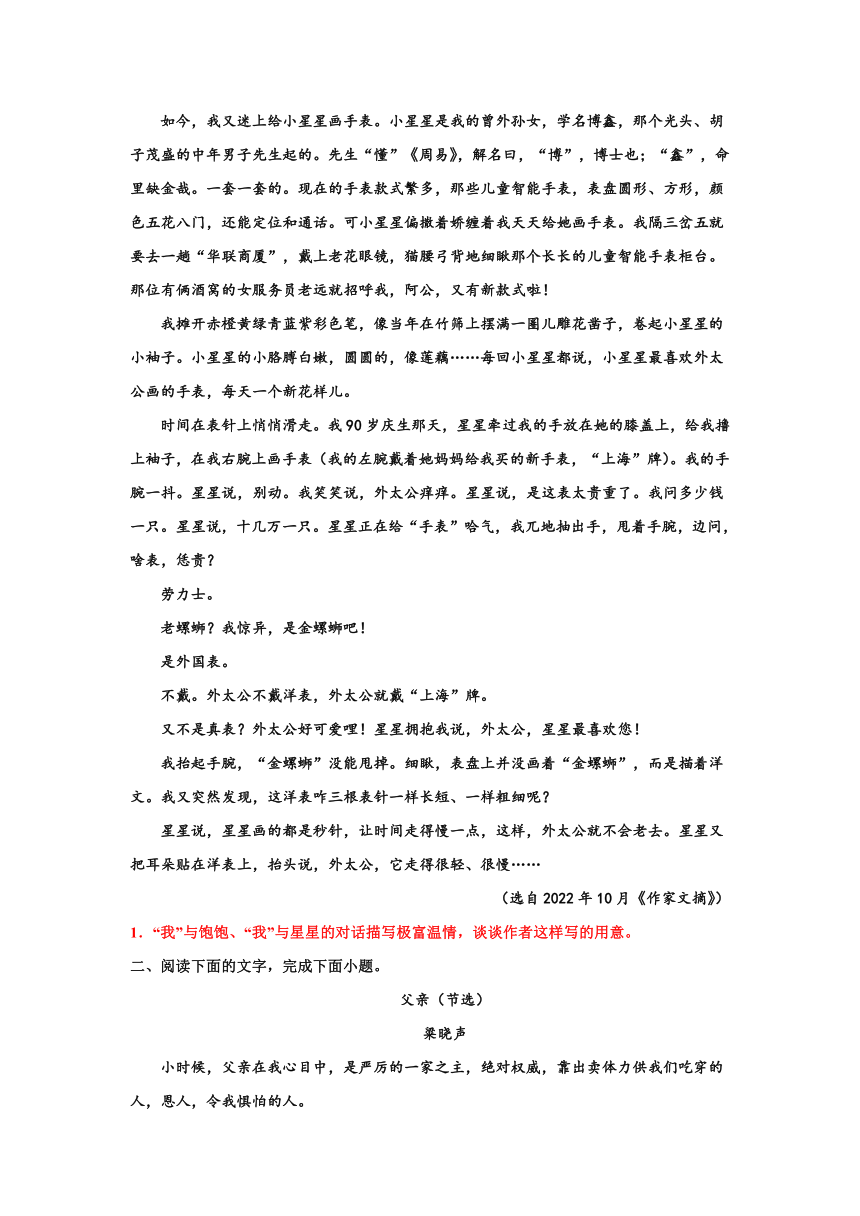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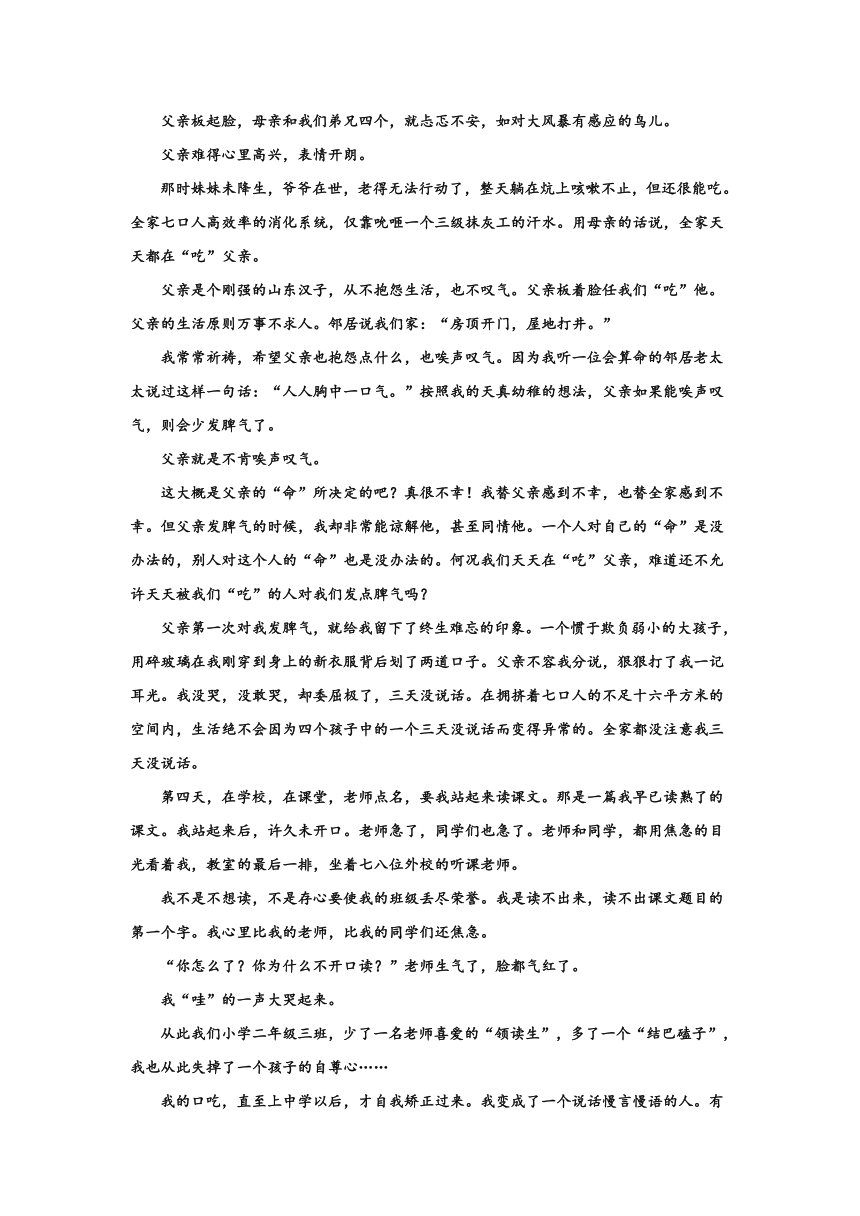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分析作者用意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手表不只是用来看时间的
红墨
爸,我想戴手表!女儿饱饱把书包往墙上的钉子一钩。
我一愣,咱家只有一个老爷钟,时常报错时。我又一想,便从饱饱书包里拿出圆珠笔,卷起她的小袖子,给她画手表。画“钟山”牌的,我还给划上“钟山”的字样。饱饱的胳膊微微颤动。我说别动,爸把“山”划成躺倒的“王”了。饱饱说痒痒,嘴角一直抿笑。我撮嘴对着“手表”哈口气,“手表”越发鲜亮。画好啰。我喊了一声。
饱饱一看,嚷嚷,爸,咋画得这么小呢 “钟山”牌的表盘特大,是我故意画小的,饱饱的手腕太细了。我说,表盘大的便宜,像钟……饱饱嘟着嘴,我就要画大的。我用指尖蘸了唾沫,抹掉,重画。表盘和饱饱的小手腕一样宽。我又画上表带,一节一节的像铁轨。饱饱高卷袖子,举着“手表”,花儿怒放般笑着,一蹦一跳地弹出家门。
“手表”模糊了,我便给饱饱重画。后来饱饱竟要求爸天天给她画一只。我说谁家有那么富裕天天换新手表?饱饱脖子一梗,我又没让爸真买手表?我就依了饱饱天天给她画新“手表”。
爸画的手表咋天天一个模样呢 有一天饱饱突然问。
我说,爸只记得“钟山”牌这样子。
那天我给饱饱又画了新“手表”。饱饱惊呼,爸,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一样粗细呢?
我说,爸画的都是时针,让时间走得快一点,饱饱长大了,工作了,就能买真手表。现在可要好好读书喔!饱饱把手表贴在耳朵上,爸,我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它走得真快。
后来饱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田雯。我不认识“雯”字。饱饱说就念底下的“文”。对呀对呀,“雯”“文”,饱饱可有文化哩!
果然雯雯赶上了1977年的高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攒了钱便给我买了一只真手表,“上海”牌呐!可我忒不高兴,雯雯你自己都没买,咋给爸买了?我赖着不肯箍上表。雯雯也成不高兴,爸,这款是男式表。又脖子一梗,爸给女儿画了无数只手表,女儿就不能给爸买一只真手表?难道雯雯也给爸画一只假手表?是不能画。我只能乖乖地戴上女儿孝敬爸的真手表,“上海”牌哩!临睡前我都要亲一口“上海”光洁、润滑的脸庞。
如今,我又迷上给小星星画手表。小星星是我的曾外孙女,学名博鑫,那个光头、胡子茂盛的中年男子先生起的。先生“懂”《周易》,解名曰,“博”,博士也;“鑫”,命里缺金哉。一套一套的。现在的手表款式繁多,那些儿童智能手表,表盘圆形、方形,颜色五花八门,还能定位和通话。可小星星偏撒着娇缠着我天天给她画手表。我隔三岔五就要去一趟“华联商厦”,戴上老花眼镜,猫腰弓背地细瞅那个长长的儿童智能手表柜台。那位有俩酒窝的女服务员老远就招呼我,阿公,又有新款式啦!
我摊开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色笔,像当年在竹筛上摆满一圈儿雕花凿子,卷起小星星的小袖子。小星星的小胳膊白嫩,圆圆的,像莲藕……每回小星星都说,小星星最喜欢外太公画的手表,每天一个新花样儿。
时间在表针上悄悄滑走。我90岁庆生那天,星星牵过我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给我撸上袖子,在我右腕上画手表(我的左腕戴着她妈妈给我买的新手表,“上海”牌)。我的手腕一抖。星星说,别动。我笑笑说,外太公痒痒。星星说,是这表太贵重了。我问多少钱一只。星星说,十几万一只。星星正在给“手表”哈气,我兀地抽出手,甩着手腕,边问,啥表,恁贵?
劳力士。
老螺蛳?我惊异,是金螺蛳吧!
是外国表。
不戴。外太公不戴洋表,外太公就戴“上海”牌。
又不是真表?外太公好可爱哩!星星拥抱我说,外太公,星星最喜欢您!
我抬起手腕,“金螺蛳”没能甩掉。细瞅,表盘上并没画着“金螺蛳”,而是描着洋文。我又突然发现,这洋表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一样粗细呢?
星星说,星星画的都是秒针,让时间走得慢一点,这样,外太公就不会老去。星星又把耳朵贴在洋表上,抬头说,外太公,它走得很轻、很慢……
(选自2022年10月《作家文摘》)
1.“我”与饱饱、“我”与星星的对话描写极富温情,谈谈作者这样写的用意。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父亲(节选)
粱晓声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们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呛,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我饭量大了,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克”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2.文中画线句连用三个整齐的短句并都以“了”字结尾,简要分析作者这样处理的用意。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出山
蒋子龙
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两天前已经通知到各委员了,霍大道知道委员们都有准备好的话,只等头一炮打响,后边就会万炮齐鸣。他却丝毫不动声色,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去点第一炮,而是让炮手准备好了自己燃响,更不在冷场时赔着笑脸絮絮叨叨地启发诱导。他透彻人肺腑的目光,时而收拢合目沉思,时而又放纵开来,轻轻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有一张脸渐渐吸引住霍大道的目光。这是一张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他是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
乔光朴没抬眼皮,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别人不说我先说,请局党委考虑,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
这低沉的声调在有些委员的心里不啻是爆炸了一颗手榴弹。徐副局长更是惊诧地掏出一支香烟主动地丢给乔光朴:“光朴,你是真的,还是开玩笑?”
是啊,他的请求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现在占的位子太好了。“公司经理”——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可攻可守。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愿干者可以多劳,不愿干者也可少干,全无凭据;权力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这是许多老干部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手的“美缺”。乔光朴放着轻车熟路不走,明知现在基层的经最不好念,为什么偏要下去呢?
乔光朴抬起眼睛,闪电似的扫过全场,最后和霍大道那穿透一切的目光相遇了,倏地这两对目光碰出了心里的火花,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乔光朴仍是用缓慢平稳的语气说:“我愿立军令状。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
乔光朴的“军令状”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更叫霍大道高兴。他激赏地抬起眼睛,心里想,这位大爷就是给他一座山也能背走,正像俗话说的,他像脚后跟一样可靠,你尽管相信他好了。就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乔光朴:“我要请石敢一块去,他当党委书记,我当厂长。”
石敢却是长时间地不吃声,探究的、陌生的目光冷冷地盯着乔光朴,使乔光朴很不自在。老朋友对他的疏远和不信任叫他心打寒战。石敢到底说话了,语言低沉而又含混不清,乔光朴费劲地听着:
“你何苦要拉一个垫背的?我不去。”石敢躲开了乔光朴的目光,他碰上一面无情的能照见灵魂的镜子,他看见自己的灵魂变得这样卑微,感到吃惊,甚至不愿意承认。
乔光朴用嘲讽的口吻,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一种讽刺,‘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道路也打开了,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瞧瞧我们这些区局级、县团级干部都是什么精神状态吧,有的装聋作哑,甚至被点将点到头上,还推三阻四。我真纳闷,在我们这些级别不算小的干部身上,究竟还有没有普通党员的责任感?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这本来是极平常的,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谁知道呢,也许人家还把我当成了傻瓜哩!”石敢又一次被刺疼了,他的肩头抖动了一下。乔光朴看见了,诚恳地说:“老石,你非跟我去不行,我就是用绳子拖也得把你拖去。”
“咳,大个子……”石敢叹了口气,用了他对乔光朴最亲热的称呼。这声“大个子”叫得乔光朴发冷的心突地又热起来了。石敢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冷漠的神情:“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以后不后悔。不过丑话说在前边,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什么时候你讨厌我了,就放我回干校。”
(节选自《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3.请简要概括乔光朴为“出山”做了哪些努力。作者写这些情节有何用意?
答案
1.①用对话串联故事,紧紧围绕画手表展开,情节上前后呼应,同时照应标题,使整篇文章结构完整,如两次画手表过程中的“痒痒”以及“表针一样粗细”等相互伏笔照应。
②细节描写,人物刻画鲜活生动。开头写爸爸画的都是时针,希望时间走得快一些,希望孩子快点长大,懂事,体现“我”对女儿的爱;结尾写曾外孙女画的都是秒针,让时间走得慢一些,希望外太公不会老去,体现她懂得知恩图报。
③小说通过画手表过程中的对话描写,表现了几代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场景,老一辈关爱后辈、后辈反哺老辈的传统美德,暗示家庭和睦、亲情温暖、敬老爱幼的主题。
④对话描写为全文增添温馨美好的生活情景,浓郁的亲情深深吸引并打动读者,具有感染力,引人入胜。
2.①连用短句,意在表明生活中的意外波折来势迅疾,接连不断,让人措手不及。
②都用“了”字结尾,表示结果之意,意在揭示这些意外给我们带来的苦难,表现我们内心的悲痛与无奈。
3.(1)努力:①立下“军令状”,如电机厂完成不了国家计划,请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②邀请石敢一起赴任,并让其担任党委书记,自己担任厂长。
(2)用意:内容上表现了乔光朴的果敢和坚毅;结构上为结尾的情节陡转蓄势,突出出乎意料的效果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手表不只是用来看时间的
红墨
爸,我想戴手表!女儿饱饱把书包往墙上的钉子一钩。
我一愣,咱家只有一个老爷钟,时常报错时。我又一想,便从饱饱书包里拿出圆珠笔,卷起她的小袖子,给她画手表。画“钟山”牌的,我还给划上“钟山”的字样。饱饱的胳膊微微颤动。我说别动,爸把“山”划成躺倒的“王”了。饱饱说痒痒,嘴角一直抿笑。我撮嘴对着“手表”哈口气,“手表”越发鲜亮。画好啰。我喊了一声。
饱饱一看,嚷嚷,爸,咋画得这么小呢 “钟山”牌的表盘特大,是我故意画小的,饱饱的手腕太细了。我说,表盘大的便宜,像钟……饱饱嘟着嘴,我就要画大的。我用指尖蘸了唾沫,抹掉,重画。表盘和饱饱的小手腕一样宽。我又画上表带,一节一节的像铁轨。饱饱高卷袖子,举着“手表”,花儿怒放般笑着,一蹦一跳地弹出家门。
“手表”模糊了,我便给饱饱重画。后来饱饱竟要求爸天天给她画一只。我说谁家有那么富裕天天换新手表?饱饱脖子一梗,我又没让爸真买手表?我就依了饱饱天天给她画新“手表”。
爸画的手表咋天天一个模样呢 有一天饱饱突然问。
我说,爸只记得“钟山”牌这样子。
那天我给饱饱又画了新“手表”。饱饱惊呼,爸,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一样粗细呢?
我说,爸画的都是时针,让时间走得快一点,饱饱长大了,工作了,就能买真手表。现在可要好好读书喔!饱饱把手表贴在耳朵上,爸,我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它走得真快。
后来饱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田雯。我不认识“雯”字。饱饱说就念底下的“文”。对呀对呀,“雯”“文”,饱饱可有文化哩!
果然雯雯赶上了1977年的高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攒了钱便给我买了一只真手表,“上海”牌呐!可我忒不高兴,雯雯你自己都没买,咋给爸买了?我赖着不肯箍上表。雯雯也成不高兴,爸,这款是男式表。又脖子一梗,爸给女儿画了无数只手表,女儿就不能给爸买一只真手表?难道雯雯也给爸画一只假手表?是不能画。我只能乖乖地戴上女儿孝敬爸的真手表,“上海”牌哩!临睡前我都要亲一口“上海”光洁、润滑的脸庞。
如今,我又迷上给小星星画手表。小星星是我的曾外孙女,学名博鑫,那个光头、胡子茂盛的中年男子先生起的。先生“懂”《周易》,解名曰,“博”,博士也;“鑫”,命里缺金哉。一套一套的。现在的手表款式繁多,那些儿童智能手表,表盘圆形、方形,颜色五花八门,还能定位和通话。可小星星偏撒着娇缠着我天天给她画手表。我隔三岔五就要去一趟“华联商厦”,戴上老花眼镜,猫腰弓背地细瞅那个长长的儿童智能手表柜台。那位有俩酒窝的女服务员老远就招呼我,阿公,又有新款式啦!
我摊开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色笔,像当年在竹筛上摆满一圈儿雕花凿子,卷起小星星的小袖子。小星星的小胳膊白嫩,圆圆的,像莲藕……每回小星星都说,小星星最喜欢外太公画的手表,每天一个新花样儿。
时间在表针上悄悄滑走。我90岁庆生那天,星星牵过我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给我撸上袖子,在我右腕上画手表(我的左腕戴着她妈妈给我买的新手表,“上海”牌)。我的手腕一抖。星星说,别动。我笑笑说,外太公痒痒。星星说,是这表太贵重了。我问多少钱一只。星星说,十几万一只。星星正在给“手表”哈气,我兀地抽出手,甩着手腕,边问,啥表,恁贵?
劳力士。
老螺蛳?我惊异,是金螺蛳吧!
是外国表。
不戴。外太公不戴洋表,外太公就戴“上海”牌。
又不是真表?外太公好可爱哩!星星拥抱我说,外太公,星星最喜欢您!
我抬起手腕,“金螺蛳”没能甩掉。细瞅,表盘上并没画着“金螺蛳”,而是描着洋文。我又突然发现,这洋表咋三根表针一样长短、一样粗细呢?
星星说,星星画的都是秒针,让时间走得慢一点,这样,外太公就不会老去。星星又把耳朵贴在洋表上,抬头说,外太公,它走得很轻、很慢……
(选自2022年10月《作家文摘》)
1.“我”与饱饱、“我”与星星的对话描写极富温情,谈谈作者这样写的用意。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父亲(节选)
粱晓声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们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呛,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我饭量大了,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克”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2.文中画线句连用三个整齐的短句并都以“了”字结尾,简要分析作者这样处理的用意。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出山
蒋子龙
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两天前已经通知到各委员了,霍大道知道委员们都有准备好的话,只等头一炮打响,后边就会万炮齐鸣。他却丝毫不动声色,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去点第一炮,而是让炮手准备好了自己燃响,更不在冷场时赔着笑脸絮絮叨叨地启发诱导。他透彻人肺腑的目光,时而收拢合目沉思,时而又放纵开来,轻轻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有一张脸渐渐吸引住霍大道的目光。这是一张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他是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
乔光朴没抬眼皮,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别人不说我先说,请局党委考虑,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
这低沉的声调在有些委员的心里不啻是爆炸了一颗手榴弹。徐副局长更是惊诧地掏出一支香烟主动地丢给乔光朴:“光朴,你是真的,还是开玩笑?”
是啊,他的请求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现在占的位子太好了。“公司经理”——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可攻可守。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愿干者可以多劳,不愿干者也可少干,全无凭据;权力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这是许多老干部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手的“美缺”。乔光朴放着轻车熟路不走,明知现在基层的经最不好念,为什么偏要下去呢?
乔光朴抬起眼睛,闪电似的扫过全场,最后和霍大道那穿透一切的目光相遇了,倏地这两对目光碰出了心里的火花,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乔光朴仍是用缓慢平稳的语气说:“我愿立军令状。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
乔光朴的“军令状”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更叫霍大道高兴。他激赏地抬起眼睛,心里想,这位大爷就是给他一座山也能背走,正像俗话说的,他像脚后跟一样可靠,你尽管相信他好了。就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乔光朴:“我要请石敢一块去,他当党委书记,我当厂长。”
石敢却是长时间地不吃声,探究的、陌生的目光冷冷地盯着乔光朴,使乔光朴很不自在。老朋友对他的疏远和不信任叫他心打寒战。石敢到底说话了,语言低沉而又含混不清,乔光朴费劲地听着:
“你何苦要拉一个垫背的?我不去。”石敢躲开了乔光朴的目光,他碰上一面无情的能照见灵魂的镜子,他看见自己的灵魂变得这样卑微,感到吃惊,甚至不愿意承认。
乔光朴用嘲讽的口吻,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一种讽刺,‘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道路也打开了,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瞧瞧我们这些区局级、县团级干部都是什么精神状态吧,有的装聋作哑,甚至被点将点到头上,还推三阻四。我真纳闷,在我们这些级别不算小的干部身上,究竟还有没有普通党员的责任感?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这本来是极平常的,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谁知道呢,也许人家还把我当成了傻瓜哩!”石敢又一次被刺疼了,他的肩头抖动了一下。乔光朴看见了,诚恳地说:“老石,你非跟我去不行,我就是用绳子拖也得把你拖去。”
“咳,大个子……”石敢叹了口气,用了他对乔光朴最亲热的称呼。这声“大个子”叫得乔光朴发冷的心突地又热起来了。石敢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冷漠的神情:“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以后不后悔。不过丑话说在前边,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什么时候你讨厌我了,就放我回干校。”
(节选自《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3.请简要概括乔光朴为“出山”做了哪些努力。作者写这些情节有何用意?
答案
1.①用对话串联故事,紧紧围绕画手表展开,情节上前后呼应,同时照应标题,使整篇文章结构完整,如两次画手表过程中的“痒痒”以及“表针一样粗细”等相互伏笔照应。
②细节描写,人物刻画鲜活生动。开头写爸爸画的都是时针,希望时间走得快一些,希望孩子快点长大,懂事,体现“我”对女儿的爱;结尾写曾外孙女画的都是秒针,让时间走得慢一些,希望外太公不会老去,体现她懂得知恩图报。
③小说通过画手表过程中的对话描写,表现了几代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场景,老一辈关爱后辈、后辈反哺老辈的传统美德,暗示家庭和睦、亲情温暖、敬老爱幼的主题。
④对话描写为全文增添温馨美好的生活情景,浓郁的亲情深深吸引并打动读者,具有感染力,引人入胜。
2.①连用短句,意在表明生活中的意外波折来势迅疾,接连不断,让人措手不及。
②都用“了”字结尾,表示结果之意,意在揭示这些意外给我们带来的苦难,表现我们内心的悲痛与无奈。
3.(1)努力:①立下“军令状”,如电机厂完成不了国家计划,请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②邀请石敢一起赴任,并让其担任党委书记,自己担任厂长。
(2)用意:内容上表现了乔光朴的果敢和坚毅;结构上为结尾的情节陡转蓄势,突出出乎意料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