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小说首段环境描写的作用(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小说首段环境描写的作用(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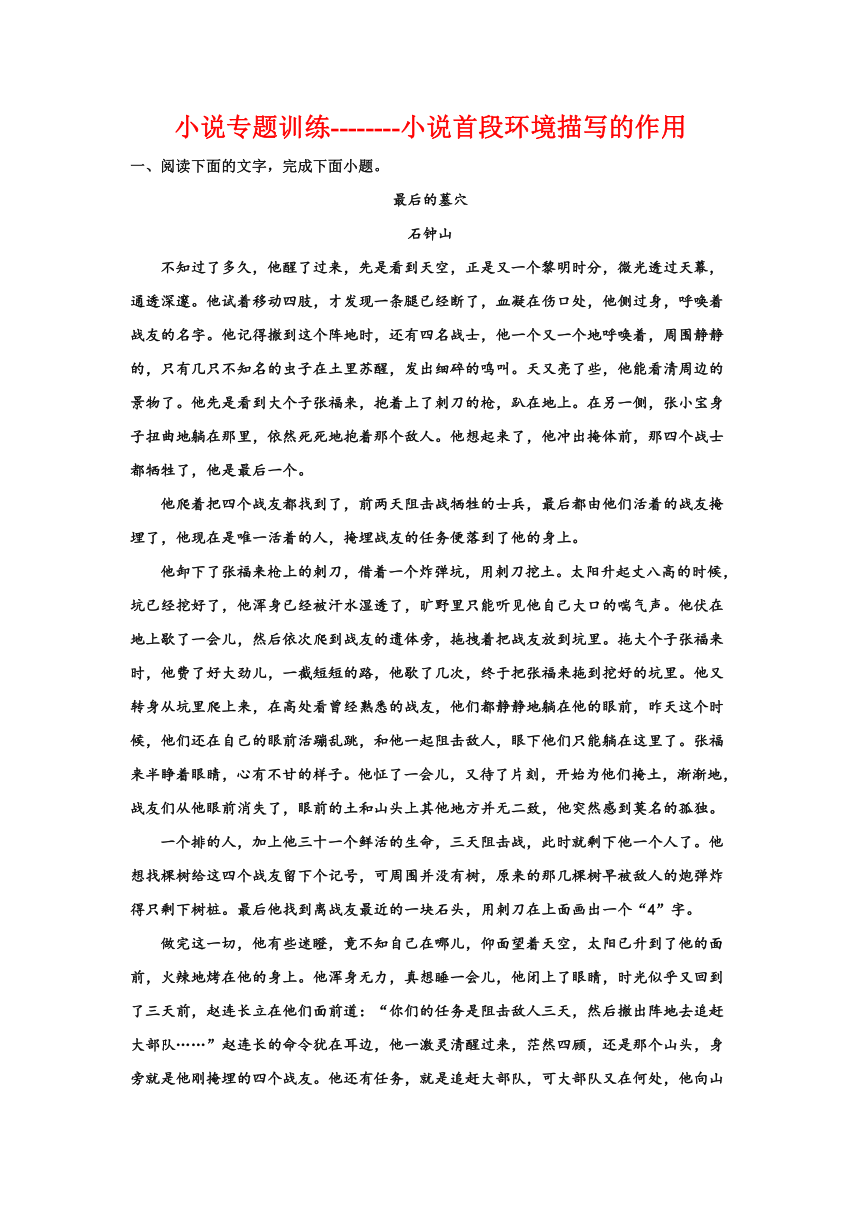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1.4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通用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5-04 17:59:58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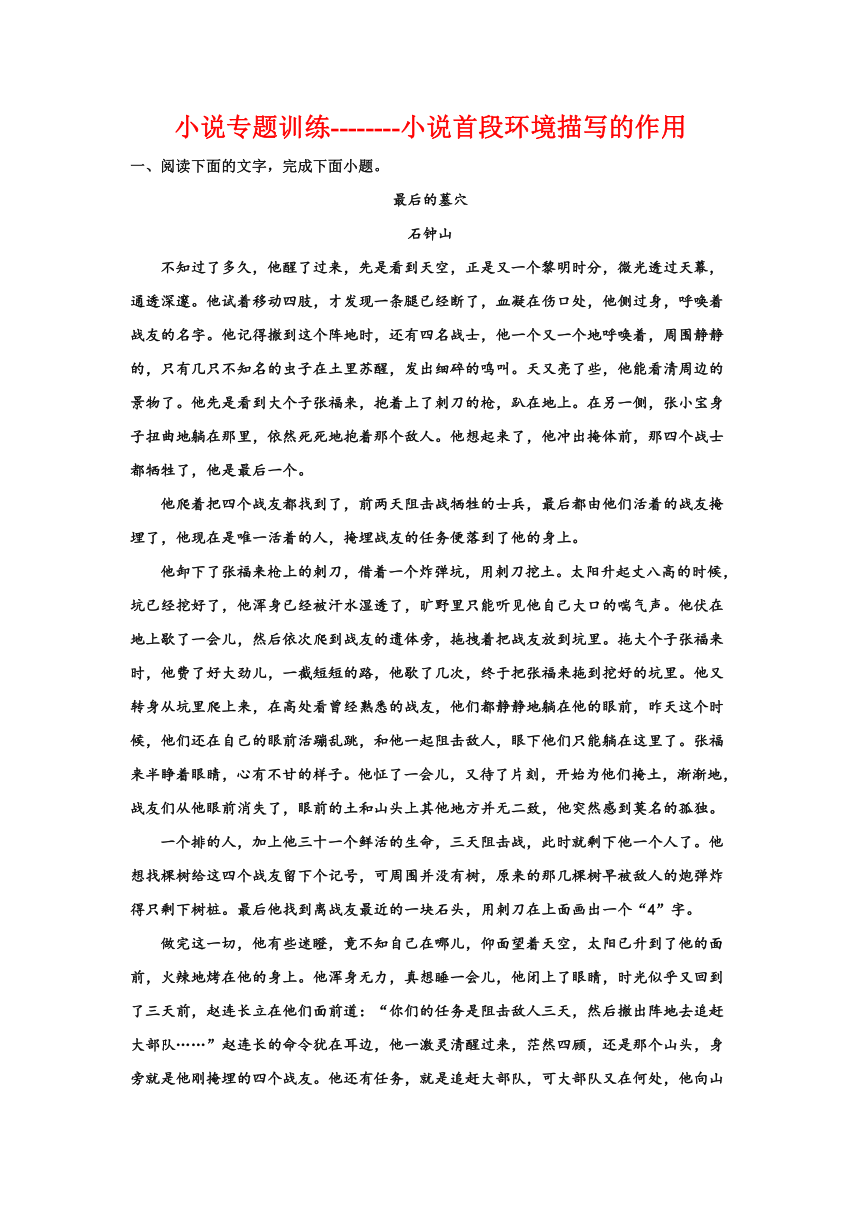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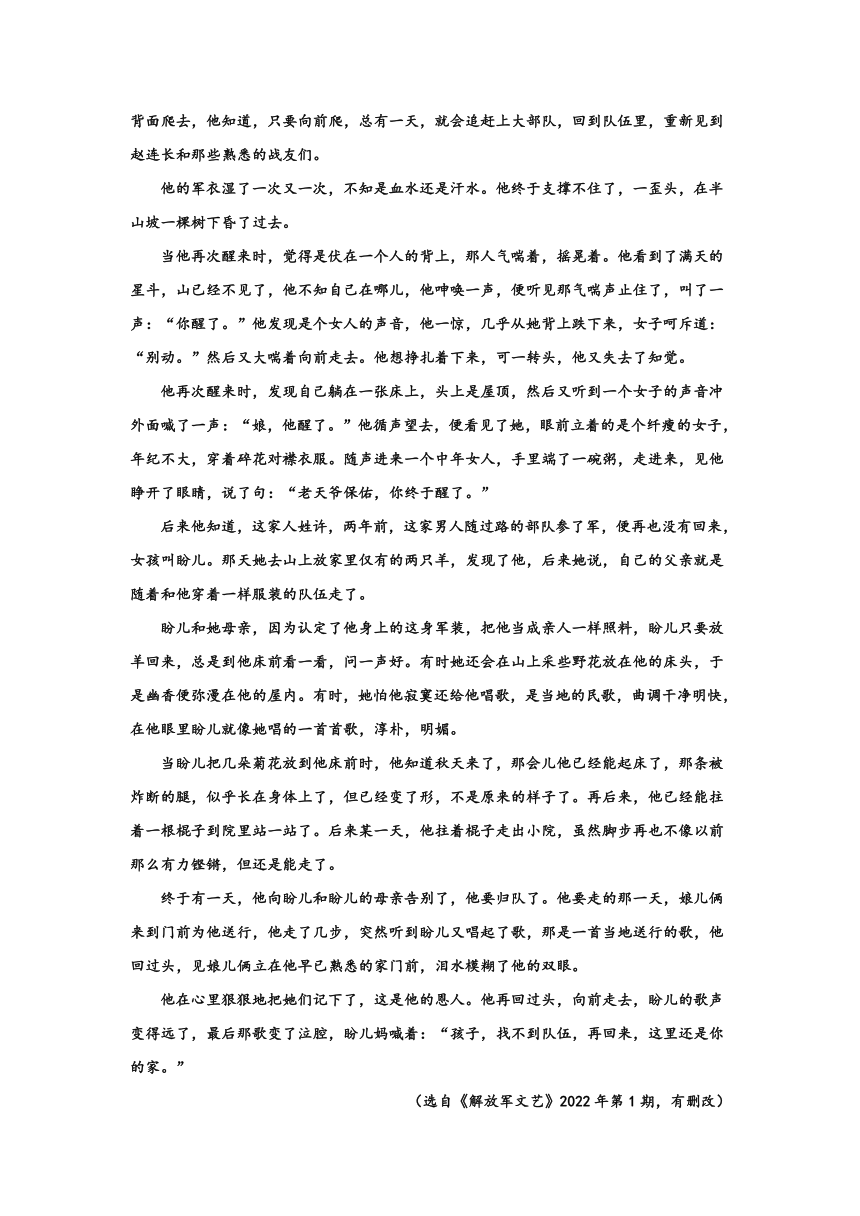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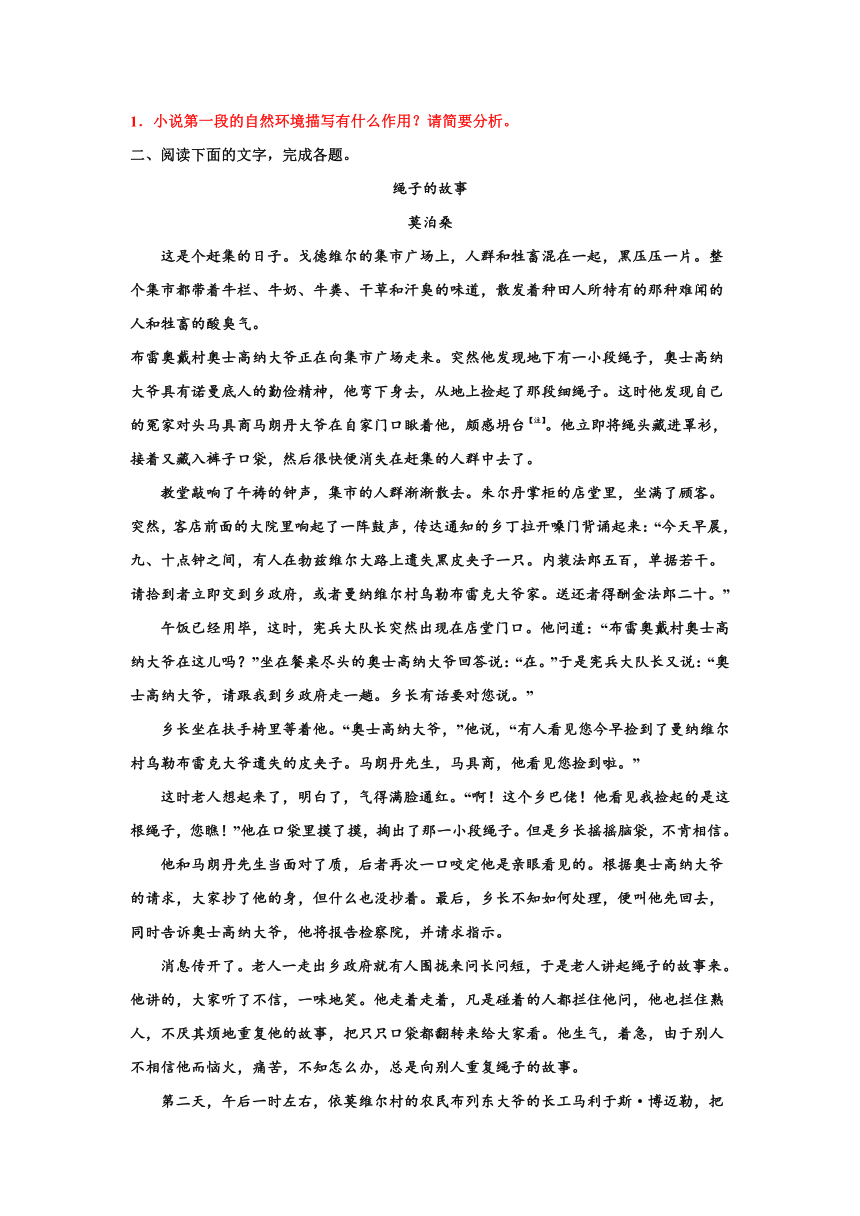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小说首段环境描写的作用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后的墓穴
石钟山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先是看到天空,正是又一个黎明时分,微光透过天幕,通透深邃。他试着移动四肢,才发现一条腿已经断了,血凝在伤口处,他侧过身,呼唤着战友的名字。他记得撤到这个阵地时,还有四名战士,他一个又一个地呼唤着,周围静静的,只有几只不知名的虫子在土里苏醒,发出细碎的鸣叫。天又亮了些,他能看清周边的景物了。他先是看到大个子张福来,抱着上了刺刀的枪,趴在地上。在另一侧,张小宝身子扭曲地躺在那里,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敌人。他想起来了,他冲出掩体前,那四个战士都牺牲了,他是最后一个。
他爬着把四个战友都找到了,前两天阻击战牺牲的士兵,最后都由他们活着的战友掩埋了,他现在是唯一活着的人,掩埋战友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身上。
他卸下了张福来枪上的刺刀,借着一个炸弹坑,用刺刀挖土。太阳升起丈八高的时候,坑已经挖好了,他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旷野里只能听见他自己大口的喘气声。他伏在地上歇了一会儿,然后依次爬到战友的遗体旁,拖拽着把战友放到坑里。拖大个子张福来时,他费了好大劲儿,一截短短的路,他歇了几次,终于把张福来拖到挖好的坑里。他又转身从坑里爬上来,在高处看曾经熟悉的战友,他们都静静地躺在他的眼前,昨天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自己的眼前活蹦乱跳,和他一起阻击敌人,眼下他们只能躺在这里了。张福来半睁着眼睛,心有不甘的样子。他怔了一会儿,又待了片刻,开始为他们掩土,渐渐地,战友们从他眼前消失了,眼前的土和山头上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他突然感到莫名的孤独。
一个排的人,加上他三十一个鲜活的生命,三天阻击战,此时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想找棵树给这四个战友留下个记号,可周围并没有树,原来的那几棵树早被敌人的炮弹炸得只剩下树桩。最后他找到离战友最近的一块石头,用刺刀在上面画出一个“4”字。
做完这一切,他有些迷瞪,竟不知自己在哪儿,仰面望着天空,太阳已升到了他的面前,火辣地烤在他的身上。他浑身无力,真想睡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时光似乎又回到了三天前,赵连长立在他们面前道:“你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三天,然后撤出阵地去追赶大部队……”赵连长的命令犹在耳边,他一激灵清醒过来,茫然四顾,还是那个山头,身旁就是他刚掩埋的四个战友。他还有任务,就是追赶大部队,可大部队又在何处,他向山背面爬去,他知道,只要向前爬,总有一天,就会追赶上大部队,回到队伍里,重新见到赵连长和那些熟悉的战友们。
他的军衣湿了一次又一次,不知是血水还是汗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一歪头,在半山坡一棵树下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觉得是伏在一个人的背上,那人气喘着,摇晃着。他看到了满天的星斗,山已经不见了,他不知自己在哪儿,他呻唤一声,便听见那气喘声止住了,叫了一声:“你醒了。”他发现是个女人的声音,他一惊,几乎从她背上跌下来,女子呵斥道:“别动。”然后又大喘着向前走去。他想挣扎着下来,可一转头,他又失去了知觉。
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头上是屋顶,然后又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冲外面喊了一声:“娘,他醒了。”他循声望去,便看见了她,眼前立着的是个纤瘦的女子,年纪不大,穿着碎花对襟衣服。随声进来一个中年女人,手里端了一碗粥,走进来,见他睁开了眼睛,说了句:“老天爷保佑,你终于醒了。”
后来他知道,这家人姓许,两年前,这家男人随过路的部队参了军,便再也没有回来,女孩叫盼儿。那天她去山上放家里仅有的两只羊,发现了他,后来她说,自己的父亲就是随着和他穿着一样服装的队伍走了。
盼儿和她母亲,因为认定了他身上的这身军装,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照料,盼儿只要放羊回来,总是到他床前看一看,问一声好。有时她还会在山上采些野花放在他的床头,于是幽香便弥漫在他的屋内。有时,她怕他寂寞还给他唱歌,是当地的民歌,曲调干净明快,在他眼里盼儿就像她唱的一首首歌,淳朴,明媚。
当盼儿把几朵菊花放到他床前时,他知道秋天来了,那会儿他已经能起床了,那条被炸断的腿,似乎长在身体上了,但已经变了形,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再后来,他已经能拄着一根棍子到院里站一站了。后来某一天,他拄着棍子走出小院,虽然脚步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力铿锵,但还是能走了。
终于有一天,他向盼儿和盼儿的母亲告别了,他要归队了。他要走的那一天,娘儿俩来到门前为他送行,他走了几步,突然听到盼儿又唱起了歌,那是一首当地送行的歌,他回过头,见娘儿俩立在他早已熟悉的家门前,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他在心里狠狠地把她们记下了,这是他的恩人。他再回过头,向前走去,盼儿的歌声变得远了,最后那歌变了泣腔,盼儿妈喊着:“孩子,找不到队伍,再回来,这里还是你的家。”
(选自《解放军文艺》2022年第1期,有删改)
1.小说第一段的自然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坍台【注】。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的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注】坍台:方言,丢脸。
2.小说中第一段的环境描写在文中有何作用?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岩(节选)
罗广斌、杨益言
乱哄哄的茶园里,坐满了人。穿西服的、穿军服的、穿长袍马褂的顾客,不断地进进出出。这家设备舒适的高级茶园,向来是座无虚设的。每当星期天,更是拥挤不堪。到这里喝茶的,不仅有嗜爱品茗的名流、社会闻人和衣着华丽的男女,还有那些习惯在茶馆里了解行情、进行交易的掮客与富商、政界人物与银行家。喜欢在浑浊的人潮中消磨时光的人,也在这里约会、聚谈、互相传播琐事轶闻,纵谈天下大事。那些高谈阔论、嬉笑怒骂的声音,加上茶碗茶碟叮叮当当的响声,应接不暇的茶房的喊声,叫卖香烟、瓜子、画报、杂志的嘈杂声,有时还混进一些吆喝乞丐的骂声,融汇成一片人声鼎沸、五光十色的闹市气氛,与那墙头上冷落地贴着叫人缄默的“休谈国事”的招贴,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和讽刺。
此刻,在纷杂的茶座之间,有两位顾客,正靠着一张精巧的茶桌,对面坐着。一个是戴墨框眼镜、穿咖啡色西服的李敬原,另一个穿蓝长袍的是许云峰。他们混迹在人海般的茶园里,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这种环境,正是地下工作者常常用来碰头和商谈某些工作的好地方。
昨天晚上和甫志高分手以后,许云峰到沙磁区委书记家里过了一夜,和他交换了意见,部署了有关人员的转移计划。
今天一早,沙磁区委书记便赶往沙坪坝去了。九点正,许云峰来到新生市场内的这座茶馆,准时会到了几天前约定在这里碰面的川东特委的李敬原,马上向他汇报了昨天晚上到沙坪书店时发现的危险,以及和甫志高谈话等情况。李敬原听了也感到意外,并且认为情况的确严重。
桌上摆的五香瓜子,已经嗑了不少。老许的手指轻敲着茶碗,外貌颇为悠闲地喊茶房来冲开水。等茶房冲过开水以后,李敬原习惯地摸了一下眼镜,耳语告诉老许:“今早上到区里去,发觉他们在转移!原来是你连夜关照的,这很及时。”
许云峰点点头,也低声问道:“区里发现了新的情况吗?”
“陈松林大概脱离危险了。”李敬原沉着地说,“区上发现,深夜里沙坪书店附近出现过形迹可疑的人……”
李敬原说这话时毫无表情,然而目光却犀利地在镜框里闪动。“照你刚才谈的情况看来,敌人昨天晚上果然动手了,这一次真是危险!”
听到李敬原谈的情况,许云峰对目前的形势感到更加严重了。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和及时防止了破坏,并不能使他高兴,相反地,他感到内疚。把备用联络站交给甫志高管,这是一种不应有的疏忽。过去虽然发现甫志高的许多毛病,但今天看来,对他的问题还是认识不足,这种人,即使一时有再好的表现,也是不能相信的。许云峰瞧了一下李敬原,他正吐着浓烟,仍然是那样的从容镇定,使许云峰明显地感到,不管风浪再大,他永远也不会张皇失措的。
茶馆里人来人往,经常打断他们的谈话。他们并不觉得厌烦,反而感到安全。
许云峰的思想飞快地发展着,他立刻联想到昨天晚上小陈谈的重要线索:黎纪纲这个危险人物,突然冒雨在书店出现,并且叫走了郑克昌,这就是敌人动手的征兆!老李说的深夜里在沙坪书店附近发现可疑的人,便是斗争的明朗化!
老许放开了思路,答道:“这是一次教训,我们考虑一下,还有什么漏洞?万一老甫昨晚上回家去?”
李敬原忽然问道:“你和他约在什么地方见面?”
“心心咖啡店。”
李敬原深思了一下,不安地说:“离这儿太近了……”
许云峰付过茶资,看看表,还不到十点钟。他随手捡起茶桌上的报纸,正要起身。可是这时,李敬原突然回到桌边,低声喊道:“老许!”
许云峰抬头,正遇到李敬原不安的眼色。
“外边有便衣特务!”
许云峰扭头向外察看,只见茶园门口,人丛里夹杂着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再往门外一望,一眼看出:便衣特务封锁了商场的所有通路。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
李敬原侧目斜视,也清楚地看见敌特的搜索圈正向商场内紧缩过来。情势十分紧迫、危险。李敬原毫不迟疑地说道:“我们走!”
这时,特务已经阻住了进进出出的人,开始清查叛徒供出的许云峰。
(摘编自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有改动)
3.小说第一段的环境描写在选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结合选文简要分析。
答案
1.(1)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为黎明时分,地点为阵地,为情节展开铺垫背景画面;(2)以声衬静,渲染宁静、孤寂、肃穆的气氛,奠定悲壮、伤感的情感基调;(3)随着时间的变化,天亮了,为“他”看清周边,介绍战友牺牲的形貌状态并挖坑埋葬四个战友做铺垫;(4)“黎明”“微光”具有象征比喻义,暗示战争即将结束,和平终将到来。
2.①首段环境描写,渲染了喧闹的氛围,展现了一个嘈杂、酸臭的集市的环境特点。
②导引人物出场;为下文奥士纳大爷有勤俭的精神,从地上去捡起了绳子做铺垫。
3.①渲染气氛。小说写乱哄哄的茶馆,为人物出场营造了典型环境。②以乱写静。茶馆的乱,为李敬原与许云峰秘密交谈提供了掩盖,突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智慧。③墙头上“休谈国事”的招贴与下文李敬原与许云峰秘密交谈形成对比,讽刺了敌人的白色恐怖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后的墓穴
石钟山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先是看到天空,正是又一个黎明时分,微光透过天幕,通透深邃。他试着移动四肢,才发现一条腿已经断了,血凝在伤口处,他侧过身,呼唤着战友的名字。他记得撤到这个阵地时,还有四名战士,他一个又一个地呼唤着,周围静静的,只有几只不知名的虫子在土里苏醒,发出细碎的鸣叫。天又亮了些,他能看清周边的景物了。他先是看到大个子张福来,抱着上了刺刀的枪,趴在地上。在另一侧,张小宝身子扭曲地躺在那里,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敌人。他想起来了,他冲出掩体前,那四个战士都牺牲了,他是最后一个。
他爬着把四个战友都找到了,前两天阻击战牺牲的士兵,最后都由他们活着的战友掩埋了,他现在是唯一活着的人,掩埋战友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身上。
他卸下了张福来枪上的刺刀,借着一个炸弹坑,用刺刀挖土。太阳升起丈八高的时候,坑已经挖好了,他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旷野里只能听见他自己大口的喘气声。他伏在地上歇了一会儿,然后依次爬到战友的遗体旁,拖拽着把战友放到坑里。拖大个子张福来时,他费了好大劲儿,一截短短的路,他歇了几次,终于把张福来拖到挖好的坑里。他又转身从坑里爬上来,在高处看曾经熟悉的战友,他们都静静地躺在他的眼前,昨天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自己的眼前活蹦乱跳,和他一起阻击敌人,眼下他们只能躺在这里了。张福来半睁着眼睛,心有不甘的样子。他怔了一会儿,又待了片刻,开始为他们掩土,渐渐地,战友们从他眼前消失了,眼前的土和山头上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他突然感到莫名的孤独。
一个排的人,加上他三十一个鲜活的生命,三天阻击战,此时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想找棵树给这四个战友留下个记号,可周围并没有树,原来的那几棵树早被敌人的炮弹炸得只剩下树桩。最后他找到离战友最近的一块石头,用刺刀在上面画出一个“4”字。
做完这一切,他有些迷瞪,竟不知自己在哪儿,仰面望着天空,太阳已升到了他的面前,火辣地烤在他的身上。他浑身无力,真想睡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时光似乎又回到了三天前,赵连长立在他们面前道:“你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三天,然后撤出阵地去追赶大部队……”赵连长的命令犹在耳边,他一激灵清醒过来,茫然四顾,还是那个山头,身旁就是他刚掩埋的四个战友。他还有任务,就是追赶大部队,可大部队又在何处,他向山背面爬去,他知道,只要向前爬,总有一天,就会追赶上大部队,回到队伍里,重新见到赵连长和那些熟悉的战友们。
他的军衣湿了一次又一次,不知是血水还是汗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一歪头,在半山坡一棵树下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觉得是伏在一个人的背上,那人气喘着,摇晃着。他看到了满天的星斗,山已经不见了,他不知自己在哪儿,他呻唤一声,便听见那气喘声止住了,叫了一声:“你醒了。”他发现是个女人的声音,他一惊,几乎从她背上跌下来,女子呵斥道:“别动。”然后又大喘着向前走去。他想挣扎着下来,可一转头,他又失去了知觉。
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头上是屋顶,然后又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冲外面喊了一声:“娘,他醒了。”他循声望去,便看见了她,眼前立着的是个纤瘦的女子,年纪不大,穿着碎花对襟衣服。随声进来一个中年女人,手里端了一碗粥,走进来,见他睁开了眼睛,说了句:“老天爷保佑,你终于醒了。”
后来他知道,这家人姓许,两年前,这家男人随过路的部队参了军,便再也没有回来,女孩叫盼儿。那天她去山上放家里仅有的两只羊,发现了他,后来她说,自己的父亲就是随着和他穿着一样服装的队伍走了。
盼儿和她母亲,因为认定了他身上的这身军装,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照料,盼儿只要放羊回来,总是到他床前看一看,问一声好。有时她还会在山上采些野花放在他的床头,于是幽香便弥漫在他的屋内。有时,她怕他寂寞还给他唱歌,是当地的民歌,曲调干净明快,在他眼里盼儿就像她唱的一首首歌,淳朴,明媚。
当盼儿把几朵菊花放到他床前时,他知道秋天来了,那会儿他已经能起床了,那条被炸断的腿,似乎长在身体上了,但已经变了形,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再后来,他已经能拄着一根棍子到院里站一站了。后来某一天,他拄着棍子走出小院,虽然脚步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力铿锵,但还是能走了。
终于有一天,他向盼儿和盼儿的母亲告别了,他要归队了。他要走的那一天,娘儿俩来到门前为他送行,他走了几步,突然听到盼儿又唱起了歌,那是一首当地送行的歌,他回过头,见娘儿俩立在他早已熟悉的家门前,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他在心里狠狠地把她们记下了,这是他的恩人。他再回过头,向前走去,盼儿的歌声变得远了,最后那歌变了泣腔,盼儿妈喊着:“孩子,找不到队伍,再回来,这里还是你的家。”
(选自《解放军文艺》2022年第1期,有删改)
1.小说第一段的自然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坍台【注】。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的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注】坍台:方言,丢脸。
2.小说中第一段的环境描写在文中有何作用?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岩(节选)
罗广斌、杨益言
乱哄哄的茶园里,坐满了人。穿西服的、穿军服的、穿长袍马褂的顾客,不断地进进出出。这家设备舒适的高级茶园,向来是座无虚设的。每当星期天,更是拥挤不堪。到这里喝茶的,不仅有嗜爱品茗的名流、社会闻人和衣着华丽的男女,还有那些习惯在茶馆里了解行情、进行交易的掮客与富商、政界人物与银行家。喜欢在浑浊的人潮中消磨时光的人,也在这里约会、聚谈、互相传播琐事轶闻,纵谈天下大事。那些高谈阔论、嬉笑怒骂的声音,加上茶碗茶碟叮叮当当的响声,应接不暇的茶房的喊声,叫卖香烟、瓜子、画报、杂志的嘈杂声,有时还混进一些吆喝乞丐的骂声,融汇成一片人声鼎沸、五光十色的闹市气氛,与那墙头上冷落地贴着叫人缄默的“休谈国事”的招贴,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和讽刺。
此刻,在纷杂的茶座之间,有两位顾客,正靠着一张精巧的茶桌,对面坐着。一个是戴墨框眼镜、穿咖啡色西服的李敬原,另一个穿蓝长袍的是许云峰。他们混迹在人海般的茶园里,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这种环境,正是地下工作者常常用来碰头和商谈某些工作的好地方。
昨天晚上和甫志高分手以后,许云峰到沙磁区委书记家里过了一夜,和他交换了意见,部署了有关人员的转移计划。
今天一早,沙磁区委书记便赶往沙坪坝去了。九点正,许云峰来到新生市场内的这座茶馆,准时会到了几天前约定在这里碰面的川东特委的李敬原,马上向他汇报了昨天晚上到沙坪书店时发现的危险,以及和甫志高谈话等情况。李敬原听了也感到意外,并且认为情况的确严重。
桌上摆的五香瓜子,已经嗑了不少。老许的手指轻敲着茶碗,外貌颇为悠闲地喊茶房来冲开水。等茶房冲过开水以后,李敬原习惯地摸了一下眼镜,耳语告诉老许:“今早上到区里去,发觉他们在转移!原来是你连夜关照的,这很及时。”
许云峰点点头,也低声问道:“区里发现了新的情况吗?”
“陈松林大概脱离危险了。”李敬原沉着地说,“区上发现,深夜里沙坪书店附近出现过形迹可疑的人……”
李敬原说这话时毫无表情,然而目光却犀利地在镜框里闪动。“照你刚才谈的情况看来,敌人昨天晚上果然动手了,这一次真是危险!”
听到李敬原谈的情况,许云峰对目前的形势感到更加严重了。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和及时防止了破坏,并不能使他高兴,相反地,他感到内疚。把备用联络站交给甫志高管,这是一种不应有的疏忽。过去虽然发现甫志高的许多毛病,但今天看来,对他的问题还是认识不足,这种人,即使一时有再好的表现,也是不能相信的。许云峰瞧了一下李敬原,他正吐着浓烟,仍然是那样的从容镇定,使许云峰明显地感到,不管风浪再大,他永远也不会张皇失措的。
茶馆里人来人往,经常打断他们的谈话。他们并不觉得厌烦,反而感到安全。
许云峰的思想飞快地发展着,他立刻联想到昨天晚上小陈谈的重要线索:黎纪纲这个危险人物,突然冒雨在书店出现,并且叫走了郑克昌,这就是敌人动手的征兆!老李说的深夜里在沙坪书店附近发现可疑的人,便是斗争的明朗化!
老许放开了思路,答道:“这是一次教训,我们考虑一下,还有什么漏洞?万一老甫昨晚上回家去?”
李敬原忽然问道:“你和他约在什么地方见面?”
“心心咖啡店。”
李敬原深思了一下,不安地说:“离这儿太近了……”
许云峰付过茶资,看看表,还不到十点钟。他随手捡起茶桌上的报纸,正要起身。可是这时,李敬原突然回到桌边,低声喊道:“老许!”
许云峰抬头,正遇到李敬原不安的眼色。
“外边有便衣特务!”
许云峰扭头向外察看,只见茶园门口,人丛里夹杂着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再往门外一望,一眼看出:便衣特务封锁了商场的所有通路。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
李敬原侧目斜视,也清楚地看见敌特的搜索圈正向商场内紧缩过来。情势十分紧迫、危险。李敬原毫不迟疑地说道:“我们走!”
这时,特务已经阻住了进进出出的人,开始清查叛徒供出的许云峰。
(摘编自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有改动)
3.小说第一段的环境描写在选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结合选文简要分析。
答案
1.(1)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为黎明时分,地点为阵地,为情节展开铺垫背景画面;(2)以声衬静,渲染宁静、孤寂、肃穆的气氛,奠定悲壮、伤感的情感基调;(3)随着时间的变化,天亮了,为“他”看清周边,介绍战友牺牲的形貌状态并挖坑埋葬四个战友做铺垫;(4)“黎明”“微光”具有象征比喻义,暗示战争即将结束,和平终将到来。
2.①首段环境描写,渲染了喧闹的氛围,展现了一个嘈杂、酸臭的集市的环境特点。
②导引人物出场;为下文奥士纳大爷有勤俭的精神,从地上去捡起了绳子做铺垫。
3.①渲染气氛。小说写乱哄哄的茶馆,为人物出场营造了典型环境。②以乱写静。茶馆的乱,为李敬原与许云峰秘密交谈提供了掩盖,突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智慧。③墙头上“休谈国事”的招贴与下文李敬原与许云峰秘密交谈形成对比,讽刺了敌人的白色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