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小说的语言(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小说专题训练-小说的语言(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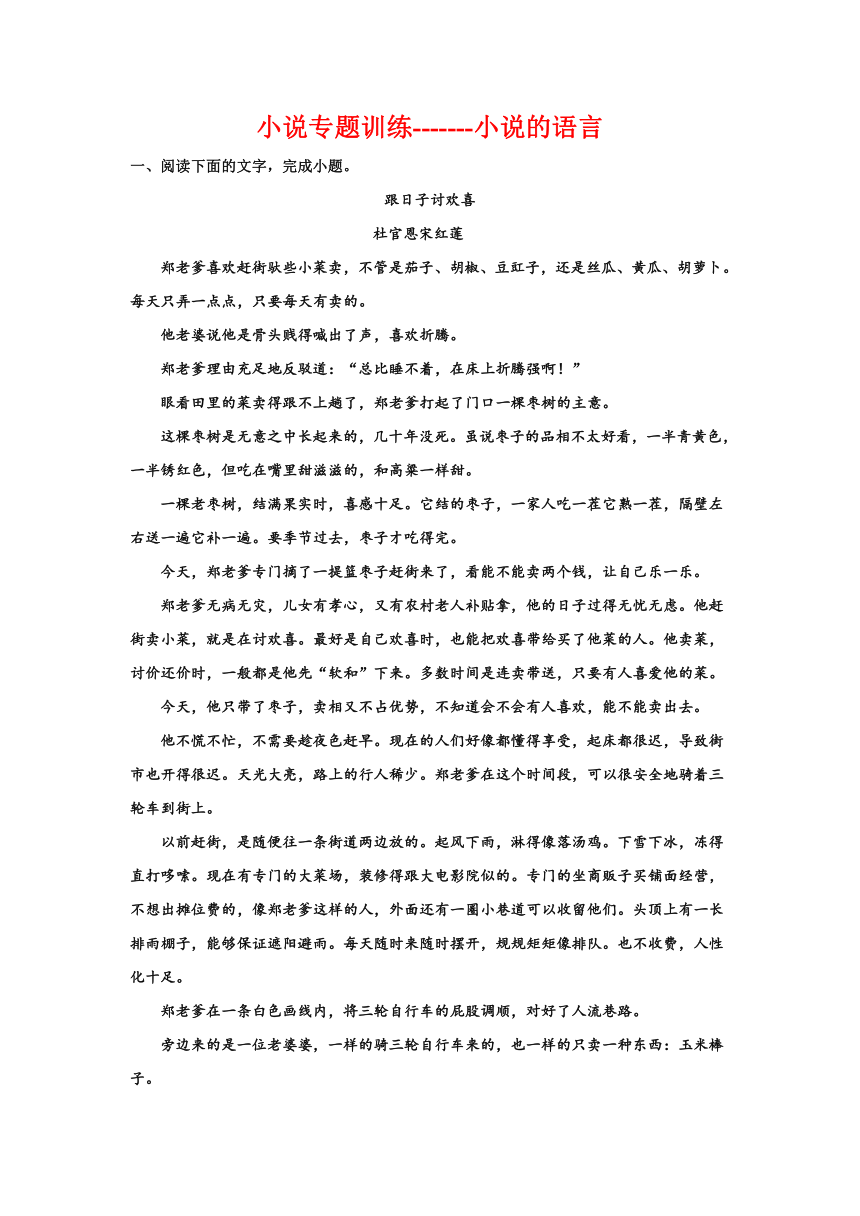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2.6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通用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5-04 20:02:57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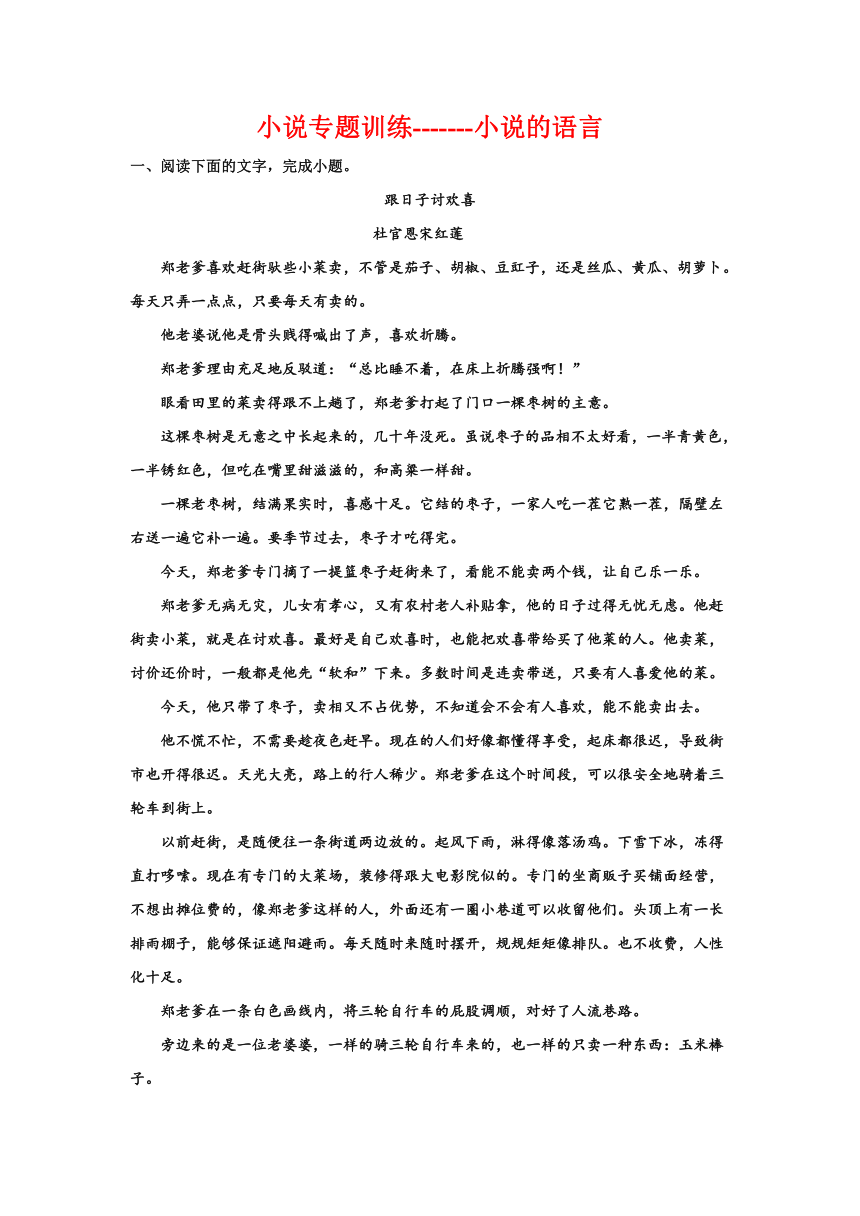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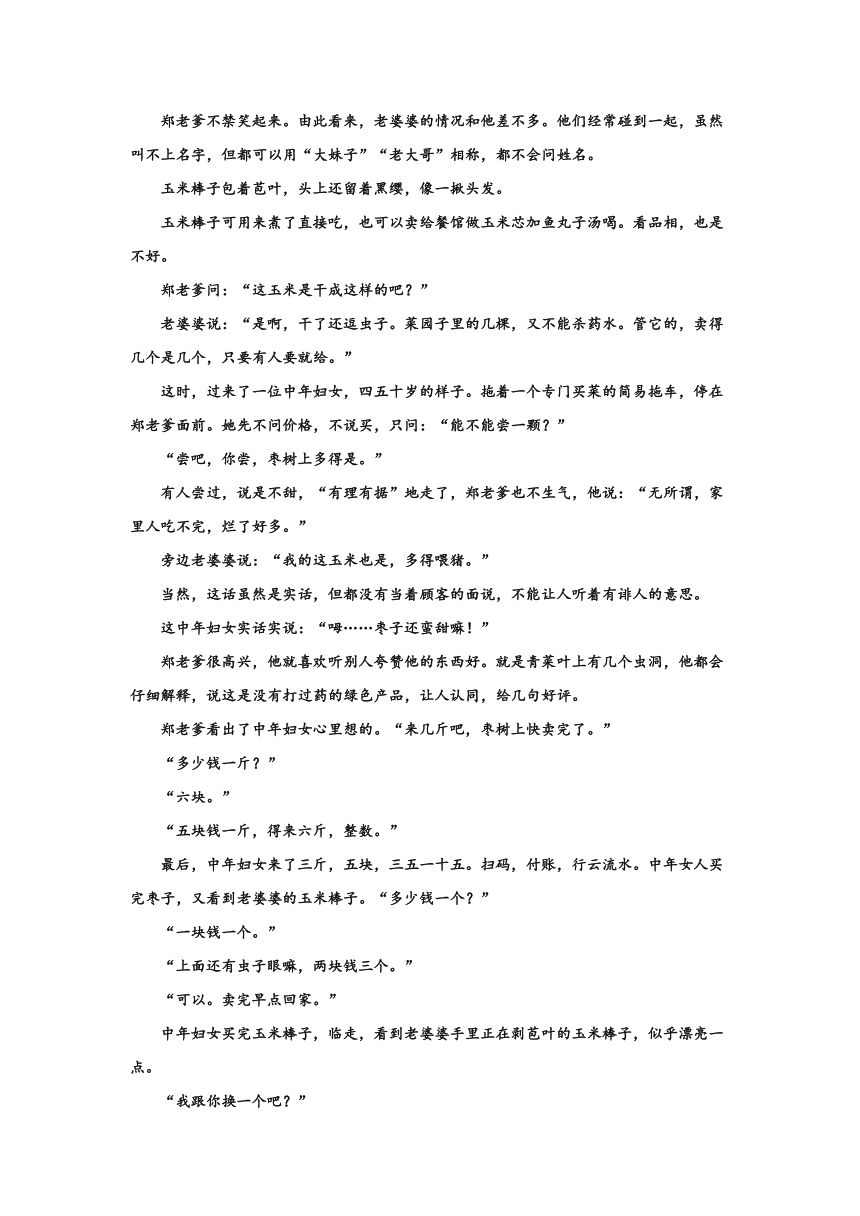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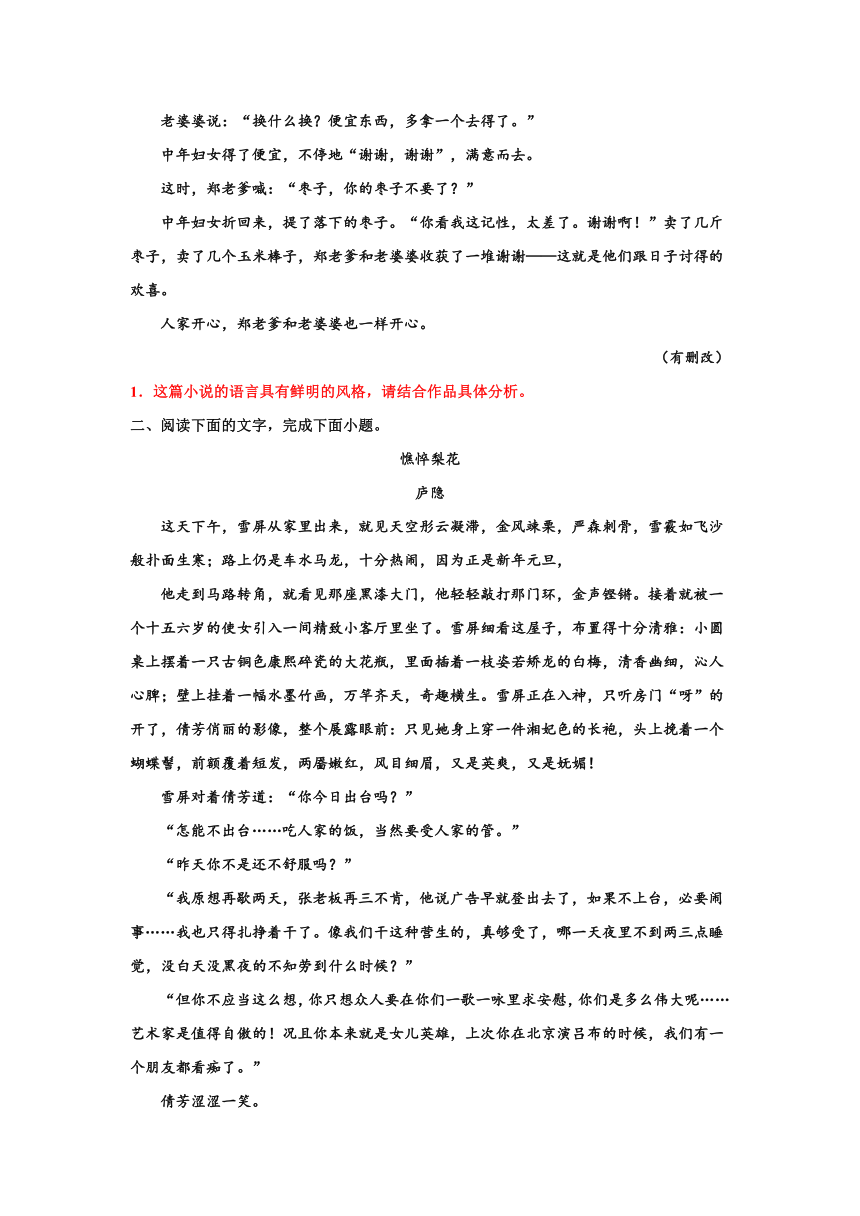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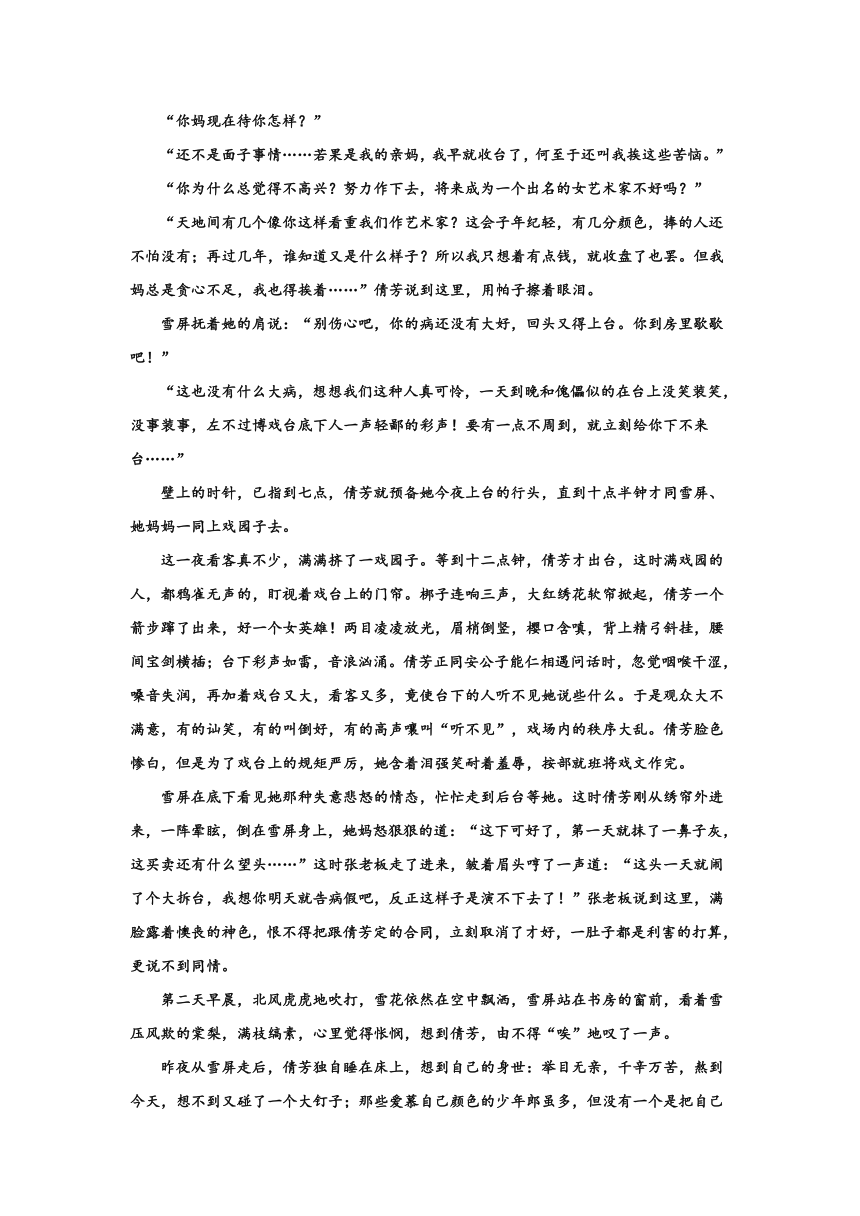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小说的语言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跟日子讨欢喜
杜官恩宋红莲
郑老爹喜欢赶街驮些小菜卖,不管是茄子、胡椒、豆豇子,还是丝瓜、黄瓜、胡萝卜。每天只弄一点点,只要每天有卖的。
他老婆说他是骨头贱得喊出了声,喜欢折腾。
郑老爹理由充足地反驳道:“总比睡不着,在床上折腾强啊!”
眼看田里的菜卖得跟不上趟了,郑老爹打起了门口一棵枣树的主意。
这棵枣树是无意之中长起来的,几十年没死。虽说枣子的品相不太好看,一半青黄色,一半锈红色,但吃在嘴里甜滋滋的,和高粱一样甜。
一棵老枣树,结满果实时,喜感十足。它结的枣子,一家人吃一茬它熟一茬,隔壁左右送一遍它补一遍。要季节过去,枣子才吃得完。
今天,郑老爹专门摘了一提篮枣子赶街来了,看能不能卖两个钱,让自己乐一乐。
郑老爹无病无灾,儿女有孝心,又有农村老人补贴拿,他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他赶街卖小菜,就是在讨欢喜。最好是自己欢喜时,也能把欢喜带给买了他菜的人。他卖菜,讨价还价时,一般都是他先“软和”下来。多数时间是连卖带送,只要有人喜爱他的菜。
今天,他只带了枣子,卖相又不占优势,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能不能卖出去。
他不慌不忙,不需要趁夜色赶早。现在的人们好像都懂得享受,起床都很迟,导致街市也开得很迟。天光大亮,路上的行人稀少。郑老爹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很安全地骑着三轮车到街上。
以前赶街,是随便往一条街道两边放的。起风下雨,淋得像落汤鸡。下雪下冰,冻得直打哆嗦。现在有专门的大菜场,装修得跟大电影院似的。专门的坐商贩子买铺面经营,不想出摊位费的,像郑老爹这样的人,外面还有一圈小巷道可以收留他们。头顶上有一长排雨棚子,能够保证遮阳避雨。每天随时来随时摆开,规规矩矩像排队。也不收费,人性化十足。
郑老爹在一条白色画线内,将三轮自行车的屁股调顺,对好了人流巷路。
旁边来的是一位老婆婆,一样的骑三轮自行车来的,也一样的只卖一种东西:玉米棒子。
郑老爹不禁笑起来。由此看来,老婆婆的情况和他差不多。他们经常碰到一起,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可以用“大妹子”“老大哥”相称,都不会问姓名。
玉米棒子包着苞叶,头上还留着黑缨,像一揪头发。
玉米棒子可用来煮了直接吃,也可以卖给餐馆做玉米芯加鱼丸子汤喝。看品相,也是不好。
郑老爹问:“这玉米是干成这样的吧?”
老婆婆说:“是啊,干了还逗虫子。菜园子里的几棵,又不能杀药水。管它的,卖得几个是几个,只要有人要就给。”
这时,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四五十岁的样子。拖着一个专门买菜的简易拖车,停在郑老爹面前。她先不问价格,不说买,只问:“能不能尝一颗?”
“尝吧,你尝,枣树上多得是。”
有人尝过,说是不甜,“有理有据”地走了,郑老爹也不生气,他说:“无所谓,家里人吃不完,烂了好多。”
旁边老婆婆说:“我的这玉米也是,多得喂猪。”
当然,这话虽然是实话,但都没有当着顾客的面说,不能让人听着有诽人的意思。
这中年妇女实话实说:“呣……枣子还蛮甜嘛!”
郑老爹很高兴,他就喜欢听别人夸赞他的东西好。就是青菜叶上有几个虫洞,他都会仔细解释,说这是没有打过药的绿色产品,让人认同,给几句好评。
郑老爹看出了中年妇女心里想的。“来几斤吧,枣树上快卖完了。”
“多少钱一斤?”
“六块。”
“五块钱一斤,得来六斤,整数。”
最后,中年妇女来了三斤,五块,三五一十五。扫码,付账,行云流水。中年女人买完枣子,又看到老婆婆的玉米棒子。“多少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上面还有虫子眼嘛,两块钱三个。”
“可以。卖完早点回家。”
中年妇女买完玉米棒子,临走,看到老婆婆手里正在剥苞叶的玉米棒子,似乎漂亮一点。
“我跟你换一个吧?”
老婆婆说:“换什么换?便宜东西,多拿一个去得了。”
中年妇女得了便宜,不停地“谢谢,谢谢”,满意而去。
这时,郑老爹喊:“枣子,你的枣子不要了?”
中年妇女折回来,提了落下的枣子。“你看我这记性,太差了。谢谢啊!”卖了几斤枣子,卖了几个玉米棒子,郑老爹和老婆婆收获了一堆谢谢——这就是他们跟日子讨得的欢喜。
人家开心,郑老爹和老婆婆也一样开心。
(有删改)
1.这篇小说的语言具有鲜明的风格,请结合作品具体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憔悴梨花
庐隐
这天下午,雪屏从家里出来,就见天空彤云凝滞,金风竦栗,严森刺骨,雪霰如飞沙般扑面生寒;路上仍是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因为正是新年元旦,
他走到马路转角,就看见那座黑漆大门,他轻轻敲打那门环,金声铿锵。接着就被一个十五六岁的使女引入一间精致小客厅里坐了。雪屏细看这屋子,布置得十分清雅:小圆桌上摆着一只古铜色康熙碎瓷的大花瓶,里面插着一枝姿若矫龙的白梅,清香幽细,沁人心脾;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竹画,万竿齐天,奇趣横生。雪屏正在入神,只听房门“呀”的开了,倩芳俏丽的影像,整个展露眼前:只见她身上穿一件湘妃色的长袍,头上挽着一个蝴蝶髻,前额覆着短发,两靥嫩红,风目细眉,又是英爽,又是妩媚!
雪屏对着倩芳道:“你今日出台吗?”
“怎能不出台……吃人家的饭,当然要受人家的管。”
“昨天你不是还不舒服吗?”
“我原想再歇两天,张老板再三不肯,他说广告早就登出去了,如果不上台,必要闹事……我也只得扎挣着干了。像我们干这种营生的,真够受了,哪一天夜里不到两三点睡觉,没白天没黑夜的不知劳到什么时候?”
“但你不应当这么想,你只想众人要在你们一歌一咏里求安慰,你们是多么伟大呢……艺术家是值得自傲的!况且你本来就是女儿英雄,上次你在北京演吕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都看痴了。”
倩芳涩涩一笑。
“你妈现在待你怎样?”
“还不是面子事情……若果是我的亲妈,我早就收台了,何至于还叫我挨这些苦恼。”
“你为什么总觉得不高兴?努力作下去,将来成为一个出名的女艺术家不好吗?”
“天地间有几个像你这样看重我们作艺术家?这会子年纪轻,有几分颜色,捧的人还不怕没有;再过几年,谁知道又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只想着有点钱,就收盘了也罢。但我妈总是贪心不足,我也得挨着……”倩芳说到这里,用帕子擦着眼泪。
雪屏抚着她的肩说:“别伤心吧,你的病还没有大好,回头又得上台。你到房里歇歇吧!”
“这也没有什么大病,想想我们这种人真可怜,一天到晚和傀儡似的在台上没笑装笑,没事装事,左不过博戏台底下人一声轻鄙的彩声!要有一点不周到,就立刻给你下不来台……”
壁上的时针,已指到七点,倩芳就预备她今夜上台的行头,直到十点半钟才同雪屏、她妈妈一同上戏园子去。
这一夜看客真不少,满满挤了一戏园子。等到十二点钟,倩芳才出台,这时满戏园的人,都鸦雀无声的,盯视着戏台上的门帘。梆子连响三声,大红绣花软帘掀起,倩芳一个箭步蹿了出来,好一个女英雄!两目凌凌放光,眉梢倒竖,樱口含嗔,背上精弓斜挂,腰间宝剑横插;台下彩声如雷,音浪汹涌。倩芳正同安公子能仁相遇问话时,忽觉咽喉干涩,嗓音失润,再加着戏台又大,看客又多,竟使台下的人听不见她说些什么。于是观众大不满意,有的讪笑,有的叫倒好,有的高声嚷叫“听不见”,戏场内的秩序大乱。倩芳脸色惨白,但是为了戏台上的规矩严厉,她含着泪强笑耐着羞辱,按部就班将戏文作完。
雪屏在底下看见她那种失意悲怒的情态,忙忙走到后台等她。这时倩芳刚从绣帘外进来,一阵晕眩,倒在雪屏身上,她妈怒狠狠的道:“这下可好了,第一天就抹了一鼻子灰,这买卖还有什么望头……”这时张老板走了进来,皱着眉头哼了一声道:“这头一天就闹了个大拆台,我想你明天就告病假吧,反正这样子是演不下去了!”张老板说到这里,满脸露着懊丧的神色,恨不得把跟倩芳定的合同,立刻取消了才好,一肚子都是利害的打算,更说不到同情。
第二天早晨,北风虎虎地吹打,雪花依然在空中飘洒,雪屏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雪压风欺的棠梨,满枝缟素,心里觉得怅悯,想到倩芳,由不得“唉”地叹了一声。
昨夜从雪屏走后,倩芳独自睡在床上,想到自己的身世:举目无亲,千辛万苦,熬到今天,想不到又碰了一个大钉子;那些爱慕自己颜色的少年郎虽多,但没有一个是把自己当正经人待……只有雪屏看得起自己,但他又从来没露过口声……倩芳想到这里,觉得前后都是茫茫荡荡的河海,没有去路,禁不住掉下泪来。正在拭泪,雪屏进来见了,不禁长叹道:“倩芳!你自己要看开点,不要因为一点挫折,便埋没了你的天才!”
“什么天才!恐怕除了你,没有说我是天才!像我们这种人,公子哥儿高兴时捧捧场,不高兴时也由着他们摧残,还有我们立脚的地方吗?”
“正是这话!但是倩芳,我总觉得你是个特别的天才,可惜社会上没人能欣赏,这自然是社会一般人的眼光浅薄,我们应当想法子改正他们的毛病。倩芳!我相信你是一个风尘中的巾帼英雄!你应当努力,和这罪恶的社会奋斗!”
倩芳听了雪屏的话,怔怔的望着半天,她才叹气道:“还有你看得起我,但我怕对不起你。你知道吧!我们这院子东边的一株梨花,春天开得十分茂盛,忽然夜里来了一阵暴风雨,打得满树花朵零乱飘落,第二天早起一看,简直枝垂花败,再也抬不起头来……”雪屏听了这话,细细看了倩芳一眼,由不得低声吟道:“憔悴梨花风雨后……”
(有删改)
2.庐隐的小说语言细腻蕴藉,在本文中主要体现在暗示性和隐喻性上。请结合文本简要赏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年关六赋
阿成
爷爷活着的时候,每逢旧历的春节,老三的父母一定要领着他们生育的四位雌雄,到爷爷的家去过年。爷爷死后,老三这兄妹四人也一定得到父母的家守岁。
这是王氏家族的规矩。
-题记
老三爷爷的也就是后来老三父亲的家,院子很阔。凭栏望去,一任江天浩浩荡荡,爽着肺腑。其住房几经修缮,父亲住着很好,很遂心,很滋润,过得也极有板眼。
每值茶余饭后,兄弟几个一律恭恭敬敬,坐在庭院的小凳上,听父亲讲《论语》。
老三的父亲是读书人。爷爷活着的时候,早早地把他送到松花江对岸的私塾,读孔子。
山东人古来就讲究智力开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再者说,“养不教,父之过”嘛。
老三的爷爷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后来成为这里的第一户居民。为了供儿子读书,捕了一辈子的鱼,卖了上百吨的鱼虾,真累!
每逢星期六,学堂放课,老三的爷爷就早早地摇了船到江南,歇船在柳荫之下,吸着早烟,等父亲。
父子俩见了面:
儿子给爹鞠一躬,说:爹——
爷爷嘿嘿地傻笑,说:儿子——
老三的父亲讲《论语》,从不看书,凭着记性。另外,小方桌上总有一壶清茶,饱饱地候着。“子曰,”父亲说,“就是孔子说。曰,就是说。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做事,不能光靠嘴,要少说。古人说:贵人言语迟。靠什么呢?靠行动,靠作。光说不做,不是仁义人;光做不说,大用之材。记住没?”
兄弟几个都点头,不说。
“子曰:融四岁,能让梨。”
“子曰:温良恭俭让。”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父亲说:“凡‘子曰’,都要背下来,方能成人。”
老三的父亲教育子女,层次比较高,很有群体意识。
……
每逢旧历的春节,除夕的年夜饭,事先一律要祭祖,儿女们要给仙逝的爷爷、奶奶的灵位磕头。父亲还要在灶前烧一沓阴币,恭恭敬敬,说些话。全磕完头,父亲站在一旁,依次给压岁钱,都是新票子:二元、一元、五角不等。
儿女们接了钱,很激动,说“谢谢爸”。
守岁之夜,不准睡觉,都要精精神神。俗话说:一分精神,一分财;十分精神,抖起来。年夜饭,老三的父亲总要讲些旧话,比如“在家敬父母,胜似远烧香”。讲的是山东泰安一个打烧饼的和一位有钱的少爷,到泰山大成殿争当天下第一大孝子的事。父亲讲得有支有板儿、有景有物,人物实在,对话不多,听了不忘,有较高的审美层次。老三一干儿女,听得入神,觉得很亲切。
老三兄弟几个,数老三的大哥最出息。
老三的大哥在地方法院工作,是副院长。每值旧历年,他总要早几天把“东西”送到父母的家里。送的东西都很实惠。算一算,一二百元不止,足够老三的父母享一个正月。
旧历三十这一天,老三的大哥领着媳妇、女儿回家,事先一定要脱掉法院的制服,换上便装、布鞋,并告诉大嫂:“到家讲话做事要注意,不能乱说,不能神气,也没什么可神气的,是事儿,听着就是了,多干活!”
大嫂笑着说:“老王啊,老王……”
大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老三的二哥一律是旧历三十的下午,骑着摩托车,驮着二嫂回父母的家过年。
老三的二哥也出息得不错,是第一代企业家。现在已是几十万元户,常常去参加市里的一些会议。二哥回家过年,自然提的都是高档货。有山珍,有海味,有洋货,分东洋与西洋,都很名贵,看着浑身痛快。
临行前,老三的二哥也一定很严肃地对二嫂说:“回家过年,有几条注意,一不要化妆,全擦掉,土一点没关系。二不能摆阔,首饰什么的,不戴。要有老有少,不准瞎白话。家里的饭,好不好吃,一律认真吃。尤其爸妈做的,要说,真好吃。听见没有?”二嫂笑笑,说:“行,听你的。就当上庙了,一天怎么也忍了。”二哥说:“对!就是这意思。”
二哥二嫂回家过年,穿着都很朴素,甚至显得过了,头发也剪得很短,像五十年代的干事。老三家境不富裕,在一家杂志社当助理编辑,也是新潮作家。回家过年,带的礼品就很一般化,是四合礼。有四种奶油蛋糕,很艺术地组装在一个礼品盒子里,并用透明的玻璃纸罩着。
老三回家过年,从不戴他的贝雷帽,上衣兜也不插钢笔、油笔。事先也要对媳妇说:“嗯——到家,看别人,他们怎样,咱怎样,千万别出挑儿……”
老三的媳妇看了看他,轻蔑地说:“熊架①!”
……
自从老三兄妹四人分别嫁娶后,凡二十余载,都回家过年这事,居在一个城市的兄妹,并不事先通通电话,也不约定一下,基本上都回去。
今年过年,兄弟几个都事先做了安排,回家过年。
老三的母亲对孩子很好,很平等,也很亲近,总是喜着脸:“三儿回来啦。”“老二回来啦。”“老四也回来啦。”都柔柔的,儿子、女儿瞅着,心里就充满了温馨的阳光。
(有删改)
[注]①熊架,山东方言,意思是看看你那德行,看看你那样子。
3.阿成小说的语言雅与俗相间,请结合文本加以赏析。
参考答案:
1.①语言通俗易懂,具有生活气息。如“骨头贱得喊出了声”“大妹子”“老大哥”等。②语言具有乡土特色、地方特色。如“干了还逗虫子”“枣子还蛮甜嘛”。③语言生动形象,运用了比喻等手法。如“淋得像落汤鸡”“像一揪头发”。
2.①自然环境暗示:天气的阴沉、寒冷、恶劣,暗示倩芳生存的社会环境压抑与艰难。
②倩芳的客厅精致清雅,白梅姿若矫龙,墨竹万竿齐天,暗示女主人品味的不俗。
③梨花隐喻,作者将备受欺凌和歧视的女主人公比作经受风雪严寒或暴风雨的梨花,暗示她最终“枝垂花败”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3.①雅:叙述语言使用文言词、书面语。如“凭栏”“方能”“一任江天”“颇为”“遂心”“瞅着”“每值”等词语,读来古朴高雅,富有韵味。
②俗:人物语言使用方言、口语。如“瞎白话”“熊架”“咱怎样”“出挑儿”“票子”等方言与口语,简洁明快,使小说生活气息浓郁。
③“雅”与“俗”融为一体,使语言既富有文采,又充满生活气息,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之美,叙事风格独特,能很好地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跟日子讨欢喜
杜官恩宋红莲
郑老爹喜欢赶街驮些小菜卖,不管是茄子、胡椒、豆豇子,还是丝瓜、黄瓜、胡萝卜。每天只弄一点点,只要每天有卖的。
他老婆说他是骨头贱得喊出了声,喜欢折腾。
郑老爹理由充足地反驳道:“总比睡不着,在床上折腾强啊!”
眼看田里的菜卖得跟不上趟了,郑老爹打起了门口一棵枣树的主意。
这棵枣树是无意之中长起来的,几十年没死。虽说枣子的品相不太好看,一半青黄色,一半锈红色,但吃在嘴里甜滋滋的,和高粱一样甜。
一棵老枣树,结满果实时,喜感十足。它结的枣子,一家人吃一茬它熟一茬,隔壁左右送一遍它补一遍。要季节过去,枣子才吃得完。
今天,郑老爹专门摘了一提篮枣子赶街来了,看能不能卖两个钱,让自己乐一乐。
郑老爹无病无灾,儿女有孝心,又有农村老人补贴拿,他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他赶街卖小菜,就是在讨欢喜。最好是自己欢喜时,也能把欢喜带给买了他菜的人。他卖菜,讨价还价时,一般都是他先“软和”下来。多数时间是连卖带送,只要有人喜爱他的菜。
今天,他只带了枣子,卖相又不占优势,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能不能卖出去。
他不慌不忙,不需要趁夜色赶早。现在的人们好像都懂得享受,起床都很迟,导致街市也开得很迟。天光大亮,路上的行人稀少。郑老爹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很安全地骑着三轮车到街上。
以前赶街,是随便往一条街道两边放的。起风下雨,淋得像落汤鸡。下雪下冰,冻得直打哆嗦。现在有专门的大菜场,装修得跟大电影院似的。专门的坐商贩子买铺面经营,不想出摊位费的,像郑老爹这样的人,外面还有一圈小巷道可以收留他们。头顶上有一长排雨棚子,能够保证遮阳避雨。每天随时来随时摆开,规规矩矩像排队。也不收费,人性化十足。
郑老爹在一条白色画线内,将三轮自行车的屁股调顺,对好了人流巷路。
旁边来的是一位老婆婆,一样的骑三轮自行车来的,也一样的只卖一种东西:玉米棒子。
郑老爹不禁笑起来。由此看来,老婆婆的情况和他差不多。他们经常碰到一起,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可以用“大妹子”“老大哥”相称,都不会问姓名。
玉米棒子包着苞叶,头上还留着黑缨,像一揪头发。
玉米棒子可用来煮了直接吃,也可以卖给餐馆做玉米芯加鱼丸子汤喝。看品相,也是不好。
郑老爹问:“这玉米是干成这样的吧?”
老婆婆说:“是啊,干了还逗虫子。菜园子里的几棵,又不能杀药水。管它的,卖得几个是几个,只要有人要就给。”
这时,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四五十岁的样子。拖着一个专门买菜的简易拖车,停在郑老爹面前。她先不问价格,不说买,只问:“能不能尝一颗?”
“尝吧,你尝,枣树上多得是。”
有人尝过,说是不甜,“有理有据”地走了,郑老爹也不生气,他说:“无所谓,家里人吃不完,烂了好多。”
旁边老婆婆说:“我的这玉米也是,多得喂猪。”
当然,这话虽然是实话,但都没有当着顾客的面说,不能让人听着有诽人的意思。
这中年妇女实话实说:“呣……枣子还蛮甜嘛!”
郑老爹很高兴,他就喜欢听别人夸赞他的东西好。就是青菜叶上有几个虫洞,他都会仔细解释,说这是没有打过药的绿色产品,让人认同,给几句好评。
郑老爹看出了中年妇女心里想的。“来几斤吧,枣树上快卖完了。”
“多少钱一斤?”
“六块。”
“五块钱一斤,得来六斤,整数。”
最后,中年妇女来了三斤,五块,三五一十五。扫码,付账,行云流水。中年女人买完枣子,又看到老婆婆的玉米棒子。“多少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上面还有虫子眼嘛,两块钱三个。”
“可以。卖完早点回家。”
中年妇女买完玉米棒子,临走,看到老婆婆手里正在剥苞叶的玉米棒子,似乎漂亮一点。
“我跟你换一个吧?”
老婆婆说:“换什么换?便宜东西,多拿一个去得了。”
中年妇女得了便宜,不停地“谢谢,谢谢”,满意而去。
这时,郑老爹喊:“枣子,你的枣子不要了?”
中年妇女折回来,提了落下的枣子。“你看我这记性,太差了。谢谢啊!”卖了几斤枣子,卖了几个玉米棒子,郑老爹和老婆婆收获了一堆谢谢——这就是他们跟日子讨得的欢喜。
人家开心,郑老爹和老婆婆也一样开心。
(有删改)
1.这篇小说的语言具有鲜明的风格,请结合作品具体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憔悴梨花
庐隐
这天下午,雪屏从家里出来,就见天空彤云凝滞,金风竦栗,严森刺骨,雪霰如飞沙般扑面生寒;路上仍是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因为正是新年元旦,
他走到马路转角,就看见那座黑漆大门,他轻轻敲打那门环,金声铿锵。接着就被一个十五六岁的使女引入一间精致小客厅里坐了。雪屏细看这屋子,布置得十分清雅:小圆桌上摆着一只古铜色康熙碎瓷的大花瓶,里面插着一枝姿若矫龙的白梅,清香幽细,沁人心脾;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竹画,万竿齐天,奇趣横生。雪屏正在入神,只听房门“呀”的开了,倩芳俏丽的影像,整个展露眼前:只见她身上穿一件湘妃色的长袍,头上挽着一个蝴蝶髻,前额覆着短发,两靥嫩红,风目细眉,又是英爽,又是妩媚!
雪屏对着倩芳道:“你今日出台吗?”
“怎能不出台……吃人家的饭,当然要受人家的管。”
“昨天你不是还不舒服吗?”
“我原想再歇两天,张老板再三不肯,他说广告早就登出去了,如果不上台,必要闹事……我也只得扎挣着干了。像我们干这种营生的,真够受了,哪一天夜里不到两三点睡觉,没白天没黑夜的不知劳到什么时候?”
“但你不应当这么想,你只想众人要在你们一歌一咏里求安慰,你们是多么伟大呢……艺术家是值得自傲的!况且你本来就是女儿英雄,上次你在北京演吕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都看痴了。”
倩芳涩涩一笑。
“你妈现在待你怎样?”
“还不是面子事情……若果是我的亲妈,我早就收台了,何至于还叫我挨这些苦恼。”
“你为什么总觉得不高兴?努力作下去,将来成为一个出名的女艺术家不好吗?”
“天地间有几个像你这样看重我们作艺术家?这会子年纪轻,有几分颜色,捧的人还不怕没有;再过几年,谁知道又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只想着有点钱,就收盘了也罢。但我妈总是贪心不足,我也得挨着……”倩芳说到这里,用帕子擦着眼泪。
雪屏抚着她的肩说:“别伤心吧,你的病还没有大好,回头又得上台。你到房里歇歇吧!”
“这也没有什么大病,想想我们这种人真可怜,一天到晚和傀儡似的在台上没笑装笑,没事装事,左不过博戏台底下人一声轻鄙的彩声!要有一点不周到,就立刻给你下不来台……”
壁上的时针,已指到七点,倩芳就预备她今夜上台的行头,直到十点半钟才同雪屏、她妈妈一同上戏园子去。
这一夜看客真不少,满满挤了一戏园子。等到十二点钟,倩芳才出台,这时满戏园的人,都鸦雀无声的,盯视着戏台上的门帘。梆子连响三声,大红绣花软帘掀起,倩芳一个箭步蹿了出来,好一个女英雄!两目凌凌放光,眉梢倒竖,樱口含嗔,背上精弓斜挂,腰间宝剑横插;台下彩声如雷,音浪汹涌。倩芳正同安公子能仁相遇问话时,忽觉咽喉干涩,嗓音失润,再加着戏台又大,看客又多,竟使台下的人听不见她说些什么。于是观众大不满意,有的讪笑,有的叫倒好,有的高声嚷叫“听不见”,戏场内的秩序大乱。倩芳脸色惨白,但是为了戏台上的规矩严厉,她含着泪强笑耐着羞辱,按部就班将戏文作完。
雪屏在底下看见她那种失意悲怒的情态,忙忙走到后台等她。这时倩芳刚从绣帘外进来,一阵晕眩,倒在雪屏身上,她妈怒狠狠的道:“这下可好了,第一天就抹了一鼻子灰,这买卖还有什么望头……”这时张老板走了进来,皱着眉头哼了一声道:“这头一天就闹了个大拆台,我想你明天就告病假吧,反正这样子是演不下去了!”张老板说到这里,满脸露着懊丧的神色,恨不得把跟倩芳定的合同,立刻取消了才好,一肚子都是利害的打算,更说不到同情。
第二天早晨,北风虎虎地吹打,雪花依然在空中飘洒,雪屏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雪压风欺的棠梨,满枝缟素,心里觉得怅悯,想到倩芳,由不得“唉”地叹了一声。
昨夜从雪屏走后,倩芳独自睡在床上,想到自己的身世:举目无亲,千辛万苦,熬到今天,想不到又碰了一个大钉子;那些爱慕自己颜色的少年郎虽多,但没有一个是把自己当正经人待……只有雪屏看得起自己,但他又从来没露过口声……倩芳想到这里,觉得前后都是茫茫荡荡的河海,没有去路,禁不住掉下泪来。正在拭泪,雪屏进来见了,不禁长叹道:“倩芳!你自己要看开点,不要因为一点挫折,便埋没了你的天才!”
“什么天才!恐怕除了你,没有说我是天才!像我们这种人,公子哥儿高兴时捧捧场,不高兴时也由着他们摧残,还有我们立脚的地方吗?”
“正是这话!但是倩芳,我总觉得你是个特别的天才,可惜社会上没人能欣赏,这自然是社会一般人的眼光浅薄,我们应当想法子改正他们的毛病。倩芳!我相信你是一个风尘中的巾帼英雄!你应当努力,和这罪恶的社会奋斗!”
倩芳听了雪屏的话,怔怔的望着半天,她才叹气道:“还有你看得起我,但我怕对不起你。你知道吧!我们这院子东边的一株梨花,春天开得十分茂盛,忽然夜里来了一阵暴风雨,打得满树花朵零乱飘落,第二天早起一看,简直枝垂花败,再也抬不起头来……”雪屏听了这话,细细看了倩芳一眼,由不得低声吟道:“憔悴梨花风雨后……”
(有删改)
2.庐隐的小说语言细腻蕴藉,在本文中主要体现在暗示性和隐喻性上。请结合文本简要赏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年关六赋
阿成
爷爷活着的时候,每逢旧历的春节,老三的父母一定要领着他们生育的四位雌雄,到爷爷的家去过年。爷爷死后,老三这兄妹四人也一定得到父母的家守岁。
这是王氏家族的规矩。
-题记
老三爷爷的也就是后来老三父亲的家,院子很阔。凭栏望去,一任江天浩浩荡荡,爽着肺腑。其住房几经修缮,父亲住着很好,很遂心,很滋润,过得也极有板眼。
每值茶余饭后,兄弟几个一律恭恭敬敬,坐在庭院的小凳上,听父亲讲《论语》。
老三的父亲是读书人。爷爷活着的时候,早早地把他送到松花江对岸的私塾,读孔子。
山东人古来就讲究智力开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再者说,“养不教,父之过”嘛。
老三的爷爷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后来成为这里的第一户居民。为了供儿子读书,捕了一辈子的鱼,卖了上百吨的鱼虾,真累!
每逢星期六,学堂放课,老三的爷爷就早早地摇了船到江南,歇船在柳荫之下,吸着早烟,等父亲。
父子俩见了面:
儿子给爹鞠一躬,说:爹——
爷爷嘿嘿地傻笑,说:儿子——
老三的父亲讲《论语》,从不看书,凭着记性。另外,小方桌上总有一壶清茶,饱饱地候着。“子曰,”父亲说,“就是孔子说。曰,就是说。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做事,不能光靠嘴,要少说。古人说:贵人言语迟。靠什么呢?靠行动,靠作。光说不做,不是仁义人;光做不说,大用之材。记住没?”
兄弟几个都点头,不说。
“子曰:融四岁,能让梨。”
“子曰:温良恭俭让。”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父亲说:“凡‘子曰’,都要背下来,方能成人。”
老三的父亲教育子女,层次比较高,很有群体意识。
……
每逢旧历的春节,除夕的年夜饭,事先一律要祭祖,儿女们要给仙逝的爷爷、奶奶的灵位磕头。父亲还要在灶前烧一沓阴币,恭恭敬敬,说些话。全磕完头,父亲站在一旁,依次给压岁钱,都是新票子:二元、一元、五角不等。
儿女们接了钱,很激动,说“谢谢爸”。
守岁之夜,不准睡觉,都要精精神神。俗话说:一分精神,一分财;十分精神,抖起来。年夜饭,老三的父亲总要讲些旧话,比如“在家敬父母,胜似远烧香”。讲的是山东泰安一个打烧饼的和一位有钱的少爷,到泰山大成殿争当天下第一大孝子的事。父亲讲得有支有板儿、有景有物,人物实在,对话不多,听了不忘,有较高的审美层次。老三一干儿女,听得入神,觉得很亲切。
老三兄弟几个,数老三的大哥最出息。
老三的大哥在地方法院工作,是副院长。每值旧历年,他总要早几天把“东西”送到父母的家里。送的东西都很实惠。算一算,一二百元不止,足够老三的父母享一个正月。
旧历三十这一天,老三的大哥领着媳妇、女儿回家,事先一定要脱掉法院的制服,换上便装、布鞋,并告诉大嫂:“到家讲话做事要注意,不能乱说,不能神气,也没什么可神气的,是事儿,听着就是了,多干活!”
大嫂笑着说:“老王啊,老王……”
大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老三的二哥一律是旧历三十的下午,骑着摩托车,驮着二嫂回父母的家过年。
老三的二哥也出息得不错,是第一代企业家。现在已是几十万元户,常常去参加市里的一些会议。二哥回家过年,自然提的都是高档货。有山珍,有海味,有洋货,分东洋与西洋,都很名贵,看着浑身痛快。
临行前,老三的二哥也一定很严肃地对二嫂说:“回家过年,有几条注意,一不要化妆,全擦掉,土一点没关系。二不能摆阔,首饰什么的,不戴。要有老有少,不准瞎白话。家里的饭,好不好吃,一律认真吃。尤其爸妈做的,要说,真好吃。听见没有?”二嫂笑笑,说:“行,听你的。就当上庙了,一天怎么也忍了。”二哥说:“对!就是这意思。”
二哥二嫂回家过年,穿着都很朴素,甚至显得过了,头发也剪得很短,像五十年代的干事。老三家境不富裕,在一家杂志社当助理编辑,也是新潮作家。回家过年,带的礼品就很一般化,是四合礼。有四种奶油蛋糕,很艺术地组装在一个礼品盒子里,并用透明的玻璃纸罩着。
老三回家过年,从不戴他的贝雷帽,上衣兜也不插钢笔、油笔。事先也要对媳妇说:“嗯——到家,看别人,他们怎样,咱怎样,千万别出挑儿……”
老三的媳妇看了看他,轻蔑地说:“熊架①!”
……
自从老三兄妹四人分别嫁娶后,凡二十余载,都回家过年这事,居在一个城市的兄妹,并不事先通通电话,也不约定一下,基本上都回去。
今年过年,兄弟几个都事先做了安排,回家过年。
老三的母亲对孩子很好,很平等,也很亲近,总是喜着脸:“三儿回来啦。”“老二回来啦。”“老四也回来啦。”都柔柔的,儿子、女儿瞅着,心里就充满了温馨的阳光。
(有删改)
[注]①熊架,山东方言,意思是看看你那德行,看看你那样子。
3.阿成小说的语言雅与俗相间,请结合文本加以赏析。
参考答案:
1.①语言通俗易懂,具有生活气息。如“骨头贱得喊出了声”“大妹子”“老大哥”等。②语言具有乡土特色、地方特色。如“干了还逗虫子”“枣子还蛮甜嘛”。③语言生动形象,运用了比喻等手法。如“淋得像落汤鸡”“像一揪头发”。
2.①自然环境暗示:天气的阴沉、寒冷、恶劣,暗示倩芳生存的社会环境压抑与艰难。
②倩芳的客厅精致清雅,白梅姿若矫龙,墨竹万竿齐天,暗示女主人品味的不俗。
③梨花隐喻,作者将备受欺凌和歧视的女主人公比作经受风雪严寒或暴风雨的梨花,暗示她最终“枝垂花败”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3.①雅:叙述语言使用文言词、书面语。如“凭栏”“方能”“一任江天”“颇为”“遂心”“瞅着”“每值”等词语,读来古朴高雅,富有韵味。
②俗:人物语言使用方言、口语。如“瞎白话”“熊架”“咱怎样”“出挑儿”“票子”等方言与口语,简洁明快,使小说生活气息浓郁。
③“雅”与“俗”融为一体,使语言既富有文采,又充满生活气息,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之美,叙事风格独特,能很好地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