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文学类文本专题训练双文本比较异同(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3届高考专题复习:文学类文本专题训练双文本比较异同(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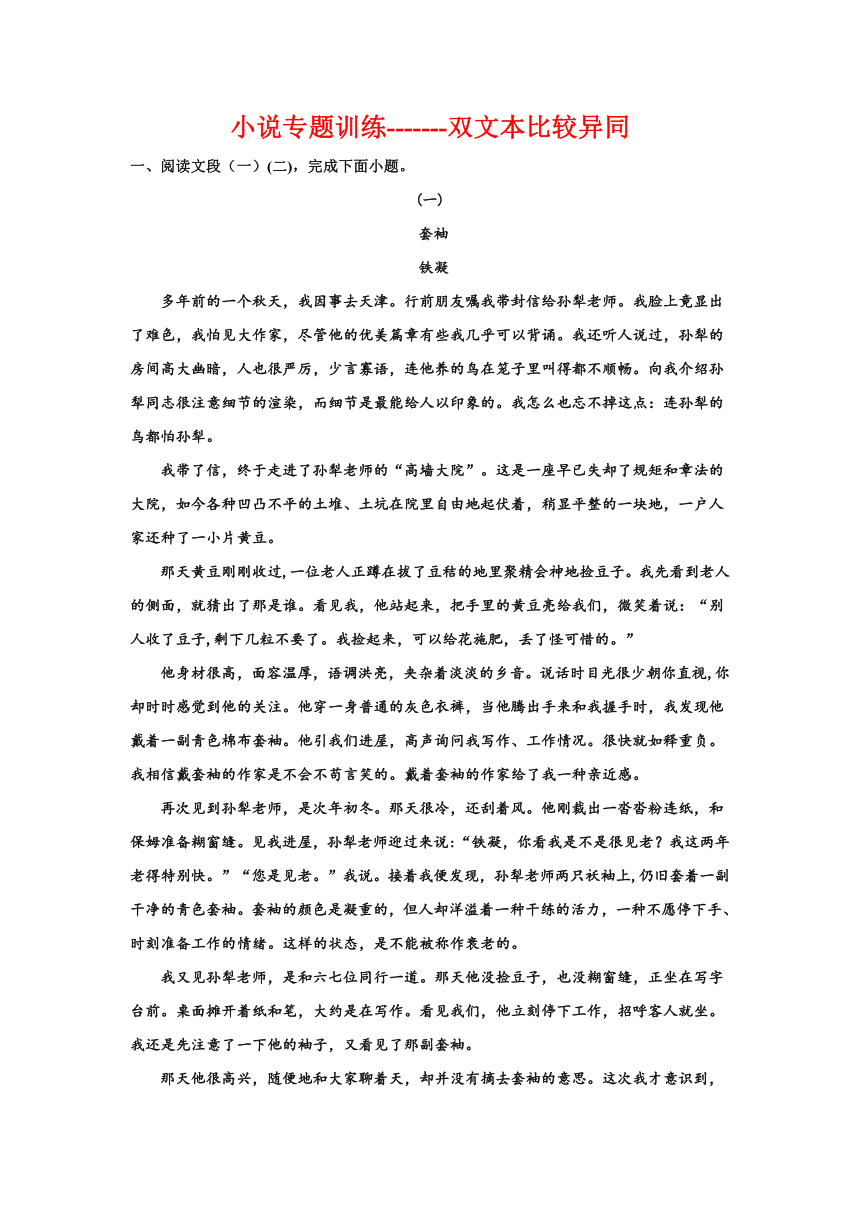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5.1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通用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3-05-06 06:44:11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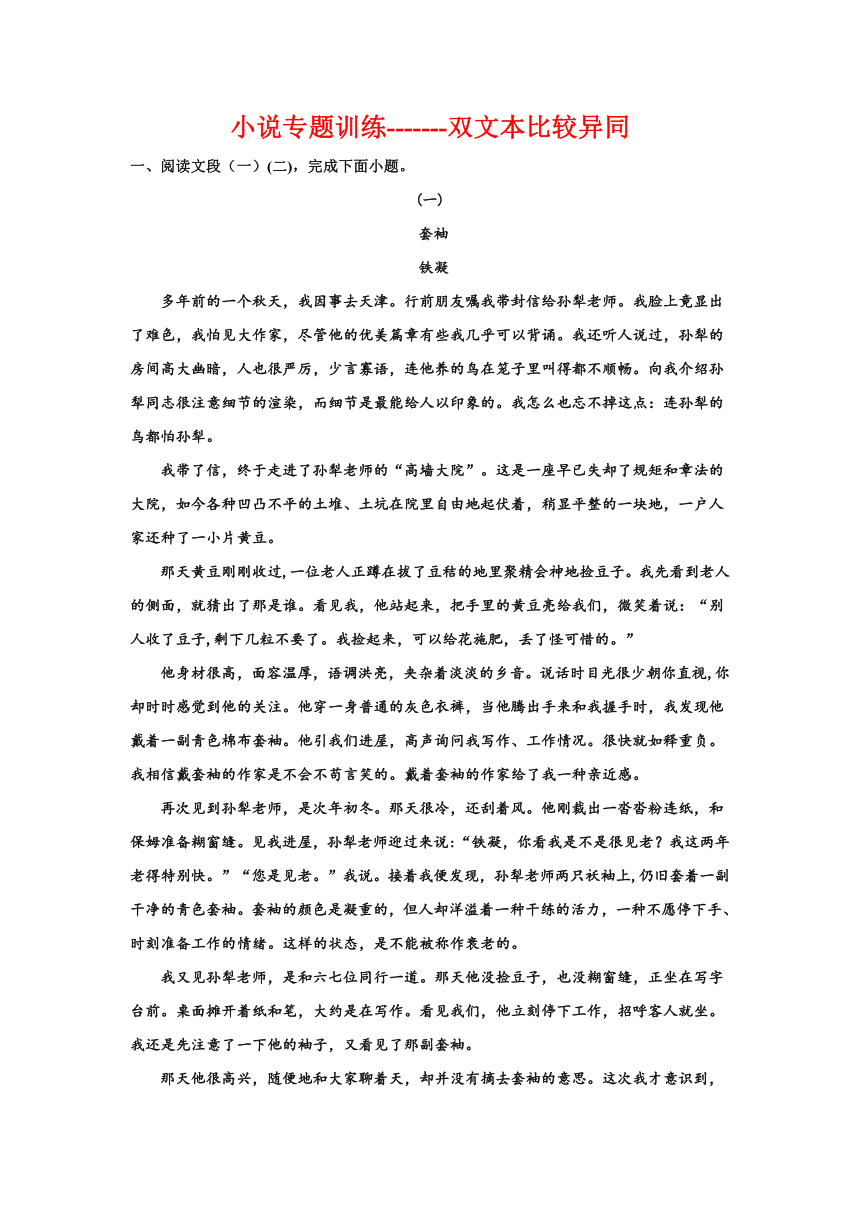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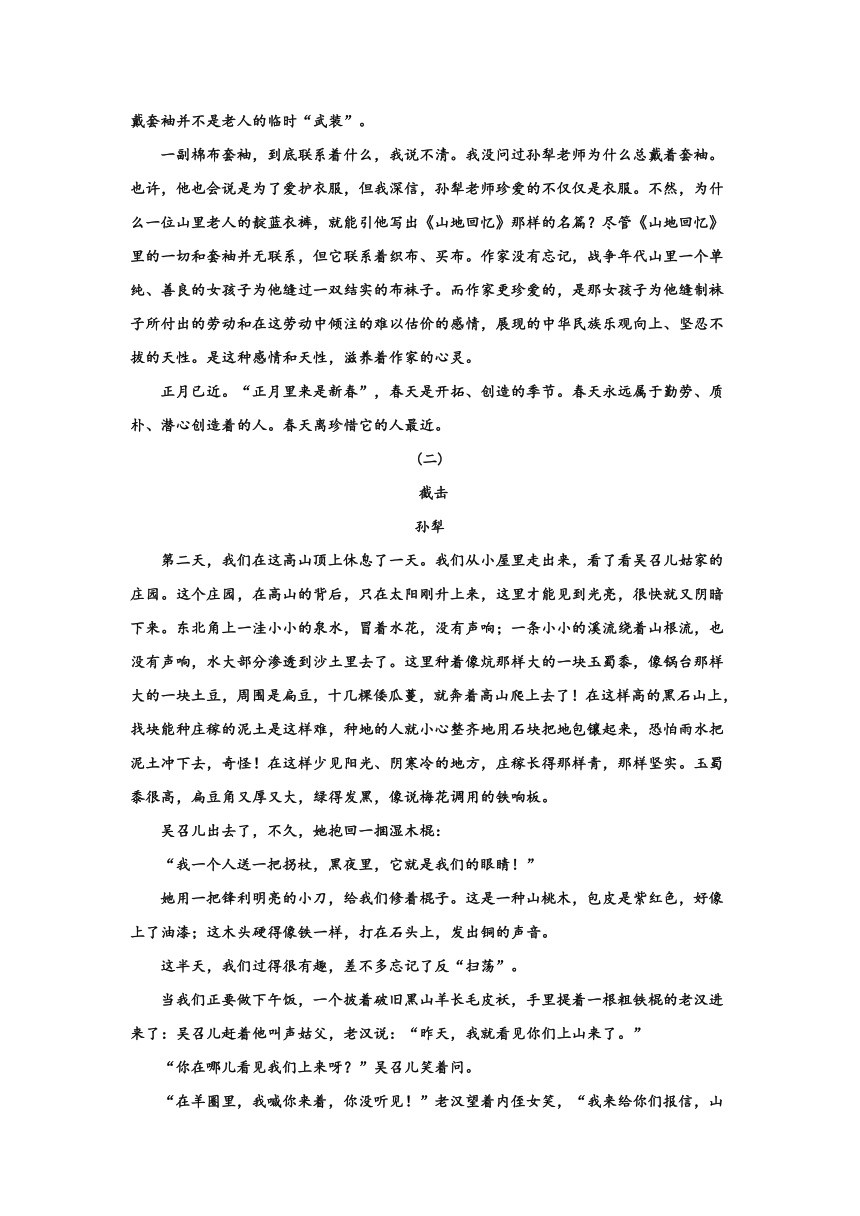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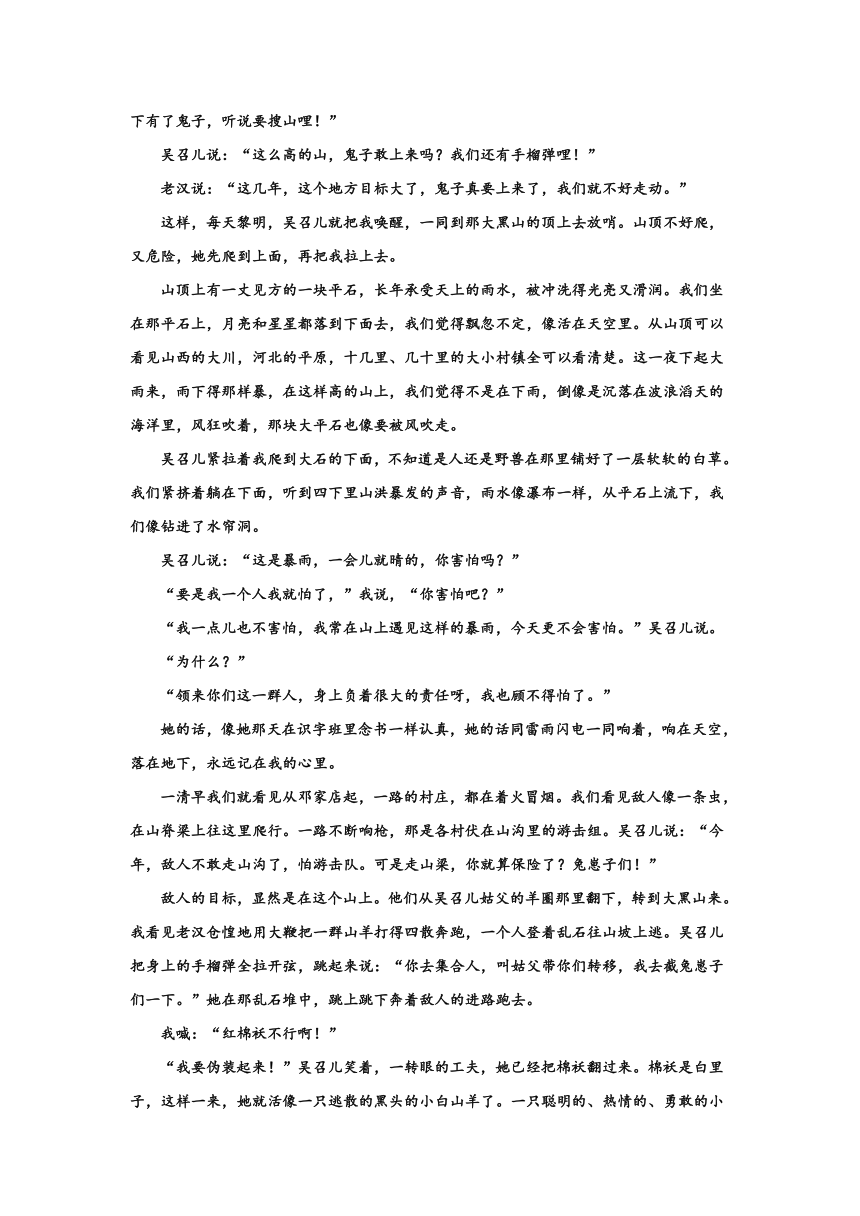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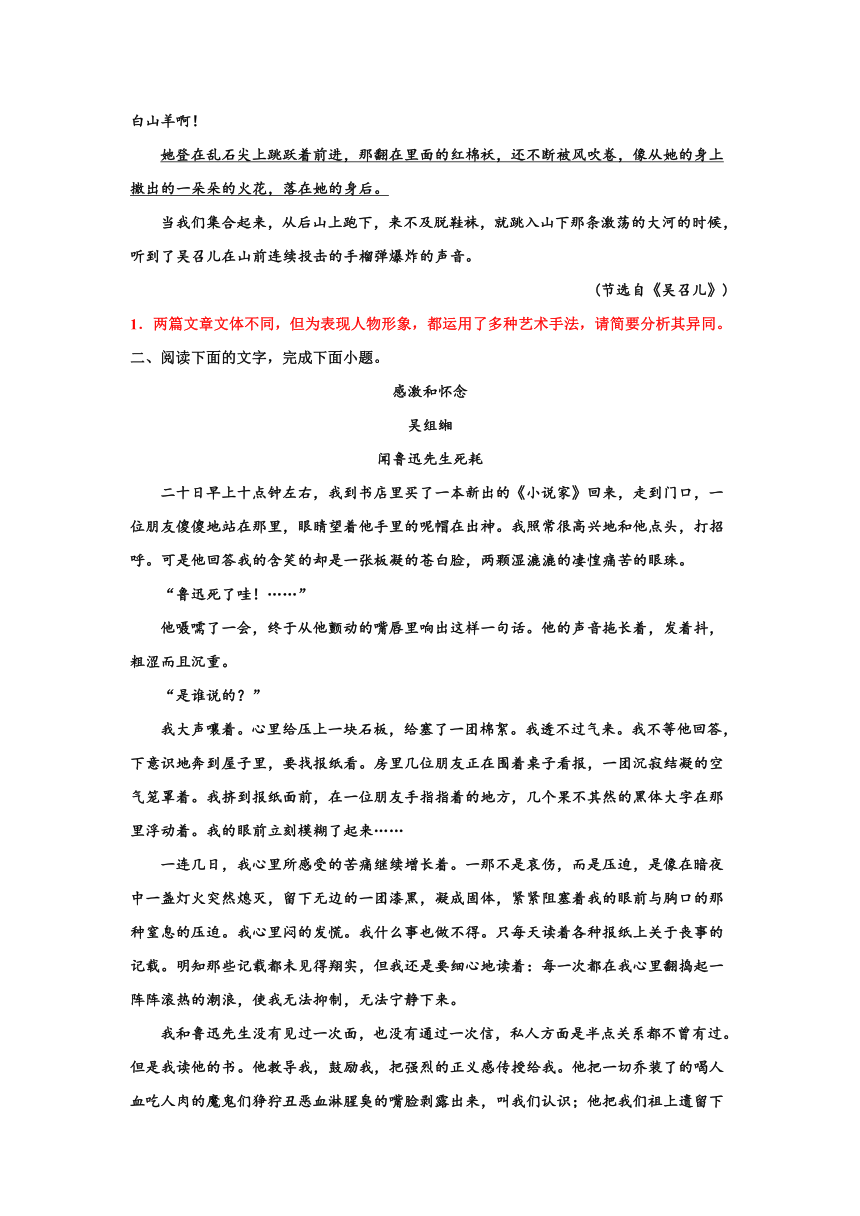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小说专题训练-------双文本比较异同
一、阅读文段(一)(二),完成下面小题。
(一)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您是见老。”我说。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二)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1.两篇文章文体不同,但为表现人物形象,都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其异同。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感激和怀念
吴组缃
闻鲁迅先生死耗
二十日早上十点钟左右,我到书店里买了一本新出的《小说家》回来,走到门口,一位朋友傻傻地站在那里,眼睛望着他手里的呢帽在出神。我照常很高兴地和他点头,打招呼。可是他回答我的含笑的却是一张板凝的苍白脸,两颗湿漉漉的凄惶痛苦的眼珠。
“鲁迅死了哇!……”
他嗫嚅了一会,终于从他颤动的嘴唇里响出这样一句话。他的声音拖长着,发着抖,粗涩而且沉重。
“是谁说的?”
我大声嚷着。心里给压上一块石板,给塞了一团棉絮。我透不过气来。我不等他回答,下意识地奔到屋子里,要找报纸看。房里几位朋友正在围着桌子看报,一团沉寂结凝的空气笼罩着。我挤到报纸面前,在一位朋友手指指着的地方,几个果不其然的黑体大字在那里浮动着。我的眼前立刻模糊了起来……
一连几日,我心里所感受的苦痛继续增长着。一那不是哀伤,而是压迫,是像在暗夜中一盏灯火突然熄灭,留下无边的一团漆黑,凝成固体,紧紧阻塞着我的眼前与胸口的那种窒息的压迫。我心里闷的发慌。我什么事也做不得。只每天读着各种报纸上关于丧事的记载。明知那些记载都未见得翔实,但我还是要细心地读着:每一次都在我心里翻捣起一阵阵滚热的潮浪,使我无法抑制,无法宁静下来。
我和鲁迅先生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次信,私人方面是半点关系都不曾有过。但是我读他的书。他教导我,鼓励我,把强烈的正义感传授给我。他把一切乔装了的喝人血吃人肉的魔鬼们狰狞丑恶血淋腥臭的嘴脸剥露出来,叫我们认识;他把我们祖上遗留下来的卑怯愚昧种种的奴隶相一一指说出来,叫我们认识。他永远站在被凌辱被损害的这一边,永远与强暴者搏斗。他教我们振奋起来,一同抗战。他原谅我们的幼稚,叫我们不要顾忌自己的缺点。我的一点聪明,智慧,一点做人的态度,要是仔细推溯,大半是他启发扶助起来的。我时时刻刻都觉得他在跟前。他的呼吸我感觉得到,他的脉的跳动,血的沸热我感觉得到。他的愤怒的眼睛我看得见,他的慈爱的脸庞我看得见。一个新鲜活跳的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眼前。
早前几个月,我听到他重病的消息。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处谈心,我说他不比高尔基先生之于苏联以及苏联的大众与青年。我们的社会与民族是正在艰苦急迫的情境中,我们的大众与青年正需要从他跟前得到教导与勇气。——像在暗夜中,我们需要灯火。
然而如今竟突然传来这样的噩耗!我第一次经验到死耗所给予的最大的痛楚。
(发表于1936年,有删改)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在鲁迅诞生百年纪念的日子,我却总想着他逝世那些年的光景;简直挥之不去。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我永远记得这一天,噩耗传来了;当时我只能从上海几家报纸了解一些情况。有许多天,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捧着报纸止不住流泪,感到未曾经验过的悲恸。
鲁迅比我年长二十七岁,我从少年初能知事即读他的书。开初并不能真懂,只觉得泼辣而富有意趣。到后来,读后能渐渐触发我产生许多联想,教我关心现实,热爱生活,进而探索自然与人生,一直归总到对国情,对社会的绺心忧念;并且注意检验自己,想着应该怎样看事,怎么做人。他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短文,我都尽力找来钻研品味。多少警句我能记诵;多少言论行事,我多熟知。
我跟先生没有一点私人交往。多年以来,我只是他的一个倾心敬仰者,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次信。我从来没有以为鲁迅会知道我这么个人。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就聘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有一天王瑶同志跟我说:“鲁迅有几封给日本朋友的信谈到你,你知道吗?”这使我大为惊诧。
把书翻出看,啊!是一本香港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里面有五六封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信件。我读了这几封信,心如浪涛翻腾,不能自安。当时对王瑶说:“唉!真该死!我一直以为鲁迅不知道我这个人!”
面对鲁迅的手泽,不由得不心跳冒汗。看到鲁迅一片关爱我的热肠,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但那种目光四射,为新文化不遗一点微力的伟大旗手的崇高的心,是我所熟悉的。
时光恍如急滩流水,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此纪念之日,想起往事,我仍然痛感当年鲁迅死得过早。今天看来,他患的并非什么不治之症。今天举目所见,何处不是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统计说,新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可惊地大大增长了。由此想到我们鲁迅,当年他若能稍自珍卫,一直活到今天,那会为我们中华民族、为世界人类,增添多少社会主义新的真美善的财富,那会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
但这毕竟是我的妄想。而且当年鲁迅对自己绝不是这么想的。
“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不如赶忙工作而少活几年!”这是鲁迅病危时候说的话。
(发表于1981年,有删改)
2.两则散文写作于不同时期,写作内容上有哪些异同?请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琐记(节选)
鲁迅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isacat。”“Isita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畔,唵哗!唵!耶!吽!!!”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用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
这回不是Itisacat了,是DerMann,DieWeib,Das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
自己仍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摘自《朝花夕拾》,有删改)
文本二:
1926年,正是鲁迅思想发生突变的前夕,当时军阀统治残酷,环境特别恶劣,斗争也很艰苦。鲁迅曾亲自参加了女师大学潮,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爱国青年的鲜血,北方军阀镇压人们的“武功”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的嘴脸,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由北京辗转厦门,困守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阁楼上,心情苦闷孤寂,思想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这流离迁徙的一年“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写成的这些回忆性散文,正是他前期生活和思想发展变化的产物。虽是回首往事,但鲁迅不是回避现实去沉醉甘美的回忆,也不是减轻痛苦去消遣休息,而是在舔尽身上伤口血痕的战斗间歇,去环顾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启示青年为进入新的战斗,做好进击的准备。在《朝花夕拾》这部散文集里,鲁迅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同“五四”以后的现实紧密联结在一起,用优美的文笔、深刻的议论、浓郁的抒情,创作了这组交织着记忆芬芳和战斗火花的散文。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3.作者在雷电学堂和矿路学堂所学功课有怎样的异同?
答案
1.相同点:两篇文章都运用了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形象。从对孙犁的语言描写中可体现出孙犁勤俭朴实、平易近人的形象;从对吴召儿的语言描写中体现出吴召儿机智敏捷、热情负责、勇敢无畏的形象。第一篇文章对孙犁的套袖进行了细节描写,体现了孙犁的朴实;第二篇文章对吴召儿截击敌人时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进行了细节描写,体现了吴召儿的机智敏捷,勇敢无畏。
不同点:《套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了欲扬先抑法,开篇渲染孙犁老师很严厉,“我”怕见孙犁老师,欲扬先抑,为后文写我对孙犁老师印象的转变以及孙犁老师的平易近人做铺垫。《截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的是直接描写。文中对吴召儿的语言动作都采用的是直接描写,体现了吴召儿的机智敏捷,热情负责,勇敢无畏。
2.同:两则散文都借鲁迅与“我”相关的事件来抒发对已故伟人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异:①写作切入点不同,第一则散文从青年对鲁迅逝世的直接反应写起,第二则散文从时光流逝、情感沉淀后的回想写起;②内容侧重点不同,第一则散文为“我”单方面对鲁迅的感激、怀念,第二则散文以信件交代了鲁迅对“我”的关爱,刷新了以往的固有认知。
3.①同:都开设外文课和传统汉文课;②异:矿路学堂开设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等新鲜的学科,而雷电学堂没有这些科目
一、阅读文段(一)(二),完成下面小题。
(一)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您是见老。”我说。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二)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1.两篇文章文体不同,但为表现人物形象,都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其异同。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感激和怀念
吴组缃
闻鲁迅先生死耗
二十日早上十点钟左右,我到书店里买了一本新出的《小说家》回来,走到门口,一位朋友傻傻地站在那里,眼睛望着他手里的呢帽在出神。我照常很高兴地和他点头,打招呼。可是他回答我的含笑的却是一张板凝的苍白脸,两颗湿漉漉的凄惶痛苦的眼珠。
“鲁迅死了哇!……”
他嗫嚅了一会,终于从他颤动的嘴唇里响出这样一句话。他的声音拖长着,发着抖,粗涩而且沉重。
“是谁说的?”
我大声嚷着。心里给压上一块石板,给塞了一团棉絮。我透不过气来。我不等他回答,下意识地奔到屋子里,要找报纸看。房里几位朋友正在围着桌子看报,一团沉寂结凝的空气笼罩着。我挤到报纸面前,在一位朋友手指指着的地方,几个果不其然的黑体大字在那里浮动着。我的眼前立刻模糊了起来……
一连几日,我心里所感受的苦痛继续增长着。一那不是哀伤,而是压迫,是像在暗夜中一盏灯火突然熄灭,留下无边的一团漆黑,凝成固体,紧紧阻塞着我的眼前与胸口的那种窒息的压迫。我心里闷的发慌。我什么事也做不得。只每天读着各种报纸上关于丧事的记载。明知那些记载都未见得翔实,但我还是要细心地读着:每一次都在我心里翻捣起一阵阵滚热的潮浪,使我无法抑制,无法宁静下来。
我和鲁迅先生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次信,私人方面是半点关系都不曾有过。但是我读他的书。他教导我,鼓励我,把强烈的正义感传授给我。他把一切乔装了的喝人血吃人肉的魔鬼们狰狞丑恶血淋腥臭的嘴脸剥露出来,叫我们认识;他把我们祖上遗留下来的卑怯愚昧种种的奴隶相一一指说出来,叫我们认识。他永远站在被凌辱被损害的这一边,永远与强暴者搏斗。他教我们振奋起来,一同抗战。他原谅我们的幼稚,叫我们不要顾忌自己的缺点。我的一点聪明,智慧,一点做人的态度,要是仔细推溯,大半是他启发扶助起来的。我时时刻刻都觉得他在跟前。他的呼吸我感觉得到,他的脉的跳动,血的沸热我感觉得到。他的愤怒的眼睛我看得见,他的慈爱的脸庞我看得见。一个新鲜活跳的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眼前。
早前几个月,我听到他重病的消息。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处谈心,我说他不比高尔基先生之于苏联以及苏联的大众与青年。我们的社会与民族是正在艰苦急迫的情境中,我们的大众与青年正需要从他跟前得到教导与勇气。——像在暗夜中,我们需要灯火。
然而如今竟突然传来这样的噩耗!我第一次经验到死耗所给予的最大的痛楚。
(发表于1936年,有删改)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在鲁迅诞生百年纪念的日子,我却总想着他逝世那些年的光景;简直挥之不去。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我永远记得这一天,噩耗传来了;当时我只能从上海几家报纸了解一些情况。有许多天,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捧着报纸止不住流泪,感到未曾经验过的悲恸。
鲁迅比我年长二十七岁,我从少年初能知事即读他的书。开初并不能真懂,只觉得泼辣而富有意趣。到后来,读后能渐渐触发我产生许多联想,教我关心现实,热爱生活,进而探索自然与人生,一直归总到对国情,对社会的绺心忧念;并且注意检验自己,想着应该怎样看事,怎么做人。他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短文,我都尽力找来钻研品味。多少警句我能记诵;多少言论行事,我多熟知。
我跟先生没有一点私人交往。多年以来,我只是他的一个倾心敬仰者,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次信。我从来没有以为鲁迅会知道我这么个人。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就聘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有一天王瑶同志跟我说:“鲁迅有几封给日本朋友的信谈到你,你知道吗?”这使我大为惊诧。
把书翻出看,啊!是一本香港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里面有五六封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信件。我读了这几封信,心如浪涛翻腾,不能自安。当时对王瑶说:“唉!真该死!我一直以为鲁迅不知道我这个人!”
面对鲁迅的手泽,不由得不心跳冒汗。看到鲁迅一片关爱我的热肠,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但那种目光四射,为新文化不遗一点微力的伟大旗手的崇高的心,是我所熟悉的。
时光恍如急滩流水,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此纪念之日,想起往事,我仍然痛感当年鲁迅死得过早。今天看来,他患的并非什么不治之症。今天举目所见,何处不是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统计说,新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可惊地大大增长了。由此想到我们鲁迅,当年他若能稍自珍卫,一直活到今天,那会为我们中华民族、为世界人类,增添多少社会主义新的真美善的财富,那会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
但这毕竟是我的妄想。而且当年鲁迅对自己绝不是这么想的。
“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不如赶忙工作而少活几年!”这是鲁迅病危时候说的话。
(发表于1981年,有删改)
2.两则散文写作于不同时期,写作内容上有哪些异同?请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琐记(节选)
鲁迅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isacat。”“Isita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畔,唵哗!唵!耶!吽!!!”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用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
这回不是Itisacat了,是DerMann,DieWeib,Das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
自己仍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摘自《朝花夕拾》,有删改)
文本二:
1926年,正是鲁迅思想发生突变的前夕,当时军阀统治残酷,环境特别恶劣,斗争也很艰苦。鲁迅曾亲自参加了女师大学潮,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爱国青年的鲜血,北方军阀镇压人们的“武功”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的嘴脸,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由北京辗转厦门,困守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阁楼上,心情苦闷孤寂,思想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这流离迁徙的一年“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写成的这些回忆性散文,正是他前期生活和思想发展变化的产物。虽是回首往事,但鲁迅不是回避现实去沉醉甘美的回忆,也不是减轻痛苦去消遣休息,而是在舔尽身上伤口血痕的战斗间歇,去环顾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启示青年为进入新的战斗,做好进击的准备。在《朝花夕拾》这部散文集里,鲁迅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同“五四”以后的现实紧密联结在一起,用优美的文笔、深刻的议论、浓郁的抒情,创作了这组交织着记忆芬芳和战斗火花的散文。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3.作者在雷电学堂和矿路学堂所学功课有怎样的异同?
答案
1.相同点:两篇文章都运用了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形象。从对孙犁的语言描写中可体现出孙犁勤俭朴实、平易近人的形象;从对吴召儿的语言描写中体现出吴召儿机智敏捷、热情负责、勇敢无畏的形象。第一篇文章对孙犁的套袖进行了细节描写,体现了孙犁的朴实;第二篇文章对吴召儿截击敌人时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进行了细节描写,体现了吴召儿的机智敏捷,勇敢无畏。
不同点:《套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了欲扬先抑法,开篇渲染孙犁老师很严厉,“我”怕见孙犁老师,欲扬先抑,为后文写我对孙犁老师印象的转变以及孙犁老师的平易近人做铺垫。《截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的是直接描写。文中对吴召儿的语言动作都采用的是直接描写,体现了吴召儿的机智敏捷,热情负责,勇敢无畏。
2.同:两则散文都借鲁迅与“我”相关的事件来抒发对已故伟人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异:①写作切入点不同,第一则散文从青年对鲁迅逝世的直接反应写起,第二则散文从时光流逝、情感沉淀后的回想写起;②内容侧重点不同,第一则散文为“我”单方面对鲁迅的感激、怀念,第二则散文以信件交代了鲁迅对“我”的关爱,刷新了以往的固有认知。
3.①同:都开设外文课和传统汉文课;②异:矿路学堂开设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等新鲜的学科,而雷电学堂没有这些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