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北师大版必修三3.10《秦腔》课件(54张)
文档属性
| 名称 | 高中语文北师大版必修三3.10《秦腔》课件(54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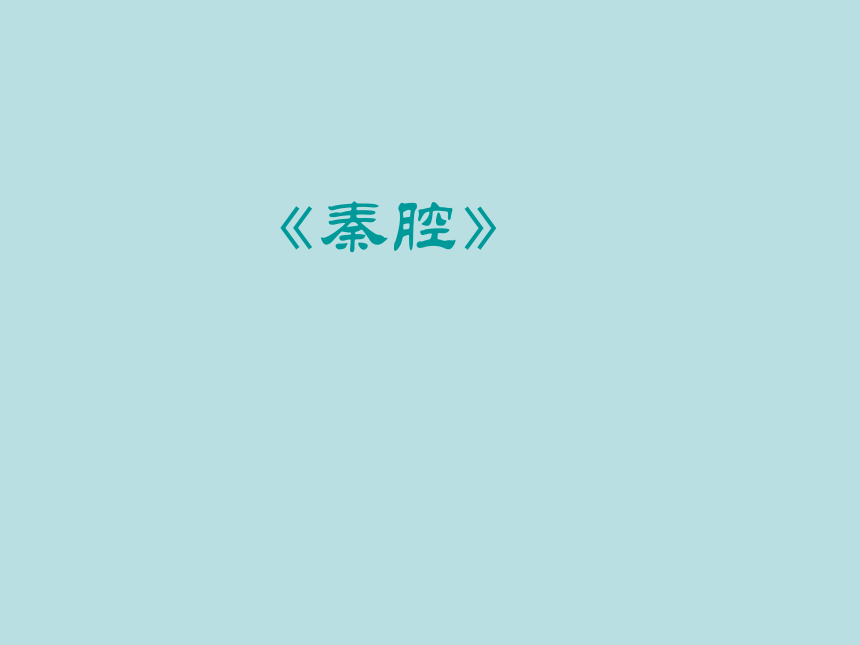 | |
| 格式 | zip | ||
| 文件大小 | 535.9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北师大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15-08-28 14:36:3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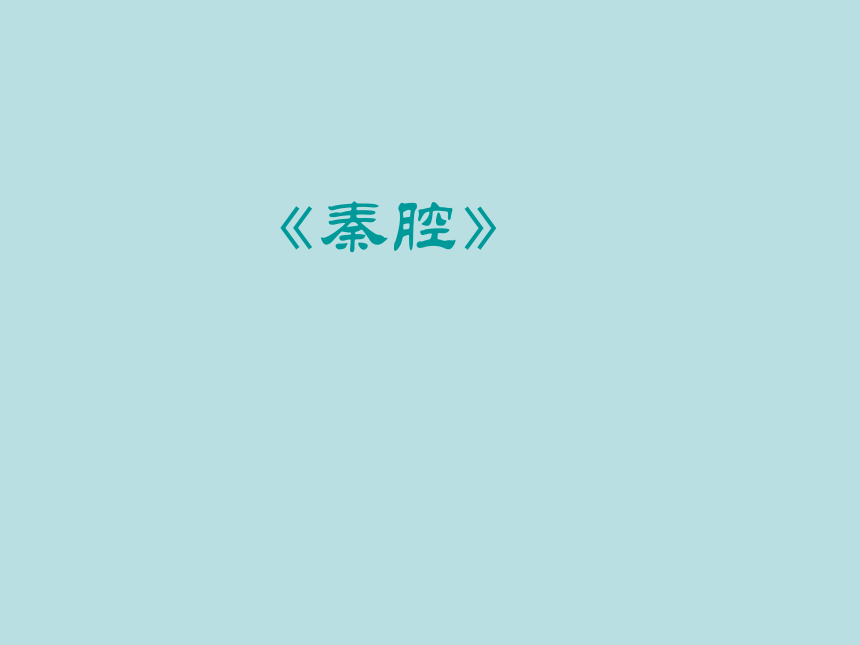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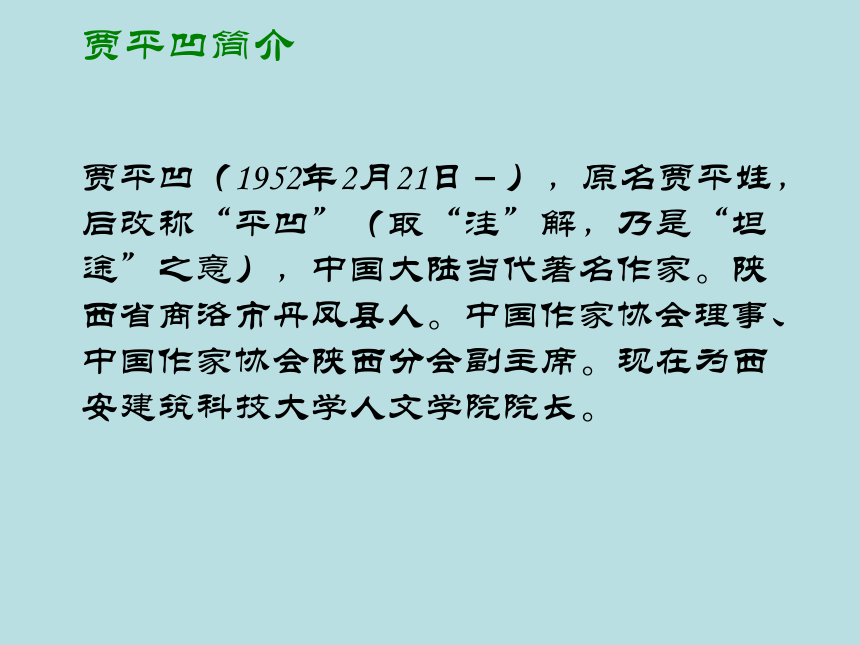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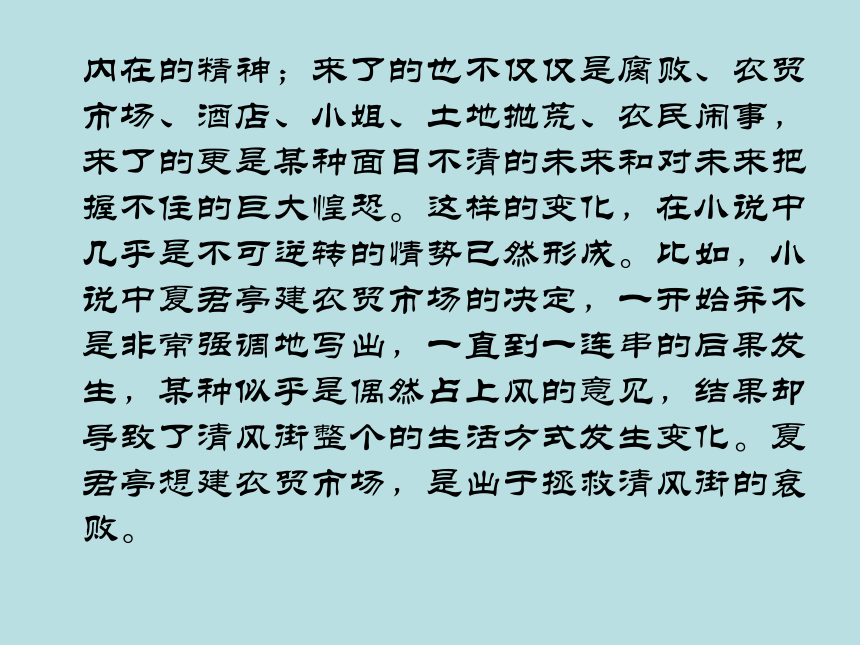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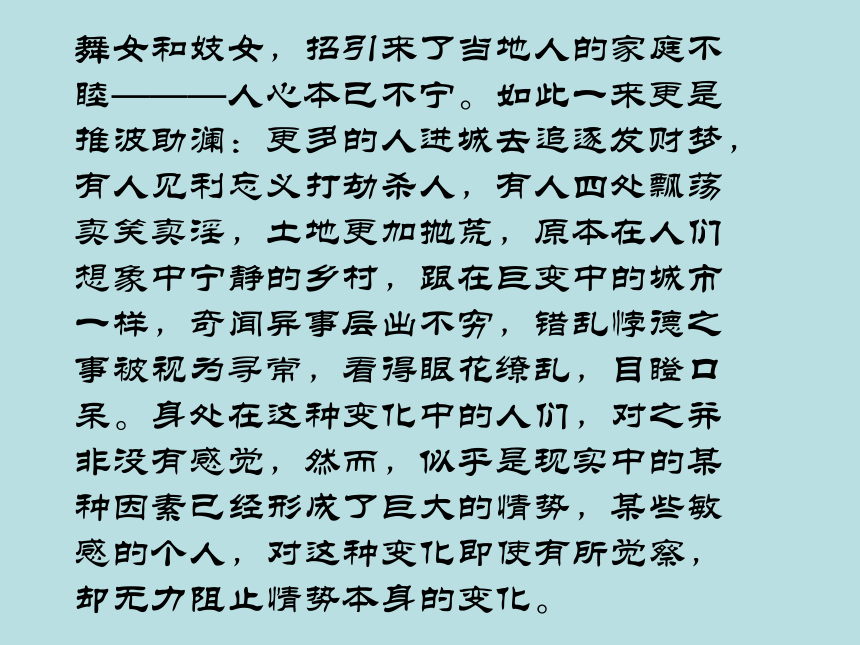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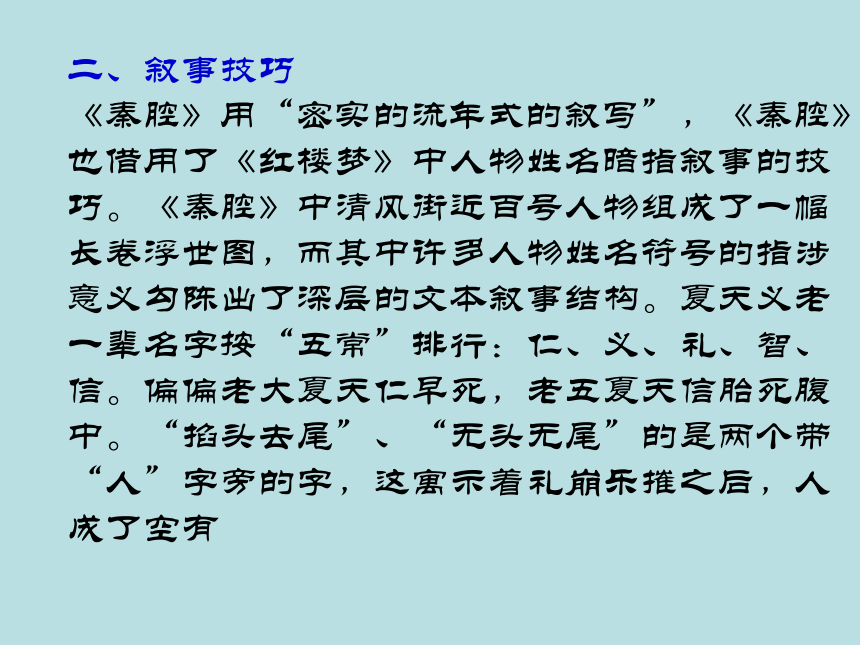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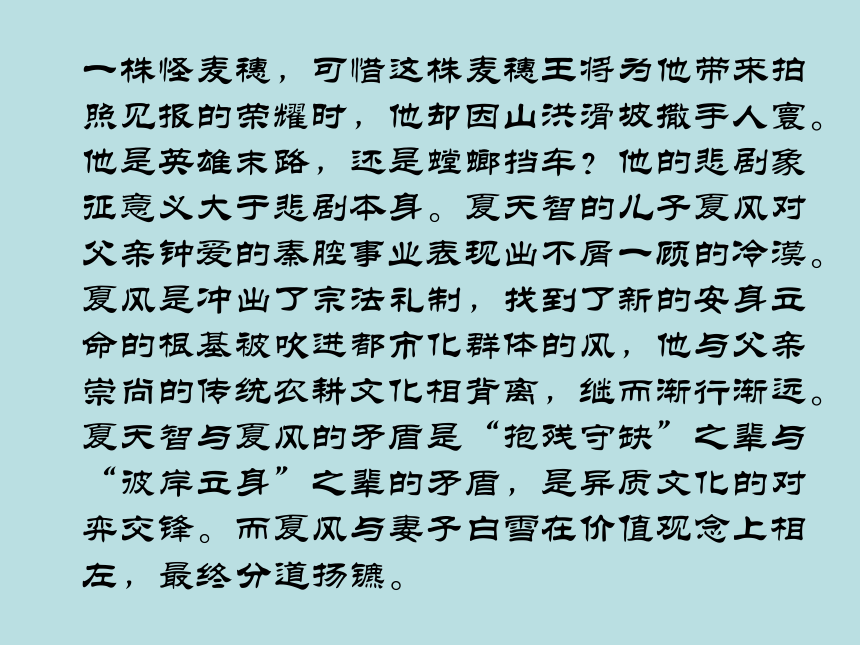
文档简介
课件54张PPT。《秦腔》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原名贾平娃,后改称“平凹”(取“洼”解,乃是“坦途”之意),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现在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贾平凹简介一、叙事节奏
贾平凹《秦腔》的叙事节奏犹如交谊舞中的慢四步。理解《秦腔》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便在理解它的叙事本身。 《秦腔》的叙事速度很慢,它所写的不过是清风街一年多时间里的事情,但由于缓慢的叙事节奏和密实的细节,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感觉却像写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沧桑巨变,借用张爱玲的一个比喻,也许可以说,《秦腔》中的时间的移动,几乎像日光,简直让人感觉不到它的移动,然而却是倏忽的。这样的缓慢的叙事速度绝非无因。 叙事艺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叙事速度,本身便是对现实变化的感应。《秦腔》所写的是乡村社会的陈年流水账,一天一天琐碎泼烦的日子,每天的日子似乎都没怎么变或者说,其中小小的变化似乎不值得太过注意,然而一天天的变化一点一点积累着,一年多的时间积累下来,最后的结果却类乎天翻地覆。不知不觉中,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巨变而且是让人忧心的巨变:不想让它走的一点点走了,不想让它来的一点一点来了走了的还不仅仅是朴素的信义、道德、风俗、人情,更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精神;来了的也不仅仅是腐败、农贸市场、酒店、小姐、土地抛荒、农民闹事,来了的更是某种面目不清的未来和对未来把握不住的巨大惶恐。这样的变化,在小说中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情势已然形成。比如,小说中夏君亭建农贸市场的决定,一开始并不是非常强调地写出,一直到一连串的后果发生,某种似乎是偶然占上风的意见,结果却导致了清风街整个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夏君亭想建农贸市场,是出于拯救清风街的衰败。
他展示了蓝图,不看大家反应,拿了树棍在墙上划着算式给大家讲,说毕了,他坐回自己的位子,拿眼睛看大家。君亭本以为大家会鼓掌,会说:好! 至少,也是每个脸都在笑。但是,会议室里竟一时安安静静,安静得像是死了人。这段引文代表的细节,这样的多少有些无趣的“现代”想象和规划式的思维方式。农贸市场的建立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效益,有先见的人借着这个机会模仿城市建立了酒楼,酒楼招引来了大吃大喝,招引来了投机客商,招引来了舞女和妓女,招引来了当地人的家庭不睦———人心本已不宁。如此一来更是推波助澜:更多的人进城去追逐发财梦,有人见利忘义打劫杀人,有人四处飘荡卖笑卖淫,土地更加抛荒,原本在人们想象中宁静的乡村,跟在巨变中的城市一样,奇闻异事层出不穷,错乱悖德之事被视为寻常,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身处在这种变化中的人们,对之并非没有感觉,然而,似乎是现实中的某种因素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情势,某些敏感的个人,对这种变化即使有所觉察,却无力阻止情势本身的变化。
一切都在变,那种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和对土地的感情,似乎也面临崩溃,且将永远流失,一去不回。对于这种变化,贾平凹在《后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写《秦腔》时的思想感情: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 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站在街巷的石碾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快地要消失了吗? 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了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了吗? 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 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贾平凹就这样沉醉在中场过后的慢四步中,节 奏缓慢得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移动……
二、叙事技巧
《秦腔》用“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秦腔》也借用了《红楼梦》中人物姓名暗指叙事的技巧。《秦腔》中清风街近百号人物组成了一幅长卷浮世图,而其中许多人物姓名符号的指涉意义勾陈出了深层的文本叙事结构。夏天义老一辈名字按“五常”排行:仁、义、礼、智、信。偏偏老大夏天仁早死,老五夏天信胎死腹中。“掐头去尾”、“无头无尾”的是两个带“人”字旁的字,这寓示着礼崩乐摧之后,人成了空有人形而没人性的两足动物。把兄弟的“五常”之序拦腰斩断。夏天礼之死,即表示从此无神可祀,人于是彻底器化,异化为无宗教无信仰形而下的两脚兽了。在夏家的下一辈中,人丁较旺的夏天义有五个儿子,五个兄弟不仅猥琐龌龊,对父母也没多少孝敬,他生养的五个儿子与秦腔名句“窦燕山教五子,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形成强烈的反讽,正可谓:仁义礼智信,金玉满堂瞎。而在夏天义身上,天义何在呢?他的威力不过是指挥一个疯子,一个哑巴和一只狗;他的成功,不过是发现了一株怪麦穗,可惜这株麦穗王将为他带来拍照见报的荣耀时,他却因山洪滑坡撒手人寰。他是英雄末路,还是螳螂挡车?他的悲剧象征意义大于悲剧本身。夏天智的儿子夏风对父亲钟爱的秦腔事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冷漠。夏风是冲出了宗法礼制,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的根基被吹进都市化群体的风,他与父亲崇尚的传统农耕文化相背离,继而渐行渐远。夏天智与夏风的矛盾是“抱残守缺”之辈与“彼岸立身”之辈的矛盾,是异质文化的对弈交锋。而夏风与妻子白雪在价值观念上相左,最终分道扬镳。
三、叙事道具
在叙事中,贾平凹善用秦腔乐谱、对联和绘画,进行隔断转换、时空挪移构筑多维的艺术符号世界。一是秦腔乐谱的穿插。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曲谱对于不懂秦腔或不识简谱的读者,可谓专业性过强。实际上它们是作为文本的情感线索贯穿全文,完全成为一种视觉上的连接符号,作为整个文本叙述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它们的存在也主要出于叙事结构上的考虑。秦人离不开秦腔,一曲曲唱段、一个个曲牌抒发着秦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秦腔在这部作品里,结构上能起到隔断转换、时空挪移的作用,从欣赏心理上看也有变化和停歇。尤其能调动欣赏者在旋律和文字之间的同感,从一个新的渠道激发读者的艺术联想和欣赏再创造。音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情绪、环境氛围的表现中发挥作用,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这部小说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线性的文字叙述有时难于表达的团块状或云雾状的情绪、感受和意会。这种描写在当代小说中都很少见到。而小说描写的县剧团的炎凉和演员命运的起伏,也成为时代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种症候。在整部小说中,秦声弥散为一种气场,秦韵流贯为一股魂脉而无处不在。它构成小说、小说中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所共有的一种文化和精神质地。更重要的是,秦腔构成夏天智和白雪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命运、气质和精神寄托,构成他们生命
本体的一部分。秦腔人文使他们有了标志性的旋律和音乐形象。白雪因秦腔而美丽,用秦腔来表达爱,在秦腔音乐中结婚、孕育新的生命,因舍不得秦腔而留在县上,以致和省城的文人丈夫少了共同语言,直到在苦音慢板中倔强着黯然离异。夏天智在村里安装高音喇叭播放秦腔是他退休后自找的职业。他是性情中人,发乎情而止于礼,是生命的呐喊者却又对社会人生有较清醒的评断,能以如此乃是得益于秦腔。秦腔戏文和戏中人物的许多价值标准成为他人生的精神坐标。他视儿媳白雪如亲生女儿,是因亲情,更是因了秦腔和秦腔戏文的价值标准。白雪要生产了,他又以表达又一代新生命在心中引燃的激情,竟胡琴拉起激越恣肆的旋律迎接孙女的降生。得知儿子和白雪终于要离婚,痛惜至极的他当下收白雪为女儿,喊“喇叭打开,放《辕门斩子》,以示对儿子的愤恨。他自己也在催人心魂的秦腔中告别这个世界。二是对联的运用。对联是汉字独有的文学样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秦腔》中,十多副对联别开生面地构成一种点缀性叙事,其功能正如《红楼梦》中的曲赋或判词。赵宏声捧出的第一副对联是戏楼联: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这在《秦腔》整部叙事中是个提纲挈领的楔子,犹如《红楼梦》开篇中的“满纸荒唐言”或者如跛足道人吟唱的“好了歌”。赵宏声是《秦腔》中处处应景凑趣的人,他的每一副对联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叙事道具。与《秦腔》乡土叙事终结的寓意紧密呼应。三是绘画的补叙。在《秦腔》中,作者绘制的四幅插图也与文本构成了互文衬语叙事。
“一条线的故事”和“靠在树干上蹭痒痒”两幅插图生动展现了秦地的乡土文化风貌,而这正是夏天义、夏天智等人毕生赖以生存的根。《秦腔》文本中简而有意的墨写式插图更是承袭了“言、象、意”的中国传统绘画式叙事。《秦腔》创造了不同于作者以往的叙事方法,取得了特别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对这一叙事方法的陌生,人们在阅读时会有些不适应,难免会产生所谓的“难度”。然而,一个艺术家要超越自我,就必须不断地寻找创新之路。塞米利安曾说“赋予不具有形式的素材以形式,这是小说家的艰巨使命”,《秦腔》便完成了这样一次使命。正如作家所言,“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心酸。
《秦腔》的复调特征
如果借用俄国人巴赫金的术语,《秦腔》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复调小说”,万言的《秦腔》其实是一场充满了各种不同声音的大型对话,是一曲沉郁悲凉、浑然杂陈的民间交响乐。无论是小说的文体还是精神,《秦腔》都为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艺术探索。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从文体上揭示出《秦腔》的大型对话体结构,我们就无法真正全面地理解《秦腔》的内在精神旨趣,《秦腔》对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形态的突破意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一、众声喧哗与文化冲突
《秦腔》具备真正的多声部性和对话性,它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复调小说。众所周知,巴赫金是在借鉴复调音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复调小说的概念的,而《秦腔》这个题目本身就来源于中国西部一种历史久远的民间剧种(音乐)。这次用“秦腔”来做长篇小说的题目,却隐含着作者小说观念的某种新变,即小说的音乐化。读者不会没有注意到,《秦腔》中频繁地出现了一段又一段的秦腔曲谱,作者有意让音乐直接走进小说文本之中,而且这些秦腔曲谱变化多端,错落有致,既有慢板也有滚板,既有欢音也有苦音,形成了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音乐风景。当然,这不过是《秦腔》在表面上的、象征性的多声部特征。真正为这部长篇带来复调品格的是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其所开创的叙述话语空间。《秦腔》选择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小说通过一个名叫张引生的疯子的视野,向读者真实地呈现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乡土中国何去何从,众声喧哗的复杂境遇。
《秦腔》的主题意蕴其实就体现在以上不同文化声音的对话之中,声音的碰撞、交汇、对抗,折射了我们这个“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文化冲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精神与欲望之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农业与市场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凡此种种文化冲突,无不在作者的心中交织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冲突,而它的艺术外化物就是这部众声喧哗的《秦腔》。这里我想起了!""写作《秦腔》的贾平凹,其痛苦更甚,因为《秦腔》中不止是乡村与城市两股风形成了龙卷,而是以上多组相互对立的声音(声浪)形成了龙卷,这股心理飓风的袭击或绞杀不能不让作者心力交瘁,心神苦累。
二、大型对话与文本结构
作为一部大型的复调小说,《秦腔》的文本具有鲜明的对话体结构特征。这首先表现为,《秦腔》的文本结构具有共时性。
贾平凹在《秦腔》中观察和表现中国乡村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共时性取向,也就是轻时间重空间。改革时代与“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区别,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勃兴和繁荣与“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凋敝与困窘,是历时地叙述一个线性的故事情节或多个故事情节交错并行,还是共时地呈现一个密密实实然而真实琐碎的乡村生活(精神)图景?作者在《秦腔》中对时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压缩,对空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秦腔》叙述的事件时间大约一年左右,而且作者没有明确交待事件时间,我们只能模糊地推算出来。这暗示了作者对时间的淡化和漠视。显然,作者有意地把中国乡村生活压缩并纳入到了一年左右的叙事时间之中,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叙事者疯子引生的特殊视野(心理空间),把中国乡村生活的新变共时地并置在一个叫做清风街的特定环境(空间)中。《秦腔》具有大型交响乐的织体结构。《秦腔》不仅拥有多旋律和多声部,而且还具有真正的多元性,《秦腔》中还有其他人物之间的对位关系,如夏家老一代人之间,及其各自媳妇妯娌之间,都在一定程度上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对话性,他们共同参与了《秦腔》共时性文本结构的建构。在人物关系上的“主体间性”是《秦腔》文本结构的又一重要特征。《秦腔》以对话开端,又以对话煞尾,从整体上体现了作者创作复调小说的艺术追求。
三、另一种乡土文学形态鲁迅是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也是最早界定乡土文学的中国作家。在鲁迅的眼中,乡土文学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作者是“侨寓”在现代城市的“乡下人”;其二,作品是“回忆故乡的”,因此“ 隐现着乡愁”。显然,贾平凹的《秦腔》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这不仅仅因为贾平凹素来以“农民”自居,他从未回避过自己“农裔城籍”的身份,更重要的在于,《秦腔》是贾平凹为自己真实确定的故乡“棣花街”———小说中叫“清风街”——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而以前为贾平凹赢得许多文名的“商州”系列小说,严格说来,其中的“商州”不过是贾平凹的“大故乡”(陕南商洛地区)而已,因此还比不上“小故乡”(棣花街)来得真切,更让作者乡愁百结。无怪乎贾平凹要在《后记》中忧伤地说:“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秦腔》对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形态的突破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作为一部复调形态的长篇乡土小说,《秦腔》中众声喧哗,充满了对话和潜对话,把世纪末的乡土中国叙述得淋漓尽致。《秦腔》不再用独白的方式展开乡土中国叙事,这既是作者的艺术选择,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后改革时代”的多元化特征使然,多元化的时代呼唤着多声部的小说,呼唤着真正的复调小说,而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贾平凹似乎总是能够敏锐地感应到时代的精神脉搏,并以创造性的形式(文体)把它传达出来。乡土的忧思
一、农村生活巨变的全景式展示
为巨变中的农村存照, 是贾平凹创作《秦腔》的初衷, 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创作理念。贾平凹申明尽管现在的写作观念多样新鲜, 他还是要强调一句老话, 即长篇小说要为历史负责, 成为一面镜子。时下中国的现实, 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尤其文化上的变化, 作家应该为此存照。以此为出发点, 他在两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是全景展示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状态;二是写出当代农村各方面的巨变。吴义勤将这种全景式展示称之为百科全书式日常乡土诗学, 认为贾平凹要建构的是一个-大而全. 的原生态的乡土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不仅三教九流悉数登场, 而且乡村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 比如-生老病离死, 吃喝拉撒睡. , 婚丧嫁娶, 风俗人情, 乃至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等, 也都得到了尽态极妍、淋漓尽致的表现。 因此, 小说叙述的虽只是清风街一年发生的事情, 但就是在清风街这个不大的舞台上, 所有村民及与之相关的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并表演出一幕幕悲喜剧, 令人喟叹, 引人深思。
二、对诸多农村问题的深邃忧思
贾平凹不仅为变化着的中国农村存照, 同时对给我们提供丰富细节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小说中把对乡村的困惑和忧思全写出来了, 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乡村变化与发展的诸多思考。这些困惑和忧思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 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它直指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 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 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贾平凹敏感地注意到了, 在清风街, 一方面是土地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 却是大量青壮年劳力流失造成的田地荒
芜, 还有退耕还林引发的各种冲突。贾平凹对农村和农民的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忧患, 守土者显然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作家也并没有把进城看成是拯救农民的良方。但如果说, 进城不是农民和农村真正的出路, 那么出路在哪里就成为了一个最现实也最难解答的问题。其二, 对于乡村文化, 作家不仅唱了一曲挽歌, 且对其衰败的原因也作了深入探询。他以主人翁的身份和责任, 观察农村的变迁, 思虑其前途命运, 描摹农村、农民在新时期转折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进而在一个更普遍、更高层面上, 表达出对乡村的关注和乡民苦难的悲悯, 揭示出乡村在新旧矛盾冲突中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内涵。他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态度介入当下、介入乡村, 在对乡村颓败命运的审视中, 他虽无法做出一种明晰的理性的价值判断, 不知道该歌赞现实还是诅咒现实, 但他直面现实、为巨变中的乡村存照、表达对乡土的困惑与忧思, 也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真实的乡村迷茫的情感
一、面对凋敝的乡村世界
贾平凹是一位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作家。使得他对乡村、对土地、对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如同飘进城里的风筝,线却系在乡村《秦腔》所写的是清风街一年左右琐碎泼烦的日子,这样的书写本身就抗拒着简单的情节抽绎与概括,但从整体气韵上,却分明能够感受
到这个乡村世界的凋敝。作品中的清风街,既无工业也无矿藏,村民世世代代在地里刨食。勤劳的本性适逢政策的开明也曾使人们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但随耕地的逐步减少,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却迅速上涨,人情世事的花销也在增大,村民的日子日渐窘迫起来,对于大多一般人家来说,情景就很是不同了。单凭地里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不少有劳力的人家便让青壮年进城打工,青壮年从村庄出走,也带走了村庄的活力,不
由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些许的萧索。村子里那些老弱病残人家的日子就更加令人揪心。
二、传统土地伦理的挽歌
土地和农民的本质关系,一直是困扰贾平凹的一个问题,《秦腔》则是乡土小说的言说模式,将知识分子的家园之思还原为农民自身的恋土、守土意识,并借助夏天义与夏君亭之间的矛盾冲突,真实反映了新旧两代农民在土地伦理上的嬗变。农民历来都是和土地系在一起的,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进程,养成了农民特有的勤劳、朴素和韧性等优良品质,作为老一代农民,夏天义身上同样体现了这些优良品质。他在清风街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带领全村兴修水利,整治农田,大搞农业建设。夏风在赵宏生卧屋里翻看的县志上,记录了他英武传奇的人生经历。在夏天义的思想观念中,农村就要以农业为主,发展农业就得保护耕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务农才是农民的正业。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新上任的夏君亭抛弃了以土地为本的传统观念,眼光放在了寻求各种致富门路上。然而,尽管君亭在作出某些决策时,有着拯救清风街衰败的考虑,但武断的决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他所难以料想的。对于这种好大喜功、为树个人政绩而妄下决断的领导形象,在商议建农贸市场的村两委会上,君 亭纸上谈兵般地展示了农贸市场的 未来蓝图,但当秦安有理有据地反驳了他那不切实际的构想时,君亭就忍不住说道:“……维持个摊子,那我夏君亭就不愿意到村部来的。” 农贸市场的建立给当地带来一定程度的效益,但预想不足的危机很快显现了出来,虽借夏中星之力缓解了销售的燃眉之急,但终不是长久之策。
三、没有秦腔的日子里
柏拉图曾经说过,音乐是人的心灵的原始反映。秦腔更是和八百里秦川上人们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早在1983 年,贾平凹就在一篇名为《秦腔》的散文中写到:“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坑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
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然而在这篇小说作品中,通过秦腔剧团被迫解散以及白雪等的悲剧命运的描述,如盐在水般融入秦人生活的秦腔,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再也无心守住收入微薄的土地,想方设法从土地上出走,加剧了农村劳力的流失和土地的大量荒芜。但正是夏君亭们的一系列单面向的现代化想象,在给乡村带来些微眼前实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当夏天智的葬礼难以凑齐抬棺之人时,君亭才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土地伦理关系的嬗变,贾平凹内心是充满忧虑的,他在后记中写道:“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难活。”《秦腔》即是为传统土地伦理唱出的一曲挽歌。最后,剧团无奈的接受了自行解散的命运,演员只能各自组成若干个乐班去走穴卖艺了。剧团的王老师唱了一辈子秦腔,不忍看到秦腔就此消亡,想出一盘带有纪念意义的唱腔盒带,以期秦腔艺术的留
存,但这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白雪热爱秦腔,为了心爱的秦腔事业,拒绝了随丈夫夏风进省城的建议,但也无法阻止秦腔的衰落,白雪与夏风的结合与分手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互不相容,白雪和秦腔在小说中是合二为一的,她唱秦腔,爱着秦腔,某种意义上她的命运就是秦腔的命运”。由此看来,秦腔真的要难逃衰微的历史命运了。其实,秦腔在乡村世界的衰微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秦腔的衰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与道德在乡村世界的衰落。在广大乡村,传统文化与道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维护日常生活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突如其来的衰落对他们来说,影响无疑是致命的。伴随传统文化与道德约束力的丧失,人们精神变得空虚,行动失去公共原则,面对万花筒一般的外部世界,内心变得无所适从。在小说中,夏天智无疑代表了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坚守者,在清风街的日常生活中,他的为人处事中总是恪守体现着扶危
济困的传统道德,洋溢闪烁着一种迷人的人性光辉。不管是他对秦安的关心匡扶,还是他对若干贫困孩子的资助,都一再强化着夏天智作为一种传统道德精神载体所独具的人格魅力,让人不由想起陈
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但在《秦腔》中,夏天智的威慑力却渐渐失去,眼瞅着清风街由于人心的混乱而变得越来越失序。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以“仁”为核心,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为仁要从最基本的孝道开始。但作品中夏天义五个儿子在对待老人问题上的表现,却处处与孝道背道而驰。乡村朴素情怀和伦理秩序的衰败,已跃然纸上;欲望挑动下人心的混乱和乡村现实的失序,已触目惊心。
四、迷茫的情感
这就是贾平凹在《秦腔》中所描绘的乡 村世界,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一曲为故乡、为土地、为传统文化与道德唱出的挽歌。“在从作品现 实到甚至有些自然主义的细致 描绘中,究竟弥漫着作者十分 浓重的主观情感。”作家想以《秦腔》 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作品中的清风街即是故乡棣花街的水中月镜中花。面对自己难以接受的现实故乡,贾平凹在写作时的情感是迷茫的,“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 由于情感的迷茫,作家面对现实故乡失去了评价能力,只能放任记忆中的人与事在作品中自由浮现。《秦腔》的叙事,从表面看来,
是喧嚣的,热闹的,但这种喧嚣和热闹
的背后,一直透着这股生命的凉气———这股凉气里,有心灵的寂寞,有生命的迷茫,有凭吊和悲伤,也有矛盾和痛苦。”《秦腔》过于贴近现实,其描述也几近还原现实,难免会被扣上种种不合时宜的政治帽子,对于这一点, 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已说得很明白:“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和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的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真实的乡村,迷茫的情感,《秦腔》以决绝的艺术勇气为当下中国乡村世界留下了一段真实记忆。
贾平凹《秦腔》的叙事节奏犹如交谊舞中的慢四步。理解《秦腔》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便在理解它的叙事本身。 《秦腔》的叙事速度很慢,它所写的不过是清风街一年多时间里的事情,但由于缓慢的叙事节奏和密实的细节,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感觉却像写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沧桑巨变,借用张爱玲的一个比喻,也许可以说,《秦腔》中的时间的移动,几乎像日光,简直让人感觉不到它的移动,然而却是倏忽的。这样的缓慢的叙事速度绝非无因。 叙事艺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叙事速度,本身便是对现实变化的感应。《秦腔》所写的是乡村社会的陈年流水账,一天一天琐碎泼烦的日子,每天的日子似乎都没怎么变或者说,其中小小的变化似乎不值得太过注意,然而一天天的变化一点一点积累着,一年多的时间积累下来,最后的结果却类乎天翻地覆。不知不觉中,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巨变而且是让人忧心的巨变:不想让它走的一点点走了,不想让它来的一点一点来了走了的还不仅仅是朴素的信义、道德、风俗、人情,更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精神;来了的也不仅仅是腐败、农贸市场、酒店、小姐、土地抛荒、农民闹事,来了的更是某种面目不清的未来和对未来把握不住的巨大惶恐。这样的变化,在小说中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情势已然形成。比如,小说中夏君亭建农贸市场的决定,一开始并不是非常强调地写出,一直到一连串的后果发生,某种似乎是偶然占上风的意见,结果却导致了清风街整个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夏君亭想建农贸市场,是出于拯救清风街的衰败。
他展示了蓝图,不看大家反应,拿了树棍在墙上划着算式给大家讲,说毕了,他坐回自己的位子,拿眼睛看大家。君亭本以为大家会鼓掌,会说:好! 至少,也是每个脸都在笑。但是,会议室里竟一时安安静静,安静得像是死了人。这段引文代表的细节,这样的多少有些无趣的“现代”想象和规划式的思维方式。农贸市场的建立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效益,有先见的人借着这个机会模仿城市建立了酒楼,酒楼招引来了大吃大喝,招引来了投机客商,招引来了舞女和妓女,招引来了当地人的家庭不睦———人心本已不宁。如此一来更是推波助澜:更多的人进城去追逐发财梦,有人见利忘义打劫杀人,有人四处飘荡卖笑卖淫,土地更加抛荒,原本在人们想象中宁静的乡村,跟在巨变中的城市一样,奇闻异事层出不穷,错乱悖德之事被视为寻常,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身处在这种变化中的人们,对之并非没有感觉,然而,似乎是现实中的某种因素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情势,某些敏感的个人,对这种变化即使有所觉察,却无力阻止情势本身的变化。
一切都在变,那种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和对土地的感情,似乎也面临崩溃,且将永远流失,一去不回。对于这种变化,贾平凹在《后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写《秦腔》时的思想感情: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 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站在街巷的石碾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快地要消失了吗? 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了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了吗? 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 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贾平凹就这样沉醉在中场过后的慢四步中,节 奏缓慢得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移动……
二、叙事技巧
《秦腔》用“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秦腔》也借用了《红楼梦》中人物姓名暗指叙事的技巧。《秦腔》中清风街近百号人物组成了一幅长卷浮世图,而其中许多人物姓名符号的指涉意义勾陈出了深层的文本叙事结构。夏天义老一辈名字按“五常”排行:仁、义、礼、智、信。偏偏老大夏天仁早死,老五夏天信胎死腹中。“掐头去尾”、“无头无尾”的是两个带“人”字旁的字,这寓示着礼崩乐摧之后,人成了空有人形而没人性的两足动物。把兄弟的“五常”之序拦腰斩断。夏天礼之死,即表示从此无神可祀,人于是彻底器化,异化为无宗教无信仰形而下的两脚兽了。在夏家的下一辈中,人丁较旺的夏天义有五个儿子,五个兄弟不仅猥琐龌龊,对父母也没多少孝敬,他生养的五个儿子与秦腔名句“窦燕山教五子,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形成强烈的反讽,正可谓:仁义礼智信,金玉满堂瞎。而在夏天义身上,天义何在呢?他的威力不过是指挥一个疯子,一个哑巴和一只狗;他的成功,不过是发现了一株怪麦穗,可惜这株麦穗王将为他带来拍照见报的荣耀时,他却因山洪滑坡撒手人寰。他是英雄末路,还是螳螂挡车?他的悲剧象征意义大于悲剧本身。夏天智的儿子夏风对父亲钟爱的秦腔事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冷漠。夏风是冲出了宗法礼制,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的根基被吹进都市化群体的风,他与父亲崇尚的传统农耕文化相背离,继而渐行渐远。夏天智与夏风的矛盾是“抱残守缺”之辈与“彼岸立身”之辈的矛盾,是异质文化的对弈交锋。而夏风与妻子白雪在价值观念上相左,最终分道扬镳。
三、叙事道具
在叙事中,贾平凹善用秦腔乐谱、对联和绘画,进行隔断转换、时空挪移构筑多维的艺术符号世界。一是秦腔乐谱的穿插。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曲谱对于不懂秦腔或不识简谱的读者,可谓专业性过强。实际上它们是作为文本的情感线索贯穿全文,完全成为一种视觉上的连接符号,作为整个文本叙述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它们的存在也主要出于叙事结构上的考虑。秦人离不开秦腔,一曲曲唱段、一个个曲牌抒发着秦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秦腔在这部作品里,结构上能起到隔断转换、时空挪移的作用,从欣赏心理上看也有变化和停歇。尤其能调动欣赏者在旋律和文字之间的同感,从一个新的渠道激发读者的艺术联想和欣赏再创造。音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情绪、环境氛围的表现中发挥作用,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这部小说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线性的文字叙述有时难于表达的团块状或云雾状的情绪、感受和意会。这种描写在当代小说中都很少见到。而小说描写的县剧团的炎凉和演员命运的起伏,也成为时代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种症候。在整部小说中,秦声弥散为一种气场,秦韵流贯为一股魂脉而无处不在。它构成小说、小说中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所共有的一种文化和精神质地。更重要的是,秦腔构成夏天智和白雪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命运、气质和精神寄托,构成他们生命
本体的一部分。秦腔人文使他们有了标志性的旋律和音乐形象。白雪因秦腔而美丽,用秦腔来表达爱,在秦腔音乐中结婚、孕育新的生命,因舍不得秦腔而留在县上,以致和省城的文人丈夫少了共同语言,直到在苦音慢板中倔强着黯然离异。夏天智在村里安装高音喇叭播放秦腔是他退休后自找的职业。他是性情中人,发乎情而止于礼,是生命的呐喊者却又对社会人生有较清醒的评断,能以如此乃是得益于秦腔。秦腔戏文和戏中人物的许多价值标准成为他人生的精神坐标。他视儿媳白雪如亲生女儿,是因亲情,更是因了秦腔和秦腔戏文的价值标准。白雪要生产了,他又以表达又一代新生命在心中引燃的激情,竟胡琴拉起激越恣肆的旋律迎接孙女的降生。得知儿子和白雪终于要离婚,痛惜至极的他当下收白雪为女儿,喊“喇叭打开,放《辕门斩子》,以示对儿子的愤恨。他自己也在催人心魂的秦腔中告别这个世界。二是对联的运用。对联是汉字独有的文学样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秦腔》中,十多副对联别开生面地构成一种点缀性叙事,其功能正如《红楼梦》中的曲赋或判词。赵宏声捧出的第一副对联是戏楼联: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这在《秦腔》整部叙事中是个提纲挈领的楔子,犹如《红楼梦》开篇中的“满纸荒唐言”或者如跛足道人吟唱的“好了歌”。赵宏声是《秦腔》中处处应景凑趣的人,他的每一副对联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叙事道具。与《秦腔》乡土叙事终结的寓意紧密呼应。三是绘画的补叙。在《秦腔》中,作者绘制的四幅插图也与文本构成了互文衬语叙事。
“一条线的故事”和“靠在树干上蹭痒痒”两幅插图生动展现了秦地的乡土文化风貌,而这正是夏天义、夏天智等人毕生赖以生存的根。《秦腔》文本中简而有意的墨写式插图更是承袭了“言、象、意”的中国传统绘画式叙事。《秦腔》创造了不同于作者以往的叙事方法,取得了特别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对这一叙事方法的陌生,人们在阅读时会有些不适应,难免会产生所谓的“难度”。然而,一个艺术家要超越自我,就必须不断地寻找创新之路。塞米利安曾说“赋予不具有形式的素材以形式,这是小说家的艰巨使命”,《秦腔》便完成了这样一次使命。正如作家所言,“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心酸。
《秦腔》的复调特征
如果借用俄国人巴赫金的术语,《秦腔》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复调小说”,万言的《秦腔》其实是一场充满了各种不同声音的大型对话,是一曲沉郁悲凉、浑然杂陈的民间交响乐。无论是小说的文体还是精神,《秦腔》都为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艺术探索。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从文体上揭示出《秦腔》的大型对话体结构,我们就无法真正全面地理解《秦腔》的内在精神旨趣,《秦腔》对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形态的突破意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一、众声喧哗与文化冲突
《秦腔》具备真正的多声部性和对话性,它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复调小说。众所周知,巴赫金是在借鉴复调音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复调小说的概念的,而《秦腔》这个题目本身就来源于中国西部一种历史久远的民间剧种(音乐)。这次用“秦腔”来做长篇小说的题目,却隐含着作者小说观念的某种新变,即小说的音乐化。读者不会没有注意到,《秦腔》中频繁地出现了一段又一段的秦腔曲谱,作者有意让音乐直接走进小说文本之中,而且这些秦腔曲谱变化多端,错落有致,既有慢板也有滚板,既有欢音也有苦音,形成了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音乐风景。当然,这不过是《秦腔》在表面上的、象征性的多声部特征。真正为这部长篇带来复调品格的是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其所开创的叙述话语空间。《秦腔》选择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小说通过一个名叫张引生的疯子的视野,向读者真实地呈现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乡土中国何去何从,众声喧哗的复杂境遇。
《秦腔》的主题意蕴其实就体现在以上不同文化声音的对话之中,声音的碰撞、交汇、对抗,折射了我们这个“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文化冲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精神与欲望之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农业与市场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凡此种种文化冲突,无不在作者的心中交织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冲突,而它的艺术外化物就是这部众声喧哗的《秦腔》。这里我想起了!""写作《秦腔》的贾平凹,其痛苦更甚,因为《秦腔》中不止是乡村与城市两股风形成了龙卷,而是以上多组相互对立的声音(声浪)形成了龙卷,这股心理飓风的袭击或绞杀不能不让作者心力交瘁,心神苦累。
二、大型对话与文本结构
作为一部大型的复调小说,《秦腔》的文本具有鲜明的对话体结构特征。这首先表现为,《秦腔》的文本结构具有共时性。
贾平凹在《秦腔》中观察和表现中国乡村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共时性取向,也就是轻时间重空间。改革时代与“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区别,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勃兴和繁荣与“后改革时代”中国乡村的凋敝与困窘,是历时地叙述一个线性的故事情节或多个故事情节交错并行,还是共时地呈现一个密密实实然而真实琐碎的乡村生活(精神)图景?作者在《秦腔》中对时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压缩,对空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秦腔》叙述的事件时间大约一年左右,而且作者没有明确交待事件时间,我们只能模糊地推算出来。这暗示了作者对时间的淡化和漠视。显然,作者有意地把中国乡村生活压缩并纳入到了一年左右的叙事时间之中,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叙事者疯子引生的特殊视野(心理空间),把中国乡村生活的新变共时地并置在一个叫做清风街的特定环境(空间)中。《秦腔》具有大型交响乐的织体结构。《秦腔》不仅拥有多旋律和多声部,而且还具有真正的多元性,《秦腔》中还有其他人物之间的对位关系,如夏家老一代人之间,及其各自媳妇妯娌之间,都在一定程度上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对话性,他们共同参与了《秦腔》共时性文本结构的建构。在人物关系上的“主体间性”是《秦腔》文本结构的又一重要特征。《秦腔》以对话开端,又以对话煞尾,从整体上体现了作者创作复调小说的艺术追求。
三、另一种乡土文学形态鲁迅是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也是最早界定乡土文学的中国作家。在鲁迅的眼中,乡土文学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作者是“侨寓”在现代城市的“乡下人”;其二,作品是“回忆故乡的”,因此“ 隐现着乡愁”。显然,贾平凹的《秦腔》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这不仅仅因为贾平凹素来以“农民”自居,他从未回避过自己“农裔城籍”的身份,更重要的在于,《秦腔》是贾平凹为自己真实确定的故乡“棣花街”———小说中叫“清风街”——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而以前为贾平凹赢得许多文名的“商州”系列小说,严格说来,其中的“商州”不过是贾平凹的“大故乡”(陕南商洛地区)而已,因此还比不上“小故乡”(棣花街)来得真切,更让作者乡愁百结。无怪乎贾平凹要在《后记》中忧伤地说:“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秦腔》对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形态的突破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作为一部复调形态的长篇乡土小说,《秦腔》中众声喧哗,充满了对话和潜对话,把世纪末的乡土中国叙述得淋漓尽致。《秦腔》不再用独白的方式展开乡土中国叙事,这既是作者的艺术选择,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后改革时代”的多元化特征使然,多元化的时代呼唤着多声部的小说,呼唤着真正的复调小说,而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贾平凹似乎总是能够敏锐地感应到时代的精神脉搏,并以创造性的形式(文体)把它传达出来。乡土的忧思
一、农村生活巨变的全景式展示
为巨变中的农村存照, 是贾平凹创作《秦腔》的初衷, 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创作理念。贾平凹申明尽管现在的写作观念多样新鲜, 他还是要强调一句老话, 即长篇小说要为历史负责, 成为一面镜子。时下中国的现实, 在政治上, 经济上, 文化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尤其文化上的变化, 作家应该为此存照。以此为出发点, 他在两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是全景展示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状态;二是写出当代农村各方面的巨变。吴义勤将这种全景式展示称之为百科全书式日常乡土诗学, 认为贾平凹要建构的是一个-大而全. 的原生态的乡土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不仅三教九流悉数登场, 而且乡村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 比如-生老病离死, 吃喝拉撒睡. , 婚丧嫁娶, 风俗人情, 乃至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等, 也都得到了尽态极妍、淋漓尽致的表现。 因此, 小说叙述的虽只是清风街一年发生的事情, 但就是在清风街这个不大的舞台上, 所有村民及与之相关的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并表演出一幕幕悲喜剧, 令人喟叹, 引人深思。
二、对诸多农村问题的深邃忧思
贾平凹不仅为变化着的中国农村存照, 同时对给我们提供丰富细节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小说中把对乡村的困惑和忧思全写出来了, 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乡村变化与发展的诸多思考。这些困惑和忧思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 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它直指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 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 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贾平凹敏感地注意到了, 在清风街, 一方面是土地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 却是大量青壮年劳力流失造成的田地荒
芜, 还有退耕还林引发的各种冲突。贾平凹对农村和农民的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忧患, 守土者显然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作家也并没有把进城看成是拯救农民的良方。但如果说, 进城不是农民和农村真正的出路, 那么出路在哪里就成为了一个最现实也最难解答的问题。其二, 对于乡村文化, 作家不仅唱了一曲挽歌, 且对其衰败的原因也作了深入探询。他以主人翁的身份和责任, 观察农村的变迁, 思虑其前途命运, 描摹农村、农民在新时期转折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进而在一个更普遍、更高层面上, 表达出对乡村的关注和乡民苦难的悲悯, 揭示出乡村在新旧矛盾冲突中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时代内涵。他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态度介入当下、介入乡村, 在对乡村颓败命运的审视中, 他虽无法做出一种明晰的理性的价值判断, 不知道该歌赞现实还是诅咒现实, 但他直面现实、为巨变中的乡村存照、表达对乡土的困惑与忧思, 也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真实的乡村迷茫的情感
一、面对凋敝的乡村世界
贾平凹是一位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作家。使得他对乡村、对土地、对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如同飘进城里的风筝,线却系在乡村《秦腔》所写的是清风街一年左右琐碎泼烦的日子,这样的书写本身就抗拒着简单的情节抽绎与概括,但从整体气韵上,却分明能够感受
到这个乡村世界的凋敝。作品中的清风街,既无工业也无矿藏,村民世世代代在地里刨食。勤劳的本性适逢政策的开明也曾使人们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但随耕地的逐步减少,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却迅速上涨,人情世事的花销也在增大,村民的日子日渐窘迫起来,对于大多一般人家来说,情景就很是不同了。单凭地里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不少有劳力的人家便让青壮年进城打工,青壮年从村庄出走,也带走了村庄的活力,不
由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些许的萧索。村子里那些老弱病残人家的日子就更加令人揪心。
二、传统土地伦理的挽歌
土地和农民的本质关系,一直是困扰贾平凹的一个问题,《秦腔》则是乡土小说的言说模式,将知识分子的家园之思还原为农民自身的恋土、守土意识,并借助夏天义与夏君亭之间的矛盾冲突,真实反映了新旧两代农民在土地伦理上的嬗变。农民历来都是和土地系在一起的,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进程,养成了农民特有的勤劳、朴素和韧性等优良品质,作为老一代农民,夏天义身上同样体现了这些优良品质。他在清风街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带领全村兴修水利,整治农田,大搞农业建设。夏风在赵宏生卧屋里翻看的县志上,记录了他英武传奇的人生经历。在夏天义的思想观念中,农村就要以农业为主,发展农业就得保护耕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务农才是农民的正业。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新上任的夏君亭抛弃了以土地为本的传统观念,眼光放在了寻求各种致富门路上。然而,尽管君亭在作出某些决策时,有着拯救清风街衰败的考虑,但武断的决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他所难以料想的。对于这种好大喜功、为树个人政绩而妄下决断的领导形象,在商议建农贸市场的村两委会上,君 亭纸上谈兵般地展示了农贸市场的 未来蓝图,但当秦安有理有据地反驳了他那不切实际的构想时,君亭就忍不住说道:“……维持个摊子,那我夏君亭就不愿意到村部来的。” 农贸市场的建立给当地带来一定程度的效益,但预想不足的危机很快显现了出来,虽借夏中星之力缓解了销售的燃眉之急,但终不是长久之策。
三、没有秦腔的日子里
柏拉图曾经说过,音乐是人的心灵的原始反映。秦腔更是和八百里秦川上人们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早在1983 年,贾平凹就在一篇名为《秦腔》的散文中写到:“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坑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
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然而在这篇小说作品中,通过秦腔剧团被迫解散以及白雪等的悲剧命运的描述,如盐在水般融入秦人生活的秦腔,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再也无心守住收入微薄的土地,想方设法从土地上出走,加剧了农村劳力的流失和土地的大量荒芜。但正是夏君亭们的一系列单面向的现代化想象,在给乡村带来些微眼前实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当夏天智的葬礼难以凑齐抬棺之人时,君亭才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土地伦理关系的嬗变,贾平凹内心是充满忧虑的,他在后记中写道:“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难活。”《秦腔》即是为传统土地伦理唱出的一曲挽歌。最后,剧团无奈的接受了自行解散的命运,演员只能各自组成若干个乐班去走穴卖艺了。剧团的王老师唱了一辈子秦腔,不忍看到秦腔就此消亡,想出一盘带有纪念意义的唱腔盒带,以期秦腔艺术的留
存,但这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白雪热爱秦腔,为了心爱的秦腔事业,拒绝了随丈夫夏风进省城的建议,但也无法阻止秦腔的衰落,白雪与夏风的结合与分手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互不相容,白雪和秦腔在小说中是合二为一的,她唱秦腔,爱着秦腔,某种意义上她的命运就是秦腔的命运”。由此看来,秦腔真的要难逃衰微的历史命运了。其实,秦腔在乡村世界的衰微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秦腔的衰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与道德在乡村世界的衰落。在广大乡村,传统文化与道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维护日常生活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突如其来的衰落对他们来说,影响无疑是致命的。伴随传统文化与道德约束力的丧失,人们精神变得空虚,行动失去公共原则,面对万花筒一般的外部世界,内心变得无所适从。在小说中,夏天智无疑代表了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坚守者,在清风街的日常生活中,他的为人处事中总是恪守体现着扶危
济困的传统道德,洋溢闪烁着一种迷人的人性光辉。不管是他对秦安的关心匡扶,还是他对若干贫困孩子的资助,都一再强化着夏天智作为一种传统道德精神载体所独具的人格魅力,让人不由想起陈
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但在《秦腔》中,夏天智的威慑力却渐渐失去,眼瞅着清风街由于人心的混乱而变得越来越失序。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以“仁”为核心,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为仁要从最基本的孝道开始。但作品中夏天义五个儿子在对待老人问题上的表现,却处处与孝道背道而驰。乡村朴素情怀和伦理秩序的衰败,已跃然纸上;欲望挑动下人心的混乱和乡村现实的失序,已触目惊心。
四、迷茫的情感
这就是贾平凹在《秦腔》中所描绘的乡 村世界,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一曲为故乡、为土地、为传统文化与道德唱出的挽歌。“在从作品现 实到甚至有些自然主义的细致 描绘中,究竟弥漫着作者十分 浓重的主观情感。”作家想以《秦腔》 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作品中的清风街即是故乡棣花街的水中月镜中花。面对自己难以接受的现实故乡,贾平凹在写作时的情感是迷茫的,“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 由于情感的迷茫,作家面对现实故乡失去了评价能力,只能放任记忆中的人与事在作品中自由浮现。《秦腔》的叙事,从表面看来,
是喧嚣的,热闹的,但这种喧嚣和热闹
的背后,一直透着这股生命的凉气———这股凉气里,有心灵的寂寞,有生命的迷茫,有凭吊和悲伤,也有矛盾和痛苦。”《秦腔》过于贴近现实,其描述也几近还原现实,难免会被扣上种种不合时宜的政治帽子,对于这一点, 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已说得很明白:“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和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的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真实的乡村,迷茫的情感,《秦腔》以决绝的艺术勇气为当下中国乡村世界留下了一段真实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