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促织》《变形记》群文联读教学设计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
文档属性
| 名称 | 14《促织》《变形记》群文联读教学设计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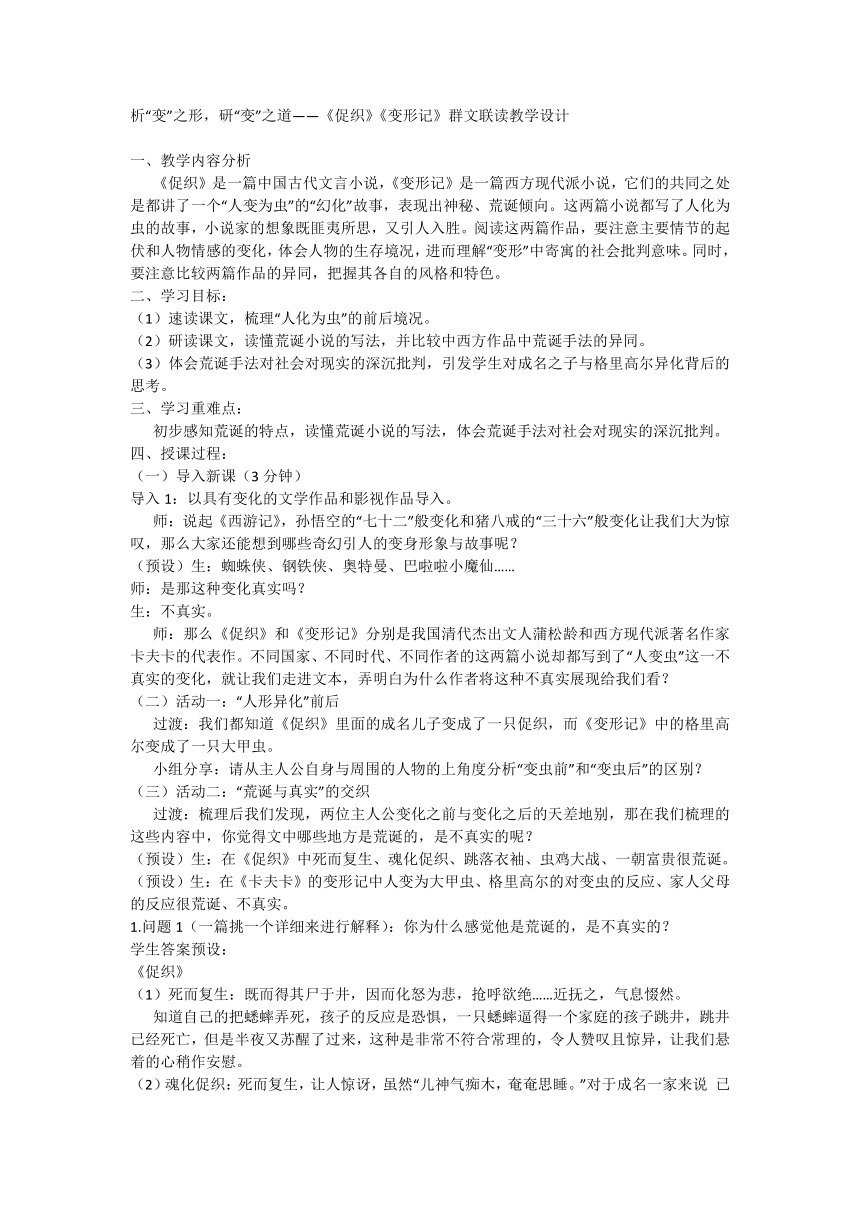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17.8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4-07-02 00:00:0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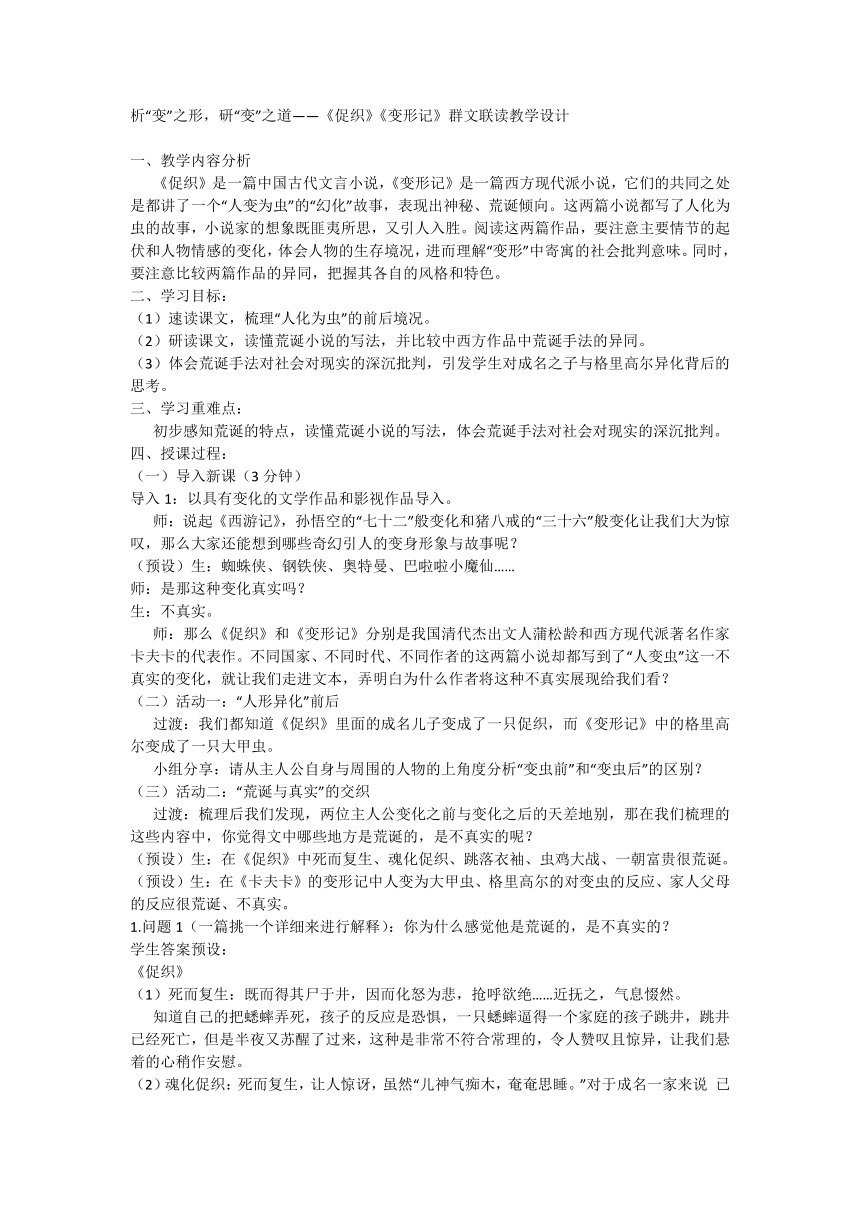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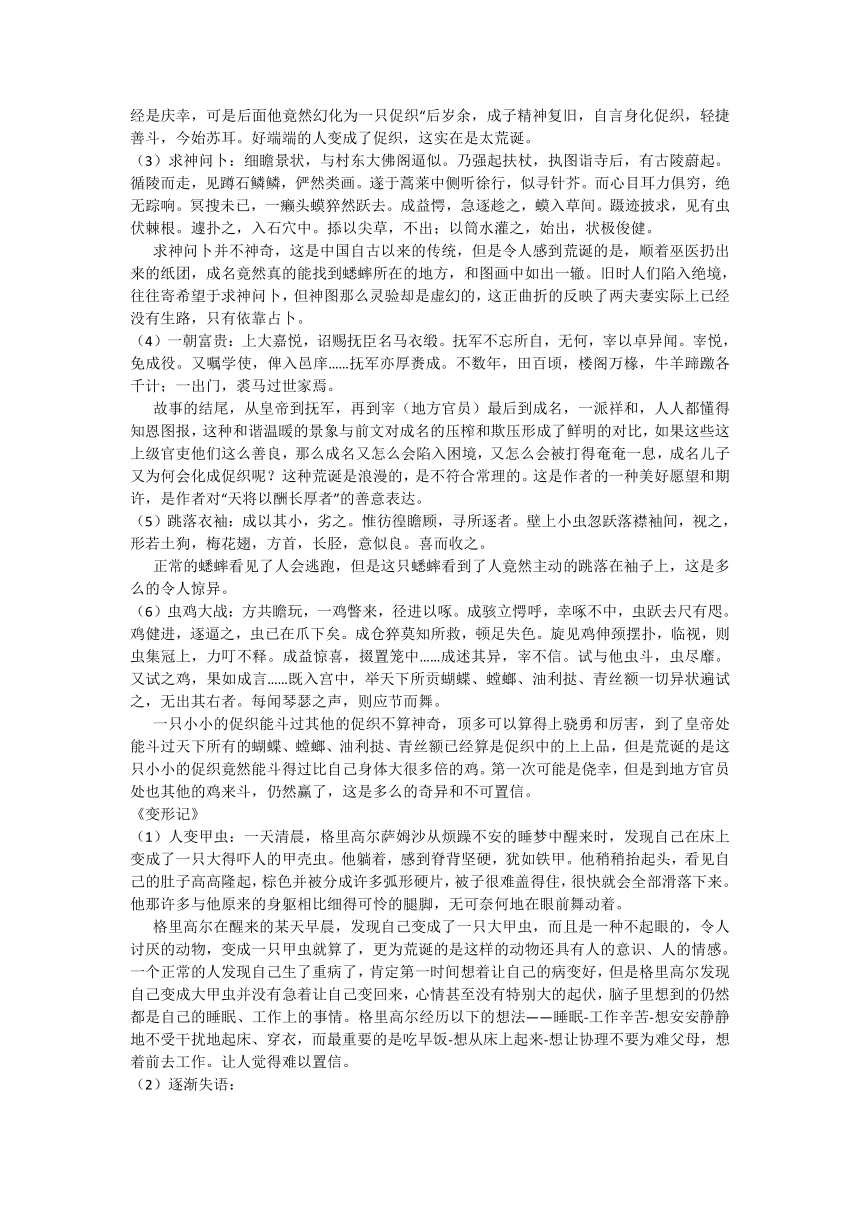
文档简介
析“变”之形,研“变”之道——《促织》《变形记》群文联读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分析
《促织》是一篇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变形记》是一篇西方现代派小说,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讲了一个“人变为虫”的“幻化”故事,表现出神秘、荒诞倾向。这两篇小说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小说家的想象既匪夷所思,又引人入胜。阅读这两篇作品,要注意主要情节的起伏和人物情感的变化,体会人物的生存境况,进而理解“变形”中寄寓的社会批判意味。同时,要注意比较两篇作品的异同,把握其各自的风格和特色。
二、学习目标:
(1)速读课文,梳理“人化为虫”的前后境况。
(2)研读课文,读懂荒诞小说的写法,并比较中西方作品中荒诞手法的异同。
(3)体会荒诞手法对社会对现实的深沉批判,引发学生对成名之子与格里高尔异化背后的思考。
三、学习重难点:
初步感知荒诞的特点,读懂荒诞小说的写法,体会荒诞手法对社会对现实的深沉批判。
四、授课过程:
(一)导入新课(3分钟)
导入1:以具有变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导入。
师:说起《西游记》,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和猪八戒的“三十六”般变化让我们大为惊叹,那么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奇幻引人的变身形象与故事呢?
(预设)生:蜘蛛侠、钢铁侠、奥特曼、巴啦啦小魔仙……
师:是那这种变化真实吗?
生:不真实。
师:那么《促织》和《变形记》分别是我国清代杰出文人蒲松龄和西方现代派著名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这两篇小说却都写到了“人变虫”这一不真实的变化,就让我们走进文本,弄明白为什么作者将这种不真实展现给我们看?
(二)活动一:“人形异化”前后
过渡:我们都知道《促织》里面的成名儿子变成了一只促织,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小组分享:请从主人公自身与周围的人物的上角度分析“变虫前”和“变虫后”的区别?
(三)活动二:“荒诞与真实”的交织
过渡:梳理后我们发现,两位主人公变化之前与变化之后的天差地别,那在我们梳理的这些内容中,你觉得文中哪些地方是荒诞的,是不真实的呢?
(预设)生:在《促织》中死而复生、魂化促织、跳落衣袖、虫鸡大战、一朝富贵很荒诞。
(预设)生: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为大甲虫、格里高尔的对变虫的反应、家人父母的反应很荒诞、不真实。
1.问题1(一篇挑一个详细来进行解释):你为什么感觉他是荒诞的,是不真实的?
学生答案预设:
《促织》
(1)死而复生: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近抚之,气息惙然。
知道自己的把蟋蟀弄死,孩子的反应是恐惧,一只蟋蟀逼得一个家庭的孩子跳井,跳井已经死亡,但是半夜又苏醒了过来,这种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令人赞叹且惊异,让我们悬着的心稍作安慰。
(2)魂化促织:死而复生,让人惊讶,虽然“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对于成名一家来说 已经是庆幸,可是后面他竟然幻化为一只促织“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好端端的人变成了促织,这实在是太荒诞。
(3)求神问卜: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
求神问卜并不神奇,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令人感到荒诞的是,顺着巫医扔出来的纸团,成名竟然真的能找到蟋蟀所在的地方,和图画中如出一辙。旧时人们陷入绝境,往往寄希望于求神问卜,但神图那么灵验却是虚幻的,这正曲折的反映了两夫妻实际上已经没有生路,只有依靠占卜。
(4)一朝富贵: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故事的结尾,从皇帝到抚军,再到宰(地方官员)最后到成名,一派祥和,人人都懂得知恩图报,这种和谐温暖的景象与前文对成名的压榨和欺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些这上级官吏他们这么善良,那么成名又怎么会陷入困境,又怎么会被打得奄奄一息,成名儿子又为何会化成促织呢?这种荒诞是浪漫的,是不符合常理的。这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许,是作者对“天将以酬长厚者”的善意表达。
(5)跳落衣袖: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
正常的蟋蟀看见了人会逃跑,但是这只蟋蟀看到了人竟然主动的跳落在袖子上,这是多么的令人惊异。
(6)虫鸡大战: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
一只小小的促织能斗过其他的促织不算神奇,顶多可以算得上骁勇和厉害,到了皇帝处能斗过天下所有的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已经算是促织中的上上品,但是荒诞的是这只小小的促织竟然能斗得过比自己身体大很多倍的鸡。第一次可能是侥幸,但是到地方官员处也其他的鸡来斗,仍然赢了,这是多么的奇异和不可置信。
《变形记》
(1)人变甲虫: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他躺着,感到脊背坚硬,犹如铁甲。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高高隆起,棕色并被分成许多弧形硬片,被子很难盖得住,很快就会全部滑落下来。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腿脚,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
格里高尔在醒来的某天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而且是一种不起眼的,令人讨厌的动物,变成一只甲虫就算了,更为荒诞的是这样的动物还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一个正常的人发现自己生了重病了,肯定第一时间想着让自己的病变好,但是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并没有急着让自己变回来,心情甚至没有特别大的起伏,脑子里想到的仍然都是自己的睡眠、工作上的事情。格里高尔经历以下的想法——睡眠-工作辛苦-想安安静静地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而最重要的是吃早饭-想从床上起来-想让协理不要为难父母,想着前去工作。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2)逐渐失语:
在小说125页,格里高尔的声音一开始还能让自己的父母听的清,虽然艰难但是还能做交流,后面则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如果真的变成了动物,那么一开始就应该听不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值得注意的是,能被听到的声音就是他说要起床或者他要前去工作时所说的话。而后面在解释自己不去上班的话,他们则是听不见的,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失聪,本质来源于他们对格里高尔的忽视以及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冷漠。这种声音的清晰与否是荒诞的。
(3)家人的反应
母亲的反应变化则是“关爱、担忧-关心、难过-害怕、-不知所措、恐惧”
父亲的反应变化则是“关心、不解-不耐烦-焦虑、急躁-露出敌意、慌乱不堪-嫌弃愤怒”。变形之前,格力高尔被视为支柱家庭的依靠;但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家人由开始的关心、担忧到后期的恐惧、嫌弃和厌恶。当一个人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异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将她变回正常的样子,可是他们没有去探求着变化背后的原因,而是顺理成章的接受了这种变形,这难道不觉得可怕和荒诞吗?
过渡:大家对小说中荒诞的部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那老师在这之中,有一个问题。
2.问题2:在《促织》中“虫鸡大战”这一环节,促织斗赢的动物为何是鸡而不是其他更凶猛的动物?
(预设)生:虫斗得过鸡是不符合现实的,是非常荒诞的,让故事充满荒诞色彩,体现了一位天才小说家的想象力。但是在现实中“鸡”是小昆虫的天敌,战胜“鸡”是有现实依据的,而如果写一只促织能够战胜老虎、狮子,就会显得很离谱,非常的离奇,反而失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点明:荒诞与真实相交织——荒诞是超乎常理,但是一定符合情理的。
师:回到《促织》与《变形记(节选)》原文,大家在这种荒诞中,还能找到哪些你感到真实的地方呢?
学生答案预设:
《促织》
(1)跳落衣袖
蟋蟀的外形、动作刻画非常真实。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写出了这只蟋蟀虽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孩童心气,好斗,骁勇善战,本领超凡,这种对蟋蟀的动作、外形的细节描写非常真实,符合一个小男孩的性格和行为,也能写出孩子对父亲的爱。
(2)人的情感展现很真实
A.成名和自己妻子的变化很真实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
孩子丢促织且自杀:妻子非常的恐惧,面如死灰;在知道促织跑了,成名非常愤怒,跑着去追究孩子的责任,在遇到孩子自杀的时候,悲痛欲绝,失去希望,尸体抱回家,之后有活过来,开心的放在床上,但依旧为失去了促织而难过,当看到空着的笼子,恐惧和忧闷又萦绕心头。在孩子发生如此大的时候的是,成名想着的是依然丢失的蟋蟀怎么办。
B.封建等级官吏的苛刻、狠毒非常真实
“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
他们因为成名“迂讷”,故意将他报充里正役,百般推脱不得,在成名不能给他们带来促织的时候,将成名打的身体残破,这种正好反应了在封建等级下的层层压迫,底层人民不能反抗的真实状况。
(3)魂化促织
一个九岁的孩子应该是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但是连一个年幼的孩子都明白促织的得与失决定的父母乃至家庭的兴衰与命运,可看当时封建社会自天子到官吏对底层百姓的层层盘剥,这种封建社会对百姓的极力压迫是很真实。
《变形记》
(1)格里高尔的工作状况很真实:工作很艰辛,四处奔波,低劣的饮食,被领导的压迫。
“天啊,”他想,“我选了一个多么艰辛的职业啊!成天都在奔波。在外面出差为业务操的心比坐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大多了。加上旅行的种种烦恼,为每次换车操心,饮食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不断变换,没有一个保持长久来往,从来建立不起真正的友情”
格里高尔旅行推销员的生存状态是非常艰难,家里的债务,家人的依靠让他不得不在这份艰辛的工作中不断的努力;推销员工作辛苦,每天都要赶着五点钟的火车出门,四处奔走;因为长期的旅行推销,自己养成旅居锁门的生活习惯;饮食低劣;缺乏真实的友情;背负家庭债务,心理压力巨大;老板苛刻冷酷,使格里高尔受尽了气,这符合一个在重压下的人的生存状态。
(2)变身甲虫之后,符合大甲虫的特点:形状很像甲虫,又大又丑陋,在转动钥匙的时候嘴角流出了棕色的液体,就像一只真的大虫子,而且他的动作:笨拙缓慢、艰难、无法自控,也正好符合一只大甲虫的生活习性,他不在具有人的行为能力,他不能很好的把门打开,从床上下来都需要费很大的劲,对虫的习性刻画得非常细节与真实,让人觉得恐惧甚至是恶心。
125第9段:“掀掉被子简单的很,只需将肚子稍稍一停被子便自行掉了下来但接下去困难就来了,尤其是他的身体宽得出奇,使得他行动十分艰难,他本来可以利用胳膊和手坐起来,但现在取代他们的是许多小细腿,他们不停的坐着动,许多动作控制不住,他若想收回一条腿,这条腿却向外伸的笔直,要是他成功的利用这条腿随心所欲的动作,其他腿就像被释放似的,极其痛苦的乱蹬起来。”
129页第20段:“头几次试站起来时,他都从光滑的柜子上滑落下来,最后他用力往上一停终于站起来了,尽管下半身痛得死去活来,他也根本顾不得了,他重重的靠到就近一张椅子的椅背上,用他的细腿紧紧抓住他的边缘,以此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于是他不说话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好好的听两位协理说话了。”
(3)父亲的啾啾声:啾啾声是人类经常去引诱动物的声音,驱赶动物的声音,他能被这种啾啾声弄晕,说明他已经具有了虫的特性,是符合情理与真实的。
133页第29段:“格里高尔怎么恳求都不管用,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的恳求,无论他多么低声下气的不停转动着脑袋……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毫不留情的逼着格里格尔回到房间里去……只要父亲不发出这种不可忍受的啾啾声就好了,这啾啾声可把格里高尔搞得晕头转向。”
(4)家人得知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反应:
在格里高尔的这个荒诞变形之下,格里高尔一直保持着虫形,母亲被格里高尔吓倒,直呼“救命”,而父亲则“恶狠狠地捏紧拳头,仿佛他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当发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这些细节将人对异变生物的恐惧的反应刻画得如此之真实,让人倍感气愤。格里高尔的父母荒诞至极,可是在小说中,他们的行为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对,因为他们身处那个荒诞的一切荒诞的行为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荒诞与真实的交织。从宏观上看,《变形记》的整个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从微观入手,围绕这个中心事件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卡夫卡的小说则是“整体荒诞、细节真实”他将荒诞与真实合二为一,在荒诞中显真实,于真实处见荒诞,将真实寓于荒诞之中,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艺术享受,如假包换,真假难辨。
启示:正如卢卡契评价说:在卡夫卡笔下,哪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最不真实的事情,犹豫细节所诱迫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荒诞”并非沉浸于非理性的虚构之中,任意天马行空,而是对生活的艺术提升,要遵循艺术的真实。小说追求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生活 的真实感,是生活提炼的艺术真实,是具有审美品质并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真实。
小结: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是运用了荒诞与真实相交织的手法,在荒诞的手法下,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虽然超乎常理,却符合情理。
(四)活动三:东西荒诞之异同
1.问题1:两篇小说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促织》中成名之子“化虫”之后能游刃有余,扭转乾坤,“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但是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在“化虫”之后在家人的厌弃中结束生命,两篇小说的结局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预设)生:我更喜欢《促织》的结局,这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写出中国人的那种对美好的追求。蒲松龄美好愿望的寄托:成名之子的“化虫”的圆满结局是表达“天将以酬长厚者”, 《促织)的变形是给长厚者安慰和奖励,这是蒲松龄在他那个时代的许诺和期待,因而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幻化出来的情节,更准确地说是表达了作者的愿望。
(预设)生:鲁迅说:“悲剧则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变形是一面镜子,目的是折射出人性中的阴暗面,折射出现代文明对人的摧残,卡夫卡的结局就是想证明在资本主义对金钱的极力追求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自我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异化,格里高尔与家人关系冷漠,工作生活对他的重压是不可解的是难以缓解的。《变形记》中的“化虫”是不可逆的,人变为虫,并且变不回来了,这是作者卡夫卡对人的“异化”的一次全方位的彻底的观察,“化虫”后外形改变,产生了虫的习性,但格里高尔依然保留了人的思维和情感,甚至从来没有放弃过人的这种“高贵性”。这也使得他本能地逃避,拒绝虫性的变化,导致他在异化之后无法自洽,更是和外界社会环境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展现卡夫卡对人性的执着、迷茫和绝望,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迷茫。
2.问题2:有人说这种大团圆结局真的是“喜剧”,你怎么看?
(预设)生:虚构的圆满结局,不仅使得成名一家翻身富贵,也使得曾经剥削压迫成名一家的官吏都获得了“恩荫”,“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这种结局,扩大了批判的范围,达到了刺贪刺虐的效果,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这种圆满的结局下,主旨更加深刻,批判性更为强烈,大团圆结局就像是一个肥皂泡一吹就破,而圆满结局的代价其实是失去人形中的人性、人类社会中的关系,喜中含悲。
(五)小结:
同:两篇小说在荒诞写法的侧重不同,《促织》有完整的情节和叙述套路,情节离奇多变,其荒诞多体现在情节上;《变形记》开篇即交代格里高尔的变形,叙述节奏慢,淡化情节动作,以人物的主观感受为主。
异:《促织》与《变形记》两篇小说在荒诞与真实交织背景下的结局看似截然不同,但其实都是为了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社会压迫对人的改变,促使人的“异化”,这种荒诞手法的运用,都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性和批判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不同的作家,通过荒诞与真实相交织的方式走向对社会最深处的批判。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一、教学内容分析
《促织》是一篇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变形记》是一篇西方现代派小说,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讲了一个“人变为虫”的“幻化”故事,表现出神秘、荒诞倾向。这两篇小说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小说家的想象既匪夷所思,又引人入胜。阅读这两篇作品,要注意主要情节的起伏和人物情感的变化,体会人物的生存境况,进而理解“变形”中寄寓的社会批判意味。同时,要注意比较两篇作品的异同,把握其各自的风格和特色。
二、学习目标:
(1)速读课文,梳理“人化为虫”的前后境况。
(2)研读课文,读懂荒诞小说的写法,并比较中西方作品中荒诞手法的异同。
(3)体会荒诞手法对社会对现实的深沉批判,引发学生对成名之子与格里高尔异化背后的思考。
三、学习重难点:
初步感知荒诞的特点,读懂荒诞小说的写法,体会荒诞手法对社会对现实的深沉批判。
四、授课过程:
(一)导入新课(3分钟)
导入1:以具有变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导入。
师:说起《西游记》,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和猪八戒的“三十六”般变化让我们大为惊叹,那么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奇幻引人的变身形象与故事呢?
(预设)生:蜘蛛侠、钢铁侠、奥特曼、巴啦啦小魔仙……
师:是那这种变化真实吗?
生:不真实。
师:那么《促织》和《变形记》分别是我国清代杰出文人蒲松龄和西方现代派著名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这两篇小说却都写到了“人变虫”这一不真实的变化,就让我们走进文本,弄明白为什么作者将这种不真实展现给我们看?
(二)活动一:“人形异化”前后
过渡:我们都知道《促织》里面的成名儿子变成了一只促织,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小组分享:请从主人公自身与周围的人物的上角度分析“变虫前”和“变虫后”的区别?
(三)活动二:“荒诞与真实”的交织
过渡:梳理后我们发现,两位主人公变化之前与变化之后的天差地别,那在我们梳理的这些内容中,你觉得文中哪些地方是荒诞的,是不真实的呢?
(预设)生:在《促织》中死而复生、魂化促织、跳落衣袖、虫鸡大战、一朝富贵很荒诞。
(预设)生: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为大甲虫、格里高尔的对变虫的反应、家人父母的反应很荒诞、不真实。
1.问题1(一篇挑一个详细来进行解释):你为什么感觉他是荒诞的,是不真实的?
学生答案预设:
《促织》
(1)死而复生: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近抚之,气息惙然。
知道自己的把蟋蟀弄死,孩子的反应是恐惧,一只蟋蟀逼得一个家庭的孩子跳井,跳井已经死亡,但是半夜又苏醒了过来,这种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令人赞叹且惊异,让我们悬着的心稍作安慰。
(2)魂化促织:死而复生,让人惊讶,虽然“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对于成名一家来说 已经是庆幸,可是后面他竟然幻化为一只促织“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好端端的人变成了促织,这实在是太荒诞。
(3)求神问卜: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
求神问卜并不神奇,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令人感到荒诞的是,顺着巫医扔出来的纸团,成名竟然真的能找到蟋蟀所在的地方,和图画中如出一辙。旧时人们陷入绝境,往往寄希望于求神问卜,但神图那么灵验却是虚幻的,这正曲折的反映了两夫妻实际上已经没有生路,只有依靠占卜。
(4)一朝富贵: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故事的结尾,从皇帝到抚军,再到宰(地方官员)最后到成名,一派祥和,人人都懂得知恩图报,这种和谐温暖的景象与前文对成名的压榨和欺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些这上级官吏他们这么善良,那么成名又怎么会陷入困境,又怎么会被打得奄奄一息,成名儿子又为何会化成促织呢?这种荒诞是浪漫的,是不符合常理的。这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许,是作者对“天将以酬长厚者”的善意表达。
(5)跳落衣袖: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
正常的蟋蟀看见了人会逃跑,但是这只蟋蟀看到了人竟然主动的跳落在袖子上,这是多么的令人惊异。
(6)虫鸡大战: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
一只小小的促织能斗过其他的促织不算神奇,顶多可以算得上骁勇和厉害,到了皇帝处能斗过天下所有的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已经算是促织中的上上品,但是荒诞的是这只小小的促织竟然能斗得过比自己身体大很多倍的鸡。第一次可能是侥幸,但是到地方官员处也其他的鸡来斗,仍然赢了,这是多么的奇异和不可置信。
《变形记》
(1)人变甲虫: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他躺着,感到脊背坚硬,犹如铁甲。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高高隆起,棕色并被分成许多弧形硬片,被子很难盖得住,很快就会全部滑落下来。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腿脚,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
格里高尔在醒来的某天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而且是一种不起眼的,令人讨厌的动物,变成一只甲虫就算了,更为荒诞的是这样的动物还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一个正常的人发现自己生了重病了,肯定第一时间想着让自己的病变好,但是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并没有急着让自己变回来,心情甚至没有特别大的起伏,脑子里想到的仍然都是自己的睡眠、工作上的事情。格里高尔经历以下的想法——睡眠-工作辛苦-想安安静静地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而最重要的是吃早饭-想从床上起来-想让协理不要为难父母,想着前去工作。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2)逐渐失语:
在小说125页,格里高尔的声音一开始还能让自己的父母听的清,虽然艰难但是还能做交流,后面则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如果真的变成了动物,那么一开始就应该听不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值得注意的是,能被听到的声音就是他说要起床或者他要前去工作时所说的话。而后面在解释自己不去上班的话,他们则是听不见的,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失聪,本质来源于他们对格里高尔的忽视以及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冷漠。这种声音的清晰与否是荒诞的。
(3)家人的反应
母亲的反应变化则是“关爱、担忧-关心、难过-害怕、-不知所措、恐惧”
父亲的反应变化则是“关心、不解-不耐烦-焦虑、急躁-露出敌意、慌乱不堪-嫌弃愤怒”。变形之前,格力高尔被视为支柱家庭的依靠;但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家人由开始的关心、担忧到后期的恐惧、嫌弃和厌恶。当一个人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异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将她变回正常的样子,可是他们没有去探求着变化背后的原因,而是顺理成章的接受了这种变形,这难道不觉得可怕和荒诞吗?
过渡:大家对小说中荒诞的部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那老师在这之中,有一个问题。
2.问题2:在《促织》中“虫鸡大战”这一环节,促织斗赢的动物为何是鸡而不是其他更凶猛的动物?
(预设)生:虫斗得过鸡是不符合现实的,是非常荒诞的,让故事充满荒诞色彩,体现了一位天才小说家的想象力。但是在现实中“鸡”是小昆虫的天敌,战胜“鸡”是有现实依据的,而如果写一只促织能够战胜老虎、狮子,就会显得很离谱,非常的离奇,反而失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点明:荒诞与真实相交织——荒诞是超乎常理,但是一定符合情理的。
师:回到《促织》与《变形记(节选)》原文,大家在这种荒诞中,还能找到哪些你感到真实的地方呢?
学生答案预设:
《促织》
(1)跳落衣袖
蟋蟀的外形、动作刻画非常真实。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写出了这只蟋蟀虽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孩童心气,好斗,骁勇善战,本领超凡,这种对蟋蟀的动作、外形的细节描写非常真实,符合一个小男孩的性格和行为,也能写出孩子对父亲的爱。
(2)人的情感展现很真实
A.成名和自己妻子的变化很真实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
孩子丢促织且自杀:妻子非常的恐惧,面如死灰;在知道促织跑了,成名非常愤怒,跑着去追究孩子的责任,在遇到孩子自杀的时候,悲痛欲绝,失去希望,尸体抱回家,之后有活过来,开心的放在床上,但依旧为失去了促织而难过,当看到空着的笼子,恐惧和忧闷又萦绕心头。在孩子发生如此大的时候的是,成名想着的是依然丢失的蟋蟀怎么办。
B.封建等级官吏的苛刻、狠毒非常真实
“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
他们因为成名“迂讷”,故意将他报充里正役,百般推脱不得,在成名不能给他们带来促织的时候,将成名打的身体残破,这种正好反应了在封建等级下的层层压迫,底层人民不能反抗的真实状况。
(3)魂化促织
一个九岁的孩子应该是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但是连一个年幼的孩子都明白促织的得与失决定的父母乃至家庭的兴衰与命运,可看当时封建社会自天子到官吏对底层百姓的层层盘剥,这种封建社会对百姓的极力压迫是很真实。
《变形记》
(1)格里高尔的工作状况很真实:工作很艰辛,四处奔波,低劣的饮食,被领导的压迫。
“天啊,”他想,“我选了一个多么艰辛的职业啊!成天都在奔波。在外面出差为业务操的心比坐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大多了。加上旅行的种种烦恼,为每次换车操心,饮食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不断变换,没有一个保持长久来往,从来建立不起真正的友情”
格里高尔旅行推销员的生存状态是非常艰难,家里的债务,家人的依靠让他不得不在这份艰辛的工作中不断的努力;推销员工作辛苦,每天都要赶着五点钟的火车出门,四处奔走;因为长期的旅行推销,自己养成旅居锁门的生活习惯;饮食低劣;缺乏真实的友情;背负家庭债务,心理压力巨大;老板苛刻冷酷,使格里高尔受尽了气,这符合一个在重压下的人的生存状态。
(2)变身甲虫之后,符合大甲虫的特点:形状很像甲虫,又大又丑陋,在转动钥匙的时候嘴角流出了棕色的液体,就像一只真的大虫子,而且他的动作:笨拙缓慢、艰难、无法自控,也正好符合一只大甲虫的生活习性,他不在具有人的行为能力,他不能很好的把门打开,从床上下来都需要费很大的劲,对虫的习性刻画得非常细节与真实,让人觉得恐惧甚至是恶心。
125第9段:“掀掉被子简单的很,只需将肚子稍稍一停被子便自行掉了下来但接下去困难就来了,尤其是他的身体宽得出奇,使得他行动十分艰难,他本来可以利用胳膊和手坐起来,但现在取代他们的是许多小细腿,他们不停的坐着动,许多动作控制不住,他若想收回一条腿,这条腿却向外伸的笔直,要是他成功的利用这条腿随心所欲的动作,其他腿就像被释放似的,极其痛苦的乱蹬起来。”
129页第20段:“头几次试站起来时,他都从光滑的柜子上滑落下来,最后他用力往上一停终于站起来了,尽管下半身痛得死去活来,他也根本顾不得了,他重重的靠到就近一张椅子的椅背上,用他的细腿紧紧抓住他的边缘,以此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于是他不说话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好好的听两位协理说话了。”
(3)父亲的啾啾声:啾啾声是人类经常去引诱动物的声音,驱赶动物的声音,他能被这种啾啾声弄晕,说明他已经具有了虫的特性,是符合情理与真实的。
133页第29段:“格里高尔怎么恳求都不管用,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的恳求,无论他多么低声下气的不停转动着脑袋……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毫不留情的逼着格里格尔回到房间里去……只要父亲不发出这种不可忍受的啾啾声就好了,这啾啾声可把格里高尔搞得晕头转向。”
(4)家人得知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反应:
在格里高尔的这个荒诞变形之下,格里高尔一直保持着虫形,母亲被格里高尔吓倒,直呼“救命”,而父亲则“恶狠狠地捏紧拳头,仿佛他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当发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这些细节将人对异变生物的恐惧的反应刻画得如此之真实,让人倍感气愤。格里高尔的父母荒诞至极,可是在小说中,他们的行为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对,因为他们身处那个荒诞的一切荒诞的行为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荒诞与真实的交织。从宏观上看,《变形记》的整个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从微观入手,围绕这个中心事件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卡夫卡的小说则是“整体荒诞、细节真实”他将荒诞与真实合二为一,在荒诞中显真实,于真实处见荒诞,将真实寓于荒诞之中,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艺术享受,如假包换,真假难辨。
启示:正如卢卡契评价说:在卡夫卡笔下,哪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最不真实的事情,犹豫细节所诱迫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荒诞”并非沉浸于非理性的虚构之中,任意天马行空,而是对生活的艺术提升,要遵循艺术的真实。小说追求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生活 的真实感,是生活提炼的艺术真实,是具有审美品质并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真实。
小结: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是运用了荒诞与真实相交织的手法,在荒诞的手法下,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虽然超乎常理,却符合情理。
(四)活动三:东西荒诞之异同
1.问题1:两篇小说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促织》中成名之子“化虫”之后能游刃有余,扭转乾坤,“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但是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在“化虫”之后在家人的厌弃中结束生命,两篇小说的结局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预设)生:我更喜欢《促织》的结局,这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写出中国人的那种对美好的追求。蒲松龄美好愿望的寄托:成名之子的“化虫”的圆满结局是表达“天将以酬长厚者”, 《促织)的变形是给长厚者安慰和奖励,这是蒲松龄在他那个时代的许诺和期待,因而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幻化出来的情节,更准确地说是表达了作者的愿望。
(预设)生:鲁迅说:“悲剧则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变形是一面镜子,目的是折射出人性中的阴暗面,折射出现代文明对人的摧残,卡夫卡的结局就是想证明在资本主义对金钱的极力追求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自我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异化,格里高尔与家人关系冷漠,工作生活对他的重压是不可解的是难以缓解的。《变形记》中的“化虫”是不可逆的,人变为虫,并且变不回来了,这是作者卡夫卡对人的“异化”的一次全方位的彻底的观察,“化虫”后外形改变,产生了虫的习性,但格里高尔依然保留了人的思维和情感,甚至从来没有放弃过人的这种“高贵性”。这也使得他本能地逃避,拒绝虫性的变化,导致他在异化之后无法自洽,更是和外界社会环境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展现卡夫卡对人性的执着、迷茫和绝望,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迷茫。
2.问题2:有人说这种大团圆结局真的是“喜剧”,你怎么看?
(预设)生:虚构的圆满结局,不仅使得成名一家翻身富贵,也使得曾经剥削压迫成名一家的官吏都获得了“恩荫”,“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这种结局,扩大了批判的范围,达到了刺贪刺虐的效果,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这种圆满的结局下,主旨更加深刻,批判性更为强烈,大团圆结局就像是一个肥皂泡一吹就破,而圆满结局的代价其实是失去人形中的人性、人类社会中的关系,喜中含悲。
(五)小结:
同:两篇小说在荒诞写法的侧重不同,《促织》有完整的情节和叙述套路,情节离奇多变,其荒诞多体现在情节上;《变形记》开篇即交代格里高尔的变形,叙述节奏慢,淡化情节动作,以人物的主观感受为主。
异:《促织》与《变形记》两篇小说在荒诞与真实交织背景下的结局看似截然不同,但其实都是为了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社会压迫对人的改变,促使人的“异化”,这种荒诞手法的运用,都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性和批判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不同的作家,通过荒诞与真实相交织的方式走向对社会最深处的批判。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 齐桓晋文之事 庖丁解牛)
- 2 烛之武退秦师
- 3 *鸿门宴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二单元
- 4 窦娥冤(节选)
- 5 雷雨(节选)
- 6 *哈姆莱特(节选)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三单元
- 7(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 8 *中国建筑的特征
- 9 说“木叶”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四单元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
- 学习活动
- 第五单元
- 10(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 11(谏逐客书 *与妻书)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六单元
- 12 祝福
- 13(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 装在套子里的人)
- 14(促织 * 变形记(节选))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七单元 整本书阅读
- 《红楼梦》
- 第八单元
- 15(谏太宗十思疏 * 答司马谏议书)
- 16(阿房宫赋 * 六国论)
- 单元学习任务
- 古诗词诵读
- 登岳阳楼
- 桂枝香·金陵怀古
- 念奴娇·过洞庭
- 游园([皂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