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高二年级下华东师大版2.5《关汉卿》课件(19张)
文档属性
| 名称 | 高中语文高二年级下华东师大版2.5《关汉卿》课件(19张) |  | |
| 格式 | zip | ||
| 文件大小 | 16.4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华东师大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16-09-23 16:42:56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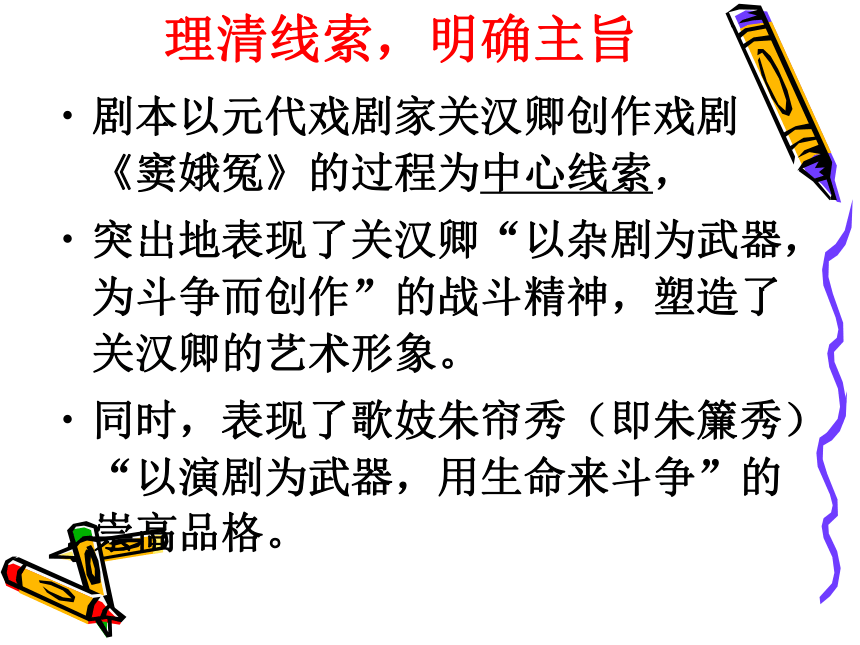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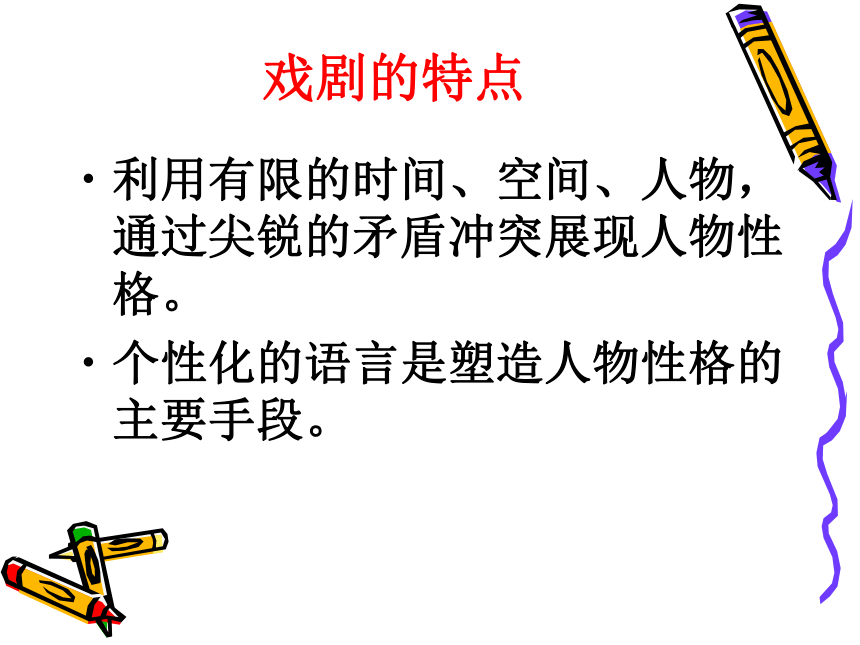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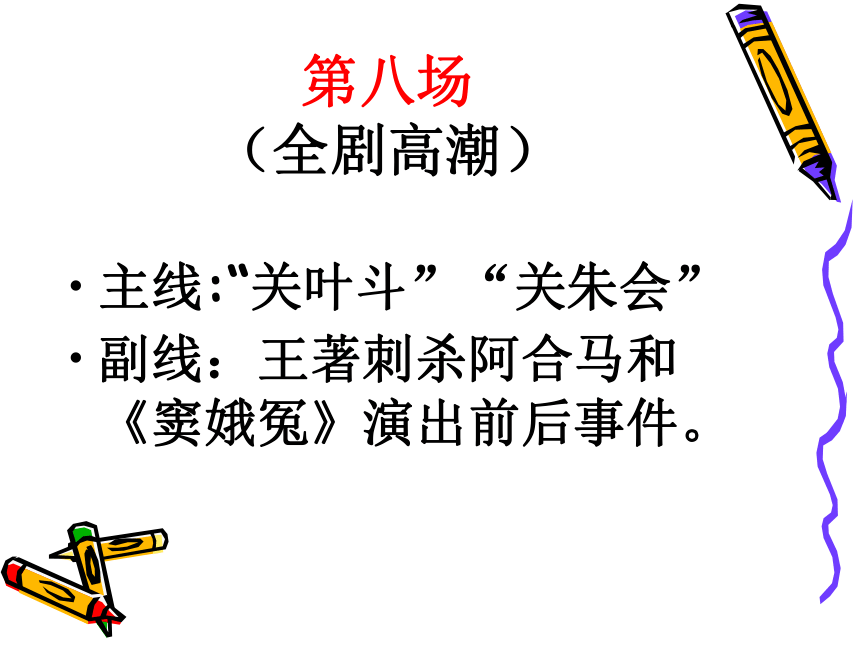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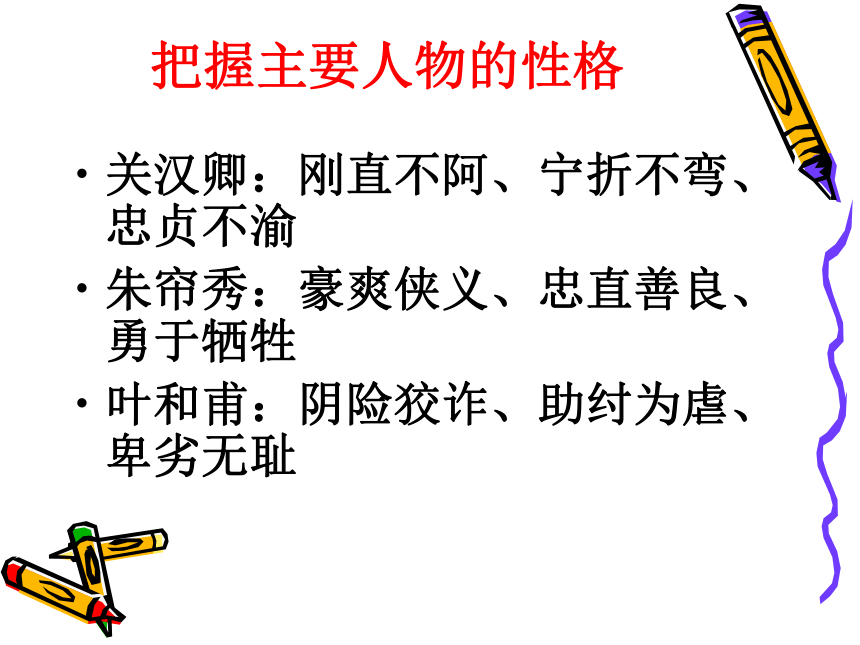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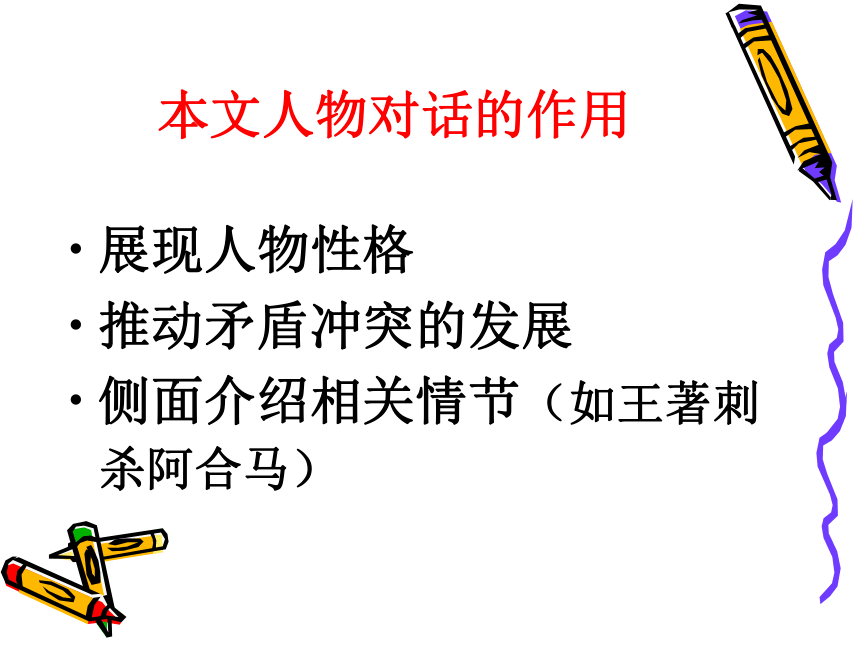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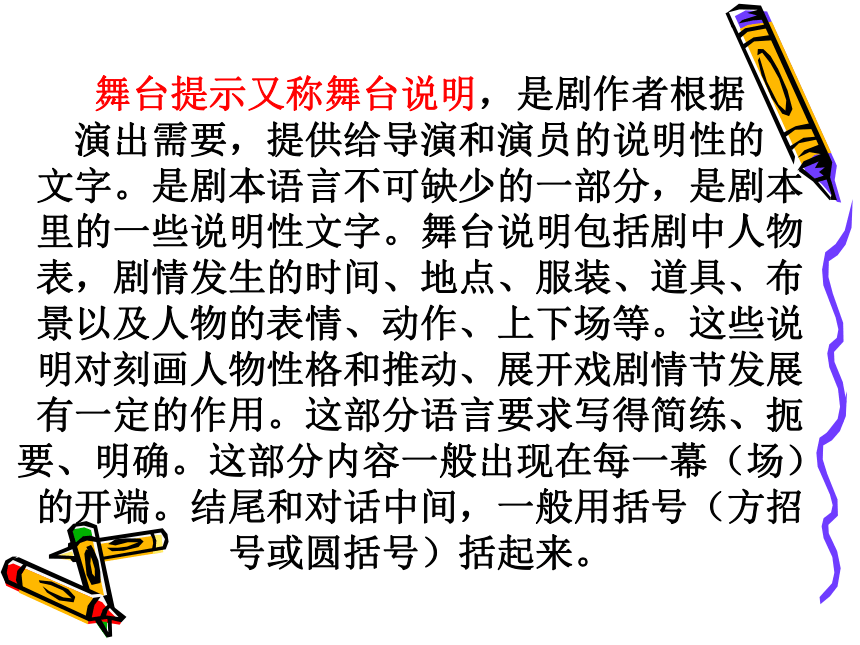
文档简介
课件19张PPT。关汉卿(节选)田汉理清线索,明确主旨
剧本以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戏剧《窦娥冤》的过程为中心线索,
突出地表现了关汉卿“以杂剧为武器,为斗争而创作”的战斗精神,塑造了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同时,表现了歌妓朱帘秀(即朱簾秀)“以演剧为武器,用生命来斗争”的崇高品格。 戏剧的特点利用有限的时间、空间、人物,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
个性化的语言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 第八场 (全剧高潮)主线:“关叶斗”“关朱会”
副线:王著刺杀阿合马和《窦娥冤》演出前后事件。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 关汉卿: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忠贞不渝
朱帘秀:豪爽侠义、忠直善良、勇于牺牲
叶和甫:阴险狡诈、助纣为虐、卑劣无耻本文人物对话的作用展现人物性格
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
侧面介绍相关情节(如王著刺杀阿合马) 舞台提示又称舞台说明,是剧作者根据 演出需要,提供给导演和演员的说明性的 文字。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剧本里的一些说明性文字。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展开戏剧情节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部分语言要求写得简练、扼要、明确。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每一幕(场)的开端。结尾和对话中间,一般用括号(方招号或圆括号)括起来。本课塑造的关汉卿的个性前后落差较大,是否矛盾?
明确:不矛盾。面对阴险狡诈、助纣为虐的叶和甫,关汉卿刚直不阿、宁折不弯,
而面对忠直善良、忠贞不渝的朱帘秀,他又深情款款、儿女情长。
这两者是统一的,能爱才能恨,反抗恶势力是他们的爱情基础,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文化英雄。鉴赏“双飞蝶”体会人物的英雄气概和纯洁而真挚的情感。关于散曲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经过长期酝酿,到宋金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流行的曲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乐曲的侵入并与中原正乐融合,导致传统的词和词曲不能在适应新的音乐形式,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可以说散曲的兴起和词的衰退几乎是同时的。称为"清曲"、"今乐府"
金元时在北方起源,故散曲又称北曲。它它有三种基本类型:包括小令、套数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主要形式。散曲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如果作家纯以曲体抒情,与科白情节无关的话,就是“散”。他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其特性有三点:
一是在语言方面,即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
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他比近体诗和词更多的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压,句中还可以衬字。小令和套数是散曲的两种主要形式,一为短小精悍,一为富丽雍容
前期散曲创作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如关汉卿及其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及小令【双调·沉醉东风】。这类作家无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自我价值的认定,或是道德修养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士大相径庭,并大多具有放荡不羁的精神风貌,而在表象之后蕴含的确实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 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这类作家不像上类一样比较彻底的抛弃了名教礼法和传统士流风尚,而是不敢信失落,力图重现传统文人价值。白朴,马致远是代表作家。之中马致远的散曲最为鲜明突出,被誉为“曲状元”。
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主要有北京人卢挚,洛阳人姚燧等。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年—1241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叟(一作一斋)。
关于关汉卿的籍贯,元大都(今北京市)(《录鬼簿》)、解州(在今山西运城)(《元史类编》卷三十六)、祁州(在今河北)(《祁州志》卷八)等不同说法。
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
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不伏老》是一首带有自述心志性质的著名套曲,气韵深沉,语势狂放,在清澈见底的情感波流中极能见出诗人独特的个性,因而历来为人传颂,被视为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之作。 在〔尾〕曲中,诗人那种桀骜不驯的情绪、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
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就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他却昂首怒吼:“我宁肯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他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甘愿以生命相交换!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的也是同样的一种精神,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
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踢球)、会打围(打也)、会插科(戏曲动作)、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一种棋艺)”。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剧本以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戏剧《窦娥冤》的过程为中心线索,
突出地表现了关汉卿“以杂剧为武器,为斗争而创作”的战斗精神,塑造了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同时,表现了歌妓朱帘秀(即朱簾秀)“以演剧为武器,用生命来斗争”的崇高品格。 戏剧的特点利用有限的时间、空间、人物,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
个性化的语言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 第八场 (全剧高潮)主线:“关叶斗”“关朱会”
副线:王著刺杀阿合马和《窦娥冤》演出前后事件。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 关汉卿: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忠贞不渝
朱帘秀:豪爽侠义、忠直善良、勇于牺牲
叶和甫:阴险狡诈、助纣为虐、卑劣无耻本文人物对话的作用展现人物性格
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
侧面介绍相关情节(如王著刺杀阿合马) 舞台提示又称舞台说明,是剧作者根据 演出需要,提供给导演和演员的说明性的 文字。是剧本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剧本里的一些说明性文字。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展开戏剧情节发展有一定的作用。这部分语言要求写得简练、扼要、明确。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每一幕(场)的开端。结尾和对话中间,一般用括号(方招号或圆括号)括起来。本课塑造的关汉卿的个性前后落差较大,是否矛盾?
明确:不矛盾。面对阴险狡诈、助纣为虐的叶和甫,关汉卿刚直不阿、宁折不弯,
而面对忠直善良、忠贞不渝的朱帘秀,他又深情款款、儿女情长。
这两者是统一的,能爱才能恨,反抗恶势力是他们的爱情基础,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文化英雄。鉴赏“双飞蝶”体会人物的英雄气概和纯洁而真挚的情感。关于散曲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经过长期酝酿,到宋金时期又吸收了一些民间流行的曲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乐曲的侵入并与中原正乐融合,导致传统的词和词曲不能在适应新的音乐形式,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可以说散曲的兴起和词的衰退几乎是同时的。称为"清曲"、"今乐府"
金元时在北方起源,故散曲又称北曲。它它有三种基本类型:包括小令、套数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主要形式。散曲之所以称为“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如果作家纯以曲体抒情,与科白情节无关的话,就是“散”。他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其特性有三点:
一是在语言方面,即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会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音节散漫化的状态。
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他比近体诗和词更多的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三是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压,句中还可以衬字。小令和套数是散曲的两种主要形式,一为短小精悍,一为富丽雍容
前期散曲创作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如关汉卿及其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以及小令【双调·沉醉东风】。这类作家无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自我价值的认定,或是道德修养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士大相径庭,并大多具有放荡不羁的精神风貌,而在表象之后蕴含的确实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 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这类作家不像上类一样比较彻底的抛弃了名教礼法和传统士流风尚,而是不敢信失落,力图重现传统文人价值。白朴,马致远是代表作家。之中马致远的散曲最为鲜明突出,被誉为“曲状元”。
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主要有北京人卢挚,洛阳人姚燧等。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年—1241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叟(一作一斋)。
关于关汉卿的籍贯,元大都(今北京市)(《录鬼簿》)、解州(在今山西运城)(《元史类编》卷三十六)、祁州(在今河北)(《祁州志》卷八)等不同说法。
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
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
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不伏老》是一首带有自述心志性质的著名套曲,气韵深沉,语势狂放,在清澈见底的情感波流中极能见出诗人独特的个性,因而历来为人传颂,被视为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之作。 在〔尾〕曲中,诗人那种桀骜不驯的情绪、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
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就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他却昂首怒吼:“我宁肯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他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甘愿以生命相交换!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的也是同样的一种精神,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
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踢球)、会打围(打也)、会插科(戏曲动作)、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一种棋艺)”。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