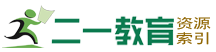史氏家族:涿鹿三千年赋税纪事(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和基层治理,约1.1万字,2.5课时)
文档属性
| 名称 | 史氏家族:涿鹿三千年赋税纪事(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和基层治理,约1.1万字,2.5课时) |

|
|
| 格式 | doc | ||
| 文件大小 | 434.7KB | ||
| 资源类型 | 试卷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历史 | ||
| 更新时间 | 2025-11-24 14:06:43 | ||
图片预览





文档简介
中小学教育资源及组卷应用平台
使用说明:
1.本故事主要服务于选择性必修一第16课《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和第17课《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内容,以虚构的家族传记故事的形式把本来枯燥难记的历史知识生动形象的展现出来,且以朝代顺序进行讲述,对16、17两课内容进行整合。主要内容是各个时期的赋税制度和户籍制度,同时也包含了井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均田制这三个土地制度,以及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和明朝的“里加制”这两个基层治理内容。
2.教师可把“涿鹿县”改为自己所教学生的所在地,并对故事里不符合当地的内容略作修改(修改的地方不是很多,除了“序章”还要注意抗日战争时期看其究竟是在敌后根据地还是国统区亦或是沦陷区)。
3.每个朝代后都有几行的空格,教师可带领学生把最重要的知识写出来。最后在表格中一起总结各朝代的赋税制度和户籍制度,不重要或教材不讲的可直接“划 / ”。故事看完后再翻看课本勾画相关知识点就更容易理解和记忆了。
4.讲东汉故事时可让学生结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4课最后的“问题探究”查看《后汉书 仲长统列传》节选的有关东汉豪强势力迅猛发展的文言文进行学习。
史氏家族:涿鹿三千年赋税纪事(西周至2021年)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和赋税制度演变学案
编者:陈慧颖
序章:涿鹿之壤
涿鹿,华北平原北缘的古老土地,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曾在此征战。这里土壤肥沃,桑干河水蜿蜒而过,滋养着世代耕作的史氏家族。他们的命运,始终与王朝更迭下的田亩、户籍、赋税紧紧交织……
一、西周:井田之上的集体劳作
(公元前10世纪)
西周时,史氏先祖“史阜”是涿鹿的一名“庶人”。他每日在井田上劳作——八块私田环绕一块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上交领主。“大伙儿先耕公田,再种私田!”史阜对儿子们喊道。这是井田制下的集体劳动,家族依附于领主,无人拥有土地私有权。
二、春秋战国:裂变的秩序
(公元前6世纪)
春秋末年,井田制逐渐瓦解。史阜的后人“史耕”发现,邻村有人开垦荒地成为地主,雇佣农民耕种。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涿鹿也按田亩征税。史耕对长子叹息:“井田公田荒废了,如今缴税看田不看人,咱家得多垦荒才成!”
三、秦朝:史秦一家的悲歌与暴政
(公元前215年左右)
秦统一天下后,涿鹿史家的史秦一老汉一家,是秦朝暴政的缩影。他家有三个儿子,命运却皆被朝廷掌控:
长子史秦城,身强体壮,被征发为戍卒,远赴北疆修筑长城,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次子史秦边,也被征为戍卒,前往南方戍守边关,同样一去不返。
只剩下幼子史秦耕在家勉力耕种几亩薄田,但收成的大半( “泰半之赋” )都需上缴,此外还有沉重的口赋压得他喘不过气,全家终年劳苦却不得温饱。
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包括更卒、正卒、戍卒)让史秦一家骨肉分离,生活困苦。乡邻皆如此,但所有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秦法严苛,动辄“轻则砍手足,重则全村连”。史秦一老汉每日都活在恐惧之中,唯恐自家遭遇不测。到了秦二世胡亥时,统治更为残暴,史家和天下百姓一样,已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
四、汉代:编户齐民的荣光与悲欢
(公元前140年 - 公元前60年)
汉初,推行“与民休息”的国策。史家后人史汉昌作为编户齐民,安心耕种着祖传的几十亩田地。当时的田税极低,汉景帝时甚至降至三十税一,史汉昌常对家人说:“当今圣上体恤我等,田税轻如鸿毛,只要肯出力,仓廪充实指日可待!”
然而,福兮祸所伏。正是这极低的税率,使得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获利最丰,势力急剧膨胀。同乡豪强张氏,勾结县衙小吏,先是暗中挪动田界,后又伪造债契,硬生生将史家大半良田划归己有。史汉昌据理力争,反遭毒打,最终郁郁而终。临终前,他握着长子史汉强的手说:“儿啊,税轻本是好事,奈何我家田少力弱,反成豪强盘中餐……这仇,要记下!”
转眼到了汉武帝时期。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左右),朝廷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之太行山以东发生特大水灾,七十万饥民亟待赈济,国库一时间捉襟见肘。一道法令传至涿鹿:向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及车船所有者征收算缗钱——即一次性缴纳10%的财产税。史汉强此时已继承家业,务农为生,本与此无关。但欺压他家的豪强张氏,不仅田连阡陌,更在郡城经营着庞大的生意,正是“算缗”的重点对象。
张氏试图隐匿财产,但两年后,武帝颁布了更严厉的告缗令 :鼓励百姓告发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者,一旦查实,被告者财产没收,告发者可得其一半作为奖赏。
史汉强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深知张家底细,遂毅然赴郡府告发。官府查抄张氏家产,果获巨万。史汉强因此获得了巨额赏赐,不仅夺回了被霸占的祖田,家道也从此中兴。他感叹道:“算缗、告缗,本是朝廷敛财之术,于我史家,竟是沉冤得雪之机!可见国之政策,福祸相依,实难预料。”
时光荏苒,到了汉宣帝时期。史汉强之侄史汉德因德行高尚、年高望重,在七十三岁那年被地方官举荐,由朝廷赐予鸠杖。授杖之日,乡里荣之。这是一根长九尺、顶端刻有斑鸠形象的特制手杖,是尊老养老的象征。史汉德凭借王杖,可以自由行走于驰道旁, 见官不必跪拜,甚至地位相当于六百石的官员,地方官需以礼相待。县中每逢大事,县令常请史汉德顾问,以示敬老尊贤。老人抚着王杖对族中子弟言道:“《礼记》云‘养衰老,授几杖’,吾皇圣明,使我老有所尊。尔等当谨守家业,忠君爱国,方不负这编户齐民之本分。” 然而,荣耀的背后,史家作为编户齐民,每年仍需按丁口缴纳口赋 (儿童税)、算赋 (成人头税),并承担相应的徭役,帝国的治理与索取,从未因荣耀而停止。
东汉末年,涿鹿史家已分为两支。一支如史汉广,凭借郡县吏职,广占良田,成为"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的地方豪强。他强占邻村水源,逼使小农"投附"为佃客,史家田产日增。而另一支远亲史汉平,祖传田地被豪强圈占,沦为"徒附",全家只能为史汉广家耕作,住破屋,食不果腹。每逢岁末,史汉平望着仓中仅剩的谷种,对幼子叹道:"同是史姓,彼为膏田之主,我为饥寒之奴!" 一场黄巾风暴,已在涿鹿的裂痕中悄然酝酿。
五、晋朝:白籍侨民与土断之痛
(公元317年 - 公元5世纪)
西晋永嘉之乱,匈奴铁骑攻破洛阳,北方陷入血雨腥风。史家年轻一辈的史晋安,携家带口,随着汹涌的南迁人潮,告别涿鹿故土,一路颠沛流离,最终渡过长江,来到淮南一带。
此时,东晋朝廷初立,为安抚和笼络像史晋安这样南渡的北方士民,实施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侨置郡县。朝廷在长江南北一带,按照流民原有的籍贯,设立了许多名称相同的州、郡、县。于是,史晋安一家被安置在了“南涿鹿县”(此为虚构的侨县名,用以教学示意,实际可能有涿郡或幽州的侨置),这个“南涿鹿”在地理上位于淮南,但在行政上却是一个虚拟的、寄托乡愁的符号。政府对侨民另立户籍,因其用白纸书写,称为 “白籍”。手持“白籍”,史晋安一家获得了极大的优待: 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长达二十年。这让他们在异乡得以喘息,重建家园。史晋安常对子女说:“虽寄人篱下,然朝廷优容,使我等保有涿鹿籍贯,不忘根本,这‘白籍’便是咱们的护身符啊!”
然而,数十年过去,问题逐渐浮现。这些享有特权的“白籍”侨民,与当地土著(登记在 “黄籍” 上的正式户籍人口)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大量的潜在税源和兵源被隐匿在侨州郡县内,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和治理效率。
于是,东晋朝廷多次推行“土断” 政策。所谓“土断”,就是取消侨州郡县的行政建制,将侨民原有的“白籍”户口断然裁撤,统一登记入所在地区的“黄籍”,让他们成为当地的正式编户,从此与土著一样承担赋税和徭役。
这一次的“土断”令下到了“南涿鹿县”。官吏上门,要将史晋安孙儿一辈的户籍从“白籍”划入“黄籍”。家族内部顿时炸开了锅。
年轻的孙子史晋兴愤然道:“凭什么?我等本是幽州涿郡人,为何要入这淮南的黄籍?这岂不是忘了祖宗?”
而持家的儿子史晋业则更为现实,他愁容满面:“入了黄籍,今年的租调、明年的徭役便一样都逃不掉了!这‘土断’一道,实是断了我等的活路啊!”
已成为族老的史晋安,历经沧桑,看得更为透彻。他制止了家人的争吵,叹息道:“都住口吧!侨置郡县,本是战时权宜之计;白籍优容,岂能世代永享?朝廷如今财政困窘,欲括户增税,‘土断’已是势在必行。我等侨民,终究是客,如今主人家要收回优待,我等又能如何?记住,我们是史家子孙,无论在涿鹿还是淮南,活下去、传承下去,才是根本。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淮南人了,这‘黄籍’……认了吧。”
土断政策像一把无情的手术刀,割裂了侨民寄托在“白籍”上的乡愁与特权。史家和其他侨民一样,被迫更深地融入南方社会,从“侨人”变成了“新人”,开始承担起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完整责任。这段经历,让史家子弟深刻体会到户籍不仅是身份证明,更是国家进行人口管理和资源汲取的核心工具。
六、北魏:均田制与租调之安
(公元485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一项影响深远的诏令颁布到了涿鹿:推行均田制。曾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史家后人史北魏,被官府召集到村社的空地上。里正指着大片无主荒地宣布:“皇恩浩荡,施行均田!男丁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见众人疑惑,里正详细解释道:“这露田啊,就是种粮食的田,不能种树,不能买卖。意思是你只有使用权,就如同这田地上的露水,你来耕种,收获归你,但年老身故后,田要归还官府,重新分配。此外,每丁再给桑田二十亩。” 里正顿了顿,强调说:“桑田可大不相同,是让你种桑树、榆枣的,算是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但同样不准买卖,须世守其业。”
史北魏分得了露田和桑田,激动不已。更让他安心的是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县令宣导时说:“今后,一夫一妇为‘一床’,每年只需向国家缴纳粟二石,这叫‘租’;再缴纳帛(绢)一匹,这叫‘调’。 这‘租’就是田租,用粮食来抵;‘调’则是户调,用你家织的布帛来抵。
史北魏扛着新领的农具,站在属于自己的田埂上,对一同分田的乡邻们感慨道:“都听明白了吧?露田是公家的,咱种粮糊口;桑田是自家的,要传给儿孙!咱交的‘租’是谷子,‘调’是布匹,朝廷法度清楚,只要安心耕种纺织,就能活下去!这真是安民的好政策啊!” 史家终于结束了漂泊,在涿鹿故土重新扎根。然而,他们也明白,这份安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府清丈土地的公平和赋税征收的稳定。
七、隋唐:大索貌阅与租庸调
(公元609年 & 公元624年)
隋朝:大索貌阅——严厉的户口清查
隋文帝年间,为了将逃避税役的隐漏人口重新纳入国家掌控,朝廷推行了严厉的“大索貌阅”政策。所谓“大索”,即大规模搜捕核查;“貌阅”,则是官吏要当面审视百姓的年龄、体貌特征,与户籍档案进行仔细比对。
这一日,涿鹿县衙的胥吏来到史家,对照着户籍册,仔细打量着史家的男丁史隋实。“册上记你年二十二,身高七尺,面有微须。”胥吏一边说,一边让史隋实站直,甚至用手比对他的身高,仔细观察他的面容是否有痣、疤痕等特征,以防有人冒名顶替或虚报年龄。史隋实心中忐忑,他知道,这次核查极为严格,目的是将那些依附于豪强、或因战乱而脱离户籍的“浮浪之人”彻底清查出来。
“大索貌阅”的核心,就是通过这种近乎人身审视的方式,将人口与户籍牢牢绑定,确保朝廷的赋税和徭役来源。 经过此番清查,史家上下被准确登记在册,再也无法逃避国家的课役。
唐朝前期:租庸调制下的相对公平
唐初承袭隋制并加以完善,推行均田制,并在此基础上施行租庸调法。史家后人史唐安分得田产,每年需向官府缴纳:粟二石(此为“租”,即田租);绢(或布)二丈、绵三两(此为“调”,即户调)。
此外,每丁每年原则上需服徭役二十日。但唐朝制度的进步性体现在“庸”上:男子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一日折绢三尺,这便称为“庸”。
这一年,史唐安决定留在家里赶农时,不去服徭役。他一边织绢,一边对儿子解释道:“儿啊,你看清楚了。这二十日的役,咱不去了,按规矩,每日折绢三尺,共缴六丈绢给官府即可。这‘庸’法,实是善政!它的本意,就是‘纳绢代役’。往年强征徭役,必须离家千里,生死难料。如今有了‘庸’, 咱百姓便有了选择。我可以安心在家耕种纺织,只需多织些绢上交,便可免去离家服役之苦,不误农时。朝廷也能稳定获得布帛收入。这比前朝一味强征力役,要仁义得多啊!”史唐安的话,道出了“庸”制在给予农民一定自由、保证农时、促进家庭手工业方面的积极意义。他对儿子总结道:“租庸调,以人丁为本,前提是户口清楚、田亩均平。如今朝廷法度森严,咱家虽是寻常编户,但只要勤劳,便可安身立命。”
八、唐后期:两税之变与《重赋》之痛
(公元780年 - 公元9世纪初)
背景:均田制的瓦解与两税法的诞生
唐玄宗天宝年间,天下承平日久, 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史家所在的涿鹿,豪强与寺院大肆侵吞民田,均田制早已名存实亡。史唐安的曾孙史唐钧一家,祖上分得的露田、桑田大多已被兼并,只能沦为豪强的佃户,生活困苦。而他的堂弟史唐裕,则凭借祖上积累的田产,守着一份不小的家业,成为地主。
由于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随之无法维持。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朝廷控制的在籍户口锐减,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安史之乱后,这种财政困境愈发严重。
面对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了一场赋税革命——两税法。诏令传到涿鹿,县令召集百姓宣导新法:“自今以后,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税!天下百姓,不分主客,一律于现居地立户,根据人丁和资产划分户等,缴纳‘户税’;再根据实际拥有的田亩数量,缴纳‘地税’。每年税款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缴纳,故称‘两税法’!”
意义:征税标准的转变与人身的松弛
新法施行后,史家两兄弟的境遇和感受截然不同。
哥哥史唐钧田产已失,按资产评定为下户,所需缴纳的户税极低。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是,官府不再像过去那样,紧紧盯着他这个人丁本身来征发无穷无尽的租庸调了。他对妻子说:“如今只需按咱这家当缴税,我便可自行外出寻些佣工活计,或安心佃种, 不必再被死死捆在户籍地上,应付那没完没了的人头税和徭役了(意味人身束缚减轻),身子骨总算松快了些。 ”
而弟弟史唐裕田产众多,被定为上户,需缴纳的户税和地税总额巨大。他虽心疼钱财,却也看到了另一面:“税负固然重,但自此以后,官府征税,只问我家资产田亩数目,夏秋两季缴纳完毕便可,我等在自家田庄如何经营,官府干涉大减,倒也自主了不少。 ”
在长安为官的史家子弟史唐文 (史唐裕之子,以科举入仕)与白居易论及此事时,看得更为透彻:“杨相公此法,最要紧处有二:其一,征税之基,由身丁转为资产,此乃千古大变,贫者税轻,富者税重,合乎情理;其二,百姓完税之后,其身较以往大为自由,官府不再事无巨细皆欲控制,此实乃‘松绑’也,利于百姓四处谋生,朝廷亦可省却诸多管理之烦。 ”
这两兄弟的境遇和史唐文的见解,正点出了两税法的两条核心意义:
第一, 征税的主要标准从人丁转为财产,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丁身为本的赋税制度。
第二, 简化税制,将各种赋役合并,以货币计税,极大地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在完成定额税收后,获得了更大的生产与流动自由。
弊端:法外横生与《重赋》的控诉
然而,好景不长。朝廷规定的两税额度很快变成了一个基数,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各种苛捐杂税又纷纷出台。史唐文一次回乡省亲,亲眼目睹了家乡的惨状:官府不仅在两税正额之外加征“科配”、“折变”,还将税款折成昂贵的绢帛,却按低廉的粮价计算,层层盘剥。他的伯父史唐钧看似人身自由了,却因苛捐杂税而依然赤贫;他的父亲史唐裕也终日愁眉不展,言说官府催逼“羡余”(地方官员为讨好皇帝进贡的额外税收),家业已难以支撑。
返回长安后,史唐文心情沉重地拜访白居易,将家乡涿鹿及沿途所见两税法之弊尽数相告……白居易听罢,愤懑难平,挥笔写下了《重赋》一诗: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史唐文读到这首诗时,泪流满面。两税法“人身控制减轻”的良法美意,早已被残酷的现实吞噬。他将诗作抄录寄回涿鹿,史唐钧在病榻前听儿子读完,长叹一声:“身子是自由了些,可这税赋若能逼死人,这自由又有何用……” 两税法后期的消极影响,通过这首《重赋》,深深地刻入了史家的记忆之中。
九、宋朝:主客分野与变法波澜
(公元1070年 - 12世纪初)
第一节:主户的忧烦与客户的艰辛
北宋熙宁年间,涿鹿县的史家后人史宋臣,是个典型的主户。所谓主户,是指在本地区拥有田产、需要承担国家赋役的“税户”。史宋臣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两百亩良田,虽非大富大贵,但在乡里也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然而,这份家业带给他的不仅是温饱,更有无尽的忧烦。
史宋臣的田产,大部分租给同村的李三耕种。李三是个客户,即没有自家田产、需要租种主户土地的佃农。每年秋收,按照“对分制”,李三需要将田里产出的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史宋臣。
这年夏天,雨水不足,收成眼看要歉收。一日,李三愁容满面地来找史宋臣:“史员外,您也看到了,这老天爷不给饭吃,今年这租子……能否宽限些时日,或者减免一些?家里娃儿都快揭不开锅了。”史宋臣看着眼前这个被烈日晒得黝黑的汉子,心中也是不忍。他叹口气道:“李三兄弟,你的难处我晓得。可我的难处,你又可知?县里的‘衙前’役(主管运送官物,亏失须赔偿)眼看就要轮到我家了,这差事凶险;春秋两税,丝帛麦粟,一样不能少;还有那按户等摊派的各类杂徭……我这家底,也是朝不保夕啊。” 李三闻言,黯然低头。这就是主户与客户的现实:客户虽无田产,不直接向国家缴纳两税,但承受着地主的地租剥削,生活艰难;主户虽享有地租,却要独自承担国家所有的赋税和徭役,压力巨大,特别是像史宋臣这样的中下层主户,往往一场重役就可能倾家荡产。
第二节:王安石变法的冲击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消息传到涿鹿,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县令召集县内主户宣导新法,其中与史宋臣关系最大的便是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和保甲法。
对于免役法,史宋臣初闻时是将信将疑。法令规定,过去由主户轮流承担的各种差役(如衙前、里正等),现在可以不用亲自服役,而是按照户等高低缴纳“免役钱”,由政府用这笔钱招募他人服役。史宋臣回家后,拨拉着算盘对儿子说:“若真如此,咱家评为四等户,算下来每年需纳役钱十五贯。虽是一笔开销,但比起让我抛家舍业,甚至冒着赔累家产的风险去押送官粮,却是划算多了!此法若成,我等便可专心经营田庄,确是德政!” 他看到了新法带来的稳定性和对生产的保障。
然而,对于保甲法,史宋臣的感受就复杂得多。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正。主户和客户都要编入保甲。更关键的是,保甲负有维持治安、纠察不法之责,但很快,更重要的职责变成了代替衙役,向民户催税。由于史宋臣识文断字,家境尚可,被推举为所在保的保长。
起初,史宋臣还觉得这是乡里对自己的信任。但很快,烦恼就来了。作为保长,他不仅要组织保丁夜间巡防,更要负责催督本保内各户的税钱和役钱。当他拿着税单走到李三家门口时,心情格外沉重。李三缴不起地租,更别说役钱了(虽然客户理论上只需缴纳同等主户免役钱的一半,称为“助役钱”,但对他们仍是沉重负担)。李三的哀求声让他无法硬起心肠。可完不成催税任务,县里责罚的却是他史宋臣。
第三节: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这年秋天,县尉督税甚急。史宋臣硬着头皮再次来到李三家。李三的妻子哭着说:“保长,不是我们不缴,实在是颗粒无收,拿什么缴啊?”史宋臣看着家徒四壁的景象,最终长叹一声,从自家本已紧张的钱袋里,垫付了李三家的助役钱。
回到家中,儿子不解地问:“父亲,为何要替他家垫付?自家尚且艰难。” 史宋臣疲惫地坐下,无奈道:“邻里乡亲,岂能真逼得他家卖儿鬻女?这保甲法,本意是寓兵于农,强兵防盗。可如今,你我这保长、保丁,倒成了官府催税的马前卒。催税本是无底洞,这‘保’竟成了紧箍咒,将咱与贫苦客户牢牢捆在一起,一损俱损。王相公的免役法,本为减农负,然执行起来,这役钱成了常例,分文不少;而这保甲法更使乡邻关系紧张,我这保长,里外不是人啊!”
他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对儿子感慨道:“朝廷法度,初衷或许是好的。但这良法美意,一到下边,为何就变了味? 本为减农负,如今保甲催税比衙役还凶,这绝非长治久安之道。我只盼这朝廷莫要再折腾,让百姓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罢。”
史宋臣的困惑与困境,正是王安石变法在基层社会执行的缩影。新法试图通过金融手段(免役钱)和社会组织(保甲)来解决问题,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底层人民的负担,并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史家的经历,为理解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注脚。
十、元朝:科差重压与户计等级
(公元1290年)
元朝至元二十七年,涿鹿已归入大都路管辖。此时的史家家长史元璋,面临着与先辈截然不同的境遇。元朝将民众分为各种诸色户计,世代相承,不得改变。史家被划为“民户”,即普通农耕户,这决定了他们的义务核心是缴纳赋税,主要是科差。
所谓科差,包含“丝料”和“包银”两项。这年春天,负责征税的蒙古达鲁花赤(镇守官) 带着通事(翻译)和差役来到村里。通事高声宣布:“奉大汗之命,征收科差!每户‘丝料’,交纳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纳银四两!”史元璋心中暗暗叫苦,这税额远比前朝沉重。他小心翼翼地从里正手中接过刻有自己名字的木质税牌,这是缴纳的凭证。
然而,真正的压迫感来自无处不在的四等人制。史元璋作为第三等的“汉人”,地位远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那位达鲁花赤甚至懒得正眼瞧他们这些“汉儿”,一切事务均由一名色目人属官处理。征收时,那色目属官随意将秤砣一压,便说丝斤不足,强行将史元璋家本就不多的粮食折价抵充。史元璋敢怒不敢言,他知道,一旦争执,等待他的可能是鞭挞。回家后,他在族谱的边角悄悄记下:“色目征税吏,恣意加秤斗,汉人田产日削,惟科差岁岁不减。” 在元朝严密的户计制度和民族等级的双重枷锁下,史家和北方众多汉人家庭一样,在赋税的重压和身份的歧视中艰难求生。
十一、明朝:黄册里甲与白银枷锁
(公元1581年)
明万历九年,涿鹿县史家的当家人是史明远。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本里(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的甲首。明朝的基层治理依靠里甲制,每里设里长,下设甲首,职责之一便是协助官府催征钱粮,管理事务。
这年春天,又到了核对赋役之时。县衙户房的书吏来到村里,带来的最重要的凭据便是两本册子:一本是黄册,详细记载了史明远家包括户主、人丁、年龄、事产(土地、房屋、牛畜)在内的全部信息,这是征收赋役的根本依据;另一本则是鱼鳞图册,上面绘有史家田地的形状、四至、亩数,并编号归档,与黄册相互印证,以防欺隐。史明远恭敬地请书吏查看册籍,心中感叹:“黄册定户则, 鱼鳞册辨田亩,朝廷之法,可谓周密。吾等编户齐民,身家尽在此二册之中矣。”
然而,真正让史明远切身感受到赋役变化的,是当时已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此法将原本田赋、徭役以及土贡、方物等各类征派,合并为一, 折银征收。史明远需将田里所出粮米、家中所织布帛,都换成白银,才能完成纳税。他带着辛苦攒下的银子赶到县衙缴纳,户房胥吏接过银子,却说要扣除 “火耗” (官方借口散银熔铸为官银有损耗的加征)。史明远心中不忿,这些银子成色上好,乃是市面上通行的金花银 (指成色上乘的足色白银),何来偌大损耗?他忍不住争辩道:“此法本为‘一概征银’,省民输送之劳,为何还有此等克扣?”胥吏斜睨了他一眼,冷笑道:“熔铸岂能无耗?此乃惯例!”史明远无奈,只得忍气吞声。回来后,他对儿子苦笑道:“一条鞭法,将赋役悉数并征,看似简便。奈何这‘金花银’入官库之途,仍有层层盘剥。清丈造册本是德政,奈何白银入府,小民仍被啃噬!”
十二、清朝:摊丁入亩与保甲连环
(公元1725年)
清雍正年间,史家后人史清田成为了族长。康熙皇帝在位时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将全国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缓和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丁银压力。到了雍正皇帝,更是推行了摊丁入亩 (又称“摊丁入地”或“地丁合一”),将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之中,一体征收。
这意味着,无地的百姓原则上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史清田对前来交租的佃户说:“皇恩浩荡, 如今丁银摊入田税,无地者不缴丁银,有田者方纳地丁,这确是恤贫的善政! ” 史家田产不少,总体税负有所增加,但税额固定,让史清田觉得心里踏实,可以安心规划生产。
但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并未放松,里甲制逐渐被保甲制取代。史清田被编入保甲,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实行连环互保。一日,邻户因灾荒实在无力完税,偷偷逃籍。结果,作为邻居的史清田一家也受到牵连,被传至县衙问话,虽未下狱,却也惊出一身冷汗。他回家后严肃告诫族人:“这保甲制,较之前朝里甲,稽查更严,连坐更甚。 今后各家须谨言慎行,敦亲睦邻,一户有失,全甲受累!” 赋税征收与人身控制,以另一种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
十三、民国:家族的南北分途
(约1937年 - 1949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家面临抉择。族长史民国一支坚守涿鹿故土,而堂弟史国栋为避战乱,携家商迁至首都南京。一家人从此命运分途。
在涿鹿,史民国和乡亲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承受日伪扫荡与苛捐杂税,也经历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为休养民力实施的合理征粮。
而留在南京的史国栋,则深切感受到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抗战后期法币已严重贬值。至1948年8月,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行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法币,并逼迫百姓兑换金银外汇。史国栋被迫将积蓄的几十两黄金和银元换成几沓金圆券。然而短短数月内,物价飞涨,金圆券形同废纸,到年底时,一石米的价格竟高达数亿元金圆券。他袋里的钱甚至买不回一袋米,半生积蓄瞬间化为乌有。
1949年,南京解放,史国栋与涿鹿的族人取得联系。通读彼此的遭遇,他们在家信中叹道: “北地虽苦,犹有生机;南国金玉,尽毁于钞。” 这段分合,深深烙印在家族的记忆里。
十四、新中国:税制嬗变与千年飞跃
(1980年 - 2021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涿鹿。史家后人史新建成为县一中的教师, 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出台后,他成为了家族史上首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成员。他欣慰地对家人说:“纳税是为国家做贡献,咱普通工薪族也有份,这是现代化国家的样子。”
时光飞逝, 2006年,消息传来: 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被取消! 史新建的堂弟、仍在村里务农的史新农得知后,激动地摆酒祭祖:“‘皇粮国税’自古天经地义,今天居然免了!这是亘古未有的德政啊!”他感到身上的担子轻了,对土地的感情更深了。
进入新时代,史家的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到家乡的脱贫攻坚战中。 2021年,当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来,史新农的孙子、已成为村干部的史振兴在家族团聚时感慨:“咱们史家三千年,从井田赋役到免税补贴,真正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尾声:赋税与民命
史氏家族三千年的兴衰起伏,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赋役制度史。从西周井田上的集体劳作,到2021年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家族命运始终与田亩、户籍和税收制度紧密交织。
这部历史揭示了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征税标准从人身转向财产,形态从劳役实物变为货币,而对民众的控制,则从严格束缚走向逐步松绑。 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深刻塑造着国家的命运与民间的生活。
纵观三千年,赋税制度犹如一把双镣的尺子。它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丈量着百姓的负担。其优劣得失,最终的标准唯有一条:是否能够休养民力,藏富于民。 当制度与民休息时,则天下安泰;当税赋竭泽而渔时,则社会动荡。史家的故事告诫我们,制度的进步,其根本尺度在于人民的福祉。
朝代 赋税制度 户籍制度
秦 赋役繁重 /
汉 人头税和田税,商人等还有财产税(武帝“告缗”) 编户齐民
晋 / 侨置郡县、“土断”
北魏 租调制 /
隋 / 大索貌阅
唐 前期:租庸调制,后期:两税法 /
宋 免(募)役法(王安石变法) 主户、客户
元 原有基础+“科差” 诸色户计(世代相袭)
明 一条鞭法 黄册
清 康熙:用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 /
21世纪教育网 www.21cnjy.com 精品试卷·第 2 页 (共 2 页)
HYPERLINK "http://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 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使用说明:
1.本故事主要服务于选择性必修一第16课《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和第17课《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内容,以虚构的家族传记故事的形式把本来枯燥难记的历史知识生动形象的展现出来,且以朝代顺序进行讲述,对16、17两课内容进行整合。主要内容是各个时期的赋税制度和户籍制度,同时也包含了井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均田制这三个土地制度,以及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和明朝的“里加制”这两个基层治理内容。
2.教师可把“涿鹿县”改为自己所教学生的所在地,并对故事里不符合当地的内容略作修改(修改的地方不是很多,除了“序章”还要注意抗日战争时期看其究竟是在敌后根据地还是国统区亦或是沦陷区)。
3.每个朝代后都有几行的空格,教师可带领学生把最重要的知识写出来。最后在表格中一起总结各朝代的赋税制度和户籍制度,不重要或教材不讲的可直接“划 / ”。故事看完后再翻看课本勾画相关知识点就更容易理解和记忆了。
4.讲东汉故事时可让学生结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4课最后的“问题探究”查看《后汉书 仲长统列传》节选的有关东汉豪强势力迅猛发展的文言文进行学习。
史氏家族:涿鹿三千年赋税纪事(西周至2021年)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和赋税制度演变学案
编者:陈慧颖
序章:涿鹿之壤
涿鹿,华北平原北缘的古老土地,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曾在此征战。这里土壤肥沃,桑干河水蜿蜒而过,滋养着世代耕作的史氏家族。他们的命运,始终与王朝更迭下的田亩、户籍、赋税紧紧交织……
一、西周:井田之上的集体劳作
(公元前10世纪)
西周时,史氏先祖“史阜”是涿鹿的一名“庶人”。他每日在井田上劳作——八块私田环绕一块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上交领主。“大伙儿先耕公田,再种私田!”史阜对儿子们喊道。这是井田制下的集体劳动,家族依附于领主,无人拥有土地私有权。
二、春秋战国:裂变的秩序
(公元前6世纪)
春秋末年,井田制逐渐瓦解。史阜的后人“史耕”发现,邻村有人开垦荒地成为地主,雇佣农民耕种。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涿鹿也按田亩征税。史耕对长子叹息:“井田公田荒废了,如今缴税看田不看人,咱家得多垦荒才成!”
三、秦朝:史秦一家的悲歌与暴政
(公元前215年左右)
秦统一天下后,涿鹿史家的史秦一老汉一家,是秦朝暴政的缩影。他家有三个儿子,命运却皆被朝廷掌控:
长子史秦城,身强体壮,被征发为戍卒,远赴北疆修筑长城,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次子史秦边,也被征为戍卒,前往南方戍守边关,同样一去不返。
只剩下幼子史秦耕在家勉力耕种几亩薄田,但收成的大半( “泰半之赋” )都需上缴,此外还有沉重的口赋压得他喘不过气,全家终年劳苦却不得温饱。
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包括更卒、正卒、戍卒)让史秦一家骨肉分离,生活困苦。乡邻皆如此,但所有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秦法严苛,动辄“轻则砍手足,重则全村连”。史秦一老汉每日都活在恐惧之中,唯恐自家遭遇不测。到了秦二世胡亥时,统治更为残暴,史家和天下百姓一样,已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
四、汉代:编户齐民的荣光与悲欢
(公元前140年 - 公元前60年)
汉初,推行“与民休息”的国策。史家后人史汉昌作为编户齐民,安心耕种着祖传的几十亩田地。当时的田税极低,汉景帝时甚至降至三十税一,史汉昌常对家人说:“当今圣上体恤我等,田税轻如鸿毛,只要肯出力,仓廪充实指日可待!”
然而,福兮祸所伏。正是这极低的税率,使得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获利最丰,势力急剧膨胀。同乡豪强张氏,勾结县衙小吏,先是暗中挪动田界,后又伪造债契,硬生生将史家大半良田划归己有。史汉昌据理力争,反遭毒打,最终郁郁而终。临终前,他握着长子史汉强的手说:“儿啊,税轻本是好事,奈何我家田少力弱,反成豪强盘中餐……这仇,要记下!”
转眼到了汉武帝时期。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左右),朝廷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之太行山以东发生特大水灾,七十万饥民亟待赈济,国库一时间捉襟见肘。一道法令传至涿鹿:向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及车船所有者征收算缗钱——即一次性缴纳10%的财产税。史汉强此时已继承家业,务农为生,本与此无关。但欺压他家的豪强张氏,不仅田连阡陌,更在郡城经营着庞大的生意,正是“算缗”的重点对象。
张氏试图隐匿财产,但两年后,武帝颁布了更严厉的告缗令 :鼓励百姓告发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者,一旦查实,被告者财产没收,告发者可得其一半作为奖赏。
史汉强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深知张家底细,遂毅然赴郡府告发。官府查抄张氏家产,果获巨万。史汉强因此获得了巨额赏赐,不仅夺回了被霸占的祖田,家道也从此中兴。他感叹道:“算缗、告缗,本是朝廷敛财之术,于我史家,竟是沉冤得雪之机!可见国之政策,福祸相依,实难预料。”
时光荏苒,到了汉宣帝时期。史汉强之侄史汉德因德行高尚、年高望重,在七十三岁那年被地方官举荐,由朝廷赐予鸠杖。授杖之日,乡里荣之。这是一根长九尺、顶端刻有斑鸠形象的特制手杖,是尊老养老的象征。史汉德凭借王杖,可以自由行走于驰道旁, 见官不必跪拜,甚至地位相当于六百石的官员,地方官需以礼相待。县中每逢大事,县令常请史汉德顾问,以示敬老尊贤。老人抚着王杖对族中子弟言道:“《礼记》云‘养衰老,授几杖’,吾皇圣明,使我老有所尊。尔等当谨守家业,忠君爱国,方不负这编户齐民之本分。” 然而,荣耀的背后,史家作为编户齐民,每年仍需按丁口缴纳口赋 (儿童税)、算赋 (成人头税),并承担相应的徭役,帝国的治理与索取,从未因荣耀而停止。
东汉末年,涿鹿史家已分为两支。一支如史汉广,凭借郡县吏职,广占良田,成为"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的地方豪强。他强占邻村水源,逼使小农"投附"为佃客,史家田产日增。而另一支远亲史汉平,祖传田地被豪强圈占,沦为"徒附",全家只能为史汉广家耕作,住破屋,食不果腹。每逢岁末,史汉平望着仓中仅剩的谷种,对幼子叹道:"同是史姓,彼为膏田之主,我为饥寒之奴!" 一场黄巾风暴,已在涿鹿的裂痕中悄然酝酿。
五、晋朝:白籍侨民与土断之痛
(公元317年 - 公元5世纪)
西晋永嘉之乱,匈奴铁骑攻破洛阳,北方陷入血雨腥风。史家年轻一辈的史晋安,携家带口,随着汹涌的南迁人潮,告别涿鹿故土,一路颠沛流离,最终渡过长江,来到淮南一带。
此时,东晋朝廷初立,为安抚和笼络像史晋安这样南渡的北方士民,实施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侨置郡县。朝廷在长江南北一带,按照流民原有的籍贯,设立了许多名称相同的州、郡、县。于是,史晋安一家被安置在了“南涿鹿县”(此为虚构的侨县名,用以教学示意,实际可能有涿郡或幽州的侨置),这个“南涿鹿”在地理上位于淮南,但在行政上却是一个虚拟的、寄托乡愁的符号。政府对侨民另立户籍,因其用白纸书写,称为 “白籍”。手持“白籍”,史晋安一家获得了极大的优待: 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长达二十年。这让他们在异乡得以喘息,重建家园。史晋安常对子女说:“虽寄人篱下,然朝廷优容,使我等保有涿鹿籍贯,不忘根本,这‘白籍’便是咱们的护身符啊!”
然而,数十年过去,问题逐渐浮现。这些享有特权的“白籍”侨民,与当地土著(登记在 “黄籍” 上的正式户籍人口)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大量的潜在税源和兵源被隐匿在侨州郡县内,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和治理效率。
于是,东晋朝廷多次推行“土断” 政策。所谓“土断”,就是取消侨州郡县的行政建制,将侨民原有的“白籍”户口断然裁撤,统一登记入所在地区的“黄籍”,让他们成为当地的正式编户,从此与土著一样承担赋税和徭役。
这一次的“土断”令下到了“南涿鹿县”。官吏上门,要将史晋安孙儿一辈的户籍从“白籍”划入“黄籍”。家族内部顿时炸开了锅。
年轻的孙子史晋兴愤然道:“凭什么?我等本是幽州涿郡人,为何要入这淮南的黄籍?这岂不是忘了祖宗?”
而持家的儿子史晋业则更为现实,他愁容满面:“入了黄籍,今年的租调、明年的徭役便一样都逃不掉了!这‘土断’一道,实是断了我等的活路啊!”
已成为族老的史晋安,历经沧桑,看得更为透彻。他制止了家人的争吵,叹息道:“都住口吧!侨置郡县,本是战时权宜之计;白籍优容,岂能世代永享?朝廷如今财政困窘,欲括户增税,‘土断’已是势在必行。我等侨民,终究是客,如今主人家要收回优待,我等又能如何?记住,我们是史家子孙,无论在涿鹿还是淮南,活下去、传承下去,才是根本。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淮南人了,这‘黄籍’……认了吧。”
土断政策像一把无情的手术刀,割裂了侨民寄托在“白籍”上的乡愁与特权。史家和其他侨民一样,被迫更深地融入南方社会,从“侨人”变成了“新人”,开始承担起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完整责任。这段经历,让史家子弟深刻体会到户籍不仅是身份证明,更是国家进行人口管理和资源汲取的核心工具。
六、北魏:均田制与租调之安
(公元485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一项影响深远的诏令颁布到了涿鹿:推行均田制。曾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史家后人史北魏,被官府召集到村社的空地上。里正指着大片无主荒地宣布:“皇恩浩荡,施行均田!男丁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见众人疑惑,里正详细解释道:“这露田啊,就是种粮食的田,不能种树,不能买卖。意思是你只有使用权,就如同这田地上的露水,你来耕种,收获归你,但年老身故后,田要归还官府,重新分配。此外,每丁再给桑田二十亩。” 里正顿了顿,强调说:“桑田可大不相同,是让你种桑树、榆枣的,算是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但同样不准买卖,须世守其业。”
史北魏分得了露田和桑田,激动不已。更让他安心的是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县令宣导时说:“今后,一夫一妇为‘一床’,每年只需向国家缴纳粟二石,这叫‘租’;再缴纳帛(绢)一匹,这叫‘调’。 这‘租’就是田租,用粮食来抵;‘调’则是户调,用你家织的布帛来抵。
史北魏扛着新领的农具,站在属于自己的田埂上,对一同分田的乡邻们感慨道:“都听明白了吧?露田是公家的,咱种粮糊口;桑田是自家的,要传给儿孙!咱交的‘租’是谷子,‘调’是布匹,朝廷法度清楚,只要安心耕种纺织,就能活下去!这真是安民的好政策啊!” 史家终于结束了漂泊,在涿鹿故土重新扎根。然而,他们也明白,这份安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府清丈土地的公平和赋税征收的稳定。
七、隋唐:大索貌阅与租庸调
(公元609年 & 公元624年)
隋朝:大索貌阅——严厉的户口清查
隋文帝年间,为了将逃避税役的隐漏人口重新纳入国家掌控,朝廷推行了严厉的“大索貌阅”政策。所谓“大索”,即大规模搜捕核查;“貌阅”,则是官吏要当面审视百姓的年龄、体貌特征,与户籍档案进行仔细比对。
这一日,涿鹿县衙的胥吏来到史家,对照着户籍册,仔细打量着史家的男丁史隋实。“册上记你年二十二,身高七尺,面有微须。”胥吏一边说,一边让史隋实站直,甚至用手比对他的身高,仔细观察他的面容是否有痣、疤痕等特征,以防有人冒名顶替或虚报年龄。史隋实心中忐忑,他知道,这次核查极为严格,目的是将那些依附于豪强、或因战乱而脱离户籍的“浮浪之人”彻底清查出来。
“大索貌阅”的核心,就是通过这种近乎人身审视的方式,将人口与户籍牢牢绑定,确保朝廷的赋税和徭役来源。 经过此番清查,史家上下被准确登记在册,再也无法逃避国家的课役。
唐朝前期:租庸调制下的相对公平
唐初承袭隋制并加以完善,推行均田制,并在此基础上施行租庸调法。史家后人史唐安分得田产,每年需向官府缴纳:粟二石(此为“租”,即田租);绢(或布)二丈、绵三两(此为“调”,即户调)。
此外,每丁每年原则上需服徭役二十日。但唐朝制度的进步性体现在“庸”上:男子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一日折绢三尺,这便称为“庸”。
这一年,史唐安决定留在家里赶农时,不去服徭役。他一边织绢,一边对儿子解释道:“儿啊,你看清楚了。这二十日的役,咱不去了,按规矩,每日折绢三尺,共缴六丈绢给官府即可。这‘庸’法,实是善政!它的本意,就是‘纳绢代役’。往年强征徭役,必须离家千里,生死难料。如今有了‘庸’, 咱百姓便有了选择。我可以安心在家耕种纺织,只需多织些绢上交,便可免去离家服役之苦,不误农时。朝廷也能稳定获得布帛收入。这比前朝一味强征力役,要仁义得多啊!”史唐安的话,道出了“庸”制在给予农民一定自由、保证农时、促进家庭手工业方面的积极意义。他对儿子总结道:“租庸调,以人丁为本,前提是户口清楚、田亩均平。如今朝廷法度森严,咱家虽是寻常编户,但只要勤劳,便可安身立命。”
八、唐后期:两税之变与《重赋》之痛
(公元780年 - 公元9世纪初)
背景:均田制的瓦解与两税法的诞生
唐玄宗天宝年间,天下承平日久, 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史家所在的涿鹿,豪强与寺院大肆侵吞民田,均田制早已名存实亡。史唐安的曾孙史唐钧一家,祖上分得的露田、桑田大多已被兼并,只能沦为豪强的佃户,生活困苦。而他的堂弟史唐裕,则凭借祖上积累的田产,守着一份不小的家业,成为地主。
由于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随之无法维持。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朝廷控制的在籍户口锐减,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安史之乱后,这种财政困境愈发严重。
面对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了一场赋税革命——两税法。诏令传到涿鹿,县令召集百姓宣导新法:“自今以后,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税!天下百姓,不分主客,一律于现居地立户,根据人丁和资产划分户等,缴纳‘户税’;再根据实际拥有的田亩数量,缴纳‘地税’。每年税款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缴纳,故称‘两税法’!”
意义:征税标准的转变与人身的松弛
新法施行后,史家两兄弟的境遇和感受截然不同。
哥哥史唐钧田产已失,按资产评定为下户,所需缴纳的户税极低。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是,官府不再像过去那样,紧紧盯着他这个人丁本身来征发无穷无尽的租庸调了。他对妻子说:“如今只需按咱这家当缴税,我便可自行外出寻些佣工活计,或安心佃种, 不必再被死死捆在户籍地上,应付那没完没了的人头税和徭役了(意味人身束缚减轻),身子骨总算松快了些。 ”
而弟弟史唐裕田产众多,被定为上户,需缴纳的户税和地税总额巨大。他虽心疼钱财,却也看到了另一面:“税负固然重,但自此以后,官府征税,只问我家资产田亩数目,夏秋两季缴纳完毕便可,我等在自家田庄如何经营,官府干涉大减,倒也自主了不少。 ”
在长安为官的史家子弟史唐文 (史唐裕之子,以科举入仕)与白居易论及此事时,看得更为透彻:“杨相公此法,最要紧处有二:其一,征税之基,由身丁转为资产,此乃千古大变,贫者税轻,富者税重,合乎情理;其二,百姓完税之后,其身较以往大为自由,官府不再事无巨细皆欲控制,此实乃‘松绑’也,利于百姓四处谋生,朝廷亦可省却诸多管理之烦。 ”
这两兄弟的境遇和史唐文的见解,正点出了两税法的两条核心意义:
第一, 征税的主要标准从人丁转为财产,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丁身为本的赋税制度。
第二, 简化税制,将各种赋役合并,以货币计税,极大地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在完成定额税收后,获得了更大的生产与流动自由。
弊端:法外横生与《重赋》的控诉
然而,好景不长。朝廷规定的两税额度很快变成了一个基数,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各种苛捐杂税又纷纷出台。史唐文一次回乡省亲,亲眼目睹了家乡的惨状:官府不仅在两税正额之外加征“科配”、“折变”,还将税款折成昂贵的绢帛,却按低廉的粮价计算,层层盘剥。他的伯父史唐钧看似人身自由了,却因苛捐杂税而依然赤贫;他的父亲史唐裕也终日愁眉不展,言说官府催逼“羡余”(地方官员为讨好皇帝进贡的额外税收),家业已难以支撑。
返回长安后,史唐文心情沉重地拜访白居易,将家乡涿鹿及沿途所见两税法之弊尽数相告……白居易听罢,愤懑难平,挥笔写下了《重赋》一诗: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史唐文读到这首诗时,泪流满面。两税法“人身控制减轻”的良法美意,早已被残酷的现实吞噬。他将诗作抄录寄回涿鹿,史唐钧在病榻前听儿子读完,长叹一声:“身子是自由了些,可这税赋若能逼死人,这自由又有何用……” 两税法后期的消极影响,通过这首《重赋》,深深地刻入了史家的记忆之中。
九、宋朝:主客分野与变法波澜
(公元1070年 - 12世纪初)
第一节:主户的忧烦与客户的艰辛
北宋熙宁年间,涿鹿县的史家后人史宋臣,是个典型的主户。所谓主户,是指在本地区拥有田产、需要承担国家赋役的“税户”。史宋臣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两百亩良田,虽非大富大贵,但在乡里也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然而,这份家业带给他的不仅是温饱,更有无尽的忧烦。
史宋臣的田产,大部分租给同村的李三耕种。李三是个客户,即没有自家田产、需要租种主户土地的佃农。每年秋收,按照“对分制”,李三需要将田里产出的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史宋臣。
这年夏天,雨水不足,收成眼看要歉收。一日,李三愁容满面地来找史宋臣:“史员外,您也看到了,这老天爷不给饭吃,今年这租子……能否宽限些时日,或者减免一些?家里娃儿都快揭不开锅了。”史宋臣看着眼前这个被烈日晒得黝黑的汉子,心中也是不忍。他叹口气道:“李三兄弟,你的难处我晓得。可我的难处,你又可知?县里的‘衙前’役(主管运送官物,亏失须赔偿)眼看就要轮到我家了,这差事凶险;春秋两税,丝帛麦粟,一样不能少;还有那按户等摊派的各类杂徭……我这家底,也是朝不保夕啊。” 李三闻言,黯然低头。这就是主户与客户的现实:客户虽无田产,不直接向国家缴纳两税,但承受着地主的地租剥削,生活艰难;主户虽享有地租,却要独自承担国家所有的赋税和徭役,压力巨大,特别是像史宋臣这样的中下层主户,往往一场重役就可能倾家荡产。
第二节:王安石变法的冲击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消息传到涿鹿,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县令召集县内主户宣导新法,其中与史宋臣关系最大的便是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和保甲法。
对于免役法,史宋臣初闻时是将信将疑。法令规定,过去由主户轮流承担的各种差役(如衙前、里正等),现在可以不用亲自服役,而是按照户等高低缴纳“免役钱”,由政府用这笔钱招募他人服役。史宋臣回家后,拨拉着算盘对儿子说:“若真如此,咱家评为四等户,算下来每年需纳役钱十五贯。虽是一笔开销,但比起让我抛家舍业,甚至冒着赔累家产的风险去押送官粮,却是划算多了!此法若成,我等便可专心经营田庄,确是德政!” 他看到了新法带来的稳定性和对生产的保障。
然而,对于保甲法,史宋臣的感受就复杂得多。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正。主户和客户都要编入保甲。更关键的是,保甲负有维持治安、纠察不法之责,但很快,更重要的职责变成了代替衙役,向民户催税。由于史宋臣识文断字,家境尚可,被推举为所在保的保长。
起初,史宋臣还觉得这是乡里对自己的信任。但很快,烦恼就来了。作为保长,他不仅要组织保丁夜间巡防,更要负责催督本保内各户的税钱和役钱。当他拿着税单走到李三家门口时,心情格外沉重。李三缴不起地租,更别说役钱了(虽然客户理论上只需缴纳同等主户免役钱的一半,称为“助役钱”,但对他们仍是沉重负担)。李三的哀求声让他无法硬起心肠。可完不成催税任务,县里责罚的却是他史宋臣。
第三节: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这年秋天,县尉督税甚急。史宋臣硬着头皮再次来到李三家。李三的妻子哭着说:“保长,不是我们不缴,实在是颗粒无收,拿什么缴啊?”史宋臣看着家徒四壁的景象,最终长叹一声,从自家本已紧张的钱袋里,垫付了李三家的助役钱。
回到家中,儿子不解地问:“父亲,为何要替他家垫付?自家尚且艰难。” 史宋臣疲惫地坐下,无奈道:“邻里乡亲,岂能真逼得他家卖儿鬻女?这保甲法,本意是寓兵于农,强兵防盗。可如今,你我这保长、保丁,倒成了官府催税的马前卒。催税本是无底洞,这‘保’竟成了紧箍咒,将咱与贫苦客户牢牢捆在一起,一损俱损。王相公的免役法,本为减农负,然执行起来,这役钱成了常例,分文不少;而这保甲法更使乡邻关系紧张,我这保长,里外不是人啊!”
他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对儿子感慨道:“朝廷法度,初衷或许是好的。但这良法美意,一到下边,为何就变了味? 本为减农负,如今保甲催税比衙役还凶,这绝非长治久安之道。我只盼这朝廷莫要再折腾,让百姓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罢。”
史宋臣的困惑与困境,正是王安石变法在基层社会执行的缩影。新法试图通过金融手段(免役钱)和社会组织(保甲)来解决问题,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底层人民的负担,并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史家的经历,为理解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注脚。
十、元朝:科差重压与户计等级
(公元1290年)
元朝至元二十七年,涿鹿已归入大都路管辖。此时的史家家长史元璋,面临着与先辈截然不同的境遇。元朝将民众分为各种诸色户计,世代相承,不得改变。史家被划为“民户”,即普通农耕户,这决定了他们的义务核心是缴纳赋税,主要是科差。
所谓科差,包含“丝料”和“包银”两项。这年春天,负责征税的蒙古达鲁花赤(镇守官) 带着通事(翻译)和差役来到村里。通事高声宣布:“奉大汗之命,征收科差!每户‘丝料’,交纳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纳银四两!”史元璋心中暗暗叫苦,这税额远比前朝沉重。他小心翼翼地从里正手中接过刻有自己名字的木质税牌,这是缴纳的凭证。
然而,真正的压迫感来自无处不在的四等人制。史元璋作为第三等的“汉人”,地位远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那位达鲁花赤甚至懒得正眼瞧他们这些“汉儿”,一切事务均由一名色目人属官处理。征收时,那色目属官随意将秤砣一压,便说丝斤不足,强行将史元璋家本就不多的粮食折价抵充。史元璋敢怒不敢言,他知道,一旦争执,等待他的可能是鞭挞。回家后,他在族谱的边角悄悄记下:“色目征税吏,恣意加秤斗,汉人田产日削,惟科差岁岁不减。” 在元朝严密的户计制度和民族等级的双重枷锁下,史家和北方众多汉人家庭一样,在赋税的重压和身份的歧视中艰难求生。
十一、明朝:黄册里甲与白银枷锁
(公元1581年)
明万历九年,涿鹿县史家的当家人是史明远。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本里(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的甲首。明朝的基层治理依靠里甲制,每里设里长,下设甲首,职责之一便是协助官府催征钱粮,管理事务。
这年春天,又到了核对赋役之时。县衙户房的书吏来到村里,带来的最重要的凭据便是两本册子:一本是黄册,详细记载了史明远家包括户主、人丁、年龄、事产(土地、房屋、牛畜)在内的全部信息,这是征收赋役的根本依据;另一本则是鱼鳞图册,上面绘有史家田地的形状、四至、亩数,并编号归档,与黄册相互印证,以防欺隐。史明远恭敬地请书吏查看册籍,心中感叹:“黄册定户则, 鱼鳞册辨田亩,朝廷之法,可谓周密。吾等编户齐民,身家尽在此二册之中矣。”
然而,真正让史明远切身感受到赋役变化的,是当时已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此法将原本田赋、徭役以及土贡、方物等各类征派,合并为一, 折银征收。史明远需将田里所出粮米、家中所织布帛,都换成白银,才能完成纳税。他带着辛苦攒下的银子赶到县衙缴纳,户房胥吏接过银子,却说要扣除 “火耗” (官方借口散银熔铸为官银有损耗的加征)。史明远心中不忿,这些银子成色上好,乃是市面上通行的金花银 (指成色上乘的足色白银),何来偌大损耗?他忍不住争辩道:“此法本为‘一概征银’,省民输送之劳,为何还有此等克扣?”胥吏斜睨了他一眼,冷笑道:“熔铸岂能无耗?此乃惯例!”史明远无奈,只得忍气吞声。回来后,他对儿子苦笑道:“一条鞭法,将赋役悉数并征,看似简便。奈何这‘金花银’入官库之途,仍有层层盘剥。清丈造册本是德政,奈何白银入府,小民仍被啃噬!”
十二、清朝:摊丁入亩与保甲连环
(公元1725年)
清雍正年间,史家后人史清田成为了族长。康熙皇帝在位时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将全国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缓和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丁银压力。到了雍正皇帝,更是推行了摊丁入亩 (又称“摊丁入地”或“地丁合一”),将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之中,一体征收。
这意味着,无地的百姓原则上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史清田对前来交租的佃户说:“皇恩浩荡, 如今丁银摊入田税,无地者不缴丁银,有田者方纳地丁,这确是恤贫的善政! ” 史家田产不少,总体税负有所增加,但税额固定,让史清田觉得心里踏实,可以安心规划生产。
但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并未放松,里甲制逐渐被保甲制取代。史清田被编入保甲,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实行连环互保。一日,邻户因灾荒实在无力完税,偷偷逃籍。结果,作为邻居的史清田一家也受到牵连,被传至县衙问话,虽未下狱,却也惊出一身冷汗。他回家后严肃告诫族人:“这保甲制,较之前朝里甲,稽查更严,连坐更甚。 今后各家须谨言慎行,敦亲睦邻,一户有失,全甲受累!” 赋税征收与人身控制,以另一种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
十三、民国:家族的南北分途
(约1937年 - 1949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家面临抉择。族长史民国一支坚守涿鹿故土,而堂弟史国栋为避战乱,携家商迁至首都南京。一家人从此命运分途。
在涿鹿,史民国和乡亲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承受日伪扫荡与苛捐杂税,也经历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为休养民力实施的合理征粮。
而留在南京的史国栋,则深切感受到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抗战后期法币已严重贬值。至1948年8月,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行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法币,并逼迫百姓兑换金银外汇。史国栋被迫将积蓄的几十两黄金和银元换成几沓金圆券。然而短短数月内,物价飞涨,金圆券形同废纸,到年底时,一石米的价格竟高达数亿元金圆券。他袋里的钱甚至买不回一袋米,半生积蓄瞬间化为乌有。
1949年,南京解放,史国栋与涿鹿的族人取得联系。通读彼此的遭遇,他们在家信中叹道: “北地虽苦,犹有生机;南国金玉,尽毁于钞。” 这段分合,深深烙印在家族的记忆里。
十四、新中国:税制嬗变与千年飞跃
(1980年 - 2021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涿鹿。史家后人史新建成为县一中的教师, 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出台后,他成为了家族史上首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成员。他欣慰地对家人说:“纳税是为国家做贡献,咱普通工薪族也有份,这是现代化国家的样子。”
时光飞逝, 2006年,消息传来: 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被取消! 史新建的堂弟、仍在村里务农的史新农得知后,激动地摆酒祭祖:“‘皇粮国税’自古天经地义,今天居然免了!这是亘古未有的德政啊!”他感到身上的担子轻了,对土地的感情更深了。
进入新时代,史家的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到家乡的脱贫攻坚战中。 2021年,当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来,史新农的孙子、已成为村干部的史振兴在家族团聚时感慨:“咱们史家三千年,从井田赋役到免税补贴,真正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尾声:赋税与民命
史氏家族三千年的兴衰起伏,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赋役制度史。从西周井田上的集体劳作,到2021年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家族命运始终与田亩、户籍和税收制度紧密交织。
这部历史揭示了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征税标准从人身转向财产,形态从劳役实物变为货币,而对民众的控制,则从严格束缚走向逐步松绑。 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深刻塑造着国家的命运与民间的生活。
纵观三千年,赋税制度犹如一把双镣的尺子。它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丈量着百姓的负担。其优劣得失,最终的标准唯有一条:是否能够休养民力,藏富于民。 当制度与民休息时,则天下安泰;当税赋竭泽而渔时,则社会动荡。史家的故事告诫我们,制度的进步,其根本尺度在于人民的福祉。
朝代 赋税制度 户籍制度
秦 赋役繁重 /
汉 人头税和田税,商人等还有财产税(武帝“告缗”) 编户齐民
晋 / 侨置郡县、“土断”
北魏 租调制 /
隋 / 大索貌阅
唐 前期:租庸调制,后期:两税法 /
宋 免(募)役法(王安石变法) 主户、客户
元 原有基础+“科差” 诸色户计(世代相袭)
明 一条鞭法 黄册
清 康熙:用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 /
21世纪教育网 www.21cnjy.com 精品试卷·第 2 页 (共 2 页)
HYPERLINK "http://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 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政治制度
- 第1课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第2课 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 第3课 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 第4课 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
- 第二单元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 第5课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 第6课 西方的文官制度
- 第7课 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拨与管理
- 第三单元 法律与教化
- 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 第9课 近代西方的法律与教化
- 第10课 当代中国的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
- 第四单元 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
- 第11课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
- 第12课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与国际法的发展
- 第13课 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
- 第14课 当代中国的外交
- 第五单元 货币与赋税制度
- 第15课 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 第16课 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
- 第六单元 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 第17课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
- 第18课 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 活动课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