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俄日朵雪峰之侧》导学案(教师版)
文档属性
| 名称 | 2.3《俄日朵雪峰之侧》导学案(教师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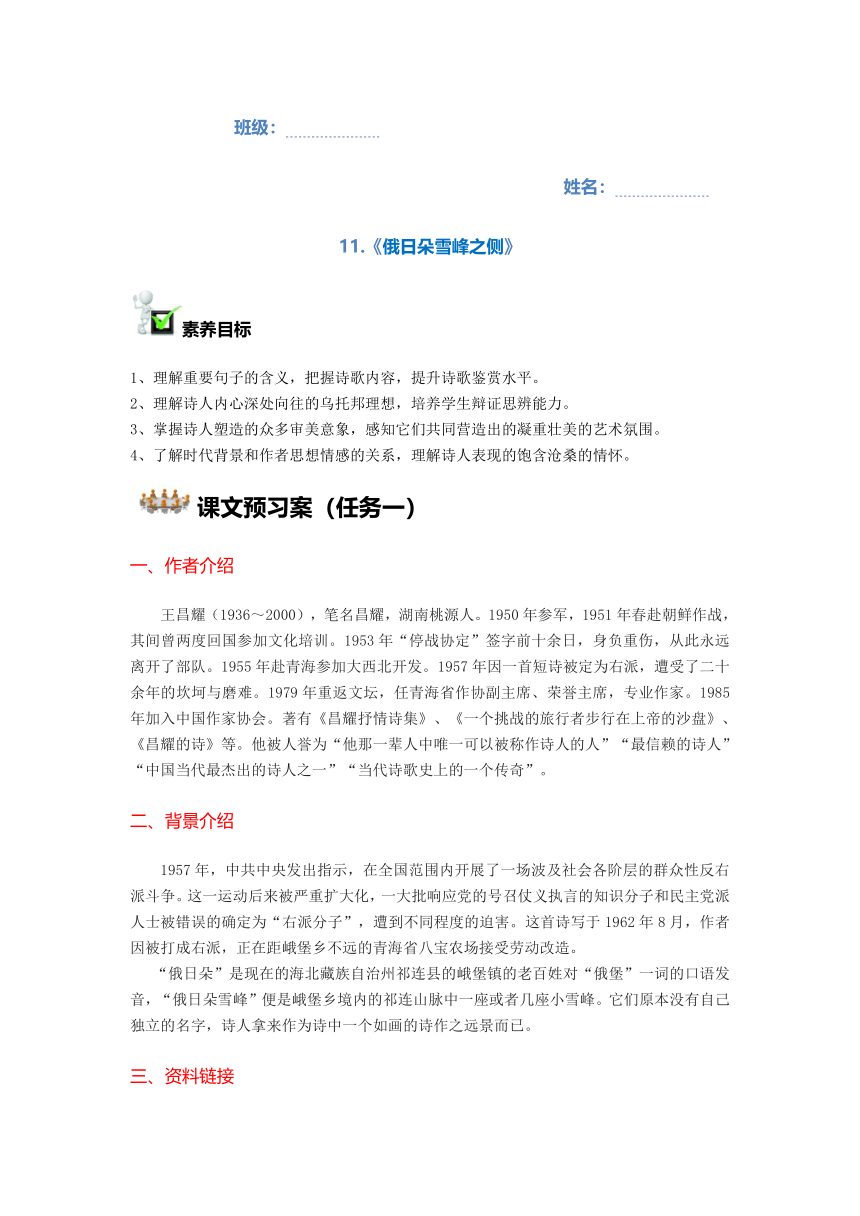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207.7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0-11-05 00:00:0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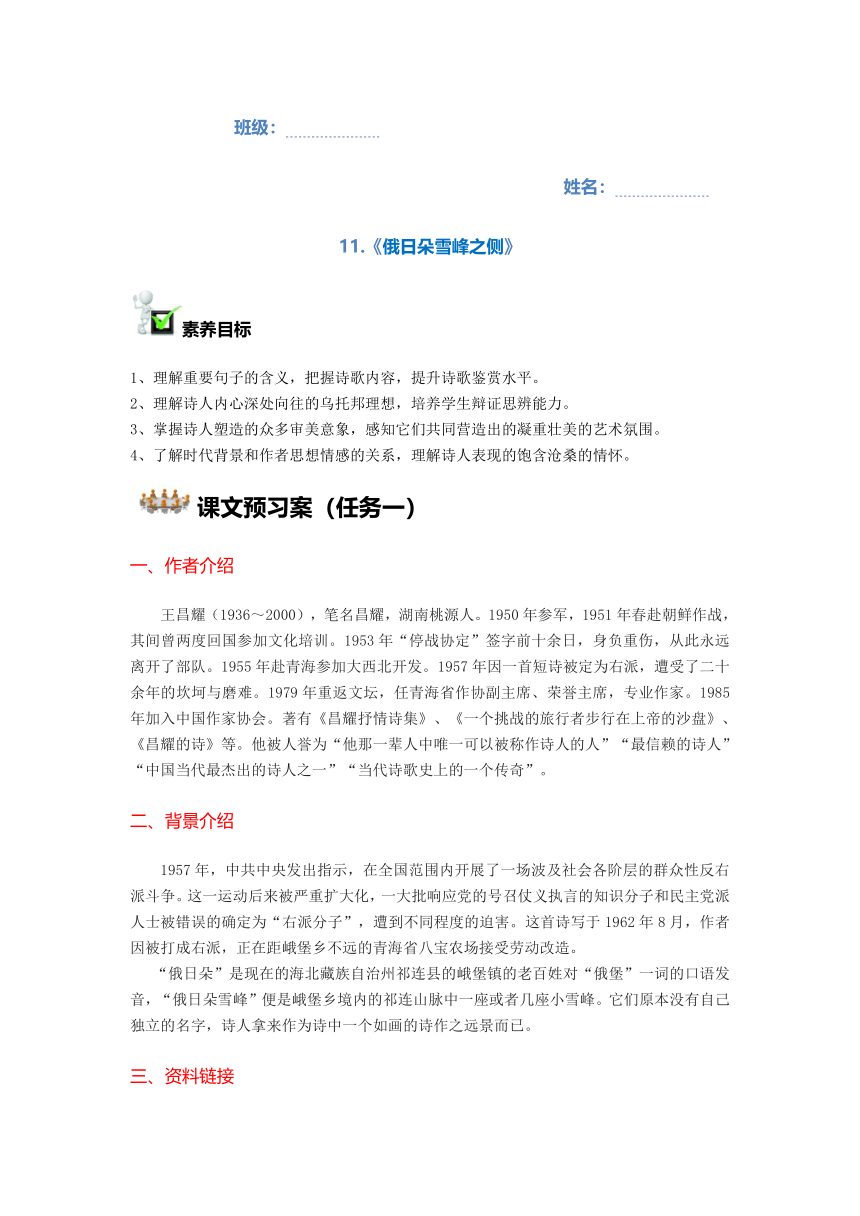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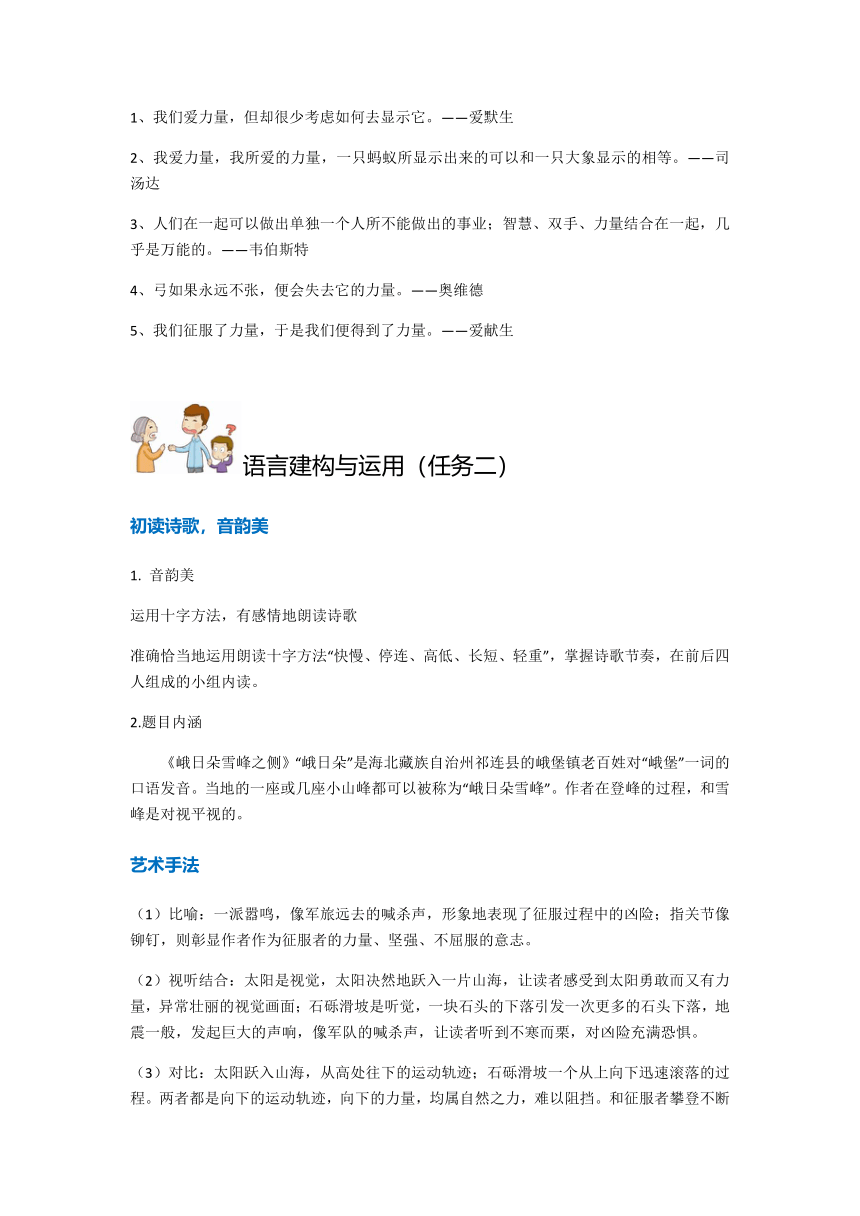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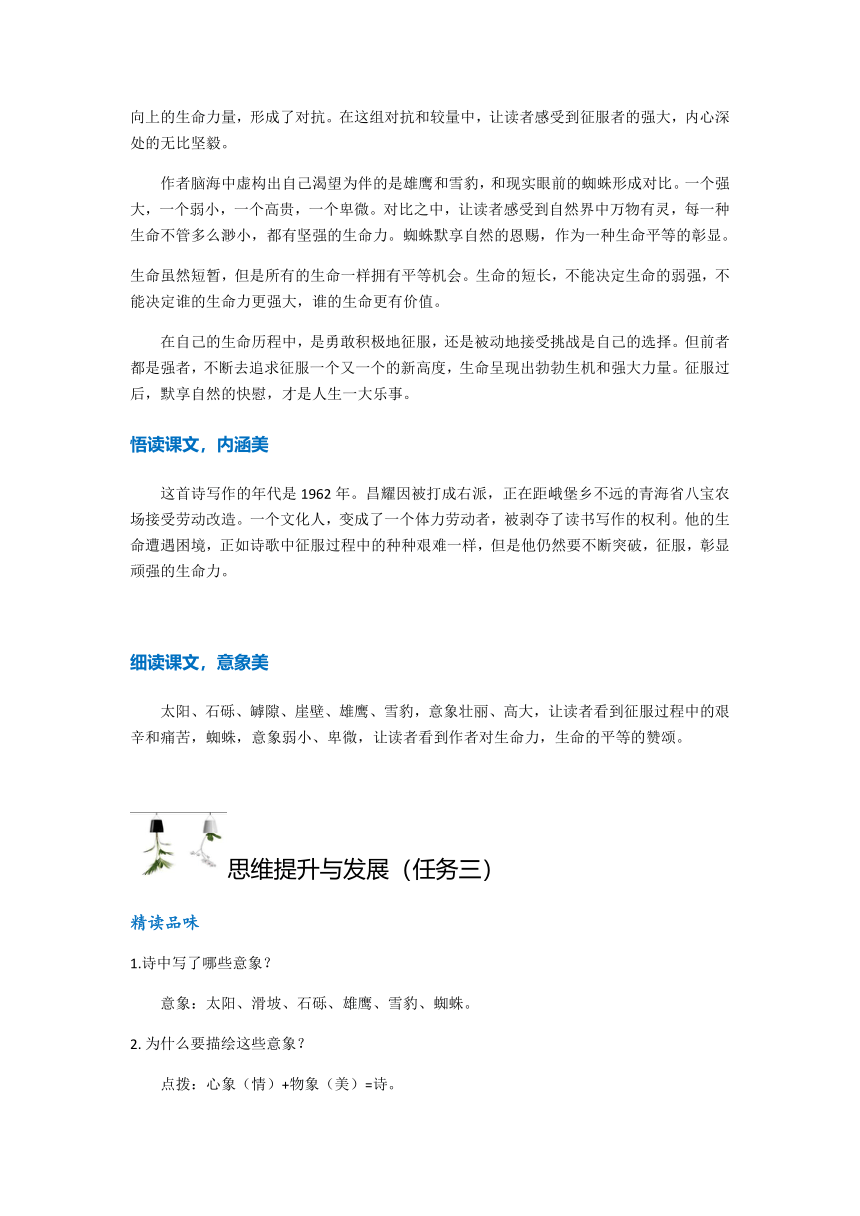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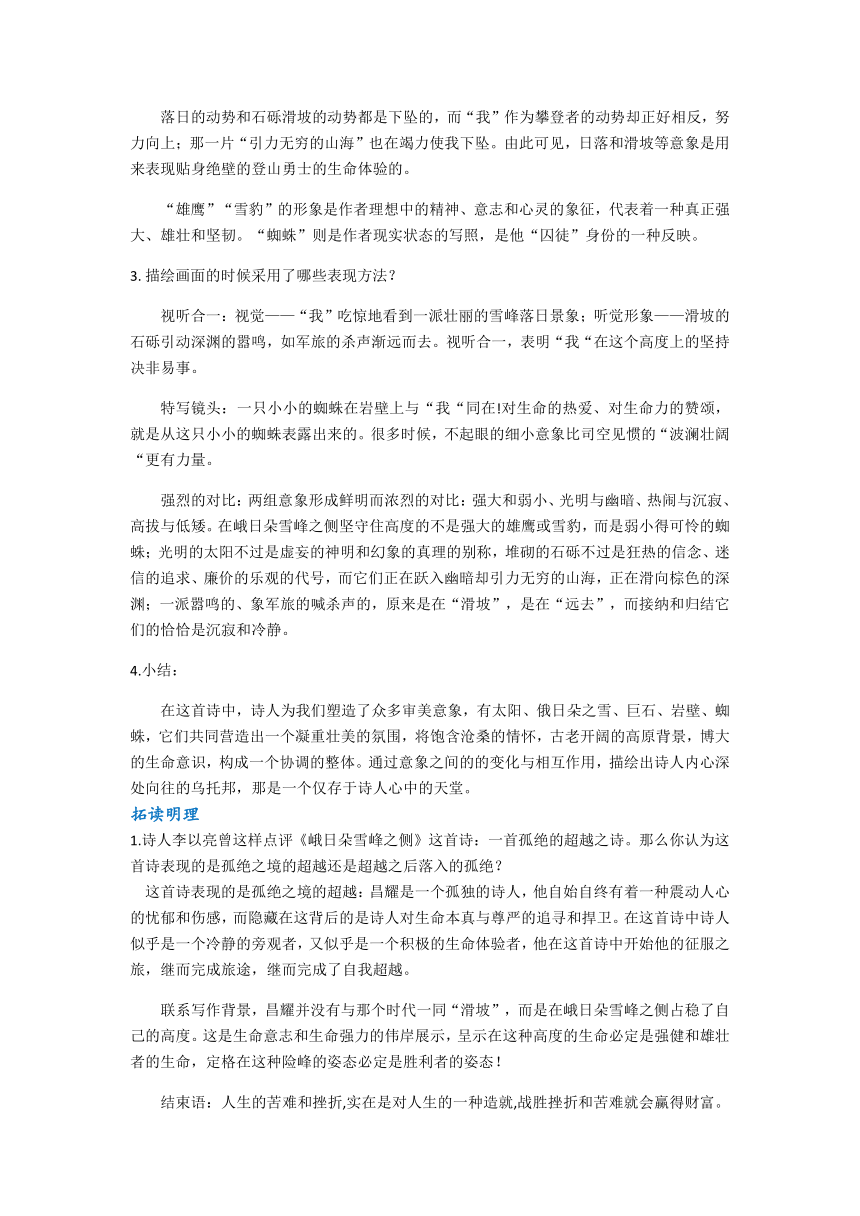
文档简介
班级:
姓名:
11.《俄日朵雪峰之侧》
素养目标
1、理解重要句子的含义,把握诗歌内容,提升诗歌鉴赏水平。
2、理解诗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乌托邦理想,培养学生辩证思辨能力。
3、掌握诗人塑造的众多审美意象,感知它们共同营造出的凝重壮美的艺术氛围。
4、了解时代背景和作者思想情感的关系,理解诗人表现的饱含沧桑的情怀。
课文预习案(任务一)
一、作者介绍
王昌耀(1936~2000),笔名昌耀,湖南桃源人。1950年参军,1951年春赴朝鲜作战,其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身负重伤,从此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赴青海参加大西北开发。1957年因一首短诗被定为右派,遭受了二十余年的坎坷与磨难。1979年重返文坛,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荣誉主席,专业作家。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昌耀抒情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昌耀的诗》等。他被人誉为“他那一辈人中唯一可以被称作诗人的人”“最信赖的诗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
二、背景介绍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反右派斗争。这一运动后来被严重扩大化,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的确定为“右派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首诗写于1962年8月,作者因被打成右派,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俄日朵”是现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峨堡镇的老百姓对“俄堡”一词的口语发音,“俄日朵雪峰”便是峨堡乡境内的祁连山脉中一座或者几座小雪峰。它们原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诗人拿来作为诗中一个如画的诗作之远景而已。
三、资料链接
1、我们爱力量,但却很少考虑如何去显示它。——爱默生
2、我爱力量,我所爱的力量,一只蚂蚁所显示出来的可以和一只大象显示的相等。——司汤达
3、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万能的。——韦伯斯特
4、弓如果永远不张,便会失去它的力量。——奥维德
5、我们征服了力量,于是我们便得到了力量。——爱献生
语言建构与运用(任务二)
初读诗歌,音韵美
1. 音韵美
运用十字方法,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准确恰当地运用朗读十字方法“快慢、停连、高低、长短、轻重”,掌握诗歌节奏,在前后四人组成的小组内读。
2.题目内涵
《峨日朵雪峰之侧》“峨日朵”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峨堡镇老百姓对“峨堡”一词的口语发音。当地的一座或几座小山峰都可以被称为“峨日朵雪峰”。作者在登峰的过程,和雪峰是对视平视的。
艺术手法
(1)比喻: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形象地表现了征服过程中的凶险;指关节像铆钉,则彰显作者作为征服者的力量、坚强、不屈服的意志。
(2)视听结合:太阳是视觉,太阳决然地跃入一片山海,让读者感受到太阳勇敢而又有力量,异常壮丽的视觉画面;石砾滑坡是听觉,一块石头的下落引发一次更多的石头下落,地震一般,发起巨大的声响,像军队的喊杀声,让读者听到不寒而栗,对凶险充满恐惧。
(3)对比:太阳跃入山海,从高处往下的运动轨迹;石砾滑坡一个从上向下迅速滚落的过程。两者都是向下的运动轨迹,向下的力量,均属自然之力,难以阻挡。和征服者攀登不断向上的生命力量,形成了对抗。在这组对抗和较量中,让读者感受到征服者的强大,内心深处的无比坚毅。
作者脑海中虚构出自己渴望为伴的是雄鹰和雪豹,和现实眼前的蜘蛛形成对比。一个强大,一个弱小,一个高贵,一个卑微。对比之中,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界中万物有灵,每一种生命不管多么渺小,都有坚强的生命力。蜘蛛默享自然的恩赐,作为一种生命平等的彰显。
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所有的生命一样拥有平等机会。生命的短长,不能决定生命的弱强,不能决定谁的生命力更强大,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是勇敢积极地征服,还是被动地接受挑战是自己的选择。但前者都是强者,不断去追求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度,生命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强大力量。征服过后,默享自然的快慰,才是人生一大乐事。
悟读课文,内涵美
这首诗写作的年代是1962年。昌耀因被打成右派,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个文化人,变成了一个体力劳动者,被剥夺了读书写作的权利。他的生命遭遇困境,正如诗歌中征服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一样,但是他仍然要不断突破,征服,彰显顽强的生命力。
细读课文,意象美
太阳、石砾、罅隙、崖壁、雄鹰、雪豹,意象壮丽、高大,让读者看到征服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蜘蛛,意象弱小、卑微,让读者看到作者对生命力,生命的平等的赞颂。
思维提升与发展(任务三)
精读品味
1.诗中写了哪些意象?
意象:太阳、滑坡、石砾、雄鹰、雪豹、蜘蛛。
2.?为什么要描绘这些意象?
点拨:心象(情)+物象(美)=诗。
落日的动势和石砾滑坡的动势都是下坠的,而“我”作为攀登者的动势却正好相反,努力向上;那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也在竭力使我下坠。由此可见,日落和滑坡等意象是用来表现贴身绝壁的登山勇士的生命体验的。
“雄鹰”“雪豹”的形象是作者理想中的精神、意志和心灵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真正强大、雄壮和坚韧。“蜘蛛”则是作者现实状态的写照,是他“囚徒”身份的一种反映。
3.?描绘画面的时候采用了哪些表现方法?
视听合一:视觉——“我”吃惊地看到一派壮丽的雪峰落日景象;听觉形象——滑坡的石砾引动深渊的嚣鸣,如军旅的杀声渐远而去。视听合一,表明“我“在这个高度上的坚持决非易事。
特写镜头:一只小小的蜘蛛在岩壁上与“我“同在!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力的赞颂,就是从这只小小的蜘蛛表露出来的。很多时候,不起眼的细小意象比司空见惯的“波澜壮阔“更有力量。
强烈的对比:两组意象形成鲜明而浓烈的对比:强大和弱小、光明与幽暗、热闹与沉寂、高拔与低矮。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坚守住高度的不是强大的雄鹰或雪豹,而是弱小得可怜的蜘蛛;光明的太阳不过是虚妄的神明和幻象的真理的别称,堆砌的石砾不过是狂热的信念、迷信的追求、廉价的乐观的代号,而它们正在跃入幽暗却引力无穷的山海,正在滑向棕色的深渊;一派嚣鸣的、象军旅的喊杀声的,原来是在“滑坡”,是在“远去”,而接纳和归结它们的恰恰是沉寂和冷静。
4.小结:
在这首诗中,诗人为我们塑造了众多审美意象,有太阳、俄日朵之雪、巨石、岩壁、蜘蛛,它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凝重壮美的氛围,将饱含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高原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通过意象之间的的变化与相互作用,描绘出诗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乌托邦,那是一个仅存于诗人心中的天堂。
拓读明理
1.诗人李以亮曾这样点评《峨日朵雪峰之侧》这首诗:一首孤绝的超越之诗。那么你认为这首诗表现的是孤绝之境的超越还是超越之后落入的孤绝?
这首诗表现的是孤绝之境的超越:昌耀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自始自终有着一种震动人心的忧郁和伤感,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诗人对生命本真与尊严的追寻和捍卫。在这首诗中诗人似乎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又似乎是一个积极的生命体验者,他在这首诗中开始他的征服之旅,继而完成旅途,继而完成了自我超越。
联系写作背景,昌耀并没有与那个时代一同“滑坡”,而是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占稳了自己的高度。这是生命意志和生命强力的伟岸展示,呈示在这种高度的生命必定是强健和雄壮者的生命,定格在这种险峰的姿态必定是胜利者的姿态!
结束语:人生的苦难和挫折,实在是对人生的一种造就,战胜挫折和苦难就会赢得财富。今天我们领悟了昌耀的人生体验,明天我们也要像他那样用自己的顽强意志去直面挫折,即使身处孤绝之境,也要笑对人生,走向成功的彼岸!??
审美鉴赏与创造(任务四)
崇高与渺小的瞬间碰撞:《峨日朵雪峰之侧》的诗意所在
诗歌开头极力描绘的是一副壮观激烈的图画:原来近乎静止的太阳,一下子跃入一片山海之中。其中“彷徨许久”与“决然跃入”形成一个明显动与静的强烈反差。而这个决然跃入的姿势是如此轰轰烈烈,以至于惊动了峭壁上石砾,这无疑有着王维“月出惊山鸟”之静动艺术的魅力:王维的动态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万物皆空的静谧,而诗人借此表达的则是这个无声动作里所蕴藏的巨大震撼。
“棕色深渊自下而上的一派嚣鸣”一句中,棕色不全是对落日的描绘,其中传达的是诗人热血沸汤的激烈情怀。这个词既有现代派诗歌无限夸张自我感觉的特征,也有着古典诗歌善于捕捉诗人最幽微心绪的魅力:当年李贺“塞上胭脂凝夜紫”中的紫色,不也是渲染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与肃穆吗?
诗人并不满足于“棕色”一词的静态和内敛,在视觉之上再接一“嚣鸣”,从听觉的角度进一步渲染,而且不满足于“嚣鸣”这样有点空洞的夸张之词,干脆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极具立体感的句子:“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一股杀气腾腾的气势扑面而来。
耐人寻味的是,落日、石砾滑落、喊杀声远去,这些都是写下降的壮观激烈,而与之形成激烈反差的是攀登者的一路向上的。下降之势越是激荡,则上升越是艰难,攀登者的行为越是悲壮。于是,“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铆钉一样的是诗人越挫愈勇的坚强意志,血液的出现则是对诗人迎难而上行为赋予了一种悲壮的色彩。
正是在这一含义的背景下,才会深刻领会诗歌首句“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在看似自谦的语气里,包含的是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一份并不满足眼前而对未来更大的艰难也毫不畏惧的自信与钢铁意志。这也正是诗人以雄鹰或雪豹自许的原因和写照。
正当我们为诗人的悲壮、傲岸和激越所感染,诗人却突然将视线转向了岩壁上一只小小的蜘蛛: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崇高感突然与渺小激烈碰撞:这瞬间让我们从狂放的喜悦中跌落于尘埃之中。每一个读者都会在此刻发出震颤,这震颤来自心灵,来自现实,也来自锈蚀的沧桑历史。诗人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万物齐一、众生平等?还是小蜘蛛比高飞的雄鹰更懂得体味生命的真谛?抑或是雄鹰的虚妄而小蜘蛛的真实?也许都有。起码“锈蚀”一词让我们感觉到了诗人此刻心底涌上的历史的厚度。也许关于梦想与历史,正是诗人想告诉我们的。只是,诗人并不肯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而这,无疑留给了我们更大的联想空间。
在整首诗里,不但雄鹰与小蜘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落日的威势与攀登者艰难跋涉更是一个更具张力的对比。落日之势越是强大,攀登者的行为越显得艰难和悲壮。而当攀登者有足够的高度俯视时,这正是哲人所谓主体战胜对立物而生的超越感、一种基于痛而生的愉悦和心灵获得自由的畅然。
好的诗歌总是呈现而不把话说透,这正是严羽所谓“不落言荃”意,也是诗歌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任务五)
昌耀的魅力——读《昌耀抒情诗集》印象
昌耀的魅力对于今天的诗坛,我想正如昌耀自己的一首诗中的第一句所说的那样: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是一种植物所盛开的真实灵性的花朵。而这朵奇葩,是大家都应该能够看到,却形容不出的一种魂;而这种魂,我称之为昌耀的魅力。
这本抒情诗集的封面,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演奏时的雕塑。雕塑的提琴家紧闭双目,正在拉琴,浑身肌肉似乎与奏出的旋律一起颤动。我猜想这恐怕就是作为诗人的昌耀,对艺术家或对诗人理想的化身了。读昌耀的诗,我就有这样全神贯注的感觉,感觉昌耀执著地迷醉于内心深处使其不能平静而随之颤动的旋律境界,本该大喘气、大吼叫、大渲染的感情,到了他的笔下,便变成了短小而沉重、冷静而透明、鲜明而形象的诗章。尤其是他对西部荒原境界的拓创,纳豪放的边塞于宁静的石头之中,写一种亘古的宁静,写到了使读者要叫喊的地步。而他的诗却不叫,他创造了一个要你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就有了逼近读者的效果,使读者于不自觉中将这种效果与原来的那种感觉进行对比,就于宁静之中创造出了间离的效果,一种你读后印象极深情感极为浓缩,却说不出所以然而几近焦急。
他的诗句,一句句都仿佛是一块生铁掰断后露出的黎明色,有灿灿亮的茸茸气息在缭绕。在我看来,这是诗人把握诗的火候的最佳状态的体现,你读这本诗集中的任何一首诗,你都会发现一瞬一瞬的感觉的时间空间,在他所表达的事物与情感中弥漫,而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生命的灵性。
在这本主要抒写中国西部的抒情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昌耀在努力去做的是怎样的工作:在他的笔下,西部不是孤立的而是上接天下连地;不是吼叫的而是宁静的粗犷的同时又是极为细微的;西部是一种放射状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的境界;是时装的节奏、一百头雄牛、冷太阳等等、等等组构的奔放的诗的谷粒。昌耀的诗的技巧都在为表达他对西部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而努力,表现出了大诗人的灵魂境界的宽阔与深刻。如集中的组诗《青藏高原的形体》(六首)、《天籁》、《旷原之野》、《去格尔木之路》、《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如果你联系起来去品读昌耀诗中的西部,便不难发现诗人对西部的感情之宏阔之冷静之呈示的爆发力之强大而直入人心。他在诗中写道:
看我旷原之野!
我的热情是我古堡前金鼓的热情。
我之啸傲是我风中胡杨的啸傲。
我的娇媚是我红氍毹上婀娜旋舞者的娇媚。
我的心跳
是我追求者怦怦的心跳。
将我全部物化为他物,而所有他物均是西部的人和物。昌耀似乎于西部再生了。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决无半分夸饰的成分,读读集中另外一首长诗《慈航》,你便能理解昌耀,便能发现一位诗人的高贵的感情。他用诗说:“我不能理解遗忘。/也不能习惯麻木。”“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是怎样的一部情书呢?“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在这首诗中,他写出了爱的被爱的离异的永居的庞大的痛苦境界,并使这个境界弥沸着青海高原的宗教的神秘意味,和人的深刻的感情极致——对被造化所雕刻的这块土地与生命的依依深情,透出了诗人坚定刚强的爱的理想、爱的不断繁衍者的不竭的创造力和再生的微笑。如果说昌耀的关于西部的诗呈示了昌耀对西部整体感觉的艺术把握和创造,那么这首长诗便可看作昌耀全部诗集的生命之核。
其实,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昌耀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写出过许多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优秀诗作而鹤立鸡群。如集中可见到的《鹰.雪.牧人》《高车》《风景》《水手长——渡船——我们》等等,显示出了青年昌耀作为诗人的灼灼才华和宁静的天赋。如五行小诗《晨兴:走向土地与牛》:“劳动者/无梦的睡眠是美好的。/富有好梦的劳动者的睡眠不亦同样美好?”“但从睡眠中醒来了的劳动者自己更美好。/走向土地与牛的那个早起的劳动者更美好。”这个短章每一句都捕捉到了一个美好的感觉形象,如果你要去仔细寻思一下便能发现昌耀的早期诗作里,就有一股大家的目光,一颗亲近与理解自然与人的神秘关系的诗心。虽然他的诗至今也没有摆脱散文化的倾向,但如果完全弃绝叙事的非诗成份,那么抒情诗的抒情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了。从这里考察昌耀坚持诗的抒情传统,我们便会发现昌耀是一位极其正派的传统诗人,他的诗所透出的审美倾向,也几乎皆源于传统,甚至接近古典。而唯其这样,他才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发出了奇特的光华。读完这本诗集你便会发现,昌耀对“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的现实的关注;对“杨柳叶儿青”的欣赏与玩味儿的目光;对西部边城新增添的24部灯的诞生而激动的赞美,等等。都表达了他极为健康的情感世界与决不虚妄的踏实沉稳的诗人品格。也正因为他是这种诗人,所以他敢于正视自身的所有的美感体验,深入到体验到的一点一滴的美的玄妙之中,并用诗呈示出美的空间感觉与时间印象。如集中的《美目》,开头一句就浓缩了无数人体验过而写不出的感觉形象“普天之下唯一血肉具足的神——是神!”接着他写道“没有童年,没有老年,永居成熟的妙龄期”。隔行,又是一句“瞬,那是诚实的飞翔。” 纯粹的诗的感觉的飞翔,怎能不令读者折服呢?这是昌耀诚实而又为美所动的心,经过艺术创造的飞翔后,更一展雄翅的飞翔。
我没有见过昌耀。但读完他的这本诗集之后,我觉得我是见过昌耀的,并被他深深吸引了。我以为昌耀的魅力在于:他不仅追求诗的深层诚实,同时也极尽全力地追求人的深层的诚实。是的,是诚实。就是到了下个世纪,诚实也是令人动容的。
昌耀!你的魅力是诚实的飞翔啊。
姓名:
11.《俄日朵雪峰之侧》
素养目标
1、理解重要句子的含义,把握诗歌内容,提升诗歌鉴赏水平。
2、理解诗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乌托邦理想,培养学生辩证思辨能力。
3、掌握诗人塑造的众多审美意象,感知它们共同营造出的凝重壮美的艺术氛围。
4、了解时代背景和作者思想情感的关系,理解诗人表现的饱含沧桑的情怀。
课文预习案(任务一)
一、作者介绍
王昌耀(1936~2000),笔名昌耀,湖南桃源人。1950年参军,1951年春赴朝鲜作战,其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身负重伤,从此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赴青海参加大西北开发。1957年因一首短诗被定为右派,遭受了二十余年的坎坷与磨难。1979年重返文坛,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荣誉主席,专业作家。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昌耀抒情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昌耀的诗》等。他被人誉为“他那一辈人中唯一可以被称作诗人的人”“最信赖的诗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
二、背景介绍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反右派斗争。这一运动后来被严重扩大化,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的确定为“右派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首诗写于1962年8月,作者因被打成右派,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俄日朵”是现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峨堡镇的老百姓对“俄堡”一词的口语发音,“俄日朵雪峰”便是峨堡乡境内的祁连山脉中一座或者几座小雪峰。它们原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诗人拿来作为诗中一个如画的诗作之远景而已。
三、资料链接
1、我们爱力量,但却很少考虑如何去显示它。——爱默生
2、我爱力量,我所爱的力量,一只蚂蚁所显示出来的可以和一只大象显示的相等。——司汤达
3、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万能的。——韦伯斯特
4、弓如果永远不张,便会失去它的力量。——奥维德
5、我们征服了力量,于是我们便得到了力量。——爱献生
语言建构与运用(任务二)
初读诗歌,音韵美
1. 音韵美
运用十字方法,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准确恰当地运用朗读十字方法“快慢、停连、高低、长短、轻重”,掌握诗歌节奏,在前后四人组成的小组内读。
2.题目内涵
《峨日朵雪峰之侧》“峨日朵”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峨堡镇老百姓对“峨堡”一词的口语发音。当地的一座或几座小山峰都可以被称为“峨日朵雪峰”。作者在登峰的过程,和雪峰是对视平视的。
艺术手法
(1)比喻: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形象地表现了征服过程中的凶险;指关节像铆钉,则彰显作者作为征服者的力量、坚强、不屈服的意志。
(2)视听结合:太阳是视觉,太阳决然地跃入一片山海,让读者感受到太阳勇敢而又有力量,异常壮丽的视觉画面;石砾滑坡是听觉,一块石头的下落引发一次更多的石头下落,地震一般,发起巨大的声响,像军队的喊杀声,让读者听到不寒而栗,对凶险充满恐惧。
(3)对比:太阳跃入山海,从高处往下的运动轨迹;石砾滑坡一个从上向下迅速滚落的过程。两者都是向下的运动轨迹,向下的力量,均属自然之力,难以阻挡。和征服者攀登不断向上的生命力量,形成了对抗。在这组对抗和较量中,让读者感受到征服者的强大,内心深处的无比坚毅。
作者脑海中虚构出自己渴望为伴的是雄鹰和雪豹,和现实眼前的蜘蛛形成对比。一个强大,一个弱小,一个高贵,一个卑微。对比之中,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界中万物有灵,每一种生命不管多么渺小,都有坚强的生命力。蜘蛛默享自然的恩赐,作为一种生命平等的彰显。
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所有的生命一样拥有平等机会。生命的短长,不能决定生命的弱强,不能决定谁的生命力更强大,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是勇敢积极地征服,还是被动地接受挑战是自己的选择。但前者都是强者,不断去追求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度,生命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强大力量。征服过后,默享自然的快慰,才是人生一大乐事。
悟读课文,内涵美
这首诗写作的年代是1962年。昌耀因被打成右派,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个文化人,变成了一个体力劳动者,被剥夺了读书写作的权利。他的生命遭遇困境,正如诗歌中征服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一样,但是他仍然要不断突破,征服,彰显顽强的生命力。
细读课文,意象美
太阳、石砾、罅隙、崖壁、雄鹰、雪豹,意象壮丽、高大,让读者看到征服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蜘蛛,意象弱小、卑微,让读者看到作者对生命力,生命的平等的赞颂。
思维提升与发展(任务三)
精读品味
1.诗中写了哪些意象?
意象:太阳、滑坡、石砾、雄鹰、雪豹、蜘蛛。
2.?为什么要描绘这些意象?
点拨:心象(情)+物象(美)=诗。
落日的动势和石砾滑坡的动势都是下坠的,而“我”作为攀登者的动势却正好相反,努力向上;那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也在竭力使我下坠。由此可见,日落和滑坡等意象是用来表现贴身绝壁的登山勇士的生命体验的。
“雄鹰”“雪豹”的形象是作者理想中的精神、意志和心灵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真正强大、雄壮和坚韧。“蜘蛛”则是作者现实状态的写照,是他“囚徒”身份的一种反映。
3.?描绘画面的时候采用了哪些表现方法?
视听合一:视觉——“我”吃惊地看到一派壮丽的雪峰落日景象;听觉形象——滑坡的石砾引动深渊的嚣鸣,如军旅的杀声渐远而去。视听合一,表明“我“在这个高度上的坚持决非易事。
特写镜头:一只小小的蜘蛛在岩壁上与“我“同在!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力的赞颂,就是从这只小小的蜘蛛表露出来的。很多时候,不起眼的细小意象比司空见惯的“波澜壮阔“更有力量。
强烈的对比:两组意象形成鲜明而浓烈的对比:强大和弱小、光明与幽暗、热闹与沉寂、高拔与低矮。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坚守住高度的不是强大的雄鹰或雪豹,而是弱小得可怜的蜘蛛;光明的太阳不过是虚妄的神明和幻象的真理的别称,堆砌的石砾不过是狂热的信念、迷信的追求、廉价的乐观的代号,而它们正在跃入幽暗却引力无穷的山海,正在滑向棕色的深渊;一派嚣鸣的、象军旅的喊杀声的,原来是在“滑坡”,是在“远去”,而接纳和归结它们的恰恰是沉寂和冷静。
4.小结:
在这首诗中,诗人为我们塑造了众多审美意象,有太阳、俄日朵之雪、巨石、岩壁、蜘蛛,它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凝重壮美的氛围,将饱含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高原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通过意象之间的的变化与相互作用,描绘出诗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乌托邦,那是一个仅存于诗人心中的天堂。
拓读明理
1.诗人李以亮曾这样点评《峨日朵雪峰之侧》这首诗:一首孤绝的超越之诗。那么你认为这首诗表现的是孤绝之境的超越还是超越之后落入的孤绝?
这首诗表现的是孤绝之境的超越:昌耀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自始自终有着一种震动人心的忧郁和伤感,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诗人对生命本真与尊严的追寻和捍卫。在这首诗中诗人似乎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又似乎是一个积极的生命体验者,他在这首诗中开始他的征服之旅,继而完成旅途,继而完成了自我超越。
联系写作背景,昌耀并没有与那个时代一同“滑坡”,而是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占稳了自己的高度。这是生命意志和生命强力的伟岸展示,呈示在这种高度的生命必定是强健和雄壮者的生命,定格在这种险峰的姿态必定是胜利者的姿态!
结束语:人生的苦难和挫折,实在是对人生的一种造就,战胜挫折和苦难就会赢得财富。今天我们领悟了昌耀的人生体验,明天我们也要像他那样用自己的顽强意志去直面挫折,即使身处孤绝之境,也要笑对人生,走向成功的彼岸!??
审美鉴赏与创造(任务四)
崇高与渺小的瞬间碰撞:《峨日朵雪峰之侧》的诗意所在
诗歌开头极力描绘的是一副壮观激烈的图画:原来近乎静止的太阳,一下子跃入一片山海之中。其中“彷徨许久”与“决然跃入”形成一个明显动与静的强烈反差。而这个决然跃入的姿势是如此轰轰烈烈,以至于惊动了峭壁上石砾,这无疑有着王维“月出惊山鸟”之静动艺术的魅力:王维的动态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万物皆空的静谧,而诗人借此表达的则是这个无声动作里所蕴藏的巨大震撼。
“棕色深渊自下而上的一派嚣鸣”一句中,棕色不全是对落日的描绘,其中传达的是诗人热血沸汤的激烈情怀。这个词既有现代派诗歌无限夸张自我感觉的特征,也有着古典诗歌善于捕捉诗人最幽微心绪的魅力:当年李贺“塞上胭脂凝夜紫”中的紫色,不也是渲染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与肃穆吗?
诗人并不满足于“棕色”一词的静态和内敛,在视觉之上再接一“嚣鸣”,从听觉的角度进一步渲染,而且不满足于“嚣鸣”这样有点空洞的夸张之词,干脆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极具立体感的句子:“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一股杀气腾腾的气势扑面而来。
耐人寻味的是,落日、石砾滑落、喊杀声远去,这些都是写下降的壮观激烈,而与之形成激烈反差的是攀登者的一路向上的。下降之势越是激荡,则上升越是艰难,攀登者的行为越是悲壮。于是,“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铆钉一样的是诗人越挫愈勇的坚强意志,血液的出现则是对诗人迎难而上行为赋予了一种悲壮的色彩。
正是在这一含义的背景下,才会深刻领会诗歌首句“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在看似自谦的语气里,包含的是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一份并不满足眼前而对未来更大的艰难也毫不畏惧的自信与钢铁意志。这也正是诗人以雄鹰或雪豹自许的原因和写照。
正当我们为诗人的悲壮、傲岸和激越所感染,诗人却突然将视线转向了岩壁上一只小小的蜘蛛: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
快慰。
崇高感突然与渺小激烈碰撞:这瞬间让我们从狂放的喜悦中跌落于尘埃之中。每一个读者都会在此刻发出震颤,这震颤来自心灵,来自现实,也来自锈蚀的沧桑历史。诗人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万物齐一、众生平等?还是小蜘蛛比高飞的雄鹰更懂得体味生命的真谛?抑或是雄鹰的虚妄而小蜘蛛的真实?也许都有。起码“锈蚀”一词让我们感觉到了诗人此刻心底涌上的历史的厚度。也许关于梦想与历史,正是诗人想告诉我们的。只是,诗人并不肯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而这,无疑留给了我们更大的联想空间。
在整首诗里,不但雄鹰与小蜘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落日的威势与攀登者艰难跋涉更是一个更具张力的对比。落日之势越是强大,攀登者的行为越显得艰难和悲壮。而当攀登者有足够的高度俯视时,这正是哲人所谓主体战胜对立物而生的超越感、一种基于痛而生的愉悦和心灵获得自由的畅然。
好的诗歌总是呈现而不把话说透,这正是严羽所谓“不落言荃”意,也是诗歌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任务五)
昌耀的魅力——读《昌耀抒情诗集》印象
昌耀的魅力对于今天的诗坛,我想正如昌耀自己的一首诗中的第一句所说的那样: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是一种植物所盛开的真实灵性的花朵。而这朵奇葩,是大家都应该能够看到,却形容不出的一种魂;而这种魂,我称之为昌耀的魅力。
这本抒情诗集的封面,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演奏时的雕塑。雕塑的提琴家紧闭双目,正在拉琴,浑身肌肉似乎与奏出的旋律一起颤动。我猜想这恐怕就是作为诗人的昌耀,对艺术家或对诗人理想的化身了。读昌耀的诗,我就有这样全神贯注的感觉,感觉昌耀执著地迷醉于内心深处使其不能平静而随之颤动的旋律境界,本该大喘气、大吼叫、大渲染的感情,到了他的笔下,便变成了短小而沉重、冷静而透明、鲜明而形象的诗章。尤其是他对西部荒原境界的拓创,纳豪放的边塞于宁静的石头之中,写一种亘古的宁静,写到了使读者要叫喊的地步。而他的诗却不叫,他创造了一个要你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就有了逼近读者的效果,使读者于不自觉中将这种效果与原来的那种感觉进行对比,就于宁静之中创造出了间离的效果,一种你读后印象极深情感极为浓缩,却说不出所以然而几近焦急。
他的诗句,一句句都仿佛是一块生铁掰断后露出的黎明色,有灿灿亮的茸茸气息在缭绕。在我看来,这是诗人把握诗的火候的最佳状态的体现,你读这本诗集中的任何一首诗,你都会发现一瞬一瞬的感觉的时间空间,在他所表达的事物与情感中弥漫,而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生命的灵性。
在这本主要抒写中国西部的抒情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昌耀在努力去做的是怎样的工作:在他的笔下,西部不是孤立的而是上接天下连地;不是吼叫的而是宁静的粗犷的同时又是极为细微的;西部是一种放射状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的境界;是时装的节奏、一百头雄牛、冷太阳等等、等等组构的奔放的诗的谷粒。昌耀的诗的技巧都在为表达他对西部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而努力,表现出了大诗人的灵魂境界的宽阔与深刻。如集中的组诗《青藏高原的形体》(六首)、《天籁》、《旷原之野》、《去格尔木之路》、《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如果你联系起来去品读昌耀诗中的西部,便不难发现诗人对西部的感情之宏阔之冷静之呈示的爆发力之强大而直入人心。他在诗中写道:
看我旷原之野!
我的热情是我古堡前金鼓的热情。
我之啸傲是我风中胡杨的啸傲。
我的娇媚是我红氍毹上婀娜旋舞者的娇媚。
我的心跳
是我追求者怦怦的心跳。
将我全部物化为他物,而所有他物均是西部的人和物。昌耀似乎于西部再生了。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决无半分夸饰的成分,读读集中另外一首长诗《慈航》,你便能理解昌耀,便能发现一位诗人的高贵的感情。他用诗说:“我不能理解遗忘。/也不能习惯麻木。”“我,就是这样一部行动的情书。”是怎样的一部情书呢?“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在这首诗中,他写出了爱的被爱的离异的永居的庞大的痛苦境界,并使这个境界弥沸着青海高原的宗教的神秘意味,和人的深刻的感情极致——对被造化所雕刻的这块土地与生命的依依深情,透出了诗人坚定刚强的爱的理想、爱的不断繁衍者的不竭的创造力和再生的微笑。如果说昌耀的关于西部的诗呈示了昌耀对西部整体感觉的艺术把握和创造,那么这首长诗便可看作昌耀全部诗集的生命之核。
其实,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昌耀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写出过许多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优秀诗作而鹤立鸡群。如集中可见到的《鹰.雪.牧人》《高车》《风景》《水手长——渡船——我们》等等,显示出了青年昌耀作为诗人的灼灼才华和宁静的天赋。如五行小诗《晨兴:走向土地与牛》:“劳动者/无梦的睡眠是美好的。/富有好梦的劳动者的睡眠不亦同样美好?”“但从睡眠中醒来了的劳动者自己更美好。/走向土地与牛的那个早起的劳动者更美好。”这个短章每一句都捕捉到了一个美好的感觉形象,如果你要去仔细寻思一下便能发现昌耀的早期诗作里,就有一股大家的目光,一颗亲近与理解自然与人的神秘关系的诗心。虽然他的诗至今也没有摆脱散文化的倾向,但如果完全弃绝叙事的非诗成份,那么抒情诗的抒情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了。从这里考察昌耀坚持诗的抒情传统,我们便会发现昌耀是一位极其正派的传统诗人,他的诗所透出的审美倾向,也几乎皆源于传统,甚至接近古典。而唯其这样,他才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发出了奇特的光华。读完这本诗集你便会发现,昌耀对“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的现实的关注;对“杨柳叶儿青”的欣赏与玩味儿的目光;对西部边城新增添的24部灯的诞生而激动的赞美,等等。都表达了他极为健康的情感世界与决不虚妄的踏实沉稳的诗人品格。也正因为他是这种诗人,所以他敢于正视自身的所有的美感体验,深入到体验到的一点一滴的美的玄妙之中,并用诗呈示出美的空间感觉与时间印象。如集中的《美目》,开头一句就浓缩了无数人体验过而写不出的感觉形象“普天之下唯一血肉具足的神——是神!”接着他写道“没有童年,没有老年,永居成熟的妙龄期”。隔行,又是一句“瞬,那是诚实的飞翔。” 纯粹的诗的感觉的飞翔,怎能不令读者折服呢?这是昌耀诚实而又为美所动的心,经过艺术创造的飞翔后,更一展雄翅的飞翔。
我没有见过昌耀。但读完他的这本诗集之后,我觉得我是见过昌耀的,并被他深深吸引了。我以为昌耀的魅力在于:他不仅追求诗的深层诚实,同时也极尽全力地追求人的深层的诚实。是的,是诚实。就是到了下个世纪,诚实也是令人动容的。
昌耀!你的魅力是诚实的飞翔啊。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 沁园春 长沙
- 2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红烛 *峨日朵雪峰之侧 *致云雀)
- 3 (百合花 *哦,香雪)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二单元
- 4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探界者”
- 5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 6 (芣苢 插秧歌)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三单元
- 7(短歌行 *归园田居(其一))
- 8(梦游天姥吟留别 登高 *琵琶行并序)
- 9(念奴娇·赤壁怀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声声慢(寻寻觅觅))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
- 学习活动
-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
- 《乡土中国》
- 第六单元
- 10(劝学 *师说)
- 11 反对党八股(节选)
- 12 拿来主义
- 13(*读书:目的和前提 *上图书馆)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七单元
- 14(故都的秋 *荷塘月色)
- 15 我与地坛(节选)
- 16(赤壁赋 *登泰山记)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八单元
- 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
- 古诗词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