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山坡羊骊山怀古》《朝天子咏喇叭》课件(共19张幻灯片)
文档属性
| 名称 | 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山坡羊骊山怀古》《朝天子咏喇叭》课件(共19张幻灯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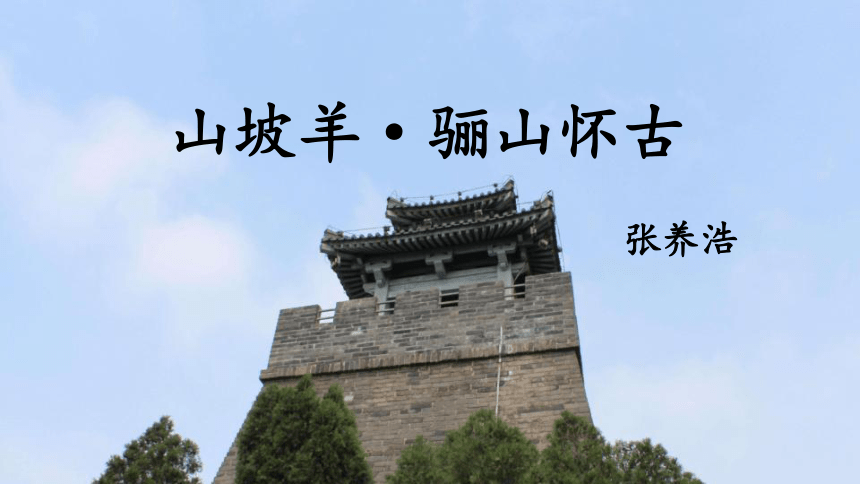
|
|
| 格式 | pptx | ||
| 文件大小 | 214.8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0-11-08 21:07:28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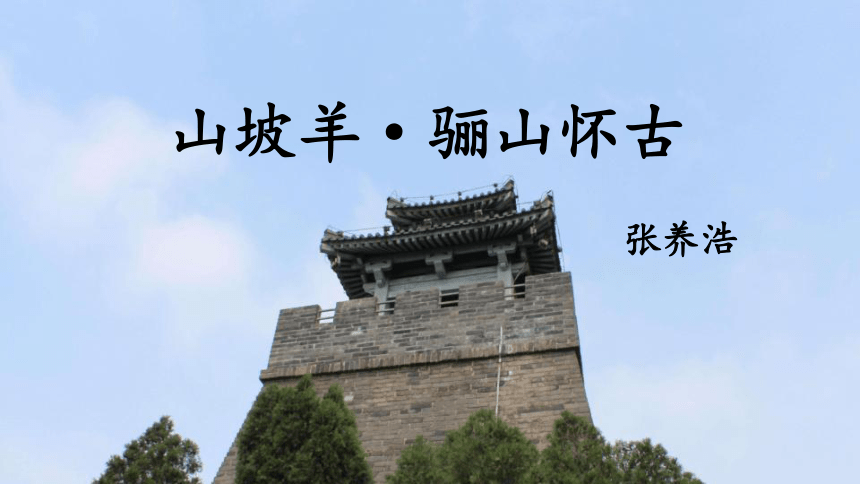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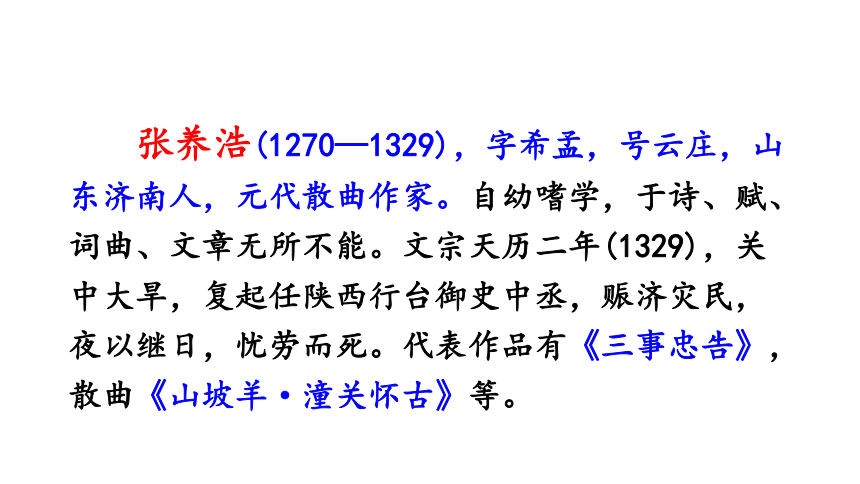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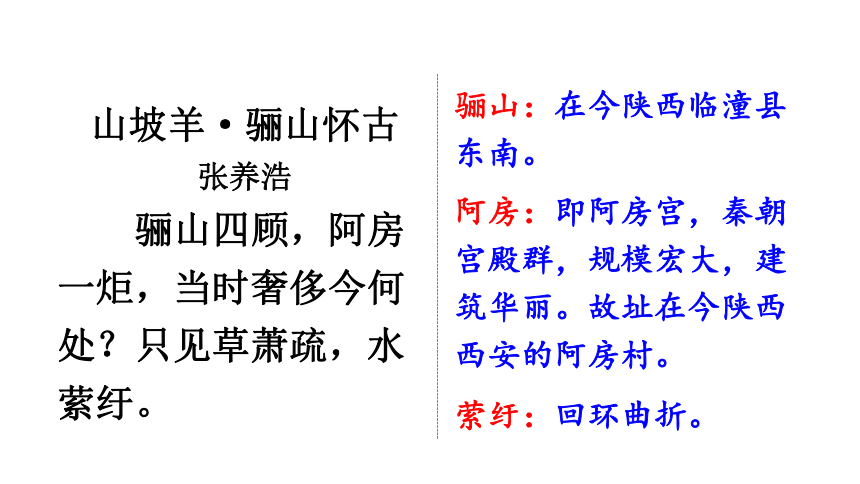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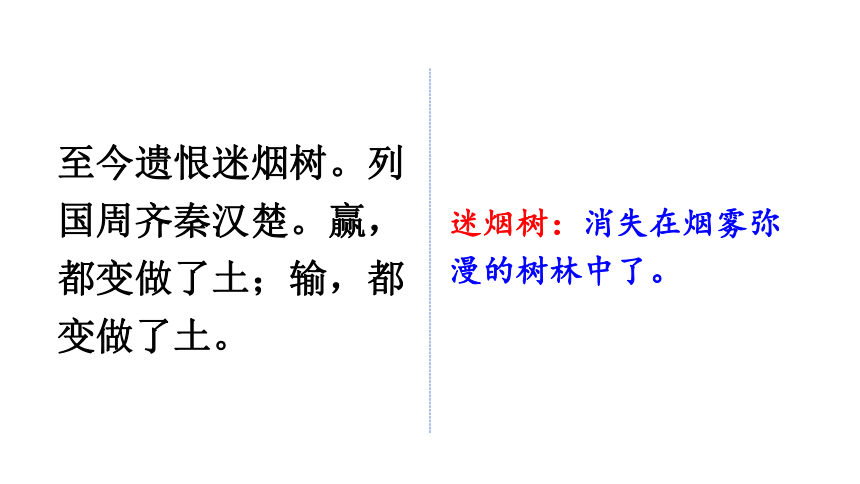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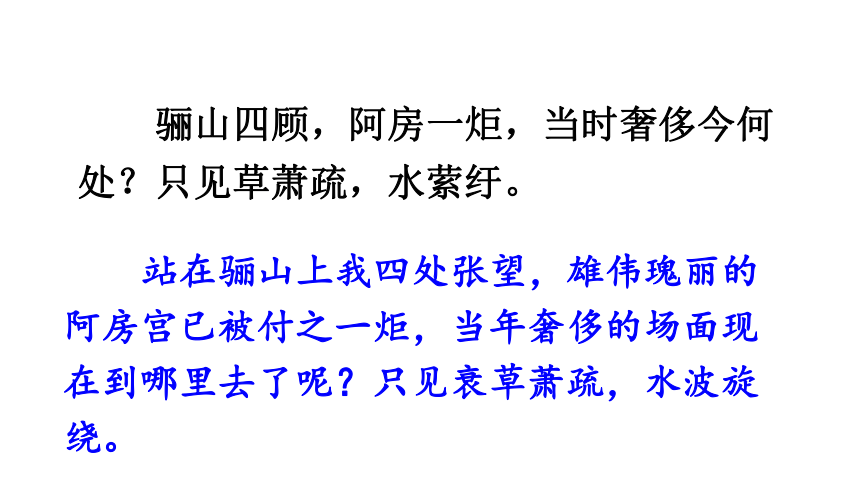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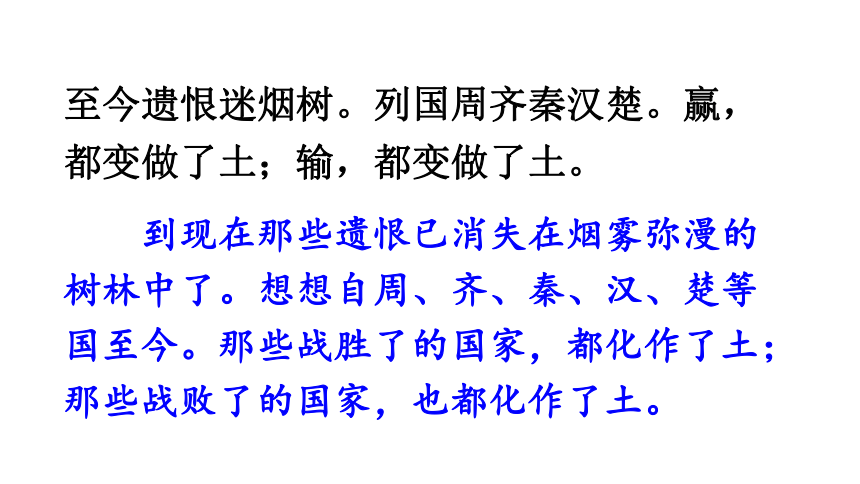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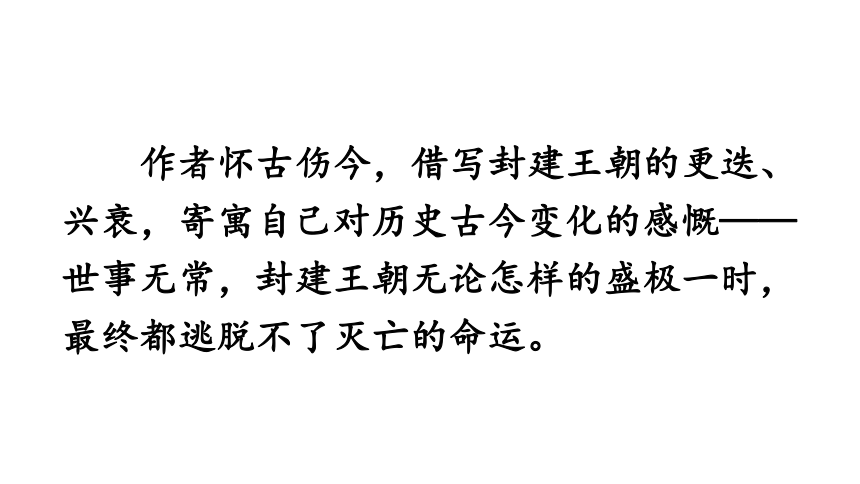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山坡羊·骊山怀古
张养浩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元代散曲作家。自幼嗜学,于诗、赋、词曲、文章无所不能。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复起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赈济灾民,夜以继日,忧劳而死。代表作品有《三事忠告》,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等。
山坡羊·骊山怀古
张养浩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
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阿房:即阿房宫,秦朝宫殿群,规模宏大,建筑华丽。故址在今陕西西安的阿房村。
萦纡:回环曲折。
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迷烟树:消失在烟雾弥漫的树林中了。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
站在骊山上我四处张望,雄伟瑰丽的阿房宫已被付之一炬,当年奢侈的场面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只见衰草萧疏,水波旋绕。
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到现在那些遗恨已消失在烟雾弥漫的树林中了。想想自周、齐、秦、汉、楚等国至今。那些战胜了的国家,都化作了土;那些战败了的国家,也都化作了土。
作者怀古伤今,借写封建王朝的更迭、兴衰,寄寓自己对历史古今变化的感慨——世事无常,封建王朝无论怎样的盛极一时,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这首曲子开头三句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是说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早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最有一句阐明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灭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规律的概括。
朝天子·咏喇叭
王 磐
王磐(约1470—1530),明代散曲家,字鸿渐,号西楼,江苏高邮人。从年轻时起即鄙视功名,筑楼高邮城西,与名流谈咏其间,因自号西楼。其散曲题材广泛,虽多闲适之作,亦有同情人民疾苦、讥讽时政的佳作。有《王西楼乐府》。
朝天子·咏喇叭
王 磐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
仗:倚仗,凭借。
官船:官府的船。这里指扰民的宦官船只。
声价:名誉身价。
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共:和。
水尽鹅飞罢:水干了,鹅也飞光了。比喻民穷财尽。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
喇叭唢呐呜呜哇哇,曲子短小,声音响亮。官府的船来往乱如麻,全凭你来抬高名誉身价。
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军人听了军人发愁,百姓听了百姓害怕。还能到哪里去分真和假?眼睁睁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江水枯竭鹅也飞光了!
本曲表面上吟咏喇叭和唢呐,实则借物咏怀,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大摆威风、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的憎恶之情。
这首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一“小”一“大”的对比中,也流露出作者的爱憎之情。一个“腔”字,道出了喇叭和宦官的共同特征,把那些贪官污吏的丑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
“抬”,就说明喇叭、唢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宦官装腔作势,声价全靠喇叭来抬,矛头指向其狐假虎威的嘴脸。小令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通篇咏喇叭咏得真切,让人信服。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有着强烈的感彩,传达了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涵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究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张养浩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元代散曲作家。自幼嗜学,于诗、赋、词曲、文章无所不能。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复起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赈济灾民,夜以继日,忧劳而死。代表作品有《三事忠告》,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等。
山坡羊·骊山怀古
张养浩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
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阿房:即阿房宫,秦朝宫殿群,规模宏大,建筑华丽。故址在今陕西西安的阿房村。
萦纡:回环曲折。
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迷烟树:消失在烟雾弥漫的树林中了。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
站在骊山上我四处张望,雄伟瑰丽的阿房宫已被付之一炬,当年奢侈的场面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只见衰草萧疏,水波旋绕。
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到现在那些遗恨已消失在烟雾弥漫的树林中了。想想自周、齐、秦、汉、楚等国至今。那些战胜了的国家,都化作了土;那些战败了的国家,也都化作了土。
作者怀古伤今,借写封建王朝的更迭、兴衰,寄寓自己对历史古今变化的感慨——世事无常,封建王朝无论怎样的盛极一时,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这首曲子开头三句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是说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早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最有一句阐明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灭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规律的概括。
朝天子·咏喇叭
王 磐
王磐(约1470—1530),明代散曲家,字鸿渐,号西楼,江苏高邮人。从年轻时起即鄙视功名,筑楼高邮城西,与名流谈咏其间,因自号西楼。其散曲题材广泛,虽多闲适之作,亦有同情人民疾苦、讥讽时政的佳作。有《王西楼乐府》。
朝天子·咏喇叭
王 磐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
仗:倚仗,凭借。
官船:官府的船。这里指扰民的宦官船只。
声价:名誉身价。
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共:和。
水尽鹅飞罢:水干了,鹅也飞光了。比喻民穷财尽。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
喇叭唢呐呜呜哇哇,曲子短小,声音响亮。官府的船来往乱如麻,全凭你来抬高名誉身价。
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军人听了军人发愁,百姓听了百姓害怕。还能到哪里去分真和假?眼睁睁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江水枯竭鹅也飞光了!
本曲表面上吟咏喇叭和唢呐,实则借物咏怀,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大摆威风、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的憎恶之情。
这首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一“小”一“大”的对比中,也流露出作者的爱憎之情。一个“腔”字,道出了喇叭和宦官的共同特征,把那些贪官污吏的丑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
“抬”,就说明喇叭、唢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宦官装腔作势,声价全靠喇叭来抬,矛头指向其狐假虎威的嘴脸。小令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通篇咏喇叭咏得真切,让人信服。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有着强烈的感彩,传达了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涵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究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 2* 梅岭三章
- 3* 短诗五首
- 4 海燕
- 写作 学习扩写
- 第二单元
- 5 孔乙己
- 6 变色龙
- 7* 溜索
- 8* 蒲柳人家(节选)
- 写作 审题立意
- 第三单元
- 9 鱼我所欲也
- 10* 唐雎不辱使命
- 11 送东阳马生序
- 12 词四首
- 写作 布局谋篇
- 名著导读 《儒林外史》:讽刺作品的阅读
- 课外古诗词诵读
- 第四单元
- 13 短文两篇
- 14 山水画的意境
- 15* 无言之美
- 16* 驱遣我们的想象
- 写作 修改润色
- 口语交际 辩论
- 第五单元
- 任务一 阅读与思考
- 17 屈原(节选)
- 18 天下第一楼(节选)
- 19 枣儿
- 任务二 准备与排练
- 任务三 演出与评议
- 第六单元
- 20 曹刿论战
- 21* 邹忌讽齐王纳谏
- 22* 陈涉世家
- 23 出师表
- 24 诗词曲五首
- 写作 有创意地表达
- 名著导读 《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 课外古诗词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