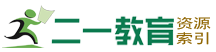浙江金华高三语文期末考试十校联考 PDF含答案
文档属性
| 名称 | 浙江金华高三语文期末考试十校联考 PDF含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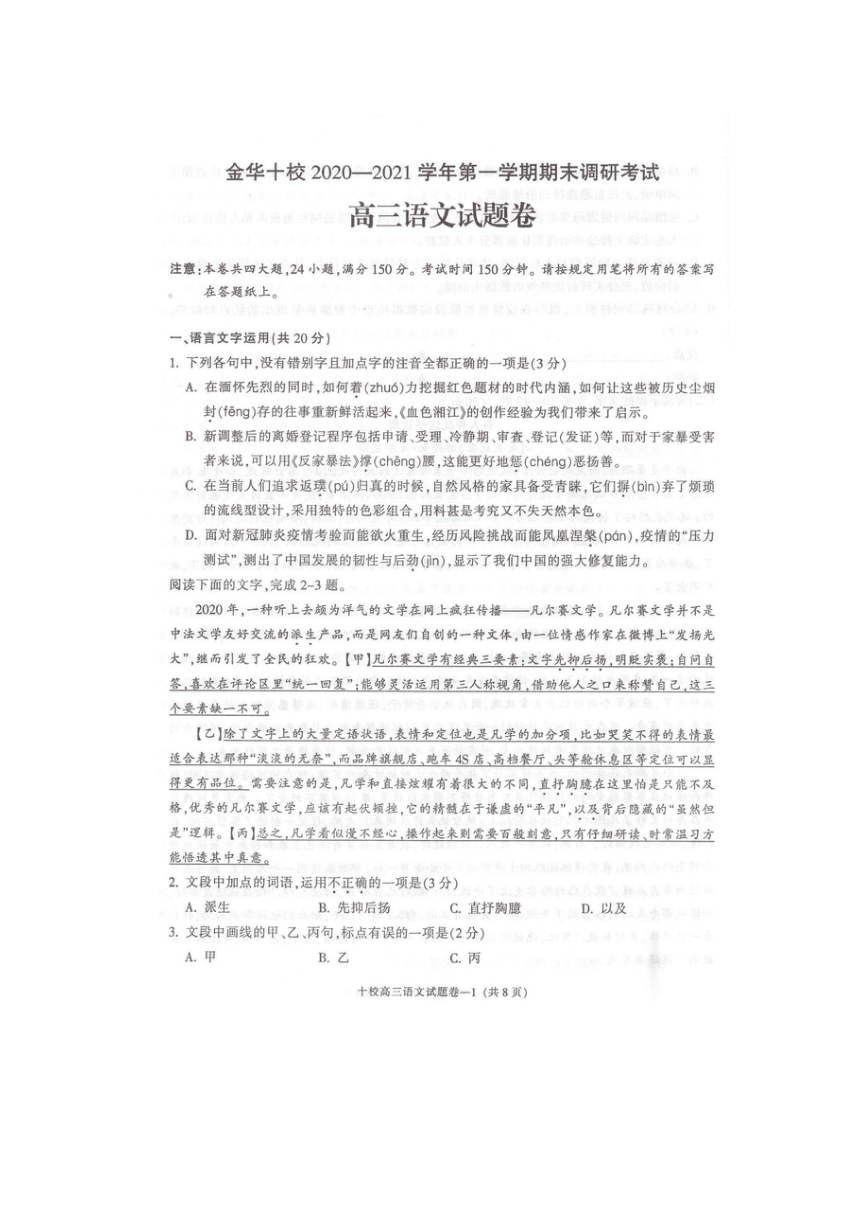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3.1M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人教版(新课程标准)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1-02-05 00:00:00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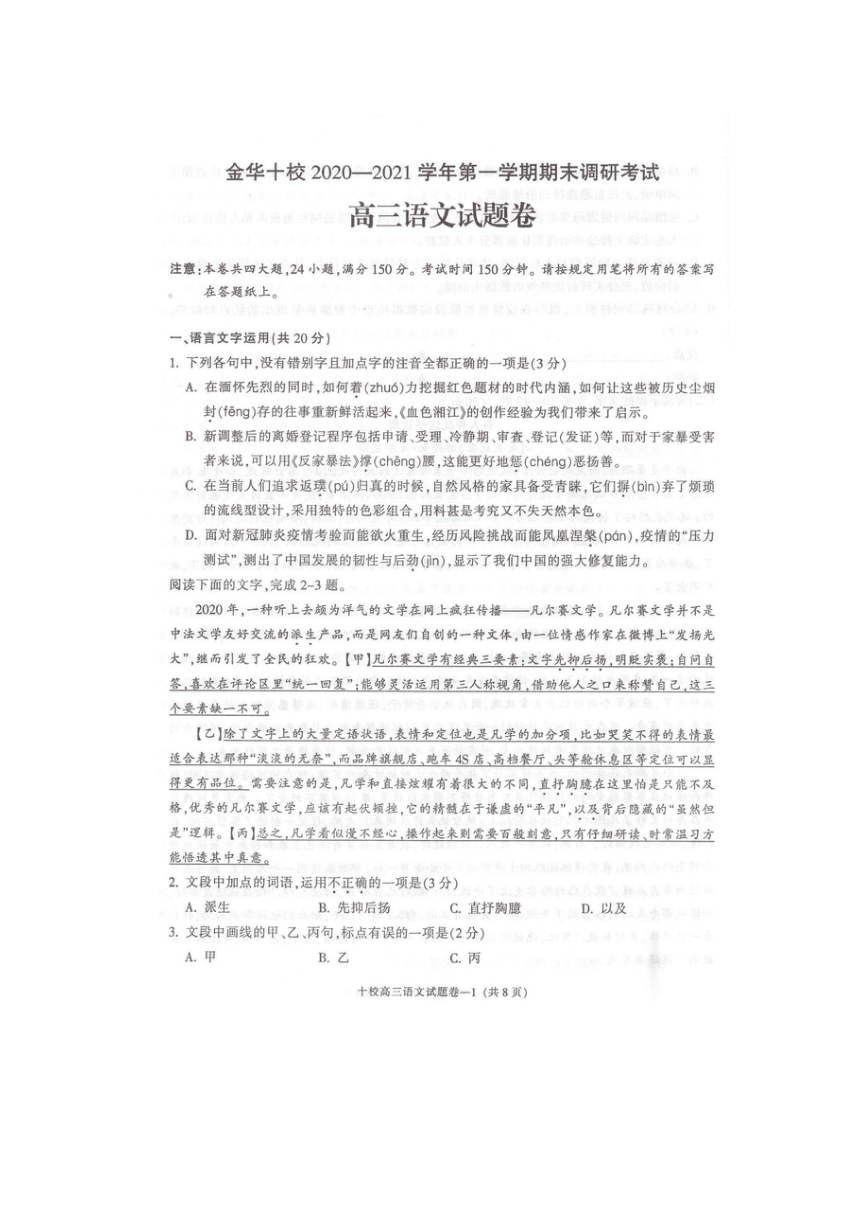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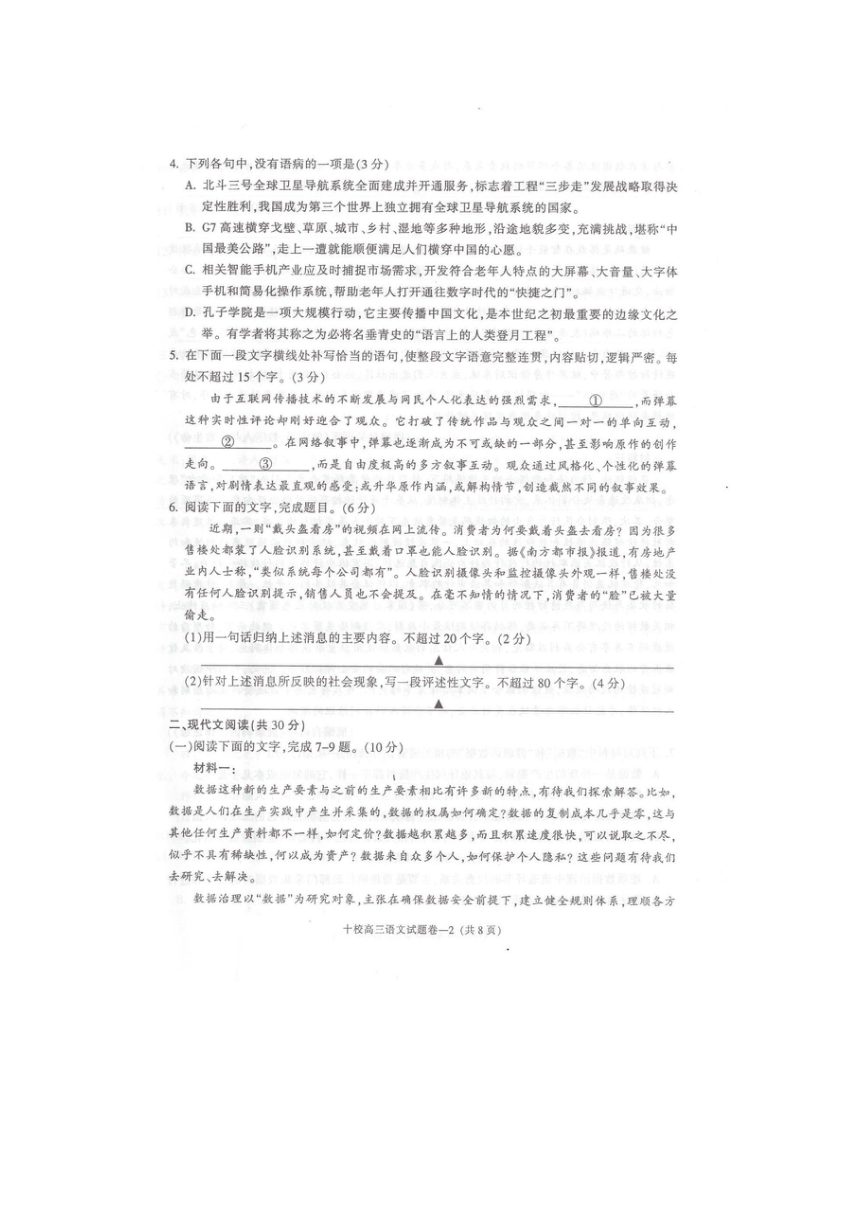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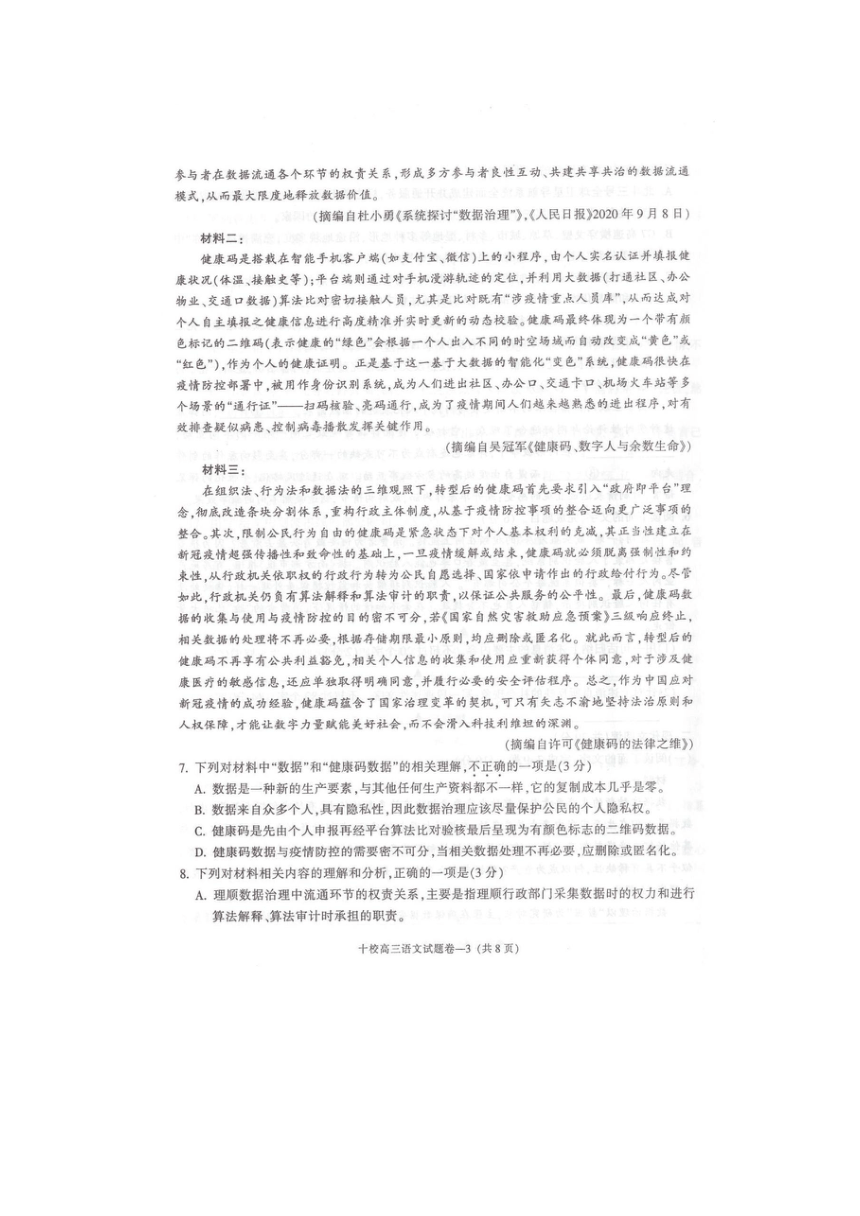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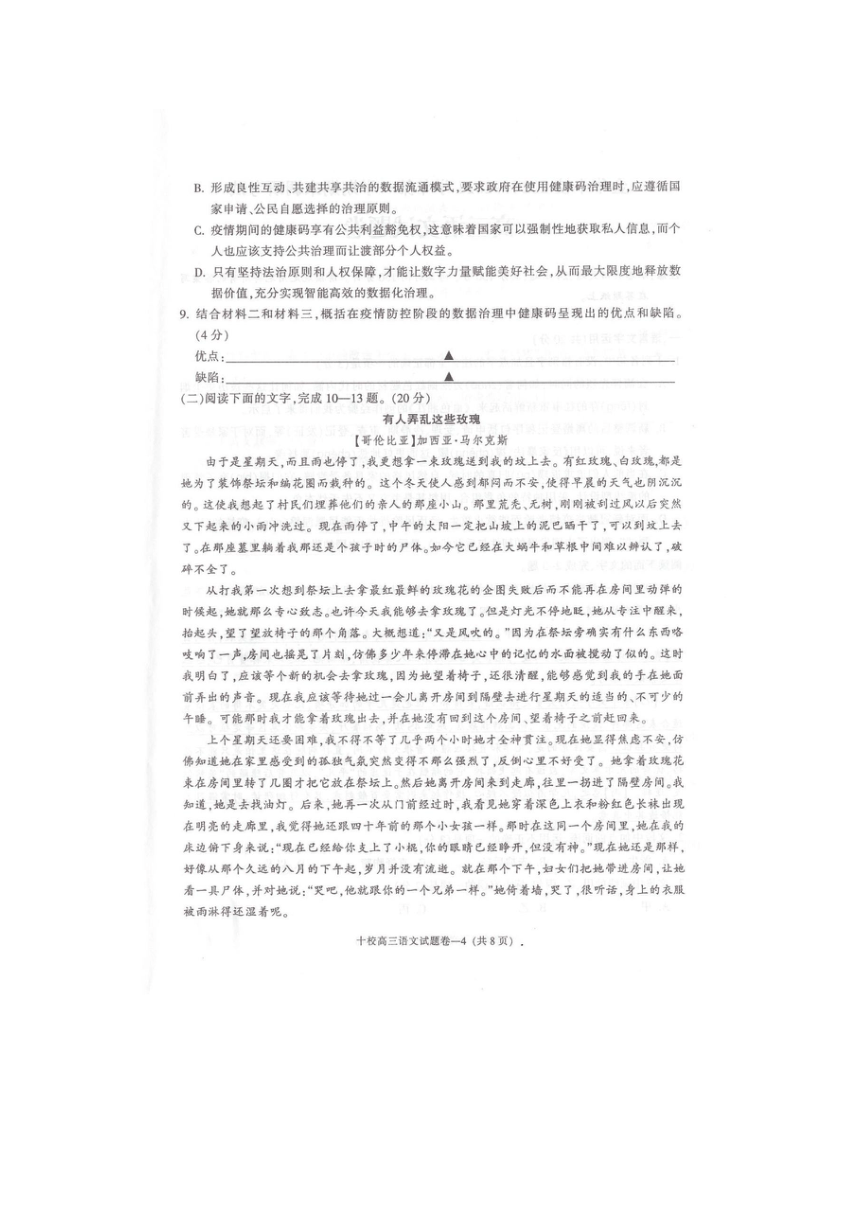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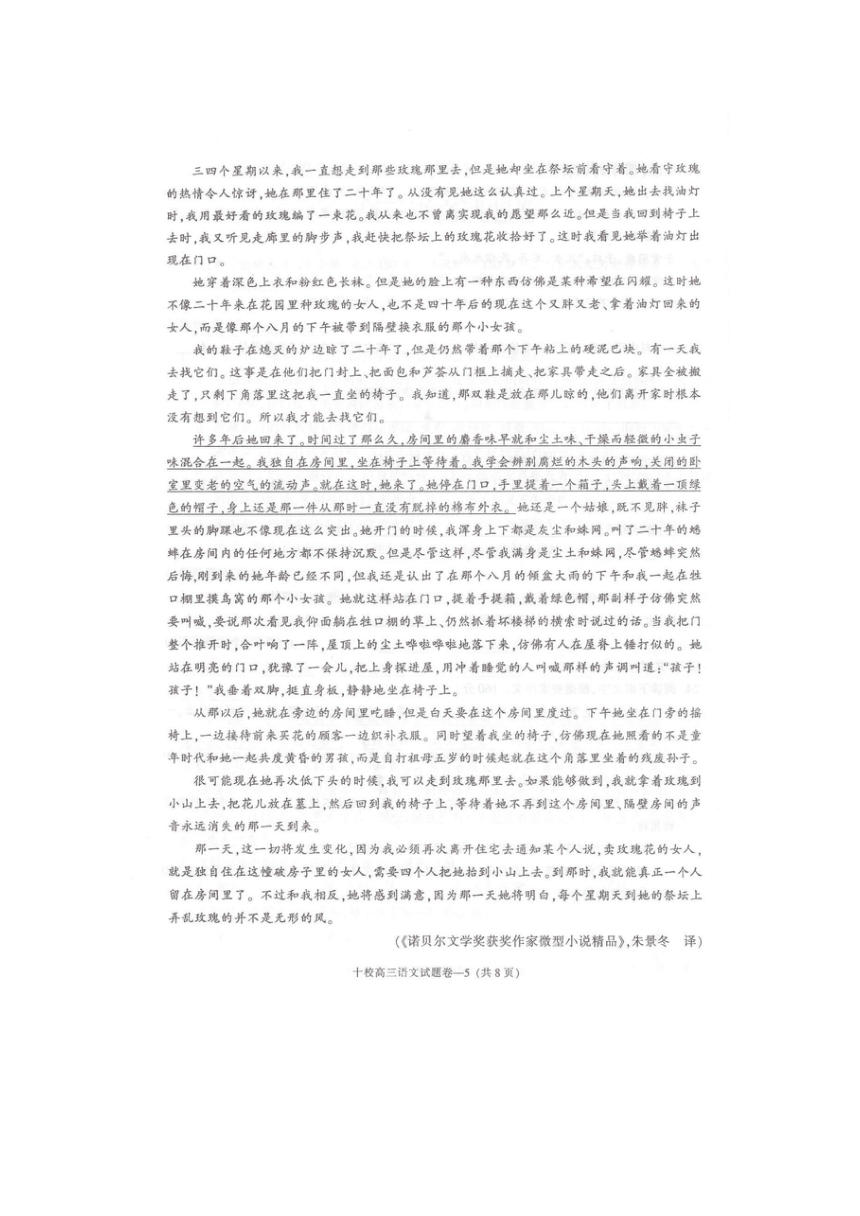
文档简介
三四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走到那些玫瑰那里去,但是她却坐在祭坛前看守着。她看守玫瑰
的热情令人惊讶,她在那里住了二十年了。从没有见她这么认真过。上个星期天,她出去找油灯
时,我用最好看的玫瑰编了一束花。我从来也不曾离实现我的愿望那么近。但是当我回到椅子上
去时,我又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我赶快把祭坛上的玫瑰花收拾好了。这时我看见她举着油灯出
现在门口
她穿着深色上衣和粉红色长袜。但是她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仿佛是某种希望在闪耀。这时她
不像二十年来在花园里种玫瑰的女人,也不是四十年后的现在这个又胖又老、拿着油灯回来的
女人,而是像那个八月的下午被带到隔壁换衣服的那个小女孩。
我的鞋子在熄灭的炉边晾了二十年了,但是仍然带着那个下午粘上的硬泥巴块。有一天我
去找它们。这事是在他们把门封上、把面包和芦荟从门框上摘走、把家具带走之后。家具全被搬
走了,只剩下角落里这把我一直坐的椅子。我知道,那双鞋是放在那儿晾的,他们离开家时根本
没有想到它们。所以我才能去找它们。
许多年后她回来了。时间过了那么久,房间里的麝香味早就和尘土味、千燥而轻微的小虫子
味混合在一起。我独自在房间里,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我学会辨别腐烂的木头的声响,关闭的卧
室里变老的空气的流动声。就在这时,她来了。她停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箱子,头上戴着一顶绿
色的帽子,身上还是那一件从那时一直没有脱梓的棉布外衣。她还是一个姑娘,既不见胖,袜子
里头的脚踝也不像现在这么突出。她开门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蛛网。叫了二十年的蟋
蟀在房间内的任何地方都不保持沉默。但是尽管这样,尽管我满身是尘土和蛛网,尽管蟋蟀突然
后悔,刚到来的她年龄已经不同,但我还是认出了在那个八月的倾盆大雨的下午和我一起在牲
口棚里摸鸟窝的那个小女孩。她就这样站在门口,提着手提箱,戴着绿色帽,那副样子仿佛突然
要叫喊,要说那次看见我仰面躺在牲口棚的草上、仍然抓着坏楼梯的横索时说过的话。当我把门
整个推开时,合叶响了一阵,屋顶上的尘土哗啦哗啦地落下来,仿佛有人在屋脊上锤打似的。她
站在明亮的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把上身探进屋,用冲着睡觉的人叫喊那样的声调叫道:“孩子!
孩子!”我垂着双脚,挺直身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从那以后,她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吃睡,但是白天要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下午她坐在门旁的摇
椅上,一边接待前来买花的顾客一边织补衣服。同时望着我坐的椅子,仿佛现在她照看的不是童
年时代和她一起共度黄昏的男孩,而是自打祖母五岁的时候起就在这个角落里坐着的残废孙子。
很可能现在她再次低下头的时候,我可以走到玫瑰那里去。如果能够做到,我就拿着玫瑰到
小山上去,把花儿放在墓上,然后回到我的椅子上,等待着她不再到这个房间里、隔壁房间的声
音永远消失的那一天到来。
那一天,这一切将发生变化,因为我必须再次离开住宅去通知某个人说,卖玫瑰花的女人,
就是独自住在这幢破房子里的女人,需要四个人把她抬到小山上去。到那时,我就能真正一个人
留在房间里了。不过和我相反,她将感到满意,因为那一天她将明白,每个星期天到她的祭坛上
弄乱玫瑰的并不是无形的风。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微型小说精品》,朱景冬译
十校高三语文试题卷—5(共8页)
的热情令人惊讶,她在那里住了二十年了。从没有见她这么认真过。上个星期天,她出去找油灯
时,我用最好看的玫瑰编了一束花。我从来也不曾离实现我的愿望那么近。但是当我回到椅子上
去时,我又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我赶快把祭坛上的玫瑰花收拾好了。这时我看见她举着油灯出
现在门口
她穿着深色上衣和粉红色长袜。但是她的脸上有一种东西仿佛是某种希望在闪耀。这时她
不像二十年来在花园里种玫瑰的女人,也不是四十年后的现在这个又胖又老、拿着油灯回来的
女人,而是像那个八月的下午被带到隔壁换衣服的那个小女孩。
我的鞋子在熄灭的炉边晾了二十年了,但是仍然带着那个下午粘上的硬泥巴块。有一天我
去找它们。这事是在他们把门封上、把面包和芦荟从门框上摘走、把家具带走之后。家具全被搬
走了,只剩下角落里这把我一直坐的椅子。我知道,那双鞋是放在那儿晾的,他们离开家时根本
没有想到它们。所以我才能去找它们。
许多年后她回来了。时间过了那么久,房间里的麝香味早就和尘土味、千燥而轻微的小虫子
味混合在一起。我独自在房间里,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我学会辨别腐烂的木头的声响,关闭的卧
室里变老的空气的流动声。就在这时,她来了。她停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箱子,头上戴着一顶绿
色的帽子,身上还是那一件从那时一直没有脱梓的棉布外衣。她还是一个姑娘,既不见胖,袜子
里头的脚踝也不像现在这么突出。她开门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蛛网。叫了二十年的蟋
蟀在房间内的任何地方都不保持沉默。但是尽管这样,尽管我满身是尘土和蛛网,尽管蟋蟀突然
后悔,刚到来的她年龄已经不同,但我还是认出了在那个八月的倾盆大雨的下午和我一起在牲
口棚里摸鸟窝的那个小女孩。她就这样站在门口,提着手提箱,戴着绿色帽,那副样子仿佛突然
要叫喊,要说那次看见我仰面躺在牲口棚的草上、仍然抓着坏楼梯的横索时说过的话。当我把门
整个推开时,合叶响了一阵,屋顶上的尘土哗啦哗啦地落下来,仿佛有人在屋脊上锤打似的。她
站在明亮的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把上身探进屋,用冲着睡觉的人叫喊那样的声调叫道:“孩子!
孩子!”我垂着双脚,挺直身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从那以后,她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吃睡,但是白天要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下午她坐在门旁的摇
椅上,一边接待前来买花的顾客一边织补衣服。同时望着我坐的椅子,仿佛现在她照看的不是童
年时代和她一起共度黄昏的男孩,而是自打祖母五岁的时候起就在这个角落里坐着的残废孙子。
很可能现在她再次低下头的时候,我可以走到玫瑰那里去。如果能够做到,我就拿着玫瑰到
小山上去,把花儿放在墓上,然后回到我的椅子上,等待着她不再到这个房间里、隔壁房间的声
音永远消失的那一天到来。
那一天,这一切将发生变化,因为我必须再次离开住宅去通知某个人说,卖玫瑰花的女人,
就是独自住在这幢破房子里的女人,需要四个人把她抬到小山上去。到那时,我就能真正一个人
留在房间里了。不过和我相反,她将感到满意,因为那一天她将明白,每个星期天到她的祭坛上
弄乱玫瑰的并不是无形的风。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微型小说精品》,朱景冬译
十校高三语文试题卷—5(共8页)
同课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