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学年高中语文统编版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峨日朵雪峰之侧》教学设计
文档属性
| 名称 | 2020-2021学年高中语文统编版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峨日朵雪峰之侧》教学设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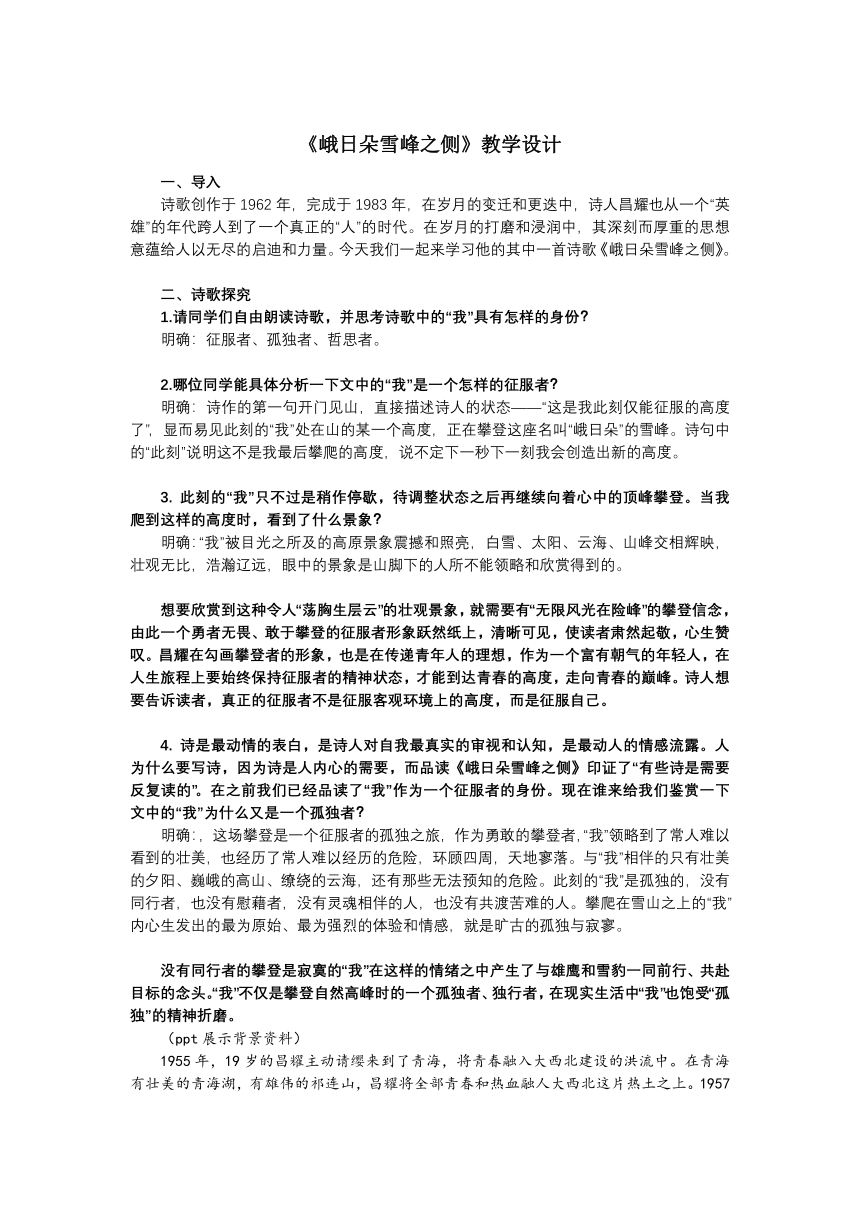 | |
| 格式 | docx | ||
| 文件大小 | 19.5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1-05-08 22:01:19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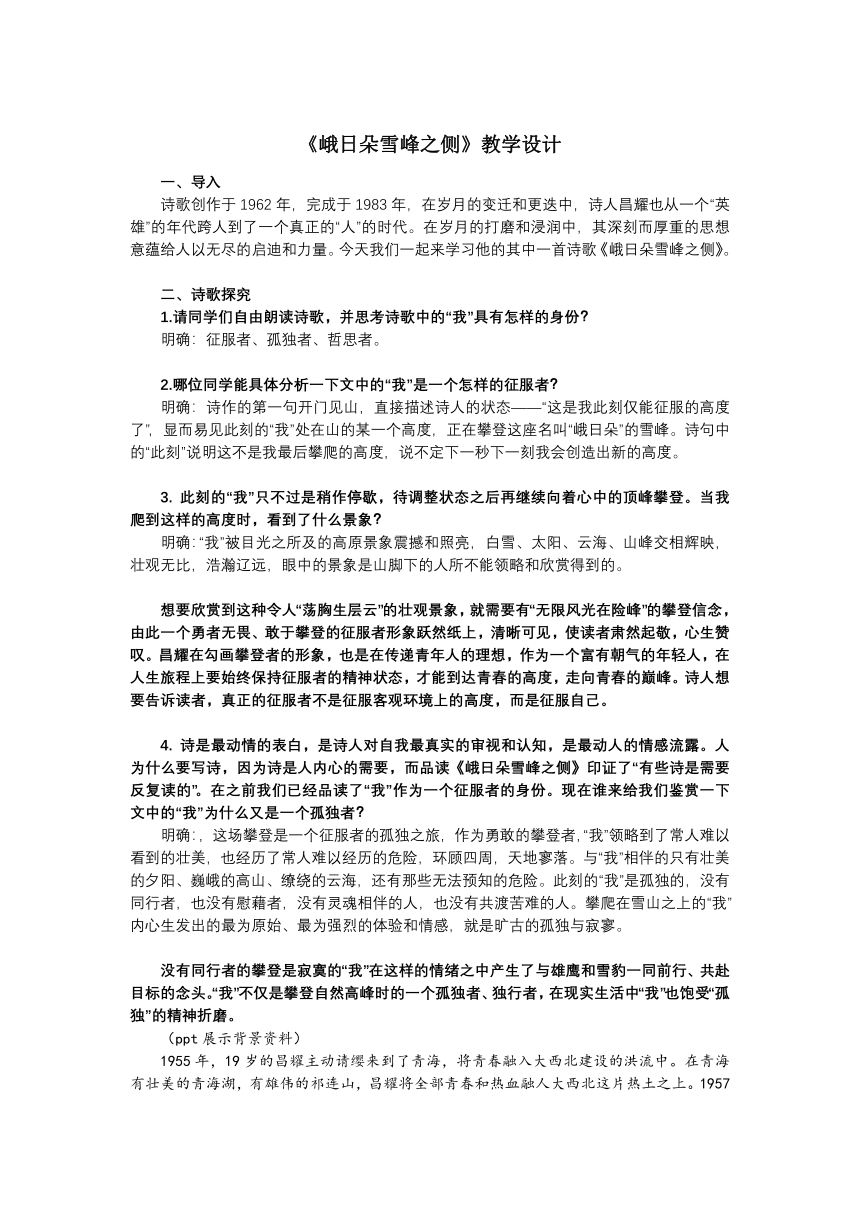
文档简介
《峨日朵雪峰之侧》教学设计
一、导入
诗歌创作于1962年,完成于1983年,在岁月的变迁和更迭中,诗人昌耀也从一个“英雄”的年代跨人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时代。在岁月的打磨和浸润中,其深刻而厚重的思想意蕴给人以无尽的启迪和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其中一首诗歌《峨日朵雪峰之侧》。
二、诗歌探究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诗歌,并思考诗歌中的“我”具有怎样的身份?
明确:征服者、孤独者、哲思者。
2.哪位同学能具体分析一下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征服者?
明确:诗作的第一句开门见山,直接描述诗人的状态——“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显而易见此刻的“我”处在山的某一个高度,正在攀登这座名叫“峨日朵”的雪峰。诗句中的“此刻”说明这不是我最后攀爬的高度,说不定下一秒下一刻我会创造出新的高度。
3.
此刻的“我”只不过是稍作停歇,待调整状态之后再继续向着心中的顶峰攀登。当我爬到这样的高度时,看到了什么景象?
明确:“我”被目光之所及的高原景象震撼和照亮,白雪、太阳、云海、山峰交相辉映,壮观无比,浩瀚辽远,眼中的景象是山脚下的人所不能领略和欣赏得到的。
想要欣赏到这种令人“荡胸生层云”的壮观景象,就需要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攀登信念,由此一个勇者无畏、敢于攀登的征服者形象跃然纸上,清晰可见,使读者肃然起敬,心生赞叹。昌耀在勾画攀登者的形象,也是在传递青年人的理想,作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在人生旅程上要始终保持征服者的精神状态,才能到达青春的高度,走向青春的巅峰。诗人想要告诉读者,真正的征服者不是征服客观环境上的高度,而是征服自己。
4.
诗是最动情的表白,是诗人对自我最真实的审视和认知,是最动人的情感流露。人为什么要写诗,因为诗是人内心的需要,而品读《峨日朵雪峰之侧》印证了“有些诗是需要反复读的”。在之前我们已经品读了“我”作为一个征服者的身份。现在谁来给我们鉴赏一下文中的“我”为什么又是一个孤独者?
明确:,这场攀登是一个征服者的孤独之旅,作为勇敢的攀登者,“我”领略到了常人难以看到的壮美,也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危险,环顾四周,天地寥落。与“我”相伴的只有壮美的夕阳、巍峨的高山、缭绕的云海,还有那些无法预知的危险。此刻的“我”是孤独的,没有同行者,也没有慰藉者,没有灵魂相伴的人,也没有共渡苦难的人。攀爬在雪山之上的“我”内心生发出的最为原始、最为强烈的体验和情感,就是旷古的孤独与寂寥。
没有同行者的攀登是寂寞的“我”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产生了与雄鹰和雪豹一同前行、共赴目标的念头。“我”不仅是攀登自然高峰时的一个孤独者、独行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饱受“孤独”的精神折磨。
(ppt展示背景资料)
1955年,19岁的昌耀主动请缨来到了青海,将青春融入大西北建设的洪流中。在青海有壮美的青海湖,有雄伟的祁连山,昌耀将全部青春和热血融人大西北这片热土之上。1957
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反右派斗争。这一运动后来被严重扩大化,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的确定为“右派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首诗写于1962
年8
月,作者因被打成右派,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唐晓渡曾说:“他以卓越的定力化苦难为财富,以爱的信念和对生死的彻悟变孤旅为慈航。”在攀登与征服的途中,昌耀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是诗人对于苦难的独特理解,是因为诗人的心中有坚守和底线,有情操和信仰,有信念和方向,有热爱和相信。诗人相信此刻的“我”会竭尽所能攀登到属于自己的高度,未来的“我”仍会保持初心,无畏,奉献,到达生命的巅峰。
5.通过以上同学们的分析,文中的“我”是一个征服者,也是一个孤独者。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老师认为“我”还是一个哲思者。昌耀运用对比的手法传递哲思,表达思考,揭示哲理,诗歌中有诸多反差式的对比手法,如:光明与黑暗、强大与弱小、高处与低处、热闹与沉寂等,然而真正坚守住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并不是强大健硕的雄鹰与雪豹,而是微不足道、微弱渺小的蜘蛛,光明与炙热的太阳不过是虚妄的幻想,堆砌的石砾不过是过度狂热的信念,盲目乐观和虚妄追求的代号而已,它们“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这些看似庞大而喧嚣的征服所带来的不过是“滑坡”和“远去”,而真正接纳阳光、石砂的却是沉寂与冷静。同时,与雪峰、落日、云海相比,人是渺小的,但人却享受到了作为攀登者所带来的征服的快感。在苍茫辽阔的雪域高原之上,征服群山的不是雄鹰,也不是雪豹,而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诗人在自然的面前,在征服的过程中,对于“征服者”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征服不单纯属于强大与喧嚣,自然的面前,一切都是平等而辩证的,在宏观宇宙的观照之下,渺小和伟大具有同等的意义,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来自于大自然的孕育,都享有平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诗人在俯仰天地的过程中征服的不仅是眼前的高峰,更是心中的高峰,诗人既有作为一个攀登者的勇气与坚毅,也有作为一个人的灵动与真实,更有作为一个智者的大爱与智慧,诗人在结尾之处告诉我们真正的“快慰”是与世间万物的心心相印,深情相拥。
三、结语
昌耀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完成了一场自我征服,经历了一场自我思辨,在坚毅而冷静、温情而细致的思考中张扬了生命的力量。正如诗中的“我”会继续向着生命的更高更美之处攀登一样,昌耀也将这个高度和美好带人了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世界中。
参考资料:对于昌耀写于1962年8月的具有鲜明整体象征特色的短诗《峨日朵雪峰之侧》,可以按照“由外而内”的次序得出两种相互衔接、彼此相关的阐释和解读。
昌耀的冷寂和沉闷来得尴尬而委屈。作为一个曾称“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并赴朝鲜作战,继而又“过继成北国的孩子”开发大西北的年轻人,凡是那个时代有的,
昌耀都不会拒绝地匀有一份,
无论是情绪、信仰也好,还是行动、作为也罢。然而,当他以一种不同于当时普遍盛行的狂热、迷乱、肤浅、喧嚣的精神理路、意念向度传达、投递他的实质相同的热情、关照和热爱时,他不由分说地遭到了拒绝和排斥;
随之而来的是他热情、关照和热爱的权绝,也就是他只被允许冷寂和沉闷。自然,这种冷寂和沉闷发酵而来的清醒和理智只能是被动和勉强的了。虽然是被动和勉强的,然而正是凭着这份清醒和理智,昌耀得以打量和思考时代与现实。于是,尽管是违心地、悲凉而无奈地成了那个时代的局外人,但因为能够客观冷静地静眼旁观,他还是完全有理由说: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
度了”。“这”恐怕就是指他这种游离于时代和现实之外的清醒和理智。然而,这“高度”实在
是一个危险的高度,因为这高度其实是昌耀自己托上去的高度,也是只有他自己看得见、感觉得到的高度,——
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高度,象昌耀这样受难的人更需要这样一个高度;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低处,是那个时代踩着的属于“右派”分子昌耀的低处。所以,昌耀只能“小心翼翼探出前额”。那么,在白定的高度,昌耀看到了什么呢——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呵,呈现于昌耀眼前的时代景观是:那曾一度被时代捧为神明、视若永恒真理的“太阳”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在人们的困惑迷惘中,终于失却了原来的高度,终于被屡遭愚弄和麻痹的时代心理决绝和抛弃了。主宰、牵引了这时代那么久的狂热,迷信,虚妄,喧嚣,在灾难和劫数的后果后,真的就要消失了吗,这时代就要归于正常和理性了吗?—
—
提前冷寂和沉闷因而得以清醒和理智的昌耀当然会惊异”了。是啊,那荒谬年代的所谓理想、所谓信念、所谓追求,真的不过是堆砌上去而根基根本不会稳固的“石砾”
,
当“太阳”
跃入山海,
时代从泛滥的狂热、廉价的乐观中摆脱出来,它们只能有“滑坡”的下场。虽然仍旧“一派嚣鸣”
和一片“喊杀声”
,但这是“自上而下”、是“滑坡”
、是“远去”
,是时代归于冷寂和沉闷以及随之而来的清醒和理智之前的“绝响”。
人生真正的艰辛和痛楚莫过于撕裂的感受。正是在时代和现实从虚浮、幻象的境界“滑”向冷寂、沉闷而失却高度的时候,诗人昌耀感受到了撕裂:
时代趋于冷寂、沉闷进而清醒、理智,不正是诗人昌耀认可和需要的吗?既然如此,在他的心灵深处必然会滋生出一种意念,那就是对自己原来所坚守的高度的意义的怀疑和否认,这样一来,
必然会产生促使自己也顺应着这时代作这种似乎合理而正当的下滑运动的心理驱动;而反过来说,时代趋于冷寂、沉闷进而清醒、理智,也恰恰是“上升”到了昌耀所在的高度,而这相对于昌耀来说,明显又是在失却高度,是一种“滑坡”。然而,诗人昌耀怎能没有自己的高度呢,特别是在饱尝与时代“亲和”之苦后,他更是害怕与时代平起平坐了。内外都有力量拉扯他下滑,这就是为什么此刻他在坚守、占据自己的高度时不得不“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其艰难和痛苦可想而知。
一、导入
诗歌创作于1962年,完成于1983年,在岁月的变迁和更迭中,诗人昌耀也从一个“英雄”的年代跨人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时代。在岁月的打磨和浸润中,其深刻而厚重的思想意蕴给人以无尽的启迪和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其中一首诗歌《峨日朵雪峰之侧》。
二、诗歌探究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诗歌,并思考诗歌中的“我”具有怎样的身份?
明确:征服者、孤独者、哲思者。
2.哪位同学能具体分析一下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征服者?
明确:诗作的第一句开门见山,直接描述诗人的状态——“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显而易见此刻的“我”处在山的某一个高度,正在攀登这座名叫“峨日朵”的雪峰。诗句中的“此刻”说明这不是我最后攀爬的高度,说不定下一秒下一刻我会创造出新的高度。
3.
此刻的“我”只不过是稍作停歇,待调整状态之后再继续向着心中的顶峰攀登。当我爬到这样的高度时,看到了什么景象?
明确:“我”被目光之所及的高原景象震撼和照亮,白雪、太阳、云海、山峰交相辉映,壮观无比,浩瀚辽远,眼中的景象是山脚下的人所不能领略和欣赏得到的。
想要欣赏到这种令人“荡胸生层云”的壮观景象,就需要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攀登信念,由此一个勇者无畏、敢于攀登的征服者形象跃然纸上,清晰可见,使读者肃然起敬,心生赞叹。昌耀在勾画攀登者的形象,也是在传递青年人的理想,作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在人生旅程上要始终保持征服者的精神状态,才能到达青春的高度,走向青春的巅峰。诗人想要告诉读者,真正的征服者不是征服客观环境上的高度,而是征服自己。
4.
诗是最动情的表白,是诗人对自我最真实的审视和认知,是最动人的情感流露。人为什么要写诗,因为诗是人内心的需要,而品读《峨日朵雪峰之侧》印证了“有些诗是需要反复读的”。在之前我们已经品读了“我”作为一个征服者的身份。现在谁来给我们鉴赏一下文中的“我”为什么又是一个孤独者?
明确:,这场攀登是一个征服者的孤独之旅,作为勇敢的攀登者,“我”领略到了常人难以看到的壮美,也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危险,环顾四周,天地寥落。与“我”相伴的只有壮美的夕阳、巍峨的高山、缭绕的云海,还有那些无法预知的危险。此刻的“我”是孤独的,没有同行者,也没有慰藉者,没有灵魂相伴的人,也没有共渡苦难的人。攀爬在雪山之上的“我”内心生发出的最为原始、最为强烈的体验和情感,就是旷古的孤独与寂寥。
没有同行者的攀登是寂寞的“我”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产生了与雄鹰和雪豹一同前行、共赴目标的念头。“我”不仅是攀登自然高峰时的一个孤独者、独行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饱受“孤独”的精神折磨。
(ppt展示背景资料)
1955年,19岁的昌耀主动请缨来到了青海,将青春融入大西北建设的洪流中。在青海有壮美的青海湖,有雄伟的祁连山,昌耀将全部青春和热血融人大西北这片热土之上。1957
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反右派斗争。这一运动后来被严重扩大化,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错误的确定为“右派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首诗写于1962
年8
月,作者因被打成右派,正在距峨堡乡不远的青海省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唐晓渡曾说:“他以卓越的定力化苦难为财富,以爱的信念和对生死的彻悟变孤旅为慈航。”在攀登与征服的途中,昌耀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是诗人对于苦难的独特理解,是因为诗人的心中有坚守和底线,有情操和信仰,有信念和方向,有热爱和相信。诗人相信此刻的“我”会竭尽所能攀登到属于自己的高度,未来的“我”仍会保持初心,无畏,奉献,到达生命的巅峰。
5.通过以上同学们的分析,文中的“我”是一个征服者,也是一个孤独者。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老师认为“我”还是一个哲思者。昌耀运用对比的手法传递哲思,表达思考,揭示哲理,诗歌中有诸多反差式的对比手法,如:光明与黑暗、强大与弱小、高处与低处、热闹与沉寂等,然而真正坚守住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并不是强大健硕的雄鹰与雪豹,而是微不足道、微弱渺小的蜘蛛,光明与炙热的太阳不过是虚妄的幻想,堆砌的石砾不过是过度狂热的信念,盲目乐观和虚妄追求的代号而已,它们“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这些看似庞大而喧嚣的征服所带来的不过是“滑坡”和“远去”,而真正接纳阳光、石砂的却是沉寂与冷静。同时,与雪峰、落日、云海相比,人是渺小的,但人却享受到了作为攀登者所带来的征服的快感。在苍茫辽阔的雪域高原之上,征服群山的不是雄鹰,也不是雪豹,而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诗人在自然的面前,在征服的过程中,对于“征服者”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征服不单纯属于强大与喧嚣,自然的面前,一切都是平等而辩证的,在宏观宇宙的观照之下,渺小和伟大具有同等的意义,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来自于大自然的孕育,都享有平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诗人在俯仰天地的过程中征服的不仅是眼前的高峰,更是心中的高峰,诗人既有作为一个攀登者的勇气与坚毅,也有作为一个人的灵动与真实,更有作为一个智者的大爱与智慧,诗人在结尾之处告诉我们真正的“快慰”是与世间万物的心心相印,深情相拥。
三、结语
昌耀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完成了一场自我征服,经历了一场自我思辨,在坚毅而冷静、温情而细致的思考中张扬了生命的力量。正如诗中的“我”会继续向着生命的更高更美之处攀登一样,昌耀也将这个高度和美好带人了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世界中。
参考资料:对于昌耀写于1962年8月的具有鲜明整体象征特色的短诗《峨日朵雪峰之侧》,可以按照“由外而内”的次序得出两种相互衔接、彼此相关的阐释和解读。
昌耀的冷寂和沉闷来得尴尬而委屈。作为一个曾称“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并赴朝鲜作战,继而又“过继成北国的孩子”开发大西北的年轻人,凡是那个时代有的,
昌耀都不会拒绝地匀有一份,
无论是情绪、信仰也好,还是行动、作为也罢。然而,当他以一种不同于当时普遍盛行的狂热、迷乱、肤浅、喧嚣的精神理路、意念向度传达、投递他的实质相同的热情、关照和热爱时,他不由分说地遭到了拒绝和排斥;
随之而来的是他热情、关照和热爱的权绝,也就是他只被允许冷寂和沉闷。自然,这种冷寂和沉闷发酵而来的清醒和理智只能是被动和勉强的了。虽然是被动和勉强的,然而正是凭着这份清醒和理智,昌耀得以打量和思考时代与现实。于是,尽管是违心地、悲凉而无奈地成了那个时代的局外人,但因为能够客观冷静地静眼旁观,他还是完全有理由说: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
度了”。“这”恐怕就是指他这种游离于时代和现实之外的清醒和理智。然而,这“高度”实在
是一个危险的高度,因为这高度其实是昌耀自己托上去的高度,也是只有他自己看得见、感觉得到的高度,——
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高度,象昌耀这样受难的人更需要这样一个高度;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低处,是那个时代踩着的属于“右派”分子昌耀的低处。所以,昌耀只能“小心翼翼探出前额”。那么,在白定的高度,昌耀看到了什么呢——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呵,呈现于昌耀眼前的时代景观是:那曾一度被时代捧为神明、视若永恒真理的“太阳”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在人们的困惑迷惘中,终于失却了原来的高度,终于被屡遭愚弄和麻痹的时代心理决绝和抛弃了。主宰、牵引了这时代那么久的狂热,迷信,虚妄,喧嚣,在灾难和劫数的后果后,真的就要消失了吗,这时代就要归于正常和理性了吗?—
—
提前冷寂和沉闷因而得以清醒和理智的昌耀当然会惊异”了。是啊,那荒谬年代的所谓理想、所谓信念、所谓追求,真的不过是堆砌上去而根基根本不会稳固的“石砾”
,
当“太阳”
跃入山海,
时代从泛滥的狂热、廉价的乐观中摆脱出来,它们只能有“滑坡”的下场。虽然仍旧“一派嚣鸣”
和一片“喊杀声”
,但这是“自上而下”、是“滑坡”
、是“远去”
,是时代归于冷寂和沉闷以及随之而来的清醒和理智之前的“绝响”。
人生真正的艰辛和痛楚莫过于撕裂的感受。正是在时代和现实从虚浮、幻象的境界“滑”向冷寂、沉闷而失却高度的时候,诗人昌耀感受到了撕裂:
时代趋于冷寂、沉闷进而清醒、理智,不正是诗人昌耀认可和需要的吗?既然如此,在他的心灵深处必然会滋生出一种意念,那就是对自己原来所坚守的高度的意义的怀疑和否认,这样一来,
必然会产生促使自己也顺应着这时代作这种似乎合理而正当的下滑运动的心理驱动;而反过来说,时代趋于冷寂、沉闷进而清醒、理智,也恰恰是“上升”到了昌耀所在的高度,而这相对于昌耀来说,明显又是在失却高度,是一种“滑坡”。然而,诗人昌耀怎能没有自己的高度呢,特别是在饱尝与时代“亲和”之苦后,他更是害怕与时代平起平坐了。内外都有力量拉扯他下滑,这就是为什么此刻他在坚守、占据自己的高度时不得不“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其艰难和痛苦可想而知。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 沁园春 长沙
- 2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红烛 *峨日朵雪峰之侧 *致云雀)
- 3 (百合花 *哦,香雪)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二单元
- 4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探界者”
- 5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 6 (芣苢 插秧歌)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三单元
- 7(短歌行 *归园田居(其一))
- 8(梦游天姥吟留别 登高 *琵琶行并序)
- 9(念奴娇·赤壁怀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声声慢(寻寻觅觅))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
- 学习活动
-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
- 《乡土中国》
- 第六单元
- 10(劝学 *师说)
- 11 反对党八股(节选)
- 12 拿来主义
- 13(*读书:目的和前提 *上图书馆)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七单元
- 14(故都的秋 *荷塘月色)
- 15 我与地坛(节选)
- 16(赤壁赋 *登泰山记)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八单元
- 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
- 古诗词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