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短歌行》教学设计2020—2021学年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
文档属性
| 名称 | 7.1《短歌行》教学设计2020—2021学年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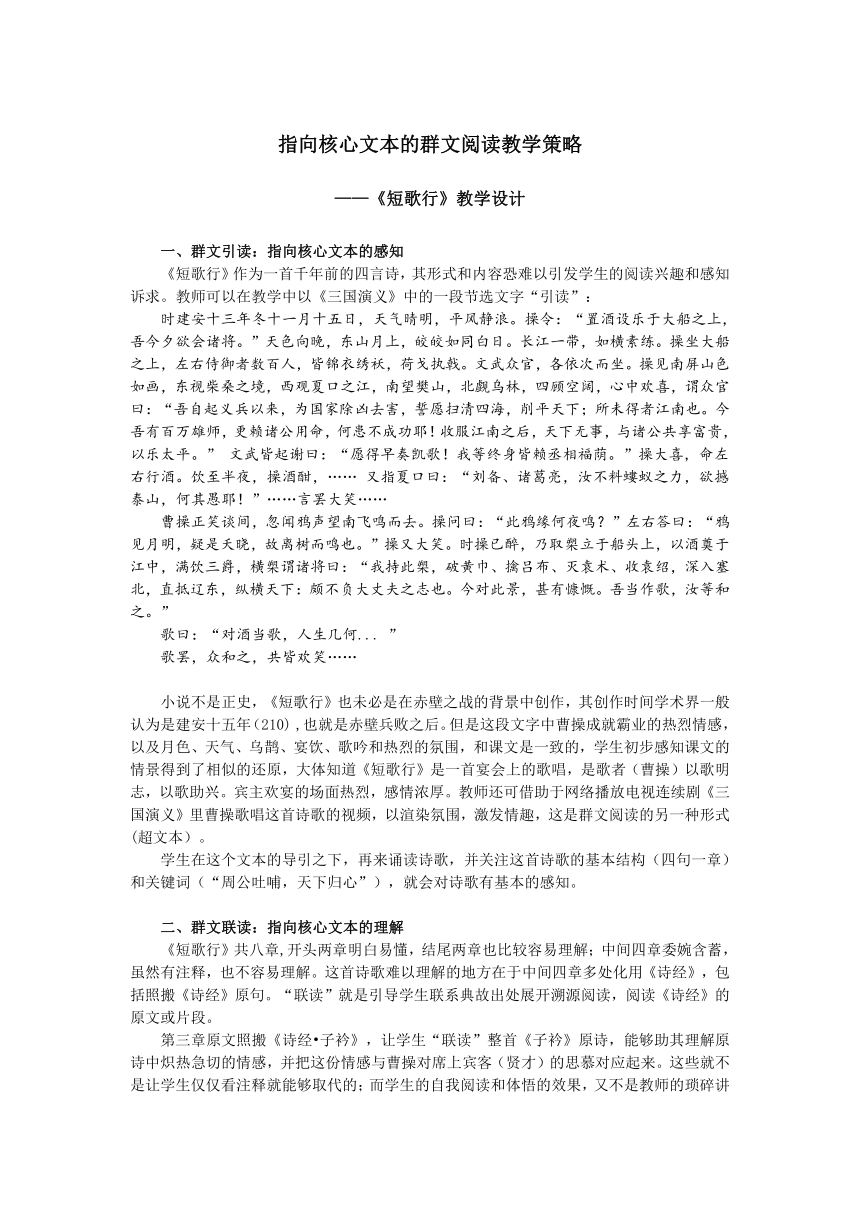 | |
| 格式 | zip | ||
| 文件大小 | 23.0KB | ||
| 资源类型 | 教案 | ||
| 版本资源 | 统编版 | ||
| 科目 | 语文 | ||
| 更新时间 | 2021-08-02 18:33:32 | ||
图片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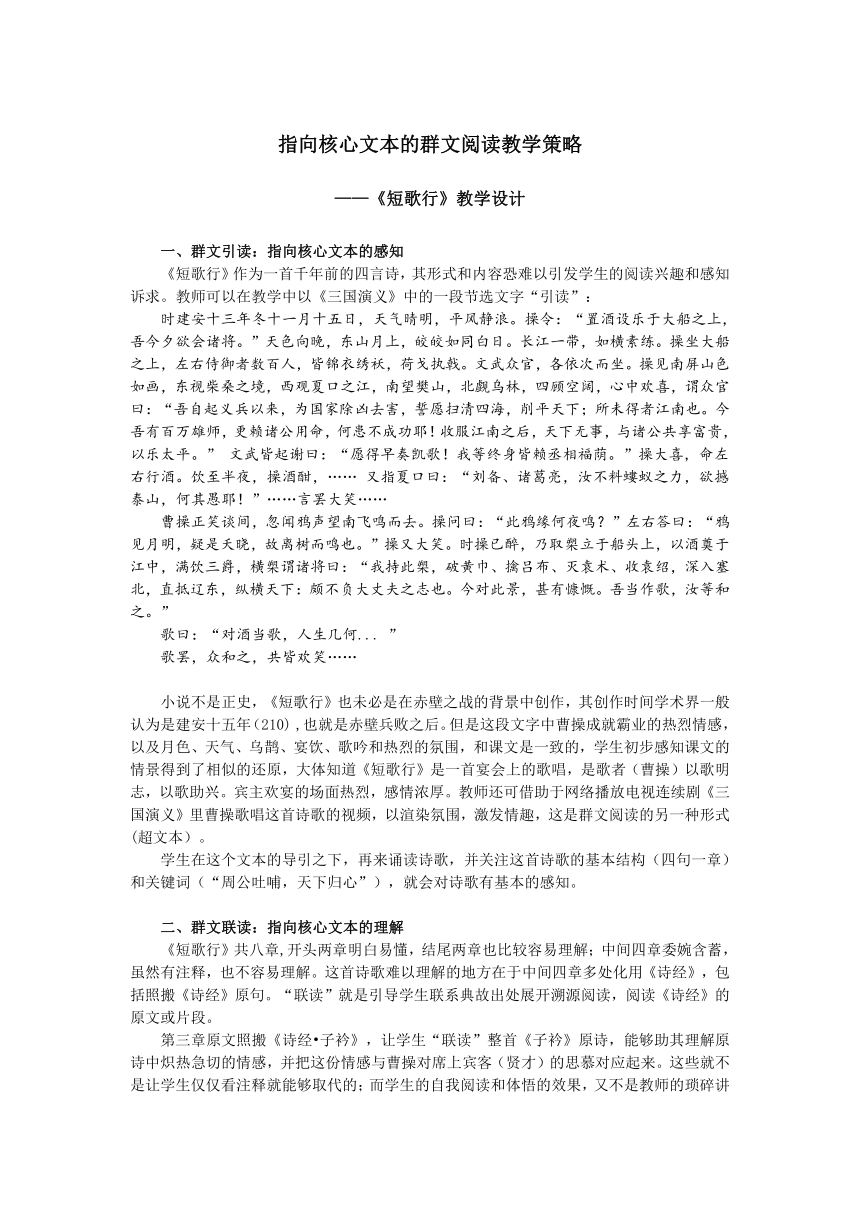

文档简介
指向核心文本的群文阅读教学策略
——《短歌行》教学设计
一、群文引读:指向核心文本的感知
《短歌行》作为一首千年前的四言诗,其形式和内容恐难以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诉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以《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节选文字“引读”:
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明,平风静浪。操令:“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吾今夕欲会诸将。”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数百人,皆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文武众官,各依次而坐。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心中欢喜,谓众官曰:“吾自起义兵以来,为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
文武皆起谢曰:“愿得早奏凯歌!我等终身皆赖丞相福荫。”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饮至半夜,操酒酣,……
又指夏口曰:“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螻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言罢大笑……
曹操正笑谈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疑是夭晓,故离树而鸣也。”操又大笑。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
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
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
小说不是正史,《短歌行》也未必是在赤壁之战的背景中创作,其创作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建安十五年(210)
,也就是赤壁兵败之后。但是这段文字中曹操成就霸业的热烈情感,以及月色、天气、乌鹊、宴饮、歌吟和热烈的氛围,和课文是一致的,学生初步感知课文的情景得到了相似的还原,大体知道《短歌行》是一首宴会上的歌唱,是歌者(曹操)以歌明志,以歌助兴。宾主欢宴的场面热烈,感情浓厚。教师还可借助于网络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里曹操歌唱这首诗歌的视频,以渲染氛围,激发情趣,这是群文阅读的另一种形式(超文本)。
学生在这个文本的导引之下,再来诵读诗歌,并关注这首诗歌的基本结构(四句一章)和关键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会对诗歌有基本的感知。
二、群文联读:指向核心文本的理解
《短歌行》共八章,开头两章明白易懂,结尾两章也比较容易理解;中间四章委婉含蓄,虽然有注释,也不容易理解。这首诗歌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中间四章多处化用《诗经》,包括照搬《诗经》原句。“联读”就是引导学生联系典故出处展开溯源阅读,阅读《诗经》的原文或片段。
第三章原文照搬《诗经?子衿》,让学生“联读”整首《子衿》原诗,能够助其理解原诗中炽热急切的情感,并把这份情感与曹操对席上宾客(贤才)的思慕对应起来。这些就不是让学生仅仅看注释就能够取代的;而学生的自我阅读和体悟的效果,又不是教师的琐碎讲解所能替代的。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第四章原文照搬《诗经?鹿鸣》,可让学生阅读《鹿鸣》原诗,从而理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比兴效果,理解曹操化用《诗经》不仅仅表达宾朋满座、共享宴饮的幸福,更是暗伏了与贤才共治天下的诺言(鹿鸣“呦呦”本就是唤来同伴分享之意,所以《诗经》用来起兴),也就是《求贤令》中“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的意思。曹操照搬《鹿鸣》的成句,但其韵味、格调与全诗妙合,令人赞叹。另外《鹿鸣》一诗是周天子“宴群臣嘉宾也”,曹操仅为汉相,虽实际执政,却并无天子之名。如此引用,也算是不拘一格,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核心文本中这些有意思的幽微意蕴,非读《诗经》原诗不能够领会。
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五、六两章是三、四两章的复调。一般认为“明明如月”
比喻贤才,以月不可掇比渴望贤才而不在。教材上的注释就是沿用了这个说法。但教材也给了另一种解释——“掇”一说同“辍”,月行不止比喻忧愁不绝。笔者以为“辍”更有意味,是化用《诗经?月出》。
《月出》写的是痴情男子不堪思念之苦,意境迷离,情思怅惘,感情炽烈。曹操暗化这首诗,以明月勾起愁思而抱怨之,尽写对贤才不堪思慕之苦(类似“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抱怨)。“忧从中来”化用“劳心悄兮”等,如盐在水中,不露痕迹,自然贴切。学生对整首原诗阅读获得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以及阅读过程中由类比迁移生成新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传统地讲解和灌输的效果。
月出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
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
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
劳心惨兮。
第六章“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笔者以为是暗化《诗经?
击鼓》。“契阔”教材释为久别重逢,但《汉典》的解释则为“生死相约”。《汉典》引清红颐煊《经义丛钞》释“契阔”:“言以生死相约为久远之辞。”举例就是曹操《短歌行》。把“契阔”解释为久别重逢当然通顺,但是这是忽视了曹操善于暗化典故的特点,忽视了诗句背后的原汁原味的原诗原句。学生通过对整首原诗阅读,理解了
“契阔谈宴”含有宾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之意,就更能够理解曹操把远道来访的客人视为生死知己的殷殷情怀,在营造的贤主嘉宾欢聚一堂的深情氛围中暗伏了自己将信守承诺,“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这一言外之意。
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三、群文比读:指向核心文本的鉴赏
经典文本都是字字珠玑,具有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这些魅力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是需要学习者在教师的引导下,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通过文意或手法与核心文本有所关联的文本的对比阅读中悠然心会的。
有人说,《短歌行》可以说是文学版的“求贤三令”。所谓“求贤三令”,指的是曹操接连颁布的三道广招人才的诏令。“求贤三令”与《短歌行》有鲜明的对应关系,把三篇“求才令”作为一组文章推荐给学生,和《短歌行》一起做群文对读,有助于学生鉴赏《短歌行》艺术上含蓄委婉、一唱三叹,深得“风人”情致的特点。
“求贤三令”
即《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三令”提出“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达了“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
的急切心情;强调不以德行限制人,用人不讲出身,不在乎是否有没有“污辱之名”。“求贤三令”呈现了曹操文章清峻通脱的特点,虽然用典不少,但是阅读难度不大。
《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举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求逸才令》或《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学生借助于注释能够比较顺畅地读懂。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回到《短歌行》的阅读,并设计一些有意思的任务或有思维含量的思考题,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乃至争论,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例如:
《短歌行》和“求贤三令”内容有哪些共通之处?
(求贤若渴、共治天下等)
哪些语言有明显对应的地方?(
如“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与“士无遗滞”“勿有所遗”等。)
《短歌行》和“求贤三令”内容有哪些不同之处?
(《短歌行》:时光短暂、建功立业。“求贤三令”:“明扬仄陋”,重才轻德。)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组群文阅读,可以引导学生提升对核心文本《短歌行》艺术特点的鉴赏。学生在阅读中会明显感受到诗歌文体的特点,例如重意象,重抒情,可以直接抒情也可以间接抒情。教师的任务设计可以进一步引发思考和鉴赏。例如:
《短歌行》为何不可以用来公告求贤?
《求贤令》为何不可以在习间吟唱?
(前者含蓄晦涩,读者不懂;后者直內散淡,席间不宜。)
《短歌行》与“求贤三令”都用了典故,作用有何不同?(《短歌行》:委婉抒情。“求贤三令”:论证观点。)
《短歌行》与“求贤三令”语言表达各有何特点?
(《短歌行》:含蓄、委婉、形象、化用,有弦外之音。“求贤三令”:直白、简洁、明确、要言不烦等。)
曹操化求偶的爱情诗为求贤的咏怀诗,既有“风人”传统(《诗经》里的比兴),又有骚人特点(屈原的爱情诗和政治诗)。正如林庚先生所说,打通了《诗经》和《楚辞》,表达含蓄而热烈。陈登原《国史旧闻》引杨钧云:“盖孟德诗文,皆有过人之处,其气概之雄伟,乃得之天生。犹之阮嗣宗,诗文皆御风而行,不许他人拟议也。”《短歌行》是曹操的代表作品,整首诗歌洋溢着深沉苍凉又积极进取的精神,浩歌一曲振林木,体现了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风骨,其文学史价值,需要学生真实的阅读实践来理解,可以通过对比阅读来辨析和体悟。
曹操写作《短歌行》之后半个多世纪,陆机也写了一首《短歌行》,诗云:
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生几何,逝如朝霜。
时无重至,华不再扬。苹以春晖,兰以秋芳。
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
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
我酒既旨,我肴既威。短歌可咏,长夜无荒。
陆机在曹操死后65年出生,身为东吴官宦之后,人晋为官,实多遭猜忌。西晋时代动荡,政治恐怖,内乱不息。陆机身处其中,内心忧惧。
这首《短歌行》流露了复杂低沉的情绪。同样宴饮高堂,同样对酒当歌,同样感慨人生,同样引用《诗经》,同样也是四言诗,看似翻版曹操,实则情感主旨格调大不一样,无非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哀婉之情难以掩饰。浩歌不再,悲歌响起,虽不乏婉转之抒情,究竟新意不足,格调不高。
在读完陆机的《短歌行》之后,再看曹操的《短歌行》,果然格调不同。开头从时间意义上写朝露人生的悲叹,基调悲凉;第七章则是从空间意义上写乌鹊人生的苦辛,从生命的无奈中生发出激昂慷慨之情。因应人生局限无奈的可以是纵情(陆曹),更可以是宏大的空间吐纳和紧迫的时间作息,是共赴霸业的集结号,是对有限生命的应答和超越(曹)。有人指出《短歌行》的“普世意义的生命意识”
更容易打动士人。更有人认为,《短歌行》直面渺小又追求伟大,于悲凉与慷慨的情感切换中“发现并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伟大和渺小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具有超时空的普遍价值,“散播出历久弥新、亘古不衰的巨大艺术魅力”。这些学者的评论,只有在曹陆二人《短歌行》的对比阅读中,才能为学生深切理解,并且激发批判意识,尝试评价作家作品,培养高阶思维和深度学习的能力。
——《短歌行》教学设计
一、群文引读:指向核心文本的感知
《短歌行》作为一首千年前的四言诗,其形式和内容恐难以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诉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以《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节选文字“引读”:
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明,平风静浪。操令:“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吾今夕欲会诸将。”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数百人,皆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文武众官,各依次而坐。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心中欢喜,谓众官曰:“吾自起义兵以来,为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
文武皆起谢曰:“愿得早奏凯歌!我等终身皆赖丞相福荫。”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饮至半夜,操酒酣,……
又指夏口曰:“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螻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言罢大笑……
曹操正笑谈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疑是夭晓,故离树而鸣也。”操又大笑。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
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
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
小说不是正史,《短歌行》也未必是在赤壁之战的背景中创作,其创作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建安十五年(210)
,也就是赤壁兵败之后。但是这段文字中曹操成就霸业的热烈情感,以及月色、天气、乌鹊、宴饮、歌吟和热烈的氛围,和课文是一致的,学生初步感知课文的情景得到了相似的还原,大体知道《短歌行》是一首宴会上的歌唱,是歌者(曹操)以歌明志,以歌助兴。宾主欢宴的场面热烈,感情浓厚。教师还可借助于网络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里曹操歌唱这首诗歌的视频,以渲染氛围,激发情趣,这是群文阅读的另一种形式(超文本)。
学生在这个文本的导引之下,再来诵读诗歌,并关注这首诗歌的基本结构(四句一章)和关键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会对诗歌有基本的感知。
二、群文联读:指向核心文本的理解
《短歌行》共八章,开头两章明白易懂,结尾两章也比较容易理解;中间四章委婉含蓄,虽然有注释,也不容易理解。这首诗歌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中间四章多处化用《诗经》,包括照搬《诗经》原句。“联读”就是引导学生联系典故出处展开溯源阅读,阅读《诗经》的原文或片段。
第三章原文照搬《诗经?子衿》,让学生“联读”整首《子衿》原诗,能够助其理解原诗中炽热急切的情感,并把这份情感与曹操对席上宾客(贤才)的思慕对应起来。这些就不是让学生仅仅看注释就能够取代的;而学生的自我阅读和体悟的效果,又不是教师的琐碎讲解所能替代的。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第四章原文照搬《诗经?鹿鸣》,可让学生阅读《鹿鸣》原诗,从而理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比兴效果,理解曹操化用《诗经》不仅仅表达宾朋满座、共享宴饮的幸福,更是暗伏了与贤才共治天下的诺言(鹿鸣“呦呦”本就是唤来同伴分享之意,所以《诗经》用来起兴),也就是《求贤令》中“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的意思。曹操照搬《鹿鸣》的成句,但其韵味、格调与全诗妙合,令人赞叹。另外《鹿鸣》一诗是周天子“宴群臣嘉宾也”,曹操仅为汉相,虽实际执政,却并无天子之名。如此引用,也算是不拘一格,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核心文本中这些有意思的幽微意蕴,非读《诗经》原诗不能够领会。
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五、六两章是三、四两章的复调。一般认为“明明如月”
比喻贤才,以月不可掇比渴望贤才而不在。教材上的注释就是沿用了这个说法。但教材也给了另一种解释——“掇”一说同“辍”,月行不止比喻忧愁不绝。笔者以为“辍”更有意味,是化用《诗经?月出》。
《月出》写的是痴情男子不堪思念之苦,意境迷离,情思怅惘,感情炽烈。曹操暗化这首诗,以明月勾起愁思而抱怨之,尽写对贤才不堪思慕之苦(类似“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抱怨)。“忧从中来”化用“劳心悄兮”等,如盐在水中,不露痕迹,自然贴切。学生对整首原诗阅读获得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以及阅读过程中由类比迁移生成新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传统地讲解和灌输的效果。
月出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
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
舒忧受兮。
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
劳心惨兮。
第六章“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笔者以为是暗化《诗经?
击鼓》。“契阔”教材释为久别重逢,但《汉典》的解释则为“生死相约”。《汉典》引清红颐煊《经义丛钞》释“契阔”:“言以生死相约为久远之辞。”举例就是曹操《短歌行》。把“契阔”解释为久别重逢当然通顺,但是这是忽视了曹操善于暗化典故的特点,忽视了诗句背后的原汁原味的原诗原句。学生通过对整首原诗阅读,理解了
“契阔谈宴”含有宾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之意,就更能够理解曹操把远道来访的客人视为生死知己的殷殷情怀,在营造的贤主嘉宾欢聚一堂的深情氛围中暗伏了自己将信守承诺,“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这一言外之意。
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三、群文比读:指向核心文本的鉴赏
经典文本都是字字珠玑,具有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这些魅力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是需要学习者在教师的引导下,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通过文意或手法与核心文本有所关联的文本的对比阅读中悠然心会的。
有人说,《短歌行》可以说是文学版的“求贤三令”。所谓“求贤三令”,指的是曹操接连颁布的三道广招人才的诏令。“求贤三令”与《短歌行》有鲜明的对应关系,把三篇“求才令”作为一组文章推荐给学生,和《短歌行》一起做群文对读,有助于学生鉴赏《短歌行》艺术上含蓄委婉、一唱三叹,深得“风人”情致的特点。
“求贤三令”
即《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三令”提出“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达了“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
的急切心情;强调不以德行限制人,用人不讲出身,不在乎是否有没有“污辱之名”。“求贤三令”呈现了曹操文章清峻通脱的特点,虽然用典不少,但是阅读难度不大。
《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举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求逸才令》或《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学生借助于注释能够比较顺畅地读懂。在学生阅读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回到《短歌行》的阅读,并设计一些有意思的任务或有思维含量的思考题,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乃至争论,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例如:
《短歌行》和“求贤三令”内容有哪些共通之处?
(求贤若渴、共治天下等)
哪些语言有明显对应的地方?(
如“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与“士无遗滞”“勿有所遗”等。)
《短歌行》和“求贤三令”内容有哪些不同之处?
(《短歌行》:时光短暂、建功立业。“求贤三令”:“明扬仄陋”,重才轻德。)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组群文阅读,可以引导学生提升对核心文本《短歌行》艺术特点的鉴赏。学生在阅读中会明显感受到诗歌文体的特点,例如重意象,重抒情,可以直接抒情也可以间接抒情。教师的任务设计可以进一步引发思考和鉴赏。例如:
《短歌行》为何不可以用来公告求贤?
《求贤令》为何不可以在习间吟唱?
(前者含蓄晦涩,读者不懂;后者直內散淡,席间不宜。)
《短歌行》与“求贤三令”都用了典故,作用有何不同?(《短歌行》:委婉抒情。“求贤三令”:论证观点。)
《短歌行》与“求贤三令”语言表达各有何特点?
(《短歌行》:含蓄、委婉、形象、化用,有弦外之音。“求贤三令”:直白、简洁、明确、要言不烦等。)
曹操化求偶的爱情诗为求贤的咏怀诗,既有“风人”传统(《诗经》里的比兴),又有骚人特点(屈原的爱情诗和政治诗)。正如林庚先生所说,打通了《诗经》和《楚辞》,表达含蓄而热烈。陈登原《国史旧闻》引杨钧云:“盖孟德诗文,皆有过人之处,其气概之雄伟,乃得之天生。犹之阮嗣宗,诗文皆御风而行,不许他人拟议也。”《短歌行》是曹操的代表作品,整首诗歌洋溢着深沉苍凉又积极进取的精神,浩歌一曲振林木,体现了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风骨,其文学史价值,需要学生真实的阅读实践来理解,可以通过对比阅读来辨析和体悟。
曹操写作《短歌行》之后半个多世纪,陆机也写了一首《短歌行》,诗云:
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生几何,逝如朝霜。
时无重至,华不再扬。苹以春晖,兰以秋芳。
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
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
我酒既旨,我肴既威。短歌可咏,长夜无荒。
陆机在曹操死后65年出生,身为东吴官宦之后,人晋为官,实多遭猜忌。西晋时代动荡,政治恐怖,内乱不息。陆机身处其中,内心忧惧。
这首《短歌行》流露了复杂低沉的情绪。同样宴饮高堂,同样对酒当歌,同样感慨人生,同样引用《诗经》,同样也是四言诗,看似翻版曹操,实则情感主旨格调大不一样,无非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哀婉之情难以掩饰。浩歌不再,悲歌响起,虽不乏婉转之抒情,究竟新意不足,格调不高。
在读完陆机的《短歌行》之后,再看曹操的《短歌行》,果然格调不同。开头从时间意义上写朝露人生的悲叹,基调悲凉;第七章则是从空间意义上写乌鹊人生的苦辛,从生命的无奈中生发出激昂慷慨之情。因应人生局限无奈的可以是纵情(陆曹),更可以是宏大的空间吐纳和紧迫的时间作息,是共赴霸业的集结号,是对有限生命的应答和超越(曹)。有人指出《短歌行》的“普世意义的生命意识”
更容易打动士人。更有人认为,《短歌行》直面渺小又追求伟大,于悲凉与慷慨的情感切换中“发现并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伟大和渺小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具有超时空的普遍价值,“散播出历久弥新、亘古不衰的巨大艺术魅力”。这些学者的评论,只有在曹陆二人《短歌行》的对比阅读中,才能为学生深切理解,并且激发批判意识,尝试评价作家作品,培养高阶思维和深度学习的能力。
同课章节目录
- 第一单元
- 1 沁园春 长沙
- 2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红烛 *峨日朵雪峰之侧 *致云雀)
- 3 (百合花 *哦,香雪)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二单元
- 4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探界者”
- 5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 6 (芣苢 插秧歌)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三单元
- 7(短歌行 *归园田居(其一))
- 8(梦游天姥吟留别 登高 *琵琶行并序)
- 9(念奴娇·赤壁怀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声声慢(寻寻觅觅))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
- 学习活动
-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
- 《乡土中国》
- 第六单元
- 10(劝学 *师说)
- 11 反对党八股(节选)
- 12 拿来主义
- 13(*读书:目的和前提 *上图书馆)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七单元
- 14(故都的秋 *荷塘月色)
- 15 我与地坛(节选)
- 16(赤壁赋 *登泰山记)
- 单元学习任务
- 第八单元
- 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
- 古诗词诵读
